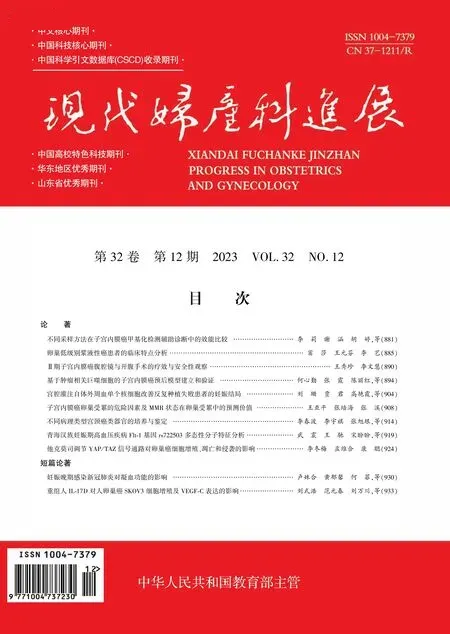子宫颈延长的诊治进展
2024-01-28谢静燕
冯 静,谢静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妇科,南京 210000)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female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FPFD)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盆底支持组织解剖结构及功能改变所导致的一系列疾病,主要包括盆底脏器脱垂(pelvic organ prolapse,POP)、压力性尿失禁(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SUI)、性功能障碍和产后功能综合征等。其中,POP是FPFD的主要病症,包括膀胱、直肠膨出及子宫、阴道脱垂等,是中老年女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现代解剖学将女性的盆底从垂直方向分为前、中、后三个腔室,从水平方向分为Ⅰ、Ⅱ、Ⅲ三个平面。当骨盆底组织支持作用减弱时,易发生相应部位器官松弛、脱垂或功能缺陷。其中中腔室的POP主要表现为子宫脱垂(uterine prolapse,UP)、阴道穹窿脱垂、小肠疝等。近年研究发现,宫颈延长(cervical elongation,CE)常与子宫脱垂关系密切[1],部分子宫脱垂患者常合并CE。既往宫颈长度是产科妊娠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指标,但在妇科疾病中少有关注。随着人口日趋老龄化及社会医疗意识的增强,POP的发病率逐年上升,CE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诊疗水平,本文现将近年来CE的诊治进展综述如下。
1 发病机制
宫颈,即为子宫颈部,上端通过宫颈内口(解剖学内口)与子宫体相连,下端通过宫颈外口深入阴道,可由阴道顶端穹窿分为阴道部和阴道上部。宫颈长度为宫颈内口到宫颈外口之间的距离,宫颈长度及与宫体的比例随年龄和内分泌状态等而变化,成年女性长约2.5~3cm。目前CE的定义仍不明确。在国际疾病分类[2]中记载有宫颈肥厚性延长(hypertrophic elongation of cervix uteri),是指宫颈脱垂的一种情况,多由子宫脱垂引起,其特征是宫颈阴道部或阴道上部的肥大、增生、伸长或拉伤,可能导致性交困难或不孕。
CE发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明确。Ibeanu等[3]对延长的子宫颈和正常的子宫颈分别进行组织病理学分析,发现延长的宫颈组织中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水平较高,推测宫颈肥厚性延长的原因之一是雌激素和孕激素降低导致宫颈局部雌激素受体代偿性增加,导致局部宫颈组织的反应性增厚[4]。国内文献报道有2例先天性CE,认为CE可能是生殖裂孔和肛提肌功能不全所致[5]。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表明[4],宫颈肥厚性延长与绝经前POP显著相关,且与前腔室或后腔室POP相比,中腔室POP与宫颈肥厚性延长显著相关,提示可能是不断加重的脱垂通过向下牵拉导致CE。既往研究表明,虽然宫颈肥厚性延长的病因尚不明确,但在育龄妇女(40岁以下)中,可能与妊娠时间长、难产相关。目前的理论倾向于,盆底组织支持结构薄弱、子宫骶韧带缺乏足够的牵引力,可能是导致CE的主要因素。长期腹压增大引起骶主韧带复合体支持结构薄弱,同时对宫颈及其周围组织造成损伤,导致局部、慢性、刺激性结缔组织增生,宫颈向下移位,表现为宫颈肥厚性延长[6]。一项单中心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显示[7],有症状的POP女性宫颈长度占子宫总长度的比例明显高于无POP的女性。Mothes等[8]发现,因POP行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中,97.6%合并CE。Berger等[9]采用MRI测量发现,女性POP患者的宫颈和宫体均延长,且宫颈延长的程度更大,数据显示39.2%的POP患者合并有CE,这表明POP是CE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此外,胎次、产次、年龄、绝经状态等也与CE发病相关。Hsiao等[10]研究发现,46.1%的POP患者合并有CE,且晚期子宫脱垂和低产次与CE显著相关。Patrick等[11]则指出,CE仅与年龄具有相关性,而与BMI、种族、胎次、盆腔手术史、绝经状态等因素无关。Liu等[1]研究表明,年龄在65岁以上、阴道总长度超过9.5cm、子宫重量小于51g、POPDI-6(Pelvic Organ Prolapse Distress Inventory 6)评分超过12分是POP患者发生CE的四个独立危险因素。
2 症状及体征
CE患者一般表现为POP症状,外阴常可扪及肿物脱出于阴道口,长期站立或劳累后加重,平卧或休息后减轻。此外,部分患者还可有阴道分泌物异常、腰骶部酸痛、腹胀等非特异症状。少部分患者可有不孕、性生活困难、性生活不适等。部分严重患者因脱出的宫颈长期接触衣物磨损,可有出血、溃疡、感染等表现。
查体时,患者需排空膀胱,取膀胱截石位,检查医师使用一次性窥阴器暴露阴道和宫颈,观察静息状态和Valsalva状态下的宫颈位置,部分患者宫颈外口达到或超出处女膜缘,行双合诊时可扪及宫颈阴道段延长。
3 诊断及辅助检查
目前诊断CE尚无明确的标准[12]。1996年Bump等[13]首次提出CE的概念,将其描述为POP-Q检查时C点下降而D点保留在较高的位置。Ibeanu等[3]在2010年一项研究中将CE的标准定为POP-Q评分中C点与D点之间的距离>8cm。2012年,Berger等[9]指出仅C点的位置是宫颈长度和CE的最强预测因素,并将CE的标准定为宫颈长度>3.38cm和(或)宫颈与宫体长度之比>0.79。2014年Dancz等[14]进行POP-Q检查、经阴道超声测量和直接解剖测量宫颈长度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宫颈解剖长度≥5cm时,应诊断CE。2019年Park等[15]在研究曼氏手术治疗子宫脱垂的疗效时,将宫颈延长定义为POP-Q评分中C点>+1,D点<-4,估计宫颈长度>5cm。也有学者[16]认为,POP-Q评分中C点≥0,D点≤-4,估计宫颈长度≥5cm,即可定义为CE。此外,有研究发现,宫体与宫颈长度之比(corpus/cervix ratio,CCR)可反应宫颈延长状态[1],因此定义CE为CCR≤1.5。
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常用的CE定义为C-D≥4cm,但其可靠性仍存争议。Finamore等[17]发现,C点>0时,C-D测量值与术后宫颈长度测量值存在显著差异。Dancz等[14]研究也证实,≥Ⅱ期POP患者的C-D测量值明显大于宫颈实际解剖测量值。Williams等[18]报道,随着POP-Q分期的加重,C-D和术后宫颈长度测量之间的一致性降低。考虑原因可能是,晚期POP患者中骶韧带薄弱,后穹窿处可能与骶韧带附着点并不对应,D点可能不是真正的宫颈近端,因此使用C-D值无法测量实际宫颈长度[19]。
此外,根据盆底Ⅰ平面支持结构稳定性不同,可将CE分为Ⅰ平面稳定的CE和Ⅰ平面不稳定的CE[20]。Ⅰ平面稳定的CE即为单纯的子宫颈延长,Ⅰ平面盆底支撑结构相对完整,无子宫下降,POP-Q检查时D点相对较高。Ⅰ平面不稳定的CE即宫颈延长伴子宫脱垂,骶主韧带复合体损伤、组织薄弱,POP-Q检查时D点下降。临床中除根据临床症状和查体体征外,还可行下列检查以辅助诊断。
3.1 超声 经阴道探头对患者进行超声评估,在矢状位上测量子宫体和宫颈长度,具有操作简单、安全无创、无放射性、可重复性高等特点[21]。记录子宫底与宫颈内口之间的长度即为超声下宫体长度,记录宫颈内口与宫颈外口之间的长度即为超声下宫颈长度。Danez等[14]对因POP行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进行宫颈长度测量评估,发现经阴道超声测量的宫颈平均长度明显短于C-D测量值和术后宫颈长度,因此可靠性相对较低。此外,重度POP患者在Valsalva状态下膨出物常超出处女膜缘,阻挡阴道口及超声探头,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经会阴超声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宫颈位置变化的影响。以耻骨联合后下缘水平作为参考线,测量静息和Valsalva状态下宫颈内口相对耻骨联合参考线的移动度,即可判断Ⅰ平面的下降程度,鉴别UP和单纯CE[22]。此外,还可测量静息和Valsalva状态下的耻骨联合到子宫底部的距离。国外研究显示,若移动度≥15mm,可有助于鉴别UP与无UP的CE(敏感性75%,特异性95%,阳性预测值86%,阴性预测值89%)[23]。经直肠双平面超声近几年兴起,由于探头位于直肠内,因此对阴道内宫颈的位置影响较小,对宫颈形态的动态观察具有独特的优势。记录静息和Valsalva状态下宫颈内口外口之间的距离即为超声下宫颈长度。以会阴体上缘水平作为参考线,测量静息和Valsalva状态下宫颈内口相对会阴体上缘参考线的移动度,即可判断Ⅰ平面的下降程度,鉴别UP和单纯CE。
3.2 MRI MRI对软组织的分辨率高,可直接观察盆腔器官、肌肉组织等解剖细节,相对无创且无辐射。而盆底动态MRI可在静息和Valsalva状态下对盆底组织进行解剖结构和功能评估,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检查方式。测量宫颈内口与宫颈外口之间的长度即为MRI下宫颈长度。以耻骨尾骨线(pubococcygeal line,PCL)为参考线,测量静息相和力排相宫颈最低点至PCL线的垂直距离,即可判断I平面的稳定性,敏感性较高。Berger等[9]研究发现,CE患者的生殖裂孔面积比无CE的POP患者更大,且阴道形态的改变可能与盆底支持系统的缺陷有关。如宫骶韧带损伤导致的Ⅰ水平缺陷可导致阴道顶端两侧下移,使阴道在横断面上失去正常的“H”形结构而呈“V”形[24]。
3.3 Foley导管 使用10号Foley球囊导管直接测量宫颈长度。研究显示[25],此法测量宫颈长度较准确,但患者常有疼痛不适感,因此多用于麻醉状态下的术前评估。在常规消毒后,通过宫颈管将10号Foley球囊导管插入子宫腔,向球囊内注入适量生理盐水,轻轻牵拉Foley导管将球囊在宫颈内口上方固定。在宫颈外口处对导管进行标记,抽出球囊内盐水后取出导管,测量标记点(宫颈外口)与球囊近端点(宫颈内口)之间的距离。
3.4 Hegar扩张器 此法原理与Foley导管相同,为侵入性检查,因此多用于麻醉状态下的术前评估。将合适大小的Hegar宫颈扩张棒置入子宫颈,达到的第一个阻力点即认为是宫颈内口。测量宫颈内、外口之间的距离即为宫颈长度[26]。
4 干预及治疗
4.1 随访观察 CE患者如无自觉症状可随访观察,定期在门诊完成POP-Q评分及相关检查、量表等,监测病情进展状况,无需特殊治疗。
4.2 保守治疗 可用于轻症或重症患者的辅助治疗。(1)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长时间站立或持重物,避免长期咳嗽、用力排便等腹压增加的状态。(2)盆底功能训练(pelvic floor muscles training,PFMT)。PFMT可恢复盆底肌张力,改善盆底功能。必要时可联合应用生物反馈治疗、功能性电刺激治疗等。
4.3 手术治疗 是重症CE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手术方式的选择应个体化,根据患者的年龄、生育要求、合并症状、全身健康状况、结合患者的个人意愿,选择合适的术式。(1)曼氏(Manchester)手术。此术式为目前治疗单纯CE的主流术式,主要包括宫颈部分切除术、阴道前后壁修补及主韧带缩短术[27]。此术式创伤较小,手术时间短,并发症少,术后恢复较快,主要适用于年龄较轻、有生育要求的患者[28]。研究显示,曼氏手术治疗单纯CE的复发率极低[15],因此临床上受到广泛应用。常见的并发症有宫颈机能不全、宫颈狭窄等[26]。(2)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vaginal hysterectomy,VH)。适用于年龄较大、无生育要求的患者,尤其是合并有Ⅰ平面下降的UP患者。研究显示[29],CE会增加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的手术时间,给术者造成挑战。常见的并发症有邻近结构损伤、术后感染等。(3)阴道封闭术。仅适用于年老体弱、身体状况不能耐受大手术的患者,术后失去性交功能,因此临床应用较少。(4)其他。当CE合并有严重的子宫脱垂或其他腔室脱垂时,可视不同情况行相应腔室的重建手术,必要时可采取联合手术治疗[30]。
5 小结
CE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研究认为CE主要与不断加重的POP有关。POP患者盆底组织支持结构薄弱,子宫骶韧带缺乏足够的牵引力,向下牵拉导致CE。目前诊断CE尚无明确的标准。常用的CE定义为宫颈长度≥5cm。部分CE患者无明显自觉症状,仅在常规体检中偶然发现。典型的症状为外阴肿物脱出,可在长期站立或劳累后加重。查体时可扪及宫颈阴道段延长,POP-Q检查C-D测量值≥4cm。盆底超声和MRI是临床常用的检查方法,Foley导管和Hegar扩张器应用不多但准确率较高,均可用于CE的辅助诊断,与UP相鉴别。CE治疗目的主要是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如无自觉症状可行随访观察,无需特殊治疗。如有外阴膨出肿物、性生活不适等症状的患者,则建议积极治疗,以免病情进一步加重。保守治疗可用于轻症或重症患者,包括调整生活习惯、盆底功能训练、生物反馈治疗、功能性电刺激治疗等。重症CE患者需采用手术治疗,其中曼氏手术效果显著,复发率低,较为常用。对于合并有其他腔室脱垂的CE患者,可视情况行盆底重建手术,需注意术前明确脱垂的类型及程度,制订全面、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是防止术后复发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