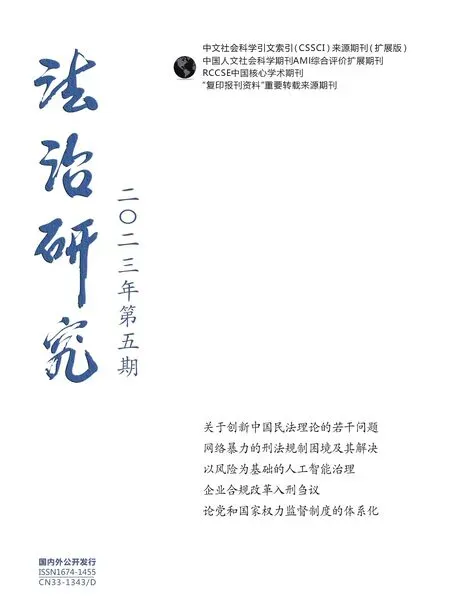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困境及其解决
2024-01-18刘宪权周子简
刘宪权 周子简
一、引言
在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社会飞跃式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各方面的风险。其中,互联网等线上技术的普及衍生出了网络暴力等一系列网络失范行为。针对网络暴力,我国在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上已有诸多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等国家机关也出台过诸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令人疑惑的是,尽管受到如此密集的法律规范规制,但网络暴力现象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武汉校园碾压案”孩子妈妈不堪网暴跳楼离世;女硕士因染粉色头发遭网暴自杀身亡;17 岁寻亲少年刘某不堪网暴留千言遗书自杀离世;泳池冲突被指殴打未成年人,德阳女医生不堪网暴轻生身亡……近年来,网络暴力造成被施暴者自杀或受到严重心理伤害的案例不绝于耳。由于社会中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国家与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刑法安全价值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①参见彭文华、傅亮:《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中国刑法学新理念》,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 年第1 期。
喉舌无骨,却杀人如刀。互联网的虚拟性无限放大了人性之“恶”,囿于网络暴力参与人员众多、主要加害人难以明确、证据难以固定、责任难以分配等特点,那些躲在背后肆意攻击他人的施暴者往往轻松逃避法律制裁。由此,网络暴力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以及现有法律规制不力等问题再次引起立法者和全社会的关注,可见有针对性地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势在必行。2022 年3 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2 年3 月8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49601.html,2023 年7 月1 日访问。2023 年4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依法严惩‘网络暴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相关犯罪,深挖背后的产业链利益链,严厉打击‘网络水军’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行为涉嫌的相关犯罪”。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304/t20230418_611553.shtml#2,2023 年7 月1 日访问。为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正常网络秩序,“两高一部”于 2023 年6 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分别从网络暴力的意义内涵、法律适用、程序适用、综合治理等方面公开征求意见。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02962.html,2023 年7 月1 日访问。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一再强调要依法追究网络暴力实施者的“刑事责任”,这恰恰反映出目前刑法针对网络暴力的规制力度不足、介入条件不明、适用罪名不清等问题。与此同时,民法和行政法已经不足以全面评价并有效规制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因此应当适时启动刑事制裁手段,依法追究严重网络暴力实施者的刑事责任。
目前,刑法主要通过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较为分散且传统的罪名规制网络暴力,这也导致相关罪名无法完全契合网络暴力犯罪中的新型行为类型,从而造成绝大部分施暴者无法受到刑法制裁窘况的出现。笔者认为,民法和行政法可以有效处理轻度的网络暴力案件,但对于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必须通过刑法才能进行有效规制。刑法规制网络暴力的前提是明确网络暴力的刑法内涵,并且抽象提炼出网络暴力的典型行为类型,在充分分析现行刑法规制网络暴力所存在的困境之后,进一步厘清相关刑法适用困境的解决路径,如此方能构建一个打击范围明确、入罪标准科学、责任分配合理的网络暴力刑法制裁体系。
二、网络暴力的概念与刑法内涵
网络暴力是一个未经官方定义就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没有“网络暴力”一词,所以网络暴力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刑法概念,而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统一的复合型名词。作为一种成因复杂的社会现象,网络暴力所指代的内容在不同场合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都有对网络暴力的不同定义和阐释。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网络暴力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定网络暴力在刑法中的意义内涵。
(一)网络暴力概念的内涵
对一个概念的准确定义是从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切描述展开的,具体而言,内涵是对一个概念本质属性的提炼,而外延则是对一个概念所包含对象范围和广度的划定。根据通说观点,“网络暴力”一词在我国的使用肇始于2006 年“高跟鞋虐猫女”⑤2006 年2 月,有网友在网站上传了一段女子用高跟鞋鞋跟疯狂踩踏一只小猫的视频,手段极其残忍,顿时引发众多网友的愤怒,随即开始对该女子进行人肉搜索,虐猫地点和虐猫女子的身份信息很快被曝出,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也及时介入,该名女子最终被工作单位解聘。和“铜须门”⑥2006 年4 月,一名网友发帖称其妻子与ID 名为“铜须”的某游戏工会会长发生婚外情等出轨行为,引起众多游戏玩家和网友对“铜须”进行人肉搜索,“铜须”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所在学校等个人信息很快被网友扒出,众多网友对“铜须”进行无下限的恐吓和骚扰,甚至连“铜须”所在学校的校长也难逃其害。“铜须门”事件影响巨大,以至于《纽约时报》《南德意志报》等国外报刊也争相报道,质疑中国网民的做法是对公民个人权利(隐私权、情感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等)的严重侵犯,“网络暴民”一词也在“铜须门”事件中诞生。等典型网络事件。从2006 年至今,网络暴力现象已经在我国出现了十余年之久,“网络暴力”一词也频频出现在各种新闻报道、媒体评论和学术研究之中。其中不乏“网络暴力”概念被滥用的情况出现,进而导致各个领域对网络暴力的界定很不统一。关于网络暴力的内涵,也即网络暴力的本质属性,笔者共梳理出以下四种目前较为成熟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暴力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异化。持论者认为,网络暴力是部分网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忽视了自身所承担的不能侵害他人权利的责任,进而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非理性、大规模、持续性的舆论攻击,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网络表达自由的异化。⑦参见张瑞孺:《“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特质的法理分析》,载《求索》2010 年第12 期。同时,网络暴力的背后蕴含着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理论的博弈。⑧参见柳思思:《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研究——欧盟治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年版。的确,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公民的言论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受到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权利的制约。一旦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权利造成侵害,那么此时公民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也将发生异化,不仅超出了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而且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网络暴力是基于道德约束的暴力行为。持论者认为,网络暴力是网民在网络空间针对特定对象发起的道德审判,重点表现为通过舆论的“集结”优势达到强制干涉他人的目的,其基本工具是洛克所谓的“名誉之法”(或称意见之法),实质上是一种道德约束。⑨参见姜方炳:《“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载《浙江学刊》2011 年第6 期。在大多数网络暴力事件中,网络暴力的实施者几乎都以“正义的化身”自居,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暴力中的少数受害者确实可能在事先具有某些道德失范甚至法律失范行为,这也可能是引起大量网民在网络上群起而攻之的主要原因。例如,“高跟鞋虐猫女”事件中的“虐猫女”就是道德失范在先,而“铜须门”事件中插足别人婚姻的主人公“铜须”也是道德失范在先。可见,一部分网络暴力实施者的动机确实是基于道德感的“油然而发”,但这种“道德审判”无异于公然动用私刑,造成道德失范者所付出的代价大大超过其“罪过”的失衡局面,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
第三种观点认为,网络暴力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舆论暴力。持论者认为,网络暴力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网民在发表意见时使用侮辱、威胁与恶意造谣等语言暴力;二是舆论对被害人造成直接或者间接伤害;三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虽然这种意见上的压制并不会造成现实的伤害,但从影响来看,这种现象也具有一定的暴力特征。⑩参见彭兰:《如何认识网络舆论中的暴力现象》,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8 月25 日,第6 版。该观点主要从“暴力”等行为特征的角度对网络暴力的概念加以阐释。
第四种观点认为,网络暴力是一种网络侵权行为。持论者认为,网络暴力在本质上是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对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以及财产权进行侵犯的群体性侵权行为。⑪参见陈代波:《关于网络暴力概念的辨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13 年第6 期。该观点主要从网络暴力所侵害的对象角度对网络暴力概念加以界定。
综上所述,从网络暴力的异化原因、主体特征、行为特征、侵害对象等角度,可以分别对网络暴力的内涵进行定义。对网络暴力的各方面本质特征加以综合,可以将网络暴力概念的内涵界定为:不特定多数的互联网用户在网络空间针对特定对象恶意发起的,以语言攻击、人肉搜索、威胁、骚扰、侮辱、造谣等方式为主要手段,具有群体性、煽动性、攻击性、持续性的严重侵害其他公民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
(二)网络暴力概念的外延
网络暴力概念的外延是指网络暴力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最大范围。对这一问题,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网络暴力是否包含由线上蔓延至线下的“网下暴力”?换言之,当网络上的语言攻击和舆论压迫转变成在现实生活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友的侵扰时,这种发生在现实空间的暴力是否还属于网络暴力的范畴?经过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被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经常被悉数曝光,姓名、住址、工作单位、手机号码、家人信息、社交动态等所有个人信息都会被肆意公开和传播,甚至连被害人若干年前的昔日“囧事”也会被扒出并沦为施暴者的谈资。当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关键信息被曝光之后,可能有部分过激的网络暴力实施者前往被害人的住所或工作地点,对其实施恐吓、谩骂、殴打等暴力行为。笔者认为,对于这种由线上蔓延至线下的暴力行为,不宜再认定为网络暴力,对相关行为直接适用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罪名即可。网络暴力一词由“网络”和“暴力”组成,“网络”是行为实施的地点,“暴力”是行为实施的性质。也即网络暴力是现实暴力向网络空间的延伸。行为实施地点的不同是网络暴力区别于现实空间中暴力的最本质因素,因此,我们应当将网络暴力的外延限制在实施地点为网络空间的行为之中。这样不仅有利于有针对性地打击和识别网络暴力行为,也有利于防止网络暴力概念的滥用和混同。
其次,网络暴力所使用的网络语言是否必须具有明显的人身攻击性?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各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互联网语言文化、网络热词、内涵段子等层出不穷。一些看似并不具有人身攻击性的词语被网民赋予了别样的“内涵”。例如,在最近发生的“武汉校园碾压案”孩子妈妈不堪网暴跳楼离世的案例中,众多网民并没有使用辱骂、威胁等具有明显人身攻击性的词语,而是通过“还能穿这么正式?”“这是孩子妈妈吗?怎么说话这么冷静??”“妈妈的穿着打扮是用了心的”“这位妈妈想成为网红吗?”等词语进行冷嘲热讽,这对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来说是极其残忍和无法接受的打击,最终导致这位母亲跳楼自杀的严重后果。笔者认为,随着互联网语言文化逐渐多元化,诸如“二次元文化”“饭圈文化”等亚文化圈的“行业黑话”也越来越多,很多传统词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并被用以恶意攻击他人。类似于“妈妈的穿着打扮是用了心”的言语,表面上看似没有明显的人身攻击性,但在网络暴力的特殊语境中,这种评论质疑完全可能对这位母亲的心理造成伤害。且在此时调侃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痛苦,在本质上无疑具有强烈的人身攻击性。因此,判断网络语言是否具有人身攻击性要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入手。对于表面上没有人身攻击性,但在网络暴力特殊语境中具有人身攻击效果的语言,我们也应认定其为网络暴力的实施手段。换言之,网络暴力所使用的网络语言不必在表面上具有明显的人身攻击性,通过看似正常的网络语言暗讽他人并且在实际上产生人身攻击效果的,即可认定其为网络暴力。
最后,网络暴力是否必须具有群体性?有观点认为,网络暴力可以由个体和群体实施。⑫参见张旺:《“网络暴力”成因探析》,载《新闻世界》2011 年第12 期。也即网络暴力不一定是群体性事件,也可以是由单一个体实施的。对此笔者不能认同。笔者认为,网络暴力必须具有群体性。我们之所以要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研究,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网络暴力事件中“法不责众”的困境。当然,个体在网络上恶意攻击他人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网络暴力的部分特征,但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远不足以达到人们通常所说的网络暴力的程度。虽然网络暴力的实施者可以追溯至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但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产生于群体性特征中。群体由个体组成,群体的力量是个体所不能企及的。因此,网络暴力的主要发起者通常都要积极煽动他人参与,只有借助群体的力量才能达到舆论压制的效果。
(三)网络暴力概念在刑法中的限缩与还原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明确了网络暴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这是网络暴力较为宏观的整体性概念。在刑法范围内,还应当对需要刑法规制的网络暴力行为进行细分和识别,将网络暴力这一内涵复杂、外延较广的概念在刑法意义上进行限缩与还原。
一方面,应当对网络暴力概念在刑法中的内涵进行限缩。因为刑法具有最后手段性,同时也是行政法等其他前置法的保障法,所以刑法规制的犯罪行为在范围上小于行政法等前置法所规制的违法行为。因此,只有达到严重程度的网络暴力行为才能受到刑法规制。质言之,并不是所有的网络暴力行为都值得刑法规制,只有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并且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网络暴力行为才能受到刑法制裁。根据相关行为的严重程度及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同,我们可以将网络暴力划分为轻微网络暴力和严重网络暴力。具体而言,轻微网络暴力是指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结果且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通过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就可以较为妥善地处理相关行为。严重网络暴力是指造成了严重危害结果且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必须通过刑法才能有效规制相关行为。笔者认为,刑法中的网络暴力应当仅包括那些造成了严重危害结果且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严重网络暴力行为。
另一方面,应当对网络暴力在刑法中的内涵进行还原。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没有“网络暴力”一词,也没有专门规制网络暴力行为的所谓“网络暴力罪”。实际上,“网络暴力”一词是对数种不同性质行为的概括,我们应当在刑法上将网络暴力还原为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具体行为,刑法理论研究中也尽量减少对网络暴力这一名词的使用。目前,刑法主要通过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较为分散的多个罪名对网络暴力加以规制。在刑法没有明文使用网络暴力这一概念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网络暴力在刑法中的内涵进行识别和还原。
综上所述,网络暴力既是一种成因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统一的非法律概念,在本质上是对多种不同性质行为的总称。从宏观角度看,网络暴力包含犯罪行为、违法行为和道德失范行为;从微观角度看,刑法意义的网络暴力仅包括造成了严重危害结果且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严重网络暴力行为。所以我们应当对相关行为适用刑法时尽量减少对网络暴力一词的使用,转而将网络暴力还原为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寻衅滋事等可以被刑法评价的具体行为。
三、网络暴力现象刑法规制的现状及其困境
应该看到,在行为方式、行为地点、行为主体、行为对象等方面,网络暴力与传统暴力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因此,在传统暴力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尚未以全面兼容网络暴力而作出调整的情况下,对网络暴力直接套用传统暴力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必然会造成刑法适用上的种种困难。
(一)网络暴力现象刑法规制的现状
目前,在网络暴力的全链条法律治理体系中,存在“严重网络暴力行为频发”“民法行政法治理无力”“刑法规制失位”等情况。⑬参见石经海、黄亚瑞:《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究》,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4 期。具体而言,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领域已经存在大量关于网络暴力的规定。《民法典》第1194 条、第1195 条、第1196 条以及第1197 条中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补救措施与责任承担”“不侵权声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等一系列针对网络暴力的民事规制措施。除此之外,《网络安全法》第12 条和第47 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 条和第42 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 条、《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21 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 年修正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都对网络暴力现象进行了规定,并且明确了网络用户和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暴力中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尽管如此,大量严重网络暴力事件依然频发,这充分证明了对严重网络暴力“民法行政法治理无力”的现状。严重网络暴力行为已经穿透了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的防线,必须由刑法作为保障法对其加以规制。
网络暴力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网络语言暴力”“人肉搜索”“捏造传播网络谣言”三种。⑭参见徐才淇:《论网络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制》,载《法律适用》2016 年第3 期。因为不同的行为方式所侵害的法益也有所不同,所以刑法往往根据网络暴力的行为类型和所侵害的法益性质来确定具体适用的罪名。首先,在网络空间煽动不特定多数网民辱骂攻击他人、捏造事实或散布谣言等行为是网络暴力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其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等人肉搜索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后,在网络空间使用语言暴力恐吓他人、起哄闹事,情节恶劣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分别以“网络暴力”“刑事案件”或“人肉搜索”“刑事案件”两组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询到了六份刑事判决文书。纵然有些网络暴力案件的法律文书中可能没有使用“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词汇,但在严重网络暴力频发的背景下,这屈指可数的刑事立案数量再次印证了对网络暴力“刑法规制失位”“刑事司法缺位”的现状。
(二)网络暴力现象刑法规制的困境及其成因
在刑法上构建网络暴力的治理体系时,必须杜绝“刑法规制失位”等情况的发生。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对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困境及其成因进行剖析。
首先,网络暴力的群体性导致“法不责众”的刑法规制困境。“法不责众”是让刑法乃至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治理手段都闻之色变的棘手难题。所谓“法不责众”,是指当某个行为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普遍性时,即使该行为具有一定的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也难以对其进行责难与处罚。⑮参见赵新河:《论扫黑除恶与矫治“法不责众”》,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9 年第4 期。所有的犯罪人都具有趋利避害性,如果其犯罪行为很容易暴露,那么犯罪人在经过理性选择以后就会选择放弃犯罪。⑯参见陈波:《猥亵行为应纳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师源性侵为例》,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 年第4 期。网络暴力的形成往往需要不特定多数人的参与,通常表现为大量网民故意或者盲目跟风对他人实施持续性的骚扰、辱骂、诽谤、威胁、人肉搜索、散布虚假信息等不法行为。正是因为网络暴力的参与主体具有群体性和不特定性,导致刑法在规制网络暴力时出现难以明确犯罪行为人以及其他方面的困境。这里至少需要讨论几个问题:其一,由于参与网络暴力的人员众多,刑法对相关人员进行规制的边界如何确定?刑法如何区分在网络暴力中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其二,网络暴力中的众多行为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又如何对其进行具体的刑事责任分配?其三,网络暴力所涉及的罪名大多是诸如侮辱罪、诽谤罪等原则上需要“告诉才处理”的自诉罪名。这是否可能导致被害人因取证困难等原因而无法得到刑法救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自诉转公诉”?这又是否可能滋生在自诉案件中公诉权被滥用的风险?以上都是由网络暴力的群体性所引发的刑法规制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网络暴力的特殊行为特征导致传统罪名的罪状无法与网络暴力行为相匹配的刑法规制困境。网络暴力在本质上属于暴力行为,但又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暴力行为。关于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暴力是指外力对他人身体的打击或强制,包括殴打、捆绑、伤害等,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的状态。从传统暴力的定义可以看出,暴力行为的对象必须是人的身体;暴力行为的实施方式必须是殴打、伤害等具有接触性且达到强烈程度的“打击或强制”;暴力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必须是被害人的反抗被压制。与传统暴力相比,网络暴力的对象是他人人格、名誉等人身权利;网络暴力的实施方式是语言暴力等非接触式的网络攻击行为;网络暴力所引起的结果是被害人受到精神伤害进而造成其自杀、自残等严重后果。通过对比可知,网络暴力与传统暴力在行为方式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本质区别。因此,在传统暴力犯罪没有将网络暴力典型行为类型予以吸收的情况下,必将导致相关罪名的罪状与网络暴力行为不相匹配,进而造成刑法无法有效规制网络暴力相关行为的窘境。
《刑法》第246 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根据刑法规定,侮辱罪的行为类型包括“暴力侮辱”和“其他方法的侮辱”两种。暴力侮辱是指直接使用暴力或者使用暴力相威胁对他人进行侮辱;其他方法的侮辱是指通过言词或文字等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而且必须达到与暴力侮辱相当的程度。⑰参见刘宪权主编:《刑法学》(第5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598 页。因为网络暴力是利用互联网实施的语言暴力,所以网络暴力不可能构成需要在现实空间直接使用暴力的“暴力侮辱”。同时,网络暴力所使用的“隐喻性”语言往往难以达到“暴力侮辱”的暴力程度,这也导致大量网络暴力行为几乎不可能以“其他方法的侮辱”的形式被认定为侮辱罪的实行行为。除此之外,构成侮辱罪还有情节严重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网络暴力行为因为没有符合情节严重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无法入罪。实际上,在网络空间肆意传播他人隐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等行为虽然可能在暴力程度上没有达到传统侮辱罪所要求的程度,但是其对被害人名誉权等法益的侵害可能并不亚于暴力侮辱。因此,侮辱罪的现有构成要件侧重于从“暴力”程度的角度认定相关行为,但网络暴力行为的暴力程度很难在外观上达到现实中“暴力侮辱”的程度,进而在我国“定性+定量”的犯罪模式中难以达到侮辱罪的“定量”要求。
《刑法》第246 条规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捏造、传播谣言只是网络暴力主要行为方式中的其中一种。相比于网络语言暴力和人肉搜索,以捏造、传播谣言的方式煽动他人恶意攻击特定对象的行为更容易被识别和定性。因此,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公开的案例中,构成诽谤罪的网络暴力行为在相关刑事判决中占据绝大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将完全捏造事实且符合情节严重的网络诽谤行为认定为诽谤罪不会引起争议,但在大量网络暴力事件中,行为人并不是完全凭空捏造事实,而只是对媒体报道进行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进而引发具有群体性的批评和攻击。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并非完全捏造事实,但却添加了行为人自身主观臆断的网络暴力行为,以诽谤罪中的“捏造事实”加以认定确实具有一定困难。由此,我们如果对诽谤罪的入罪标准不作出调整,那么大量捏造部分事实诽谤他人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行为将无法得到刑法规制。
《刑法》第253 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17 年“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称《解释》)。《解释》第1 条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解释》第2 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解释》第3 条规定,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以及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根据《刑法》与《解释》的内容可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而《解释》则主要从“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和违法所得“数额”等方面对本罪的入罪标准进行规定。但是,在大量人肉搜索型的网络暴力事件中,网友扒出并传播的照片、社交动态等被害人的个人信息都是被害人主动在微博等社交软件上发布的信息。根据《解释》第1 条规定,被害人已公开的照片等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根据《解释》第2 条和第3 条规定,转发他人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属于“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不属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因为目前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明文禁止在互联网上转发他人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换言之,虽然相关转发或传播行为属于“未经被收集者同意”的情形,但相关行为既不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构成要件,也不符合《解释》中规定的非法收集和牟利等条件。因此,相关人肉搜索行为难以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293 条规定,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 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可见,上述司法解释的内容涉及对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定。但是,由于相关规定中具有“破坏社会秩序”与“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要求,这导致对网络暴力现象适用寻衅滋事罪的范围大打折扣。相比于现实空间中的传统暴力,网络语言暴力具有间接性的特征,而且施暴者往往高举“伸张正义”和“言论自由”的大旗。如果行为人不采用起哄闹事等手段,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正常发表不具有辱骂等攻击性质的“隐喻性”评论,那么这种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就难以被界定为对社会秩序或者公共秩序造成了破坏。因此,对被害人造成严重精神伤害的网络暴力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发生混乱,进而可能无法构成寻衅滋事罪。
最后,网络暴力的“舆论失焦”效应导致刑法难以通过因果关系理论对行为人进行刑事追责的困境。在“网络信息茧房”“公众接受信息窄化”“网络话语权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信息一旦在网络上曝光,就可能被自媒体以及其他互联网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在传播过程中,舆论和舆情很难被其中一方所主导,舆论中心也逐渐偏离最初的议题,继而导致舆论失焦现象的发生。⑱参见蹇昶、杨宗科:《舆论失焦中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载《传媒》2023 年第9 期。通过对这种“舆论失焦”效应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行为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之后就可能难以控制接下来的舆论走向,众多网络主体的参与可能改变甚至违背信息发布者的原意。因此,如何在刑法上证明信息发布行为与最终社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将客观上由众多参与主体共同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仅归责于少数行为主体?又如何证明或推定信息发布者的主观内容?这些均是司法实践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见,“舆论失焦”效应也在刑事追责等方面引发了大量刑法难以适用的困境。
四、网络暴力现象刑法规制的困境解决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犯罪样态将发生重大改变,这也给传统刑法以及刑事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⑲参见储陈城:《刑法修正的趋势与约束机制的演变》,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 年第2 期。刑法因为重视稳定性而无可避免地带有滞后性,但这种滞后性应当体现在立法之中而不是萦绕于理念之上。⑳参见张小宁:《经济刑法理念的转向:保障市场自律机制的健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 年第1 期。对于网络暴力问题,国家应当采取多主体、多环节、多举措的全链条治理模式,并且将刑法规制作为最后治理手段。在严重网络暴力的刑法治理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及时作出合理的应对之策。
(一)网络暴力现象刑法规制的模式选择
关于网络暴力现象刑法规制的模式,主要有“增设新罪名”与“解释、修改旧罪名”两方面的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既然刑法立法及司法多次对原有罪名进行修补与解释仍不能有效追诉网络暴力行为,那么就应当有理有节地考虑将其增设为新罪名”。㉑石经海、黄亚瑞:《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究》,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4 期。也即应当在刑法中增设“网络暴力罪”。也有学者认为,“立足现行实定法,虽然相关法律未对网络暴力的法律责任作出直接规定,但网络暴力并未游离在法律规制之外,对所涉具体行为都可以视情适用相关规定作出处理”。㉒喻海松:《网络暴力的多维共治——以刑事法为侧重的展开》,载《江汉论坛》2023 年第5 期。持论者进一步主张,因为网络暴力所涉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刑法不能简单地通过增设新罪的方式对网络暴力进行规制,而是应当采取类似于民事、行政领域中“就事论事”的模式对网络暴力的不同行为类型进行分别评价。
笔者认为,就网络暴力当前所表现出的种种特征来看,刑法应当采取对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的罪状和法定刑进行解释或修改的规制模式,而不宜在刑法上增设专门的“网络暴力罪”。理由如下:首先,通过对现有罪名的解释或修改,网络暴力的主要行为类型完全可以被相关罪名所涵盖。如前文所述,网络暴力的三种主要行为类型分别是网络语言暴力、人肉搜索和捏造传播谣言。从刑法保护法益的性质和与罪名的符合程度来说,对网络语言暴力型的网络暴力行为完全可以适用侮辱罪和寻衅滋事罪等罪名;对人肉搜索型的网络暴力行为完全可以适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寻衅滋事罪等罪名;对捏造传播谣言型的网络暴力行为完全可以适用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等罪名。从立法简洁性的角度看,如果经过专门的刑法解释和修改之后,对涉网络暴力的相关行为完全可以适用刑法中的现有罪名。也即在刑法中增设“网络暴力罪”实际上并没有必要。其次,增设“网络暴力罪”并不能有效解决刑法规制网络暴力的现有困境,反而将衍生出其他问题。支持增设“网络暴力罪”的学者主张,应当将“网络暴力罪”置于《刑法》第246 条侮辱罪、诽谤罪之后,作为第246 条之一。可见,持论者在本质上是将“网络暴力罪”依附于侮辱罪和诽谤罪,主要是欲对涉网络暴力侵害名誉权等人身权利的行为加以刑法规制。但是,这无法将涉网络暴力对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社会管理秩序等其他法益造成侵害的行为归入规制的范围之中。因此,增设“网络暴力罪”不仅没有彻底解决刑法规制网络暴力时存在的“法不责众”、因果关系不明等现有困境,反而可能限缩了刑法对网络暴力的打击范围。因此,笔者认为,对网络暴力进行刑法规制的侧重点不应放在增设新罪名上,而应放在科学合理地解释或修改既有罪名的构成要件和适用条件上。最后,网络暴力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既包括多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方式,也可能对隐私权、名誉权、社会管理秩序等不同性质的法益造成侵害。正如前文观点,网络暴力是对多种不同行为的总称,因此,笔者主张在刑法中对网络暴力概念进行还原,将本就不是法律概念的“网络暴力”在刑法上还原为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寻衅滋事等具体行为。这样即能以“大象无形”和“无招胜有招”的方式用刑法有效规制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同时,我们应当在相关法律文件中弱化使用网络暴力这一指代内容复杂、含混不清的概念。
(二)对网络暴力刑法规制中“法不责众”等问题的解决
网络暴力之所以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是因为煽动者使用了“移情手法”,即引导“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在审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网络事件时能够“感同身受”,从而将之前“相似不公正经历”或者社会生活中积攒的负面情绪在网络事件中发泄出去。通过移情手法,可以将个体冲突演化为阶层对立、将问题解决转换成情绪发泄,从而将个体事件上升为群体事件、普通事件上升为公众事件。㉓参见石立春:《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西南交通大学2019 年博士学位论文。在网络暴力中,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融入群体的“从众心理”、借题发挥的“发泄心理”、道德审判的“英雄心理”、质疑政府的“逆反心理”等不良心态发挥着重要作用。㉔参见吴传毅:《“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盲从效应与宣泄心理》,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4 期。因此,对网络暴力刑法规制中“法不责众”、刑事归责依据等问题的有效解决,无疑是织密网络暴力刑事制裁法网的关键路径。
笔者认为,网络暴力刑法规制中的“法不责众”现象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只要对隐蔽在群体之下的关键个体进行精准辨识,即可破解“法不责众”的难题。“法不责众”最令人困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个“众”字。“众”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近义是“多”,反义是“寡”。目前,并没有学者能够从人员数量上明确几人以上就能称之为“法不责众”中的“众”,进而将具有群体性的网络暴力列为刑法难以治理的对象。笔者认为,不应当从人员的数量上对“众”进行理解,而应当从人员的不特定性上对“众”加以阐释。如果犯罪人是特定的多数主体,那么即使是上百人的犯罪集团也丝毫不存在“法不责众”的问题。但是,如果参与犯罪的主体是具有不特定性的多数主体,那么将极大地影响刑法对相关行为的正确定性和惩治力度。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网络暴力事件都会持续较长时间,其间有大量网民不断涌入参加。也正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参与到网络暴力之中,所以造成了网络暴力参与主体的不特定性,进而形成了“法不责众”的表象。事实上,在网络暴力的所有参与主体中,发起者、组织者、煽动者、教唆者等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是相对固定和明确的,处于网络暴力参与主体的“核心”,而被煽动者、跟风参与者等行为人虽然在客观上对网络暴力产生了助力作用,但其在本质上处于网络暴力参与主体的“外围”。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处于“核心”的网络暴力参与主体具有特定性,而处于“外围”的网络暴力参与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类似于这种“核心”固定而“外围”流动的群体性事件古已有之,在我国刑法史上也存在不少针对类似群体性事件的相关规定,这些中华法系的古老规定对当下治理网络暴力仍有着借鉴意义。
《尚书·胤征》中记载了夏朝国君发布的命令“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大意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唐律《名例》篇中记载“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㉕唐稷尧:《论我国刑法分则中的组织行为》,载《中外法学》2022 年第6 期。可见,对于具有群体性特征的犯罪行为,刑法应侧重于对发起者、组织者、煽动者、教唆者等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进行惩治。更何况,煽动者一般采取在网络上发帖、造势等不针对特定被煽动对象的煽动行为,这反映出被煽动加入网络暴力的网民很难与煽动者形成共同犯罪的故意,两者之间甚至都很难建立沟通联系。因此,与网络暴力主犯没有形成共同犯罪故意且没有犯罪通谋的被煽动者等网络暴力“外围”参与主体,根本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也即跟风评论等网络暴力“外围”参与主体的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没有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按犯罪认定没有道理。这就进一步印证了刑法应当着重打击发起者、组织者、煽动者、教唆者等在网络暴力中起主要作用行为人的正确性。对上述人员进行刑法制裁,也能起到良好的犯罪预防和遏制网络暴力迅猛势头的法律效果。
(三)现有罪名对网络暴力的兼容路径
我们既然选择了不单独增设“网络暴力罪”的刑法规制模式,那就要通过现有罪名全面兼容网络暴力的所有行为类型,在刑法上对各种严重网络暴力行为分而治之。具体而言,通过现有罪名全面兼容网络暴力的路径主要有:
1.运用刑法解释原理对现有罪名进行扩展和调适,也即充分运用客观解释、目的解释等刑法解释原理对严重网络暴力行为加以认定
对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直接决定着刑法对网络暴力行为的定性,进而影响到刑法规制范围的大小。根据刑法理论通说,主要的刑法解释立场包括主观解释说、客观解释说和折中说。其中,主观解释说恪守立法原意对刑法解释的限制作用,认为刑法解释应当围绕立法原意进行,同时主张刑法条文的规范含义不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客观解释说认为法律的含义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因而对法律的解释也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折中说认为刑法解释采用主观解释还是客观解释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其内部又分为“主观的客观解释说”等不同观点。㉖参见刘宪权:《元宇宙空间犯罪刑法规制的新思路》,载《比较法研究》2022 年第3 期。笔者认为,通过适当运用刑法解释原理的方式可以解决大部分网络暴力刑法规制问题。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以合理规制严重网络暴力为目的,对侮辱罪等具体罪名进行适当的扩大解释或目的解释,可以将大部分严重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尽可能通过刑法解释解决网络暴力刑法规制困境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既能够保障刑法规范的相对稳定,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
首先,应当将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名誉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认定为侮辱罪中“以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的情形。目前,在侮辱罪的司法认定中,往往要求“以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在暴力程度上必须达到与在现实中直接使用暴力相当的程度。但是,发生在现实空间的侮辱行为和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侮辱行为肯定在行为方式上具有较大差异。对于发生在网络空间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刑法认定其是否构成侮辱罪的侧重点不应只放在与现实暴力的对比上,而要放在重点考察相关行为对公民人格、名誉等法益的侵害程度上。在网络空间发表具有人身攻击性的语言,属于语言暴力的一种,其在暴力的表现形式上与现实空间中强制、强迫他人等肢体暴力具有本质区别。根据客观解释原理,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都属于广义上的“暴力”,虽然表现形式和行为地点不同,但上述两种暴力行为都可以对他人的人格、名誉等法益造成严重侵害。因此,具有明显攻击性和侮辱性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可以通过客观解释将其认定为与“暴力侮辱”具有相当性。换言之,在网络空间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名誉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侮辱罪中“以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的情形,进而构成侮辱罪。
其次,应当将断章取义、“添油加醋”等曲解事实并大肆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认定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捏造”在广义上包括完全捏造和部分捏造。关于诽谤罪中的“捏造”一词,理论通说认为其仅指无中生有、凭空制造虚假的具体事实,也即仅包括完全捏造而不包括部分捏造。笔者认为,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添油加醋”等曲解事实并大肆传播的行为看似仅仅捏造了部分事实,但这并不能绝对否定相关行为转变为完全捏造的可能。在各种网络信息目不暇接的当下,网民很难直接判断出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为博人眼球,对媒体报道断章取义,添加自己编造的事实并大肆转发、传播,如果对他人人格、名誉造成严重侵害的,应当构成“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形。根据目的解释,捏造部分事实诽谤他人且造成人格、名誉受到严重侵害的行为应当入罪;根据文义解释,捏造部分事实的行为并没有超出“捏造”的最大文义射程。因此,在网络空间断章取义、“添油加醋”等曲解关键事实并大肆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属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形,进而构成诽谤罪。
2.对于通过刑法解释原理仍无法兼容的网络暴力行为类型,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现有罪名的构成要件或法定刑,及时通过修改刑法的方式对相关罪名进行修正
首先,应当对部分罪名的罪状进行修改。刑法应当将提供、传播他人已公开个人信息且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肉搜索行为规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人肉搜索案件所涉个人信息,不少来自被网暴者工作单位的信息公告栏等渠道,实际上属于公开信息的范畴。”㉗同前注㉒。获取他人已经处于公开状态的个人信息无须征得同意,属于合法行为。但是,在未经权利人同意、被权利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权利人重大利益的情况下,行为人将合法获取的他人已公开个人信息实施传播、提供等未经“二次授权”的行为,造成他人个人信息泄露等严重后果的,应当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除此之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类型是“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因为在网络上公开他人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属于出售行为,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只能强行将“公开”行为纳入“提供”行为的范畴。“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 条规定,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 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是,一般而言,提供行为的对象具有特定性,而公开行为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可见,提供行为的对象范围相对较小,而公开行为的对象范围相对较大。用一个范围相对较小的概念(提供行为)去涵盖一个范围相对较大的概念(公开行为)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修改刑法条文的方式将公开他人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评价范围,而不能通过司法解释将范围不同的两个概念强行合并。具体而言,可以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规定的犯罪行为类型修改为“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如此一来,无论是未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还是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都能被刑法纳入保护范围。
其次,应当对部分罪名的法定刑进行调整。经过互联网虚拟性、快捷性、即时性、传播性等技术原理的加持,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侮辱和诽谤行为通常会产生比现实空间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此基础上,网络暴力的群体性和持续性更是再次提高了相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㉘参见石经海:《论网络暴力的实质与刑法适用规则的完善》,载《法律科学》2023 年第5 期。例如,网络暴力事件中受害人的自杀率就远远超过传统侮辱罪或诽谤罪中受害人的自杀率。由此可以看出,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网络暴力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可能远远超过发生在现实空间的传统侮辱或诽谤行为。目前,侮辱罪和诽谤罪的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有期徒刑。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且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网络暴力行为,侮辱罪和诽谤罪的最高法定刑难以满足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因此,刑法应当在侮辱罪和诽谤罪中增加一档法定刑,同时以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而言,可以在《刑法》第246条中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通过以上修改,我们可以有效解决侮辱罪和诽谤罪在规制严重网络暴力行为时可能存在的罪刑失衡等问题。
五、结语
当前,提升刑事治理现代化水平,乃各国应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之关键所在。㉙参见彭文华、董文凯:《我国核准追诉制度的条件及其完善——以“南医大奸杀案”的追诉时效为视角》,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5 期。对网络暴力进行刑法规制体现着自由主义观念与社会责任观念的激烈交锋。公民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都享有言论自由的法定权利,但是任何权利都有边界。刑法对网络暴力行为的规制并不是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是对超出权利合理行使范围的越界行为进行合理规制。这不仅是对良好网络环境的维护,更是对那些在网络暴力事件中受到严重人身侵害的受害人进行刑法保护的需要。对网络暴力应当采取“分而治之”的刑法规制模式,通过刑法解释和刑法修改等措施,利用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多个罪名可以较好地兼容网络暴力的主要行为方式,形成多个罪名对严重网络暴力行为的共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刑法能够对严重网络暴力行为进行规制,但单靠刑法的力量来遏制所有网络暴力现象是远远不够的。网络暴力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司法机关、网络平台、学校、家庭、社区、媒体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合作和参与,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网络暴力的价值导向和高压态势,以多部门、多领域的合作机制共同治理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