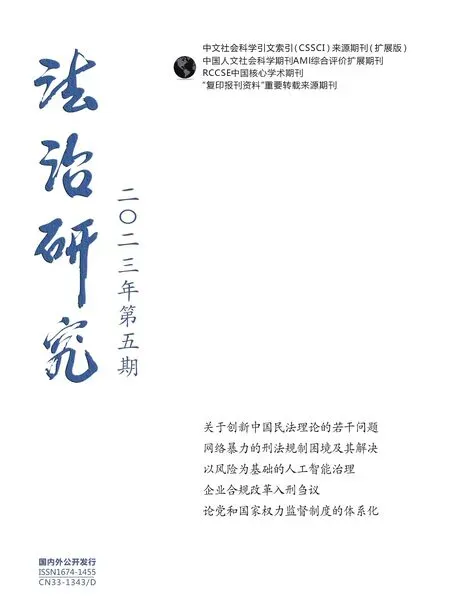《民法典》中近亲属医疗同意的规范构造
2024-01-18周雅婷
周雅婷
《民法典》对医疗知情同意规则的规定基本沿袭《侵权责任法》,置于《民法典》第1219 条第1 款第2句,其中第2 句前段是患者知情同意规则,后段是近亲属医疗同意规则。较之《侵权责任法》第55 条改动处有三:(1)第1 款第2 句前段中的“书面同意”改成“明确同意”;(2)第1 款第2 句后段中的“书面同意”改成“明确同意”;(3)第1 款第2 句后段中的“不宜向患者说明”前增加“不能”的情形。①《民法典》第1219 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法条表述来看,前后段间使用分号,意指前后段在法律上作同等评价,即近亲属同意等同于患者的同意。因此,近亲属同意规则应属于医疗知情同意规则的组成部分,其立法目的和规范意旨应与患者的知情同意规则相一致。但近亲属同意本质上并非患者本人的同意,何时近亲属得为同意,近亲属的范围如何界定,当近亲属意见和患者意见或者患者可推测的意见不一致时如何处理,近亲属同意在法律上性质如何,医生是否可根据自身专业和经验判断而不采纳近亲属意见,以及近亲属滥用同意权的法律后果等,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日常医疗活动中由近亲属进行同意的情况极其常见,疫苗接种、孕妇生产、外科手术等都需要近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也产生许多问题,典型如“肖志军拒签事件”“榆林产妇跳楼事件”,其他如手术中更改麻醉方式未取得近亲属同意②参见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8 民终2829 号民事判决书。、拔牙后脑出血近亲属补签知情同意书③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贵民申5252 号民事裁定书。等情况亦属常见。当然,医疗活动中还存在大量同时向患者和近亲属告知并取得同意,分别签署知情同意书或者在同一知情同意书上均签名的情况,此时的近亲属同意应为患者自身同意的加强或者患者同意的证明人,与本文所讨论的近亲属医疗同意不属于同一范畴,也非法条所规定的近亲属同意。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近亲属医疗同意是指只要取得近亲属同意,医生便可实施医疗行为的情形。
《民法典》第1219 条的规定丰富了近亲属医疗同意的类型,更重要的是,置于《民法典》中有了体系解释的条件和必要,目的解释也有更为丰富的资源。本文尝试从解释论角度对近亲属医疗同意规则进行阐述,就教于方家。
一、近亲属医疗同意的规范功能
(一)医疗行为的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医疗行为作出明确规定。通常认为《医师法》第22 条中的“医师的执业活动”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 条中的“诊疗活动”是相类似的概念。④参见王岳主编:《医事法》(第3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 年版,第15 页;艾尔肯:《论医疗行为的判断标准》,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4 期。《医师法》第22 条第1 项规定“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 条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学界使用较多的还有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对于医疗行为的界定,其中我国台湾地区认为:“凡以治疗、矫正或预防人体疾病、伤害、残缺或保健为直接目的,所为的处方或用药等行为的全部或一部之总称,谓为医疗行为。”⑤转引自陈聪富:《医疗责任的形成与展开》,台大出版中心2019 年版,第2 页。日本学者认为:“医疗行为是指疾病的预防、患者身体状况的把握和疾病原因以及障害的发现、疾病和障害治疗以及因疾病引起的痛苦的减轻,患者身体及精神状况改善等为目的对身心所作的诊察治疗行为。”⑥转引自艾尔肯:《论医疗行为的判断标准》,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4 期。应该说,各国各地区对于医疗行为的界定大致相同,是指针对人体疾病的治疗、预防及保健行为。
(二)医疗行为伤害说与非伤害说立场
医疗行为是针对人的身体的行为,难免造成人体伤害。但就一般社会观念,人们很难将医疗行为与伤害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医疗行为存在伤害说和非伤害说。医疗行为伤害说肇始于德国法院“骨癌截肢案”判决,该案认为医疗行为具有伤害性,阻却违法必须征得患者同意。⑦参见钱叶六:《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与紧急治疗、专断治疗的刑法评价》,载《政法论坛》2019 年第1 期。此后,医疗行为伤害说为德、日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接受,尤其在刑法领域,基于医疗行为伤害说立场讨论医疗行为正当化的成果颇丰。⑧参见曹菲:《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研究——德日的经验与我国的借鉴》,载《刑事法评论》第29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40 页以下。而医疗行为非伤害说则认为医疗行为的本旨在于恢复患者身体健康、保全患者生命,行善原则被认为是医生必须履行的积极义务,⑨Marc Stauch &Kay Wheat,Text,Cases and Materials on Medical Law and Ethics,Routledge Press,2015,p.17.只要医疗行为是出于维护患者身体健康的目的,就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不能认为是伤害。⑩同前注⑦。在父权主义医疗时代,医疗行为非伤害说为主导,强调医者仁术。即便在医疗行为伤害说早期,也以“业务权说”进行正当化解释,认为医疗行为是为国家、个人的利益并为法律所承认,只要从医学知识上足以达成医学目的,且法律未明文禁止就是被允许的,即使可能对病人身体造成伤害。⑪同前注⑦。但随着病人权利运动的推进,患者自己决定权获得重视,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也从“业务权说”转向“患者同意说”,患者最佳利益成为医疗行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且须重视患者的主观意思。患者的知情同意逐渐成为医疗行为正当化的核心根据。⑫参见满洪杰:《医疗损害责任法的体系反思与解释论构建》,法律出版社2022 年版,第146 页。普遍认为,医疗知情同意规则成为医疗活动中的基本规则,奠定医疗行为的合法基础。⑬参见王岳主编:《医事法》(第3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 年版,第49 页。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司法实务对医疗行为伤害说出现动摇。不少实务见解认为,如果医疗行为未造成患者健康上的伤害,即便医生在医疗行为前未进行充分告知,医生也无责任,患者也无任何请求权可主张,⑭BGHZ 176,342.并认为该种情形如果允许患者以人格权受侵害而请求损害赔偿,有过于扩张医生义务之虞。⑮同上注。此种实务见解实际上缓和了医生在医疗行为伤害说下的责任,被不少法院采纳,亦获得学界支持。在德国实务中,还有极少数人认为,即使患者基于医生的不完全告知而同意治疗,如果患者在同意时已经知道嗣后可能发生的医疗风险,医生对于该风险也不承担赔偿责任。⑯BGHZ 168,103(111).该种案型的说理实际上是否认医疗行为伤害说,在德国属少数见解,遭到学界批评。由此可见,即便在德国,医疗行为伤害说也时常被动摇。只有在医生未取得患者同意实施医疗行为,并造成患者健康损害时,稳健地采医疗行为伤害说,而在未造成患者损害时,多采上述第一种案型的见解。
实际上,医疗行为伤害说与非伤害说出现模糊化趋势。⑰参见吴志正:《解读医病关系IV 医疗诉讼篇(下)》,元照出版公司2022 年版,第65 页。对于医疗行为客观上属于增进或维持患者健康必要且相当、具有社会正当性而符合诊疗规范及当时医疗水平之要件者,无论采医疗行为伤害说还是非伤害说,其结果并无实质差异。其中,采医疗行为伤害说,是不预先对医疗行为进行违法性与否的评价,而是假设其符合伤害行为构成要件,再在违法性阶层进行审查。而采医疗行为非伤害说,则将医疗行为违法性与否的评价提前至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先判断该医疗行为是否属于正当的医疗行为。换言之,从法规范评价层面来看,医疗行为伤害说实为一种阶层式犯罪构成或侵权构成分析的前提假设,其目的乃基于法律分析逻辑上的考虑,为让医疗行为正当化事由得以在违法性阶层上进行系统探讨或体系建构。从判断结果来看,二者的界限渐趋模糊,区分意义已不明显。德国学说上也认为,医疗行为正当化需要主观上出于医疗目的,客观上遵守一般医疗准则,具有医学适应性,而患者之所以同意接受医疗行为,也是建立在知悉及确信医生的行为是根据医学知识,符合一般医疗准则,以及遵守一切医疗常规下所为。⑱Tröndle/Fischer,StGB,54.Aufl.,2007,§223,Rn.13.即便如此,本文认为,不能让此种法律逻辑上的医疗行为伤害的预设进入到现实医疗实践的价值判断中,换言之,医疗行为伤害说应当仅停留在法律的逻辑推演中,不可进入一般民众对医疗行为的评价,否则,不但不助益于医患关系的和谐,反而加深医患鸿沟。
(三)患者自主决定人格价值
医疗知情同意规则的核心在于保障患者自主决定权,即患者自己的身体与健康由自己决定。其核心要素在于意思决定自由,即患者在决定自己身体与健康时,不受他人欺诈、胁迫或不法干涉。如果患者受医生欺诈、胁迫而同意接受治疗,通常认为医生侵害患者自主决定权。但在患者因医生非欺诈而为之劝告、通知、说明、介绍时,即便信息有错误或者不充分,进而作出决定,也不能认为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受到侵害。医疗实务上,医生未善尽告知义务,致使患者在不充分的医疗信息下同意接受治疗,就属于这种情形。对此,如果认为此时患者意思决定自由未受欺诈、胁迫或不法干涉,则患者不能因自主决定权受到侵害请求损害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
但实际上,对人身完整性的自主决定,虽然具有意思决定的权利外观,但与物权上的自主处分和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对身体健康与人身完整性的自主决定,除有意思自由成分外,更有人的尊严不因疾病而有减损的意义,彰显其独特人格价值,属于人格尊严延伸,或者具有“知的利益”和“做决定的自由”⑲参见杨秀仪:《论病人自主权——我国法上“告知后同意”之请求权基础探讨》,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07 年第2 期。
(四)规范功能重构
基于上述讨论,医疗知情同意规则在民法上应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医疗行为法律上正当化事由。此种正当化事由并非认为医疗行为本身具有伤害性,而是指当医疗行为固有风险现实化时责任的分担,或称之为医疗固有风险分担功能。二是患者的一项重要权利及人格价值。称之为患者自主决定人格价值。就近亲属医疗同意而言,因其属于知情同意规则的一部分,理应具有上述两种规范功能。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近亲属同意等同于特定情形下患者自己同意,暗含一种法定授权。从权利保障角度,属于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延伸,也是特定情况下对患者权利的保障。从责任分担角度,医疗固有风险非属纯粹患者个人风险,其中身体损害当然只能由患者自身承受,但因身体损害带来的照顾责任和经济负担有不少会由家庭成员承担,因此,近亲属同意不能简单认为是代理患者同意,毋宁说,近亲属同意意味着家庭和家庭成员对医疗固有风险的分担。
二、近亲属医疗同意的适用类型
《民法典》第1219 条第1 款第2 句后段将近亲属医疗同意规则区分为“不能向患者说明型”和“不宜向患者说明型”两种类型。
(一)不能向患者说明型
此种类型指患者欠缺同意能力时,例如婴儿、幼童、精神不济或神志虚弱的人,或者昏迷无法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此时可以由近亲属同意。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患者同意能力的判断基准。
只是一些简单的色素附着或者是一些牙石、色素导致的,可以进行洗牙这样的治疗,去除这些黑色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色素。还有,建议患者可以多吃一些含粗纤维的食物。
民法上与同意能力最接近的当属法律行为制度。民法采定型化行为能力制度,即主要以年龄划分行为能力的有无和范围,辅之以辨认能力标准。实际上,行为能力的有无是事实问题,应当结合行为人年龄、智力及精神状态就具体法律行为进行具体判断,不应设立统一标准。⑳参见梁慧星:《民法总则讲义》(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51 页。考虑到实践中难以贯彻,故采定型化行为能力制度,而法律行为能力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同意则属于行为人对自己权益的处分,非属交易场合,只需要在同意时认识到可能发生的损害,并不需要具有法效意思。㉑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7 页。因此,通说认为,患者的同意能力应基于患者个别的识别能力而非行为能力来判断,不能完全适用民法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
但行为能力制度对于患者同意能力而言,仍具有适用空间。首先,8 岁以下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同意能力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20 条规定,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医疗同意。其次,8 岁至18 岁智力和精神状态正常的未成年人,是否认为欠缺同意能力,不能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9 条,应当引入个别的识别能力标准,也就是在个案中就患者个别的识别能力进行具体判断。㉒参见孙也龙:《医疗决定代理的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18 年第6 期。只要具有识别能力,仍可以进行有效的同意,而不是必须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但对于重大医疗行为,通常认为须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此重大医疗行为和患者个别识别能力的判断应交由医生。关于未成年人的代为医疗同意,荷兰《民法典》规定具有参考价值。荷兰《民法典》第7 编第450 条第2 项规定:“患者为12 岁至16 周岁的未成年人时,亦应取得有监护权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但为避免患者遭受严重伤害,虽未取得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仍可以进行医疗处置。于父母或监护人拒绝同意时,如经病人谨慎考虑后,仍愿进行医疗行为的,亦同。”第447 条第1 项规定:“16 岁以上未成年人,因其已具备医疗契约之行为能力,自己成为得为同意之人,得单独同意医疗处置行为。”㉓法条英文版见网站:http://www.dutchcivillaw.com/civilcodebook077.htm,译文转引自陈聪富《:医疗责任的形成与展开》,台大出版中心2019 年版,第146 页。最后,对于成年人则完全适用个别的识别能力标准。换言之,即使是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人患者,在具体情况下欠缺识别能力,则无同意能力,应由其近亲属同意。反之,应由患者自己同意。
比较法上,英国《心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2005)就同意能力认定一般标准包括“诊断标准”和“功能标准”。诊断标准指的是有大脑损伤或者大脑功能障碍。功能标准指的是因大脑损伤导致个体不能自主决定。㉔参见[英]乔纳森·赫林:《医事法与伦理》,石雷、曹志建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08 页。后者强调的是,如果一个没有大脑损伤的患者拒绝所有治疗,仍然认定其具有心智能力。
(二)不宜向患者说明型
此种类型主要基于保护性医疗理念。为避免和减少对患者的影响,医务人员常须就患者个人隐私、病情、治疗过程等采取一定程度的保密等保护性措施。如针对癌症晚期患者,出于保护患者情绪和精神状态的考虑,不向其说明真实病情和治疗措施,而仅向家属说明。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立法上早有此概念,如2008 年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 条第2 句规定“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保护性医疗的伦理基础是医生行善原则,在我国,主要是家庭主义医疗传统的体现。但实际上保护性医疗是在特殊情况下将患者本人的医疗决定权经由医生斟酌裁量而移交于患者近亲属。㉕参见李欣慧、李明:《我国保护性医疗制度及其存在的法律问题》,载《医学与哲学》2021 年第2 期。这与强调患者自主权的医疗知情同意规则相悖。原《侵权责任法》第55 条只规定“不宜向患者说明”类型,与患者本人知情同意相并列,说明在“不宜”场合,患者近亲属的同意视为患者本人的同意。但“不宜”二字非属规范用语,其适用的具体范围、手段、方式、程序等不明确,虽医疗实践中多适用于末期患者和绝症患者,但实际上判断标准难以界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主观性较强。如果说“不能向患者说明型”还有基于患者具体识别能力的考量,那么“不宜”型则主要基于医方从专业角度的主观判断。因此,要严格该类型的适用情形,并且在出现合适的可以告知患者本人真实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告知患者本人,回归到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
需要说明的是,保护性医疗理念是否属于医疗实践中的惯例。日本最高裁判所1995 年在一起医疗纠纷案件中认为,对于某癌症患者医院未告知其病情真相不属于未尽告知义务,实际上是认可医疗惯例,限制患者知情同意的适用。㉖参见[日]能见善久:《日本法中的医疗责任》,赵廉慧译,载《判解研究》2007 年第1 辑(总第33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 页。我国将“不宜向患者说明型”规定在条文中,可以说是将医疗惯例法律化。就其适用效果,如上文所述,不宜扩大其适用范围,否则患者自身知情同意将空洞化,但是否认定为立法上的不足,还需审慎考虑。其一,保护性医疗理念不仅是医疗惯例,也是医疗领域的立法惯例,同时是传统东方社会人情交往善意原则的体现,不能因为其确定性不足而主张删除。其二,法条中并非说不宜向患者说明就减轻或免除医生告知义务,而是必须向患者近亲属告知,并非剥夺患者的知情权,应该是患者的直接知情权变成了间接知情权,而同意权改由近亲属行使。此为医疗惯例上升为法律规范后的改良,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其三,随着我国患者权利意识的不断提升,医学知识的不断普及,医疗技术和水平的不断进步,不宜情形在医疗实践中的适用会自行减少。试想十年前听到的癌症多为不治之症,如今一些常见癌症已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患者自身的可接受度也在提升。如果一味认为保护性医疗是陋习,应当摒弃,看似有利于患者自身权利保障,实则某种程度上加重患者负担,也不符合我国社会生活实际。
(三)近亲属的范围
对于近亲属同意的主体范围,医疗卫生领域立法曾经有过“家属或关系人”的表述。㉗比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 年)第33 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执业医师法》(1999 年)第26 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从实务操作来看,因欠缺规范性和确定性,近几年相关立法都陆续修改为“近亲属”的表述。对于近亲属的范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一般规定中的第1045 条第2 款作出了界定,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值得说明的是,位于侵权责任编的第1219 条是否一定要适用第1045 条第2 款关于近亲属的规定。有学者认为,第1045 条第2 款的规定本质上属于婚姻家庭法的范畴,并非所有关于近亲属的规定都要作统一适用,应根据相关制度的立法目的进行具体解释。㉘参见陆青、章晓英《:民法典时代近亲属同意规则的解释论重构》,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本文赞同该观点。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法概念的相对性”能够修正“法秩序的统一”这一原则,且此种修正不仅表现在不同法律中,甚至在同一部法律中,概念也可能需要作不同的解释。㉙参见[德]托马斯·M.J.默勒斯《:法学方法论》(第4 版),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6 月版,第329 页。“近亲属”概念在《婚姻家庭法》和《侵权责任法》中功能不尽相同,或者说重要性不能等同,因此并非要完全进行一致解释,但第1045 条第2 款对近亲属范围的界定对于此处的适用仍具有规范意义。
具体而言,可区分三种情形。第一,如果8 岁以下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同意能力类推适用《民法典》第20 条规定,就会出现法定代理人范围比近亲属范围窄的情况,法定代理人指的是监护人,通常就是父母。因此,针对8 岁以下未成年人,可为医疗同意的近亲属范围应限定为法定代理人,此种解释既符合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也符合保护低龄未成年人的目的。但有疑问的是,当父母没有同意能力或不在场时,能否类推适用《民法典》第27 条第2 款关于监护人顺位的规定。应区分不同情况来看,在父母没有同意能力且丧失监护能力的情形,直接适用第27 条第2 款,此时不存在类推适用;在父母没有同意能力但未丧失监护能力的情形,比如父母酒醉未醒或父母重病意识不清时,应类推适用第27 条第2 款;父母不在场且无法联系上的场合,应类推适用第27 条第2 款,由祖父母、外祖父母行使同意权,祖父母、外祖父母无同意能力时,由有同意能力的兄、姐行使同意权,若后期联系上父母,应告知父母并取得其同意;父母不在场但可以联系上的场合,理应取得父母的明确同意,但可由在场的其他近亲属代为签字。第二,8 岁至18岁具备识别能力的患者,对于重大医疗行为,可代为同意的主体范围应与8 岁以下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一致。第三,8 岁至18 岁不具备识别能力的患者和成年不具备识别能力的患者,可代为同意的主体范围应与第1045 条第2 款的近亲属范围相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在极端情况下,若患者无一近亲属,仅有长期同住照顾的“关系人”,如保姆或未婚伴侣,该“关系人”能否实施医疗同意。我国立法上基于保护患者利益和防止同意权滥用考虑,对于可代为医疗同意的主体范围进行限缩,从实施效果来看,有助于规范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但确实存在不便之处。针对上述极端情形,可区分三种具体情况对待。第一,与成年监护制度衔接。当该成年患者已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时,根据《民法典》第33、35 条规定,可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由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代理进行医疗同意,但应当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第二,当该成年患者非属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却无识别能力时,实践中医院往往会在对患者进行医疗行为前,要求患者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由特定主体代为作出医疗同意㉚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2 民终6046 号民事判决书。,此时应当尊重患者的意思自治。若患者选择“关系人”代为医疗同意,医院应当尊重。第三,如患者在入院时已陷入无意识状态,无法取得书面授权委托书,此时应适用《民法典》第1220 条关于紧急情况下知情同意的特殊规定。
三、近亲属医疗同意的法律性质
(一)推定的同意
有学者认为近亲属的同意属于推定的患者同意。㉛参见魏超《:论推定同意的正当化依据及范围——以“无知之幕”为切入点》,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2 期。所谓推定的同意是指现实中没有当事人的同意,但如果当事人知道事实真相后当然会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对当事人一致的推定所实施的行为,属于基于推定的同意行为。㉜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8 月版,第301 页。这种同意被认为是法益主体的一种“拟制意志”,是一种规范的结构,而非真实的意志。㉝参见车浩《:论推定的被害人同意》,载《法学评论》2010 年第1 期。推定的同意阻却违法的前提是,无法取得或者无法及时取得患者的承诺。构成推定的同意须符合以下要件:(1)法益的可支配性;(2)承诺人的处分权限;(3)承诺人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4)患者未作出承诺;(5)干预符合患者的假定意愿;(6)主观的违法阻却要素。㉞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医疗刑法导论》,王芳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43 页。
(二)推定的同意的参考资料
有学者认为近亲属的同意应属于患者推定的同意的重要参考资料。㊲参见王皇玉:《强制治疗与紧急避难——评基隆地方法院九十五年易字第二二三号判决》,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51 期。认为在推定的同意概念下,已经隐藏替代不理性当事人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而所谓理性的决定则取决于利益衡量的思考。因此,家属的意思应属于患者的理性决定与利益衡量的一项参考资料。㊳参见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元照出版社2006 年版,第359-360 页;车浩:《论推定的被害人同意》,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1 期。基于该观点,当法定代理人与配偶间或同顺位近亲属之间对患者是否进行治疗发生不同意见,比如该医治而不医治,医生可基于患者可推测的同意,违反某些近亲属意愿而为治疗行为。就理性患者而言,近亲属对其作出的不利的医疗意见,患者不应受约束。也就是说,近亲属无权作出与理性病人意见相违背的意见。正如学者所言,当一种侵犯如此密切地触及人格的核心,这种允许是一种不能代表的决定。㊴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 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16 年12 月版,第375 页。
(三)理性患者的判断基准
通常认为,近亲属的同意意见应基于理性患者的考量,或者应最大限度尊重患者的真实意愿。所谓理性患者指的是该患者在作出是否进行某项医疗行为决定时,已经对该项医疗行为具有实质重要性的危险有充分了解,是在掌握了重要的医疗信息基础上衡诸自身情况所作出的决定。㊵参见杨秀仪:《美国“告知后同意”法则之考察分析》,载《月旦法学杂志》2005 年第6 期。也就是医生在告知时基于客观上患者对于医疗信息的需要,并考量医生的适当裁量余地,形成的客观标准。
(四)我国应坚持推定的同意说
我国目前理论和实务界通说采推定的同意,从《民法典》第1219 条表述来看,也是认可近亲属的同意与患者本人同意具有相同的效果,即认可推定的同意。㊶同前注㉛。但我国台湾地区有改采推定的同意的参考资料的趋势,其目的在于规避近亲属对同意权的滥用,主要情形是当近亲属意见重大且明显损害患者利益时,医院可不采纳。
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应坚持推定的同意说。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从法条文义及条文变迁来看,我国始终坚持患者的同意与近亲属的同意具有同一性,早期立法甚至将患者同意与家属同意并列,并须同时具备。这主要基于自古以来根植于中华文化中的家族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认为,家族中个人的生老病死、兴衰荣辱是属于家族事务,而非单纯的个人事务。㊷参见陈传勇:《医疗知情同意权的合理配置》,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1 期。实际上,即便是患者本人同意,通常情况下,意见的形成也是基于家庭成员的共同讨论和决定,而近亲属同意,在非紧急情况下,也多数是此前已经家庭成员讨论。因此,近亲属同意应当与患者本人同意具有相同效果,性质上就属于推定的同意。
其二,从与患者本人同意的关系来看,立法和实践逐渐纠正了过去家属同意代替患者同意,患者和家属同时同意,以及患者或家属任选其一同意的不明确状态。增加了“不能向患者说明型”,更强调患者本人的同意,使得我国医疗知情同意规则更接近保护患者自主权的本旨。但是,是不是说明我国形成了近亲属同意为补充的“补充同意模式”,㊸同上注。值得讨论。本文认为并未形成该模式,原因有二:一是适用近亲属同意的情况并非少数。“不能”和“不宜”情形的判断多数是医生基于具体情形的经验判断,法律规范在此仅具有指导意义,无强制性,亦无检验功能。因此,从适用比例上来看,不能认为近亲属同意是例外。二是医疗实务中,医院往往会要求患者签订委托授权书,将自己的同意权分配给特定近亲属或者直接由特定人行使,此时的近亲属同意因具备了委托授权,产生了代理的效果,实际上变成了患者本人同意。换言之,近亲属同意在具有授权的情形,并非患者本人同意的补充。既然不是补充,那么第1219 条中的近亲属同意,性质上就应属于推定的患者的意思。
其三,基于反面解释,若近亲属的同意属于可推测同意的参考资料,亦即医生可以基于专业判断或医生推测的患者本人的同意,而不听取近亲属意见,这其实是让医生陷入风险和不确定状态。若治疗之后患者恢复一定健康,但产生高昂费用,患者术后表示若是知道这样让家庭背上沉重负担,自己会选择不治疗,那么费用承担问题如何解决?若治疗后患者恢复意识,但有后遗症,该损失是由患者自行承担还是医生承担?因此,宜认定近亲属同意等同于患者本人同意,通常情况下,医生不得推翻。
但是,采推定的同意说存在当近亲属意见明显违背理性患者意见时的处理问题。此时涉及近亲属滥用同意权的判断和法律适用,下文详细论述。
四、近亲属滥用同意权的法律适用
近亲属滥用同意权通常指近亲属意见重大且明显损害患者利益。一般来说,指的是该医治而近亲属不同意医治情形。对于近亲属执意要医治情形,难谓滥用同意权,因为不能做医疗行为恶意的假设。因此,对于近亲属滥用同意权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紧急情况下近亲属拒绝治疗,二是非紧急情况下近亲属拒绝治疗。
(一)紧急情况下近亲属拒绝治疗
在紧急情况下,患者本身无法做同意与否的表示,而患者近亲属表示不同意继续治疗时,医生是否应依据近亲属意见而停止医疗行为。此时,患者病情紧急,无法表达意见,如果不予以治疗,可能立即死亡,而患者近亲属拒绝治疗,但并非患者本人表示拒绝治疗。医生将陷入理性病人意见与家属意见二者不一致的抉择难题。此时,是否可适用《民法典》第1220 条进行紧急诊疗,关键在于近亲属拒绝治疗是否属于该条规定的“不能取得近亲属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 号)(以下简称《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解释》)第18 条规定了不能取得近亲属意见的情形“(一)近亲属不明的(;二)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的;(三)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四)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其中第一、二种情形属于客观不能,显然不能适用,能否适用第三、四种情形,从文义解释上,此二种情形属于主观不能中的近亲属意见不明确,而非近亲属明确拒绝,实难进行涵摄。对于此问题,学理和实务多有分歧。学理上有观点认为,此处的“不能”仅指客观不能,不包含主观不能。㊹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643 页。在立法机关释义书中可以看到,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建议在“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意见”后增加“或者近亲属意见明显不利于患者”,但最后没有被采纳。对此,立法机关的解释是,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情况多种多样,比较复杂,如果一概规定医疗机构可以实施强行治疗,不但违反了意思自治原则,同时对患者及其家庭也不一定有益。㊺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54 页。
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认为,应当对“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意见的”情形进行扩张解释。例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指引》第36 条规定,当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近亲属的意见不一致且形不成多数意见的,以及近亲属的意见明显不利于患者利益时,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为挽救患者生命,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指引》(2015 年)第36 条规定“:下列情形,患者生命垂危且不能表达意见,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为挽救患者生命,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一)近亲属不明或者无联系方式的;(二)有联系方式但联系不到近亲属的(;三)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四)近亲属的意见不一致且形不成多数意见的(;五)近亲属的意见明显不利于患者利益的;(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前款情形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怠于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造成患者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有观点认为,医疗机构在是否采取紧急救治措施上,患者近亲属的意见重大且明显地损害患者利益时,医疗机构应当拒绝接受患者近亲属的意见。㊼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年版,第404 页。
本文认为,对于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紧急情况,医生应就患者的身份、年龄、病史、当时的病情,参酌患者曾经表示的意思等,基于患者最大利益原则,作出医疗决定,实施紧急诊疗行为。如果医生认为,依据理性病人的决定与患者近亲属意见相同的,比如,患者年事已高,病情严重,患病时间长久,生不如死,曾经表示不愿再给子女增加负担,可依据患者家属的意思,不为医疗行为。但如果患者家属的意见重大且明显损害患者利益时,医生应基于患者本身可推知的意思,为患者进行医疗行为,而此时近亲属的拒绝治疗应认定为同意权的滥用。《民法典》第132 条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效果以承认权利存在、否认其行使为原则,具体而言,权利行使为民事法律行为应认定无效,为事实行为应禁止或停止该事实行为。㊽同前注⑳,第220 页。对于近亲属同意权,基于前述论证,其为推定的患者的同意,也就是在患者不能或不宜作出医疗决定之时,近亲属的同意视为患者同意,可认为属于近亲属拥有的一项合法权利,理应受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约束。通常来说,认定权利滥用应由司法机关来判断,不能交由权利人或相对人自行判断。但本文认为,在近亲属意见对患者有重大不利益时,应赋予医生根据其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近亲属构成权利滥用而不采纳近亲属意见的权利。此时,医生虽面临评估患者意见的难题,但这既属于医生的紧急救治义务㊾《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27 条第1 款:“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也属于对于患者温暖的关照,为医疗伦理中行善原则的表现。㊿参见陈聪富:《医疗责任的形成与展开》,台大出版中心2019 年版,第192 页。因此,在“肖志军拒签事件”中,患者关系人肖志军拒绝签字以及卫生行政主管人员的指示,使得医生发生错误认识,误认为自己并无行剖宫产进行紧急救治的义务,或者误认为自己不进行救治有违法阻却事由,但实际上,这种错误认识在民法上无法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但拒绝治疗行为对于患者的死亡具有原因力,可依据过失相抵原则,减轻医生的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在2013 年增订医疗契约条文时,在第630 条之4 第1 项第4 句规定:“急迫措施之同意无法适时取得时,得依可得推知之病人意愿,于无同意情形实施。”51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德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589 页。
(二)非紧急情况下近亲属拒绝治疗
在非紧急情况下,医生履行告知义务后,近亲属表示不同意继续诊疗。此时因为情况非紧急,不为继续治疗不至于造成患者重大损害或生命危险,不宜认为是权利滥用。比如肾结石患者疼痛难忍,但不至于威胁生命,近亲属不同意手术治疗,此时医生应尊重近亲属意见。医生依据近亲属拒绝治疗的意见而不予治疗,就属于患者推定的同意,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即使产生损害,也无须负赔偿责任。不治疗虽不至于发生生命危险,但对患者有重大不利益,是否可认为患者近亲属意见属于同意权的滥用,值得讨论。
医疗实务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医生为避免陷入患者和近亲属意见相左的两难境地,不告知或不充分告知,而进行手术或特殊治疗手段。如果事后患者治疗效果良好,一般不会产生分歧,如果事后患者治疗效果不好,在多数医疗纠纷案件当中,5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申7965 号民事裁定书。因无法证明不告知或不充分告知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适用2021 年生效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解释》第17 条5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 条规定:“医务人员违反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义务,但未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这里涉及医生违反知情同意的告知义务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对此,学说上存在主观说、客观说、修正的主观说。主观说认为此时因果关系的判断应依据患者的个人情况。54Buchan v.Ortho Pharmaceutical(Canada)Ltd.,(1986)25D.L.R.(4th)685.客观说认为应以理性患者作为判断标准,但同时也须考量患者的特殊情境。55See JONES,supra note17,at556-557.修正的主观说认为应采主观说,但必须考量客观上的评价。56See JONES,supra note17,at562.我国司法实务中,有判决认为“医方虽然术前对脑梗塞的发生、术式的选择上沟通不充分,但是根据患者周某某双膝关节病变情况,市一院选择双膝关节置换术有手术指征”,57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7 民终1536 号民事判决书。“周某某术后脑梗塞并非市一院未尽说明义务所致”58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申7965 号民事裁定书。。从该判决来看,所采立场为客观说,也就是以理性患者为判断标准。但也有判决认为“违反告知、说明义务的过失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与其他诊疗行为的过失不同,其通常不会造成人身的损害,而是表现为在医师充分告知的情况下患者若作出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与实际发生的后果之间的差额。若两种后果之间不存在差额,或实际后果比作出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要好,则可认为不存在损害后果,医方不必承担赔偿责任”。59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 民终129 号民事判决书。应该说,该判决所采立场为修正的主观说。
医疗实务的现状和司法实务的立场,实际上会变相成为医生不履行或不充分履行告知义务的理由,长此以往,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会加剧。对此,学说上出现二行为理论,即医生在实施治疗前的告知说明行为与后续医疗行为属于二行为,各有其行为标的、义务与责任。60同前注⑮,第42 页。根据该理论,告知说明义务履行责任的基础在于保障患者自主决定权,而后续医疗行为责任基础在于保障患者接受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行为,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责任,不能等同。亦即,如果医生违反告知说明义务,但后续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不得以违反知情同意规则推定医疗行为可归责。本文赞同该观点,应该说从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结合来看,有采此意的倾向,理由如下。其一,《民法典》第1219 条第2 款规定医生违反知情同意规则的请求权基础,但何为“造成患者损害”需要进一步明确,《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解释》第17 条明确规定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始得请求赔偿责任,对“损害”进行了具体化。但是司法实务上对于二者间的因果关系仍有不同理解。如果僵化地认为需要未履行知情同意义务直接造成人身损害,则该条将无法适用,因为所有的损害只能是由医疗行为产生。如果认为不同手术方案的选择将产生不同后果的差额属于损害,虽然更具合理性,但是证明和说理难度较大。但如果只要医生存在知情同意的履行瑕疵就认定损害,则又过于扩大医生责任。因此,将知情同意义务与后续医疗行为进行二行为的分隔讨论,具有精确划分责任的优势,值得肯定。其二,从客观医疗实务上看,患者并非听取医生告知说明后就一定会接受后续医疗行为,期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使得二行为并非一定前后相继发生,因此二行为理论是符合医疗客观实际的。其三,从造成患者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进程来看,违反知情同意规则的行为只是制造了患者法益侵害的可能性,需要患者或近亲属作出同意而实施后续医疗行为才可能发生人身损害的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非紧急情况下,如果近亲属拒绝治疗的意见对患者有重大不利益,同样应认定近亲属同意权滥用。当然,为避免某一个医生的专断,应有一定的程序保障,比如经科室综合诊断形成意见等。此时应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220 条,认定此情形属于“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紧急情形,医生可以基于患者的推定的同意,违反近亲属表示的意愿而为治疗行为,无需承担因知情同意规则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当然,如果后续医疗行为存在过错造成患者损害,则应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