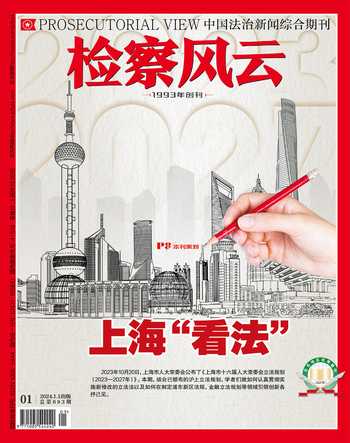对上海金融立法规划的若干建议
2024-01-12倪受彬
倪受彬
中国的金融立法应该伴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换言之,金融立法计划和内容应该建立在对金融业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而且这种理解一方面要回应金融乃至实体产业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在借鉴历史、他国经验乃至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期性。因此,上海未来的金融立法应注重体系协调和趋势把握。
所谓的体系协调包括既有立法的存废改立之间的关系。要在立法评估的基础上,从法律的内容、立法审查和矛盾协调的各方面对现有金融立法及其他立法中的金融制度规范和协调的方面进行梳理,防止法律内容之间的矛盾,以安定法律之间的内在秩序。此外,应注重“特别法和普通立法”之间的协调,即浦东引领区立法,长三角创新实验区、临港新片区、自贸试验区在外资进出、结算账户等制度创新、行政执法便利措施等方面,与一般立法之间的协调。一方面要增强法律实验效果,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制度套利。根据立法法金融事权属于中央,要做到央地协调。当然,上海可以发挥地方立法权限,在立法权限中通过引入国际高标准(软法)的适用来提升自己的立法能级,从而发挥金融改革立法试验田的作用,为全国性的金融立法探索新的经验。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的修订完善已列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未来五年立法规划(2023—2027年)。
此次《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的修改,应该从原来的宣示性立法向促进性和功能性立法转变;应该加强这部法规对未来金融立法的统摄作用,成为未来金融立法的主干线,包括金融基础设施立法、金融开放的制度安排;应该从“国际化”的制度功能实现和保障方面做文章,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国际高质量资本(长期投资基金)在上海集聚——其中包括外资汇兑的自由化便利化,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的真正落地,合格投资者等政策从试点到全面落地的制度衔接和改革;此外,在临港新片区,从新兴金融创新的角度更应通过对接全球最高贸易金融规则方面进行真正探索和落地,包括国际组织惯例规则等置入交易条款,在司法上推进跨国的承认和执行安排,以增强金融法渊源的国际化。

未来的金融立法应注重体系协调和趋势把握 (图文无关)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绕不开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核心命题。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立法还要探索在岸人民币市场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互动。此外,在人民币双边和多边结算方面也应进行制度創新。
《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已经纳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未来五年立法规划(2023—2027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条例的评价功能和引领作用不容忽视。而金融作为服务业,服务能力、安全水平和产品设计能力本身又是产业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上海目前的金融服务水平和开放程度离一流金融营商环境的构建尚有一定的距离: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价是以市场成熟为逻辑前提的,即竞争的市场化和产权的多元化为基础;而上海目前金融竞争程度和产权多元化还存在不足。笔者建议,未来上海的金融立法应该从市场主体的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角度入手,增加金融市场的活力和竞争程度,开放更多金融领域给外资和民营企业,打造充分发挥金融作用的制度基础。
上海的金融立法应着眼于科技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要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对未来金融业态的重塑作用,从而从制度创新、风险研判和企业合规等方面进行制度构造。上海的金融立法要与现有的数据立法、人工智能立法等相衔接,将上海建成科技金融的高地。科技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用会极大地改变金融业原有的交易模式、监管方式和金融风险样态,科技金融本身属于价值中立,关键在于科技金融如何应用。一方面,科技金融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金融的地域性和时间维度,使得金融的普惠性增强;另一方面科技金融本身就强化了金融的跨市场性和地理依存性,使得金融监管变得更为复杂。所以,要善用科技手段研判和预测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情况通报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市场规律,保护金融投资者的金融隐私和金融利益,防止危害金融伦理的金融监管用力过猛和公权力的滥用。
上海具有很好的自律监管条件。应该将自律监管和他律监管,国内金融管理和国际金融自律组织的作用关联起来。上海的金融同业公会、银行业同业、证券基金同业、金融调解中心等组织的金融自律功能应该在立法中被很好地激活;从经费、制度保障和自律意见的应用等方面探索出真正市场化和内部治理的金融业组织共同体;与国际金融自律组织的合作也应纳入未来立法的计划中。上海应该积极加入全球金融自律规则甚至全球标准的制定,在软法和金融多元化制度创设中发出中国声音和上海声音,在利率定价机制、大宗金融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创设与修改中发挥大国金融和全球主要市场的话语权。
近些年,上海的绿色金融立法进入了快车道。继《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推出后,《上海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条例》也将正式出台。此外,上海在碳市场建设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合规等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上海还在转型金融安排、长三角一体化金融安排、气候投融资试点方面与全球主要城市进行合作和竞争。随着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推进,上海将来的金融立法必须回应和顺应全球绿色转型的需求。
上海可以发挥地方立法权限,在立法权限中通过引入国际高标准(软法)的适用来提升自己的立法能级,为全国性的金融立法探索新的经验。
未来的金融立法应该考虑到产业绿色转型和金融业本身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一方面,上海应利用现有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应加强金融立法的安排,包括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金融绿色统计和监测制度等;此外,气候投融资领域的金融立法也应落到实处,包括境外绿色债券发行、境外主权财富基金入股境内绿色项目和退出安排,金融机构环境责任等方面。
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内在地要求其必然也应该是纠纷解决中心。高质量的裁决服务能力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业聚集。上海现有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包括金融法院、金融仲裁机构、金融同业调解、商事调解中心、诉调对接等。但是,这些机制还无法起到多元化解机制的作用,无法分流法院的案件,各机制之间的联通机制尚未形成。未来的金融立法应该着力打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堵点并形成漏斗式的纠纷筛检机制。上海的示范判决就是很好的制度创新。
此外,上海还应积极引入国际组织和国际人才参与上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积极利用《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等制度安排和经验,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韧性和弹性。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