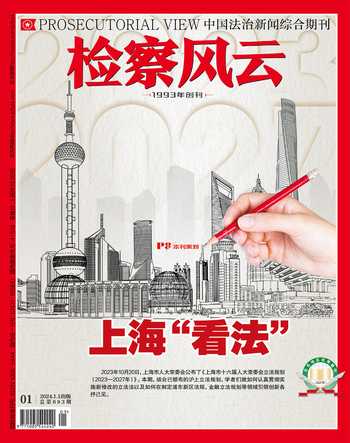创新与边界:探索地方立法权的实践空间
2024-01-12王桦宇韦欢芫
王桦宇 韦欢芫

上海市在全國率先形成了“1+X”的地方性法规集群 (图/IC photo 图文无关)
2023年3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立法法自2023年3月15日起施行。这次修改是继2015年3月15日立法法首次修改之后的第二次修改,特别是在对第七十二条进行修改后,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相较此前规定,将地方立法事项的环境保护扩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并新增了基层治理作为地方性立法事项。与此同时,立法法的此次修改还就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事项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新的历史时期,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按照立法法的要求高质量地完成地方性立法工作,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我国宪法第一百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这一规定是我国地方立法权的基本宪法渊源,也是前次和此次立法法修改的主要制度背景。不过,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我国的具体立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重要立法都是中央立法,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央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等诸多层次;在地方立法方面,包括省级地方在内的各级地方不仅在总体上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涉及的相关领域也不够丰富,层次体系也不够清晰,立法质效相对不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成为立法工作的主要指导原则。建构科学合理的中央和地方立法体系,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宪法框架下推动地方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创新,适度放宽地方立法权限,使地方治理需求与立法权限范围大体一致,为不同区域的立法主体留出充分的制度竞争空间,能够促使地方改革走上法治轨道,激发地方上更多的制度创新积极性。拓展地方立法权的立法空间,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整体立法领域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特别是鼓励地方在属地治理上进行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有利于在中央现行立法基础上进行“因地制宜”地细化与展开,提升上位法执行的针对性、可实施性和可接受性。应该说,地方立法权是对中央立法权的必要补充和具体展开,相关地方立法体系也是国家整体立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全面准确理解地方立法权,首先应当从国家法制统一性这个角度来把握,不能过于强调地方立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就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关系而言,中央立法权是宪法规定的当然立法权,由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行使,而地方立法权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特定的事项领域、地域区划等范围内得以行使并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还需要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地方立法权的行使需要严格遵循法律的有关规定,在不与上位法冲突和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法律执行的适应性、属地管理的创新性、基层治理的多样性等方面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与此同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立法权也需要积极作为、主动担当,有效补全地方立法权的实践短板。此次立法法修改,上海、海南等地的地方立法权还被写入具体的法律条文中,作为两个地方的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明确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区实施。”也就是说,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在两个层面行使地方立法权:一是普遍意义上的地方立法权,就作为省级层面的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一立法主体制定不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二是特定意义上的地方立法权,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就浦东改革创新实践需要,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区实施。
就第一个层面而言,近年来上海市积极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和路径,在全国率先形成了“1+X”的地方性法规集群,先后制定修改《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结合上海市的具体情况在营商环境、地方金融监督、知识产权保护、中小企业促进和公平竞争的方面制定了上海规则;就第二个层面而言,相继出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深化“一业一证”改革规定》《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上海市健全浦东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等18部浦东新区法规,涵盖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促进自主创新、发展绿色生态、深化城市治理等五大领域,有力地推动了浦东引领区与自贸试验区双区联动发展战略。
上海地方立法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和宝贵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上海市如何推进高质量的地方立法工作,推动更多的浦东法规、上海法规能够在试点成熟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也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除了一些全国各地方立法权行使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外,主要涉及上海地方立法权的总体定位问题,因为总体定位决定了立法方向和技术路径。上海既是一个省级行政区,有权行使省级层面的地方立法权,制定省级层面的地方性法规;又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需要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体现城市特色,承担因地制宜地规范和指导城市治理的立法功能;上海还是一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而拥有浦东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主体,需要更多的探索试点和改革创新。因此,如何准确认识自身地方立法权的定位,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和精准推进这些立法模块就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五年里,上海将紧密围绕“四大功能”布局,在深化改革、城市治理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有所作为,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法治“施工图”。
2023年10月20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23—2027年)》。规划围绕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创造高品质生活和实现高效能治理六大方面展开。这些地方性法规,一些是针对省级行政区的经济社会行政管理事项,一些是涉及国际大城市的历史文化、绿色发展和基层治理的品质内涵建设,一些是紧密联系浦东新区改革创新、先行先试进行实践的立法项目,较好地回应了上海地方立法权的总体定位问题。
(作者王桦宇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韦欢芫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