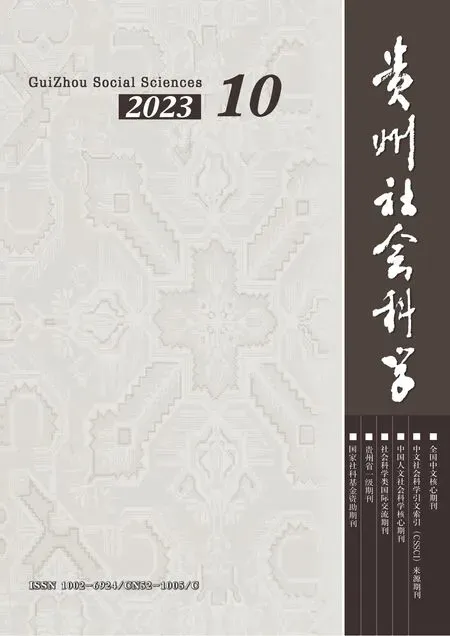论宋代“文化重置”
——以宋徽宗与皇权审美意识形态为例
2024-01-09张节末
张节末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一、宋代“文化重置”的发生
“文化重置”[1]是有宋一朝的特定文化战略,通过向中国文化之早期核心回归,宋代文化的定位和品格相较于汉、唐发生了跨越式的基础之变。“重置”是非历史的、非革命的、渗透性的重大文化突破,即通过回溯蓄力,为前行开辟道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于宋代进入了近代,从唐至宋,国家社会人群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间箭头。然而宋代却是一个上下一致求复古的朝代,其经典诉求是“回向三代”(夏商周)。
宋儒所提出的跨越汉唐儒学而直接承续思孟之道统说,可以视为宋代“文化重置”的思想史路径。道统论是关于中国文化核心合法性的论辩。孟子曾经排出一个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和孔子的圣人谱系,称他只是听闻孔子的教诲而已。言下之意,儒家学术之统到他以后就中断了。一千年以后,唐代的韩愈重新连接了这个传承谱系,他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2](《送王埙秀才序》)钱穆称“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3],唐到宋的儒学谱系保持了连续性,是因为有了韩愈。
宋儒大不满于汉唐两代的儒家没有防住“二家”即佛教和老庄之学,动摇了中国文化的根基。韩愈虽然提出了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核心,却未能拿出重磅的文献依据。朱熹决绝地提出,儒家的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颢、颐)上承孟子的,他谈到《中庸》时强调:“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4](《中庸章句序》)程氏兄弟把《中庸》挖掘出来,加以考订,重新整理面世,使得“千载不传之绪”得以接“续”下去。所谓的“续统”,意味着奋力向中国文化的早期核心回归,这就是复古,它是文化的重光。朱熹认定,一旦文献依据被找到,纯正的“道统”必须跨越汉唐而直接思孟。儒学在宋儒手里的复兴,就是中国思想史传统的“文化重置”。
然而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辉煌的大帝国,若是“道统”意在跨越它们,那么两大帝国的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也能跨越吗!宋儒似乎以为,《中庸》之复现将被视为中华历史的新起点,不得不说,此一观念是收缩性的,非连续的,甚至是非历史的。然而,宋儒又坚信,只有完成了向中国早期思想的回归,以此为基点,才可能开启新的不同于汉唐两大帝国辉煌文化的更为辉煌之文化融合。宋代整体面临重估,我们要重新掂量宋代文化的意义和性质。
“文化重置”是宋代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化运动,近世前进之潮流与复古回溯之退却构成了方向相反的文化引流与回归,如何化解冲突并推动文化改良,是宋代文化的基本格局。皇权的强化导致日益上升的中央集权倾向、科举制的推行养成了庞大的士群体作为文化中坚,城市化和商业模式培养了新的市民阶层,这三股力量的汇流,使得社会结构扁平化了(1)在宋代的文化阶层中,因为中央集权,门阀世族和藩镇是没有生存和发展空间的。。阶层之间固然存在差异,不过因为博弈而得到弥合,成为聚合的胶合剂而非分裂因子,文化结构变得紧致起来,“文化重置”获得了土壤。
审美意识形态在“文化重置”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观察宋徽宗所主导的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三个例证,看到了不同于宋儒思想史“文化重置”的另一种博弈式的“文化重置”,在此,文献并不那么具有决定性,而非理性的感觉与祥瑞之征则占了上风。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切近地了解在不可阻挡的近代化潮流下,皇权审美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复古这一看似倒退的文化政策以实现“文化重置”的。
二、徽宗改乐:适时之宜,以身为度
《宋史·乐志》云:“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5]293,北宋9位皇帝中有6位亲自主持了音乐改制,其中针对古琴的规制、器形、弦数与乐律实行三番五次的改造,尤以宋徽宗大晟乐的改制最为全面细致。显然,改乐是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一件大事。然而,所有的改乐操作最后居然是以徽宗对乐曲的主观之听觉判断而告一段落。乍一看,政治与美学之间,美学获得了优先性,复古似乎仅仅是一个口号。其实不然,若是将改乐作为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一个个案来观察,是极富理论探讨价值的。整个改乐过程,皇帝与包括乐官在内的群臣之间,发生了有趣的博弈。
宋代尚书礼部员外郎陈旸作《乐书》,他对神宗说:
臣闻,先天下而治者在礼乐,后天下而治者在刑政。三代而上,以礼乐胜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胜礼乐,而民风偷。是无他,其操术然也。[6]
这里,可以注意三点。一、礼乐“先天下而治”,它比“后天下而治”的刑政更重要,这是审美意识形态优先论。二、“三代”以下礼乐之治就失去了优先权。三、如欲当代民风醇厚,就要跨越一切“以刑政胜礼乐”的时代,复三代之古。这就是“文化重置”。
在必须复古的战略和紧迫感上,宋代的君臣取得了一致。然而在具体操作时,则容易发生技术上的分歧。如宋太宗与琴待诏朱文济因“古琴弦制”发生争议,古琴原为五弦,后来太宗效仿文武王将五弦古琴改为七弦,复又命再增加两弦,如此制成九弦琴。他说:“琴七弦,朕今增之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5]2944这是直接把音乐与政教等同了,则在审美意识形态上就不免有所亏。作为古琴专家,朱文济则以为七弦足以满足演奏功能,就不肯在殿上演奏九弦琴,以至于不得已在九弦琴上只以七弦演奏曲子。(2)除宋太宗外、徽宗外,还有仁宗制两仪琴、十二弦琴、高宗制盾形琴,神宗以琴事纳贤,神宗时亦改乐制,突出琴声,以防“金石夺伦”等。
宋徽宗制大晟乐,新创一个五等琴,用于大晟乐的祭祀与朝贺。他接着太宗改乐的思路,以五、七、九为生成之数,将其依次隔二递减得一、三、五、七、九这5个数,以“一”为数之始,“三”为阳数首成……五等琴便指宫廷雅乐中所使用的弦数为一、三、五、七、九的古琴。奏乐时五床琴为一组,统一其各部位的尺寸,使其可以“象二十四气”“象期三百六十日”“象四时”。这样,就沿着太宗改乐的路,继续复杂化和外在化。
这种复古外在化的繁文缛节还在其次,它的本质其实是神秘化。蔡京向徽宗推荐一位叫魏汉津的人,他本来是蜀地脸上刺字的兵卒,自称师事唐代仙人李良,得传鼎乐之法。他向徽宗进言改乐之法。
三年正月,汉津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7]2998
魏汉津此法的核心是,禹以手指长度定黄钟之律。以不同手指的不同位置来定不同律管的音高,这就是所谓的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这是一个主观的方法。大司乐刘昺并不认可这个方法。
宋徽宗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7]2998
五等琴是做出来了,规模也很可观,不过音乐并没有引来吉祥的凤凰。徽宗做梦了,梦中有人告诉他,那是因为音乐改制没有依照您的手指作为尺度。醒来后徽宗就后悔。当初只是听信了内侍黄经臣的话,皇帝的手指不可以给工匠看到,只是伸手略作比度,无人知晓是徽宗手指的尺寸。现在神托梦来了,那就再一次把中指的尺寸量给蔡京,让大司乐刘昺秘密试验。徽宗的手指尺寸实际要长于向来制乐所使用的尺寸,但是,刘昺一直隐藏着魏汉津的乐律之论,仍然以原先的尺寸为标准,造了长笛呈上。
这里可以发现三件有意思的事情:琴待诏朱文济不肯演奏九弦琴,内侍黄经臣言皇帝之手指不可示人,大司乐刘昺不执行魏汉津的乐律之论。如果把这三件事联系起来,或许可以发现皇权审美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皇帝与乐官、臣僚之间的真实的博弈。皇帝的话臣子可以抗命,皇帝虽然生气但并不发作。
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鼎、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阙,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迺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8]
这一段大晟新乐的记录值得细细推敲,先是按魏汉津说,铸帝鼎和八鼎,意在“铸鼎以起律”。然后按大司乐刘昺的建议去郑卫之音,配上舞蹈。新乐制成,可以演奏了,徽宗下旨先演奏旧乐。还未演奏完,徽宗就说“旧乐如泣声”,终止了演奏。然后演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到了崇宁四年九月初一,鼎和乐都成了,演奏新乐,这时“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徽宗梦境终于实现了。“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大晟新乐当然是以复古为旨归,徽宗的中指作为音乐的尺度,与千年前的黄帝和大禹是一致的,这样,大晟新乐“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作为“一代之制”,就获得了权威性。显然,皇帝的手指是灵验的,所以他说:“适时之宜,以身为度”。然而,旧乐之被否定仅仅是因为徽宗的听感像哭声而已,并非基于音乐制度的考察,甚至与徽宗的中指长短也没有关系。如果说旧乐有违于黄帝和大禹所创立的古制,那无非是说其没有“以身为度”即依照徽宗的中指尺寸制成。我们把徽宗否定旧乐、以身为度和有鹤来仪三样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当下的“适时之宜”,这样,复古的命题被偷换成了“当下”的现实即“以身为度”,而所谓的“旧乐如泣”乃是汉唐以来的音乐被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重置”的本质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
在围绕着音乐改制的君臣博弈中,传统与现实、文献与美感也发生着博弈。复古并非简单地回到过去,复古之“古”与重置之“新”被拉起一个足够长的长时段,它标志着中华文明的长度。复古乃一充满仪式感的操作,意在获得对于文化新变的权威认可。此一认可并非皇权本身可以操控,它须以祥瑞为其兆象。因为获得的兆象可能是祥瑞的反面即灾异,具有偶然性,显然,祥瑞天降是非理性的,可遇而不可求。简言之,复古是这样一种文化设计,即对于从古到今这么一个超长时段的认可与崇拜,虽然可以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安排,然而其成功却往往出于偶然,于当下获得证成,仅仅在于一个“象”,而宋代皇权审美意识形态恰恰确立于此过程。
三、纯色革命:汝瓷天青色与青铜器吉金色的博弈
用鼎是三代以来形成的国家制度,它是中华文化之“象”。宋徽宗改乐的同时铸九鼎,说明鼎的重要性从未动摇。我们在博物馆看到青铜器,觉得它的颜色是青绿色的,或者有点灰黑色,发暗,那是器物氧化后的颜色。青铜器的本色或正色是金色,青铜古来就叫“金”。西周从簋的器内底上有如下铭文:“从易(赐)金于公,用乍(作)寳彝”。从簋的主人叫“从”,他的主公赏赐“金”于他,他就以这些“金”铸造了这件青铜礼器。青铜器由铜和锡按一定比例铸成,铜是红色,锡是银色,铜和锡比例不同,青铜器的颜色也随之不同,《周礼·考工记》记载了六种铜锡的不同配比(3)“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汉)郑玄注:《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7—1098页。。因不同的保存条件,青铜器上锈斑颜色也有差异,我们常见的是青绿色,但也有一些呈黑色,如四羊方尊。青铜器的金色从来就是高贵的,被称为“吉金”(4)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戎生编钟的铭文称:“……遣卤积,彼潜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协钟。”意谓铸钟所用之“吉金”是用卤积(盐)从繁汤这个地方换来的。,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因此,我们知道礼器以金色为本色,金黄色在中国传统中最高贵,是国格之象。
然而,就在宋代,瓷器部分地取代了青铜器,获得国家文化之“象”的制度性与权威性。宋太祖实行对已殁父母或其他帝后之“御容供奉”,在宫观之中专设一殿作供奉,称“御神殿”。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以修玉清昭应宫,特置东〔窑〕务”[9],玉清昭应宫专用于供奉宋朝圣祖及太祖太宗像,举行祭祀活动。过一年,宋真宗下诏“御神殿”的供奉礼仪“如飨庙之礼”,纳入国家礼仪制度。与此相应,北宋时期礼院时常议及郊祀祭器改用陶瓷器。宋《郊庙奉祀礼文》曰:
礼院仪注,(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10]
礼院给出古人祭天的原则“古者祭天,器皆尚质”,“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是追用古制,盖因它们“因天地自然之性”,所以称天之德。礼院执掌祭祀的规制,这里没有提到青铜器,而是建议“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
北宋神宗元丰时期,朝廷官员也提议在郊祀中使用“陶器”,引《宋朝仪注》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用龙杓,未合于礼意。请圜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椫杓。”[11]
这些“新修祭器”的国家行为,均提出祭祀时以陶瓷器取代青铜器,就是以“古者祭天,器皆尚质”“以素为质”的名义公然改制。而这种改制其实质是复古。然而,如果要求“以素为质”,那么玉更合适,以它制作的祭器比青铜器更早,而唐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了品质“类玉”的纯色瓷器,就是越瓷。
唐陆龟蒙《秘色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以千峰翠色为越窑青瓷色彩归类,也即所谓“秘色”。唐代茶圣陆羽为了喝茶而推崇青瓷碗,对青色的品位有更细腻的区分和界定,他道,“越瓷类玉”“越瓷类冰”“越瓷青而茶色绿”[12]。越窑青瓷具有“类玉类冰”的品格,因而把越州碗列为茶碗之上品。从此,“类玉类冰”就是瓷器制作与品鉴的最高标准。尽管吴越以进贡之目的烧造“秘色”青瓷,用于从宫廷、墓葬到日用的广泛需求,不过其审美标准却是民间人士确定的。
然而宋徽宗却是眼高一着,为了适应新的祭祀要求,宋徽宗命新修汝州窑,以提升瓷器烧制品质。汝窑烧造出了类玉的天青色各种瓷器,后来南宋时又在临安建了修内司窑,同样是烧造高品位的青瓷。
不过,宋代之尊贵青色并非唐代以来品茶尚青之风的简单延续,瓷器取代青铜器作为祭器的建议,已经上升到审美意识形态的高度。果不其然,围绕玉辂的颜色究竟应该是黄色还是青色,徽宗与他的幕僚之间发生了又一次博弈。蔡京四子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二有这样一条记载:
玉辂者,乃商人之大辂,古所谓“黄屋左纛”是也。色本尚黄,盖自隋暨唐伪而为青,疑以谓玉色为青苍,此因循缪尔。政和间,礼制局议改尚黄,而上(宋徽宗)曰:“朕乘此辂郊,而天真为之见时青色也,不可以易以黄。”乃仍旧贯,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辂尚青,至今伪也。[13]

图1 卤簿玉辂图(局部),南宋,辽宁博物馆藏
玉辂乃帝王所乘之车。“黄屋左纛”的黄屋指皇帝车乘的车盖,最上面饰以数圈玉片,为黄色。帝王所尚之色本来为黄色,但是隋唐以降人为(伪)地将它改为青色,原因可能是因为“玉色为青苍”,后来这一转读就因循下来。政和年间,礼制局拟议改回尚黄,这时宋徽宗发话了:我乘玉辂去郊祀(祭天地),看到天的颜色映在车上,玉明明是青色的,不可以改易为黄。蔡絛接着记,官员们于是收回拟议,依然“玉辂尚青”,将错就错。
在博弈中,皇家礼院以古代文献为遵,可以称为文献派,徽宗以亲眼所见为实,可以称为感觉派。如果说隋唐“玉色为青苍”是误读,那么宋徽宗却绝对没有误读。其实,玉之色本来或青或黄,不过徽宗决定,青优于黄。出于某时某刻的一个主观视觉,真的那么具有决定性吗?无疑,那一时刻是徽宗亲见祥瑞的一刻。徽宗视觉中的天青色,赋予他吉祥之消息。天青色,乃是一个审美直观,它重置了皇家祭礼用色制度。
汝瓷天青色和早先越窑的青色有些不同,后者以绿为主,间或偏黄,而天青色则以浅蓝色为基调。天青色以玉的纯粹、透明、温润和稀缺性高标其品格,它作为祭器部分取代青铜器,返回到了更早的玉器时代,理所当然地被赋予“天”的权威感和秩序感。青铜器的器型予人以国家庞大体格整体之威压,厚重奇诡,而天青色瓷器却予人天人一体的宁静、通透和秩序。天青色瓷器与金色青铜器之间,精神与物质上各个层次均发生强烈对比。青铜器上往往刻有铭文,乃历史不可磨灭的记载,而天青色之瓷器却不能铭文,脱离了文字,历史似乎不再连续。相对于青铜器式的大国重器,天青色等纯色的瓷器以其美学品格而非礼制品格或历史品格获得国格的赋能。一方面,回归到久远玉器之品质,曰复古,另一方面,取代或部分取代了历史文化的承重基座——青铜器,礼器被重置了,这是用色制度上由皇权审美意识形态主导的一场悄悄的文化革命。[1]
四、祥瑞:复古的后置之象
观察徽宗朝皇家用乐和用色制度的改制过程中所发生之君臣博弈,发现了“祥瑞”一锤定音的作用。祥瑞是事件中可感的吉利之象。音乐改制时徽宗梦到的凤凰来仪、郊祀时看到天映玉辂之青色,均是当下之感官经验,然而它们却被徽宗赋予了高于仪轨和文献的崇高性、权威性,同时又使得执政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以及某种程度的普世性。作为一种预兆之“象”,它的出现是古代审美意识形态的非理性标志,在上下一致求复古成为共识的宋代,它使得复古的目的后置到当下,具有革新的品格。这有类于我们所谓的现代性。可以研讨一下徽宗的《瑞鹤图》。

图2 宋徽宗《瑞鹤图》,绢本设色 辽宁博物馆藏
徽宗自提序言及诗如下: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俪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记其实。清晓觚棱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似拟碧鸾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
政和二年(1112)正月十五上元节的第二天(正月十六),汴京皇城端门降临了祥瑞。那天,忽然有白色之祥云低拂盘郁于端门以及与之相联的宫殿群之上,仿佛进入了仙境。人们一齐仰头观望,自然期盼着会发生什么大事情。白云为祥瑞拉开了序幕,接下来有一大群鹤飞鸣降临,其中两只分别停止在屋顶的两个鸱尾之端,右边那只昂然而立,悠然作回首观望状,左边这只似乎刚刚降临,身体作Z字状,双爪牢牢抓住鸱尾,重心似尚未调整到位,也正作扭头观察状,互为呼应。两鹤之间的上方留出少许天空,暗示了端门的中轴为画面的中心。由是,左右两只鹤以它们生动的降落演出闲适之态,完成了鹤群与端门倒梯形屋顶的连接,这两个支点使得画面获得了上下一体感。其余18只鹤还在端门之上盘旋翱翔,它们完全打开翅膀,以各自的姿态飞翔,或向下俯冲,或平飞翱翔,或昂首向上,以端门为中心作扇面之展开,居然无一重样,如音乐演奏一般具有节奏感。民众长久地观赏此壮观的景象,赞叹不已。鹤群于端门之上盘旋恒久,最后迤俪朝西北方向飞散。
不过,鹤群全体张开的翅膀,显然与鸟群上下飞翔的真实不符。通常,下降中的鹤其翅膀完全打开以保存身体平稳,姿态最为优美,平飞翱翔的鹤其翅膀需要作波浪状以获得升力,上升中的鹤其翅膀则更需要用力振张,以便拉升。实际上平飞和上升两种状态下鹤之翅膀不会完全张开。天空中所有18只各种动态的鹤选取其翅膀完全打开的飞翔形体,为的是创造众鹤群聚的观感,这使得画面并不舒朗,这意味着画作需要装饰性的平面。然而,众鹤之翅膀大面积的白色动态在占据画幅上部3/5面积的更大的天青色天空衬托之下,体现了宁静祥和的装饰效果。有研究者以“超现实”指称徽宗《瑞鹤图》的美学旨趣,是有道理的。
群鹤翔集国家权力中心——端门,这样的祥瑞事件,它仅仅是针对宋徽宗皇帝一人之梦,还是具有某种普世性!有人把徽宗与李煜比,称他耽于艺术而荒于管理国家,如果说李煜词的千古绝唱过于悲,对于个人的命运关注过多,那么徽宗似乎乐观多了,难道他仅仅是把玩艺术并玩物丧志而已?分析《瑞鹤图》的美学旨趣,肯定存在着艺术之上的人文关怀,序言云“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诗云“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瑞鹤降临、徘徊嘹唳,对于彼时彼地之往来人众百姓均是祥瑞,那么它的性质如何界定?是如基督之爱还是如菩萨之慈悲?
祥瑞是纯粹之中国传统,它当然是非理性的,可望而不可即,它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踪迹过于飘忽。祥瑞向人们传送国泰民安的美好消息,它当下发生、当下证成,于是人们就欲以艺术将其固定下来。好在祥瑞本来就是一个直观之“象”,如果把它与祈求它的具体事件加以区隔,使这个“象”形式化或程式化,这样它就不再是个人的欲求了,它成为审美意识形态,获得了普遍性的品格。如果说天青色因徽宗命建汝窑而获得类似当今流行色之权威发布,那么祥瑞也不会仅仅只是宋徽宗的一个梦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祥瑞乃复古的后置之象,乃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完成形态,决非个人之孤情寡绪!
五、结语:时间箭头之重合
从北宋9位皇帝有6位亲自主持音乐改制看,复古是一个文化战略,它并非权宜之计。如前文所揭,內藤湖南所谓的唐宋之变——中国于宋代进入了“近世”,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间箭头。我们又看到,“回向三代”的复古又把时间箭头指向作了倒转,此乃中国文化内在结构所决定的。然而,由于把当下发生的祥瑞视为复古成功的标志,祥瑞之今就与复古之古连接成一条时间线,它的时间箭头不再指向远古,而与“唐宋之变”的历史发展箭头获得了一致,传统与现实两股能量终于汇流在一起。于是,我们不得不对“回向三代”重新评估,复古既是蓄力也是对前进方向的校准,即通过复古使历史在发展的同时稳定文化核心不变,保持同一个发展方向。显然,文化重置必须在革新而不是革命的意义上推进。围绕宋徽宗音乐改制和天青色发生的两次君臣博弈,理学的影响并不显著,祥瑞则是源于中国早期与占卜、算卦、徵验等相关的取象传统。方士魏汉津帮助徽宗设计了乐改模型,道教显然强化了此一传统,而对于佛教则存在明显的防范。从思想史角度观察,宋儒的道统体系剔除韩愈更像是一种策略,这样的文化重置是思想史的、理性的、文献为征的。从美学的角度观察,文化重置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摆荡空间,比较而言,宋徽宗的乐改因流于形式而显得保守,但是瓷器的国家改色却近乎革命。徽宗在青铜器和瓷器之间做出了选择,天青色竟然推动了国家用色制度之“纯色”方向及其美学运动。而祥瑞之象作为复古的目的,维系并稳定了文化的本质。区别于宋儒的文化重置策略,用乐和用色制度的重置是审美意识形态的、非理性的、祥瑞为征的。复古与祥瑞,构成了文化重置战略的两极,我们就是在此两极之间观察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