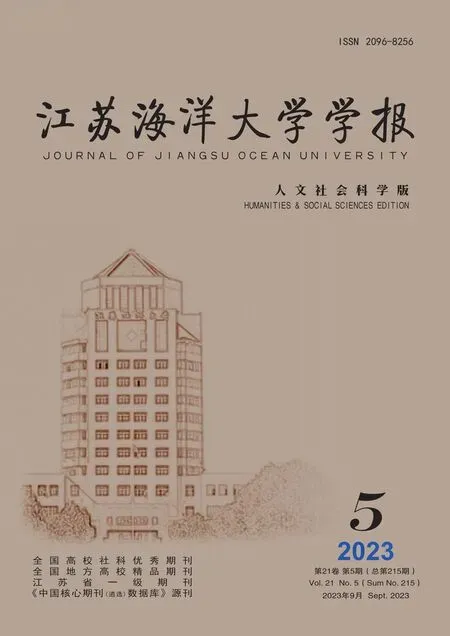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伊迪丝·华顿的“新英格兰”小说解读*
2024-01-02魏懿
魏 懿
(上海建桥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2)
一、引言
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以其著名的“老纽约”系列小说在20世纪初的美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华顿常被视为一名纽约社会变迁的“风俗记录者”[1]460,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的文学评论较多集中在其《欢笑之家》《国家风俗》《纯真年代》等几部主要的“老纽约”小说,而对于华顿其他题材的小说则关注较少。研究华顿的专家琳达·马丁认为:“与同时代的伍尔夫、凯瑟、巴恩斯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女作家相比,研究华顿的学者所使用的评论方法还不够丰富。”[2]208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重新解读华顿的作品给予了启示,同时也为进一步挖掘华顿小说中的女性写作提供了全新视角。
发表于1911年的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和1917年的长篇小说《夏日》是华顿创作的两部“新英格兰”题材小说,它们都以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生活为叙事背景,探讨了女性在压迫与反抗、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倾向。在这两部小说中,华顿摈弃了她所熟悉和擅长的“老纽约”社会题材,女主人公不再是出生于大都市的上流阶层名媛,而是贴近大自然的乡村女性。有些评论者对于出身纽约上层社会的华顿能否真实展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生活提出了质疑,华顿的好友同时也是著名作家兼评论家的亨利·詹姆斯就曾指出:“她(指华顿)比其他人的作品更属于纽约,而不是其他地方。”[3]97然而事实证明,华顿的“新英格兰”小说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成就方面都毫不逊色于“老纽约”小说。因此,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这两部作品,将进一步推动读者去感受和挖掘华顿小说中丰富的思想内涵。
二、男性视野下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性
小说《伊坦·弗洛美》以男主人公伊坦和妻子细娜以及细娜的表妹玛提之间的情感纠葛为叙事线索,讲述了新英格兰地区偏远乡村中的一段情感生活。由于该小说涉及婚外情、一夫二妻等道德禁忌话题,《伊坦·弗洛美》因此成为了华顿众多小说中最受争议的一部作品。在小说的《自序》中,华顿本人曾直言不讳地说道:“当我把我的故事结构轮廓向少数朋友说起时,我立刻遭到了毫不含糊的反对。”[4]4果不其然,小说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抨击。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这部小说没有任何道德价值。”[2]127另一位知名评论家弗农·帕灵顿虽然认可华顿在小说叙事方面所展现的技巧,但与此同时又颇为困惑地质疑道:“她(指华顿)为什么要将技巧浪费在如此不重要的题材上面?”[5]294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一些女性评论家却对该小说予以了肯定。例如,伊丽莎白·埃蒙斯认为,《伊坦·弗洛美》解释了“一种特定的男性恐惧:在男性的生命中女性的影响噩梦般地从正面变成了负面”[6]。另一位女性评论家辛西娅·沃尔夫认为,小说中的叙事者“我”就是作者华顿本人,其叙事构建出的伊坦正是“华顿对于自己内心那部分(压抑和消极)的恐惧”[7]179。遗憾的是,虽然她们意识到了这部小说中所存在的两性对立与矛盾,但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的解析和探讨。
“生态女性主义质疑所有的统治关系,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改变掌握权力的人,还在于改变权力结构本身。”[8]77《伊坦·弗洛美》中存在着两个统治结构,即人类对于自然的统治以及男权对于女性的统治。在叙事者“我”的眼中,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斯塔克菲尔镇“有电车,有自行车,有乡镇邮局,那些分散的乡村间的交通已变得十分方便”[4]16,“我”来到斯塔克菲尔镇工作也与当地大型电厂的建设有关。由于人类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开发,原本闭塞的斯塔克菲尔镇已经融入了美国的城市化进程。然而,城市化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开发并未给小镇带来城市文明的繁荣。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使得乡村的年轻人离开了乡村环境,城市化进程给新英格兰地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加剧它的隔绝和孤立,就像伊坦的母亲所抱怨的那样:“自从火车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走这条道了。”[4]36即使像伊坦·弗洛美这样留在乡村的人,也由于城市化进程而被迫与土地分离。房子是联结乡村人与土地之间的纽带,正如叙事者“我”所感觉到的那样:“因为它展示了一种联系于田园的生活,因为它本身包容着温饱的源泉。”[4]34生态女性主义作家帕特·莫拉认为,“房子”这一概念在人类与土地的一系列必要联系中发挥着换喻和隐喻的作用,“因为人类是这个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特表达——房子”[9]25。然而,《伊坦·弗洛美》中的乡村房子却是“可悲的丑陋”[3]32和“萎缩的建筑”[4]34。在“我”看来,城市化进程给斯塔克菲尔镇的自然环境带来的是“堕落的日子”[3]16。伊坦·弗洛美“萎缩的躯干”[3]34与斯塔克菲尔镇“萎缩的建筑”构成了小镇里人与自然之间的象征隐喻。
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影响到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评论家拥有一个共同信念,“即在男权文化中,女性所受的压迫与非人类自然受到的破坏和滥用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10]127。《伊坦·弗洛美》曾被一些评论家视为一本不道德的书,“他(指伊坦)不应该在有家室的情况下与另一个女人(指玛提)产生情愫,更何况他的妻子还生着病”[2]127。伊坦和玛提之间的感情描写成为该小说被诟病的主要原因。然而,伊坦和玛提之间的情愫首先是建立在对大自然共同爱好的基础之上,“他(指伊坦)对于自然之美总是会比别人更加敏感。……即使在他最苦闷的时候,田野和天空也能带给他深沉而有力的感动”[4]52,当他知道玛提和自己一样会为“冬天山后冷而红的落日,茬地山坡上的飞云,或是铁杉投射在晴雪之上的深蓝色影子”[4]54感到惊奇时,“他秘密的灵魂终于找到了表达的词汇”[4]54。在伊坦的眼中,玛提总是与充满活泼生命力的自然元素联系在一起,她的笑声是“春雪融化后的山间小溪”[4]68,她的脸是“夏天清风底下的麦田”[4]132。在伊坦看来,“纯净的空气和野外的漫长夏日可以恢复玛提的活泼与弹性”[4]88,甚至“太阳的殷红和雪的洁白中都有她的存在”[4]86。玛提变成了欣欣向荣的大自然的化身,满足了伊坦潜意识里“要求变化和自由的渴望”[4]74。生态批评学者迈克尔·齐墨尔曼认为:“男性会将女性设想为自然,但又会害怕和仇视女性,他们会尝试否定自己身上的女性或自然成分,并去控制外部他们认为属于女性和自然的事情。”[11]在小说中,当伊坦第一次在火车站见到玛提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她看上去不像是一个会做多少家务活的姑娘”[4]50。伊坦疏远妻子细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她近来常常埋怨家务活的繁重”[4]54,“抽象的所谓家务活无法引起她的兴趣”[4]55。在伊坦的意识里,女性与“家务活”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父权制构建的模式中,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负责挣钱养家,而女性则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男性,无偿地进行家务劳动。“家务活”成了社会构建女性身份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同玛提对伊坦所说的:“有许多女仆能做到的家务活我至今仍然做不好——我的力气也不够。但是只要她肯告诉我怎么做,我都愿试试。”[4]72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瓦尔·布鲁姆德认为,女性与家庭事务之间的联系源于男性的工具理性思维,“由于女性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与自然不相延续,她们被安排的工作是为物质生活服务,专注于家庭物质生活,所以女性的自我身份和本体论倾向与自然更相延续”[12]36-37。如同人类使用工具理性主宰女性化的自然,男性个体也会使用理性工具从自然化的女性中获得实用价值。伊坦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伊坦对大自然的爱并不会使他喜欢在田地里干活。他总是想成为工程师,住在大城市里。”[4]102在无法实现工程师的梦想后,他以锯木坊作为自己的谋生产业。无论是“工程师”还是“锯木坊”都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改造。当面对自然化的玛提时,伊坦也同样流露出支配的快感,“他紧紧抱住她,感觉她的睫毛像被捕获的蝴蝶一般扑打着他的脸颊”[4]170-172。当伊坦感到自己的语气完全将玛提征服时,“他的心里充满了骄傲。……这种令人兴奋的支配感只有将一根大木头滚到山下的锯木坊时才能感受到。”[4]126华顿在文本中使用了“被捕获(netted)”、“征服(subdue)”和“支配感(sense of mastery)”等带有强烈等级支配含义的词汇,从而将女性置于自然场域之中,女性与自然一起成为被男权征服和支配的对象。
如果说玛提代表着父权审视下自然化的女性,那么伊坦的妻子细娜则代表着父权统治下的真实女性。小说中,家庭成为细娜唯一的归宿,同时也成为囚禁她的牢笼,正如她自己抱怨的那样:“医生说如果我继续这样像奴隶一般干活,我很快会没命。”[4]160婚前的细娜也曾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她喋喋不休的话语在伊坦的耳中如同音乐一般”[4]102,伊坦曾把她视为“健康之神”[4]104。然而,婚后的生活却让细娜逐渐从开朗变成沉默,从健康变成病态。伊坦也意识到了这一变化:“她(指细娜)终年闷闷不乐自艾自怜地生活在他身边;她变成了一头神秘不测的怪物,一股毒气从她长年的沉默中分泌出来。”[4]168有的评论家认为细娜婚后的沉默和病态臆想源于家庭的束缚,“对于深陷家庭囹圄的妇女,家庭和丈夫是她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她们束缚于孤独单调的家庭生活,除了疯掉和死亡,她们无路可逃”[6]。细娜从婚前健康到婚后病态的转变,与玛提被置于自然场域的征服支配是一致的,其本质都是父权制对于女性所造成伤害的结果。华顿在小说中多次暗示,活泼的玛提和病态的细娜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女性实为同一形象。例如,在第四章中,当玛提开门时,伊坦“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他以为会看见他的妻子站在门口;但是门开了,站在他面前的是玛提。玛提站立的姿势就跟细娜一样,一手提着灯,映衬着厨房幽暗的背景”[4]116;在第五章中,当伊坦凝视玛提时,“他看见她的年轻的棕色脑袋靠在靠枕上,靠枕上出现了他的妻子狰狞的面容。伊坦猛然一惊,好像另外一张脸掩盖掉了新来者的脸”[4]128。在伊坦的凝视下,自然柔弱的玛提与病态狰狞的细娜融为一体,构建起了自然与女性在男性统治下的关联性。
三、异族母亲的身份追寻之旅
《夏日》是继《伊坦·弗洛美》之后华顿创作的第二部“新英格兰”题材小说,也是华顿“对陷于衰败的乡村生活的农村进行全面探索后的产物”[5]36。由于《伊坦·弗洛美》之前所遭受的非议,《夏日》的出版并未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充分关注和认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夏日》的研究较少。但作为华顿本人最为满意的五部作品之一(1)华顿曾列举自己最满意的五部作品,它们分别是《国家风俗》(1913)、《夏日》(1917)、《孩子们》(1928)、《哈德逊河》(1928)和《上帝降临》(1932)。,《夏日》无疑倾注了作者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入思考。相较于《伊坦·弗洛美》,《夏日》对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对蛮荒自然与城市文明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更为细腻的描写。
与《伊坦·弗洛美》中的玛提一样,《夏日》中的女主人公夏洛蒂·罗伊尔也属于自然化的女性形象,她对于大自然的爱源自其天性。“对于大自然里所有的光线、空气、香味和颜色,她体内的每一滴血液都会对此做出反应。她喜欢干燥的山野小草抚摸上去的粗糙感,喜欢把脸凑近百里香嗅闻它们的芬芳,喜欢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和棉质上衣以及落叶松在风中摇摆时发出的吱嘎声。”[13]12夏洛蒂对于大自然的亲近感明确了她与自然界之间的天然纽带,“她是从山里被带来的;来自于那阴沉地高耸于雄鹰山脉的斜坡上的陡峭悬崖,它是孤独的山谷永恒的幽暗背景”[13]4。由于夏洛蒂“从山里被带来的”的特殊身份,她在其所居住的北多默镇上与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哈特查德小姐曾提醒她:“记住自己是从山那里被带来这儿的,闭上嘴,学会感恩。”[13]4美国女性生态评论家薇拉·诺伍德认为,西方主流社会常会把边缘化的群体等同于蛮荒的大自然,“相比起其他美国女性,这种与非人类自然相联系的认知常把美国的其他族裔女性群体放置在文化界限之外”[14]177。白人文化会将“更为低级的种族”安插在自身与自然之间作为一个缓冲地带,这种排斥异己的文化模式无疑对夏洛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夏洛蒂看来,“山那里是一个坏地方,来自那里是一种耻辱”[13]4,“她知道自己在北多默镇上属于最卑微的人,来自山里是最可怕的耻辱”[13]13。在自卑心理的驱使下,夏洛蒂渴望拥有当地白人的蓝色眼睛,“她挑剔地看着自己镜中的形象,第一千次希望自己拥有像安娜贝尔·巴尔奇一样的蓝眼睛”[13]2,她认为“北多默镇代表着精致文明中所有美好的东西”[13]4。对于同样来自山里的力夫·怀特,夏洛蒂也是以鄙视的态度对之,“她感到羞耻,生怕被人看到自己在和力夫·怀特说话”[13]39。小镇的主流文化要求夏洛蒂拥有可接受的身份并同时否定自我的原始身份,然而来自大山的天然属性却使得夏洛蒂对于山那边始终充满了好奇,“她对于自己变得越来感兴趣,即使令人憎恶的东西也变得有趣起来,因为它们是她自身的组成部分”[13]41。
夏洛蒂的两次大山之旅成为了她对于自我异族女性身份的认同之旅。第一次是陪同哈尼进山采风。尽管夏洛蒂在心中默念“我属于这里——我属于这里”[13]59,但是山中的一切还是让她充满了恐惧和鄙视,“本能和习惯使她在这些沼泽居民中成为一个陌生人,这些人就像生活在兽穴中的昆虫一般”[13]59。在夏洛蒂的眼中,“那个女人的目光令人不安,而那个熟睡的男人的脸显得如野兽一般肿胀,她(指夏洛蒂)在感到恶心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恐惧”[13]57。在夏洛蒂的凝视中,“兽穴(lair)”、“昆虫(vermin)”、“沼泽(swamp)”、“野兽(bestial)”等词汇描述将山里人降级到了与自然界同等的地位,山里人和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一样被重新进行了文化构建,种族被赋予了蛮荒自然的特征。这是夏洛蒂作为一名异族女性被不断思想构建和文化殖民的结果。在夏洛蒂看来,山里的生活与山下的北多默镇构成了蛮荒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她感到自己的生活环境显得充满平和与富足”[13]58。夏洛蒂的第一次大山之旅可以说是蛮荒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一次再现,夏洛蒂未能在二元对立的差异中找到联系,而仅仅证实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
第二次大山之旅是在夏洛蒂经历了被养父当众羞辱和意外怀孕等事件之后,她对于大山深处的故乡产生了巨大的情感转变,“她认为正是自己血液里的某些东西使得大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也是逃离所有包围和困扰的必然归宿”[13]167,大山成为了夏洛蒂的精神家园,“以前当她眺望被阳光照射的山谷并凝视着大山的时候,大山对她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而现在它变成了现实”[13]176。摒弃了之前将山里异族视为蛮荒自然的白人视角,夏洛蒂这一次真正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同类,“这些是我的族人。我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13]182。值得注意的是,夏洛蒂这一次进山正逢其亲生母亲病逝,与此同时她体内又孕育着新的生命。新旧生命的交替,使夏洛蒂在感悟自身种族身份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大山自然环境的艰辛,“她开始想象如果她在大山里成长,穿着褴褛的衣服奔跑,睡在地上蜷缩于母亲身边就像眼前这些蜷缩在老怀特夫人身边面色苍白的孩子一样,她的人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13]184艰苦的自然环境迫使夏洛蒂思考另一个与自己性别有关的新身份——异族母亲。一个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母亲不得不思考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未来,“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摆脱这样的命运,她仿佛拥有了力气跋山涉水,仿佛能承受任何生活所加在她身上的负担”[13]185。生态女性主义评论家唐纳·哈拉维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的是有限位置与处境意识,而并非超越或分裂主客体。”[15]190就夏洛蒂而言,异族的身份意识让她明白在大山的自然环境中抚养孩子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而山下的北多默镇则代表着富足的城市文明,能为孩子提供一个有保障的未来。美国女作家阿德里安娜·里奇认为:“在父系文化里每一个女性都极其缺少母爱,因为性别和种族歧视使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性缺乏自尊,她们也无法将自尊传送给自己的后代。”[16]315她认为要在有保障的环境中建立令人满意的母子关系,这对于个人在世界上的自尊和安全感的培养至关重要。在小说的结尾,夏洛蒂嫁给自己的养父罗伊尔先生正是对于自身处境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她知道和他在一起她很安全”[13]200。犹如当年母亲将她从山里带到北多默镇上送人抚养一样,如今夏洛蒂面对腹中的孩子时,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两代异族母亲在面对蛮荒和城市时都理性地选择了后者,这也是城市文明对于自然影响的必然结果。但和自己的母亲近似抛弃的做法不同,夏洛蒂会始终陪在自己孩子的身边,“她要这个孩子;她想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使这个孩子成为大山和其无名父亲之间的纽带”[13]203。母爱的陪伴与关怀会将大山异族的尊严传递给下一代。
夏洛蒂从最初对于异族身份的自卑、鄙视到最终的接纳与理性的选择,说明了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在不断觉醒,而最终嫁给养父的结局又透露出当时女性的尴尬处境——女性虽在精神上实现了觉醒,但在物质上仍不得不依赖于男性。如同大山的生活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山下城市文明的影响,女性在物质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父权。正如结婚第二天夏洛蒂在养父罗伊尔先生的脸上所看到的那样,“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个让她既感到羞耻但又感到安全的表情”[13]205。女性尽管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来自男性的安全保障,但依附于男性的现实却带给女性羞耻的生存处境。
四、男性的支配与女性的主导
《伊坦·弗洛美》和《夏日》中的主要男性角色大都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这不仅体现在父权制对于女性和家庭经济的掌控方面,同时也体现在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控制欲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方面。在《伊坦·弗洛美》中,伊坦虽然在意识层面渴望支配玛提,但低下的经济能力使其无法实现传统父权制所设定的男子气概。小说中多次暗示伊坦是一个收入微薄的男性:当细娜准备去看病时,“她的丈夫(指伊坦)对于这种远行颇为畏惧,因为这要花不少钱”[4]92;当细娜表示身体不舒服时,“他就预感到她会立刻要钱,她要长久地攫取他有限的收入”[4]158。有限的收入使伊坦内心对于女性和家庭的控制欲与男权的普适要求之间产生了鲜明的矛盾冲突。细娜在经济上的负担以及玛提在经济上的依赖都给伊坦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这正是父权制构建下的理想模式对于部分男性所产生的必然影响。
与伊坦相比,《夏日》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卢修斯·哈尼和罗伊尔先生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占有欲。与接近蛮荒自然的夏洛蒂相比,哈尼和罗伊尔先生更接近父权制的城市文明。在夏洛蒂的眼中,“尽管哈尼显得有些害羞,但他却拥有某种城市的经历所赋予的力量”[13]35。城市经历使哈尼始终以城市文明的视角审视大山周遭的一切。当陪同哈尼进山采风时,夏洛蒂就已感到哈尼与周围环境之间格格不入,“她知道怀特一家不可能伤害自己,但是她不确定他们会怎样对待一个‘城里人’”[13]57。对生活在大山里的怀特一家而言,哈尼代表着“城里人(city fellow)”,他的到来让“一家人脸上浮现出焦虑的神情”[13]59。尽管哈尼并未像北多默镇上的居民那样对山里人表现出鄙夷,但在与哈尼的交往中,夏洛蒂始终感到“似乎在他们之间竖立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13]152,这道障碍源于两人之间的种族差异,也源于蛮荒自然和文明城市之间的鸿沟。尽管哈尼声称爱着夏洛蒂并会娶她,但小说曾暗示他在和夏洛蒂交往的同时,和安娜贝尔·巴尔奇也保持着亲密关系。在小镇的庆祝晚宴上,夏洛蒂发现哈尼和安娜贝尔举止亲密,“一瞬间他俩让她明白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在她所爱的人的温柔体贴的表象之下是难以捉摸的神秘生活:他和其他人——和其他女人的关系”[13]139-140。对于哈尼而言,夏洛蒂只不过是一个散发着野性自然气息并能排遣小镇无聊生活的玩物而已,他真正的婚姻伴侣则是像安娜贝尔那样拥有“一双蓝眼睛”[13]2的白人姑娘。夏洛蒂和哈尼之间的爱情注定以始乱终弃的结局收场。
另一位男性人物罗伊尔先生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父权制和城市化的特征。“作为北多默镇上唯一的律师,他家的屋顶与覆盖市政大楼和邮局的屋顶一样高。”[13]23绝对的权威性使罗伊尔先生看上去“极具专业权威感和男性的独立感”[13]23。与哈尼将夏洛蒂视为玩物不同,罗伊尔先生将夏洛蒂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作为夏洛蒂的养父,他在妻子去世后曾试图性侵夏洛蒂。当他发现夏洛蒂和哈尼在内特尔顿市幽会时,他醋意大发,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夏洛蒂:“你这婊子——你这该死的,彻头彻尾的婊子。”[13]106在他的眼中,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像异教徒一般群聚在一起”[13]49。对罗伊尔先生而言,一切与自己不同的人和物都是怪异的,是需要进行改造的。在北多默镇的庆祝晚宴上,罗伊尔先生对小镇的周边自然环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北多默镇是一个可怜的小地方,它几乎隐没在壮丽的自然风光之中:如果回到此地的人头脑中带着这样的感受,或许它能成为一个更大的地方,一个比周围的自然风光宏伟的多的地方。”[13]138在罗伊尔先生看来,自然风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北多默镇的城市化进程。他号召那些前往大城市的小镇居民回来建设小镇,“我们中的一些人像你们一样年轻时去往繁忙的大城市,去干一番伟大的事业,现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这里——回来建设”[13]137。
如同对待异族女性一样,自然也被视作可以进行文化构建和可以被殖民改造的场所。在这一点上,夏洛蒂的异族女性身体和大山的自然环境同样遭受了父权制和城市化的威胁,两者在形式上融为了一体,自然与女性的身体一样都将经历沦落、诋毁和改造的过程。在男权和白人主义盛行的城市环境中,女性与自然面临着共同的处境——变成男性和人类改造与支配的对象。尽管哈尼和罗伊尔先生性格不同,对待夏洛蒂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将夏洛蒂视为可以像自然一样被男性操控的个体。无论是哈尼对夏洛蒂的始乱终弃还是罗伊尔先生娶了怀孕的夏洛蒂,这都是父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物质化占有。
生态女性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德·奥博纳说:“很少有人意识到男权社会应对此负责,处于危险之中的正是男性自身……男性支配的城市化和科技化的社会使土地不再肥沃,女性不再扮演她们本该扮演的主导角色,而这最终有损于包括男性在内的地球本身。”[17]66《伊坦·弗洛美》中,伊坦和玛提最终撞树身残的意外结局,正是男性在渴望支配自然与女性过程中由于无法调整自身追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预示着在旧有男权统治下男性也同样无法获得健康的发展。华顿在小说中将由玛提代表的自然、由细娜代表的现实家庭女性和由伊坦代表的男性放置在由男权统治的同一屋檐下,形象地揭露了男权统治对于三方所造成的伤害。在小说结尾处,原本孱弱的细娜担负起了照料身体残疾的伊坦和玛提的责任,“二十多年来她始终保持着那股力量照料着两个人。在那场事故发生前,她觉得她连自己都照顾不了”[4]254。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瓦达娜·西娃认为:“女性可以用来治愈病态的父权制度发展,那些受威胁最大的女性最有可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因为她们拥有主流群体和优势群体所不具备的两方面认知。”[18]47
与细娜一样,《夏日》中的夏洛蒂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具备“主流群体和优势群体所不具备的两方面认知”,她既意识到异族女性在男权文化的环境中养育后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同时又意识到大山的异族文化在下一代中延续的重要性。她没有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将孩子完全交由“文明人”抚养,而是选择在获得经济保障的前提下由自己抚养,这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了下一代会像自己一样被白人主义所同化。有的研究者认为,夏洛蒂嫁给养父罗伊尔先生的结局意味着女性对于男权的屈服,“未婚先孕且被情人抛弃的困境迫使她屈服于罗伊尔的建议,即嫁给她之前甚至感到有些厌恶的后者”[19],但值得注意的是,夏洛蒂并未甘心屈服,在和罗伊尔先生结婚的前夕,她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女性的力量,“当她想到他(指罗伊尔先生)的时候,她总是把他想成一个令人憎恨的障碍。但是当她选择做出努力时,他又变成一个自己能够以智取胜并能支配驾驭的人”[13]195。与《伊坦·弗洛美》中最终扮演家庭主导角色的细娜一样,夏洛蒂也将会运用女性的智慧和毅力在男权文化的环境中担负起一位异族母亲的责任,从而主导自己和孩子的命运。
《伊坦·弗洛美》和《夏日》相似的结局,透露出华顿对于女性“扮演她们本该扮演的主导角色”的期待。华顿肯定了女性能够担负起主导角色的能力,她相信被赋予主导地位的女性能够纠正和医治男权统治下变得残缺的男性与自然。
五、结语
作为华顿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英格兰”题材小说倾注了作者对于当时女性生存现状的感悟,通过细娜、玛提和夏洛蒂等人物形象,读者能看到华顿本人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心路历程。华顿在创作《伊坦·弗洛美》的时候,她的婚姻正走向终点,“当她在写作方面变得越来越自信时,她和泰迪·华顿的婚姻却走向没落”[13]x,家族成员对于华顿写作事业的讥讽以及婚后长达28年的痛苦婚姻生活都使华顿充分认识到女性在追求自身价值时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诚如女性文学评论家苏珊·米诺特在《夏日》的序言中所说:“《夏日》中年轻的夏洛蒂·罗伊尔那种被隔绝和未开化的状态,正是她(指华顿)同样孤立无援的处境的写照。”[13]viii无论是《伊坦·弗洛美》中被婚姻囚禁的细娜还是《夏日》中由于异族身份被排斥的夏洛蒂,读者从中都可以看到华顿的影子。同时从这些女性人物的反抗与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读者也可以感受到华顿作为女性作家对于自身艺术事业的坚定追求。
除了个人因素以外,华顿所生活的时代也使她对美国女性的生存状态给予了高度关注。华顿创作“新英格兰”题材小说的20世纪前20年正值美国女性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在当时关于“女性问题”的各种社会大讨论中,华顿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女性在当时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处境,并在其作品中创造出了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新女性是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崛起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群体,“新女性之所以会获得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到了19世纪后期她们以强健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和文学作品之中。她们的出现不仅体现了新的价值观,并且也向现有的秩序提出了挑战”[20]481。细娜、夏洛蒂以及华顿“老纽约”系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华顿对于新女性形象不同角度的诠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描写纽约上层名媛生活的“老纽约”系列小说不同,在“新英格兰”题材小说中,华顿有意识地将女性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自然环境相结合,玛提和夏洛蒂等女性人物具有较为鲜明的自然化倾向,她们暗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性。在《伊坦·弗洛美》和《夏日》中,女性与自然都成为了男性眼中的“他者”。男性/女性、蛮荒/城市、白人/异族等父权文化中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这两部小说中都明显地展现出来,表现出鲜明的生态女性写作倾向。从这一点而言,华顿继承了萨拉·奥恩·朱厄特、薇拉·凯瑟、克拉丽丝·丽斯佩克托等美国女作家的传统,为美国的生态女性书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