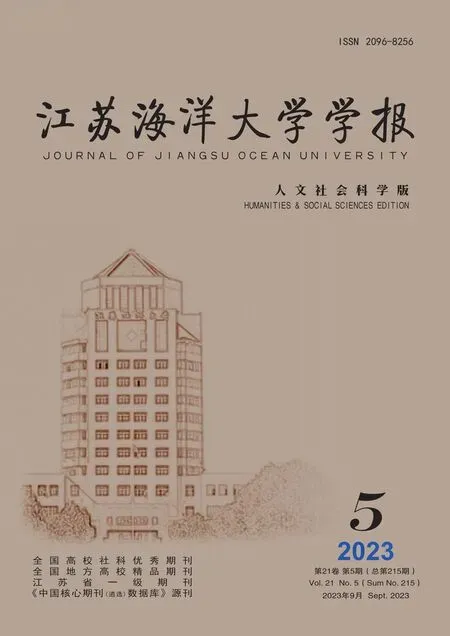散文翻译中的显化现象研究
——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
2024-01-02张顺生陈兆瑞
张顺生,陈兆瑞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随着语料库翻译学的不断发展,汉英互译中的显化现象备受关注。其中原因不难理解: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思维模式以及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显隐性是指是否存在外在的语言形式上的标志,译者对译出语的文字表征深层认知加工的过程就是显化。汉英语言的隐性和显性内容相差悬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散文形散而神聚、寓意深邃、语言优美、韵味悠长,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当代翻译家张培基(1921—2021)在文学翻译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其代表作《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以下简称《散文选》)语言自然流畅、雅俗共赏,语篇神韵犹存,力求既完美地保持原文的信息、功能,又再现原文的风格或味道[1]。鉴于散文体裁特点,英译过程中存在许多典型的显化现象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近年来,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作品备受高校广大师生以及其他翻译爱好者的推崇。已有学者从跨句法[2]、中西思维方式[3]、接受美学[4]、文化负载词[5]等角度对张培基英译散文开展研究,但鲜有学者探讨张培基英译作品中的显化现象。有鉴于此,本文试以张培基《散文选(一)》为例,从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三个方面考察现代散文汉英翻译中的显化现象并分析其成因,以期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提供启示。
一、显化及其分类
显化(explicitation)和隐化(implicitation)是一对相对的概念。显化是指“译文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呈现原文潜在信息,译者添加解释性的短语或使用关联词语等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和可读性”[6]55。据此,可以将显化看做是一种翻译技巧。Blum Kulka提出显化假设,将其视作翻译共性之一,主要体现在衔接形式上的显化[7]17-35。国内学者柯飞主张,显化不应局限于语言衔接形式的变化,意义层面亦有体现[8],译者在译文中添加显化表达使原文隐含信息以更清楚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王克非借助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对显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英汉互译过程中,目的语文本都呈现扩增特点[9],验证了Blum Kulka的显化假设。实现翻译“信达雅”的要求,显化是必经之路。姜菲和董洪学认为,翻译过程是基于译者认知的显化加工过程,显化翻译的实质是认知理念或思维,译者可以挣脱“原著中心论”的束缚,更好地发挥源语与目的语之间语码转换的中介作用,暗合严复提出的“译者将全文神理融合于心,下笔抒词,自善互备”[10]的观点。上述可见,诸如显化等翻译共性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语言特征,还可以从译者、文本类型、文化等视角进行探讨。本文认为,显化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技巧,而是语言背后思维方式、文化的映射,译者要以目的语语言文化为规则,在心智空间里对原文本文化规则加工,将源语文化“化”出并融入目的语中。
关于显化分类,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inay & Darbelnet认为显化可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11]24,但这种分类显化界限不够明确;Klaudy根据显化成因,将显化分为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12]81;胡开宝和朱一凡依据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对语言纯理功能的划分[13]31,将显化划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14]。
二、汉语的隐性特征和英语的显性特征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
显化翻译研究硕果颇丰,如胡开宝、朱一凡基于自建的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语料库,对汉译文本中显化现象及其动因进行了研究[14];姚琴对比《红楼梦》霍译本和原著,发现译者采取释意、增添等方式以显化林黛玉的人物特征的意义[15];许家金、徐秀玲基于可比语料库,研究发现相比于原创英语,翻译英语的衔接显化特征更为显著[16];冯全功则鉴于中英两种语言、文化、诗学、思维等差异,将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的显化分为句法显化、语用显化、思维显化和意境显化,并分析其成因[17];王雪明在显化翻译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信息型文本、以应用为导向的汉译英显化策略体系[18];杨颖、卢卫中考察了译者在政治文本英译时所采取的显化操作[19]。然而,以往翻译的显化研究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多限于政论文本、科技文本以及典型小说,缺少对散文这一重要文学体裁英译显化现象的考察;二则研究多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对其中典型的显化现象进行统计,鲜少关注译文语篇特征,对意义或语义层面上的显化研究有待深入[19],这种研究范式难以深入解析显化现象产生的内因。
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胡开宝等提出的显化分类框架[14],将散文英译中的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结合体认翻译学的体认机制,分析《散文选(一)》中译者显化策略的运用。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1) 为实现意合与形合的转换,《散文选(一)》是否存在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上的显化翻译?(2) 若存在,显化策略应用及其成因如何?
(一) 汉语的隐性特征和英语的显性特征
不同的语言形式反应不同的现实世界。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认为原文和译文都是基于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的活动,其核心原则是现实——认知——语言[20]116。过去几十年里,英汉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如此形彼意,此简彼繁,此刚彼柔,此客彼主等[21]5。受中国传统哲学背景(儒释道)及文化长期影响,汉民族表现出一种重整体、讲含蓄、重顿悟、重主体的思维模式及认知心理图式[22]。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汉语是重心神领会的语义型语言,注重隐性连接和语义连贯,以神统法、以意驭形。英民族则受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和欧洲理性主义的影响,在语言形式上具有一种重客观理性、重逻辑、重结构完整的鲜明特征。英语是形合语言,注重显性连接和形式接应,以法摄神,以形寓意。也就是说,不同民族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知的差异最终会体现在语言上。
(二) 中英语言差异对翻译的启示
鉴于汉语语法是隐性的,英语语法是显性的,英汉互译过程中要做到形式上的对等,必须进行源语到目的语语言结构的转换,即语法型与语义型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树式结构语言和竹式结构语言之间的转换[21]81。若盲目直译而没有顺应译语的语言形式,译文就会拗口、不自然。体认语言学认为,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必然象似于认知,且在认知作用下一定程度上象似于现实[20]307。因此,重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译者的翻译思维认知要契合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习惯。
三、研究方法
(一) 语料选择
如鲁迅所说,“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23]2。《散文选》共四辑,是大学英语专业选用最广泛的翻译教材,其内容涉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大批杰出人士的代表性作品,如李大钊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胡适的《不要抛弃学问》、朱自清的《背影》《匆匆》、老舍的《想北平》、巴金的《做一个战士》、梁实秋的《时间即生命》以及季羡林的《文学批评无用论》等,皆寓意深邃,为警醒世人之作,散文中鲜活的思想至今读来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的译介都有较为成功之处,而抱憾之处在于散文译介受到“冷落”,而《散文选》是对中国知识层面的代表人物思想的译介,是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人思想脉搏的一面三棱镜[1],也是国内翻译教学课堂上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教材。鉴于此,笔者选取《散文选(一)》中的名篇并细致阅读,对比原文,发现英译文中存在许多显化现象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 语料分析
本文拟根据相关学者对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以及语篇功能信息显化的定义,从这三个角度对张译散文作品中的显化进行分类,研究发现译者在词法、句法、篇章层面都实现了化隐为显的操作。当前翻译研究的重点转向“翻译过程”,需要从认知角度来深入解释译者大脑“黑匣子”的运作机制。研究翻译过程必然要关涉译者认知加工的程序和方式[20]549。而王寅所提出的本土化理论体认翻译学表现出极强的应用性和解释力。故此,本文借助体认翻译学中的体验认知、隐转喻、事件域认知模型等体认机制考察了这一操作背后的动因。
四、张培基散文英译显化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概念功能信息显化
概念功能是指人们使用语言描述主客观世界,所表达的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刻有民族烙印。语言形式的不同表达的背后是民族心理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这是英汉对比更为深层的对比。所以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同时需要关注原文语码隐含的概念、文化、意图。概念功能信息显化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原语符号所隐含的概念功能信息明朗化[14],具体表现为文化意象显化、概念意义显化、语用含义显化等。
1 文化意象显化 文化意象信息顾名思义指将原文中的深蕴的文化信息明晰化表达出来。体认翻译学强调不同民族在体验和认知上的差异最终会体现在语言形式上。文化意象或成语蕴含着一个关于民族的人性、人生和人情的认知结构,其形成离不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在经过多个类似事件的认知加工后,概括出原型意义,从而成为了某一地方区域的固定表达,具有了约定俗成性。鉴于此,译者在翻译文化信息时要协调运用解释性翻译、厚译、套译等技巧,将使译文既符合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认知理解的需求,同时准确完整地将原文承载的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显化。
例1 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账……[23]268
译文:It may be a modern version ofWu Yi Xiang,a special residential area of nobility in the Jin Dynasty southeast of today’s Nanjing,whereeach family…[23]271
译文除了语言衔接形式上存在显化现象外,内容意义层面亦有之,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往往含有丰富的文化负载词,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例1中的“乌衣巷”是一个文化负载词,曾是晋朝望族居住地,隐喻豪门贵族曾经荣华富贵,后来家道中落、败落凄凉。翻译此类意象时,直译并不可取,“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8]。体认翻译学认为语言层面的翻译可以采用字词兼认知的方法[20]340,传递原文的文化意象。译者采取了丰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处理“乌衣巷”,明示了原文所隐含的文化信息,增强其可读性,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英汉民族中会使用不同的意象表示同一喻意,归根到底是体认方式的不同。“桃花源”,语本《桃花源记》,隐喻一个避世离俗、象征着美好生活的地方。该表达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但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可能会产生“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因此,体认翻译学认为译者可以基于认知层面处理此类文化意象,主要存在两种方法:其一,直接译出原意象的原型意义;其二,换用译语中的物象或意象来反映认知意义[20]341。张培基采用“直接套用”的译法[24],直接套用英语中的单词,将“桃花源”转换成译语读者熟知的Shangri-La(香格里拉),意象不同,喻义相似,“貌离而神合”,处理得当无斧凿之痕。“香格里拉”语出自James Hilton的《消失的地平线》,是一个远离喧嚣,与世界隔绝的神秘之地,这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异曲同工,达到翻译等效。又如译者在翻译作家老舍《想北平》时,文中“九牛一毛”套译为英语习语“a mere drop in the ocean”,转换了形象,“形异而义似”。
2 概念意义显化 概念意义显化是指译者倾向于在目的语文本中明确交代意义笼统词汇或抽象词汇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14]。在散文中,有些语言表达具有模糊性,符合汉语意合的特点,是读者责任型语言,需要读者根据语境领悟其含义。体认翻译学强调将认知意义与当前语境中的事件联系起来。例如,张培基在翻译李大钊名篇《今》的题目时,基于现实层面[20]343,创造性地译成了TheLivingPresent,增译“living”用以强调“present”在语篇中的内涵,暗合美国诗人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诗歌APsalmofLife一诗的名句“Act, act in the living present!”凸显了对青年人珍惜当下的谆谆教诲: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Make use of time if you love eternity)。
例2 不管厂里也好,里弄也好,有事找陈伊玲准没错。[23]278
译文:Whether the factory orher neighborhoodwas in need of some help, she was always considered the right person to approach.[23]282
例2中,“里弄”是上海方言,意为胡同。在翻译时,如若直译成“alley”,目的语读者将会产生理解困难,原文语境中的“厂里”和“里弄”指的是该场所里面的人。“里弄”是“全豹”,“里弄里的人”是“豹的斑纹”,前者的概念更大,这其中实际上是借代或转喻(metonymy)手法的运用。隐转喻实质是“突显(salience)”问题[20]278,原文突显一个“整体”意象来指代“局部”。原文的语言符号隐匿着不言而喻的文化意义,并且可以在特定语境中被激活。由于语言发轫于人的体验和认知,一方面,原语文化中的人对此十分熟悉,很容易激活记忆中的认知框架。另一方面,对于译语读者而言,很难激活类似的认知。为减少读者的语用推理,需要译者填补默认值(default value),翻译时作显化处理。故译者采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借代式翻译,以部分代整体,将“里弄”这一意义显化为“街坊(neighborhood)”,减少译语读者阅读过程中所付出的认知努力。
3 语用含义显化 语用含义显化,即译者直接译出原文中一些修辞或表达较为含蓄语句的语用含义[14]。语用学注重研究在特定语言交际环境中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语用学的意义观”注重语言成分的用义,用义在句级水平上的表现称为语用含义,需要借助语境推导出来,对于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张培基在翻译过程中将源语的委婉语句或隐喻等修辞在具体语境中的语用含义显化,遵守了语用翻译学的合作原则,准确传达原文作者意图,避免信息晦涩难懂。
例3 ……就一个人跑去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23]106
译文:…I’ll go strolling around the streets aloneon an empty stomach, or shut myself up in my small roomwith nothing to eat.[23]111
隐喻是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两种概念建立的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域的联想。“喝西北风”和“喝自来水”是惯用语,其生成受到历史因素、心理因素和联想因素的影响。在冬季,若肚子空空,再被西北风(西伯利亚寒流)一吹,给人饥寒交迫的感觉,让人不禁将“喝西北风”与“挨饿”关联起来。由于西北风这一概念的产生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外国读者无法在其认知领域进行概念关联。“喝自来水”亦同理。鉴于此,译者遵守语用学的合作原则,依据认知层面的翻译,放弃物象进行隐喻认知加工策略[20]335,直接显化其修辞的语用意义,类似于意译。故译为“on an empty stomach”和“with nothing to eat”,使译语读者从译文中获得与原文读者极其类似的感受,但这种译法无疑流失了原文中所要传达的中国文化元素。
王寅认为,“异化”和“归化”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可采用“异化兼归化”的策略,可以弥补单独使用一种方法造成的缺憾[20]275。一则让译语读者感受异域风情,促进文化互通,二则使读者通晓其义以不影响正常的阅读。主要包括直译+意译、直译+注释和以注点题。例如,张培基将表达友谊深厚的“总角之交”和“竹马之交”合译为“children playing innocently together”,虽显化了文字意义,易于读者理解,却流失了中国文化元素,属于欠额翻译。冯全功指出,翻译时添加注释能为译文读者提供足够的文化背景,扫清理解障碍,因此对典故进行直译未尝不可[17]。笔者认为像“总角之交”这类文化表达,可以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既能促成交际,又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
(二) 人际功能信息显化
语言的人际功能是指说话者在具体情景中表达他的态度和判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人际功能信息显化主要指译者凸显原文隐含的语篇中人物的语气和态度以及语篇中人物的情感、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14]。具体表现为情态意义显化和评价意义显化。
1 情态意义显化 散文具有“含蓄美”,表达比较委婉,留有余地。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句间暗含的情态信息,根据语境揣摩其情态意味,并借助情态动词加以显化。
例4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我走了;到那边来信!”[23]48
译文:I said, “Dad, youmightleave now.”…“Imustbe going now. Don’t forget to write me from Beijing!”[23]51
例4原文出自朱自清《背影》中作者与父亲的对话,“你走吧”根据语境可以推出语气较弱,译文使用“might”弱化了句子的语气,以示晚辈对父亲的尊敬。而“我走了”说话者是父亲,根据语境,父子双方到了离别之际,英译添加“must”强化了父亲不得不与儿子分别的动作,蕴含着父子依依惜别之情。显然,“must”的语气要强于“might”,译者的细致处理实则凸显了情境中人物角色关系、身份和地位,十分妥帖。
2 评价意义显化 评价意义显化主要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动机、意识形态和他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在散文英译过程中使用带有评价性意义的形容词或副词对原文隐含的价值判断加以明示,以体现说话者的态度和情感等。
例5 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23]364
译文:I find it really hard for meto subscribe to those views which describe cooperation as “surrender”, “humiliating”, “suffering losses” or “being duped”.[23]368
汉语非常遵循时间顺序反应因果关系,构句如同临摹绘画,与现实事件发生顺序相似。该句是一个“叙事——表态”事件域,符合汉语“顺序象似性”原则。而英语是“蒙太奇式”语言,可按照语言自身表达习惯组句[20]310。译文符合语言突显象似性特点先说重要信息,以引起听着注意[20]307,且遵循英语先“表态”后“事实”的习惯,显化了句与句之间的语义逻辑,使得语篇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语义整体。
(三) 语篇功能信息显化
语篇功能一般通过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进行体现。对应地,语篇信息功能的显化主要指句法结构显化和逻辑关系(衔接)显化。体认语言学中的“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al)”适用于翻译过程研究,解释原文语句所描述的事件域是如何在译语中再现的[20]304。译者根据体认解释出原文所描述事件域中的成分要素,并在译语中寻求对应关系。
1 语法结构显化 体认语言学强调语言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对语言结构的描写要体现认知过程。受传统思维模式影响,汉语在造句谋篇上形成了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22]。在保证语义逻辑连贯的前提下注重隐性衔接,句段如竹节般并置开来,连接标记不明显,“竹式结构”是汉语流水句的一个特征。而英语句子往往以形统神,主谓提纲挈领,其他成分依附句子主干,结构完整严谨,以丰富的形态变化制约句式布局,呈现空间性“树型构造”的特点。汉英民族思维认知的差异致使在英译时宜采用增译法,以顺应英语形合特点。
(1) 代词显化。汉语表现出话题象似性的特点,分句的话题象似于思维的起始点,主语可以省略[20]307,这反映了汉语重于意念,“万物皆备于我”,体现“人治”。而英语主谓结构严谨,每个句子都有主语,没有主语就是省略。鉴于此,在汉译英过程中为避免歧义使原文信息更明确,译者把散文中隐去的主语转换为英语的显性主语。
例6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23]21
译文:Some people say, “Onceyouhave a job,you’ll come up against the urgent problem of making a living.How canyoumanage to find time to study?[23]23
汉语意合,构句不拘泥于主谓结构,在不影响语义逻辑关系的前提下,常常采用零回指,且频率比英语要高,上文的例5和例6都出现了零回指现象,人称省略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语文化的高语境特征[17]。英语注重形式结构,必须符合硬性语法特点,英译时需要主语指认并进行显化。在英语中可以借助代词前指代正常的、无标记的语言形式,而汉语则常用零形式。故上述例子中译者分别增译人称代词“I”和“you”。根据图形—背景理论[20]277,译文中突显(Salience)人称代词,可看做图形或焦点,并以此为认知参照点来审视其他因素。译文显化了原文隐含的信息,关联到语言的认知机制及其对应的现实世界,生成符合译文读者的识解方式和习惯的译文,从而保持了语篇的连贯性。
(2) 时态显化。英语有时态变化,而汉语没有此类变化,通常借助语序、词语或意义隐含来表达语法意义。汉语是临摹式语言,语序象似于时序和文化定势,具有显著的顺序象似性的特点[20]307,各句段间按照事理发展顺序来暗示关系,这与汉民族重于主体意识和整体思维的认知特点有关。散文是抒发作者情感记叙类文学体裁,包含对过去的叙述、对现在的感悟或对将来的设想,必定涉及语法时态问题。鉴于汉语句子中的时态表征渗透在字里行间不够明显,通常需要读者根据具体语境中体会出来,是读者责任型语言,因此英译时需要采用显化的时态标志。
例7 你真比来的时候还瘦了。你没有去照照镜子。[23]332
译文:You are thinner than when you firstcamehere.Haveyoulookedat yourself in the mirror?[23]358
例7表示过去时的“came”以及现在完成时的“have looked”都是译者根据语境进行的转换。原文的时体特征并不明显,英译需变化动词的形态以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3) 化“竹”为“树”。流水句包含多个句段,追求流动的节奏,人称代词常采用零回指,句段间没有显性的关联词语,结构松散且变化多样,不滞于形,句段可以是句子、短语、或形容词词组等,但语义逻辑表达清晰。
例8 一个憔悴异常的乡人,衣服补衲的,头发很长,在他底腋下,挟着一个纸包。[23]327
译文:Hewas an emaciated-looking peasant,dressedin patched clothes andwithunkempt hair,carryingunder his arm a paper-parcel.[23]353
例8原文是由5个句段组成,没有逻辑连接词。认知语言学认为,在复合句中,主句是焦点,从句是背景,与人类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顺序一致。主谓宾结构是图形/背景理论在句法层面的体现。主语“he”是施事,是能量传递的源头,概念上凸显的事物,位于运动链的首位。从而确定了凸显部分,剩余信息常被看作背景,作状语。张提取事件链中“一个憔悴异常的乡人”作为主干,看作能量传递的起点。使用过去分词“dressed”和现在分词“carrying”分别引导的伴随状语对逻辑主语“乡人”进行更加具体的描述。运用介词短语“with unkempt hair”修饰主语。这种“树式结构”的转换更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
2 逻辑关系显化 翻译实践中选择正确的衔接形式有助于生成连贯的篇章。语言象似于体验和认知,古汉语没有句读,句间的语义逻辑全凭读者领悟。所以汉语造句谋篇侧重隐性衔接,句间关系模糊、隐含,而英语连接手段多且使用频繁,用于表达语法和逻辑关系,汉英此形彼意的特征在逻辑关系组织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条件关系、转折关系、递进关系等。因此,逻辑关系显化指英译时借助关联词、介词等手段以显化原文本隐含的认知逻辑。例如上文例1中,译者通过增译关系副词“where”引导从句,将汉语流散的各句段的主从关系凸显出来,符合英语树式结构的特征。
(1) 条件关系显化。
例9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23]55
译文:Ifswallows go away, they will come back again.Ifwillows wither, they will turn green again.Ifpeaches shed their blossoms, they will flower again.[23]57
中国的作品翻译要让外国人知之、甚至乐之、好之方可,要尽量模仿或采用符合译语的表达方式[24]。“条件—结果”可视为“因果事件域”,应当遵循“顺序象似性原则”[20]321,按照“先条件,后结果”的顺序构句。译者在汉译英过程中,为明示原文隐性的条件逻辑关系,都添加了连词“if”成为显性条件句。要实现“形似”“神似”缺少不了显化这一必要途径[10]。例9中,译入语保留了译出语的排比结构,力求形似、神似,三个连贯的排比句富有节奏感,保持了原文篇章连贯,还原了原文的韵味,唤起了读者的对于时间流逝的思辨。同时,译文以“if”起句,读者脑海不禁想起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西风颂》中的名言:“If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away?”译文用词洗炼,语言地道,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接受和审美体验。
(2) 递进关系显化。
例10 母鸡们咯咯咯地叫起来了,鸡雏们也啁啁地争食起来了。[23]122
译文:Atthe clucking of the hens, the chicks scrambled for the feed, chirping.[23]123
例10中“母鸡叫”和“鸡雏争食”是事件链上的两个接连着发生的活动,体现汉语“顺序象似性”特点。译者增译介词“at”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形显意,明示了鸡雏抢食是对母鸡叫声的反应。英语是作者责任型语言,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减少读者为理解内容所做出的语境推导努力,使用衔接手段严谨地表达言者之意,使译文既符合译语读者的思维习惯,又准确传达原文字里行间的逻辑意义。
例11 我不禁汗涔涔泪潸潸了。[23]55
译文:At the thought of this, sweat oozes from my forehead and tears trickle down my cheeks.[23]57
例11中,“at the thought of this”是译者根据前后语境增添出来的,承上启下,更符合英语逻辑。不过,从英文语法上讲,似乎将“at the thought of this”改为“when I think of this”更好。逻辑关系的显化体现了把汉语悟性思维转换为西方理性思维的倾向。
总之,译者在进行句子翻译时只有先站在原文作者的视角体验,才能正确地认知原文,并且要充分考虑汉英两个民族之间的认知差异,显化原文句子的意义,生成地道的英语表达。语言象似于认知,也就是说,翻译过程是语言认知的过程,绝不能完全照搬汉语的表达模式,还应该考虑译语读者的现实体验和认知努力,尽量减轻其认知负荷。
五、结语
本文基于张培基《散文选(一)》,以体认翻译学为关照,借助实例探讨了中国现代散文英译文的显化现象。研究通过实例验证了Blum Kulka所提出的显化假说。在散文英译过程中,概念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较为常见。概念意义显化主要通过将原文本中意义笼统词汇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明晰化。语用含义显化直接译出原文中修辞或含蓄语句的语用含义,以帮助读者理解。语篇功能信息显化主要体现为使用关联词、介词或使用其他手段,使得译文前后衔接自然,促进语篇连贯。出现不同层次显化的主要原因是语言形式和文化背景、体验认知的差异。英汉语法特征体现出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英语语法体现“法治”,富有强制性,重形合,以法摄神,以形寓意,形式化显化程度较高;汉语语法体现“人治”,富有弹性,重意合,以意驭形,形式化显化程度较低[21]13。显化程度的高低除了语言形式化程度,还有赖于译者对于原文的解码认知,对于目标语读者的判断以及译者思维框架下运用的显化手段。综上,汉译英时需要进行一定的显化,译者要综合运用翻译方法和技巧,使译文既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又可以准确地传达原文文字表征下深蕴的意义,符合读者阅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