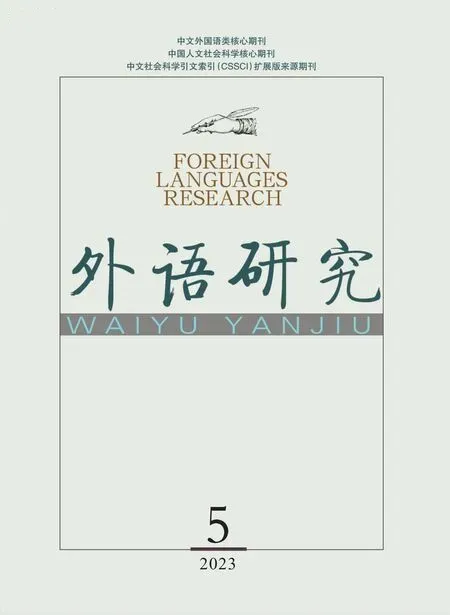《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家庭抗逆力论析*
2024-01-02王秀梅
申 圆 王秀梅
(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0.引言
当代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47-)的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The Brooklyn Follies,2005)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作品。主人公内森·格拉斯(Nathan Glass)看似行径荒唐,却能在面对各种破坏性的经验时进行优势取向分析,整合社区与家庭资源,建构人际间的信念共享系统,最终实现了对“荒唐”的逆写。奥斯特在接受采访时称,《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实质上是“对普通人的礼赞,对日常生活之美的礼赞,关乎活着的神秘与喜悦”(Morris 2013:165),这种礼赞指向了后“9·11”时代“小说建构共同体模式的能力”(Heffernan &Salván 2013:163),指向了具有“凝聚性和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关系”(李金云2016:137)的伦理吁求,指向了人物集群在布鲁克林这座城市体验到的“地方依恋”与栖居诗意(朴玉2014:74)。奥斯特在该作中建构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家庭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结构性抗逆力的展现而使每个家庭成员“被赋予声音、得到承认、得以命名”(Trofimova 2014:156)。与奥斯特在《纽约三部曲》(The New York Trilogy,1987)、《巨兽》(Leviathan,1992)、《日落公园》(Sunset Park,2010)等作品中刻写的碎片化城市经验不同,《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关注碎片的整合,聚焦身份重构、对话生成的过程,而对此过程的叙述与家庭抗逆力紧密相连。
家庭抗逆力研究始自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初是针对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语境中的家庭压力问题而进行的研究。20 世纪50 年代,希尔(Reuben Hill)提出了衡量家庭压力适应性的ABCX 模式:A(the event/stressor)是指压力事件,或称压力源;B(the family’s resources for meeting the crisis)指家庭抗压资源;C(the family’s definition of the event)是指家庭对压力事件的定义;X(family crisis)代表导致家庭日常生活节奏遭到破坏的危机(Hill 1958:139-150),明确了家庭抗逆力的要素构成,并指出A 与B 和C 的相互作用导致X 的生成。在ABCX 模式的基础上,20 世纪60 年代后,强调“后危机变量”(post-crisis variables)的Double ABCX 模式和FAAR 模式(model of 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sponse)(McCubbin &Patterson 1983:11),将家庭类型(family types)考量在内的T-double ABCX 模式(T 代表家庭类型,McCubbin&McCubbin 1989:9)等相继萌生。随着病理学和临床社区实践的完善,家庭压力问题研究在新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者从家庭压力理论(family stress theory)和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中汲取理论养分,侧重探赜危机处境中家庭自我修复的潜能,其系统性、动态性、灵活性、情感支持性、预防导向性和正向展望性标志着家庭问题研究“从问题焦点、缺陷视角向能力基础和优势视角的范式转变”(纪文晓2015:29)。21 世纪家庭抗逆力研究的代表人物沃尔什(Froma Walsh)指出,“抗逆力”(resilience)是“从逆境中复原,并变得更为强大和善于利用资源的能力”(Walsh 2011:4),而“家庭抗逆力”(family resilience)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种应对与适应性的过程,是家庭作为功能实体通过信念体系、组织模式、沟通过程在应对挫折、处理危机、缓解压力等方面所发挥的效力,强调在关系网络中实现止损效应,促成个人和家庭的正向成长(ibid.: 15)。在《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家庭抗逆力是建构情感共同体、推进叙事进程的重要因素。奥斯特对内森一家特定的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行为系统的书写突出了能力取向的家庭抗逆力在后“9·11”时代的精神指引作用,反映了奥斯特对主体间性、家庭效能、幸福伦理等问题的深刻思索。
1.家庭信念系统: 能力取向的家庭图式
家庭信念系统是指家庭作为抗逆单元面对危机时,家庭系统及其文化中主要的共有信念(ibid.: 54-55)。《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家庭共有信念可以归结为:在危机中聚焦能力,促成转机。小说的主人公内森是促使这种信念生成的核心人物。内森是一位56 岁的退休保险经纪人,罹患肺癌,与妻子离异,选择回到童年的故乡布鲁克林疗伤以寻求精神上的新生。内森的女儿雷切尔(Rachel)、外甥汤姆、外甥女奥罗拉(Aurora)等是处于家庭关系网络关键节点上的若干失意的人物,他们因受内森“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积极哲学的影响而重新诠释危机事件,重拾对自我、对家庭、对生活的信心,并形成预示着良性家庭生态的关系图式。
为逆境创造意义并将其渗透到家庭互动过程中,是小说中家庭信念系统形成的关键。内森通过与外甥汤姆的对话,分享家庭故事,传递家庭信念,为家庭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情形正名,个体在家庭蓝图中确定自我未来发展的坐标,从而生发出新的、健康的生命感受。在讲述家庭故事的过程中,零散的信息会编织成有意义的文本,使原本隐匿的家庭成员再度清晰,并谱写新的家庭乐章。讲述家庭故事促成家庭成员转危为安,并强化家庭成员的互动,勾勒出富有建设性的家庭关系图式。在小说中,内森和汤姆通过交谈使失败变成共同的经验,使对抗逆境变成家庭故事的关键词,降低失败带给人的屈辱感,这种“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为家庭生活创造了意义。内森以为汤姆会在伯克利或哥伦比亚这样的名校任教,但实际上,汤姆经历家庭变故、学业失败、求职挫败的打击后,自暴自弃。内森鼓励汤姆将目光转向生活中各种美好的事物,最终令汤姆的事业重整旗鼓。而汤姆对内森的精神安慰也同样重要。内森将与汤姆“尽可能经常地共进午餐当作一件要事来做”(奥斯特2008:73;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午餐使例行的家庭互动仪式化,而仪式化的结果是使温馨的交谈情境不断复现,淡化了内森内心孤寂无依和一事无成的感觉,使家的意义在仪式中生成,使个人危机变为共有的挑战,从而改变家庭功能失调的境况。
小说中家庭信念系统的形成还得益于基于家庭脉络的、对未来的正向展望。尽管内森身患癌症,但他仍以一种聚焦潜能的视角将与威胁相关的信息适当过滤,并吸纳这些威胁性信息带来的启发,这种乐观的精神为整个家庭共识愿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起初,内森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之后,从纽约回到出生地布鲁克林,搬进新居,在后花园种花,到公园散步,去“公园坡地理发店”理发,到“电影天堂”店铺租录像带,去“布莱特曼阁楼”看书,这种“忙着活”的态度表明内森并没有因为疾病的困扰而为自己的生活设限,而是通过让自己忙碌起来的方式增加新的选择项,对压力事件作出新的评估,藉此减弱“抑制性的信念”(constraining beliefs)(Wright et al.1996:5)的影响力,而增强了“促发性的信念”(facilitative beliefs)(ibid.:229)的效能。内森试着从丧失健康的痛苦中解脱,去感受周围事物的美好。乐观精神的持存驱散了内森的无助感,他并不认为“困境是持续的、无止境蔓延的,总是针对自己而来的”(Walsh 2011:66),“不论医生对我的病情作任何预测,要紧的是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命中注定”(3)。这种对未来的正向展望通过内森传递到每位家庭成员身上,建构了可以强化正向思考的家庭环境,聚拢了挑战危机时家庭成员之间共享价值感的信心。
内森不是独自挑战顽疾的“独行硬汉”(a rugged individual)(Dalmage 2004:212),而是想方设法使整个家庭获得对未来掌控力的人物。内森的女儿雷切尔生性坚强,却也因丈夫出轨而面临婚姻崩溃的痛苦处境。内森认为雷切尔的丈夫特仁斯(Terence)撒谎说自己没有外遇是因为他不想失去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应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建议雷切尔暂时忘掉特仁斯一段时间,并劝她说两人之间还有很多希望,“一起欢度未来的希望。有孩子的希望。有猫有狗的希望。有树有花的希望”(222)。内森关注家庭关系修复的可能性,并建议对有过错的家庭成员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加速了雷切尔和丈夫的情感止损过程,避免了在非理性状态下引发关系的决裂,为重建可协商的伴侣关系创造了机会。雷切尔在不幸流产之后再度怀孕,而一个即将诞生的孩子作为夫妻情感和代际情感的纽带,凝聚了整个家庭对未来的期待,并改变了家庭生命周期的律动,使家庭经历了从活力丧失、创伤愈合、生机复萌的转折,让希望可视化,从而增强了家庭信念,提升了“关系质量”(relationship quality)(McKinley 2022:112)。内森除了帮女儿雷切尔度过婚姻危机之外,还通过分析压力源、压力事件和压力症状,帮助外甥汤姆重新振作,帮助外甥女奥罗拉挣脱作为宗教狂热分子的丈夫的魔掌,帮助露西与母亲奥罗拉重聚。内森这一系列的努力使整个家庭获得了一种从核心人物出发、成员间交互影响的“能力取向”(competence-based)(Walsh 2011:150)的危机应对模式。这种模式意在发掘家庭环境中可利用的资源,肯定成员的长处和优势,赞赏成员积极的意图,将焦点从抱怨转移到目标,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为“系统取向”(systems-based)(ibid.: 139)的正向思维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拓展了家庭的关系性意义。
除了为逆境创造意义和正面的展望之外,“灵性”(spirit)是小说中家庭信念系统形成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在关爱和亲密的关系中,难免会有些风险和失落,因此家庭就需要一个能够超越他们经验与知识的价值系统”(ibid.: 72)。灵性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信念支持,包括“相信人类的终极状况,或是一套人们努力达成的价值观,也可能包含无法通过平常的语言及意象来表达的神圣或神秘的经验”(ibid.:73)。哲学思想、艺术追求等富有超验性和灵感的精神表达构成了灵性的主要内容,使家庭成员生发出一种人与自然、与世界相联结的、更为宏大的生命意识,激发家庭成员的精神共鸣以锻造更有价值感的家庭文化。在小说中,文学成为内森和汤姆的心灵庇护所,为家庭提供了战胜厄运的灵感。他们谈论梭罗、爱伦·坡、弥尔顿、惠特曼、马拉美等作家的趣闻轶事和写作风格,藉此逃离此时此地的束缚,间接地丰富了内森和汤姆的时空经历,营设出家庭的精神“逃逸线”。汤姆支持内森撰写《人类愚行大全》(The Book of Human Folly),并肯定内森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文学以灵性影响着内森一家对人生逆境的意义建构与回应方式。梭罗和其他作家成了这个家庭中不见踪影却又至关重要的成员,无声地讲述着创伤与复原的故事,激发内森一家重新捕捉快乐的能力,促成家庭成员之间深层次的精神交流,减轻成员的预期性焦虑,最终以“有益健康的”(salutogenic)(ibid.: 59)信念系统引导家庭掌握塑造精神共同体的艺术,以灵性开启新的生命历程。
2.家庭组织模式:统合感作用下的协同抗逆
家庭信念系统是内森一家面对逆境时在价值观支撑,而具有良好应变品质的家庭组织模式(family organizational patterns)则是内森的家庭成员间形成关系性抗逆力的结构因素。组织模式是“家庭危机的缓冲器”(family shock absorbers)(ibid.: 83),受家庭内部和外部各种规范的形塑与制约,为处于动荡和危机中的个体重获家庭的“统合感”(sense of coherence),即“家庭在应对一种特定的危机时所感觉到的一致性”(ibid.: 60)提供了组织保障。有效的家庭运作包括以下组织要素:“弹性”(flexibility)、“联结感”(connectedness)、“社会与经济资源”(soci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ibid.: 84)。在小说中,弹性为人物调节自我内心的失序状态、修复破坏性的家庭组织模式提供了认知支撑;家庭成员间的联结感在主体间性层面为新的家庭组织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情感支撑;社会与经济资源,尤其是社区资源,则为家庭抗逆力的巩固提供了更宏观的结构性支撑。正是由于这三种要素的协同介入,在统合感作用下的抗逆模式最终呈现出在场性。
内森的家庭有一种“适应改变的能力”(capacity for adaptive change),这种弹性组织模式使家庭整体的抗逆力如同被拉伸的弹簧般“向前弹出”(bouncing forward)(ibid.),顶住压力,以灵活性调整僵化的家庭关系,并满足家庭与时俱进的需求,建构新的家庭秩序和自我内心的秩序。首先,内森的家庭做到了在破裂中维持稳定。内森寻花问柳导致自己婚姻解体,但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并采取写信的方式试图改善父女关系。“您不知道您的信对我有多重要,近来有那么多坏事情发生,这正是我需要听到的。如果我现在能得到您的支持,我想我能熬过一切”(218)。内森主动预设了家庭的变故对女儿可能产生的重创,因而做出种种努力重申自己作为父亲的承诺与责任,重建可信赖的父亲形象。雷切尔因为内森努力修复关系而选择原谅父亲,逐步还原以往的生活节奏。内森在一种关系的动态平衡中弥合情感的裂痕,并通过强化扩展亲属系统中成员的联络调整原本松散的家庭结构,向女儿暗示,即使父母离异了,家仍然在,引导女儿将家人欢聚一堂的场景作为一种在内心深处所召唤的“内在意象”(internal image)(Forrester 2000:13)刻入自己的记忆,使家庭的未来变得可期,而不是以放任自流的态度将女儿的命运和家庭的未来灾难化。这种适时的结构调整使内森一家克服了对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惧,增强了整个家庭度过危机的信心,提高了家庭抗逆力。
其次,小说中家庭的弹性模式还体现在“多元家庭结构”(varied family structures)的呈现方面。内森、女儿雷切尔、雷切尔的丈夫特仁斯、雷切尔腹中的孩子代表了父母身处两地的单亲家庭及血缘延续所生成的新的家庭脉络。而内森、内森的妹妹琼、内森的外甥汤姆、外甥女奥罗拉的联结则代表了由直系血亲家庭形成的关系性抗逆力的案例。内森收留了奥罗拉离家出走的女儿露西,组建起由亲戚照顾的扩展家庭。内森家庭的弹性模式,已相异于20 世纪50 年代在美国达到顶峰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结构”,不再遵循传统的双亲家庭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功能的丧失。多元家庭结构具有人际资源聚集与分散的灵活性,在抚育和保护脆弱的家庭成员方面可形成即时性的照顾团队,比如内森和乔伊斯恋爱后,露西就搬到了舅舅汤姆和舅妈哈尼的住处,并受到两人的悉心照料,直到露西和母亲相聚才搬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仨已凝聚为一个亲密的小家庭”(263)。内森说露西是他们家庭中每个人的孩子,家庭成员间为了孩子协同合作,聚焦最有效的照顾方案,而非为抚养权争执不下,“较高的家庭抗逆力与较低的育儿压力相联结”(Kim et al.2020:651),这种“包容性的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Walsh 2011:94)塑造了内森一家既有高度的弹性又能相互支援的家庭伦理。
联结感是家庭组织模式的第二个核心元素,是内森的家庭成员间保持合理情感结构的体现。联结感在此意指个体在家庭中所寻求的情感联系与满足(ibid.),既包括成员间相互关心、提供慰藉这一共同目标,也包括成员间对彼此性格差异和需求差异的尊重,“高度凝聚”(high cohesion)或“紧密联结”(strong connection)并不意味着“纠缠”(enmeshment)(ibid.:96)。内森一家成员间的相处之道是一种“有距离的亲密”(intimacy at a distance)(ibid.: 97),成员间保持着清晰的独立空间,又不乏彼此支持走出逆境的承诺和行动。内森收留了离家出走的露西,以临时监护人的身份建立起与露西的代际联结,照顾这个九岁女孩的饮食起居,并将其未来纳入自己的未来。内森在家庭层级组织中的家长身份助其树立起领导者的权威,但他并未越界制定各种行为规范要求露西遵从,而是选择倾听孩子的心声,“让她确信确定权完全在她手中”(134)。内森通过建构张弛有度的联结感,使露西走出父母失职、“同理疲劳”(compassion fatigue)(Figley 1995:1)的危机情境,使其完成了从失去在家庭中受重视的角色到获得情感补偿的过渡,使其感受到从家庭失能到家庭统合的变化,也使其更懂得与自己内心的恐惧和解,并增强对家人的信任。“求同存异、亲密有间”成为该家庭联结感的合理化表达,打破了家人之间疏离与防备的藩篱。相较于石黑一雄《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中的耻感文化对家庭生活的压抑,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坚果壳》(Nutshell,2016)中的复仇和阴谋对家庭凝聚力的冲击,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西北》(NW,2013)中多元文化语境对家庭成员身份定位所带来的困惑,保罗·奥斯特以刻写家庭成员间适宜的联结感建构了新的情感图式。
社会与经济资源是家庭组织模式的第三个核心因素,其中社区资源作为社会协同抗逆的重要一环,增强了小说中家庭系统的开放性,令家庭成员获得新的抗逆资源,尤其是一种建构在同理心基础上的团体情境,故而良好的社区效能和人际交互作用成为内森一家探寻危机解决之道的新契机。布鲁克林对内森的情感召唤建构了重返母腹的安全感,而社区作为承载内森对布鲁克林地方经验的重要场域,以其对家庭生活的渗透力进一步帮助内森克服“非家”恐惧,并降低内森一家在面对危机时的无力感。内森所在的社区环境庞杂:白、棕、黑色皮肤的混杂,外国口音的多声部合唱,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迈的养老金领取者,捡破烂的流浪者等等(171),这样的社区没有模范角色和神话传奇,有生活的美好也有不如意,社区如同一面棱镜,映射出邻里及自己的不完美,这种祛魅后的真实令内森欣然接受。雷切尔、露西和奥罗拉因内森与该社区结缘,并感到在这里生活安适自如,该社区的人情风物成为内森一家可分享的共同话题,显示出移情和疗伤的功效。此外,该社区以主体间性的区域性影响,重新营设了内森一家的人际关系图谱,在社区结识的新朋友逐渐成了内森一家在困境中的精神依托。书店老板哈里去世后,内森、汤姆、南希一家和“一些好心的街坊邻里”(210)参加了他的葬礼,邻里共同告慰逝者的过程生成了共享的哀悼叙事模式,对逝者所怀的悲痛情绪转化为生者之间的相互抚慰,促成力比多投射对象的成功转移。邻里之间的关切之情使内森一家的家庭组织模式突破了血缘的局限,转为因地缘关系而萌生的心缘共同体,从而拓宽了“家”的“关系性意义”(the relational meaning)(Walsh 2011:56)。
3.家庭行为系统:规则界定框架下的家庭沟通与问题解决过程
除家庭信念系统和家庭组织模式的支持外,有效界定规则的家庭行为系统有助于家庭成员从聚焦症状到关注力量的状态转化,减轻同情倦怠,实现成员间的良性沟通,解决问题,从而降低家庭失能的风险。内森一家通过清晰的沟通、坦诚的情感分享、合作解决问题,实现了“多重压力家庭”(a multistressed family)(ibid.: 254)治愈性正义的生成。
清晰的沟通要求家庭规则的明确性。规则是用来规范互动、设定行为预期及界定关系的(Minuchin 1974:58-59)。内森希望家人之间能够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需求和顾虑,并获得回应,建构情感共同体,而自我表露和语言反馈可视作内森一家的行为预期准则。非语言沟通以及沉默则可能会减损沟通的清晰度,从而导致困惑、焦虑和误解。九岁的露西因听从母亲的安排,只身一人离家投靠舅舅汤姆。当露西敲开汤姆和内森的门,无论他们问她什么,女孩始终缄默不语。后来露西因不想被送去帕梅拉家寄养,悄悄在内森的汽车油箱里灌满了可乐,以阻止内森将自己送走,但却险些导致车祸。“在家庭成员避免接触、阻碍知识、记忆或恐惧沟通时,那些没有被说出的部分将被压抑,表现为情绪或心理上的症状,或者在其他人际关系或生活情境中表现出来。”(Walsh 2011:109)露西担心自己被送走的恐惧通过她蓄意制造事端而得以宣泄,但这种短暂的情绪释放很快被内疚和自责取代,继而演变为对即将到来的规训与惩罚的新的恐惧。当家庭内部的即刻惩罚降低澄清误会的可能性,会使原本紧张的互动关系继续恶化。内森作为当家人,他与露西的沟通准则是:营设缓释空间,让对方舒解未得到处理的情绪,通过“体恤”的伦理引导对方道出苦衷,清楚了解逆境,与对方充分探讨事件的意义和影响,让听话人与说话人共同表明他们对彼此的预期以采取应对措施,抵挡余震和后续压力。同时,内森通过向露西阐明福祸相依的道理,减轻了露西的负罪感,有助于避免家庭沟通中的相互斥责、羞辱与病态化倾向,让代际危机变得可理解、可处理。
清晰的家庭规则是家庭沟通中抗逆信息得以传递的前提,而坦诚的情感分享是家庭沟通中情绪互动的催化剂,是内森帮助外甥女奥罗拉摆脱丈夫宗教控制的必要条件。在类似全景敞视监狱的家庭中,奥罗拉坦诚分享情感的意愿被教会的权威和丈夫一心尊奉上帝的意志所消解。妥协取代了协商,谨言慎行抑制了情感输出,她的家也变成了负载着宗教训诫的符号空间,不容许正常世俗情感的僭越。斯宾诺莎(2015:97)将“情感”解释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大卫对妻子言行的控制改变了奥罗拉“我感故我在”的存在方式和自发的情感流露方式,活力的衰退使喜悦、希望等积极的情感枯萎,反复的消极互动令奥罗拉在这个难以公开表达情绪的家中感到窒息。内森设法营救奥罗拉,对她说,“我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243),这种真诚的安慰使奥罗拉对投入新的关系和人生追求开始有所希冀。两人从机场到布鲁克林一直交谈,由于内森抚慰性的情感参与,奥罗拉讲述的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了她和内森共同讲述的故事,双方明确创伤经验并彼此回应,有助于推进创伤的治愈进程。
增强家庭抗逆力还需要在沟通过程中合作解决问题。家庭成员之间通过沟通、决策、行动,在关系脚本中进行抗逆实践。奥罗拉与南希的同性恋情可能发展为整个家庭关系危机的压力源,对此,内森所采取的行动是对奥罗拉进行同理关怀,两人通过谈话合作解决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合作解决问题涉及个体的“同步敏感性”(synchronic sensitivity),即能适时“调节对对方话语行为的回应。每个行动接着前一个行动平稳进行,对前一个行动给予确认,并对后续行动发出邀请。参与者最大限度地适应这种彼此交织的行为方式”(Gergen 1998:166)。倘若内森对奥罗拉和南希采取歧视、批评的态度,那么内森的家庭角色可能由发挥领导效能陷入被敌视的脚本,从而加速关系的破裂。但由于同步敏感性,内森对奥罗拉的叙述进行了双重倾听:一方面是奥罗拉讲话的内容,另一方面是他们关系的轨迹,其目的是为了让两人的关系从尴尬情境中解脱出来,逐渐趋于理想境地,化解压力源。交谈双方对彼此言语的肯定有助于在维持关系的过程中专注于可达成的抗逆目标。内森与奥罗拉达成合作关系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彼此意见上的所有分歧,而在于双方在协调关系的过程中能够预设到否定话语生成后可能导致的对家庭关系的冲击,从而通过话语行为中的理解尽量避免意见分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内森与奥罗拉之间的“同步敏感性”构成了彼此的精神支持,指向了两人对新的家庭人际潜能的探掘,以及在避免家庭成员角色刻板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两人的合作意味着彼此作为对方话语意义赋予者这一身份的在场性,继而为家庭建构了不同以往的优势评估框架。
4.结语
奥斯特以能力取向、统合感和动态化为重心的家庭抗逆力书写生成了危机与潜能的对话、个体与关系网络的对话、现在与未来的对话。无论从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还是家庭沟通与问题解决过程来看,小说都展现了以抗逆力为生命线的能量观。这体现了奥斯特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投入的信任,对突出统合感、利于创伤复原的家庭效能的期待,及其对相互关怀、“自愈”并“愈他”的幸福伦理的追寻,建构了突出创伤可愈性的文学路径,为后“9·11”英语小说中的情感共同体书写提供了强调家庭优势视角的独特范式。与奥斯特《纽约三部曲》等后现代风格作品相异,《布鲁克林的荒唐事》现实主义的审美向度中蕴含着作家对后“9·11”时代城市主体日常生活的观照,承载着“正向前瞻”的价值旨归。奥斯特在小说中对家庭抗逆力意义的诠释反映了其对关系福祉的关切,折射出“介入写作”的温度,也映衬出其创作的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