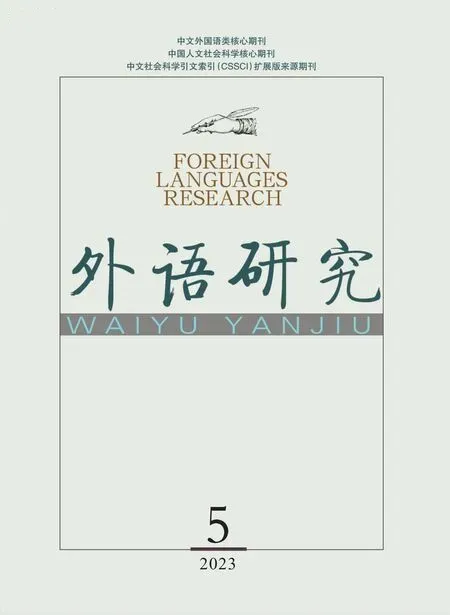语言哲学思想实验的基本特点与常见方法*
2024-01-02杜世洪周方雨歌
杜世洪 周方雨歌
(西南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0.引言
坐而论道,这个词语常用来描述哲学家的工作,即人们在谈论哲学家的工作方式时,总是倾向于使用“armchair”(扶手椅)来刻画他们的工作状态,意指哲学家坐在椅子上思考哲学问题,而不会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忙活(Strevens 2019:1)。然而,却不能由此断言,哲学家不做实验。哲学家常做的实验叫思想实验,而思想实验不仅对哲学研究很重要,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思想活动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Miscevic 2022:21,25)。哲学思辨离不开思想实验,因此哲学家的工作状态可描绘成“四在”:身在椅子上,心在实验室;大脑在运转,观点在云集。
广义的语言哲学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而语言哲学的核心工作是概念考察。哲学家在进行概念考察时,离不开思想实验,例如笛卡尔的恶魔、洛克的王子与鞋匠、霍布斯的忒休斯船、休谟的蓝色阴影、康德的先验空间、莱布尼兹的中国王、尼采的无限轮回、詹姆斯的吉姆等。在现代语言哲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些著名的思想实验,例如罗素的太空茶壶、维特根斯坦的甲壳虫、艾耶尔的鲁滨逊·克鲁索、摩尔的玻璃花、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和缸中之脑、蒯因的土著兔子、古德曼的蓝绿宝石、塞尔的中文房间、罗蒂的对脚人等。思想实验是语言哲学概念分析的重要形式。
语言哲学发展至今,出现了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李金彩,刘龙根2015;李金彩2022;Haukioja 2015)。在性质上,实验语言哲学却是思想实验的具体化呈现,属于哲学思辨的新形式(Ludwig 2018:385)。语言哲学研究不乏思想实验。面对语言哲学中的思想实验,需要思考的三个问题是:思想实验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思想实验的常见方法是什么?思想实验的目的与价值何在?
1.思想实验的基本特点
思想实验是在心灵(mental)实验室里进行想象性的、假设性的、论辩式的概念分析活动(Brown 2011:1;Tittle 2005:x)。思想实验这一术语本身具有隐喻性,但在学理及旨趣上,它与常规实验并无二致。思想实验是在理论探讨、问题思考、观点争鸣、概念甄别等活动中就难点难题而进行假定性说明或推论(王洪光2022)。思想实验在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特别是在哲学追问、逻辑推理、科学探索、语言论证、语义辨析和日常对话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梁义民,任晓明2007)。思想实验常常以奇特的方式直接提供或间接呈现新认识、新思考、新观点等(Gendler 2000:1)。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芝诺的阿基里斯、柏拉图的洞穴、卢克莱修的长矛等都是经典的思想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牛顿的水桶、爱因斯坦的电梯、图灵的模仿游戏、薛定谔的猫等也是著名的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针对专业性的理论问题,而常常使用日常语言表述出来,表面上不乏娱乐性,但在深层里却具有学术启发性。在语言哲学的具体活动中,思想实验常常用于概念分析、假说提炼、认识澄清、分歧化解、观点发布、理论选择、理论推行等。思想实验有助于语言哲学的概念分类与概念辨析。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卡佩兰等人的概念工程研究等都有思想实验性质(杜世洪,田玮2022)。思想实验企图证明的观点或者解答的问题往往是前沿问题或者尚无定论的问题,即思想实验具有先导性、开拓性以及暂时确定性的特点。像普特南的孪生地球、蒯因的土著兔子等思想实验对意义问题提供了先导性和开拓性的启示。
在现有条件无法满足的时候,在无法回答的难题面前,思想实验或许能够提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解答。例如,对于宇宙是否有边界这个问题,至今难有定论,但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利用思想实验,暂时证明“宇宙是无边的”。卢克莱修的思想实验可简述为“卢克莱修的长矛”(Lucretius’s spear)(Tittle 2005:4-5):如果认为整个宇宙是有限的,那么人就能够跑出这个界限;而且假设人用足够强大的力量掷出一柄长矛,这长矛就会持续飞行。在这种情况下,这长矛会停止吗?会被什么东西阻挡住吗?卢克莱修说,若无什么东西阻挡,这长矛会一直处于飞行中;若长矛被某种东西阻碍住了,这种东西是要占据空间的,那么这就足可证明阻碍长矛飞行的那东西后面还有某种东西,即物后有物。这最终证明宇宙是没有边界的。当然“卢克莱修的长矛”这个思想实验,旨在为古罗马时期的问题“宇宙是否有边界”提供一种看似有理的解答。这个实验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没有考虑到影响长矛飞行的许多因素。卢克莱修的这个思想实验恰好说明有些思想实验存在另外一个特征:粗朴性。
概括起来说,语言哲学的思想实验呈现的基本特点是思想的先导性、观点的开拓性、知识的暂时性和实验过程的粗朴性。
2.思想实验的常见方法
思想实验是一个大概念,包括各种各样的思想实验。从方法论层面来看,语言哲学的思想实验重在凸显论辩中的焦点问题,即哲学家往往通过思想实验来聚焦论辩中的某个问题,从而证明该思想实验所凸显的问题是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以凸显的问题为分类原则,思想实验可以分为三大类:凸显论辩目的的思想实验、凸显论辩逻辑的思想实验和凸显理论态度的思想实验。思想实验的类型反映的是思想实验的方法,或者反过来说,实验的方法正是实验类型的写照。当然,这三种分类方法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有联系,只是各自的重心不同而已。另外,这三种分类并非是闭合性分类,而属于开放性分类,当然会接纳新的分类。
2.1 凸显论辩目的
思想实验大都具有明确的、特殊的目的。凸显论辩目的的思想实验重在探讨实验的外在有效性与内在有效性(Sartori 2023)。思想实验的场景基本上都是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场景或者在现实世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况(Kuhn 1977)。因此,实验的有效性主要建立在认识论的基础上,而认识论的核心在于追问实验中所涉知识或所述观点是否可能。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却在可能世界成为可能。凸显论辩目的这类思想实验的特殊性往往从可能世界中体现出来。
出于特殊目的,凸显论辩目的这类思想实验常常基于以下某种(或某些)因素:经济性、娱乐性、教育性、理解性等。例如,“莱布尼兹的中国王”(Leibniz’s King of China)是以娱乐的方式来助人理解一个观点:个人身份并非由个人梦想来建构,而是根本离不开个人记忆。这项实验内容如下:设想市井中的张三平日里梦想成王;突然有一天张三获得了成王的机会,但条件是要抹去张三头脑中的一切记忆,即张三一旦成为中国王,就要以崭新的状态去面世。在这种情形下,张三本人的原有身份就被消灭,而新建的身份完全不同。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人类的记忆是人类身份的决定因素,纯粹的梦想并不是身份的决定因素。
这里所举的“莱布尼兹的中国王”这一思想实验,它凸显的实验目的是验证人类的记忆是否对其身份具有决定性。虽然在现实世界里,因为伦理的限制,实验者不会(也不能)真正抹去被试的记忆,但是为了达到实验的目的,这样的思想实验能获得论证的有效性。
2.2 凸显论辩逻辑
哲学论辩中的思想实验具有假定性。在假定的情况下,凸显论辩逻辑的思想实验涉及的是“真势模态”及相应的反驳情况(吴亚军,杜世洪2023)。以逻辑结构为中心的思想实验是关于两种“真势模态的反驳者”(alethic refuters)的假定性场景,即对某项陈述的真与否进行考察,就应该从逻辑论辩角度来设想必然性反驳者和可能性反驳者会怎样反驳该项陈述。给一项命题陈述添加模态算子,完全可能会得到新的命题。模态算子关涉的是三大类模态性:第一类是道义模态,即关于允许和禁止的模态;第二类是知识模态,即关于知道和相信的模态;第三类是真势模态,即关于可能和必然的模态。在这三类中,真势模态最为基本,因此在做命题陈述时,就要注意必然性反驳者和可能性反驳者会做出的反驳会是什么(Sorensen 1992:135)。例如著名思想实验“盖梯尔的史密斯和约翰”对传统的知识观做了驳斥。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泰阿泰德篇》以降,存在一个传统的知识观,即认为命题知识就是业已证明的真信念。可是,盖梯尔(Edmund L.Gettier)却用思想实验对这个知识观提出了质疑(Gettier 1963)。“盖梯尔的史密斯和约翰”这项思想实验的要义是:假设有史密斯与约翰二人要申请同一工作岗位。史密斯相信约翰将会得到这个岗位,而且史密斯还明确知道约翰的衣袋里装着十枚硬币。于是史密斯产生一个信念:将会获得这个工作岗位的人,衣袋里一定装着十枚硬币。然而,面试结果却是史密斯本人获得了这个岗位,而且碰巧史密斯本人的衣袋里刚好也装着十枚硬币。如此一来,史密斯的信念——将会得到这个岗位的人衣袋里装着十枚硬币,获得了证明,就成了真,而且史密斯有充分的理由断定这个信念就是真知识。盖梯尔的思想实验指出的问题是:史密斯把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而且还在并不知道自己也装着十枚硬币的情况下,偶然地满足了“一切知识都是业已证明过的真信念”这项陈述的成真条件(ibid.:121)。在盖梯尔看来,这项陈述在逻辑上却面临着来自真势模态的必然性反驳,即这项陈述的必然性存在纰漏。这是来自真势模态的必然性反驳的典型案例,而真势模态的可能性反驳的经典例子就是“全能的神是否能够创造出一块巨石以致全能的神自己也无法搬动”(Brown &Fehige 2019)。这项不需要实验内容的思想实验完全可能会让那些相信神是万能的人头痛不已。
2.3 凸显理论态度
与前两大类思想实验相比较,以理论态度为中心的思想实验的关注范围与聚焦点相对来说都要小一些,即这类思想实验的目的很明确:实验者持有明确的理论态度,来考察某理论(或某观点)是否可靠。这类思想实验要么是建设性的,要么是摧毁性的。对某个问题(或观点)进行建设性支持或者摧毁性批判,这种做法凸显的是理论态度。波普(Karl Popper)把这类凸显理论态度的思想实验分为辩护性思想实验和批判性思想实验(Richardson &Dowling 2012)。例如罗素的“五分钟世界”这个思想实验就是关于怀疑论者反科学世界观的批判。反科学的怀疑论者持有的错误观点有“记忆是虚假的”“时间这个概念是虚假的”等。对此,罗素把常识和逻辑分析结合在一起,提出“五分钟世界”这一假设(Russell 1921:159):逻辑上完全可能的是,这个世界只是五分钟前才诞生的,而且这个世界就是诞生时那个样子,世界上的人只记得完全“虚假的”过去。
罗素的“五分钟世界”这个思想实验的基本假设是,对某事的记忆在逻辑上完全独立于某事实际发生时的情况。罗素这个思想实验带有幽默调侃的意味,旨在驳斥怀疑论者的反科学世界观。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完全能够记得昨天的事情,昨天的新闻等,甚至记得身上穿的牛仔裤已经褪色了等历历在目的过去种种。怀疑论者当然会反驳罗素的“五分钟世界”这个假设,而且他们可能会质问,五分钟的世界怎可能同长达几十亿年的世界一样呢?如果他们这么提问,那就等于自动承认时间有长有短。既然时间有长有短,那它怎么会是虚假的呢?罗素的“五分钟世界”设计得比较巧妙,有力地批判了怀疑论者的世界观。
3.思想实验的目的与价值
思想实验是“理想主义者的实验”,是在不具备现实条件的情况下,单凭“思想构建”的具有启示意义的实验(Miscevic 2022:7)。思想实验的目的及价值常常不言而喻,而且不可忽视。思想实验常有以下之一或更多的目的:(1)提出一个深刻的且意想不到的问题;(2)回答一个暂时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3)揭示某种思想中隐藏的问题;(4)诊断出某个貌似确定的观点的混淆之处;(5)支持某个暂时缺乏确切证据的观点;(6)挑战某个观点、某项定论、某个假设等;(7)验证某个定义的恰当性;(8)验证某个原则的适用性。当然思想实验的目的远不止这些,但这些方面是思想实验的重要作用或目的。
虽然思想实验具有明显的价值,如拓展理论认识和消除错误观点,但是思想实验因其简单粗朴,会遭到来自具体科学那些自认为是精密实验者的嘲讽。然而,对思想实验的嘲讽或者批判,这本身就属于哲学的思辨活动。柏拉图说,哲学始于好奇与困惑。为了满足好奇之心,消除困惑之雾,实验当然不失为一种重要手段。实验的要义在于达到实验目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任何实验都有存在的价值。思想实验的总目标在于通过假设来获得知识的确定性。围绕这个目标,思想实验以其简约的实验方式来支持或反驳某理论、某观点,来完善概念,来拓展认识,来提出问题等。
在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思想实验。下面根据思想实验常见的三大方法,分别阐述最为著名的三大思想实验:维特根斯坦的甲壳虫(Wittgenstein’s beetle)、普特南的孪生地球(Putnam’s twin earth)和蒯因的土著兔子(Quine’s Gavagai)。这三大实验不仅代表了思想实验的三大方法,而且还享有共同的研究主题:探究语词的意义问题。
4.语言哲学的三大思想实验
现代语言哲学具有大量人们耳熟能详的思想实验。从内容来看,有些实验较为简单如弗雷格的后院之树、赖尔的大学探寻者等,而有些较为复杂如维特根斯坦的甲壳虫、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和蒯因的土著兔子等。这些思想实验都具有原创性,因此甚至可以说,每个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哲学家似乎都有专属的思想实验。
4.1 维特根斯坦的甲壳虫
在方法论上,“维特根斯坦的甲壳虫”属于目的凸显的思想实验。在实验中,维特根斯坦要凸显的目的是——力图证明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语词并不意味着他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义,语词所涉的心理意识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
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第293 节详细地叙述了他的甲壳虫实验。维特根斯坦(2020:143-144)说: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而且盒子里面装着的东西叫“甲壳虫”。每个人都不能查看别人的盒子,而且每个人只看着自己盒子里的甲壳虫,都声称自己知道什么是甲壳虫。像这样的话,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每个人的盒子里装的东西并不一样,而且盒子里的东西还在经常变化。试想一下,“甲壳虫”是这些人共同使用的单词吗?如果是,这个词则总是用作某物的名称,而盒子里的东西在语言游戏里根本就没起什么作用,甚至没被当回事,因为盒子完全可能是空的。人们可以把盒子里的东西进行“约分”,这样一来,无论它是什么,它都会被抵消掉。
维特根斯坦这项思想实验的目的是要讨论“语言的本性”(Cohen 2005:87)。人们误以为使用同样的语词就是在谈论同样的事物;而实际上,他们谈论的事物有可能并非是一回事,甚至连谈论的方式都不同。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下来,维特根斯坦说,个人头脑的意识,个人感觉到的疼痛,这些就像个人盒子里的甲壳虫一样。个人自己有感受,别人则无法打开这盒子,即我们根本无法像苏芮所唱的那样“痛苦着你的痛苦”。因为我们拥有的只是相同的语词,而语词背后的意识内容则各不相同。如果有人自称他“痛苦着我的痛苦”,那么他的话根本就属于意义不清且达意不明。
维特根斯坦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许多哲学伪问题或者概念混淆问题。原因是哲学家们错误使用语言或者在日常语言中装神弄鬼,制造了伪问题。语言并无什么固定的本质,意义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本质。维特根斯坦把意义同语词的具体使用结合起来,认为语词的意义不是由什么固有本质决定的,而是由具体使用决定的,即意义在于语词的使用中。这是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有力批判。
4.2 普特南的孪生地球
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发起猛烈批判的还有普特南。普特南力图证明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存在逻辑错误。根据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意义观,语词与意义的关系反映的是语词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认识本来不错,可是形而上学实在论者还认为,语词的意义取决于人脑内在的表征。有了内在表征,就可以推断出世界的真与意义二者属于内在交互的结果,即意义是内在的而且具有相对性。对此,普特南认为形而上学实在论者的逻辑谬误在于一方面把意义归为内在的,另一方面又把意义看成是相对的。这就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于是,普特南设计出“孪生地球”这一思想实验,从逻辑上驳斥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属于凸显论辩逻辑的思想实验。
普特南在其文章《“意义”的意义》中提出一个问题(Putnam 1975:139):意义是在头脑中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普特南运用孪生地球这个思想实验来驳斥“意义的心理状态决定论”(Tittle 2005:100-101):知道一个词的意义就是知道心理状态中的“存在之事”(a matter of being),而且如果两人对同一个语词做出不同的理解,那么这两人肯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这个理论观点显然掉进了相对主义的泥淖。通过孪生地球这个实验,普特南力图证明的观点是:意义是由(头脑)外部环境决定的,是由事情的真来决定的。普特南的思想实验内容如下:
假设银河系里有一个完全像地球的另外一个星球,我们称之为孪生地球。孪生地球上的人的语言甚至也是英语。孪生地球上有一种液体完全像地球上的水,孪生地球上的人也把这种液体称之为“水”,但不同的是孪生地球上的“水”的成分是XYZ,而不是我们地球上的H2O。在正常状态下,XYZ 与H2O 没什么区别,即XYZ 既能解渴,又是孪生地球上江海湖泊的组成,而且孪生地球上的雨水也是XYZ。如果地球人乘坐宇宙飞船来到孪生地球,那么地球人自然而然就会把孪生地球的“水”和地球的水看成是一样的。然而,当地球人发现孪生地球的“水”是XYZ 时,地球人就会说:在孪生地球上,“水”这个词意指XYZ;或者说,在孪生地球上单词“水”的意义是XYZ。
至此,问题出现了:地球上的水是H2O,孪生地球的“水”是XYZ,而且地球和孪生地球都讲英语。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单词“水”却有两种不同的外延意义:水可用来指代孪生地球的“水TE”,它的意义在地球人看来并不是水;地球人用“水”表示“水E”,但在孪生地球人看来,它的意义也不是他们的水。这就是说,单词“水”的外延取决于“水E”时,它完全是由H2O 分子组成;而取决于“水TE”时,它完全是由XYZ分子组成。至此,普特南想证明的观点是:如果单词的意义是由人脑内部的心理状态决定的,那么地球人的用词“水”和孪生地球人的用词“水”二者应该具有相同的意义;然而,具体情况却并非如此。
到此,普特南继续进行假设。他说,假设时间回到1750 年,那时地球人的化学发展不足,人们还不知道水的成分是H2O,孪生地球人也不知道他们的水的分子是XYZ。假设地球人“奥斯卡1”并无关于水的信念,孪生地球人“奥斯卡2”也没有关于“水”的信念,而且“奥斯卡1”和“奥斯卡2”两人看上去完全一样:一样的外表、一样的感觉、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内心独白等。然而,单词“水”的外延在地球上是H2O,在孪生地球上是XYZ;这一事实在1750 年如此,在1950 年也如此。在1750 年,虽然“奥斯卡1”和“奥斯卡2”具有同样的心理状态,但是他们二人对“水”的理解却是不同的。这一点可由后来的科学发展来证明。至此,完全可以说,单词“水”的外延并不是说话者心理状态的一种功能。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实验为其“语义外在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4.3 蒯因的土著兔子
对于语词与对象的关系问题,蒯因对意义确定论持怀疑态度,即蒯因并不认为语词与对象之间具有确定的意义关系。本着怀疑精神,蒯因论述了三种不确定性:理论证据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确定性和翻译的不确定性(Quine 1990:1)。据此而言,蒯因的土著兔子这个实验属于凸显理论态度的思想实验。
蒯因在其著作《语词与对象》第二章“翻译与意义”中创造出一个单词“Gavagai”(大概是指土著人口中的兔子)(Quine 1960/2013:26)。蒯因设计出这个思想实验,目的是要考察语词与它们所表征的对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考察翻译与意义之间的影响因素,从而驳斥意义确定论。蒯因说,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一位语言学家,在没有任何翻译的情况下,只身来到一个土著部落。这位语言学家根本不懂土著部落的语言,却要编撰一部关于这个部落的翻译词典。于是,他仔细观察和收集土著部落的一切数据,而且似乎只能获得表层的客观数据,例如观察到土著人的行为举止、听到或看到土著人的说话场景等。有一天,一只兔子飞快跑过,见此情景,土著人大声说出“Gavagai”来,于是这位语言学家就把土著的话记录下来,并试着翻译成“兔子”。
对于这条记录,这位语言学家还要在以后的场景中进行验证。这里的问题是,这位语言学家记录的数据和翻译的语词在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土著人的认可呢?假定土著人的语句有S1,S2 和S3 三句,它们实际上各自对应的是“动物”“白色”和“兔子”。由于外在刺激的环境总是不同,无论相关与否,土著人关于外在刺激环境的反应总是单一性的,而且就算土著人表达的语词有意义,然而土著人每次只会自动地说出“S1,S2 和S3”当中的一句。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语言学家怎样才能感觉出土著人本应在任何场合下都该说出S1,可碰巧他却说出的是S3 呢?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即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土著人本应该说出S1,而实际上他却偏偏说出S2。对于这些情况,这位语言学家该如何求证呢?即这位语言学家怎样做才能确证土著人的那句“Gavagai”说的就是“兔子”而不是别的什么如“动物”“白色”“看,一只兔子”等呢?
对于这个问题,蒯因说这位语言学家能做的就是做到尽量接近。要决定“Gavagai”到底意指什么,这位语言学家还需要指着跑过的兔子,而向土著人提出“这是一只兔子吗?”这样的问题来求证。在这个实验中,蒯因要表明的观点是,语词的意义只能在其他意义的语境中得到确定,只能在整个语言的语境中得以确定。
维特根斯坦的甲壳虫、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和蒯因的土著兔子,这三个典型实验分别代表的是语言哲学思想实验的三大方法或类型。思想实验的方法决定思想实验的类型。这三大实验具有共同的主题:考察语词的意义问题。通过实验,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语词并不能确保表达同样的意义,因为语词的意义由具体使用来决定;普特南明确断言,意义不在大脑中;蒯因认为,语词与对象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意义关系,意义具有不确定性。
5.结语
作为哲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思想实验并不苛求实验条件,不会耗费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自然就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首选方法。思想实验无法完成的,或许会由常规实验来完成。然而,在不需要常规实验的情况下,在常规实验无法达到思想的深邃之境的情况下,思想实验却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方法。作为想象性的、假设性的、论辩式的概念分析活动,思想实验企图证明的观点或者解答的问题往往是前沿问题或者尚无定论的问题,即思想实验具有思想的先导性、观点的开拓性、知识的暂时性和实验过程的粗朴性等特点。
思想实验常常以奇特的方式直接提供或间接呈现新认识、新思考、新观点等。思想实验的方法决定了其类别。常见的思想实验可分为三大类:以论辩目的为中心的思想实验、以逻辑论辩为中心的思想实验,以及以理论态度为中心的思想实验。维特根斯坦的甲壳虫、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和蒯因的土著兔子,这三个典型实验分别代表的是语言哲学思想实验的三大方法或类型。这三大实验具有共同的主题,即考察语词的意义问题。
语言哲学思想实验的目的与价值表现为,支持或者批判错误的意义理论,验证命题陈述的可靠性,考察某些概念的恰当性,考察某些认识的正确性等。为了在某种规定范围内获取新的认识,思想实验本身应该遵循它应有的实验准则。思想实验在挑战或者揭示谬误认识的过程中本身还要避免带来新的谬误。常规实验也罢,思想实验也罢,只要是实验,完全有可能出现实验结果并不可靠的情况。即便如此,思想实验因其必要性而不会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