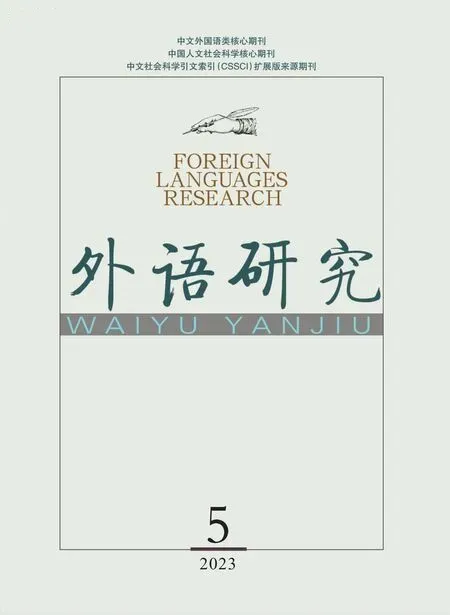语义最小论视阈下的语词意义再议*
2024-01-02刘利民
黄 乔 刘利民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0.引言
语义学与语用学之争目前主要呈现为语义最小论与语境论之争,围绕是否存在语境独立的句子语义内容、句子语义内容是什么、其与言语行为内容以及意图的关系等话题而展开,是所言与所含(Grice 1975)话题的延续和发展。作为句子意义的直接构成,语词意义也卷入到这场论战之中。语境论坚持语义不充分确定性(semantic underdeterminacy),句子和语词都只有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才有确定的意义(Carston 2002)。而语义最小论主张语境对句子意义的影响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语境敏感词的数量十分有限,自然语言中绝大部分语词的意义不受语境影响(Borg 2012)。可见,语义最小论与语境论关于语词意义的看法截然对立,体现为语境独立与语境依赖之分,或者说,在零语境下语词是否具有确定的意义之分。
《外语研究》近年刊载的《最小论视域中的语词概念:实质与批判》(吴亚军,杜世洪2021)一文认为语词意义是不确定的,语义最小论追寻的“最简概念”是“形而上的虚构”。本文拟在语义最小论框架内对语词意义进行再探讨,澄清语词意义的来源与特征,辨析语词意义与概念意义①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回应吴亚军和杜世洪(同上)的相关质疑。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语义最小论与语境论之争,也能为意义与使用、语义与语用等话题提供思路和启发。
1.语词意义:来源与特征
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选取语词根据句法组合规则构造句子以表达意义,听话人则基于句法规则和语词意义来理解句子意义。成功的语言交际要求听话人与说话人掌握同一套句法组合规则,以及对语词意义有相同的理解。前者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毕竟绝大多数语言都有清晰的语法规则;而后者却不容易实现,原因在于“意义”本身就是“一团乱麻”(陈嘉映2003:47)。这也是语言交际出现不充分理解乃至误解的缘由所在。因此,语词意义到底有何特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考察语词是如何获得意义的。
1.1 语词意义的来源
意义的来源是外在客观世界,但意义却是大脑认知操作的内在产物;这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忠实再现,背后潜藏着人类作为认知主体的加工操作。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看(黎明,刘利民2019:64-68),语言获得意义大致要历经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经验得以在人类大脑结构中留下印记,形成感受性的、模糊的意义;第二,这些感受性意义在人类的认知操作下逐渐以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居于复杂的、相互牵连的网络关系中,构成个体拥有的思想;第三,人类的思想是内在的、私人的,而思想的传递则以语言为载体。这样一来,语词和句子就编码了思想的内容,语言也就获得了意义。认知语言学也有类似看法。赵艳芳(2001:35)以“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语言符号”的方式揭示了语言获得意义的过程。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人们能动认知客观世界的过程,语言使用主体的认知加工操作生成概念,概念的进一步提纯凝练为语言意义。总之,人类的交流实际上就是思想的传递,但人类没有传心术(telepathy),无法直接将个体概念传递给他人,这直接促使思想性的内容用语言来表达。
当然,语言固定思想的过程并非无章可循,语言形式与意义成分的结合由语言社区约定而来。早在一百多年前,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Saussure 1916)中就指出,语词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任意结合,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经规约,语词就能表达所指概念。不过,语词恐怕无法编码语词所指概念的全部意义内容。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思想的结构是非线性的、整体的,而语言的结构却是线性的、可分的,两者结构的不对称注定了思想意义远远比语言意义丰富、复杂。换句话说,“概念的整体多维性与语言的线性单维性之间存在矛盾,以单维度的语言表达来表征多维、动态的概念是不可能的”(黄乔,刘利民2021:582)。
著名哲学家Quine(1960)关于“Gavagai”的思想实验是一例很好的说明。假设一位语言学家要去考察一门从未被研究过的土著语言,他没有词典、参考书或者译员,只有通过观察土著人在什么条件下做出什么言语行为反应来构建一部翻译手册。一天,一只白兔从面前跑过,土著人说出“Gavagai”,那么语言学家应该如何做记录呢?理论上,他至少有以下选择:“这是一只白色的兔子”“一只白兔跑过去”“这只兔子跑得很快”等等。很可能的是,每次一只白兔跑过去,土著都说出“Gavagai”,而这几种选择与说出“Gavagai”的当下环境条件是融贯的。那么,要判断“Gavagai”到底指称上述记录句中哪个事件是异常困难的,原因在于语言学家只能根据自己的信念系统和当下环境作出判断,但他没有把握土著的信念系统,因而极可能他对土著语句的翻译是不正确的。本文借此说明,语词“Gavagai”给不出土著人说出这个语词时所包含的所有信息,“用一维的语言难以记录四维事物的时空结构信息”(叶峰2016:75)。兔子的大小、颜色、性别、奔跑的速度、方向等都可能是由“Gavagai”编码的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要理解“Gavagai”的意义就必须以理解其他语词为基础,后者编码了土著人关于世界的诸多信息。循此推演,语言学家几乎无法完成对土著语言的研究。
这表明,我们关于语词所指对象的认识可能非常丰富,呈现为信息网络结构,但在使用语词编码这些认识时,语词只能截取相对而言十分少量的信息。这是由概念多维性与语言单维性之间的结构不对称造成的。问题自然是,语词编码概念的哪些意义内容呢?
1.2 语词意义的特征
本文认为,单维语言表达式只能承载概念的一个维度,语词无法编码概念的全部意义内容,而只能选取概念的一个意义内容片段作为语词意义;这一片段是不可再分的、区别性的概念意义片段,是语言社区规约的结果,一经约定就不能轻易发生变化。我们之前将如此这般的语词意义称为“形”(刘利民2019),现在改称为“概念形式”(Conceptual Form,简称C-Form),即语词意义是概念形式。作此改变的原因在于,本文观点受到公孙龙的直接影响,理应采纳其合理术语。公孙龙提出,“马者,所以命形也”。语词“马”是用来命名形式的,但这种形式不是直接经验感知到的马的外形,而是语词“马”(horse)所指马概念(HORSE)之形(刘利民2015:34)。
诚然,我们对概念知之甚少,但是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均认可概念是心理实体,这算是使得讨论概念成为可能的操作性定义。如果把概念视为实体,那么它逻辑上必然具备形式和内容。这并不意味着概念(在经验感知层面)有特定形式,但在谈论某个概念或区分不同概念的时候,我们关于概念的了解必须有它是其所是的个体性(ITNESS)。即使不具有概念的其他任何信息,个体性也能将一个概念与其他概念分开。这能在Prinz 的想法中找到支持,他认为概念是代表一个类别的代理型(proxytype),而代理型是有界形状表征(bound shape representation);代理型有清楚的范围界限,在思维中标记代理型是对客观对象的操作模拟(Prinz 2002:149-150)。按此,代理型必须是个体化的心理实体,在思维过程中充当代理的个体性即是区分此概念与彼概念之依据。
本文提出的C-Form 并不类似于计算机中的文件夹名称——通过双击文件夹名称来访问其中的文件,毕竟文件夹名称可能与内容无关。事实上,CForm 本质上是概念性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标签;标签可以是任意的,但C-Form 却不是任意的,它是一个概念的识别信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只掌握C-Form(而缺乏任何其他信息内容)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能够区分不同概念。例如,普特南(Putnam 1973)承认分不清榆树和山毛榉,但他确信语词“elm”指的是榆树,语词“beech”指的是山毛榉。这表明普特南有ELM 概念,且明确知道它不同于BEECH 概念,但在他的头脑中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无内容的(content-free),即它们只是ELM 概念和BEECH概念的C-Form。又如,本文作者只有QUANTUM 概念的C-Form,除了量子与力、磁等不同这一认识之外,对量子一无所知。本文的C-Form 更接近于幼儿的WATER 概念。成年人的WATER 概念可能与其他属性有关,例如湿的、可用于解渴、灭火等,这些属性是WATER 概念的成分。与成年人不同,幼儿可能只知道WATER 概念可以应用于水,即幼儿能够把语词“water”锁定在水中(Fodor 1998:156);但幼儿的WATER 概念很可能缺乏成年人的WATER 概念所具有的其他相关信息,因为幼儿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湿的、什么是渴或什么是火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幼儿掌握的其实是C-Form WATER。
简言之,本文的观点是,假设概念作为心理实体存在,那么C-Form 就是概念的形式。道理很简单,实体必有其形;概念既是心理实体,亦不可能无形?诸如动物、跑得快、食草的等都可以是HORSE 概念的特征,但这些特征都不是HORSE 概念的个体性;甚至马科动物也不是,因为驴、斑马等都属马科。使HORSE 概念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化的概念的唯一要素是C-Form HORSE,所有其他相关特征都可以或不可以与之关联。反过来说,C-Form 确认了所指概念的唯一性,不管这个概念的其他特征多么复杂,也不管这个概念的内容如何变化。按此,说“不同的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有相同的概念”,这仅仅意味着他们有相同的概念形式,而他们可能在概念的内容方面有很大甚至有根本的不同。当儿童的WATER 概念不同于化学家的WATER 概念,而化学家的WATER 概念又不同于哲学家的WATER 概念时,不同的是概念的内容,而不是概念的形式。这就是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近年来成为哲学热门课题的重要原因:概念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但是它的CForm 保持不变。概念工程不是话题的转换,因为即使内容可能被完全取代,C-Form 仍然存在。物理学中的ATOM 概念仍然是ATOM 概念,尽管“不可再分”已经不是这个概念的基本定义成分。对于WOMAN概念,内容不再仅仅是女性、成人、人类,而是被极大地丰富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被其他特征所替代,例如地位、性别意识、无助感等社会心理属性(Cappelen 2018:13-14)。然而,语词“woman”的意义仍然是C-Form WOMAN,适用于相同的指称对象,任何关于WOMAN 概念的讨论仍然是关于女人而不是男人的话题。如果概念工程是对世界的操作(ibid.:46),那么它所涉及的是概念的内容,而不是概念的形式。
至于C-Form 与语词的匹配,本文同意陈波(2014)的观点,即这只是一个社会习俗问题。索绪尔仍然是正确的,语词是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不过,所指不是概念,而是概念不可或缺的识别信息。这能解释为什么两个关于同一概念有着非常不同的概念内容的个体可以互相交流:他们不同的是概念的内容,而相同的是语言社区中与语词联系在一起的CForm,后者提供了语言交际的起点。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信念网络,或者每个概念都有相同的内容,那么语言交际中的不理解、误解根本不会发生。现实情况是,语言交际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人们在概念内容上存在差异;但语言交际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确保人们谈论的是同一个对象,无论他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多么不同。恰恰是C-Form 保证了语言的公共性与内容的可调性。
综上所述,本文主张语词的概念域中存在最简概念成分,它是概念意义中决定语词是其所是的一个特殊意义片段。须说明的是,我们未曾宣称这一片段是“语词概念集合的抽象”(吴亚军,杜世洪2021:34),抑或,“所有概念成分的共相”(同上:38)。这一片段曾被称为“碎片化、静态化抽象”(刘利民2019:7),但这里的“抽象”并不是对语词所有概念成分的抽象、概括。具体而言,语词意义是C-Form,是概念意义的一个片段(而不是共相),而不是直接的感觉经验;虽然语词意义最终来自感知经验,但语词意义本身不能还原为物理经验。如果说语词指称的客观对象在“具体”层面,那么内在于大脑的语词意义在“抽象”层面。
2.语词意义与概念意义的关系
在上一节,本文试图说明C-Form 是(广义)概念意义的一个片段,其具有决定概念是其所是的意义内容。不过,即便承认存在“最简概念”(即本文的CForm),“它与其他概念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吴亚军,杜世洪2021:36)。本文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Sawyer(2021:239-240)对概念(concept)与关于概念的思考(conception)的区分找到答案。Sawyer 指出,概念是心理表征,是思想命题内容的组成部分,而关于概念的思考是主体为概念关联的信念集合。例如,语词“horse”的概念就是HORSE,而关于HORSE 概念的思考就包括跑得快、通常作为交通工具、能驼重、人类的战友等。须注意,关于概念的思考是关于概念指称对象的一系列具体属性描述,但其并没有说清楚概念到底是什么,即HORSE 概念本身无法由属性描述确定。
这说明语词既能表达概念,也能启动关于概念的思考,并且掌握概念与掌握关于概念的思考是两码事。就两个个体掌握的内容来看,有以下四种逻辑可能:
[1] a.两个个体掌握相同的概念,但掌握不同的关于概念的思考;
b.两个个体掌握相同的关于概念的思考,但掌握不同的概念;
c.两个个体掌握相同的概念以及相同的关于概念的思考;
d.两个个体掌握不同的概念以及不同的关于概念的思考。
逻辑[1d]表明两个个体没有使得交际得以成功的任何基础,他们在自说自话。逻辑[1c]在日常交际中十分罕见,除非提前约定好相关语词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军事命令、飞行手册、科研论文等需要严格定义的文本。逻辑[1b]和[1a]都可以在普特南那里找到例证:首先,孪生地球思想实验说明奥斯卡和孪生奥斯卡有关于WATER 和WATERTE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却掌握了相同的关于概念的思考。其次,普特南与园林专家将不同的关于概念的思考联系到相同的ELM 概念上。因此,两个个体掌握同一概念对于他们掌握与同一概念所关联的关于概念的思考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更为重要的是,Sawyer 实际上暗示了以下主张:两个个体可以掌握相同概念的同时,却可以不具备与这个概念关联的任何关于概念的思考。这也是Del Pinal(2018:179)所说的有些语词只有E-结构(Estructure)而没有C-结构(C-structure)的情况。②非常有可能的是,我们和普特南都知道语词“elm”指称ELM 概念,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说不出关于ELM概念的更多内容。又如,语词“量子鞋垫”(quantum insole):或许我们知晓这个词指称QUANTUM INSOLE 概念,但关于这个概念的思考却很可能是空集。但如果两个个体掌握相同的关于概念的思考时,他们一定事先掌握了概念,不管他们掌握的概念是否相同;毕竟,关于概念的思考是主体为概念赋予的信念。总而言之,掌握概念和掌握关于概念的思考不仅是两码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对称的;掌握概念并不预设掌握关于概念的思考,但反过来并不成立。
这为辨析语词意义和(狭义)概念意义的关系提供了启发:语词既有语词意义,又有(狭义)概念意义,但语词意义和(狭义)概念意义并不是一回事。就两个个体掌握的内容来看,有以下四种逻辑可能:
[2] a.两个个体掌握相同的语词意义,但掌握不同的(狭义)概念意义;
b.两个个体掌握相同的(狭义)概念意义,但掌握不同的语词意义;
c.两个个体掌握相同的语词意义以及相同的(狭义)概念意义;
d.两个个体掌握不同的语词意义以及不同的(狭义)概念意义。
逻辑[2d]说明两个个体在自说自话,不具备成功交际的必要基础。逻辑[2c]在自然语言交际中大都限于专业领域讨论,例如,“不可抗力”和“艾滋病”等。逻辑[2b]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普通人很可能无法将狼和狗区分开来,原因在于他们关于语词“狼”和“狗”的概念意义几乎没什么差别:四条腿、四肢修长、嗅觉灵敏等。这些特征给普通人留下的印象是狼和狗是没有区别的,而动物学家却能够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区别性特征;虽然普通人关于语词“狼”和“狗”的概念意义没啥差别,但实际上指向的却是不同的对象,即掌握的语词意义并不相同。就[2a]而言,以语词“black hole”为例,普通人可能只知道这个语词的语词意义,即指称BLACK HOLE 概念,但对于天文科学家来说,他们不仅知道这个语词指称BLACK HOLE概念,而且还知道具有强大吸引力、存在于宇宙空间中的天体等内容。
那么,掌握语词意义与掌握(狭义)概念意义是否有对称关系呢?掌握(狭义)概念意义是否预设掌握语词意义呢?反之是否成立?在此之前,有必要重申本文针对“概念意义”的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主张语词意义来源于(广义)概念意义,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区分性意义片段。(广义)概念意义是关于语词指称对象的一系列属性描述,其中的一个描述就告诉了我们语词意义是什么。说两个个体关于同一个语词掌握相同的意义内容,实际上说的是他们掌握相同的语词意义,这个语词意义是(广义)概念意义的一个区分性片段,而除此之外的概念意义(即狭义概念意义)在他们大脑中是可以有巨大差别的。
如上所述,Sawyer(2021)主张掌握概念并不预设掌握关于概念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掌握语词意义并不预设掌握(狭义)概念意义,毕竟(狭义)概念意义无法讲清语词意义是什么。语词“horse”的意义是C-Form HORSE,这一语词意义来自(广义)概念意义,而除此之外的(狭义)概念意义包括跑得快、通常作为交通工具、能驼重等都无法成为C-Form HORSE 的候选项,因为后者是“一切关于马的陈述、判断和推论等思想及其表达所必然涉及,却不包含任何此意义之外的属性描述(颜色、大小、功能、类属,甚至本质属性等)的意义”(刘利民2019:11)。语词意义只负责区分此概念与彼概念,除此之外的关于语词所指对象的属性描述是(狭义)概念意义的工作。语词意义一经语言社区规约,就不能轻易发生变化,而(狭义)概念意义随着经验的丰富和认知的发展可以不断扩充,但后者并不能决定语词意义。换言之,语词的C-结构无法决定这个词的E-结构(Del Pinal 2018:202)。
概念与关于概念的思考的理论区分是有道理的。虽然不具有区分开榆树和山毛榉的关于对应概念的思考,但普特南坚持他掌握ELM 概念。这并不排除普特南不具有任何关于ELM 概念的思考,尽管后者可能是不清晰的、不准确的乃至不正确的。实验研究表明,普特南断定他所掌握的是ELM 概念而不是BEECH 概念,可以不借助有关ELM 概念的任何其他信息(Haukioja et al.2021)。然而,如果要询问ELM概念从何而来,本文的立场就能给出较好的回应。根据本文观点,普特南掌握的ELM 概念实际上是CForm ELM,后者本身不包含任何其他内容。这为本文区分语词意义与概念意义提供了启发。个体可以掌握对应于某个语词的概念,而不具有关于这个语词所指概念的更多信息;类似地,个体可以掌握某个语词的语词意义,但同时又不掌握这个语词的概念意义。概念与关于概念的思考不是一回事,语词意义和概念意义也不是一回事。
既如此,如果同一个体在不同时刻关于(音响形象意义上的)同一个语词符号掌握的概念成分有区别,那么在这两个时刻,这一个体掌握的仍然是(音响形象与概念相结合意义上的)同一语词符号;因为语词的概念形式并未改变,直觉到的差异来自(狭义)概念意义的不同。这与吴亚军和杜世洪(2021:35)的观点恰好相反。这之间的差异来自对以下问题的不同回答:在概念成分变化时,是否需要相应地创造一个新的语词来固定新的概念?假设“马”在不同时刻的概念成分不同,本文认为同一个体在不同时刻习得的是语词“马”,并且“马”的语词意义并未发生变化,这由“马”的概念形式所保证;而他们认为习得的是语词“马1”与“马2”,并且“马1”与“马2”的语词意义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根据在于,“语词的音响形象犹如外壳,如果其内所包装的概念成分不同,语词符号(的意义)就不相同”(同上:36)。
按照他们的观点,特定概念成分由特定语词来固定,那么自然语言中的语词数量就会爆炸性增长。这会引发以下问题:第一,自然语言中的一词多义现象将不复存在,毕竟每个义项都由不同的语词来标示。这甚至也与语境论的观点相悖:尽管Carston(2019)认为所有实词都至少潜在地是一词多义的,但诸多义项寄生在(音响形象意义上的)同一语词符号上。第二,纸质词典的词条数量会无限膨胀,毕竟概念成分是动态变化的、持续更新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现代汉语词典》只有词条“马”(2017:866),而没有“马1”“马2”或“马3”。的确,概念会一直更新,但语词(符号)并不需要发生改变——变化的是概念内容而不是概念形式,这得益于对语词意义与概念意义的严格区分。这样一来,跟他们的看法不同,本文主张概念诸多成分中有一个不变的成分(即C-Form),后者保证了语词的跨语境同一性;我们关于语词所指概念成分的充实、饱满,对于语词意义来说不是替代而是补充。或者说,语词意义本身跨语境同一,但所指对象的内容由环境或其他因素所工程建构(engineered)。
在更宏观的层面,本文认为语词意义是确定的,而吴亚军和杜世洪(2021)认为语词意义是不确定的;分歧在于对“确定性”的不同理解。在语义最小论与语境论之争的背景下,确定性有语义确定性与语用确定性之分。语义确定性是本文着力论证的对象,即语词自身具有的、决定语词是其所是的意义片段——C-Form;假如没有这种确定性,语言使用者似乎可以使用任意一个语词来表达任意概念。语用确定性则建立了语词与客观世界中具体所指对象的联系。关键的是,语用确定性建立在语义确定性的基础之上。例如,语境敏感词“他”的语义确定性即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外的第三人,但具体指的是哪个人则是掌握语词“他”的语词意义之后的、在客观世界的语用落实。于是,本文与吴亚军和杜世洪(同上)并不直接对立:本文聚焦的是语义确定性,而他们关注的是语用确定性。虽然如此,本文力图说明语义确定性是基本的、首先的,而语用确定性是派生的、其次的。如果不存在语义确定性,跨语境的语言交际如何可能?
3.结语
本文从语词获得意义的过程入手,说明语词无法编码所指概念的全部意义成分,而只能在语言社区的集体约定下编码某一特定片段。受公孙龙启发,本文将这一片段称为概念形式,其作为语词意义具有使得概念是其所是的个体性,因此能够区分此概念与彼概念。根据Sawyer(2021)对概念与关于概念的思考的严格区分,本文认为语词意义与(狭义)概念意义的区分是必要的。第一,(狭义)概念意义无法决定语词意义,个体可以掌握语词意义的同时而不掌握这个语词的(狭义)概念意义。第二,虽然概念是动态变化的,但语词符号本身并不需要改变——发生变化的是概念内容而不是概念形式。
因而,吴亚军和杜世洪(2021)的相关质疑有待商榷:他们从认知语用的角度探究语词意义,指出了语义最小论可能面临的麻烦,但却未能很好地区分开语义确定性与语用确定性。本文不否认语用确定性的价值,但重在阐明语义确定性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不仅为语义最小论视阈下的语境独立的语词意义观提供了辩护,也指明了这种语词意义的来源与特征,完善了语义最小论的理论架构。当然,针对语义最小论的挑战还远不止本文讨论的范围,有关语词意义的论辩仍将继续。
注释:
①本文讨论的“概念意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意义指的是(语词所指)概念的全部意义成分,而狭义概念意义指的是广义概念意义减去语词意义之后剩下的、未被语词编码的概念意义内容。如无特别说明,第二节论及的“概念意义”是狭义,其他地方是广义。当需要引起注意时,本文也会加以标识。
②具体而言,前者表征决定语词外延对象的原子信息,而后者是与外延对象相关联的一系列信念。本文的C-Form 非常类似Del Pinal(2018)所说的E-结构,即只有决定语词外延的意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