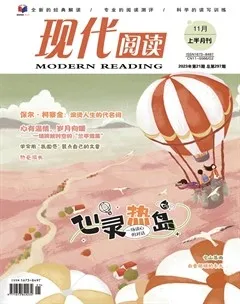回不去的美好:阅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双重视角
2023-12-29梁开喜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历来有“批判说”“对比说”以及“儿童心理说”等,这样的多元探讨是有意义的,但就语文教学而言,也给老师们带来了一些困惑和不便。
这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状况或许与部分老师对文本的态度有关。在笔者看来,从培养学生基本的审美鉴赏力出发,结合作者生平、兼顾文体特征、尊重文本逻辑,乃是作品解读的正途,而在文本之外探幽索隐或无限延伸则是不足取的。
儿童视角:亲切感人的怀念之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于1926年9月,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遭受着北洋军阀等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也经受着守旧势力的排挤。在恶劣的处境中,鲁迅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可以说,散文集《朝花夕拾》是鲁迅在纷扰芜杂中努力寻找的“一点闲静”,虽说它也留下了当时社会斗争的影子,偶尔也可见对“正人君子”们的“顺手一击”,但最核心的是作者童年生活和青年求学历程的真实记录,萦绕其中的是亲切感人的怀念之情。
这种亲切感人的怀念之情,从“百草园”部分可以完全体现出来。百草园是一个荒园,但在无拘无束、烂漫无邪的儿童看来,却是那样有声有色、多姿多彩。作者一连写了12种动植物,写到了它们带给“我”的无限趣味: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长吟的鸣蝉,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低唱的油蛉和弹琴的蟋蟀们,蜈蚣,斑蝥,何首乌和木莲,还有比桑椹要好得远的覆盆子,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的生机勃勃、新鲜可喜,甚至“短短的泥墙根”和“断砖”都牵引着童年的“我”猎奇的目光。而亦真亦幻、充满了惊险意味和神秘色彩的“美女蛇”的故事,还有冬天捕鸟的情景—作者在自然的妙境天趣中渗入人情常理—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了民间文化的魅力以及劳动者的经验与智慧。
这种亲切感人的怀念之情同样弥漫在对“三味书屋”的叙写之中,其整体脉络和格调是一以贯之的。“折梅花”“寻蝉蜕”“捉苍蝇”“喂蚂蚁”,儿童总能在这些看似无趣的事情上乐此不疲。或是在先生读书的时候,也可以“做戏”和“画画儿”。“三味书屋”的生活不再是放纵不羁的,但空间的转移并没有带来行为上的抗拒或情感上的不适,从顽童到读书郎,贪玩与好奇的心性一如既往,而即或是在先生的喝问之中,在书声鼎沸之中,在习课之中和习课之余的“不务正业”之中,也无不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那一份自在与自由。循着纯净而新奇的儿童之眼,我们看不到太过沉重的东西。严厉的先生其实是温厚的,枯索的诵读也并没有损害生命的元气。作者回忆的重心始终不在其苦,而在其乐,从这个意义上讲,“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实际上是鲁迅情感过滤之后的两个童话。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生活不是割裂的或者对立的,它们之间不是此扬彼抑、相互排斥的关系,百草园的无羁与三味书屋的有限,都是作者内心深处曾经晶莹夺目的带露的朝花。
成人视角:追昔抚今的轻声感喟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没有感伤、惆怅、遗憾、沮丧和成年鲁迅所惯用的那种调侃和讽喻。在成人视角的叙述和议论中,这些无疑是可以捕捉到的,但它对作品整体的暖色和轻松的调性似乎没有构成什么影响。一派天真的儿童视角与带有几分严正、深沉和忧伤的成人视角明暗交织,使得作品在追昔抚今之中,既有对童年生活的温暖回忆,也埋伏着对中年处境的轻声感喟。而这后一点,恰恰是不少读者断章取义的地方。
从文章开头的“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到结尾的“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都是现在时的叙述者视角。不过,与其说这里有什么微言大义,毋宁说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结构和情感上。结构上的呼应自不待言,从情感上讲,逝者如斯、物是人非,甜蜜的回首之中,当然也有时光不再和对家道中落的叹惋,更有中年艰难辛苦欲回童年而不得的无奈。站在童年视角,一切都是美好的;而站在成人视角,一切又都回不去了。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回忆性散文都难免或多或少地具有过去和当下的双重视角,一方面是亲切的怀念,另一方面是对旧时光的重新打量,从前的生命体验与现在的复杂心境总是缠绕在一起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自然也是如此。但我们如果把这种成人视角的吉光片羽的叙述简单而夸张地理解并上升为某种主题,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法做到循文入义、逻辑自洽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文中有对“怪哉”的探问,就误认为作品的主题是表现儿童对知识的渴求一样。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最合宜的姿态,乃是首先把它当作用“闲静”来抵御“纷扰”的写实的回忆性散文来看。唯其如此,我们才会明白,文中的“先生”,就是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现实生活中的“先生”也是“方正、质朴、博学”的,鲁迅对他充满了敬意;作者让一个现实生活中备受尊敬的老师成为自己笔下被嘲笑和被批判的对象,是完全说不通的。
值得一提的是,课后的“积累拓展五”颇具开放性和启发性:“文中那个活泼可爱、尽情玩耍的小鲁迅宛在眼前,你看到文字后面那个拿笔写作的‘大’鲁迅了吗?你觉得这个‘大’鲁迅是带着怎样的情感来写本文和《朝花夕拾》中其他文章的?”很多老师在施教过程中把“‘大’鲁迅”理解为“大写的鲁迅”或“伟大的鲁迅”,而不是成年鲁迅;把“‘大’鲁迅”理解为将笔当作匕首和投枪的鲁迅,而不是拉开了距离带着那一份眷念和惜别之情回望童年的鲁迅,因而在文本解读时就免不了有些用力过猛,这或许是我们在把握作品“双重视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
课堂指引
总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篇幅较长,意蕴丰富。我们一方面要知人论世,对相关背景知识诸如《朝花夕拾》小引、寿镜吾其人其事等做些补充,为推动学生的深度阅读提供必要的支架;一方面又要“以本为本”,避免在教学内容和教学重点的把握上顾此失彼、旁逸斜出。在具体施教过程中,我们不妨与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名著导读《<朝花夕拾>:消除与经典的隔阂》勾连起来,这样,既能激励学生从“这一篇”走向“这一部”,又能在经典作品的阅读方法上,给予学生正确而切实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