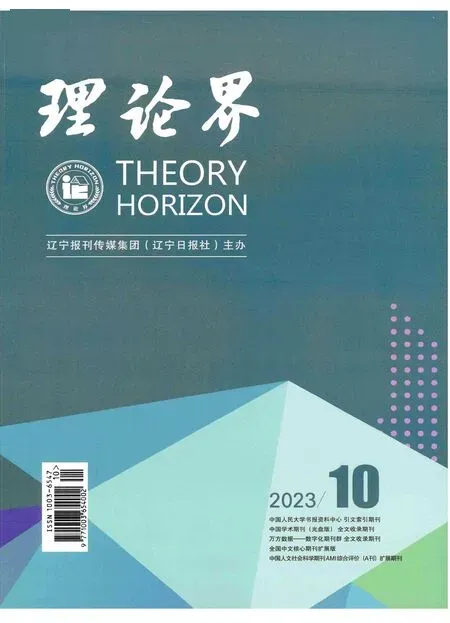从“两端”到“中和”:王船山性情思想重构中的价值转向
2023-12-29杨超李萌
杨 超 李 萌
学界于苏东坡、朱子两派性情观歧异,讨论甚多,然于此二脉性情之辩互斥模式的化解之道,无有触及。此外,已有研究,将王船山性情观划入道德宽松或道德严格主义阵营之中,亦有未尽之处。
一、问题指向:苏东坡、朱子两派内外偏执中的“性情之辩”
北宋以降,由于受到佛学、道学较为完备形上学说的挑战,孔子所罕言的“性与天道”,成为诸多儒者无法回避的论题。在此情境下,“性”(天性)、“情”(人情)之关联,作为“性与天道”学说中最为核心的议题,为学界争讼不已。
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主情一派,以七情为性,重人之情。苏东坡欲终止聚讼不止的性情论争,在总结历代学人性情思想的基础之上,批判了孟子及荀子的性善、性恶论说,认“喜、怒、哀、乐”为性,并主张性、情无善亦无恶,但可为善为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1〕苏东坡将纷繁复杂的人性之争,归咎于孟、荀,较之二者非此即彼的人性论,更青睐扬雄人性善恶相混之说。在苏东坡这里,“仁义礼乐”与“喜怒哀乐”均为人之性,二者犹如白纸,无善无恶,可以给人以随意创作的自由:“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2〕“俗儒”所言的“仁义礼”之“性”,实际上亦出自“喜怒哀乐”之“情”。
在性情关系上,苏东坡主张情可见性,情本性末。苏东坡认为前人所言之性,均似性而非真性:“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3〕性不可见,可见之性非性,那我们应当如何见性?“方其(性)变化,各之于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4〕所以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见性以情。“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5〕圣人之道,实为情之道,不循可见之情,而尊不可见之性,则必然本末倒置。
苏东坡持此性情观,亦有现实考量。其一,在修身之法上真其性情。“饮酒,人情所不免。禁而绝之,虽圣人有所不能。”〔6〕孔子并不主张灭绝人情,《论语》有言:“惟酒无量”。苏东坡认为,其“真性情”的主张并非凭空捏造:“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转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求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7〕微生高向邻居讨醋转借朋友,孔子谓其“不直”;陈仲子刻意压抑自然欲望,近似迂腐,为孟子所不取;陶渊明光明洒落,或仕或隐,任性而为之,至今为人称道,因此,性情以真为贵。
其二,在治理之则上贱礼贵情。苏东坡强烈反对以刑法灭情的做法:与其以礼扼性制情,不若放任性情自流,物极必反,恶去则善来:“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8〕以情为恶,隆刑重法,压制人自然的欲望与情感,终会自取灭亡。与刑法相比,礼教对人自然性情的戕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此礼之所以为强人而观之于其末者之过也。”〔9〕丧葬之礼,将人不愿意持续的悲痛,延续至三年;婚嫁之礼,却使得本应该享受持久的快乐,不得终日。所以,不宜以礼法强加于百姓,堵不如疏。
苏东坡之门生秦观,曾如此盛赞苏东坡的道德性命之学:“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10〕秦观认为,性命之学方为苏东坡学说之精华,以文章称颂苏东坡,名尊而实卑。但在朱子那里,让苏东坡及其门人引以为傲的性命之学却不名一文:“东坡说话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间又自有精处。如说《易》,说甚性命,全然恶模样。”〔11〕苏东坡学说确有其可取之处,但天人性命之学却不得要旨。
及朱子之世,胡五峰等人对苏东坡以“情”为“性”之主张极为认同:“胡五峰说性多从东坡子由们见识说去。”〔12〕更有甚者主张失却中道喜怒哀乐,亦是人之常性,朱子于此批判道:“如此,则性乃一个大人欲窠子!”〔13〕于朱子而言,胡五峰之辈沿袭苏东坡之性情观,以欲代性,不分善恶与是非。所以,打破不分性情,甚至以欲为性的局面,是朱子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首先,朱子判未发是性,已发是情;性为仁义礼智,情为四端、七情;性为理所赋,全善无恶,情因气而成,有为善或为恶的可能。二程批判了以爱言仁之说,严格地区分了性、情之不同:“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14〕朱子承继并发展二程之学说,认为性为未发,情为已发,依此而言,不仅喜怒哀乐爱恶欲是情,四端亦是性之动:“盖谓情可为善,则性无有不善。所谓‘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恻隐是情。恻隐是仁发出来底端芽,如一个谷种相似,谷之生是性,发为萌芽是情。所谓性,只是那仁义礼知四者而已。”〔15〕仁义礼智为未发,无有不善,然而发出来却有不善,是何故?“只有性是一定。情与心与才,便合着气了。心本未尝不同,随人生得来便别了。情则可以善,可以恶。”〔16〕在朱子看来,四端之情虽由理而出,无有恶处,但七情却是气之所动,气有渣滓,故有为恶的可能。
其次,在性情关系层面,朱子主张性本情末,心主性情。“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17〕因性之难见难言,与苏东坡相类,朱子也主张以情见性:性为形,情为影,性发动为情,由四端“情”之善,可以看到性之善。与苏东坡不同的是,在朱子这里,性情有本有末,性具有更为根本性的作用,情之于性,如影随形。“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至动时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则混然体统自在其中。心统摄性情,非笼统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18〕朱子认为性为心之体,寂然不动;情为性之用,感而遂通;心管摄、分别性情,静时主宰性,动时主宰情。
最后,在工夫论上,朱子认为“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心是做工夫处”,〔19〕故未发时须涵养人性,已发后省察人情,以此存善去恶。“存养是静工夫。静时是中,以其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也。省察是动工夫。动时是和。才有思为,便是动。发而中节无所乖戾,乃和也。”〔20〕依朱子之意,不论是存其善,还是去其恶,都需要在心上做工夫:心在静时,思虑不起,需要持敬涵养,以此察觉天地之心,而存其善;心受到声色货利引诱而动,则需要克己省察,以去其已萌之恶。“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21〕心之本体万理具足,静时全其本体,动时发其功用,如此,便能做到天理流行,人欲尽去,不论是已发还是未发,始终保持在一个应然之善的状态。
究其根本,苏东坡、朱子性情之辩可以规约为内外之争。苏东坡重人之情:真其情,直其情:“从来性坦率,醉语漏天机。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22〕通过情的自由外放,获得身心的满足。朱子重人之性:以至善之性为标的,涵养未发之性,省察已发之情,其批评东坡不屑于礼法,厌恶修身工夫之行径:“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23〕朱子以性的内收,由性及情,由内达外,显乎本然之善,消除人情为恶的可能性。
二、学理意涵:王船山内外交养的性情主张
王船山对苏东坡与朱子的“性情之辩”,有较为直接的评议:“或人误以情为性,故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今以怵惕恻隐为情,则又误以性为情,知发皆中节之‘和’而不知未发之‘中’也。(作者按:言‘中节’则有节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节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由性善故情善,此一本万殊之理也,顺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则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将以知性之不善与?此孟子所以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见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喜、怒、哀、乐之中节者征性也。”〔24〕王船山认为苏东坡与朱子的“见性之方”均不可取:苏东坡以仁义礼智为情,以情之有善有恶,而知性之可善可恶;朱子以四端为情,以四端之善,而知性之善。王船山批判性地继承了二者对性情的界定,认为仁义礼智、四端均为性,而七情为情,性为善,情可善可恶。那么,作为宋学殿军之一的王船山,当如何取二者性情观之长,以去其短?
首先,王船山凸显了情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性自行于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动则化而为情也。”〔25〕情独立于性之外,并非为性的附属品。因此,我们要肯定情的释放,以“达情者以养其性”。〔26〕朱子认为性已经是至善至美的,“存养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27〕故其着重未发时的涵养,与已发之时的省察,以情之善显性之善,以保证道德实践的至善境地。于王船山而言,性是日生日成的,而性的生成,离不开情的助力:“功罪一归之情,则见性后亦须在情上用功。……既存养以尽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为功而免于罪。”〔28〕朱子与王船山有关情是否有能动性的差异,最为集中地显现在二人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一章的诠解之上:“‘实’与‘本’确然不同。本者,枝叶之所自生;实者,华之所成也。《集注》谓‘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其意亦犹此’,是大纲说道理,恐煞说二者是实,则嫌于以仁民、爱物、贵贵、尊贤等为虚花,故通诸有子之说,以证其有可推广相生之义。”〔29〕朱子释“本”为“仁性”之根基,其以孝悌为爱、为用、为情,在此视域下,守住内心的“仁性”之根基,才是第一要务,相比之下,尊贤、贵等之实事,只是“仁性”自然外显而成的“虚花”。“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0〕而仁为体为用,涵养仁体之根基,向外扩充,则孝悌之情不请自来。王船山解“本”为“实”,如此爱之情为花,仁之性为实,花有其能动性与独立性,有花方能有实。王船山肯定朱子由性生情之说,否定其以性显情之论,以彰显性之于情的能动性:“若情固由性生,乃已生则一合而一离。如竹根生笋,笋之与竹终各为一物事,特其相通相成而已。又如父子,父实生子,而子之已长,则禁抑他举动教一一肖吾不得。情之于性,亦若是也。”〔31〕情自有其能动性,情之于性相通相成,如竹之与笋、父之与子,交相成长,以此生生不息。
其次,王船山亦强调以性之善,对七情之恶适度地节制。苏东坡的“以情为性”之说,与朱子的“以性为情”之论,均有其危害。“若尽其情,则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炽然充塞也,其害又安可言哉!”〔32〕苏东坡“以情为性”,尽其性情,则七情不加节制,人欲充塞。“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见,人之不以人心为吾俱生之本者鲜矣。……性有自质,情无自质,故释氏以‘蕉心倚芦’喻之;无自质则无恒体,故庄周以‘藏山’言之。无质无恒,则亦可云无性矣。甚矣,其逐妄而益狂也!”〔33〕在情上用力,随其自然,放任人情,最终只会沉溺于物欲之中。已发之情,需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性的节制,情方能保持中道,并助力性之实现。“夫情苟善,而人之有不善者又何从而生?乃以归之于物欲,则亦老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之绪谈。抑以归之于气,则诬一阴一阳之道以为不善之具,是将贱二殊,厌五实,其不流于释氏‘海沤’‘阳焰’之说者几何哉!”〔34〕朱子“以性为情”,尽四端之“善情”以显性,将不善归于物欲对人心的引诱,则容易陷入释老的禁欲主义。所以,王船山主张情已发之后,亦可以“性”节“情”:“喜怒哀乐之情虽无自质,而其几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节,则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敌灵,静不胜动,且听命于情以为作为辍,为攻为取,而大爽乎其受型于性之良能。”〔35〕情已发之后,如若有性介入,则在实际的道德实践中,恶亦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最后,王船山试图彰明性情的交相互养之道。“故普天下人只识得个情,不识得性,却于情上用工夫,则愈为之而愈妄。”〔36〕苏东坡任情之自然发露,以见性之可善可恶;朱子以四端之善,以显性之善。二者均在情上用功,并未注意到,情在已发之后,性的制约作用。“以恻隐而行其喜,以喜而行其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怒、哀、乐之交待以行也,故曰交发其用。”〔37〕此外,情独立于性的能动性,可以助力善性由内及外的扩充:“今夫情,则迥有人心道心之别也。喜、怒、哀、乐(作者注:兼未发),人心也。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作者注:兼扩充),道心也。斯二者,互藏其宅而交发其用。虽然,则不可不谓之有别已。”〔38〕性引导、制约情的生发,情助力、促进性的实现,性情相互交养,共同致力于善之扬、恶之去。
合而论之,王船山批判了苏东坡与朱子两派呈互斥之势的性情思想:以性统情,易陷入枯槁,缺乏生机;混情为性,则人情炽然,物欲横流。随后,王船山借由对情之自主性、能动性的凸显,以及以性之善于人情之恶的提防、抑制,彰明性情的交相互养之道,以存善去恶,无过无不及。
三、价值转向:王船山在“宽松”与“严格”之间的性情观
侯外庐曾在其“早期启蒙说”中,将王船山与其他明清之际儒者的理欲与性情观,划入道德宽松主义阵营。〔39〕王汎森与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针锋相对:“许多持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道德主义者。”〔40〕在他看来,王船山虽然是一位自然人性论者,但其理欲观、性情论均属于“道德严格主义”。郭齐勇借由对朱子、王船山性情观歧异之比较,认为“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超过了朱子”。〔41〕
如前所论,从王船山对苏、朱性情观之张力的纾解上,可以看到,王船山对情的警惕远高于以苏轼为代表的重情主义,此无须赘述。但我们不能以此判断,王船山之性情观隶属于“道德严格主义”。
相反,朱子对情在未发露之时的警惕高于王船山:王船山作为宋明理学中身心实践向社会实践学说转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其以外在结果为导向与判断标准,认为内在未发的七情,不可称之为善,因此,不需要耗费过多精力操存、涵养。在朱子看来,未发的喜怒哀乐为性,至善而无恶,王船山质疑朱子的此种论调:“喜怒哀乐未发,则更了无端倪,亦何善之有哉!中节而后善,则不中节者固不善矣,其善者则节也,而非喜怒哀乐也。”〔42〕如依朱子所言,“李林甫未入偃月堂时,杀机未动,而可许彼暂息之时为至于仁乎?”〔43〕朱子主张七情未发为“性”为“仁”,故其尤为重视对于未显露时“喜怒哀乐爱恶欲”内在的操存,涵养暂时未发“怒”“恶”之“杀机”,即为片刻“性”之“仁”。王船山认为未发的“喜怒哀乐”了无端倪,不可以称之为“善”,因此,放弃对使“喜怒哀乐”始终保持为未发之“性”状态的追逐。
此外,朱子对已发之情的警惕,亦不亚于王船山。在朱子那里,情的最优状态,是恢复到性之平静如水的局面,如此则天人合一,而方能重现天地之心:“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底。”〔44〕朱子认为四端之情经天命之性所生,七情之情是由气质之性生发。性为平静之水,情为水之流动。而不正当的欲望是由气所赋之形体,在外界声色嗅味的引诱下,情的泛滥所导致的。王船山认为“喜、怒、哀、乐,只是人心,不是人欲”。〔45〕其对已发后泛滥之情(即朱子所谓之“欲”)的界定,明显宽松于朱子。如追求美味,在朱子看来便是“人欲”,而王船山则主张“欲无味,则无如无口”,〔46〕对美味的执着,是人最自然的情感,不需要过度克制。
再者,从肯定已发之时情对性的助力,褒扬“过”与“不及”之情的功效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较之朱子,王船山对情的宽松。其一,船山批判了朱子将情之善对于性的助力,视为理所当然的看法:“不善虽情之罪,而为善则非情不为功。盖道心惟微,须借此以流行充畅也。如行仁时,必以喜心助之。情虽不生于性,而亦两间自有之几,发于不容已者。唯其然,则亦但将可以为善奖之,而不须以可为不善责之。故曰‘乃所谓善也’,言其可以谓情善者此也。(作者注:《集注》释此句未明,盖谓情也。)”〔47〕情具有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并不是性的附属品。其二,王船山认为朱子之说,忽略了已发之情,在实际的道德实践中,可亦助性的一面:“孟子言‘情可以为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过、不及者亦未尝不可善,以性固行于情之中也。”〔48〕过与不及之情,亦可以为善。
所以,我们可以将王船山的性情观,划分在涵化“放情”与“敛性”之间的道德中道主义阵营中。正如船山所言,性与情交相互养、松弛有度,方能相得益彰:“愚于此尽破先儒之说,不贱气以孤性,而使性托于虚;不宠情以配性,而使性失其节。”〔49〕王船山之性情观在凸显情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基础上,亦着力于对七情之恶的遏制,较好地彰明了性情的和合之道,为此后儒家性情思想的发展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