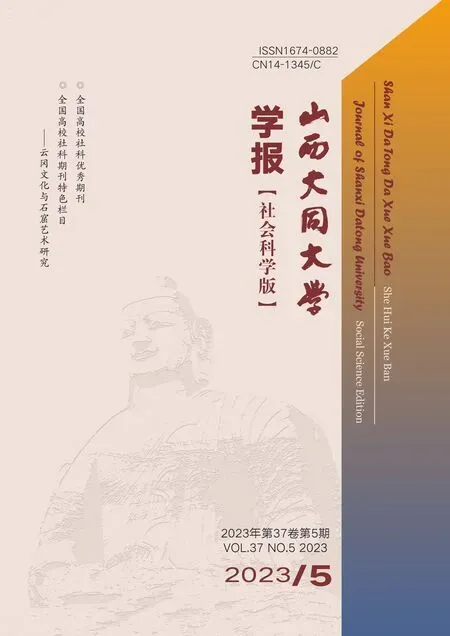《诗》时代长江文化意义生成与意指可及
2023-12-29王列生
王列生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时间线性不同位置,《诗》文本长江文化直接叙事,先后有《国风·周南·汉广》、《国风·召南·江有汜》和《周颂·荡之什·江汉》诸篇,当然间接关联的篇章抑或语用也还不少,个案如《常武》提及的“如飞如翰,如江如汉”足以确证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召南之诗或南国之事的篇章,都与长江文化或多或少意义关涉。如果仅以《诗》时代和长江流域作为事态还原的目的论时空背景,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特定线性过程长江文化生成演绎的标志性意义定位域,且能在其它资料充实和佐证条件下逼近某些历史真相。这种逼近,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命题建构而言,或许有助于宏大命题者涉事长江文化总体性言说之际,理性姿态地确立言说与命题之间有条件意指关系建构可及性,以及言说可及过程中的真值条件和概念边际。此议的切要在于,作为流域文化的总体性长江文化价值命题,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仅仅是一个现代治理语用创建,其创建的目的与合法性,不过在于神圣精神隐喻统辖下流域文化资源整合与开发的知识拟置与社会构思,而历史现场的文化史状况却既无总体性长江文化存在实体,亦无与这一实体相统一的长江文化神圣精神隐喻,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晰宏大叙事者究竟给定了哪样一些价值凸显的长江文化精神义项或隐喻向度。
一
《诗》时代社会生存延展与社会意义生成之前,长江自然本体的诸如《释名》所谓“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1](P56)或者晋郭璞恣肆渲染的“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聿经始于洛沬,拢万川乎巴染。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晦运,状滔天以淼茫。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出信阳而长迈,淙大壑与沃焦”,[2](P557)抑或《山海经·中山经》粗线勾勒如“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崌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多䲀鱼”,[3](P126)都无不表明于地理学知识域,至少中古以前还处于极为浑噩的认知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体现为“江”特指“长江”,依然没有存在论总体性完整指涉,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对起源、流域乃至穿越路线精准性的一系列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地理学对长江本体作存在论科学定位以前,长江即便在自然意义上,也只是具证与想象混杂与共的代际绵亘模糊概念,尽管在这样的模糊概念下,亦不乏精准且清晰的古代地理叙事,细节知识个案如《水经注》三卷“江水”描述中,常常令人叹为观止地阅读到诸如“沌水上承沌阳县之太白湖,东南流向为沌水,迳沌阳县南,注于江。谓之沌口”。[4](P689)
凡此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仅就自然地理学审视角度而言,“江”即使作为具有模糊性的总体概念,极限语指也应止步于非全称态集合语义,而非本体澄明的聚焦语指。问题还在于,既然这一总体概念状况一直滞存至现代地理学的中国入场,以及基于这种入场对长江大范围知识突进和最终获取的成熟把握成果,那么对于两千六百年前的《诗》时代岁月更迭而言,长江作为自然地理总体概念,就更会在聚焦缺失前提下连集合的可及程度亦非常受限。《汉广》所云“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5](P41)《江有汜》所云“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5](P64)《江汉》所云“江汉湯湯,武夫洸洸……于疆于理,至于南海”,[5](P684)字里行间都无不是所议对象茫然无奈的作诗主体心理写照。诸如《易》所谓“象曰:山下出泉”[6](P26)的一般道理,或者《书》具证的所谓“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7](P81)无不与《诗》的长江观念一起,知识共聚于流域总体性极为模糊而地域分存性相对清晰。正因为如此,就“江”的自然知识谱系而言,此后数千年都沿着《诗》时代知谱源而代际延展其谱系日渐繁富的地域化在地求证,所以往往更多读到的是地域长江知识代际分异,如《孔传》云:“江于此州分为九道”。《正义》曰:“《传》以江是此水大名,谓大江分而为九,犹大河分为九河也”。《浔阳记》有九江之名,虽名起近代,义或当然。……张须元《缘江图》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乌土记,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鸟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廪江,参差随水长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终于江口,会于桑落洲。”[8](P204)
但对历史地理学而言,除了将“江”的自然地理流域或地域给予时域定位以外,还一定会在时域定位过程中不断地将自然地理社会化,由此也就意味着超越性地衍生表层事态的社会事件关联与深层的文化意义生成。就前者而言,《左传》叙事的“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诸梦中”,杜预注之为“蒙,泽名,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有云梦城”,[9](P371)或者《尚书》对下江财富构成状况所给定的“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错。厥贡惟金三品”,[7](P80)皆是表层事态的简单呈现。就后者而言,则无论朱熹说《江有汜》“是时,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国,而嫡不与之偕行者。其后,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10](P14)还是姚际恒同题之议的“《集传》以‘啸’贴‘悔’,以‘歌’贴‘处’,意味索然”,[11](P44)都是对文化意义生成的直接抵牾之论。其实无论自然地理学还是历史地理学切入,抑或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彼此抵牾与相互趋同,都必然会在历史演绎维度逐步实现文化意义生成的增量与拓值,所以对于那些人文地理学家而言,就会始终致力于“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12](P11)意义生成与价值累积,仅就长江文化的社会建构进程而言,由此获得时空具象与指涉意象的知识升华,并且不断地在建构和升华生存依偎与精神寄托,从而展开那个时代人与长江的直接生存关系与间接文化功能,也就是在物质界面与精神界面,确立当时历史场域的某种文化信仰,一种若恍若惚或实或虚的精神家园。
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不仅在空间中必然有彼此并列的历史,而且在时间上也必然有前后相继的历史”,[13](P852)而这一结论的逻辑延伸更在于,所有诸如此类的历史生成,都存在于更为本体性的发生前提,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3](P55)《诗》时代整个长江文化流域的社会建构与历史演绎,同样是在这样的前提及其生成史中展开的,其建构无外乎“人的对象化”与“对象的人化”动力互驱。因为这种动力互驱从而在“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10](P11)过程里,不断建构长江流域社会,并不断生成集合概念下的长江流域文化。如果技术化到应用地理学界面,其数千年建构成果的当代形态甚至可以较大程度地,捕获于诸如“垂直航空摄影的使用”[14](P586)等一系列现代技术工具,尽管这种使用对《诗》时代长江文化风貌而言,或许只有微不足道的逆向分析知识效果。
二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即使超越性地在历史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知识界面对当时的“动力互驱”事态还原,其真相也只能至于地域文化地缘生成而非流域文化整体精神凸显。也就是说,在现代长江文化治理命题提出之前,从来就没有过流域覆盖的“长江文化”指称、“长江文化”理念直至“长江文化”精神,尽管此议仅仅只是以《诗》时代边际事态作为存在真相的分析对象。或许有论者会认为“滔滔江汉,南国之纪”,[15](P300)可以成为流域性长江文化精神否定判断的逆向肯定证词,其实不然,无论朱熹“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10](P12)释名,还是王应麟“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16](P2)持论,皆不具有总体性指涉功能与普遍性价值指向。况《多方》之“弗克以尔多享天之命”[7](P253)的自律所言中,流域的地理长江必不能为其中所指定位的任何一方,所以长江文化聚焦在《诗》时代既无所载亦无可能,“南国之纪”由此依然只有地域统辖意义或者文化维系功能。
基于这样的前置条件,我们就应该以理性的姿态,追诉历史地理现场的长江文化生成真相,因为就《诗》时代自然长江的四百多年进程而言,必然会发生与这一进程相同步的社会生活丰富延展、文化意义复杂生成以及历史脉络纠缠递进。具证社会生活丰富延展的“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5](P64)具证文化意义复杂生成的“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6](P15)具证历史脉络纠缠递进的“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7](P150)诸如此类,都是意义生成和历史演绎现场发生事态。问题在于,就事态进程而言,现有的知识文献所能支撑的长江文化真相,并非某种或者某些精神特征隐存其中,并由此确立起长江文化作为特定流域文化的总体形态或整体形态,从而构成所在时域抑或绵及其后漫长岁月民族精神理想、民族文化信念乃至民族生活风尚的集体无意识图腾,进而以其异质于具象图腾日常生存维系,功能性地无限发散着抽象图腾精神社会历史建构伟力。似乎它既能吻合于列维——斯特劳斯看重的“表现群体的对象”,[17](P76)更能吻合于卡尔·曼海姆设定的“处于公理层次上的精神社会学,社会本体论及其与思想的历史特征的关联”,[18](P95)总之是殷殷寄托于此类图腾的功能形式,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建构史上充分展现其本体价值托重姿态,俨然卦象之设所能效果凸显的诸如“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尊三才而两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安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贤,知来者逆”。[6](P185)与这样的虚拟意愿恰恰相反,《诗》时代长江文化的意义生成与存在特征,更大程度上表现为“由北而南”文化延展路线,及其延展过程中不同地域文化板块,按照时间线性与向量的异质性形态认同,而且是地域文化认同或区域认同文化形态生长后果的“相互间的喜爱将个体的集合转变成一个群体”。[19](P110)
就“延展路线”论,无疑与历代《诗》家所谓“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汉广》序又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是也”,[5](P13)又所谓“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不直名为‘周’,而必连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于南方故也”,[20](P2)具有高度文化涵化过程一致性,与文化人类学的“涵化原理”高度嵌合。而就“地域文化”或者基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地缘文化”论,则《诗》时代整个长江流域的不同地域,实际上都因所在时域不同“文化促发力”内在驱动,形成不同地域文化形态或者地缘文化板块,并且彼此间其异质性远远大于同质性,它们在自然长江的地理维系下自在生长、自存个性并且自发传播,地理维系在此并不具有长江文化的地域形态以及地缘板块的认同化或叠合态文化整合功能。只不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以“江汉朝宗于海”为标志性识别代码的“荆楚文化”,此时作为南化文化成果的地域文化形态或地缘文化板块,最具长江文化的历史表征功能与地域凸显价值,而且所有这一切,在最具关联意义的经典文献中,有其更为充分同时也更为妥靠的事态呈现。
其实就“荆楚文化”作为《诗》时代最具表征意义的长江区域文化形态或地缘文化板块而言,必然是时间线性与意义向量的渐进产物。对四百多年递进时间与向量的整合压缩而给予意义归纳或意指定位,显然具有强制阐释的知识暴力特征。仅就《诗》文本的直接叙事而言,从《周南·汉广》、《召南·江有汜》到《周颂·江汉》,除了时间维度跨越由文王而至宣王数百年间社会史进程之外,还在于这种跨越,实际上隐存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社会制度史乃至社会意义史等社会变迁,而社会变迁在任何生存界面都必然意味着文化变迁,此议之际,则直接意味着长江的区域性文化变迁。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一直接叙事界面,对所发生的《诗》时代文化变迁给予学理分析,则至少可以切分为《汉广》和《江有汜》时期所表征着的日常人文倾向,以及《江汉》时期所呈现出的社会历史症候,因而其所涉及的知识分析工具,前者会较多牵系于文化人类学,而后者则会更多地关涉文化社会学,尽管在两个具体知识域内,会有诸多问题处于交叉地带与学理叠合空间,但知识工具的功能取向分异或许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如此,则日常人文倾向居于支配地位的“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言刈其萎。……言刈其驹”,[5](P40)乃至意义生成事态具有内在关联的《鹊巢》、《采蘋》和《汝墳》等,或者与《江有汜》具有相同历史地理背景的《草虫》、《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野有死菌》、《驺虞》等,其所反映的就必然大都是早期周人围绕江汉地缘的主流文化建构事态,且以地域文化知识方式,生成于“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21](P22)抑或“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水大水,其无津涯”[7](P142)的时代大转折。于此背景之下,与史学家焦点关注“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5](P536)有所不同,人类学家的审视视野会更倾情于诸如“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5](P51)或者相同母题甚至相似叙事方式的“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5](P46)其对某种在地文化特别倾情的心理动力在于,人类学家对《诗》时代以江汉为基本地缘纽带的区域性南土,更具人文演绎的生存论文化还原追问兴趣,并且与应劭式文献述事的“后飞廉使奔属。飞廉,风伯也”[22](P364)有所不同,亦与伏尔泰式一己之见的“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23](P90)迥然相异,他们会在追问过程中以严格的田野作业程序,尽可能在《诗》时代经典文本以及后世关联文本中,捕获其意欲最大量值,捕获的诸如日常生活风尚,原始祭祀方式,器物功能分类,两性氏族藩衍,社会价值维系,语言交往过程,时空观念内涵,以及文化发生机理等诸多留存痕迹,俨然个案具证知识路线的“要研究青铜容器和陶器,我们就得研究古代中国的饮食习惯,而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器物本身便是有用的资料……在《诗经》和《楚辞》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于宴饮和食物生产情况的生动的描写”。[24](P33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人类学知识取向的“证明初民生活状态的简陋,证明他们在心智方面的能力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渐进化,证明他们向文明之途胜利迈进时为了克服重重障碍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25](P4)足以使“荆楚文化”作为标志性区域而非流域长江文化获得《诗》时代的坚实确证,亦如学术界对后继“楚文化”巅峰时域的研究曾经取得的丰硕成果,足以使增量和拓值意义上的所指地域文化形态,既能空间有效覆盖亦能时间有效绵延。
与此不同,《诗谱》定位《江汉》作于周宣王中兴之际,因而其所言说的“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章,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东铺。/江汉湯湯,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事,王心载宁。/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来甸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5](P684)其意义生成就远非毛享一句“《江汉》,君吉甫美宣王也。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26](P579)所能概括或者指引。至于后世文本揣度如“盖此诗乃召公旋师奏凯之后,论功行赏之时所作。末章‘虎拜稽首’之下云,‘明明天子,令闻不已’,是穆公归功于上之言。此章则为宣王推美于下之词”,[27](P373)或者诗旨提要如“《江汉》则言宣王之征乱讨罪,而因及召伯之贤,而不专于召虎”,[28](P3503)同样大都止于《诗》语义而不及于《诗》语境,乃至《诗》时代其所具有的社会本体绽出功能。虽然自汉四家《诗》说先后张扬,直至清代小学家群起作《诗》义的精准化训诂、声读和义疏,对《诗》的理解、传承乃至现实张力功高盖世,但汲汲于木却茫茫于林,《诗》研究史有所功能缺失是不争事实,且我们站在当下知识语境,基于现代问题意识或者拥有更多分析工具,那些缺失必然会更加凸显和放大。此议之际,如果转换至文化社会学视角分析《江汉》的知识场域,就会很容易从前人已然洞察《江汉》《常武》乃征淮夷这类简单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关联至所有事涉厉、宣、幽或美或刺的《诗》作,并在这样的关联中能够深度揭蔽涉事隐存着的社会延展、矛盾纠缠、利益冲突和国家建构等《诗》时代的一系列革命性转折,以及由这些转折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后果。虽然此议重点,并非还原《诗》时代《江汉》时期的较为完整历史现场与较为系统的社会演绎义项,并从宣王中兴或者厉、幽败国的《诗》本文兴观群怨深情诉说中,寻找那些曾经的社会蕴涵与历史镜鉴,但有一点却很明确,那就是从《诗》时代长江历史地理的线性延伸过程而言,《江汉》时期较之《汉广》与《江有汜》时期,已然发生意义生成方式和意义存在形态的地域生存转向,意即一种由旨在道德教化和人文教化向重在权力分享的全面社会扩张的去地域化突进过程。
其突进的宏大背景社会根源在于,不是人文教化已经终结,而是周王朝至此必须严竣面对诸如“瞻我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5](P693)或者极端状况的“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采!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29](P7)并在纷繁复杂的面对之后,要么政权强大于“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5](P691)要么民生托举起“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戚,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29](P10)所有这些“面对”与“处置”,无论肯定价值在场还是否定价值在场,其几何级数线性生存增量与递进存在拓值的社会后果本身,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文化和社会的进展、进化乃至进步,因而也就一定呈现为意义生成渐变与突变交往驱动的历史格局。恩格斯所谓“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0](P186)无疑可以实现对西周社会发生史整个过程的事态覆盖,而且愈是社会延伸就愈具有事态覆盖的知识有效性。
三
当我们回到文化意义生成的此在议题之际,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诗》时代长江文化命题指涉的现场事实,那就是从时域早期至晚期的意义生成函数曲线,呈现为两大主旨抛物线的非叠合延伸,并且可描述为早期人文主旨曲线,其抛高明显大于社会主旨,此后则社会主旨的曲线抛高轨迹更具抬升的垂直逼近,尽管这种抬升丝毫不意味着对前者的压制乃至置换。所以很显然,《诗》时代的南土及荆楚文化,总体体现为人文主旨和社会主旨双重意义生成的增量与拓值互驱递进态势。与此同时,虽然九域治内总体态势的社会文化裂变,确如王国维一言止之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徵也”,[31](P465)但对荆楚乃至南土的江汉地域延展与区域性长江文化圈生存建构而言,后者的建构强度、力度以及难度,亦非王氏知识答案所能靶向解读乃至解读有效。所以跟进的问题就是,在殷周代际转换和《诗》时代宏大背景诸多议题暂且悬置条件下,基于这种背景的区域长江文化所意义生成的两大主旨,其精准所指究竟何在?就目前笔者的肤浅理解,或许可以在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学理叠加基础上,所指定位于以巫筮祭祀为切要的“日常人文风尚”和以道德建构为引领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且在文化发展功能实现过程中,极为明显地呈现为前者发散态而后者凝聚态。
就第一大主旨定位而论,传统知识史过度单一强调“文化涵化”的一面,也就是所谓“由北而南”及其具议如“文王之国在于岐周,东北近于纣都,西北迫于戎狄,故其风化南行也,从岐周被江汉之域”,[16](P7)而忽视了“文化自衍”的一面,也就是“由内而外”地方性知识的在地功能自适,个案如“南蛮数为寇逆,其民有道后服,无道先疆”,[1](P78)其对隐存的在地文化消息就非常丰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江汉之域或者广义南土的人文风化,应该理解为“由北向南”与“由内而外”的互驱结果,其交互必然表现为内驱动力与外驱动力合力形成过程,而且是“文化扩散”所谓“来自一个源头”,[32](P244)与“文化本能的诸如“那些马林诺夫斯基最富地区性的地区性细节”[33](P90)相类似的选择性接受后果。“涵化”与“自衍”的能量互驱,在四百多年《诗》时代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孕育、培植、滋养并且延展着江汉之域的文化风尚,抑或南土之民的人文形态。这些文化人文,不仅显形于语言陈述的诸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5](P150)或者“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5](P54)抑或“维雀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5](P45)而且更隐形于非文字记载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与衣食住行,以及其它生存不可或缺的细节行为方式之中。那些“野有死麕,白茅包之”,[5](P64)或者那些“彼茁者蓬,壹发五豵”,[5](P68)无不是隐喻取向中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细节流露。基于功能和秩序取向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人文风尚,其生存论现场事态与存在论可还原丰富义项,远非既有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所能完全追诉,但这些已获得追诉的所在时空人文风尚意义生成,却能以文化症候的可审视功能与可洞穿缝隙,使我们一定程度地得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并由此展开对无限发散地域文化意义生成给予自由姿度的无尽想象,亦如他们站在《诗》时代时空位置,自由地想象更为遥远从前的“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北,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7](P19)
在这一定位过程中,无论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成果的事实支撑究竟能至何种程度,有一点可以基本肯定,那就是人文风尚在江汉之域日常生活意义结构中,以巫筮祭祀活动行为价值功能最为切要,或者说它是义项编序中的核心要素所在。周王朝虽“厥命惟新”却终究是“旧邦”,因而殷商至西周的人文传统与日常习俗,在生存论界面的普遍因沿必为常态,所以《诗》中周人尚卜尚筮的“尔卜尔筮”[5](P134)与崇祭崇祀的“于穆清庙”,[5](P706)与有商一代居社会生活绝对支配地位的“占卜不仅成为其他所有祭祀的基础,而且也是其他所有活动的前奏曲”[34](P219)之间,既构成类似陈梦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等文献所揭蔽的知识谱系关系,亦构成大批商周考古成果所澄明的行为传承关系。进一步,则不仅《周南》《召南》中花草虫鸟多为祭祀活动特定功能需要的灵物,而且雅、颂之作亦多为祭祀活动矇瞽诵辞,而这些宫廷祭仪在风化南土与“滴渗”日常过程中,极大程度上会在去仪式化的同时,获得巫筮习俗蔚然成风的草根性、原生态和日常化,由此而在区域长江不断风化扩展的土地上,发散出在强度和形态等诸方面都相异于其它区域文化代际相仿的巫筮文化生活风尚。顾炎武在议论“楚吴诸国无诗”时,提及“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乎”,[35](P146)考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同时代事成王,因而《诗》时代早期江汉区域长江文化积累下生灵遍乞巫筮的文化风尚,某种意义上也是周初体制的“服”制度使然。但《诗》时代后期周室衰微,邦国之《诗》由此衍生出尚难一一确证的方国之《诗》,即《诗》知识史争议不断的所谓“变风”“变雅”,因而必不越五百里的“小楚”“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奥,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21](P326)也就在社会变迁中演绎为数千里江山“大楚”的“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21](P327)而这种演绎,恰恰就首先体现为作为区域长江文化的“楚文化”覆盖面愈来愈大,而且愈来愈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中文化性格凸显的地域文化形态。尽管楚文化的巅峰状态存在于《诗》时代之后的《楚辞》时代,亦即所谓“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36](P54)但隐存的文化逻辑在于,无论就其深度、广度还是高度,这一巅峰都是《诗》时代江汉之域日常人文风尚的文化延展成果。
就第二大主旨定位而论,其实在从《诗》时代缘起到《楚辞》时代,在地域文化形态化中,深刻地蕴含着三个时段的国家意识形态引领:(一)周邦国颠覆殷商过程中,尽可能将其自拟的意识形态内容渗透于周公召公采邑抑或王化南土。(二)夷王势微延续至厉宣幽社会矛盾冲突激化,导致周王朝不得不将意识形态维稳社会功能发挥到其致。(三)平王东迁后,邦国弱而方国强,由此而有方国国家意识形态在“变风”、“变雅”中异端性超越,其中包括以江汉为地缘纽带的楚国,最终产生以屈原为代表的激情精神意识形式,这一形式秦汉以后逐渐演绎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过程中,兴起之初的周王朝青春勃发于“周虽旧邦,厥命帷新”,[5](P532)非常自信地矢志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6](P14)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P22)其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至少在广阔的南土能够殷鉴之后“至于海表,罔有不服”,[7](P262)由此才有善政后果的“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5](P54)显然,这是青春的西周王国与众多南国。但是,它在一步步深陷“历史周期率”难以自拔之后,就有王政大溃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恶政后果的“厉王虐,国人谤王……王不听,于是国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29](P5)一直溃败至天人感应的毁灭性“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29](P13)所以立身厉、幽之间并崛起于“共和”之政背景下的宣王,尽管踌躇满志于邦国中兴,并且有征淮夷大胜记载的“江汉湯湯,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5](P648)却终究在“既亡南国之师”[21](P29)后无力回天,而其所谓“中兴”的支撑杠杆,说到底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泡沫宣传的“既敬既戒,惠此南国……不留不处,三事就绪”,[5](P690)显然,这是没落的西周王国与非自立不足以地缘生存维系的南土。自此之后,当周王朝沦落为怜悯对象的“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5](P147)历史进入春秋后,各大小方国纷纷于征伐中奋求自兴,由此而有“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而王不加服,我自尊耳”,[21](P337)并且由楚成王芈熊頵的“于是楚地千里”,[21](P337)迅速膨胀至庄王芈侣“问鼎中原”的“遂至于雒,观其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9](P368)而问鼎的底气从根本上肇自王化后果的“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9](P259)显然,方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普及度和影响力,此时都已占据更高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所“崩”所“坏”的不过是周王朝的邦国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功能匹配的制度体系。第三阶段的存在格局,历史穿越春秋战国,文学涵括《诗》时代、《楚辞》时代及其诸子百家散文时代,直至秦一统中国与再后的汉交往四方。
可惜在董仲舒及一大批汉儒博士因“利禄诱引”而主动抑或被动步入“独尊儒术”一条思想史乃至知识史通道以后,《诗》时代四百多年历史演绎的国家意识形态精神建构,其此起彼伏的复杂性与相生相克的丰富性,都在由周公而孔孟的礼乐教化功能与道德规范价值统而尽之的给定叙事中真相遮蔽,其遮蔽处当然包括楚国历史形成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同质性之外异质性鲜明的精神个体性。之所以后世称道楚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且屈原乃“爱国主义者”时,会滋生诸多逻辑抵牾,也就是不解何以无论春秋方国林立还是战国七雄崛起,为何只有楚文化语境与屈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可以担当“爱国主义”之崇称,一切都是真相遮蔽和时域事态黑箱化处理的岐义后果。其实回到《诗》时代宏大背景,回到从江汉之域到楚地千里的社会变迁现场,由周而楚的邦国与方国之间政治关系从无到有与社会存在结构形态由单一到复杂的历史递进过程,除了人文风尚的日常意义不断生成外,还有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气质转换建构,区域长江文化或者说后置楚文化概念的意义生成及其价值凸显,无疑是两个意义向度于所在时域地缘凝聚的文化成果,此后走向颠峰并且历史绵延的楚文化蔚为大观,只不过这一文化成果的标志性存在状态。
总而言之,从以上两大主旨定位及其关于这种定位关联讨论中,相对清晰地揭示了基于“江汉”或者“南土”的区域长江文化意义生成过程、指向和被汉儒以来矮化乃至消解了的意义后果及其价值地位。而且这种揭示的有效性还在于,它是以自然前置条件为逻辑起点的知识还原过程。这种还原,就其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而言,既吻合“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4](P147)亦吻合于“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纽带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么,这是血缘纽带的各种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同样发生蜕变的结果”。[30](P168)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所议区域长江文化,或者说《诗》时代楚文化从孕育到走向颠峰的生成史描述,言说合法性就不是问题。
四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议题的所议进程至此已经终结,因为事态很明显,即使此议的区域长江文化意义生成并非意味着聚焦态总体长江文化存在论概念存在于《诗》时代历史语境,但集合态长江文化生存论宏大现场及其多元文化构成却同样是基本历史事实。这实质上也就是说,《诗》时代除了江汉地域长江文化抑或楚文化意义生成之外,作为集合概念及其命题指涉的长江文化,还有另外的意义生成现场与作为成果的异质性文化存在形态。
首先是长江下游的“吴文化”及其越灭吴后地域覆盖更为广阔的“吴越文化”。虽然吴的历史创建自太伯受封始,创建之时“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37](P10)但1954年江苏丹徒出土之宜侯夨簋所云“宜地”乃非故吴而已至长江下游,则作为康王时代的宜侯已然从陕西故吴汧陇一带迁徙至江南,丹徒西周墓葬铜器考古发现与宝鸡一带同类发现的一致性,足可成为这种虽无详载文献却实际已越数千里徙而重建的确证。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谓“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亡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21](P238)除了确证由中国而江南的既往历史之外,还留下了寿梦时吴始兴之前约二世而竟不知何徙之遥的时间缝隙。然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如果《吴越春秋》的“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於乎哉:礼也”,[37](P17)与《左传》对在位二十五年吴王所述的“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38](P548)能够互为时序支撑,则寿梦称王或者说吴国在长江下游崛起当在鲁成公五年,即公元前586 年,也就是《诗》止于“陈风”《株林》《泽陂》周定王之时仅相距数十年,从而意味着吴国的长江下游存在史与《诗》时代至多只有这一时域的叠合时间,此无疑为“十五国风”未采“吴风”的有力证据之一,而这一证据乃与亦未采“楚风”的实际根由就语指重心而言迥然有别,因为得风气之先的楚风就在《二南》之中。
既然《史记》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时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21](P345)则除了非确指历史叙事成份之外,就与《越绝书》开宗明义的“谓勾践时也。当时之时,齐将伐鲁,孔子恥之”[39](P1)时域叠合,由此确证其此乃《诗》时代之后的历史现场事态。而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可歌可泣的江南争雄战事,无论《吴越春秋》所载如“于是大夫种、范蠡曰:‘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恥,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志,居危而不以为薄”,[37](P178)还是《左传》所载“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越人以归”,[38](P1049)都是晚至春秋末的事,去《诗》时代更远,本当更在此议范围之外。问题在于,虽然时域处于《诗》时代之后,而从公元前473 年吴王夫差自缢,立国114 年而亡,成为所谓“春秋史”终结的时间标志,再至“楚咸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吴故地至浙江……而越以散,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其所延伸时域的社会变迁已是战国时期递进事态,此时长江中下游几为楚一统江山,但这中间易被遮蔽的文化史事实,就是一方面吴越被灭于楚,并不意味着已然成熟地域文化形态的吴文化,由此就在方国政治更叠中,逐渐被同质化甚至发生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替代”。而另一方面,则是《诗》时代“西北虞”徒居为“江南吴”的移民文化后果,与吴越故地时域内原生在地文化融汇之前,在地江南文化乃至区域内百越文化,乃是长江下游文化的基本生存形态,其演进历程当与楚文化由江汉的长江地域文化延展拓值而来共同其意义生成规律。恰恰就是这一规律,逻辑而且历史地确证着《诗》时代的长江文化,或者说《诗》时代长江下游原生文化与移民文化,是完全异质于江汉文化的区域长江文化板块,只不过其历史确证证据,还有待考古学未来能进一步给定的知识充实与历史澄明,恰如数千年来人们能现实地感受着楚文化与吴文化,各以其独特存在形态存身于不同长江区域,虽同一流域却并未同质化为整合态意义生成的一以贯之流域文化。
其次是关联性更为密切的上游巴文化,或曰巴蜀文化。之所以说“更为密切”,是因为虽吴文化也可与“荆蛮”上溯系于“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21](P237)而所谓“荆蛮”乃荆州、荆山一带的蛮族,其族本当江汉流域土著居民,但更加吊诡当然也更具本源价值之处在于,徙至宝鸡商代末期“吴国”或“虞国”的弓鱼氏荆蛮,恰恰就是逆水而迁的荆山巴族原住民,即当代学者所述的“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商末至西周中期,宝鸡市区渭水两岸和凤县故道河谷一带,曾存在一个异姓方国——弓鱼国”,[40](P33)且《后汉书》所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41](P823)中的巴氏,反过来又是弓鱼氏迁徙前的故族。这实质上也就意味着,即便东吴后的吴文化可追溯至西北虞时太伯、仲雍者辈,曾与弓鱼氏荆蛮有过文化接触乃至文化涵化,也依然不过西美尔式的有限滴渗关系,而长江上游或者汉水上游的巴文化,乃至弓鱼由虞南迁四川的“賨民”(后世又称板楯蛮)及其所形成的文化区,却与江汉荆蛮以及江汉区域长江文化具有直接同源关系,所以称其族群文化关联“更加密切”的言说合法性无可置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长江下游吴文化或者说吴越文化形态化基本发生于《诗》时代之后不同,长江上游巴文化或者说巴蜀文化,其区域文化的形态化过程却在《诗》时代已经完成,无论“其民质真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言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其好古乐道之诗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42](P5)抑或“武王伐纣,蜀与焉……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复声也”,[43](P80)皆为凿凿无疑之实锤。只不过《诗》时代之末及春秋开启逐鹿中原的历史帷幕之后,这些本就边缘的族群及其区域文化必然更加边缘化,或许此即《诗》未收其诗而《书》亦未详其事之依据所在。其实在《诗》之前,学者就认为“青铜时代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从商代就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引进,二者形成了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相近文化”,[40](P228)武丁时期卜辞如“葵丑卜,豆贞,王比奚伐巴方”[43](P342)或“贞,我共人伐巴方”,[43](P6467)足证那一时期巴文化区域的形态化强度,足以令遥远中原的商王朝引以为隐患。
然而,尽管如此高度同源,仍然因所处长江流域上游而形成族群间和区域差异所致的异质性文化形态,进而在宗教信仰、婚姻观念、丧葬习俗、栖居方式、居住日常、建筑风格、精神气质、语言交往、文字符号等难以穷尽的生存论文化义项中,铸就其文化规定性意义上的部落族性,也就是在非现代民族指涉的古老初始语义层次,确立该部落共同体个性化“在地”的“差异的参考点是文化表现”。[44](P27)由于巴人在《周南》《召南》王化江汉地域之前已经越荆山而去,甚或从一开始就在长江上游的崇山竣岭之间“王制屏之远方”,[45](P384)且“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42](P5)享男女篝火之欢,崇悬棺天葬之仪,以原住民的自然开化进程心性怡然于化外之地,岂非别具一格的原生文化?其实如果要将巴文化身居长江上游的地域文化个性以理性知识姿态予以言明,只要从语言地理学一个维度就足以获取存在性洞穿效果,因为“人就在语言之中”,[46](P1122)虽然只是哲学家存在论之思的一种陈述方式或反思向度,却可以所指功能覆盖于从最原始的氏族部落到所谓最文明化的精英群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自然地理的社会语言异质表征方式中,就能以“语言地图”的知识作业方式,通过呈现区域文化形态的某种典型特征,能够使得形态间性及其差异化地域关系得以明晰,其学理依据在于“语言地理学认为语言要素(语言形式)在地域上存在着有序的地理分布,这种空间有序是指可以凭借地理分布去构建历史的地域间关系”。[47](P10)晋郭璞序杨雄《方言》,声称“盖闻方言之作,出乎輶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48](P1)除足证方言调查与解析实际上就是语言地理学知识路径外,还透露一个消息,那就是楚方言和吴方言皆纳入《方言》一书的化内各语言板块分析系统,而巴方言则摒弃于化外而不纳,因而其文化形态的地域个性凸显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在整个《诗》文化时代,巴文化或者更宽泛地说巴蜀文化,其意义生成的文化成果完全能肯定性地存在于所在长江区域,只是它的存量及其时域内线性增量轨迹,目前还只能用混沌学知识方式总体性予以肯定。
其三还在于,一个隐存的意义生成极为纠缠的事实是,在巴文化区域之上,《诗》时代的长江文化还有其“江之永矣”超越巴、楚、吴的《诗》时代意义生成史流域距离完全被遮蔽,被遮蔽的理由在于,无论《诗》时代崇信的《禹贡》岷江源头定位“总流域”缘起持论,还是《诗》之后既久《释名》公共汇流释义的支源皆源“大流域”缘起持论,抑或更为晚近《水经注》以汉水出蟠冢“小流域”缘起持论,都已被现代地理学确证为认识长江尤其其源头所在的知识错误,而这一错误的意义遮蔽最大危险在于,从巴文化上溯至长江真正缘起的三江源地区,凡数千里而在《诗》时代竟无被认知的先民生存活动及其这些活动的区域文化意义生成史,抑或意义生成后果,所以后世仅仅以巴、楚、吴三种文化形态意义凸显作为集合态长江流域文化,显然就是非完整指涉的知识误区。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千古经典,其中“江水”阐证凡三大部份,不谓不详,甚至不谓不精到,随机摘录一段“江水自武阳东至彭亡聚。昔岑彭与吴汉溯江水入蜀,军次是地,知而恶之。会日暮不移,遂又东南迳南安县。西有熊耳峡,连山竟险,楼岭争高。汉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悬溉有滩,名垒坻,亦曰盐溉,李冰所平也”,[4](P633)堪称自然、历史乃至神话的交相辉映,足见其意欲知识效果最大化的不懈努力。此种知识努力,延展至清代小学大家胡渭撰《禹贡锥指》,便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附论江源》,尽举《华阳国志》、《益州记》、《太平寰宇记》、《入蜀记》、《通鑑地理通释》、《书注》、《经籍志·寻江源记》、《徐霞客传》等深度关涉文本,并以小学家的功力与严谨努力予以知识化辨别,无疑为此议涉身者同时也为千百年众说纷纭,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概念知识谱系。然恰恰就是这位考据大家,对于钱谦益《徐霞客传》徐氏河自昆侖之北而江亦自昆侖之南几乎逼近原委的地理卓识,却终究在“余谓霞客所言东西南北,茫然无辨,恐未必身历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8](P570)的愚崇《尚书》故论中,扼杀于真相将明之前,也使其广博精绝的长江知识考据言说坍塌于源误瞬间。
处此知识辨别位置,议者或以为只是长江源头的地理定位之误,岂不知在这样的误解中,会导致江源绵亘之下的广阔江源文化区域于《诗》时代的在场缺失,当然更从本体意义上否定了长江存在的起源真实性与流域完整性,而这样的本体性否定又岂是“历史局限”所能轻易开脱?如果说“荒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功能在于周王朝对四方边疆少数民族的柔性治理方式的话,[49](P484)那么较之巴文化区更为遥远的江源顺流而下的广大地区,必是“荒服”治理对象之一,其绵亘长度就一定远超上游巴文化区、中游楚文化区及下游吴文化区。长江穿越的江源顺流而下广大区域,只要它还是“荒服”对象,就一定有氏族部落人群所形成的社会及其文化意义生成。顺流而下所关联程度不同的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大片西南地区,在司马迁笔下描述为“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隽、昆明,皆编发,随蓄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隽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徒、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以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21](P830)虽然其中所述对象一些存在于《诗》时代以后,而另一些所在地域或所述氏族亦与长江流域基本无涉,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毕竟有些部落及他们的先祖在整个《诗》时代乃至更早,就通过长江源顺流而下广阔区域,以文献未曾详加记载的生存状态开拓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并形成相对宽泛的文化形态,由此开启他们所经验的区域长江文化乃至化内不可企及的诸多文化价值目标。岷江流域及其蚕丛与鱼凫等文化颠峰成果遗存“三星堆”,以其别有洞天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中原殷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形态”,[50](P142)而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要素在于,自江源顺流而下至巴文化区接口端,除《史记》、《汉书》、《山海经》及《水经注》偶所提及的西陲古族外,还有多少依江而居的类似古族生存于斯,至此仍是所在历史时空之谜。甲骨文区别汉代“西羌”氏族的古羌之“”、“”、“”或“”,按今人释义之“羌字从羊从人谊为牧羊之人(有时又常绳索表示牵羊之意”,[51](P114)或按古人解读之“《商颂》‘从彼氐羌’。《笺》云:‘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王制》曰:‘西方曰戎。是则戎与羌一也”,[45](P146)虽则彼此之间不无意义缝隙,但“古羌”而后来“西羌”指涉的历史代际之差却具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留给我们所思空间在于,那些牧羊的古羌在长达数千里的江源顺流而下两岸,他们与别的毗邻古族一起,一定会创造属于他们共同生存开拓的区域文化形态,而在这种形态尚未获得足够的文献支撑与考古澄明之前,我们还至多只能将其笼而统之地称之为诸如“江源文化”,或者说漫长江源的区域长江文化。
所议至此,就《诗》时代长江文化的实存状态而言,至少可以于流域维系切分出四大区域文化板块,而且是彼此文化形态个性鲜明且异质性凸显的区域长江文化个性化意义生成事实。尽管其中不乏同质性义项,但流域性的同质化义项扩容乃至此后漫长历史渐进的复杂过程,至今亦不意味着意义生成异质性的区域长江板块,已经在同质性替代中丧失其背景性日常文化支撑与驱动的社会能量。
五
按照传统研究范式,所议至此可以告一段落,因为它已经在知其然的言说努力过程中,将《诗》时代长江文化意义生成的异质性复杂生存状况,自圆其说出一种知识脉络,知识地图,或者知识呈现方式。但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样的范式,带来了某种问题丢失的学理危机,因为无论文字狱高压逼出来的有清一代才子小学家们,如何将“知其然”绵密到何种精细无漏的事态还原程度,却终究未能在“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引伸中揭示出常人更加难以洞见的真相。就此议而言,意义生成如此,或者以他们的功力可以“如此”得精准或厚重十倍,但这种生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在《诗》时代宏大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由此意义生成的长江文化究竟以何种价值方式存身于“天下”“万国”乃至亿万万的“在场者”?否则其意义生成的事态澄明,就会失去所在时代的价值换算关系,由此也就依然只是在场而无交往的非活性历史实在。尽管小学家们功力何等了得,但他们的“了得”由于历史的原因,基本止步于问题茫然。
我们当然可以在他们止步的地方,找到各种价值指向分异的突围路线,而我所意欲突围的知识靶向仅仅定位于,所议至此的那些意义生成对所在历史时空及涉事在场者来说,其意指何以可及或者说如何可及?这一提问的前置学理条件在于,《诗》时代生存于长江流域中任意一个区域内先民,即使贵族般体验着“当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妾御之数,媵遇忧思之劳而无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过也。此本为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后兼嫡也”,[5](P64)或者民间日常经历“此由世乱民贫,故思以麕肉当雁币也……此女恶其无礼,恐其过晚,故举春而言,而实往岁之秋冬亦可以为婚矣”,[5](P65)则从毛亨到孔颖达的意义解读精准度究竟如何,都不影响这些“体验者”抑或“经历者”对长江作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茫然不知究竟的凝视关系,而且对那些远离长江文化的海量中国先民而言,他们甚至连此类极为有限的在地体验与经历都不曾发生,因而对边缘长江也就更加只能想像性抵达所谓“江之永矣,不可方思”。[5](P41)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无论与长江处于何种涉身抑或涉事关系,其实都不得不首先以观念建构及其存在形式作为想象性抵达的功能支撑,而这势必也就在递进意义上关乎“意义生成”之后的“意义所指”,即每一与长江发生观念关联的个体,总是以其自身的意义指涉来理解和把握长江文化,因而生存论的随机意指关系,就成为长江观念和长江文化实际衍生后果。总之,意义生成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对观念抵达而言,始终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意指关系的随机建构发生,才是意义实现过程中由可能性驱动而至的实在性。如果说这是《诗》时代历史现场事态的话,那么过程本身的进展必然自始至终关涉可及性问题,不考虑可及的一切必然逻辑叙事,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谵妄成份,而所谓“可及”又兼容着“机理性可及”与“在场性可及”,所以我们就选择前者作为此议的叙事重心,也就是试图明白,《诗》时代的人们是以怎样的可及方式形成其长江观念抑或长江文化想象空间。至少就我个人而言,《诗》时代意义生成的长江观念或长江文化的意指可及,无外乎“茫然态可及”、“边缘化可及”和“区域性可及”最具代表性,尽管这并不排除其它可及方式也会程度不同地抵达长江文化的意义生成。
《淮南子》以山势说道势,顺议“水定则清正,动则失平。故惟不动,则所以无不动也。江、河所以能长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天”,[51](P525)议论去《诗》后凡数百年,其所言江依然浑浑然不知所以。那么回溯至《诗》时代历史现场,则《书》之“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5](P81)又或者“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5](P87)则更加恍惚、浑沌甚至起源之误及方位之错等,就是知识史完全可以归谬于进阶之理所当然的所议事态,何况宋王应麟也依然恪守故训之“江源,在松州交川县,至茂州岷山,自岷山东流,别而为沱,至通州海门县入海。《山海经》:‘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崃山、岷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52](P193)又别说为“江水出茂州汶山,岷山,又谓之汶山,今汶山县。朱氏曰:‘出康军岷山’东流,至苏州许浦入海”。[16](P17)但问题是,这种认识递进并非实质性突围,丝毫不影响那个时代对长江观念或者长江文化“茫然态可及”价值判断持论,亦即完全可以断定那个时代的长江观念及长江文化想象空间,基本处于茫然和浑沌状态,因而也就意味着后继任何知识史位置,都不能以《诗》时代长江观念和长江文化作为无条件肯定的必然知识成果,至多只能作为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或然性当时见解,因而也就是混沌态可及的文化功能状态。对此,学理追诉的目的,不在于历史虚无主义的逆向否定,更在于价值坚守的科学精神与知识理性,而其效能则不仅能穿越时间通道,从而实现对真实的《诗》时代及其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坦然回眸,而且可以规避由此及后人们以无条件肯定命题和大词虚构。在价值论维度,历史虚构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负面等值。
《史记》一句“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21](P227)禹疏九江之事被想像成比江、汉之域王化旧事重要得多的长江文化衍生事态,可见太史公所阅读到的《诗》时代长江文化叙事资料少之又少。《汉书》所谓“自此之后……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53](P747)这个“之后”,其实不仅远禹时代久矣,而且远《诗》时代亦久矣,大抵汉时所治之地形地貌实际结构状态。其实《地理志》议及的“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汜。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21](P744)虽是基于汉时位置自远古至近前地理风俗一锅煮,但其中显然隐存着诸多《诗》时代的文化消息,而个别消息则间接透露着处于《诗》时代早期的楚之初,相较中原,乃边缘地带无疑,吴则更盛,至于巴、蜀及江源顺流而下广大区域,那都是边缘之外的氏族部落与风土人情。至于《山海经》描述的诸如“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54](P298)或者考古资料确证巴族进入青铜时代的所谓“该遗址的时代下限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55](P417)抑或《诗》时代区域文化自衍的“杜宇氏蜀国的时间大概在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先后发现的遗存有:新繁水观音遗址;广汉月亮湾遗址;彭州市从瓦街两处西周青铜器窖藏;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成都青羊宫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指挥街遗址的部分遗存和金沙遗址等”[56](P230),诸如此类,尽皆长江流域各文化板块于《诗》时代尽在边缘化范围“之内”或者“之外”历史还原。这一还原意义在于,无论商周以前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板块与其它中原区域文化板块究竟发生过多少种类的文化移动关系,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商末至春秋前期,周王朝由崛起而衰落的整个《诗》时代,长江观念和长江文化都是边缘化的存在状态,有些板块甚至是基本丧失生存价值关联的化外之地,所以至多只能具有边缘化可及的在场文化功能。
《诗地理考》谓“作《诗》者在江、汉合流之处”,[16](P18)此与郑樵持论的“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57](P865)高度一致,朱熹详述的“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系于天子也”,[10](P1)虽与前二者定位有所不同,但《诗》缘起于二南并且总体而言意义生成于江、汉之间广阔南土的持论,其同质性远大于异质性。如果将诸如此类的意义生成定位,越千古而价值链接于孔子笃信不疑的“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立也与”[58](P690),其实就引申出一个重大的文化发生学事态,那就是不仅《诗》的历史起点由文王起事于商末的“勉勉我王,纲纪四方”[5](P557)始,而且确指定位于“由北而南”的江、汉地域之间。由此所引领性日常生存伦理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不及物诗化功能形式,在走向“率尔天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目标进程中,渐延渐展地覆盖其基于常识社会学与道德形而上学所指内涵教化隐存其中的“价值体系”,及其在整个“王土”之上以《诗》的方式抵达“暗藏在每种语言中的内涵系统内在于每个语言——文化共同体”。[59](P95)这一重要发生学事态的延伸意义在于,《诗》时代的长江观念和长江文化,由此就在大规模时空悬置的客观状态中,聚焦于江、汉之域或曰南国之地,而且这种转换直接导致率尔天下都将以此对长江和长江文化给予想像性观念定性,进而也就意味着整个《诗》时代任何涉事个体对长江和长江文化的可及,说到底不过是区域性可及,而流域性的文化可及则显然是其后历史演进的持续建构产物。此议长期屈抑于忽视的学理危机在于,一方面会失去所谓“变风”、“变雅”之前对意义生成地域发生因缘的深度追问兴趣,另一方面,则会使得江、汉之域意义生成,在长江文化流域性存在与历史性变迁中的得风气之先凸显价值地位丧失殆尽,此外还会因这种丧失而导致共时性对历时性抑或价值平面对价值层级等生存复杂性的当代遮蔽。就这一议题而言,无论历史地理学、时间地理学、时段地理学,还是空间历史学、区位历史学以及文化发生学的知识介入,都将会在不期然而然中获得与传统《诗》解大相径庭的脱颖成果,因为这种知识介入方式已然“为当代研究提供了共享的问题与专题”,[60](P37)而这与哈特向所谓“过去30余年间,地理学的发展以对区域地理学兴趣日增为特点”,[61](P545)至少在核心问题凸显与关联问题域扩容等方面会带来较大进展。无论将有何种进展,但此时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诗》时代的“长江文化”,说到底是地域可及的江汉之间区域文化。
如上三种“可及性”讨论的价值在于,尽可能规避人们在还原和提及特定历史时空意义生成之际,往往容易在放弃边际条件下随意将其陈述为无限可及的普遍事态,因而就会在那些边际条件非限定言说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亦如当下不乏对长江文化甚至长江文化精神,无条件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纲纪之所在的大词口号肆意滥呼。这种滥呼既不符合民族精神意识史事实,更会使本来具有的不朽价值有意无意中趋于消解,其知识恶果将类似于恩格斯否定杜林所直言的“一句话:最初为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费’,而后来的‘成果’却等于零”。[13](P642)
余论
立足当下,回眸历史,谋划未来,我们实际上面临两个既交叉又分异的现实问题:其一,在长江文化命题的集合态历史演进和价值积淀中,真实还原所要保护和传承对象的存在状态与发生真相。其二,在长江文化命题的聚焦态资源整合与靶向开发中,理性思考所要开发和实现目标的可能途径与可行方案。前者属于存在论知识范畴,后者属于生存论知识范畴,但归根结底又都在本体论界面统辖于自然长江与人文长江,并且关键在于统辖于传统基础上,有效完成两个命题间的功能嵌位关系、逻辑转换关系和互驱指向关系,否则就会实际层面乃至具体操作界面一地鸡毛。解决这些问题乃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神圣而且浩大工程,惟其神圣,任何涉身者都无权利夹其一己之私而有些丝知识亵渎,惟其浩大,则容不得每一位献身者在忠诚、理性和慎之又慎等一系列缺失中言之谵妄或行之鲁莽,哪怕这一切尚处未实际操作进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