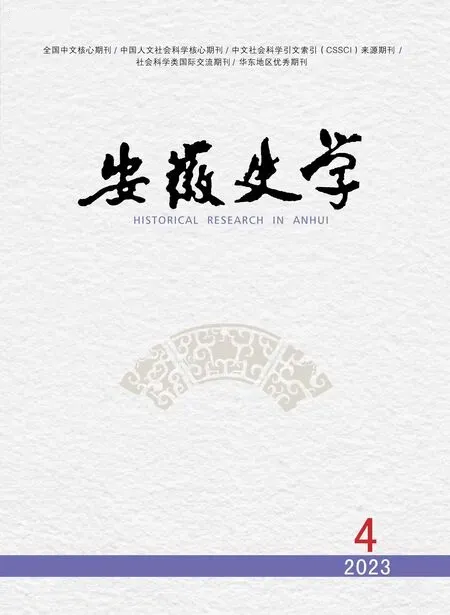论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派史的书写
2023-12-25戚学民唐铭鸿
戚学民 唐铭鸿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历来记载桐城派史的官私著作较多。(1)清代的观点,私家以曾国藩、王先谦等人为代表,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亦对桐城一地的学派先贤有所记载;官方以国史《文苑传》为主。近代以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等书亦极为重要。20世纪“文学史”学科诞生以来,学界对桐城派史的研究丰富多彩,桐城派的脉络发展、文艺理论、学术特质、作品成就等本体层面的成果颇为丰硕。近年来对桐城派史的学术史研讨独树一帜。(2)典型的研究,如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桐城派相关研究可参见综述类文章,如江小角、方宁胜:《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顾》,《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张晨怡、曾光光:《桐城派研究学术史回顾》,《船山学刊》2006年第1期。诸种文学史大多肯定桐城派在清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其中,如郭绍虞认为桐城派系清代唯一最大古文流派的观点,对学界影响甚重。相对于本体层面的桐城派文人和作品的研究,在历史认知层面对各种桐城派史的讨论尚有待发之覆。
在各种桐城派史之中,清廷官方代表的清史《文苑传》的记载有独特价值。在清史《文苑传》的多个稿本中,有系统的古文史记载,桐城派史一直是其中记载重点。笔者曾略论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钦定国史文苑传》和第四次稿《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记载。(3)戚学民:《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戚学民、唐铭鸿:《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温馨:《陈用光与清国史馆〈文苑传〉中桐城派谱系考》,《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桐城学人陈用光在国史馆期间建构桐城派之古文正统地位,为后来的修史工作奠定基础。而清史《文苑传》其他档案对桐城派史的记载内容鸿富,值得进一步研讨。
清史《文苑传》的桐城派史记载有一个特色,即嘉道时期和民国清史馆时期,均有桐城派传人参与纂修。清史《文苑传》的桐城派史较之私人著述有正史的权威,桐城派人在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参与纂修使得其中的桐城派史更加厚重。桐城后学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对《清史稿》整体成书的贡献,学界曾有讨论。(4)目前,学界对清史馆内桐城学人的研究重点在行谊、交游等事实层面,对于有关桐城派建构的工作重视不足。许曾会关注到马其昶《文苑传》、姚永朴《食货志》、姚永概“诸名臣传”等编修方面的成就,张秀玉则对姚永概《清史拟稿》做过详尽分析。上述研究均未提及姚永朴撰《文苑列传》稿本,亦未能对马其昶的论述具体展开分析,未免可惜。参见许曾会:《桐城派与〈清史稿〉的编修》,《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张秀玉:《姚永概〈清史拟稿〉考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张秀玉:《清末民初桐城派士人的“倔强坚守”——以客居北京的桐城籍作家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4期。清史馆中桐城学人对桐城派史的书写规模更大,学界尚无深入研究。具体到姚永朴对清史《文苑传》中桐城派史的撰述之功,更不为人知。姚氏曾纂成《文苑列传》,涉及对桐城派史的书写,但其成果长期以档册形式保存在清史馆档案全宗之中。本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姚永朴拟清史《文苑列传》稿本档案为中心,讨论他对桐城派史的书写。
一、姚永朴与清史《文苑列传》
姚永朴,字仲实,安徽桐城人,姚莹之孙,曾师事同乡方宗诚、吴汝纶,对近代教育事业为功甚巨,所撰《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等书影响重大,与姻兄马其昶、弟姚永概均为清末民初桐城派代表人物。马其昶和姚氏兄弟是民国初年知名桐城学人。姚氏兄弟为“姚门四杰”之一姚莹之孙,马其昶之夫人姚氏为二人之姊,姚永朴则迎娶马其昶之妹,桑梓情谊与姻亲联结,使得三人关系紧密。姚永朴于1914年至1922年期间在清史馆任职八年,由协修升至纂修,担任列传、《食货志》纂修工作,《清史稿·食货志》中《盐法》《户口》《仓库》《茶法》等为其所撰。但是他对清史《文苑传》的纂修亦有贡献,涉及桐城派史的书写,却不为人知。
如前所述,桐城学人对《清史稿》成书的贡献,学界已经有所考察,但是他们具体纂修工作有待深入讨论。姚永朴曾对清史《文苑传》的桐城派史记载有贡献,但当事人回忆未及此点。如曾师承姚永朴、马其昶的李诚记述,“帮助马通伯撰写光绪、宣统两代列传的,有纂修姚永朴和邓邦述”。(5)李诚:《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江淮文史》2008年第6期,第79页。朱师辙也说姚永朴曾经编纂光宣两朝列传,却并未提及其纂修《文苑列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案全宗揭示了姚永朴在《文苑传》中的工作成果。台北故宫博物院馆文献编号701006315的《文苑传目》档册,记载了清史馆内诸纂修官的《文苑传》分工情况。据此,姚永朴曾为《文苑传》撰戴名世、方东树、梅曾亮、吴德旋、汤鹏、包世臣、冯桂芬、吴汝纶、方宗诚等9人传,并上呈史馆。
前述《文苑传目》中所载姚永朴所撰的9个传记,以题名《文苑列传》的四个档册存世。按照内容,实际上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多人传记汇稿本。这包括文献编号701006791朱丝栏抄本《文苑列传》,是戴名世、方东树、梅曾亮、吴德旋、汤鹏、包世臣、冯桂芬、吴汝纶8人传记汇稿。另外包括文献编号701006792的红格抄本、署名《文苑传》的档册,为戴名世、方东树、梅曾亮、吴德旋、包世臣、吴汝纶6人传记的清缮本。其二是《方宗诚传》档册。这体现在文献编号701006789的《文苑列传》朱丝栏抄本和文献编号701006790的《文苑传》红格抄本,两者均是《方宗诚传》单传。
姚永朴《文苑列传》未注明纂修工作的详细时间,但其撰著当在1914至1921年期间。按清史馆开馆后,缪荃孙担任总纂,总辑《儒林传》《文苑传》等。他曾到馆商议具体纂修事宜,在京逗留约一月(6)《缪荃孙全集·日记三》,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347,345,443页。,与史馆同仁多有互动沟通,其间亦曾与姚永朴会面。(7)《缪荃孙全集·日记三》,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347,345,443页。之后,缪荃孙主要在沪办理《文苑传》等传记的纂修工作,并曾于1916年5月入京交五卷本初稿(8)《缪荃孙全集·日记三》,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347,345,443页。,后又于1918年7月交一卷补稿。(9)《缪荃孙全集·日记四》,第85页。马其昶则于1916年应馆长赵尔巽之聘,入馆任总纂,负责编纂《儒林传》《文苑传》。(10)陈祖壬:《桐城马先生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1921年,马其昶纂成《文苑传》。
姚永朴的《文苑列传》应形成于1916年进馆之后(缪荃孙已经在1915年呈缴了清史《文学传》),1921年《文苑传》成稿之前。两种不同《方宗诚传》档册封面上有“协修姚永朴”字样,根据章钰、张尔田等人回忆,在1916年马其昶添聘入史馆前,姚永朴仍为协修,而在朱师辙的回忆记载中,姚永朴最终升至纂修。(11)笔者按,马其昶在名录中被列为“后来添聘者”,显然章钰手书此名单在其被聘之前,故有此推断。参见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40页。此具体升迁时间不可考,但可以确定,至《方宗诚传》编纂之时,姚永朴仍任协修。此条可以作为《文苑列传》成稿时间的佐证。
清史馆曾经有对清朝时已经立传者另起炉灶的计划,留存至今的清史馆档册中有多种重辑的人物传记。《文苑传目》及姚永朴《文苑列传》显示,史馆对缪荃孙撰《文学传》(清史《文苑传》第六次稿)也有所不满,组织了重纂。赵尔巽对缪荃孙所纂《儒学传》《文学传》稿本曾有评价:“所惜为传四十,而重者乃至廿人之多,未免空费日力。若如鄙见,先将欲纂之人见示,则无此弊矣。以后仍望先行抄示,馆中已纂者即当另录副呈阅。(择要可,全录亦难。)其文字之纠正,篇幅之分合,听公择定,并祈转告絅斋,取一致之行动为要。”(12)钱伯城、郭群一整理:《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据赵尔巽意见,缪荃孙抄示的四十个传记中,竟有二十个传与清史馆存稿重复,比例相当高。清史馆因时代动荡,常为人手不足、经费有限而苦恼,再有重复工作,降低了效率。赵尔巽提议将已纂之人整理录副,是提高撰修工作效率的必要之举。
清史馆对缪荃孙呈缴的《文学传》有意见,这是马其昶任总纂,纂成清史《儒林传》《文苑传》第七次稿的的原因。《文苑传》第七次稿的具体情况容本人另文研究。本文仅指出,这次重纂原有的构想可能规模较大,包括新增和重撰某些人物的传记。姚永朴《文苑列传》当奉史馆总裁或总纂之命而作,是这次重纂的过程稿之一。姚氏《文苑列传》多位正传均为桐城派中人,其中的戴名世、方东树、梅曾亮、吴德旋、吴汝纶、方宗诚更是今日桐城派史研究中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因为馆务的变动,姚氏《文苑列传》仅一位被采用,其余传稿成为档案史料。
二、《文苑列传·戴名世传》与早期桐城派史记载
姚永朴撰《文苑列传》虽然只有9位正传人物,但多个传记涉及桐城派史的某些重要问题,是桐城派史的重要史料。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姚永朴首次为戴名世立正传,客观上把清史《文苑传》桐城派史向前伸展到清初。《文苑列传·戴名世传》是戴氏首次在清史《文苑传》中立传。桐城派在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纂修时即被载入(13)戚学民:《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但戴名世因政治问题并未在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获得立传。按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纂修工作中,因政治问题未能立传人物不止戴名世一人,其他如钱谦益、屈大均、魏禧等明末清初重要文士也是同样遭遇。
姚永朴纂《戴名世传》参考了方苞《南山集序》与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主要遵循了马其昶既有传记的思路,但文字内容有删减。《戴名世传》在列述了传主生平行谊后,主要记载了他的古文及史学成就,收录其《答余生书》的大段原文。姚永朴记载了戴氏获罪经历及结果,称其“夙负文誉,既构祸,遂无有道其为人者,或及之,辄隐其名”。(14)姚永朴:《文苑列传·戴名世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6791,第2、1、1页。本文档案皆为台北故宫博物馆藏,下不再标藏地。戴名世出身桐城,与方苞往来密切,其学“长于史” 且“天下又翕然称其古文”。(15)姚永朴:《文苑列传·戴名世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6791,第2、1、1页。本文档案皆为台北故宫博物馆藏,下不再标藏地。
姚永朴强调戴名世的史学成就及古文成就。“其学长于史,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于是天下又翕然称其古文。”(16)姚永朴:《文苑列传·戴名世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6791,第2、1、1页。本文档案皆为台北故宫博物馆藏,下不再标藏地。这是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的表述。(17)马其昶:《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97页。而《桐城耆旧传》中记载戴名世负才自傲,“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18)马其昶:《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97页。,姚永朴并未引述。戴名世对方苞之言,见方苞《南山集序》与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姚永朴撰《戴名世传》标注将《南山集序》纳入,或许便与这句话相关。《戴名世传》主要参考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兼及方苞《南山集序》。
姚永朴并未将戴名世纳入桐城派的脉络中加以描述,全篇除了提及方苞外,未涉及刘大櫆、姚鼐,而是将戴名世视作籍贯桐城的一位独立学人而表述。显然,姚永朴没有以戴名世为“桐城之祖”,此点可供学界参考。按学界对戴名世的生平经历、文集版本,以及“南山案”始末等事实的考证等研究较多,研究重点在于戴名世是否是桐城派一员,或戴氏与桐城派的关系等。民国以来,梁启超、柳亚子、章太炎、陈石遗、吴孟复、刘声木等人均视戴名世为桐城派成员。然近年亦有学者提出异议,如王达敏认为姚鼐对桐城派的建构是桐城立派的关键,而戴名世并不位于这一体系中。
姚永朴《戴名世传》对传主学问成就的评价,似乎低于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的说法。按马其昶评:“(戴名世)先生生平酷慕司马子长之文,每引以自况。”(19)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297页。随后载录《孑遗录》中《答余生书》的内容。姚永朴则未将戴名世与司马迁相对比,也并未记录戴名世以司马迁自况之心。在正史传记中,将传主与过往文人名士相比拟以显示传主成就是典型做法。如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多用帝王评价来彰显作者水平。姚永朴没有采纳马氏对戴氏之文的评价,显然别有看法。姚永朴《戴名世传》也并未采用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这一段话:“上尝问文贞:‘自汪霦死,谁能为古文者?’对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对,上亦不之罪也。”(20)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297页。此文贞为李光地。按,马其昶引此事,是为了展示戴名世之古文被康熙和李光地所肯定。姚不采纳马其昶对戴氏古文两处高度评价,可见微意。姚永朴在《戴名世传》最后加了一句:“名世死后,其遗稿为徒友所私写而存之者,今尚十余卷。”(21)姚永朴:《文苑列传·戴名世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5页。这与目前学界所知相符。姚氏也补充记载戴名世被化名为“宋潜虚”以留存文集的情形。
如前所述,姚永朴的《戴名世传》基本上脱胎于马其昶的《桐城耆旧传》,对一些具体表述有所删减。纵览各种《戴名世传》,在论述其史学成就时,都参考《答余生书》的内容,强调《孑遗录》的创作事实。或许这确是戴名世的成就重点,又或许这与他最终罹难息息相关——在这样的衬托下,戴名世的古文成就似乎没有那么“耀眼”了。但事实上,戴名世的古文的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马其昶、姚永朴将对其古文的记载放在史学之前,便是显证。且方苞为《南山集》作序,姚永朴又引用该序,也是对戴氏古文的推崇。
姚永朴为戴名世在清史《文苑传》立传,是将其作为古文和史学的代表。但姚氏笔下的戴名世并没有大书“桐城派”,全传中只是客观叙述了戴名世籍贯桐城的事实。尽管文字是引用自马其昶的《桐城耆旧传》,但是并没有强调戴名世与桐城派的联系。这种很克制的书写是正史和私家著述的差异。在桐城派立场上,当然对桐城派脉络说得越广越好,但正史记载必须严谨审慎。姚永朴任职清史馆,承命为桐城前辈戴名世立传,却不强说戴氏为桐城派,这种谦抑态度应被重视。
今日学界习知的《戴名世传》是刊行的《清史稿·文苑传》(卷484)中的《戴名世传》,该传底本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全宗中文献编号701007911无名列传汇稿本《戴名世列传》。(22)《戴名世列传》,文献编号:701007911,第191—194页。此一汇稿本未采用姚永朴的《戴名世传》,而是另起炉灶。后来付梓的《清史稿·文苑传》中《戴名世传》则在汇稿本的底本基础上进一步删改,记载更加简略。姚永朴本被放弃的原因,以及这后两个版本的《戴名世传》作者都待考。但无论如何,姚永朴的《戴名世传》是清史馆中第一个为戴氏撰写的传稿,将马其昶的私著上升为正史,客观上将桐城文人在正史《文苑传》的记载提前到清初。姚氏的《戴名世传》是戴氏和桐城派史的一则重要史料。
三、《文苑列传》与嘉道时期桐城派史的增改
姚永朴《文苑列传》中方东树、梅曾亮、吴德旋三篇传记是对嘉道时期桐城派史的增补与改写,是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点。姚鼐及其门人在桐城派发展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嘉道时期也是桐城派发展的重点。清国史馆和清史馆时期的桐城派史记载均强化姚鼐的地位。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姚鼐便已立正传,并经钦定成稿。《续文苑底稿》对姚鼐的传人有重点记载,梅曾亮、管同、姚莹等立正传。民初清史馆续纂《文苑传》,对清国史馆时期的传稿有因有革。姚永朴《文苑列传》重纂姚门弟子数人传记,显示了清史馆对桐城派史的重视,是正史系统中嘉道时期桐城派史的重要资料。
《文苑列传》中的《方东树传》极富意义。在清史《儒林传》与《文苑传》纂修过程中,因受汉宋之争的影响,方东树迟迟未获立传。缪荃孙曾引张之洞之言,“南皮师云,植之本属汉学,后自揣不能胜诸家,故反用之,以猎取名誉,为温饱计”(23)缪荃孙:《方东树仪卫堂集跋》,《缪荃孙全集·诗文一》,第220—221页。,对方东树颇为不满。光绪年间缪氏主持纂辑《儒林传》《文苑传》,均没有为方东树立传。特别是《续文苑底稿》(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底本),为多名姚鼐后学,特别是姚门四杰立传。“姚门四杰”的具体构成,姚莹、曾国藩、王先谦等诸家说法不一,但总不出姚莹、方东树、刘开、管同、梅曾亮五人。《续文苑底稿》中姚莹、管同、梅曾亮均有正传,刘开是附传,方东树传则阙如。
但方东树终于在陈伯陶主持纂辑清史《儒林传》中立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国史馆档案,《方东树传》位于七十三卷本《儒林传》中,系上卷第二十九,为新辑传记。该传记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分别为编号701003929、编号701005252、编号故殿033496。虽然版本不同,但传文内容相同。其中,701005252为成兴斋稿纸版本。此《方东树传》国史馆本传是陈伯陶主持纂修的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此次纂修的具体情况本人另文研究),时间已经到了清末。
《儒林传·方东树传》记载了方东树力宗程朱,反对汉学和阳明学的学术主张和作为。重点在以《汉学商兑》为核心的理学著述,将《汉学商兑》视为“海内竞尚考证”(24)《儒林传·方东树传》,文献编号:701003929,第16、20、15、19—20页。背景下为宋学张目之作,指出该书在当时获得学界强烈反响。有关方东树与“桐城派”之间的关系,本传记载与姚鼐的师承,也记载其引领了理学风气,“然桐城自东树后,学者多务理学云。”(25)《儒林传·方东树传》,文献编号:701003929,第16、20、15、19—20页。本传对传主古文有所提及,称其“学古文于同里姚鼐”(26)《儒林传·方东树传》,文献编号:701003929,第16、20、15、19—20页。,“古文简洁涵蓄不及鼐,能自开大以成一格”(27)《儒林传·方东树传》,文献编号:701003929,第16、20、15、19—20页。,但因为是《儒林传》,所以古文不是记载重点。清史馆时期,缪荃孙再度担任总纂,将方东树从《儒林传》移入《文学传》,降为姚鼐的附传。
姚永朴在《文苑列传》中将方东树从附传升为正传。姚氏《方东树传》依据国史馆《儒林传》同名传记、《安徽通志》、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纂成。《安徽通志·方东树传》内容极为简单,未出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和国史馆旧传的范围。但姚永朴《方东树传》记载重点发生了变化。其一,对方氏古文和诗歌的表述明显变多,这明显是依据《文苑传》内容,调整了记载重点。传文指出方东树师承姚鼐,博览群书,学问广博:“师事姚郎中鼐,泛览秦汉以来载籍,自诗文、训诂、义理,以逮浮屠、老子之说,无不综练。”(28)姚永朴:《文苑列传·方东树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7、8、9页。诗文成为方氏最主要的成就。
其二,姚永朴《方东树传》强化了传主文章坚持理学的特色。该文利用阮元汉学泰斗的身份,引用他晚年对方东树文学的称赞,来衬托其古文成就,“盖其义理一本程、朱,而考证之精、文辞之辨,又足以佐之。”(29)姚永朴:《文苑列传·方东树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7、8、9页。这也是《儒林传》方氏本传中没有的内容,是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的写法。
其三,也是最值得重视的,姚永朴在《方东树传》中写了一条桐城传承脉络,而这在国史馆的《儒林传·方东树传》、《安徽通志》和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均没有。姚永朴挑明了方东树师承姚鼐,这不见于《儒林传·方东树传》,而引自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另姚氏将方宗诚、戴钧衡、苏惇元纳入附传,称“桐城自姚鼐后,东树为耆宿,门下知名者曰方宗诚、戴钧衡、苏惇元。”(30)姚永朴:《文苑列传·方东树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7、8、9页。在清史《文苑传》中,方东树被提升为姚鼐的重要传人,再度开枝散叶,有壮大桐城派之功。
总体而言,姚永朴的《方东树传》更多地参考了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的内容,基本上与马氏说法一脉相承,首次将姚鼐与方东树间的师承关系写入了正史,并强调方东树是姚鼐的重要传人。《方东树传》无疑在《文苑传》中增强了桐城派的厚度。
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梅曾亮传》和《管同传》的重撰亦值得重视。梅氏和管氏作为“姚门四杰”,是桐城派史研究的重点。梅曾亮有将桐城派在京师发扬光大的重要作用,为学界重视。(31)如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一书,专章论述了梅曾亮与桐城派古文在京师传播的关系,同时分析了梅曾亮与桐城派在岭西的发展。梅曾亮和管同均在《续文苑底稿》中立为正传。姚永朴《梅曾亮传》中的双行夹注记载显示,该文系根据国史馆本传和梅曾亮《书管异之文集后》撰成。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中,缪荃孙纂有《梅曾亮传》(附毛岳生)和《管同传》(附子管嗣复、刘开)。《清史列传》根据的七十四卷本中亦有《梅曾亮传》,管同和毛岳生为附传。缪荃孙纂成的《续文苑底稿》中的《梅曾亮传》和《管同传》被沿用,七十四卷本《文苑传》同名传记与其区别不大。《续文苑底稿·梅曾亮传》内容出自《正雅集》《江宁府志》《朱琦柏枧山房文集书后》《屺云楼诗话》《柏枧山房文集》《国朝先正事略》。《管同传》内容出自《续江宁府志·文苑传》和《因寄轩文集》。
姚永朴《梅曾亮传》记载和前述国史馆同名传记有明显区别。(32)姚永朴:《文苑列传·梅曾亮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11—14、11—12、11—12页。第一,国史馆时期的《梅曾亮传》和《管同传》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大篇幅地引用二人著作中的原文——梅曾亮的《民论》《臣事论》《上汪志伊书》和《刑论》,管同的《言风俗书》和《筹积贮书》。这虽为《史》《汉》书法,但在清史《文苑传》显得特别。然而,姚永朴的《梅曾亮传》写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梅曾亮《民论》等文章的引用变少,把更多的篇幅放在了具体的文法理论的表述、讨论和评价上。这样的书写方式的改变,使得传记整体性、连贯性更强。这与缪荃孙《文学传》和后来《清史稿·文苑传》的同名传记写法均不同。
第二,管同被降为附传。姚永朴将管同作为《梅曾亮传》的附传,大大增加了管同和梅曾亮之间的互动。这从对梅曾亮《书管异之文集后》的引用中可以直接体现。梅曾亮和管同合传,且传中仅有此二人,是《文苑传》体系中独特的写法。其余版本,皆以梅曾亮与毛岳生合传,或梅曾亮、管同、毛岳生三人合传等。
第三,传主古文成就,增加了管同如何劝说梅曾亮从事古文创作的经过,彰显了桐城派为古文的思路和审美取向,并有对骈体文的批评。这些内容,是从《书管异之文集后》引用(按,《书管异之文集后》几乎全篇被姚永朴引用)。
缪荃孙对此写法是:“(梅曾亮)少时文喜骈俪,既游姚鼐门,与管同友善。同辄规之,始颇持所业相抗,已乃一变为古文词。义法一本桐城,稍参以归太仆。”(33)缪荃孙:《梅曾亮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第25页。姚永朴改写为:“(梅曾亮)少好骈体文,与同邑管同友,同语之曰:‘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曾亮曰:‘诚有是,然《哀江南赋》《报杨遵彦书》,其意固不快耶?而贱之也。’同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庄、周、司马迁之意,来如云兴,聚如车屯,则虽百庾、徐之词,不足以尽其一意。’曾亮遂稍稍学古文辞。同不尽谓善,曰:‘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驳见。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34)姚永朴:《文苑列传·梅曾亮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11—14、11—12、11—12页。
第四,对梅曾亮的学术史定位不同。姚永朴对梅曾亮京师经历及从姚鼐游的表述与前人不同,把梅氏塑造成了“姚鼐传人”,俨然是京师文坛核心。缪氏记载是:“(梅曾亮)居京师二十余年,笃老嗜学,与宗稷辰、朱琦、龙启瑞、王拯辈游处,咸啧啧称赏其才。一时碑版记叙,率其手笔。”(35)缪荃孙:《梅曾亮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第25页。姚永朴《梅曾亮传》则载:“会桐城姚鼐主讲钟山书院,因游其门。及官京师,复交会稽宗稷辰、临桂朱琦、龙启瑞、马平王拯。久之文乃深古雅洁,群推为姚氏后劲。有求古文法者,辄相诏曰,盍谒梅郎中?然曾亮于少年不徒导以文事,每接见,必以择交游、端言行、勤读书三者为戒。时宦官有欲纳交文士者,慕曾亮名,就门请谒,曾亮笑曰:吾岂学康对山哉!卒谢之。”(36)姚永朴:《文苑列传·梅曾亮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11—14、11—12、11—12页。“久之”以后的话在国史馆本传和《书管异之文集后》中都没有,是姚永朴新增。
《管同传》在《续文苑底稿》中有为桐城派立派的重要作用。然而,姚永朴《文苑列传》《管同传》并没为桐城派立派,只记载了管同从姚鼐学的事实和陈用光对他的提拔。
总体而言,在姚永朴的笔下,梅曾亮被塑造为了姚鼐之后的重要传人,是“姚氏后劲”,是桐城派在京师的核心,有着关键的学术史地位。而管同和梅曾亮一样,都是姚鼐后一辈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姚永朴的《梅曾亮传》中,未像缪荃孙《续文苑底稿》一样明言“桐城派”,但却处处展示着桐城派的学派脉络和古文家法。姚永朴撰《方东树传》和《梅曾亮传》都记载了姚鼐后学的传承。尽管重撰《方东树传》和《梅曾亮传》没有被后来的《清史稿·文苑传》采用,但仍然是记载嘉道时期桐城派史的重要文献。
四、《吴汝纶传》与晚清桐城派史的书写
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后期传人吴汝纶(其附传人物张裕钊、范当世、朱铭盘、贺涛)的记载更加重要。这一组人物均为晚清桐城后学,清史《文苑传》此前的稿本《续文苑底稿》等成形于光绪年间,下限是咸同时期,对在世的吴汝纶等人无法立传。清史馆时期,已经有条件对清史进行通盘考察。就桐城派史而言,清末去世的吴汝纶等人有必要写入。但是吴汝纶等人是否在清史《文苑传》中立传,史馆诸人意见不统一。姚永朴《文苑列传》的《吴汝纶传》反映了清史馆内部对此争论的一个处理方式。
今日学界对吴汝纶的研究,除了关注吴氏文学观念、文学活动、学术成就、与桐城派末期古文的关系外,对其教育活动,以及晚清中日之间近代教育交流的关系非常重视。除了吴氏现实活动,其身后形象的书写本身也是晚期桐城派史的一个事件,而学界尚无讨论。(37)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受到重视,包括他在莲池书院及京师大学堂中的活动、赴日考察的经历,以及对西学的态度等。同时,作为二十世纪初文学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相关研究亦很丰富。此外,吴汝纶与严复、林纾等人的关系也受到关注。
姚永朴撰《吴汝纶传》载:吴氏与张裕钊同出曾国藩门下(38)姚永朴:《文苑列传·吴汝纶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页。,并在政治上承其照拂,多任学堂教育事业,吴汝纶亦得李鸿章提携。清末民初西学输入的背景下,吴汝纶的态度颇为开明,他一方面饱读经史,固守古文根基,“汝纶好文出天性,凡周秦(原文泰,误,引者注)古籍,太史公、杨、班、韩、柳,以逮近世姚、曾诸家书,丹黄不去手。其治经,由训诂以求通文辞。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我国所独优。”(39)姚永朴:《文苑列传·吴汝纶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页。又积极研习西方新学术。“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40)姚永朴:《文苑列传·吴汝纶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页。,强调对西方博物格致之学的吸纳,并曾赴日本考察学制。在姚永朴笔下,吴汝纶不仅是一位思想并不拘泥的传统学人,在中西交往的过程中,其同样受到西方好尚文学者的礼遇与追捧,“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踔海来请业”(41)姚永朴:《文苑列传·吴汝纶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页。,“其国自君相及教育名家皆备礼接欵,求请题咏,更番踵至”(42)姚永朴:《文苑列传·吴汝纶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页。,可见吴汝纶及桐城派在文章上的造诣蜚声海外。整个传记,凸显出了清末数千年未有的变局下,西学东渐,桐城派代表人物对西方思想的积极接纳。而吴汝纶的同门张裕钊虽未曾出洋,但在国内亦谨守桐城义法,加以教育传播,“中岁后主讲江宁、河北、直隶、陕西各书院,成就后学甚众,尝言学文不从桐城诸先辈绪言入,终难免庞杂叫嚣之习”(43)姚永朴:《文苑列传·张裕钊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7、36、36页。,对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多有归纳传播,且影响深远,“世以为知言”。(44)姚永朴:《文苑列传·张裕钊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7、36、36页。知新与守本,均是桐城派的特色。
姚永朴《吴汝纶传》系根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姚永概所撰《行状》纂写;张裕钊以下诸人事据《濂亭集》、吴汝纶《文集》《尺牍》纂成。该传的附传人物为张裕钊、范当世、朱铭盘、贺涛,附传人物的组合安排是独特的。多个《吴汝纶传》稿本中,马其昶、缪荃孙拟的附传人物是萧穆,《清史稿》最终的版本则是萧穆、贺涛、刘孚京。
在描述吴汝纶和附传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姚永朴用了如下表述,这是他的创新:“初汝纶与张裕钊皆从曾国藩游,以文学相友善。裕钊门下最知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汝纶门下最知名者有贺涛。”(45)姚永朴:《文苑列传·张裕钊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7、36、36页。这句话显示了姚永朴设计这个传记的思路,以及这个传记内部的人际逻辑,这是与马其昶、缪荃孙等人不同的。总的来说,《吴汝纶传》是将吴汝纶、张裕钊作为曾国藩门生记载,同时又集中收入了他们的传人。《张裕钊传》载:“尝言学文不从桐城诸先辈绪言入,终难免庞杂叫嚣之习。”(46)姚永朴:《文苑列传·张裕钊传》,文献编号:701006791,第36、37、36、36页。强调了对桐城文法传承的重要性。同时收录了张裕钊论作文的一些观点,其中如“因声求气”等,都是对刘大櫆等人的传承。
在吴汝纶身后的众多传状中,姚永朴引述了姚永概所撰者,不仅因为二人兄弟亲缘且共同师承吴汝纶,更因为姚永概所拟本来就是为了国史采择而写:“谨就闿生所述,参以见闻,稍加撰次,以待名公卿上闻,付史馆垂编录。谨状。”(47)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吴汝纶全集》卷4,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147页。目前《吴汝纶全集》中收录的传状有: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贺涛《吴先生行状》、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贺涛《吴先生墓表》、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吴闿生《先府君哀状》《先府君事略》、李刚己等《祭桐城先生文》、谷钟秀《祭桐城先生文》、早川新次《在安庆寄邦人书》。序跋则有贺涛《桐城吴先生经说序》、籍忠寅《桐城吴先生日记序》、吴闿生《记先大夫尺牍后》、吴闿生《跋先大夫日记》。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的《吴汝纶传》是清史馆《吴汝纶传》的基础。清史馆时期,缪荃孙、李景濂、马其昶、姚永朴等人都曾纂辑过《吴汝纶传》。根据缪荃孙《文学传》的双行夹注可知,其《吴汝纶传》亦是根据马其昶的《桐城耆旧传》所修,正传传主吴汝纶,附传萧穆,在引用既有文本的基础上,自己新增了一句话,表明了人物组合的逻辑:“而汝纶通西学,萧穆通考据,在桐城为别调,在文学则为通材也。”(48)缪荃孙:《吴汝纶传》,《文学传》,上海图书馆藏本,无页码。
姚永朴的《吴汝纶传》的价值,在上述诸文中可见。按清史馆系统中共有四种《吴汝纶传》。版本一,1918年6月14日《大公报》载李景濂所撰《吴挚甫先生传(清史馆稿)》。该版本仅见于报刊之中,并未出现在正式的《文苑传》稿本内,且报纸中收录并不完全。这一传记,收录在了今日的《吴汝纶全集》中。
版本二,系缪荃孙《文学传》(清史《文苑传》第六次稿)中所收录的《吴汝纶传》。从双行夹注中可见,缪氏所用文字本诸于马其昶所撰《桐城耆旧传》。马氏《桐城耆旧传》撰成于光绪十二年,其中有吴挚父、萧敬孚二先生合传。(49)⑤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444—448、445页。逐字对比,缪氏《文苑传》第六次稿系对于《桐城耆旧传》文本的缩写,部分地方完整誊录,部分地方缩减内容,极少地方增添信息。《文苑传》第六次稿中,增加一句评判性的语句,在《桐城耆旧传》文本中未见:“桐城之文,名冠天下,悉研理学,摹声调以为古。而汝纶通西学,萧穆通考据,在桐城为别调,在文学则为通才也。”(50)缪荃孙:《吴汝纶传》,《文学传》,上海图书馆藏本,无页码。
版本三,即最为人熟知的《清史稿》中所收录之《吴汝纶传》。这一版本,在第八次稿中出现,在吴汝纶正传下,附传人物由仅有萧穆一人,扩充至萧穆、贺涛、刘孚京,其中萧穆、贺涛均与吴氏有学缘关系。版本三的文字,与版本二在语言组织等方面截然不同,应为纂修官(马其昶,抑或金梁,待考)弃前稿不用,重新纂辑而成。
版本四,为姚永朴所撰《吴汝纶列传》。姚永朴继缪荃孙之后重撰《吴汝纶列传》,对缪氏文做了修改。同时对马其昶同名传记的行文作了删改,精简内容,比如删去了吴汝纶自日本归国后在桐城县兴办教育的事迹,“桐城学风大起,自先生也。”(51)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444—448、445页。与之相对的,缪荃孙对吴汝纶兴办教育的事情比较重视。在对吴汝纶教育成就的评价上,这一写法的区别是值得重视的。
总之,姚永朴第一次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人物吴汝纶在清史《文苑传》中立传,是晚期桐城派史的一次重要书写。清史《文苑传》中的桐城派史下限由此被延展到清末。桐城派中人不仅能固守理学传统,坚持古文,更能在激变的时代中设法接纳西学,迎接新世。作为《文苑列传》的最后一位人物,意味深长。尽管姚永朴的《吴汝纶列传》最后未被《清史稿》采用,但它是正史系统内的《吴汝纶传》之一,对晚期桐城派史的记载仍然值得注意。
结 语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对桐城派的记载是清代古文史的重要内容。在多种桐城派史之中,清史《文苑传》的记载相当重要。在历时百年的清史《文苑传》纂修历程所形成的多个过程稿中有系统的古文史记载,而桐城派史记载居于主导地位。本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相关档册为基础,讨论民国初年清史《文苑传》纂修过程中,姚永朴对桐城派史的纂述之功。
清史馆档案中存有姚永朴纂《文苑列传》4个档册,其中有多位桐城派人物,涉及对桐城派史书写的多个方面。姚永朴在清史《文苑传》中为戴名世立正传,把正史内的桐城派史向前延伸到清初。姚永朴又重纂了方东树传和梅曾亮传,对到清史《文苑传》第六次稿为止的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史进行了重写。姚永朴为吴汝纶新立传,把《文苑传》中的桐城派史拉长到清末。姚永朴在清史《文苑传》中书写的桐城派面貌,再次强调了桐城派在清代古文界的正统地位。尽管姚永朴《文苑列传》的9个正传,最后只有《沈桂芬传》《汤鹏传》被收入汇稿的《清史稿·文苑传》中。但是他关于桐城人物的传记保留至今,仍然是桐城派史珍贵资料。
清史《文苑传》中的桐城派史书写有一个特色,即桐城派中人深度参与,以桐城人说桐城文。姚永朴继陈用光之后,延续了桐城士人在清史《文苑传》中纂写桐城叙事的传统。就本文所论《文苑列传》而言,姚永朴本就是桐城派中人。他拟的《文苑列传》有多位桐城派传人,而其文献多参考马其昶为表彰记载乡里先贤所撰写的《桐城耆旧传》。马其昶对桐城诸人的记载和评价,对于姚永朴的纂修有重要影响。除《桐城耆旧传》外,姚永朴在纂修工作中亦多方引用桐城人士所撰之传状志铭等文本,如方苞为戴名世所撰《南山集序》、梅曾亮《书管异之文集后》、姚鼐《惜抱轩文集》、陈用光《太乙舟文集》等。姚永朴所引用的大多数的论述均出自桐城派人士,或者桐城派圈子。桐城文的纂述小传统经桐城人之手,深度渗入到正史撰述中,强化了正史中桐城派记载。
姚永朴《文苑列传》反映了桐城派史的丰厚内蕴,本文仅仅在文献层面考察其桐城派史记载的部分问题,更多的意蕴尚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