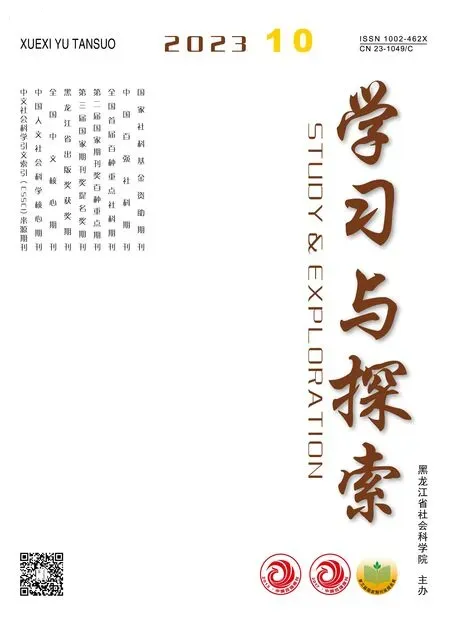《梅苑》词的入世主题与宋代文人的政治理想
2023-12-23凌念懿
凌 念 懿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咏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常见题材。咏梅文学的主题,大多或是赞美梅花的清高孤傲,凌寒独放,不媚世俗,或是称颂梅花的清雅高洁,幽深淡远。从咏物词的比兴传统来看,人格化的梅花或是孤傲不屈的忠贞傲骨之士的寄托,或是喻闲云野鹤般的隐逸高士比拟。《梅苑》是两宋之交黄大舆所编选的一部专题收录咏梅词的词选,共收录宋代咏梅词四百多首,以佚名词作为主。虽然学界向来不乏对于宋代词选或是咏梅文学的关注,但是对于《梅苑》深入细致的研究却十分有限。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梅苑》之中出现了咏梅文学史上极为少见,学界也几乎从未论及的积极入世的梅花形象。虽然这一类梅词在《梅苑》之中只占20%左右,也并未成为咏梅传统中的经典的、具有范式意义的梅花形象,但这种胸怀用世之志的梅花却实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声,因此也十分值得探究。
一、蕴藉悠远的“和羹之志”
《梅苑》梅词对于用世之志的抒发,最直接的莫过于对梅子可作“和羹”的直接赞美。“和羹”即一种配以不同调味品而制成的汤羹。梅与和羹的结合,最早的来源为《尚书》,《说命》篇云:“若作酒醴,尔惟曲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孔安国传云:“盐咸梅醋,羹需咸醋以和之。”[1]374此处所说的“梅”,显然是有酸味的梅子。《说命》一篇所讲的,乃是商王武丁向在野之贤士傅说请益治国之道并委以重任之事。《说命》中又云:“酒醴须曲糵以成,亦言我须汝以成。”[1]374“曲糵”在文中有辅佐君王之意,与之相对应的盐梅应当也有同样的内涵。在后世文学史之中,“盐梅”以及“和羹”一同,已经常常作为治国用世的意义出现了。如《贞观政要》:“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2]59杜甫《昔游》中有诗句:“吕尚封国邑,傅说已盐梅”[3]565,《立秋日雨院中有作》中又云:“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3]462宋代以前,“盐梅”“和羹”“调鼎”等意象只是零星出现在一些诗歌中喻治国贤士,很少见于咏梅文学之中。但在《梅苑》中,词人将“盐梅”中原本指梅子的“梅”化用在吟咏梅花的词作中。梅花是用以“和羹”的梅子生命的前奏,而梅子是梅花“和羹”之愿的延续,词人将梅花与梅子的概念一以贯之,“和羹”及其相关意象才在咏梅词集中出现,并与梅花形象得到了充分的结合。
双头莲
佚名(1)因《梅苑》中选词大部分是无名氏之作,而表达出用世之意的梅词又几乎尽数出自无名氏笔下,本文中未标明作者的《梅苑》引词则默认为无名氏所作,不复赘述。
触目庭台,当岁晚凋残,恁时方见。琼英细蕊,似美玉碾就,轻冰裁翦。暗想蜂蝶不知,有清香为援。深疑是,傅粉酡颜,何殊寿阳妆面。 惟恐易落难留,仗何人巧把,名词褒羡。狂风横雨,枉坠落、细蕊纷纷千片。异日结实成阴,托称殊非浅。调鼎鼐,试作和羹,佳名方显[4]223。
梅花生于冷落之地,虽高洁美丽,却无人欣赏。词人为梅花所忧虑的却不仅是细蕊遭受雨打风吹,更是花落难寻,佳名不显,直至凋零也不得遇欣赏者。然而词人在末句却笔锋一转,虽然眼下清冷困苦,但是等到他日梅树结果成荫,调和鼎鼐的时候,方是其用得其所,价值得以真正实现之时。梅花盛开时的生命是灰暗的,凄苦的,而只有梅花长出果实之后方能慰藉当下的不幸。这种情感内涵是一般咏梅词很少出现的。相类似的表述还有《万年欢》中的“终须待、结实和羹,恁时佳味堪尝”[4]232;又一首《万年欢》中“且留取、累累成实。终须待、金鼎调羹,偏与群芳春色”[4]232;《喜迁莺》中“望林止渴功就,不数夭桃繁杏。岁寒意,看结成秀子,归调商鼎”[4]218;“成实后,有调和鼎鼐,一般滋味”[4]219;《满庭霜》中“堪调鼎,蒙蒙烟雨,滋养待和羹”[4]220;《捣练子》“叶底青青如豆小,已知金鼎待和羹”[4]239等等。词中对于梅花的清雅高洁虽然也有关注,但是生于苦寒天气、荒凉环境中的梅花在词人看来因不能得到欣赏呈现一种寂寞痛苦的状态,而梅花的生命意义便寄托到了有丰富和羹意味的梅子。在原本是吟咏梅花的作品中,将歌颂的重心转移到花落后所结的梅子上,而非梅花本身,这是《梅苑》中表达入世之志词作的一个突出特点。《绿头鸭》[4]211中亦有这样的书写:
敛同云。破腊雪霁前村。占阳和、孤根先暖,数枝已报新春。如青女、谩同素质,笑姑射、难并天真。疏影横斜,澄波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驿畔,行人立马,回首几销魂。 江南远,陇使趁程,踏尽冰痕。 有个人人。玉肌偏似,移我索对金尊。捻纤枝、鬓边斜戴,嗅芳蕊、眉晕潜分。素脸笼霞,香心喷日,寿阳妆罢酒初醒。待调鼎,须贪结子,忍见落纷纷。宿天晓,愁闻画角,声断谯门。
梅花渴望“移我索对金尊”,脱离当下的凄冷苦寒之地,更是期待自己花落之后能够多结梅子,以实现和羹之志。“忍见落纷纷”看似是咏花词中常见的对于落花的惋惜,这在咏花诗词中十分常见,却因前一句“须贪结子”有了别样的内涵:对于花的怜惜,实际却是对于有和羹之用的梅子的爱惜。《满庭霜》中“莫放高楼弄笛,忍教看、雪落纷纷。堪调鼎,蒙蒙烟雨,滋养待和羹”[4]220;《南乡子》中“月里何人横玉笛,休吹。正是芳梢着子时”[4]255等词句,都是对于梅子的珍惜的体现。同时,对于花的爱惜也延伸到对于枝条的爱惜上,如《罥马索》中“懊恨春来何晚,伤心邻妇争先折”[4]212;《望梅词》中“等和羹大用,休把翠条谩折”[4]230;《西地锦》中“暗香浮、疏影横斜。寄取和羹未为晚,却免教攀折”[4]248。对于梅子的爱惜是咏梅词审美关注点的转移,这样的咏梅词也在普通咏花词的基础上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这首《绿头鸭》下阕采用拟梅自述口吻,写出梅花的渴望与期待,其情比其他咏梅词更为深切,也更明显地展现出了作者深层次的创作动机:借梅花之口来直接说出词人自己内心入世和羹的政治理想。虽然《梅苑》中表达用世之志的词作较少采用这种以梅花为第一人称的方式,但是它们借咏梅寄托的身世之感无疑是相通的。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中表示:“咏物词……不管其数量如何繁多,内容如何驳杂,其审美形态盖不出乎以下几种:第一,以形容尽致为终极的审美的;第二,融咏物与艳情为一体的;第三,政治寓言式的,将难言或不能言的事物以咏物的形式表现出来。”[5]429《梅苑》中的梅花,强烈渴望着暗含政治寓意的“和羹”,词人对于它们的吟咏显然属于第三类。梅花对和羹的向往,也是词人渴望施展政治抱负的间接表达。词中以梅花比拟“举于版筑之间”的传说,同时也是词人的自喻。盐梅和羹之典与梅花原本并无关系,《梅苑》的佚名词人开拓了自《尚书》以来以盐梅喻治国贤臣的表意空间,深入挖掘了其中在野贤士得到赏识并辅佐君王的内涵,以“点铁成金”之笔将其融入咏梅词,成为词中梅花形象转向积极入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对欣赏者的渴求
承接和羹之志,对于梅花的欣赏者的书写也是《梅苑》中塑造积极入世的梅花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欣赏者的渴望也是梅花心怀和羹之志的另一种体现,这在一些词作中有直接的表述,如王和父《万年欢》:
雅出群芳。占春前信息,腊后风光。野岸邮亭,繁似万点轻霜。清浅溪流倒影,更黯澹、月色笼香。浑疑是、姑射冰姿,寿阳粉面初妆。 多情对景易感,况淮天庾岭,迢递相望。愁听清吟凄绝,画角悲凉。念昔因谁醉赏,向此际、空恼危肠。终须待、结实和羹,恁时佳味堪尝[4]232。
梅花占得先时、幽香独绽,然而却生于荒野寥落之处,加之庾岭遥远,更是无人前来欣赏。梅花感于昔日的醉赏者,对比今夕寂寞,不禁伤心断肠。词的结尾,作者不忘强调结实和羹对于梅花的重要意义:即使此刻独处荒郊野岸,无人欣赏,当有朝一日梅子得以和羹,完成抱负,方能慰今日之“危肠”。《梅苑》中,对于欣赏者渴望与期盼的直接表述还有很多,如“算知空对,绮槛雕栏,孜孜望人攀折”(《黄莺儿》)[4]221;“墙头半开,却望雕鞍无故人”(《婆罗门引》)[4]234,等等。
除此之外,文学史上曾有过咏梅名篇的文人,也大都以具有代表性梅花的欣赏者、知音的形象出现在《梅苑》的词作中,被反复地追思、赞颂。
蓦山溪
前村雪里,漏泄春光早。似待故人来,束芳心、幽香未老。溪边昨夜,雨过却参横,云旖旎,玉玲珑,不遣纤尘到。 无情有意,寂寞谁知道。幽梦觉来时,淡无言、风清月暸。何郎去后,憔悴少新诗,空怅望,倚楼人,玉笛霜天晓[4]208。
这首词中对于梅花的渴望与等待反复渲染。言其“似待故人来”,而“幽香未老”可见其虽等待多时,但初心未改。下阕又说梅的寂寞无人知晓,与“何郎去后,憔悴少新诗”相呼应。何郎即何逊,作有咏梅名篇《咏早梅》(一作《扬州法曹梅花盛开》),这首诗在咏梅文学史上具有范式意义,其吟咏模式多为后世所因袭效仿。作为咏梅诗的开拓者、文学史上梅花的第一个知音,他的形象也常常在后世各种咏梅文学中出现。在《梅苑》中,何逊则多是以梅之伯乐,梅花最早欣赏者的形象出现的。这首词中的梅花自何逊之后等不到知己,只能在空怅望之中憔悴。这里的梅花褪去了传统咏梅文学中的清高与孤傲,虽然同样是孤独,却在孤独之中期盼着寻访者,是典型的“士不遇”的形象。此首词通篇大有“惟草木之凋零兮,恐美人之迟暮”[6]8之意味,深蕴“骚”情。黄大舆在《梅苑序》中亦有云:“目之曰《梅苑》者,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日所录,盖同一揆。”[4]195《离骚》内涵丰富而深刻,《梅苑》中词虽不能与之相较,但其中强烈的用世之心,得不到欣赏、认可的悲恸却是与屈骚之旨相通的。何逊在《梅苑》之中的出现频率很高,如《鹧鸪天》中“却月凌风度雪清。何郎高咏照花明”[4]245;《江梅引》中“南州故苑,何郎遗咏,风台月观”[4]199;《万年欢》中“算当时寿阳,无此表格。应寄扬州,何逊旧曾相识”[4]233,等等。
杜甫也许是唐代第一个对梅花着眼较多、涉笔较多的诗人[7],他的《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江梅》等对后世咏梅文学也有较深的影响。因此杜甫也常以与何逊相似的形象出现在咏梅词中,如“何逊扬州,拾遗东阁,一见便生清兴”(《喜迁莺》)[4]218;“东阁赋新诗,惭愧当年杜拾遗”(《南乡子》)[4]255;“少陵为尔东阁,美艳激诗肠”(《梅花曲》)[4]220;“少陵诗兴,犹爱清香”(《洞庭春色》)[4]203,等等。
除了对于有过咏梅名篇的诗人的歌颂与追思,对于寿阳公主的书写也常常间接地表现出梅花对于欣赏者的渴望。寿阳公主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之女,据《太平御览》卷九七〇引《宋书》:“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8]4299因而“寿阳公主”“梅花妆”也因此成为后世咏梅文学中的常见典故,在《梅苑》中亦是如此。《梅苑》中用此典的词作,大多意在表现梅花的娇俏美丽,如:“傅粉酡颜,何殊寿阳妆面”(《双头莲》)[4]223,“浑疑是、姑射冰姿,寿阳粉面初妆”(《万年欢》)[4]232,“素质偏怜匀澹,羞杀寿阳人”(《婆罗门引》)[4]234;或将何逊与寿阳公主并列,如“梁苑奇才动佳句,汉宫娇态学严妆”(《雪梅香》)[4]236;或是将梅花当下的无人欣赏与昔日受到寿阳公主的喜爱进行对比,如“谁人宠眷?待金锁不开,凭阑先看。曾飞落、寿阳粉额,妆成汉宫传遍”(《折红梅》)[4]219,等等。
如果说对梅花和羹之志的反复吟咏是词人自身用世之志的抒发,那么此处梅花对于赏花者的渴望,也是词人自身对伯乐的期盼,对于自身未受赏识,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悲慨之吟了。梅花纵然美丽清香,但若无何逊、杜甫等诗人的欣赏和吟咏,梅花的美丽是徒劳的,是一种自怨自艾的美丽,是带有悲剧性的。在这些词作之中,梅花的美是需要向外寻求价值寄托的,而非其他主题的咏梅词中的那般悠然自得,即使没有欣赏者,依然可以自我欣赏与肯定。
三、意义独特的空间想象
《梅苑》之中有大量的对于梅花所处空间的书写,其中主要展现的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空间意象,一是凄冷荒凉的荒郊野外,二是温暖富丽的庙堂之上、庭院之中。可以说,前者是梅花所处的当下,后者是梅花所向往的理想之地。
梅花出现的典型空间,首先是远离热闹与喧嚣的乡村:
江村路曲,问青帘、与酌余醅(《汉宫春》)[4]198;
夜来深雪前村路,应是早梅初绽(《水龙吟》)[4]199;
占断陇头风光,正雪里,前村独步(《蓦山溪》)[4]207;
敛同云,破腊雪霁前村(《绿头鸭》)[4]211;
前村昨夜,先报春消息(《蓦山溪》)[4]206;
漏新春消息,前村数枝,楚梅轻绽(《定风波慢》)[4]213;
好是前村雪里,一枝开处,昨夜东风布暖(《望远行》)[4]215。
同时,“竹篱”“茅舍”及其表述也都是在《梅苑》之中出现频率极高的空间意象:
竹篱茅舍,典型别是清白(邵公济《念奴娇》)[4]202;
低傍小溪,斜出疏篱,似向陇头曾识(刘无言《花心动》)[4]202-203;
向篱边竹外,前村雪里,青稍尤瘦,疏影溪边(《洞庭春色》)[4]203;
疏篱茅舍,回首试轻辞(《蓦山溪》)[4]206;
野水溪桥,竹篱茅舍,何似玉堂金阙(《选冠子》)[4]228;
冷落空山道。匹马骎骎又重到。望孤村,两三间、茅屋疏篱(《洞仙歌》)[4]231;
幽香远远散西东,惟竹篱茅屋(《西地锦》)[4]248。
或是水边、驿站旁:
无人共折,傍溪桥、雪压霜欺(《汉宫春》)[4]198;
忆得去年冬,数枝梅,低临水畔(《蓦山溪》)[4]208;
疏影横斜,澄波清浅,暗香浮动月黄(《绿头鸭》)[4]211;
水亭边,山驿畔(《定风波慢》)[4]213;
生怕有、江边一树,要堆轻雪(《雨中花》)[4]234;
据鞍惊见,梅花的皪,篱边水际。……正水村山馆,倚阑愁寄,有多少,春情意(《水龙吟》)[4]200。
范成大在其《梅谱》中云:“江梅。遗核野生,不经栽接者……凡山间水滨,荒野清绝之地之趣,皆此本也。”[9]254《梅苑》之中,生长在山间、水滨、荒寒清绝之地,不经栽接的梅花,便与范成大所描述的江梅十分契合。《梅苑》中亦有直写江梅的,如《选冠子》“憔悴江山,凄凉古道,寒日澹烟残雪。行人立马,手折江梅,红萼素英初发”[4]288。毕嘉珍在《墨梅》一书中指出,范成大之江梅“标识出梅花无人关注的美丽是与被忽视的士人,或者更肯定地说,是与士大夫与世隔绝、洁净、出世的生命相为一致的”[10]6。在《梅苑》里的很多词作中,它们的确感同身受地唤起文人的身世处境,其形象蕴含着隐喻寄托。但是在这些入世主题的梅词中,孤芳幽独的江梅所象征的那些被忽视的士人表现的不是出世的、与世隔绝的,而是不甘的、苦闷的、渴望入世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词人都刻意表现梅花的不如意,梅花在这样的空间中呈现出孤苦无依、怀才不遇的形象:
野岸邮亭,繁似万点轻霜。清浅溪流倒影,更黯澹、月色笼香……念昔因谁醉赏,向此际、空恼危肠(《万年欢》)[4]232。
前村雪里,漏泄春光早。……无情有意,寂寞谁知道(《蓦山溪》)[4]208。
免教向、深岩暗谷,结成千万恨(《击梧桐》)[4]205。
更免逐、羌管凋零,冷落暮山寒驿(《东风第一枝》)[4]224。
谁把瑶林,闲抛江岸(《惜黄花》)[4]237。
无人共折,傍溪桥,雪压霜欺(《汉宫春》)[4]198。
清幽荒凉的环境是咏梅传统上的常见空间,在《梅苑》中的所描绘的梅花入世形象的词中,词人着意渲染、凸显梅花在此种环境之下的悲戚、困窘。一般在经典的咏梅文学对于梅花形象的塑造中,梅花在所处的空间之中都是表现出坦然接受的一面。梅花虽然并不是对于所处的空间一定心满意足,但是至少认可所处的空间可以成就自身的价值。林逋的《山园小梅》之中,梅枝在水畔弄影,在月下暗吐芬芳,充满清高闲逸的雅趣。陆游《卜算子》之中,虽然“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写尽梅花的荒凉哀伤,但是梅花仍然保持自我的高洁品格不变,“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11]174,这种品格也是梅花生命意义的一种体现,是梅花处于这样空间下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方式。而在《梅苑》所书写的这些空间之中,梅花大多是对于所处空间不满并且不甘的,是一个无法实现自我意义的空间,而这也正是词人对于自身当下所处的晦暗政治境遇的隐喻。
正因如此,《梅苑》之中有多处对于梅花渴望被移栽,渴望改变所处环境的心态的书写。词中有时会展现出梅花自信的一面,如《汉宫春》:“寂寞槿门牛巷,有清香自倚,不怕低回。终须会逢赏目,健步移栽”[4]198,但更多的时候,梅花则是处于一种无奈的怅惘之中:
击梧桐
雪叶红凋,烟林翠减,独有寒梅难并。瑞雪香肌,碎玉奇姿,迥得佳人风韵。清标暗折芳心,又是轻泄、江南春信。最好山前水畔,幽闲自有,横斜疏影。 尽日凭阑,寻思无语,可惜飘琼飞粉。但怅望、王孙未赏,空使清香成阵。怎得移根帝苑,开时不许众芳近。免教向、深岩暗谷,结成千万恨[4]205。
东风第一枝
腊雪犹凝,东风递暖,江南梅早先拆。一枝经晓芬芳,几处漏春信息。孤根寒艳,料化工、别施恩力。迥不与、桃李争妍,自称寿阳妆饰。 雪烂漫、怨蝶未知,嗟燕孤、画楼绮陌。暗香空写银笺,素艳谩传妙笔。王孙轻顾,便好与、移栽京国。更免逐、羌管凋零,冷落暮山寒驿[4]224。
这两首词中同时出现的“王孙”意象在一般咏梅文学之中极少出现,梅花一贯绝尘拔俗的形象与王孙、繁华等意象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在这两首词中“王孙”却以一个正面的,梅花之贵人、提携者的形象出现了。词中梅花希望得到有地位的王公贵族的赏识,被移栽至繁华热闹的皇家园林或是国都,从江边野梅变成一株被显贵者所养的苑梅。若非如此,梅花便只能向“深岩暗谷,结成千万恨”,“羌管凋零,冷落暮山寒驿”。词人认为没有王孙欣赏乃至移栽,梅花的清香便是空无意义的,这是《梅苑》中表达用世之志的词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些咏梅词中,梅花自身的美丽与清香无法自我成就其价值。在大多经典咏梅文学中,梅花的凌寒独放是梅花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可以自成意义,梅花的清新雅致亦可以自成意义。但是在这里,梅花却需要有梅子和羹才、需要有他人的欣赏与认可才能实现价值。此处的梅花,也完全成了郁郁不得志,又非常能够渴望身居庙堂的文人的化身。
前文提到,咏梅诗之中由于对于梅子的爱惜,不愿被随意折枝,“伤心邻妇争先折”中,梅花所伤心的,并非被折,而是未能等到能真正赏识自己的人,却被邻妇先行折走,让自己的价值不能遇到与之匹配的欣赏者。《声声慢》[4]197之中,就描写出了一次理想的折枝:
严凝天气,近腊时节,寒梅暗绽疏枝。素艳琼苞,盈盈掩映亭池。雪中欺寒探暖,替东君、先报芳菲。暗香逮,把荒林幽圃,景致妆迟。 别是一般风韵,超群卉、不待淡荡风吹。雅态仪容,特地惹起相思。折来画堂宴赏,向尊前、吟咏怜伊。渐开尽,算闲花、野草怎知。
梅花在严寒之中,凌寒傲雪绽放,带来了春天将至的讯息,幽香也装点了荒凉的园圃。这是上阕所书写的内容,一般来说,以上内容是传统咏梅诗词对于梅花的吟咏所涵盖的基本层面,词的内容至此也基本结束了。但是在下阙词人笔锋一转,将咏梅的内涵进一步延伸:梅花由荒林幽圃,被折向了画堂之中,以供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之上细细品赏吟咏,而此时的梅花,才是得志的、自我实现了的状态。在荒凉之处装点景致,幽香暗传的梅花所成就的最终价值是需要借“画堂宴赏”来体现,肯定其生命价值的再次是外事外物,而非梅花自身。又如《西地锦》[4]248中:“凭君折取向玉堂,只这些清福”,《尾犯》中:“好把琼英摘。频醉赏,舞筵歌席”[4]215,等等。在竹篱茅屋间开放的梅花,渴望的是被折取后带往玉堂。此处的折枝与之前的希冀被移栽是同一重含义,都是词人借梅花传达出自身在前途渺茫的遭际之中对于去往更能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环境的心驰神往。
四、宋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境遇
《梅苑》中集中出现的积极入世的梅花形象在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的产生与词人的身份、词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虽然《梅苑》中的大部分选词皆为佚名词人之作,无法通过考证具体作者的生平去了解他们的仕途境遇,但是我们可以试着从宋代士人求仕的大环境入手,分析他们所处的历史世界与其词作的关联。据黄大舆自序,《梅苑》编成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且所选皆为宋人作品,因此这一时期宋代士人的历史境遇或许可以作为了解《梅苑》中词人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态的一个参考。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于《概括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12]10,其中唐宋变革的最大体现便在于政治。宋代的政治体制,由制魏晋隋唐的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宋代取消了从政的门第的限制,科举制度的完善让大量的非贵族出身的读书人也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活动中来,委以重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政治架构的突出特点。宋太祖就曾有言:“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13]449-486太宗也对李畴等人说:“中书枢密,朝廷正人所出,治乱根本系焉。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14]600至熙宁四年(1091年),三朝元老,时为枢密使的文彦博与神宗论政中亦有云“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见当时“共治”已成为君臣之间的共识。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宋代文人士大夫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极其鲜明,任何时候都更加体现出“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可见当时“共治”已成为君臣之间的共识。
同时宋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教育,在全国各地大量兴办官学,对于私学和新兴的书院也十分鼓励提倡,为更多人提供了就学进而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并且,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大量刊行印发,知识得到广泛、迅速地传播。君王的重视、时代精神的昂扬、教育的普及,这样的政治环境使不同阶层的读书人都有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对于仕途的期许,与君王共治天下成为北宋读书人心中最热情蓬勃的理想。
然而,通往晋升之路的大门虽然打开了,但是士人们想要通过重重考验进入官场,却并非就此简单轻松了起来。取士范围的扩大,应试考生人数也不断膨胀,竞争也日益激烈。两宋读书人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自北宋后期起,不论地近京畿的州县,或川广等偏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15]北宋诗人晁冲之《夜行》诗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16]13866,就写出了即使荒凉乡村之中的儒生仍在彻夜苦读的情形,不免让人联想到上文中所说荒野孤村中独自开放的点点江梅。据统计,全国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数,在真宗时期的第一次科举(998年)约为10万,到英宗治平元年(1068年)就达到了42万人左右[17]76-77。以至于至南宋中期,如果将全国应举和准备应举的读书人都统计在内,人数可能接近百万[18]529,科举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从11世纪晚期开始,学有所成的学者数量超过了政府所能提供的职位。由于考试标准不断提高,职位数额有限,以及竞争激烈,不少儒学考生在考试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作弊手段。成功及第者还要相互竞争,在已经过于拥挤的官僚机构中谋求职位”[19]232。
总的来说,宋代的政治体制由前朝的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后,读书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与更加广阔的入世道路。一些原本无缘进入政权中心的寒门子弟开始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给了宋代读书人极大的信心与希望,渴望通过政治能够自我实现。然而,日渐残酷的科举竞争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苦等数年,甚至一生也无法完成自己的“和羹之志”。宋代读书人对于科举的热情与期望值可以说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而他们饱满高涨的从政热情与日益艰难的晋升之路间产生了极大的落差。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历史环境,也更能深入地理解他们为何会如此集中地借梅花发出官运仕途的感慨,以至于梅花在此一时期中被赋予了积极入世的新形象。下层文人的生命境遇本身就与梅花有很多层面的相通,在宋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荒野之中所见寂寞盛开的梅花更能引起他们的兴发感动。学有所成、充满理想而又很难在拥挤的官僚体制之中谋得一席之地,与梅花的美丽芬芳,而又得不到欣赏的命运高度契合。于是,宋代读书人发现了梅花的另一面,另辟蹊径地将他们渴望致君尧舜而又困难重重的命运寄托于梅花。这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一时代会集中出现以梅抒发用世之志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