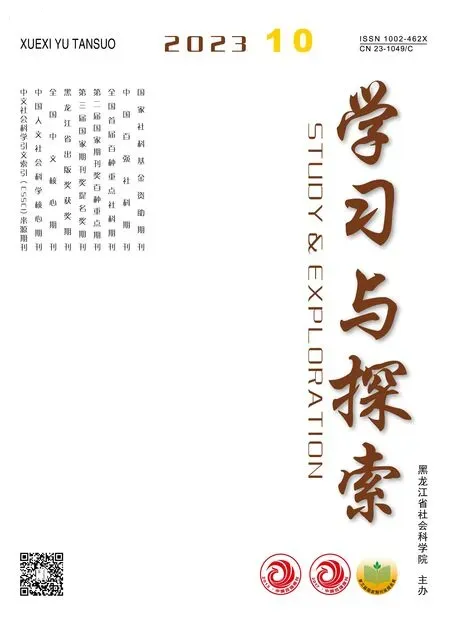中国文论“载道”传统的现代进程及意义
2023-12-23王丽娜
韩 伟,王丽娜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文字作为一种承载人类思想意识的符号自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丰富的功能性。伴随文学作品和文学形式的丰富以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断多元化,文学在表达创作主体情感、承担社会功能和传递文化价值层面担负起了重要的责任,因此文学、政治、社会、创作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国古典文论中将文学与现实功用的关系概括为“载道”。有关“道”的含义各家观点不尽相同,其中儒家之道在历史变革中成为主流思想,孕育出了“载道”精神并不断发展。“文以载道”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作为一种基本问题显现出来的,在近现代似乎没落了,实际上却在重构中获得新生。
一、“文以载道”作为基本问题的演递
“文以载道”作为基本问题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再到体系化的过程。“载道”思想在孔孟处就已发生,但尚没有明确指出“文”与“载道”之间的必要性,是以“文学内容”与“道德属性”之间的制约关系展现出来的。春秋末年,孔子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成为最早的诗歌正统,又强调“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从这一点来说,作为“言”的诗歌在道德上就有了约束。这种判断对于中国古典文论观具有原型意义,也将“文”与“道”绑定起来。孔子以“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尧曰》)肯定了“诗”与“德”的联系,并认可了文学的功能性,埋下了“载道”传统的种子。孟子沿着“思无邪”的理论进一步提出“知人论世”说,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对时代背景的掌握,是了解作者性情、考察作品思想倾向的前提。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知人论世”的内在逻辑就是强调文学作品具备承载作者品性、时代风习的潜能。但“文”的“载道”功能被完全接受是在汉代经学的繁荣中实现的。儒学在汉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文”与“道”的关系被具体化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行为准则。独尊儒术的汉朝强调“移风易俗”,董仲舒将“教化移俗”的方法总结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载道”的轮廓更加清晰。然汉代“劝百讽一”的文风,也使文学丧失了它应有的批判性。
这种功能的偏离,促使魏晋时期重提“重道”传统,刘勰提出“文从道出”“文以明道”,明确将“道”作为文学的源泉。“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1]9刘勰认定“文”与天地一同产生,并为这一结论找到了切实的根据——“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9,颜色、形状、形象就是“道之文”,这里的“道”是天地自然。刘勰用“自然之道”作为文学的起源,也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要求。“道沿圣以垂文”[1]14,自然之道靠圣人用文章显示,“圣因文而明道”[1]14,圣人用文章来说明自然之道,只有这样才能“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1]14。刘勰延续了孔孟时期对文学功能性的肯定,将“道”裁定为“自然之道”,但“本乎道”之“道”更多是指“儒家之道”。虽然刘勰身处玄学盛行的南朝,但综观《文心雕龙》全篇,不难发现儒家思想贯穿始终。“道沿圣以垂文”就要求想要“明道”就必须“征圣”,向圣人学习。刘勰所追随的“圣人”就是孔孟先贤。“圣人之情,见乎文辞”(《文心雕龙·辨骚》),圣人之贤能,皆在其传世文辞中得以实现,而圣人之文辞,正是儒家经典——“五经”,也就是《文心雕龙·宗经》中所推崇的。《文心雕龙》明确了想要为“从道而出”之“文”,就要“宗经”“征圣”,这一方面巩固了“载道”传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使之重回儒道正统。
“唐、宋古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口号,那就是文以明道,或者称文以载道,并由此而提出一系列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的理论……而究其指导思想,除了社会现实的种种原因外,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刘勰。”[2]517中唐的古文运动,延续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道关系的阐发。韩愈以“仁义”来界定儒家之道,直接与老子之道彻底区分,“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3]13文章回溯儒家之道开创于尧、舜、禹,经古代圣王、孔孟传承,因秦暴政、佛老盛行致儒道衰微“不闻圣人仁义之说”,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必须恢复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原道》首次完成了儒道传承的谱系梳理,明确了儒道的本源和内涵,形成了与佛老之道对抗的态势,并对“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这一论断进行了直接的阐明。到了宋代,仁宗即位之后,古文运动的重振,使得儒家道统全面活跃于北宋的政治舞台。北宋“文以载道”的重要话语发起者之一欧阳修继承了韩柳的“文道观”,他在《送王陶序》明确提出“六经皆载圣人之道”[4]1085,“六经载道”实质上就是“文以载道”。欧阳修的“载道”相对于韩柳而言,内涵更为宽广。欧阳修极其重视“六经”,认为“六经者,先王之治具,而后世之取法也”[4]1191,一方面视“六经”为“载道之文”,但另一方面又不以其为道统的绝对真理,而视之为记载古事的范本。“尧、舜、禹之事,载于《书》者,为万世之法”,“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也”[4]1759。在欧阳修的“道统观”里,“六经”所载的是“古事”,“道”蕴藏在其中。如此看来,“六经”既是道统思想的反映,又是先贤“以文载道”的一种实证。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推崇欧苏之文,认为“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那寻常底字”[5]3573,“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5]3573。朱熹以“源”观“文”之出处,提出“文出于道”,离开“道”便无“文”的存在。“载道”传统在理学大厦中完成了体系化:“道”即“理”,它先于天地而生,是超越形器的绝对精神,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宇宙原理,同时也是“人之所共由”“事理之当然”的道德准则,是社会伦理的标准,自然也是为文的标准。“文皆从道中流出”肯定了“文”的终极根源是“道”,“文”的本质和最高追求也是“道”,同时规定了文学的内容及其本质都是由“道”决定的,以“理”为依据。更进一步朱熹所言“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5]3587,将“腔子”也就是文学形式的表现也归为“天生”,即由“道”决定。“文”不是因“道”产生,而是“流出”,“文”是“道”“理”的显现,两者之间成为一种体用关系。理学家所提出的“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周子全书·通书·文辞》)及“作文害道”(《二程全书·语录》)等观点,实际上是在以否定“文”的方式来强调为文要显现“道”“理”,必须将“文”的重要性建立在“道”的首要性基础之上。
宋代以后“载道”传统或以“重道”或以“轻文”或以“文道统一”的形式显现,但只是一种批评倾向的循环,再没有跳出“文以载道”的逻辑,故不赘述。
二、现代文论对“载道”传统的批判重估
鸦片战争敲响了封建统治的丧钟,被动进行社会变革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思想上都面临巨大冲击,文学思想也不例外,而对“载道”传统的批判贯穿了整个现代文论的成长期。新文学运动的各方力量均以推翻“文以载道”为己任。这种批判的肇始,先于新文学运动,在五四运动后逐渐达到峰值。“中国最近八十年来的学术开创者”王国维,文学革命的代表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以及当时文学团体的核心人物茅盾等共同打造了一个批判“载道”传统的理论阵地。他们从拆解文道关系、质疑“道”之所指、探讨文学本质等不同角度对“文以载道”加以批判。
1904年,王国维开始运用西方批评理论对《红楼梦》进行评论,率先使用中西批评交融的方法为现代文学批评拉开了序幕。虽然他并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对文学革命也有抵触态度,但是他的思想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具有奠基意义,特别是他对“载道”的批判,可以“先驱”视之。王国维率先站在审美是非功利性的高地,发出了批判“文以载道”的呼声。他强调中国文学受政治、教化的直接影响,少有“纯文学”“真文学”。王国维认为所谓“纯文学”“真文学”必须是非功利的,“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餔餟的文学,决非文也”,“文绣的文学不足为真文学”[6]16。他将中国文学不够发达的原因归结为过分强调政治功能性,并援引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认为“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6]19,坚持回到以文学自身来发展文学的立场,强调“为文学而生活”,创造纯粹的文学作品,抛却世俗功利特别是政治使命,进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的历史进程。王国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诗人等都有兼为政治家的嫌疑,称“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7]3。
与王国维所持观点相近的还有周作人,他将“载道”传统与宗儒等而视之。“载道”被其视为维护帝王利益传递帝王思想的手段,认为这种传统导致了文学创作和民族发展的缓慢,周作人也主张以“纯文学”建立新的文学独立性。1908年,周作人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理论探讨,一方面批判了“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教法,割取而定之”[8]6,认定“删《诗》定礼,夭瘀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夫孔子为中国文章之正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则后之零落又何待夫言说欤”[8]6。另一方面归纳了文学的“四义”——“必行之楮墨者”[8]10,“必非学术者”[8]10,“人生思想之形现”[8]11,“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8]12。直到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仍然坚持这种否定“载道”传统的观点,指出“言志”与“载道”的区别,“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作‘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9]38。周作人主张文学应该只有情感没有目的,创作如果报以实用的目的,就已经不是“纯文学”了。他的矛头不仅指向古典文学中宗儒、载道、八股等,也指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将一切有目的的文学均视为“载道”的文学。刘半农也是“纯文学”一派,企图彻底将文学独立出来以拆解文道关系,他认为“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做一谈”[10],甚至将《诗经》都排除在文学之外,在他眼里中国古典文论中“文道一体”的关系不过是一种虚构。王国维、周作人、刘半农都试图从拆解文道关系的角度还原中国文学的“真正形态”。
总体来看,现代文论试图重新界定文学的实用性与非实用性、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以此为标准划分文学与非文学,并将这种判断方式作为对传统文学观念的颠覆。然而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山水自然文学、“吟咏情性”的抒情诗文、表达诗人超脱个人境界的诗文,都属于现代文论意义上的“纯文学”范畴。之所以造成现代文论判定古代没有“纯文学”,是由于划分标准的差异,中国古代没有“纯文学”的概念,但并不代表没有“纯文学”的作品,古人更不会以“实用性”去判定文学作品是否蕴含“载道”精神。因此现代文学以“纯文学”的创作标准去批判“文以载道”的创作传统,在逻辑上无法对应,这实属一种误判。摆脱实用性、现实功利性,提出“为艺术而艺术”,是“纯文学”带给中国现代文论的新愿景,但却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纯文学”作为作家的创作目标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近现代社会是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文艺工作者更无法脱离社会现实创作所谓“纯文学”。在革命时期,在社会政治不宁的状态下,所谓有实用性的“非纯文学”自然特别发达,这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相反地,被批判的“载道”传统却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学的要求和期待。
与拆解文道关系,强调文学独立性不同,一部分文学革命的先锋对“文以载道”的批判是从质疑“道”之所指入手的。胡适在阐释“言之有物”时强调“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11]。认为“物”之所指应为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以“情感”代替“道”,从而实现对“载道”传统的否定,主张以“言之有物”代替“文以载道”。同样倡导文学革命的陈独秀也对“文以载道”大加挞伐,他提倡写实主义,认为文学应该指导现实生活,发挥改造社会的作用,认为“文以载道”的要求应该被表现现实生活替代。他将矛头直指儒学,将儒家思想等同于封建统治,将“载道”传统作为儒家核心文化而予以否定。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陈独秀认为“三大主义”与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有本质上的区别,他承认韩愈是“文界豪杰之士”[12]96,但认为中国文学“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12]96。
无论是“言之有物”还是“三大主义”,不过是对“文以载道”的再次阐释。以“情感”“现实生活”代替传统“儒道”,实际上在批判的同时把自己带进了“文以载道”的逻辑。胡适所谓“言之有物”的思路与“文以载道”在本质上是同样的出发点——文学是工具,是手段。胡适只是以“物”的概念替换了“道”,以“言”的表达替换了“文”。陈独秀虽然批评了胡适的“言之有物”观,“‘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然不善解之,学者亦易于执其遗月,失文学之本义也”[12]208,直指胡适没有将文学的价值完全独立出来,但是自身也并没有跳出文道关系的理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也是在强调以文学为用,虽然打着批判“文以载道”传统的大旗,但实质上真正批判的是封建道统之“道”,而不是“文以载道”之“道”。“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2]94,不也是“文以载道”吗?“文以载道”提供了新文学重新思考自身价值的基本思路,也成为文学革命讨论的重要内容。
文学革命中最重要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茅盾,对于“载道”传统的批判是从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出发的,在论及文学本质的同时讨论了作家身份和创作手法的相关问题。茅盾认为中国文人往往将经史子集都看作文学,却将真正的文学淹没了。在他眼中,文学“构成的元素”一方面是“我们意识界所生的不断常新而且极活跃的意象”[13],另一方面是“我们意识界所起的要调谐要整理一切的审美观念”[13],他用审美和意象来概括什么是文学,从而批评中国以往的文章都是“有为而作”[14],古哲圣贤以文章为手段宣传道统观念,作文是替当权者歌功颂德的手段罢了。茅盾亦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文以载道”的负面影响加以批判,他认为“载道”传统是“有毒的”创作观念,导致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抛弃真正的人生不去观察不去描写”[15],反而将所谓“圣经贤传”的内容作为文章的“柱意”,将凭空想象出来的内容作为“因文见道的大作”。茅盾将“载道”传统对作者、作品及创作方法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以促成新文学的新路径。实质上,其目的是为文学争取社会地位,确立新文学的价值。“文以载道”也曾同样是为文学发声,确立文人、文学作品社会价值的理论依据,如果从理论目的来看,茅盾的批评与“文以载道”的目的无二。
新文学倡导者对“载道”传统的排斥不乏误判和夸大的嫌疑,他们看似是以颠覆“载道”传统为目标,并提供了各种理论依据,但这种批判的实质是对封建思想的痛斥。古典文学所载之“道”在新文学革命者的论述中就是封建道统,他们意图将文学从这种道统约束中彻底解放出来。此种背景下,作为方法的“载道”就被视作封建思想的一部分被连带否定了。实际上,一方面,现代文论对“载道”传统的批评从未跳出“文道关系”的逻辑,因此在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文以载道”的同时彼此之间也无法认同;另一方面,这种批判也使得“载道”传统以批判对象的身份一直保持在场,为新文学的理论进步提供了思路。集中的批判给了中国现代文论重新思考文学的作用及其本质的可能。文学革命正是在反叛传统的过程中有了新的生机,“载道”传统也在进行时代改造,融入新的内涵。批判激起人们对固有传统的重新认识,传统也因此得到赘续和承接。
三、“载道”传统的现代面孔
文学革命铺垫下的革命文学于20年代中期兴起,“文以载道”的传统在革命文学中重获崭新的现代面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结合社会现实重提文学与革命、文学与阶级、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内在逻辑亦与“文以载道”高度一致。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告别了“五四”所开启的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整个社会的急速变革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运用,同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再次成为文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以不同的政治目标成立的不同文学团体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载道”传统逐渐蜕变为全新的面孔融入新的文学思潮。
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接受了左翼路线,将处于低潮的革命以文学的形式完成政治上的持续,同时形成了左翼文学阵营。“文学工具论”的调子在革命文学团体中重现生命力,创造社的骨干李初梨就明确提出文学的任务是“反映阶级的实践和意欲”[16]。然而这种倡导逐渐出现偏激的转向,在“左倾”机械论的影响下,以创造社、太阳社中冯乃超、李初梨、潘梓等为代表的成员对鲁迅、茅盾等五四时期已经崭露头角的大家进行了批判清算。他们认为鲁迅不过是“封建余孽”,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毫无现代意味,指责茅盾的文章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反动派“强有力的文字”。这种攻击引起了围绕着革命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亦涉及“文学”本质的讨论,探讨文学是否应该成为新时代“载道”的工具。鲁迅、茅盾都明确赞成革命文学的倡导,但始终反对文学工具论。鲁迅批评创造社、太阳社只是纸上写下的“打打杀杀”,是“空嚷”,而茅盾则认为太阳社、创造社忽略了文学的本质,走上了标语口号化的道路。“左翼”文学团体犯了将文学等同于政治的错误,与历史上将“载道”等同于为政治服务并将其视为创作唯一宗旨的偏见如出一辙。而鲁迅、茅盾虽然不赞成文学工具论,但仍然肯定文学承载着“倡导革命”的使命。这样一来,围绕革命文学产生论争的双方,看似对“文以载道”持有不同意见,实际都认可“文”具备“载道”的属性,只是在“载道”的具体内容和创作方法上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论争使现代文学跳出对“纯文学”的幻想,同时,在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社会进程相匹配的过程中,使“载道”传统找到了现代性新出路。
将“文学”作为斗争工具的观点不仅在“左倾”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中间越发高涨,而且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宣言中,也有公开表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声音,转而对文学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加以考察。梁实秋认为“文艺而躲避人生,这就是取消了文学本身的任务”“文学里面是要有思想的骨干,然后才能有意义,要有道德性描写,然后才有力量”[17]438。沈从文明确表示,他的文学创作企图“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18]68。朱光潜对自由主义作家有关政治、社会、艺术的思考做出了典型的总结“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所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19]2,自由主义阵营同样对文学“洗刷人心”再造民族灵魂的作用予以重视。这亦与“文以载道”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现代文学一方面想要彻底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获得独立,另一方面,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兴起又对文学的社会功能进行重新诠释。1930年,郭沫若为“文以载道”恢复声誉,他提出“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20]86,封建时代“文”所载之“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文学革命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新时代“自由平等的新道”与封建社会的道是对立关系,也因此不得不产生“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 对“载道”传统的抨击被定义为“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新文学”也在载“新道”。朱自清也表现出与郭沫若类似的倾向,“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21]480。文学的社会功能在现代中国被全面接受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现代文学的“载道”面孔进一步清晰勾画,提倡“文学为政治服务”,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指导理论,这符合现代中国迫切的政治需求。但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中写道,“马克思主义主张以艺术服从政治……就是要求艺术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和利害”[22],提出“没有描写所谓超阶级人性的文艺”的观点,这些主张就多少有极端的嫌疑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将文艺单纯视作政治规训工具的做法,就是这种极端倾向的具体化。
中国现代文学的序曲从文学革命过渡到革命文学,延续了“文以载道”的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在与西方思想接触以后,文学的功能在复杂的关系和各种力量作用下被不断重新阐释,得到新的内涵。“文以载道”虽然被作为文学革命要推翻的目标,但仔细考察就能发现,对“道”的概念替换没有改变“文以载道”的精神内核,对文学本质的争论反而发挥了文学和文人在社会进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与作用。同时,在现代语境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一步拓宽了“文”的形式。除了传统的文章,还要求小说、戏剧、诗歌、辞赋等文学样式都要承担“载”新时代之“道”的功能。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具有极特殊的性质和地位,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学责任感,正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文以载道”精神的集中体现。
“文以载道”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进程中先以“批判对象”的身份促使文学理论家们从现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新思路思考文学的价值,又以“理论指导”的面孔实现了新时代、新内涵的转化,被重新重视起来。在当下文学实践和理论建设中“载道”传统仍然充满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3]54,成为当下文艺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文以载道”与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渐融合,“载道”的使命也从肩负“阶级革命”的重任转向为“体现人民性”。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24]。“文以载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瑰宝本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同时,“载道”传统在中国现代文论的进程中也一直承担着“古为今用”的角色,“道”的内涵已随着时代而进步。如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4]以推进“文化自信”正是当代文艺作品应“载”之“道”。体现、传播、承载“文化自信”是当代文艺工作更高层次的追求。但提倡“文以载道”,不是机械地重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而是实现文艺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发展方向。
“文以载道”强调文学与政治、道德的关系,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这种理论内核经过古典文学理论的洗礼和现代文论的重构,证实了它的合理性。“载道”传统为现代文论的建立提供了“支持”,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中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作为中国古典文论基本问题的“文以载道”并没有随着前现代社会的消亡而消失,反而在现代文论确立初期就起到了重要的“相反相成”的作用,并随着时代进步获得了新生。在当下,“文以载道”更是肩负起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新使命,成为当代文艺工作者自身的价值旨归。当代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更应延续“载道”精神,要“既往”更要“开来”,铭记文学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文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