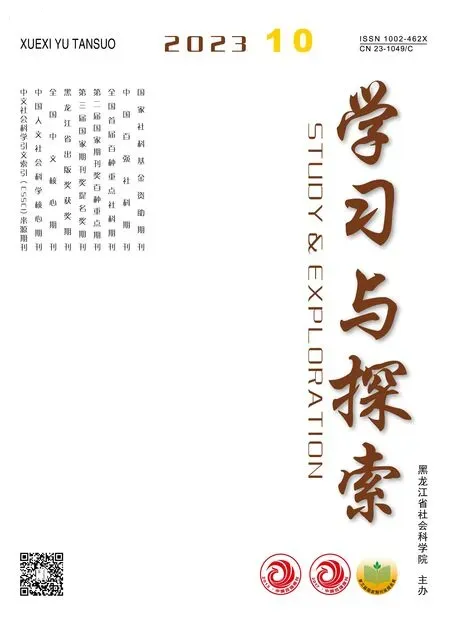主体规训与媒介融合下的网络社会交往异化拓展
2023-12-23吴海琳曾媛媛
吴海琳,曾媛媛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一、异化理论演进与网络社会交往异化新形态
(一)异化理论的演进
“异化”这一概念可溯源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异化被定义为个体自然权利向国家权利的让渡,异化被理解为权利的“转让”[1]132。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将社会分为“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两种形态,进一步提出人类一旦迈入“文明社会”,会受到文明的束缚,从而产生异化,他认为异化指“文明社会”对人的约束,致使人出现“异己性”[2]45,为解决“文明社会”的异化问题,卢梭尝试给出以建立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药方。可见,异化概念最早缘起于探讨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权利转让与约束。
在马克思从实践立场分析劳动异化之前,黑格尔使用异化概念说明意识与现实的分离与对抗:“精神是对一个独立的客观现实的意识;但是自我和本质的那种统一体与这种意识相对立,亦即纯粹的意识与现实的意识相对立……当前的现实直接以它的彼岸,亦即以它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为对立面,反之,思维则以此岸,亦即以它自己异化出来的现实为对立面。”[3]39黑格尔进而阐释了绝对精神通过异化与异化之扬弃完成自我实现的发展过程。费尔巴哈则是用异化概念阐明客体同主体脱离并反客为主、压抑主体的过程,从唯物主义角度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异化观的批判。“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乎就是人之被异化了的、被对象化了的人格性”[4]267,费尔巴哈强调人把自身“异化”成了上帝,从人自身分离出的上帝反过来支配人,借此揭示基督教的本质,并超越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观,奠定异化分析的唯物主义视角。
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批判继承基础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阐述了其著名的劳动异化思想,将异化引入对工业社会工人劳动及劳动过程的分析,提升了异化概念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5]267-268马克思通过反思劳动异化的私有制基础,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人同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展开了全面批判。
首先,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5]268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产品在本质上是对劳动者价值的贬损,工人的劳动越多,被剥削和奴役的程度越重。其次,工人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是被迫和受摧残的劳动,致使“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5]270-271。再次,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意识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是人同动物的主要区别,基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但“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5]274。最后,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相异化的结果,“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5]276,尤其是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敌对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调和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础上倡导寻求人类自由与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被视为“异化”扬弃的最终途径。
同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并非完全限定在劳动层面,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探讨了交往异化议题,从社会关系视角探究市民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异化问题,完成交往异化内容的补充[6]。马克思通过对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活动进行分析,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已然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人们的交往也不再基于需要,而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货币[7]136-142,批判以货币为媒介的交往异化体现了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延续,更为后来者推进交往异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中审视西方工业社会的交往异化现象。哈贝马斯将社会行为划分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与交往行为四类,他指出这四类行为分别关联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对应客观世界、规范调节行为指向社会世界、戏剧行为连接主观世界,而交往行为能“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8]135,即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侧重与单一世界发生关联,而交往行为能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统一起来,因而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是社会合理进化的基础。为实现合理的社会进步,哈贝马斯强调将交往行为展开的“生活世界”与目的或策略行为展开的“系统世界”进行区分,“要把社会同时构思为体系和生活世界”[9]164,体系受工具理性驱动,目的是统筹经济与政治的有序发展,而生活世界则由交往理性驱动,依托文化传递、社会规范和个体社会化在主体间达成理解与互动。“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9]169可见,生活世界中的主体交往依赖于文化提供的知识储备、合法秩序的社会调节、个性实现的社会化途径。系统和生活世界依据各自的理性原则协调运转是社会合理进化的保障,然而现代社会系统的运作逻辑逐渐入侵交往行为展开的生活世界,致使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断被现代社会的市场机制和管理机制侵入,生活世界不断萎缩,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理性被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工具理性侵袭,进而导致了社会交往异化问题。
通过对既往异化理论的梳理,异化概念的实质内涵与异化分析的延展逐渐清晰。其一,异化的含义主要体现为异己力量的生产,即主体亲手制造出反对自身的异己对象和异己关系,主体异化批判是异化分析的根本。其二,对异化现象的分析不必限定于某一特定领域,可结合社会形态变迁关注新型异化现象,推进异化分析的延展,如哈贝马斯对于“语言”媒介在交往实践中重要性的强调,形成对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分析对“资本”媒介批判的有力补充。其三,马克思“劳动异化”与哈贝马斯“交往异化”理论扎根生产与生活实践,植根异化的现实基础更有利于对复杂异化现象及其根源展开前提批判。当下网络社会来临为异化分析的延展奠定了新的现实基础,在新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推进并发展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异化理论,关注网络社会中的新生异化现象并展开反思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使命。
(二)网络社会交往异化新形态
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应用与人们生活结合愈加紧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2618亿GB。(1)数据来源: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l。如卡斯特所言,“我们对横越人类诸活动与经验领域而浮现之社会结构的探查,得出来一个综合性的结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10],信息技术推动下的网络社会崛起深刻改变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以网络为媒介的新型社会交往形态。网络社会为大众构建了新型交往空间,信息技术的普及化应用使得交往主体间的互动频度和广度无限延展,拓展了人们的交往形式,并不断更新媒介中介下的各式交往体验,但网络社会交往也日益彰显出技术依附性、双域叠合性和数字区隔化特征。
首先,网络社会交往呈现出对技术的深度依附性特征。网络社会拓宽人际交往边界、降低沟通和交往成本,使社会交往更有效率。截至2022年12月,我国互联网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38亿,占网民整体的97.2%,(2)互联网即时通信产品主要包括以钉钉、飞书为代表的企业端产品和以微信、QQ等为代表的个人用户端产品。数据来源同①。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依赖网络媒介展开。此外,网络社会交往还表现在人们对算法技术的依赖,除商业平台通过大数据实现对潜在消费群体的精准推送和定向售卖,网络交友软件也利用算法分析增加配对成功率和用户下载使用率。移动互联网作为重要交往载体发展迅猛,但也使网络社会交往实践对于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形成高度依赖,加深了对网络技术媒介中介的依附性。
其次,网络社会交往具有双域叠合特点。早期网络社会交往只是形成“线上缺场”交往与“线下在场”交往的简单区分,当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集成应用使网络社会交往实践愈加复杂,AI、AR、VR、MR等技术已经突破线上与线下交往空间分隔,使网络社会交往日益呈现双域叠合特征。
最后,网络社会交往显现出数字分化与区隔特征。数字分化表现为因价值原则和理想信念差异而形成的网络群体间分化、网民直接经验的在场世界与依托传递经验展开的缺场世界的分化、数字鸿沟导致的群体分化等[11]。同时,网络社会借助大数据搜集与人工智能精准推送,使得大众陷入自身偏好的信息茧房不能自拔,进而导致网络交往主体间的数字区隔。
网络社会交往形式对于技术的深度依赖、交往空间的叠域性,以及交往后果的数字分化与区隔凸显了网络化时代社会交往的复杂样态,结合网络化时代社会交往实践新进展,着力探究网络社会交往异化新形态,关注新时期网络社会中主体规训与媒介融合下的异化再生产,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角下的异化理论并拓展网络社会交往实践相关研究。
二、主体规训下的网络社会交往异化延展
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催生平台经济迅速崛起,网络社会的劳动与交往实践日益具有相伴而行的交织性特征。劳动过程涉及劳工、平台、生产商、消费者、代理商等多方主体交往关系的构建,网络社会的劳动实践日益嵌入交往实践。网络社会来临一方面建构了新的劳动与交往空间,增添新的工作与交往机遇,但由于劳动实践与交往实践的耦合,也会形成对主体全包围式的规训与控制,致使不同网络主体呈现不同的异化表征。“网络精英”“网约劳工”“普通网民”和“数字难民”群体在不同层面陷入网络社会交往异化困境。
(一)流量变现裹挟下的“网络精英”与能动性退化
“网络精英”指深谙互联网使用技术或网络社会发展规律,并在网络平台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人,不同于传统时代对于精英的定义,在web3.0时代的“网络精英”可以是掌握互联网时代流量变现规律并获取价值的普通人。流量变现强调用户通过大众点赞、关注、转发的高频量来证明自身的市场价值,用以谋求资本青睐,最终凭借广告、带货等方式赢得相应利润的过程。“网络精英”能够在网络劳动与交往实践中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虽有部分收益被网络平台、管理公司等攫取,但由于“网络精英”凭借流量可以迅速积累大量经济资本并实现社会地位跃升,因此,尽管他们知晓平台经济中潜在剥削的存在,仍然选择投入网络劳动与交往实践中,最终产生网络规则规训下的行为异化。
“网络精英”呈现主体能动性退化的异化特征。“网络精英”为争夺用户注意力,不断放低姿态甚至无原则地迎合用户趣味,以出奇、怪诞、险峻等方式吸引大众眼球,进而博取流量收益,近期网络上“审丑奇观”“大胃王吃播”“极端户外探险”等因此爆火。主体性体现为个体所做出行为选择出于自身需要,然而“网络精英”的选择却常常受制于MCN机构。(3)MCN(Multi-Channel Network)即多频道网络,指服务于内容生产者、平台方、广告方等相关方的中介机构。MCN通过孵化或签约“网络精英”为其提供资源链接、运营管理等服务,促成“网络精英”流量变现,最终MCN根据协议分配原则抽取利益分成。据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2022年MCN机构数量超40000家,预计2025年将超60000家,(4)参见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2021—2022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报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9023895314413439&wfr=spider&for=pc。随着网红经济的崛起未来还将产生更多的MCN机构。“网络精英”个体很难以寡敌众在网络社会吸引流量,于是加入MCN成为必然选择,“网络精英”需要服从MCN的统一管理要求,并严格执行其定下的绩效指标,因此,在内容制作、更新时间、合作品牌等方面的选择常受制于MCN。此外,“网络精英”与MCN在获得流量收益后,会延续热度持续打造同一品类的内容生产,进而使“网络精英”被MCN与用户粘贴上某一类别的身份标签,致使其只能进行圈定类别的内容制作,长久佩戴“标签”引发“网络精英”陷入创造性枯竭困境。因此,“网络精英”群体在网络流量变现中呈现主体能动性退化的异化特征。
(二)算法支配下的“网约劳工”与隐性控制
平台经济的崛起使各类经济平台进驻人们日常生活,如餐饮配送平台、工作分包、众包平台、移动出行平台等。平台经济以弹性、灵活的工作方式吸引大批劳动者,“网约劳工”群体不断壮大。“网约劳工”的劳动过程与结果需要多方反馈与评价,因此,平台经济下“网约劳工”的劳动过程与交往过程具有高度的复合性。网络化时代平台经济拓展劳动与交往实践的同时,“网约劳工”的劳动与交往过程亦被平台算法规则严密管控,并在算法支配下走向异化。与“网络精英”也部分受制于流量变现下的算法逻辑不同,“网约劳工”的劳动与交往实践几乎完全陷入算法的隐性控制与平台的全面驯化。
“网约劳工”在平台算法支配下遭受劳动与交往层面的双重隐性控制。劳动层面的隐性控制通过劳动时间的弹性化和对自愿劳动意识的驯化达成。网络劳工看似获得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和灵活,但过度竞争迫使他们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于是劳动者只能再以牺牲这一自由和灵活为代价来换取养家糊口的收入[12]1-20。劳动时间的弹性化和自由化掩盖了劳动过程的受控化与平台资本对劳动成果的压榨。此外,隐性控制更体现在“赶工游戏”中“制造同意”的过程。“游戏代表了一种需要,而需要确实是‘支配性利益要求抑制’的社会的产物。这种需要的满足不仅再生产了‘自发的奴役’(同意),也产生了更多的物质财富。”[13]89布若威指出,当工人将劳动过程视为游戏,会自愿提升劳动强度,为自己争取劳动时间以促成超额完成任务。隐秘控制下合作意愿的生产是“网约劳工”反思性与自觉性缺失的异化表征,如网约车司机调查揭示了该群体持有此类工作“挺有意思”“自己是老板,像是在为自己工作”的普遍心态[14];外卖骑手在“接单游戏”中形塑出对超时劳动的认同[15]。在交往层面,一方面劳工为获取“游戏”胜利,通常会在前期与影响“游戏”进度的中间力量(如生产者、代理商)“搞好关系”[16],加剧了劳工在交往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算法运用评价机制再生产出“网约劳工”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由于消费者拥有对“网约劳工”单向赋分评价的权利,评价涉及内容不仅包括准时性、正确性等客观量化指标,还包括态度类的主观测评,而评价结果直接影响“网约劳工”的经济收入,因此他们不得不对消费者“唯命是从”。可见,新时期的算法支配与平台管理实现了对“网约劳工”群体更为全面和隐秘的控制,使其丧失了自觉性与平等性,人与劳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网络化时代得以再生产。
(三)数据生产下的普通网民与自主性减弱
大数据时代普通网民在网络社会中生产的信息数据的商业价值与日俱增。网络技术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交互平台,为人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提供广泛助力,也不断延展人们社会交往的频度与广度,使得人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日益以网络平台为媒介展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在信息时代数据生产驱动力下普通网民的网络信息数据价值被深度开发。网民在网上留下的浏览与消费印记会生成相应数据传送至网络平台,一方面,平台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与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用户群体的全方位数字画像,进而赢得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平台会将部分数据卖给广告媒体,提升广告的精准投放度,借由广告牟利。“对广告而言,预测和分析是十分关键的,每一比特的数据不管多琐碎都拥有潜在的价值。”[17]108互联网平台对网民生产的海量数据进行吸纳,并有效利用其信息数据的商业价值为自身牟利,反观网民非但没有数据收益,还面临隐私暴露风险。但广大网民通常只有同意相关霸王条款允许平台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才能正常使用各类应用程序,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普通网民处于被隐蔽侵权的非对等地位。
马克思认为“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18]73,而网络社会中的网民大众在网络实践中不仅不能占有自身产出的数据收益,甚至还受到监视与管控,导致网民群体的自主性日益减弱。此外,“新信息技术可以让工作任务分散化,同步即时地在互动式通信网络里协调整合,不论是横跨各州大陆,或是在同一栋大楼的不同楼层”[10]320,网络社会即时交互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工作场景中,线上加班成为常态;日益丰富的网络娱乐活动更使“宅”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线下社会交往空间被变相压缩。
最后,数据库优化带动搜索引擎强势发展,改变了个体的思考方式以及群体的讨论与协作习惯。以往没有百度、谷歌等搜索平台辅助,面对问题人们只能通过人际交流结合独立思考做出审慎抉择,因此波兹曼认为在印刷术文明形态中人们的逻辑表达能力更佳[19]63。但网络化时代人们遇到问题更倾向于“拿来主义”,对网络搜索的依赖与碎片化认知会降低主体自主表达与深入思考的能力。总之,数字化时代伴随网络数据商业价值的突显,普通网民日益被对象化为数据生产工具,生产与交往行为也日益依赖网络媒介。无论是被工具化还是对工具的过分依赖都是人自主性减弱的异化表征,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使普通网民陷入新形态下的异化困境。
(四)数字鸿沟分化中的数字难民与数字区隔
网络社会分化与网络社会发展相伴生,数字分化与数字不平等日益显现,形成数字鸿沟下的群体区隔。数字鸿沟指社会中不同群体对互联网的可及性和使用上的差异性产生的不平等,前者指向国家公共政策和基础设施供给,后者源自用户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差异[20]。虽然我国居民用网环境持续得到改善,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仍有24.4%左右的人没有接入互联网,而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61.9%,同时在落实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任务后,47.0%的网民掌握数字化初级技能(如信息搜索、文件传输);仅有27.1%的网民初步掌握数字化中级技能(如加工、处理、利用数字化资源)。(5)数据来源: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l。网络的接入和使用差异正在生成网络化时代的新型不平等,无法接入互联网或数字素养低的群体成为“数字难民”,他们难以跨越网络技术下的数字鸿沟,在网络应用日益频繁的现实生活中遭受新的社会排斥与区隔。
“数字难民”或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无法进入网络社会,或囿于自身生理机能、学习能力等因素限制而成为网络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数字化时代其主体性和自由性受到严重制约。首先表现在该群体与网络社会发生脱嵌,习惯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数字难民”尚未掌握足够的网络化、智能化技能,面对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二维码”,滋生不安与不便,但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为该群体预留足够长的适应时间,在数字化的生活空间中“数字难民”显得无所适从,导致部分群体避免参与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交往实践,在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面前与社会日渐脱节。
此外,“数字难民”遭受歧视与冷漠对待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交往层面,还存在于家庭内部的代际交往之中。网络社会中“年轻人是富裕者,而年老人是匮乏者”[21]238,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亲代与子代间的地位关系在数字化时代得以倒置逆转,无论出于主观忽视或工作繁忙、流动在外等客观原因,子代陪伴与反哺的缺失使数字鸿沟难以弥合。总之,数字社会转型正日益生产着基于数字资质差异而形成的新的不平等,数字区隔是网络化时代社会交往异化的新形态。
“网络精英”“网约劳工”“普通网民”“数字难民”四类群体在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中呈现能动性退化、隐性控制、自主性减弱、数字区隔的异化表征。当下物联网、人工智能、算法运力与大数据技术的迭代更新,技术集成下媒介融合日趋显著,媒介融合进一步增加了网络社会交往异化的复杂性,交往异化的媒介分析视角是对主体分析视角的有力补充。结合网络社会最新进展考察媒介融合下的网络社会交往实践,揭示交往异化的复杂化与深化具有重要价值。
三、媒介融合下的交往原则破坏与异化深化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交往原则对于规范交往行为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运用普遍语用学规范交往行为,以克服交往异化。“一个追求沟通的行为者必须和他的表达一起提出三种有效性要求:所做陈述是真实的;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8]131哈贝马斯强调行动者依据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言语沟通原则达成有效沟通和行为协调是克服交往异化的重要保障。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交往媒介不断拓展并深度融合,导致媒介融合下网络社会交往关系日益复杂化,“真、正、诚”的沟通与交往原则在交往形式与空间扩展中受到新的冲击。
媒介融合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22]。早期研究关注多元媒介如何实现整合升级,后期日益强调媒介融合从业态革新转向引发社会形态变革的重要性[23]。总之,网络技术发展使媒介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然而人机融合、虚实融合、产消融合引发交往主体、交往空间与交往体验的深刻变迁,对规范交往行为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原则构成新的挑战。
(一)人机融合:交往主体拓展下的真实性遮蔽
媒介融合引发最为实质的变革在于媒介不再是工具,而是人的延伸。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感觉和感官的扩展与延伸[24]87,强调媒介能够扩大人本身的机能,当下的人机融合更使机器由延展人感官机能的中介变为交往主体,ChatGPT的出现引发更深层的人机关系大讨论。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于2022年11月推出聊天机器人程序,它是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虽然智能AI生成的虚拟角色早已进驻大众日常生活,如SIRI、天猫精灵、小爱同学等通过问答模式实现人机互动,但早期聊天机器人难以跳出设定好的模式化回答框架,并且对人类语言多样化使用习惯不够熟悉,往往带来人机交互中的违和感与无效性。而ChatGPT基于大数据和人类实时反馈进行强化学习,对语言模型进行调整,使得自身的生成能力与交互能力大大提升,逐步模糊人与机器的边界。在生成能力层面,ChatGPT依托大数据技术收集语料信息进行深度学习,不仅能够根据用户偏好给予回答,还能通过回溯过往数据在合理逻辑下递进对话[25]。此外,ChatGPT卓越性能还表现在聊天过程中能兼顾用户的情感需求,利用共情拉近距离,通过适当情感回应让用户体会感性交往的乐趣。富有逻辑的递进对话和包含情感的交流过程依赖人机交互能力的提升,机器已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和对象化产品,而是具有生成与学习能力的交往主体。
人机融合的深度发展把人从简单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但自其勃兴以来的隐忧亦有增无减。在社会交往层面,ChatGPT的出现使得交往主体得以拓展,传统交往行为发生在真实主体之间,而ChatGPT的出现增添了人机交往的新维度,交往主体实现延展的同时,也冲击着社会交往的真实性原则,更易导致交往行为异化。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真实性原则强调“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wahr)陈述(或陈述性内容,该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26]3。而ChatGPT通过拣选语料库中的语言片段输出内容,语料库中的内容源自网络数据收集,海量数据良莠不齐,既包括真实信息,也包括虚假数据,导致ChatGPT信息供给的真假杂糅,人们难以形成对于真实性的有效判断。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与犯罪行为将进一步瓦解主体间的交往信任,危害网络社会交往秩序。此外,出色的语言理解与交互能力让ChatGPT不但可以回答用户问题,还能给予恰当的情感回应,但长期沉溺于人机交流情境,势必挤压主体间真实交往实践,引发现实社会原子化的加剧。
(二)虚实融合:交往空间分化下的正当性困惑
媒介融合下元宇宙的生成在拓展交往空间的同时也引发空间分化下的交往行为异化。2021年“元宇宙”(Metaverse)一词随着扎克伯格宣布将Facebook改名为Meta席卷全球。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元宇宙在中国未来的潜在市场规模为8万亿美元。(6)资料来源:《摩根士丹利:中国互联网行业报告——元宇宙!下一代移动互联网?》,https://www.sgpjbg.com/info/30546.html。元宇宙是资本驱动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网络及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电子游戏技术融合打造的全新交往空间,引发网络社会交往空间的进一步分化。早期网络社会交往存在“线下”与“线上”两种交往方式,“线下”表现为在场交往的面对面互动,“线上”则是主体依托即时通讯设备开展的缺场交往,线下互动具有直接真实性,线上互动具有间接虚拟性。而在元宇宙中的社会交往有别于早期“线上”与“线下”交往空间的简单分割,交往主体可以借由“分身”,以可“感知”的方式进入网络世界,即“虚拟现实造就知觉在场,数字孪生成就分身在场”[27]。数字孪生通过渲染技术对现实世界进行拟真呈现,“针对物理世界中的物体,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建构一个在数字世界中一模一样的实体”[28]3-4,打造更具真实体验感的虚拟空间。行动者的数字“分身”可突破传统线下“具身”交往的时空有限性,赋予交往更大的自由性与便捷性,同时通过穿戴体感设备带来与“具身”交往一样的直观感知和沉浸式体验。元宇宙使虚拟交往空间与现实交往空间同生,个体的数字“分身”与肉体“具身”共在,体现了网络社会交往虚实空间的深度融合,这对传统社会交往的正当性原则发起严峻挑战。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正当性原则指出“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richtig)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26]。元宇宙虚实相融、“具身”与“分身”共同在场的多重交往实践会危及主体对于交往正当性原则的认定。一方面,虚实融合特性使得现实空间中的主体交往被挤压,衍生拟像世界规则对真实世界规则的挑战;另一方面,符号虚拟性与感知真实性的融合,以及虚实角色在不同空间的穿梭与杂糅也会冲击交往主体在不同场景下的规范认知与判断。总之,虚实混合空间的交往规范与交往秩序尚未有效建立,人们在虚实边界间切换与跳跃,不仅容易将原有隐私侵犯、网络暴力等交往失序行为投射到虚拟场景中,还会生成以“分身”交往挤压甚至替代“具身”交往的新型网络社会交往异化。
(三)产消融合:交往功利化中的真诚性偃息
产消合一过程反映了新兴网络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融合过程,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的融合深刻影响人们的交往诉求与交往体验。产消合一概念最早由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出,“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只要我们既生产又消费我们自己的产品时,我们就是在进行‘产消合一’”[29]151,强调生产与消费相互融合的状态。但最初这一概念因互联网和媒介发展的有限性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伴随网络信息技术引发影视娱乐产业变革,产消融合实践得以迅速拓展,产消合一理念才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2019年Netflix推出的《黑镜:潘达斯奈基》,采用多重叙事结构在电影领域将产消融合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的命运交给观众,观众的不同选择推动剧情的不同走向,观众在深度互动体验中完成观影消费过程和参与电影生产过程,最终影片收获良好的票房与口碑。(7)资料来源:《自由意志是假象——黑镜:潘达斯奈基》,https://www.sohu.com/a/595583290_120112342。2018年由Quantic Dream制作的人工智能题材互动游戏——《底特律:变人》在SONY PS4平台上线,2023年1月,官方宣布该作全球销量已突破800万。(8)资料来源:《官方宣布底特律变人全球销量已突破800万》,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418167501466827&wfr=spider&for=pc。游戏背景设定在2038年的虚拟底特律城,玩家根据章节分别扮演三位主角,并在不同选择中决定游戏结局,华丽的游戏画面及扣人心弦的人物命运选择,为玩家提供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9)资料来源:《底特律化身为人Quantic制作的人工智能题材互动电影游戏》,https://baike.baidu.com/item/底特律%EF%BC%9A化身为人/50876568?fr=ge_ala。产消融合在影视娱乐业形成破竹发展之势。
产消融合一方面依赖资本推进生产与消费过程变革,将消费者前置,通过吸引消费者参与内容生产,提升消费积极性的同时创新生产方式,推动资本增殖。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是产消融合模式可持续的保障。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与加入生产环节的热情,以及生产者对生产边界的开放和观众欲求的捕捉均依赖强大的网络技术支撑,缺少优质的“代入感”或产生共同生产的“违和感”都会使产消融合不可持续。最后,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将产消融合延展到生活与交往领域。抖音、快手、小红书的迅猛发展将生产与消费的合一过程推向深化,每个消费者都是生产者的时代已然来临,日常生活与交往实践在自媒体和短视频时代从后台走向前台。因此,资本和网络技术共同推进了产消融合模式的发展,而生产过程对消费者的依赖只是新经济形态制造的消费者地位提升幻象。在生产与消费的融合过程中,商品化逻辑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植入生活世界,导致交往诉求日益功利化,真诚性交往体验日益稀缺化。
主体兼顾生产与消费角色,会冲击交往的真诚性原则,致使网络社会交往陷入市场化、商品化困境。近年来产消融合机制推动的偶像养成类节目掀起全民娱乐高潮,偶像选手们的排名、有效播出时长要依靠观众的“生产”而决定,观众为送自己喜欢的选手“出道”在线上为选手投票、线下购买指定周边商品为选手积攒人气,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的消费与偶像生产实践交织融合在一起。社会交往的真诚性原则要求“言说者必须真诚地(wahrhaftig)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能信任他)”[26]。真诚性表现为言者真诚表达内心世界,以求与听者的情感融合和建立信任关系。但在现实中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支持被商品化、市场化,真诚被功利化目的侵袭。粉丝在追星过程中将偶像认定为“家人”进行经济与情感投入,而部分偶像与平台利用粉丝达成个人出道与资本增殖布局,感性交往受资本控制、真诚被商业化利用,因此出现大量“偶像失格”的“饭圈乱象”。总之,产消融合将系统的策略行为植入生活和交往领域,不断侵袭交往的真诚性原则,进一步加剧网络社会的交往异化。
人机融合、虚实融合、产消融合是媒介融合深化的当代表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有助于加深对新时期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社会交往异化现象的理解。媒介深度融合在拓展交往形态与交往空间的同时,也破坏着社会交往合理化所依赖的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原则,致使网络社会的交往异化日益深化。
四、结 语
网络社会的崛起带来交往空间的拓展,但网络交往实践的依附性、叠域性与区隔性特征也逐步显现。不同类型网络主体在不同网络场景中被分类规训,并呈现不同的异化特征,被流量裹挟的“网络精英”、被算法控制的“网约劳工”、被锁定在数据生产和监控中的“普通网民”,以及被数字鸿沟分割的“数字难民”从不同维度透视出网络化新时期异化的全面延展。同时,媒介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延展了异化的范围和深度。人机交互的主体拓展、虚实融合的交往空间、产消合一的商业运营冲击社会交往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原则,致使交往关系陷入新的异化困局。网络社会的技术更迭日新月异,在异化理论的演进中审视当下网络社会交往实践,对网络社会交往异化展开批判,反思网络化新时期主体规训与媒介融合下的异化拓展,对推进异化理论、丰富网络社会研究,以及促进我国数字社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