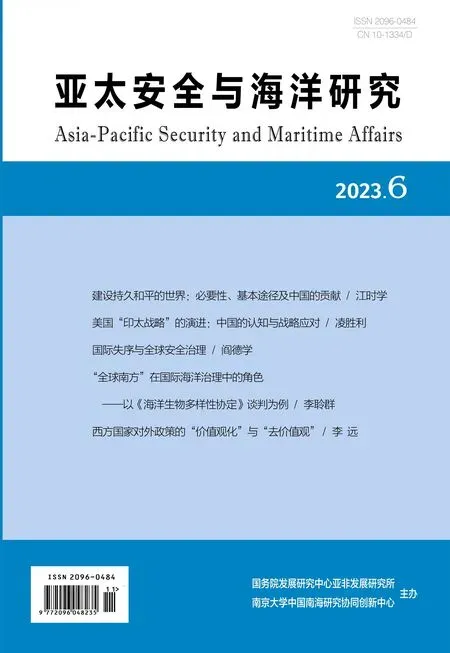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与“去价值观”
2023-12-22李远
李 远
内容提要: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之间变化不定的相关性,是西方国际关系实践中充满争议的现象。从广义的价值观理解来看,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扩张,而非传播中性理念。通过构建以战略利益、价值偏好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并提出基于“字典序偏好”的价值观对外政策决策模型,可以解释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决定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国家决策中,涉及国家生存的战略利益是凌驾于价值偏好目标之上的考虑,而安全目标也是优于经济目标的考虑。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的案例说明,由国际结构决定的“战略利益”,决定了对外政策变化的总体方向和浮动空间,而“价值偏好”决定了价值观目标是否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之间变化不定的相关性,是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实践中充满争议的现象。西方国家长期以“民主灯塔”“人权法官”等自居,在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行其所谓“普遍价值”时,往往以“价值观”为由,对他国进行干预,然而有时又会做出违背其极力宣扬的“价值观”的举动。如何解释西方国家所谓“价值观”要求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一致和偏差,是对外政策分析的重要议题。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价值观化”或“去价值观”?
近年来,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攻势不断加强。拜登执政后,美国大力推进构建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价值观同盟”,部分欧洲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德国“红绿灯联盟”政府上任后的种种迹象,也显示其对外政策有“价值观化”的倾向。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分别以全球体系和欧洲体系的主导大国美国和德国为例,对于研判目前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于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与“去价值观”,现有研究往往偏重问题的一侧。现实主义针对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有尖锐批评,因为价值观所提供的政策指向常是模糊甚至矛盾的,且盲目追求价值观目标易引发灾难性后果,故认为私人领域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应适用于公共领域的政策决定。(1)George F. Kennan,“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Affairs,Vol.64,No.2,1985,pp.205-218.从这一立场出发,研究者自然以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作为待解释的反常现象。但也有学者主张,应正视理念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事实上,在放大到足够的时间尺度后,可以观察到“暴力的价值观输出”其实是人类历史中常见的现象。(2)John M. Owen,TheClashofIdeasinWorldPolitics:TransnationalNetworks,States,andRegimeChange,1510-201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即使关注当代,也确有研究表明,二战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能够影响国家的结盟行为。(3)Brian Lai and Dan Reiter,“Democracy,Political Similarity,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1816-1992,” 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44,No.2,2000,pp.203-227.对于这类研究者,对外政策的“去价值观”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是待解之谜。但这两种研究问题的提法,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需要兼顾二者关切。
本文将在“理性政策”范式(4)“理性政策”是对外政策分析中广为应用的范式。一般假设如下:(1)政策是国家或政府的选择;(2)国家或政府是单一理性决策者;(3)政策被选中以作为对特定战略问题的回应;(4)政策选择是静态的;(5)政策是理性的选择,涉及国家目标、政策选项、选项后果和理性选择的过程。参见:Graham T.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63,No.3,1969,pp.689-718。有学者基于心理学研究成果,质疑理性选择的假设是否过强,安德鲁·法卡斯(Andrew Farkas)为此提供了一个演化模型以作辩护:人类个体的决策行为或许不够理性,但决策的制度过程会使集体决定比个体决定更理性。参见:Andrew Farkas,“Evolutionary Models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3,1996,pp.343-361。下为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价值观化”或“去价值观”提供解释。首先将引入价值观的广义理解,指出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扩张,而非传播中性理念。其次,为解释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提出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指出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即战略利益、价值偏好。最后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说明上述变量何以驱动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
一、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非中性的意识形态
西方学界在研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问题时,经常不自觉地假设一种“中性理念说”,即认为西方国家主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是被普遍接受的中性理念,故其价值观对外政策是理所当然、天然合法的“布道”行为。这种误导性的假设常见于:当研究者试图解释国家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时,倾向于为西方国家提出“理念性解释”,即归因于政策制定者的“自由主义偏好”,而为非西方国家提出“物质性解释”,即归因于统治者延续政权的动机。(5)Nathan Levine,“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Inevitable—Like It or Not,” ForeignPolicy,August 6,2021,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8/06/china-us-liberalism-democracy-authoritarianism-ideology-competition-cold-war[2023-08-03].这种做法暗含的认识是,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是因深信“自由民主”理念,故试图将之传播,而非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实际上并不相信本国的意识形态,只是为了保全政权而参与意识形态竞争,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只有西方自由民主理念是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上,这种“中性理念说”并不成立。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无外乎是一种非中性的意识形态,以下引入广义的价值观理解以证此论。
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宜做如下界定:首先,价值观属于道义的范畴,是关乎是非对错、正邪善恶的价值规范,具有普适性、公正性和自愿执行性,这一点区别于伦理。(6)Mark R. Amstutz,InternationalEthics:Concepts,Theories,andCasesinGlobalPolitics,Washington,DC: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8,p.7.其次,价值观是政治道义,适用于共同体(如国家、区域、国际社会等)的政治生活,而非私人关系或行为,这一点区别于个人道义。(7)Ibid.,p.8.共同体有大小之分,大共同体可能是几个小共同体的集合,如东北亚共同体可被视为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和蒙古六个国家共同体的集合,东北亚各国家共同体之间的事务其实是东北亚共同体的内部事务。此外,由于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是国家共同体,故不妨对价值观二分处理:一是管理国家间事务的国际价值规范(如国家应以何种方式处理国际争端),二是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国内价值规范(如国家应以何种原则对待公民)。(8)此处同于康德的“国家律”(law of states)和“世界公民律”(world-citizen’s law)。前者即管理国家行为的规则,以明确的准则规定出国际关系中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后者是基于人类个体作为世界共同体成员的平等身份,规定特定权利为任何国家内任何个人不可分割之所有,不可被任何国家或个人侵犯。参见:Robert McElroy, MoralityandAmericanForeignPolicy:TheRoleofEthicsinInternationalAffai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 31-33。最后,价值观应有“普遍价值观”和“狭隘价值观”之分。“普遍”与“狭隘”是相对而言的:共同体越小,价值观受众越有限,则价值观的形成越可能受到地方上的历史、宗教、文化等特殊背景的影响,价值观的内容就表现得越具象、越复杂、越特殊,即价值观越狭隘;相反,共同体越大,价值观受众越广泛,则价值观的形成越可能脱离于地方上的特殊背景,价值观的内容就表现得越抽象、越简洁、越宽广,即价值观越普遍。(9)此处借鉴了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对“大道义”和“小道义”的探讨。参见:Michael Walzer,ThickandThin:MoralArgumentatHomeandAbroad,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4,pp.1-19。
从来源上说,大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脱胎于小共同体的狭隘价值观,代表了狭隘价值观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也可以说是多个小共同体间的共同价值观。具体来说,如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一种普遍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以高度抽象、简洁、普遍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项理念为内容,脱胎于中国在实践中长期坚持的“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价值原则,凝聚了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10)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5版。很难想象这12个字会在任何一个国家被公开反对,即共同体很少在普遍价值观上发生冲突。但若进一步说,何为和平发展,何为公平正义,何为民主自由,则各个国家很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共同体间的价值观冲突往往发生在这一层次。
共同体有以自身的狭隘价值观为参考系,要求其他共同体接受或遵守这套价值观的倾向,通常做法是将客观上受众有限的狭隘价值观误认为或有意描绘为广泛接受的普遍价值观。(11)“为了把全球合法性赋予那些合乎西方国家利益的行为,‘世界共同体’成了‘自由世界’的委婉表达。”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Affairs,Vol. 72,No. 3,1993,pp.22-49。如果实施者掌握足够强大的话语权,那么这种“泛化”操作可以是极具欺骗性的。冷战后西方对国际话语的主导即是实例,其大肆鼓吹自由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胜利,垄断对民主自由的阐释权,这种将狭隘价值观伪装为普遍价值观的操作,给予受众极大的错觉。(12)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Interest,No.16,1989,pp.3-18.
从广义的价值观理解来看,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只是一种狭隘价值观,是非中性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扩张并不具备其所宣扬的合法性。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应对“中性理念说”有所警惕,避免在理论构建时掉入话语的陷阱。
二、理解价值观对外政策的解释变量
理解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需要对两个问题做出回答:第一,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为什么需要价值观目标?第二,传统的物质性利益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本文试图提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以回答上述问题。这里借鉴了德国学者埃利亚斯·戈兹(Elias Götz)对“干预变量”的见解,即结构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变量共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政策,但结构变量是决策的主导因素,而单位变量仅对结构变量的解释力起补充作用,故称为“补充性干预变量”。(13)Elias Götz,“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ies,Intervening Variables,and Paradigmatic Boundaries,” ForeignPolicyAnalysis,Vol.17,No.2,2021,pp.1-13.这一见解为本文识别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解释变量提供了一般指导。具体而言,由国际结构决定的“战略利益”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决定了对外政策变化的总体方向和浮动空间,而“价值偏好”是必要的补充性干预变量,决定了价值观目标是否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一)战略利益
战略利益通常是对外政策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无论“价值观化”还是“去价值观”。一个基本逻辑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以(物质性)生存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战略利益由此衍生。其中,有两点关键假设:第一,无政府是国际结构的主要特征,国家自负生死存亡之责,对外政策需要遵循国际结构的“奖惩规则”,否则将使国家面临危险的境地。第二,国家天然追求生存,而安全与繁荣是生存下最重要的两项子目标。在较短的时间维度上,安全近乎为生存,主要指“领土完整与国内政治秩序自主”。(14)John J. Mearsheimer,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New York:W. W. Norton &Company,2001,p.26.而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上,国家追求的不只是简单的“延续”,而是一种更长久的、可持续的生存,这要求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因为繁荣通常意味着未来有更多财富、人口、科技等社会经济资源可供转化为“有效权力”。(15)Ibid.,p.46.因此,至少在有限的程度上,对外政策可被看作战略利益(主要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表达。
战略利益的政策指向和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密切相关。战略关系大致可分为合作性、竞争性和中性三种类型。一般而言,战略关系的合作性越强,则国家越倾向于保持或改进这种互利状态,有利于合作性的政策更可能被施行,而有损于合作性的政策则更可能被回避,如美国长期淡化和埃及、以色列、沙特等中东战略伙伴的价值观差异;战略关系的竞争性越强,则国家越倾向于保持或强化竞争中的优势,有利于竞争地位的政策更可能被施行,而不利于竞争地位的政策更可能被回避,如欧盟试图将对外商贸与价值观捆绑以实行隐性贸易保护;(16)参见程卫东:《欧盟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人民论坛》2021年第34期,第92—96页。战略关系越中性,则其中的利益指向越不明确,战略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越不显著。
(二)价值偏好
国家的价值偏好是价值观目标的一种来源,是影响“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的一种补充性干预变量。价值观塑造国家政策偏好的形成,在默认只基于物质性因素的“偏好集”中增加理念性因素,由此国家利益中兼有了物质性利益(如确保国家生存)和理念性利益(如维护“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此,价值观以理念性利益的形式成为对外政策的内在目标,如现实主义模型中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权力最大化等物质性内在目标。国家角色论和民主和平新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者,如卡莱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主张政策制定者对国家角色的理解是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特殊的理解导致特殊的目标和行为;(17)Kalevi J. 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14,No.3,1970,pp.233-309.后者,如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W. Doyle)主张自由主义理念外化为西方国家的社会主流意识和国家制度形态,进而导致西方国家在对待同类和异己时有不同的偏好。(18)Michael W. 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PublicAffairs,Vol.12,No.3,1983,pp. 205-235;Michael W. 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Part 2,” Philosophy&PublicAffairs,Vol.12,No.4,1983,pp.323-353.而后安德鲁·莫拉夫西克(Andrew Moravcsik)就自由主义理论有关国家偏好的见解做了重要的范式整合工作,指出影响国家偏好的三类因素:一是社会价值观的分布,二是社会行为体的博弈,三是国内制度和社会群体的关系。(19)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1,No.4,1997,pp.513-553.
广义上看,价值偏好使得价值观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狭义上看,价值偏好使得价值观与战略利益“同台竞技”,二者或为竞争关系,即国家需在其间做权衡取舍,或为合作关系,即二者指向了相近的政策选项。逻辑上说,对普遍价值观的偏好代表了人类共同价值在国家决策中的内化,实际上是国际关系进步的体现,但对狭隘价值观的偏好则更近乎一种偏见,容易诱使国家泛化自身的狭隘价值观,甚至引发国家间的价值观冲突。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对外政策常为后者,标榜“民主”“人权”“自由”等所谓普遍价值,搞意识形态划线的国家阵营。(20)参见王文、贾晋京、胡倩榕:《如何化解西方价值观外交中的“词汇陷阱”》,《对外传播》2021年第12期,第56—59页。
价值偏好的影响力与偏好强度应是正相关的。作为目标的理念性利益相比其他利益越是重要,即偏好越强,则相应的“价值观化”越可能发生。一般而言,价值偏好强度受到文化背景、历史经历、社会意识、执政者价值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不过,也有研究质疑价值偏好在对外政策中的实际作用有限。(21)Arman Grigoryan,“Selective Wilsonianism:Material Interests and the West’s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44,No.4,2020,pp.158-200.因此,价值偏好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应被审慎对待,既不该过度推崇,也不应完全忽视。
除以上两种因素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也能够对价值观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比如,决策者追求国内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动机是价值观目标的另一种来源。当国内合法性较弱(如国内舆论对政府高度不满)或者国际声誉较差时,对外政策更可能“价值观化”。但为了简化分析和便于构建模型,本文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战略利益”和“价值偏好”这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上。
综上所述,“战略利益”和“价值偏好”是影响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的两个主要解释变量(如图1所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生存,由此衍生出物质性的战略利益是结构解释变量,国家的价值偏好是补充性干预变量,会影响政策选项的具体成形。除了这两个主要变量,还在一些其他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特定政策选项得以输出为“价值观化”或“去价值观”的对外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本节虽然对影响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变量进行了分析,但却无法说明这些变量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影响政策制定的,下文将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

图1 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的分析框架

图2 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决策模型
三、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决策行为模式
解释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阐明其现实主义基础,即在何种条件下西方国家会将“价值观”付诸实践。上文对价值观对外政策的解释变量进行了分析,但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依然是一个“黑箱”,下文提出基于“字典序偏好”的价值观对外政策决策模型,以期对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黑箱”进行学理层面的推断。当然,此处提出的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决策模型并不必视为一个经过严格检验的一般理论,而可以视为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者一种理论视角,从而可以对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与“去价值观”提供一种行为解释。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价值观对外政策中的偏好序列,主要涉及国家生存目标(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等战略利益)和价值偏好之间的排序。在生存目标内部,仅就性质而言,国家安全是优先于经济繁荣的目标。(22)参见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2页。其基本逻辑在于,远期生存以近期生存为前提,福祉增加以组织延续为前提。在利益量和利益紧迫性接近的条件下,国家决策中安全目标是优于经济目标的考虑。而在生存和价值偏好之间,确保生存是国家的必然义务,但推行价值观只是国家的可能选项。(23)“政府是代理人,而非委托人,其主要义务在于对其所代表的国家社会之利益负责,而非听从于个人的道义冲动……当政府肩负起统治的责任时,一些假设已经暗含其中,即国家主权、政治自主、军事安全、人民福祉务必得到保障。”参见:George Kennan,“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Affairs,Vol.64,No.2,1985,pp.205-218。因此,只要国家生存的不确定性和安全担忧继续存在,生存目标终究是凌驾于价值偏好目标之上的考虑。基于上述假设,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目标偏好符合一种“字典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s)(24)“字典序偏好”的概念来源于决策理论中对于理性个体选择行为的解释,指的是如果个体的偏好服从一定的序数顺序,一般来说最重要的偏好将会被优先满足,次要的偏好则之后才会被满足。参见叶中行、林建忠编著:《数理金融——资产定价与金融决策理论(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设国家可追求的对外政策X包括生存(s)、价值偏好(v)两个维度。其中,国家的生存目标追求又包括安全(c)、经济(e)两个维度。对任意的对外政策方案x,x′∈X,若x比x′更受偏好,即当国家选择出台对外政策x而非x′时,须符合三点必要条件之一:其一,x较x′更能促进安全目标c;其二,x较x′更能促进经济目标e,而对安全目标c的影响基本无异;其三,x较x′更能促进价值偏好目标v,而对安全目标c和经济目标e的影响基本无异。(25)上文“字典序偏好”的数学表述如下:设国家可追求的对外政策X是n维线性空间Xn中的一个子集,对X中的每两个元素,给定一个偏好关系,记为 ≻,即对任意的对外政策方案x,x′∈X,若x比x′更受偏好,就记作x≻x′;若x比x′更不受偏好,就记作xx′;若认为x和x′效用无差异,就记作x~x′。具体而言,设国家可追求的对外政策X包括生存(s)、价值偏好(v)两个维度,x=(s,v)∈X。其中,国家的生存目标追求又包括安全(c)、经济(e)两个维度,可用集合S表示,s=(c,e)∈S。则国家对外政策的“字典序偏好”为:(1)当且仅当s≻s′,或s~s′且vv′时,满足(s,v)(s′,v′),即xx′;(2)当且仅当c≻c′,或c~c′且ee′时,满足(c,e)(c′,e′),即ss′。据此可知满足xx′的三种情形为:当c≻c′时,则ss′,故xx′(i)当c~c′且e~e′时,则ss′,故xx′(ii)当c~c′且e~e′,且当vv′时,则xx′(iii)以上构成了价值观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基础。
此外,若假设对外政策的制定者是理性的,则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可用下图表示。价值观挑战是整个政策过程的“道义启动键”(26)这里的价值观挑战,是指对于西方国家所谓“价值”的挑战,而正如本文第一节中所分析的,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扩张,而非传播中性理念,因此一些非西方价值观体系的行动也可能被视作挑战。之所以将价值观挑战称为“道义启动键”,是因为如果没有需要解决或可以作为借口的价值观挑战,则西方国家也谈不上要通过对外政策实现什么价值观目标。,国家在外部环境中(客观上能够且主观上愿意)感知到价值观挑战后,产生回应价值观挑战的政策选项,并基于目标偏好和对目标行为体反应的预期,理性评估政策选项的预期结果,即政策若执行将引致的损益状况,最终依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完成决策,将政策选项转化为合适的政策回应。
结合前述“字典序偏好”假设提出的识别标准,我们可以对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决策行为模式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1:如果西方国家追求价值观的政策选项预期将对安全目标产生危害,那么即便将显著促进经济目标,其政策回应也一般为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
推论2:如果西方国家追求价值观的政策选项预期不对安全目标产生危害,但却能显著促进经济目标,那么其政策回应一般为对外政策的“去价值观”。
推论3:如果西方国家追求价值观的政策选项预期不影响近期生存目标(安全和经济),但却能显著促进价值偏好目标,那么其政策回应一般为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
四、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与“去价值观”案例
基于上述框架,下文选取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四个代表性案例。这四个案例分别是:1972—2012年美国对华政策、2015年前后德国对埃及政策、2013年至今美国对华政策和2021年以来德国对华政策。案例选择考虑了探索因果的案例分析之需,前两个与后两个案例中的对外政策分别出现鲜明的 “去价值观”和“价值观化”,保证了被解释变量取值的差异分布,合乎验证因果的需要。此外,对美国和德国案例的选择也考虑了案例本身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美国和德国分别是全球体系和欧洲体系的主导大国,研究其对外政策决策规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美国和德国是西方国家中价值偏好较强的国家,美国在冷战后奉行了多年的“自由主义霸权”政策,而德国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后现代或后民族国家”(27)参见熊炜、姜昊:《“价值观外交”: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1期,第105—124页。,这两个国家均有通过对外政策实现其价值观目标的动机。
(一)对外政策的“去价值观”
1.案例:美国对华政策的“去价值观”
冷战开启后的20余年中,美国对华政策充斥着意识形态敌意与偏见。然而,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至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以前,价值观问题淡出了美中关系议程。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中美秉承“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意识形态因素在两国关系中几乎销声匿迹。(28)Anne F. Thurston,“EngagingChina:FiftyYearsofSino-AmericanRelations,” in Anne F. Thurston eds.,Engaging China: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1,p.19.90年代,价值观差异一度困扰两国关系,但当时的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顶住了国会的压力,没有改变对华接触的基本方针。此后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也持续扩大和深化对华接触。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内部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异议并未消失,但务实接触始终主导着美国对华政策。(29)Thomas Fingar,“The Logic and Efficacy of Engagement:Objectives,Assumptions,and Impacts,” in Anne F. Thurston eds.,EngagingChina:FiftyYearsofSino-American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1,p.45.
中美安全关系的合作性转向,是美国对华政策“去价值观”的主要原因。冷战伊始至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美苏冷战格局的出现,中国采取对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中美长期处于军事对抗状态。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出现转机。70年代,尼克松政府遵循现实主义的均势逻辑,开始接触中国,希望联中抗苏。(30)Thomas Fingar,“The Logic and Efficacy of Engagement:Objectives,Assumptions,and Impacts,” pp.33-34.此后,随着中美建交,两国的安全关系也逐渐转向合作性。冷战结束后,中美不再面临苏联这一共同威胁,但90年代的国际环境依旧充斥着混乱、灾难与不确定性。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走向何方尚未可知,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3年索马里地方军阀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爆发冲突,1994年朝鲜半岛爆发核危机,巴尔干半岛上的大小内战更是持续了十年之久。因此,美国审慎维持了与中国的合作性安全关系。(31)Ibid.,p.42.2001年小布什上任时已对华有所疑虑,他在竞选时曾表示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32)参见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6—130页。但随后的“9·11”事件,让反恐战争成了美国安全议程中最首要的关切,极大转移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关注,这使得其任内和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仍以务实合作为主。(33)Thomas Fingar,“The Logic and Efficacy of Engagement:Objectives,Assumptions,and Impacts,” p.46;Aiden Warren and Adam Bartley, U.S.ForeignPolicyandChina:SecurityChallengesDuringtheBush,Obama,andTrumpAdministrations,Lond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1,pp.77-80.
中美合作性经济关系的建立,更加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去价值观”。尼克松访华后,中美经济关系逐渐解冻。1979年《中美贸易协定》签署后,中美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幅放宽对华技术转让,标志着美国对华全面经济接触的开始。(34)参见李巍:《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外交评论》2019年第5期,第54—80页。90年代,中美陷入了短暂的最惠国待遇之争。1993年5月,克林顿签署行政令,将1994年7月以后的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价值观条件挂钩,此举引起了美国商界、联邦经济部门和国会中贸易派议员的极大不满。当时,这些经济界人士对美中经济关系前景抱有极高的期望,担心价值观冲突会损害经济利益,于是对克林顿政府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游说活动,最终迫使克林顿放弃了价值观条件。此后,美中经济关系正常化成为美国国内共识。而后直至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中美经济关系不断良性发展,虽不乏摩擦,但总能以对话形式解决。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对华的价值观偏好逐渐趋于温和,美国政界对美中价值观差异的主流看法是,在长期的接触和互动中,中国会自然发生政治改革,最终成为美国主导秩序下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35)Aaron L.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W.W.Norton &Company,2011,pp.100-116.美国政治精英的这种共识,也使得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干扰长期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2.案例:德国对埃政策的“去价值观”
2011年中东变局后的德国对埃及政策一度有浓厚的价值观色彩。2013年7月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推翻,8月其支持者与军方发生流血冲突,随后欧埃关系迅速恶化,对埃大部分援助、对话均被暂停。德国指责埃及军方的做法是“民主倒退”,对军方为缓和关系所做努力视而不见,多次拒绝军人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的访问请求。
2015年巴黎恐袭案和欧洲难民潮后,德国对埃政策开启“去价值观”进程。同年3月,德国经济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代表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邀请塞西访德,背弃了此前“议会选举作为国事访问之前提”的说辞。5月,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到访开罗,强调德埃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中东稳定、遏制非法移民上的共同利益。6月,默克尔在柏林会见了塞西及其代表团,其间西门子公司与埃及政府签署了价值80亿欧元的合同,一举成为埃及能源市场的最大供应商。2016年7月,德埃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建立安全合作的制度平台。2017年3月,默克尔到访埃及,再次强调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的紧迫性。同年7月,德埃就移民问题达成合作协议。这一阶段,管控非法移民、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中东北非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塑造德(欧)埃关系的四大议题,价值观的地位显著下降。(36)参见钱磊:《道义还是利益:中东变局以来德国埃及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德国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32页;Adel Abdel Ghafar,“EU-Egypt Relations:The Delicate Balance of Economic,Security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Adel Abdel Ghafar,ed.,TheEuropeanUnionandNorthAfrica:ProspectsandChallenges,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9,pp.149-172。
德埃安全关系的合作性转向,是德国对埃政策“去价值观”最主要的原因。恐怖袭击和难民危机助推了这一转向。中东变局后,德国短暂忽视了埃及在地区安全上的作用。2014年后,欧洲反恐形势趋于严峻,2015年1月《查理周刊》总部遇袭,同年11月的巴黎恐袭成为法国战后最严重的一次恐袭事件,2016年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再度发生爆炸案。(37)参见周秋君:《恐怖主义在欧洲发展的新态势及其原因分析》,《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29—37页。另一方面,欧洲难民压力也持续升高。2015年4月,地中海三起重大难民沉船事故造成两万多人丧生,欧洲爆发难民危机。
这一背景下,埃及在管控非法移民和缓解难民压力上的价值凸显。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直言:“德国的安全始于埃及的海陆边境。”(38)Hanan Fayed,“New German FM sets human rights as basis for ties,Egypt highlights role in curbing illegal immigration,terrorism,” EgyptToday,February 12,2022,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1/112827/New-German-FM-sets-human-rights-as-basis-for-ties[2023-08-03].2016年起,埃及强化了对北部边境的管理,意在向欧洲证明:埃及是有能力缓解欧洲移民压力的。(39)Jan Claudius Völkel,“Fanning fears,winning praise:Egypt’s smart play on Europe’s apprehension of more undocumented immigration,” MediterraneanPolitics,Vol. 27,No.2,2020,p. 183.同年,埃及推出《反走私法》,认定非法移民是受害者而非罪犯,只有走私犯需要接受惩罚。欧盟对此大为赞赏,因为如果埃及能够更加人道地处置难民,那么其境内难民可能更愿意留在原处,而不是冒险穿越地中海进入欧洲。埃及以《反走私法》向欧洲传递一种信号,即埃及是欧洲应对非法移民的可靠伙伴,但欧洲需要向埃及回馈资金及其他支持。(40)Ibid.,pp.179,185.2022年2月,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访问埃及,当谈及德埃合作的“人权基础”时,埃及外长萨迈赫·舒克里(Sameh Shoukry)以“埃及在移民管控和反恐打击中所做的重大贡献”作为回应。(41)Hanan Fayed,“New German FM sets human rights as basis for ties,Egypt highlights role in curbing illegal immigration,terrorism,”EgyptToday,February 12,2022,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1/112827/New-German-FM-sets-human-rights-as-basis-for-ties[2023-08-03].事实的确如此。正是埃及军队的管控,使得2016年9月以后再无非法移民船只驶离埃及海岸,这也使得德埃价值观矛盾难以超出温和批评、象征表态的范畴。
经济关系的合作性发展,是德国对埃政策“去价值观”的另一重要原因。集中体现在军火贸易。2010—2015年间,德国政府仅授权了1.6亿欧元的对埃武器出口。(42)Christian Achrainer,“Germany’s Problematic Billion Euro Weapons Deals with Egypt,” InternationalePolitikQuarterly,January 12,2022,https://ip-quarterly.com/en/germanys-problematic-billion-euro-weapons-deals-egypt[2023-08-03].然而,2016年埃及一跃成为德国武器的第四大接受国(3.99亿欧元),此后这一排名几乎年年攀升,2020年时已位居第二,2021年德国对埃武器出口接近50亿欧元,此前单个国家单年获批的最大额度是17.8亿欧元。(43)Ibid.来自埃及的巨额订单,使得压制价值观议题的“热度”有利可图。已有研究表明,德国在“主要常规武器”(MCW)的出口中并未对所谓“非民主国家”有差异对待。(44)Hendrik Platte and Dirk Leuffen,“German Arms Exports:Between Normative Aspirations and Political Reality,” GermanPolitics,Vol. 25,No. 4,2016,pp. 561-580.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更是指出,德国近30年来系统性地违反着自己的武器出口规定,致使德国的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向战区。(45)参见《研究称德国三十年来一直违反武器出口规定》,搜狐网,2020年7月23日,https://www.sohu.com/a/409231761_313834[2023-08-03]。合作性的经济关系下,务实开展合作、审慎发展关系比再挑起一场“价值观冲突”更为明智。
(二)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化”
1.案例: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观化”
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初现“价值观化”的趋势。中美的价值观矛盾首先集中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试图在南海借价值观之名,将对华接触中的消极成分由被动的“防范”转为更加主动的“规制”。(46)参见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21—37页。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随着美国对华挑起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观化”趋势加剧。2020年2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成立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联盟”,抹黑中国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尤其在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热衷于使用冷战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不仅将美中矛盾上升为制度之争,更是多次联手盟伴在价值观议题上对华施压。2021年12月,美国举办的所谓“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就是典型例子。拜登政府还“尝试扩展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的联盟体系,寻求以较低成本改善同盟友的关系,争取更多盟友参与制衡中国”(47)参见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期,第11—17页。。
中美安全关系的竞争性转向,是美国对华政策“价值观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安全疑虑加深,中国的经济腾飞、军事现代化和“有所作为”的新外交战略都让美国感到不安。(48)Aiden Warren and Adam Bartley, U.S.ForeignPolicyandChina:SecurityChallengesDuringtheBush,Obama,andTrumpAdministrations,p.87.这一时期,美国一边积极拓展对华合作,一边通过“施压、对冲和制衡”管控美中的分歧与矛盾,试图在平稳与安全之间找到合适的政策均衡点。(49)Ibid.,p.150.至2015年,美国政界愈发认定中国就是美国霸权地位的威胁,美国对华政策到达了一个“转折点”。(50)David M. Lampton,“The Tipping Point - Can We Amplify What We Have in Common?” Horizons,Summer,2015,No.4,https://www.cirsd.org/files/000/000/000/64/e61868279520fa206781b66b4e54cd1e288d7bef.pdf[2023-08-03].而后的特朗普和拜登时期见证了美国对华政策从“战略接触”到“战略竞争”的根本转换,自小布什政府起长期积聚的对华安全疑虑最终被引爆。2019年3月,美国成立“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历史上美国分别针对苏联和恐怖主义威胁成立过三次“当前危险委员会”,此举意味着“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政界共识。总之,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安全目标逐步调整为“战略竞争”,中美价值观差异也从对华合作的“绊脚石”变为对华竞争的“利器”。
中美经济关系的竞争性转向,是美国对华政策“价值观化”的另一原因。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中美经济关系仍以合作性为主,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称赞“美中合作的范围前所未有”。然而,2017年后,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由经济接触转为经济竞争,对华竞争的策略由最初以关税壁垒为主的“市场战”,逐步调整为以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产业政策和经济外交相配合的“技术战”。(51)参见李巍:《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外交评论》2019年第5期,第54—80页;任星欣、余嘉俊:《持久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外科技打击的策略辨析——日本半导体产业与华为的案例比较》,《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第110—136页;李巍:《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2年第12期,第43—47页;宋国友、张纪腾:《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3期,第2—31页。随着中美经济关系愈发趋于竞争性,过去在中美关系中起“稳定器”作用的美国商界也趋于缄默,一些美国企业开始向美国政府抱怨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甚至将之归因于中国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与美国国内本就敌视中国的某些意识形态团体不谋而合。中美竞争性的经济关系也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观化”打开了空间。
美国的价值观偏好也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观化”。随着中美安全和经济关系趋于竞争性,美国政治精英也开始改变对中国的价值观判断。2022年,拜登入主白宫,其政府对外政策团队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都在价值观议题上表现激进。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是一位有自由干涉倾向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价值观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对利用人权议题打压别国的手段轻车熟路。(52)Anthony Galloway,“Biden’s pick for the next secretary of state is Australia’s choice too,” BrisbaneTimes,November 23,2020,https://www.brisbanetimes.com.au/politics/federal/biden-s-pick-for-the-next-secretary-of-state-is-australia-s-choice-too-20201123-p56h5j.html[2023-08-03].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有类似倾向,主张对华政策的目标在于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环境。(53)“Interview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ake Sullivan,”CNN,November 7,2021,https://transcripts.cnn.com/show/fzgps/date/2021-11-07/segment/01[2023-08-03].
2.案例:德国对华政策的“价值观化”
历史上,德国长期对华执行务实政策。早在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政府时期,已有人质疑德国政府在对华价值观议题上搞“静默外交”,所谓“以商促变”不过是对“重商主义对华政策的道义辩解”。(54)参见国懿:《利益与价值观博弈下的德国对华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79页。此后,为调和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的矛盾诉求,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时期形成了一种“精巧的制度内分工”,一面由总理施罗德充当“孜孜不倦的贸易促进者”,另一面由外长约施卡·菲舍尔(Joseph Fischer)占据“道义高地”低调地提出“价值观批评”。(55)Jorn-Carsten Gottwald,“Business As Usual:Red-Green Policies toward Pacific Asia,” in Hanns W. Maull eds.,Germany’sUncertainPower:ForeignPolicyoftheBerlinRepublic,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p.252.默克尔政府上台后,价值观问题一度成为中德关系发展的阻碍,但2009年以后德国逐渐回归务实路线。(56)参见国懿:《利益与价值观博弈下的德国对华政策》,第227页。2017年,德国兴起新一轮对华“怀疑主义”思潮,认为对华政策未达到“以商促变”的预期。(57)参见赵柯、孙琬璐:《寻找对华新战略——德国转向“新西方”政策?》,载郑春荣主编:《德国发展报告(2018):默克尔4.0时期的德国何去何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64—275页。2021年11月,“红绿灯”三党达成组阁共识:一方面,重申德国的外交、安全与发展政策应基于价值观,强调“与民主伙伴密切合作,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强调德国对华战略是欧盟对华共同政策框架的一部分,沿用欧盟对华“伙伴、竞争者、对手”的三重身份定位处理对华关系。(58)参见《德国对华战略出炉,中德关系怎么走》,新华网,2023年7月17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7/17/c_1212245243.htm[2023-08-03]。总之,近年来德国对华政策出现了“价值观化”的趋势。
乌克兰危机以前,中性的安全关系和日趋竞争性的经济关系是德国对华政策“价值观化”的主要原因。中德关系中没有真正的安全利益冲突,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德分处欧亚大陆两端,这一地理隔阂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力量投送困难”。(59)Stephen M. 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65.所以,即使在中国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也难以对德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长期以来,经济关系是德国对华政策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事实上,早在1972年建交之前,联邦德国就已经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德国一直相信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增长的财富将促进其经济繁荣,因此对中国崛起持相当积极的态度。(60)RafaUlatowski,“German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Strengthening the Liberal Order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Affairs,Vol.98,No.2,2022,pp.383-402.
此外,尽管中德均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却长期保持较高的贸易互补性,这得益于中德间“技术换市场”的共生关系,即德国对华出口资本品,中国用以发展工业,并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廉价消费品,再出口至德国。(61)Hans Kundnani and Jonas Parello-Plesner,“China and Germany:Why the Emerging Special Relationship Matters for Europe,” European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May,2012,https://www.files.ethz.ch/isn/173460/ECFR55_CHINA_GERMANY_BRIEF_AW.pdf[2023-08-03].中国对德国汽车、机械和工程设备不断增长的需求,是过去30年带动德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引擎,甚至帮助德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快速实现“V”型复苏。(62)参见《德国媒体:中国经济为世界复苏进程提供重要驱动力》,央视网,2020年10月21日,http://m.news.cctv.com/2020/10/21/ARTILl87WNXrHWi4qVBZiXwN201021.shtml?spm=C96370.PsikHJQ1ICOX.Em32AuyOHUeL.5[2023-08-03]。
不过,这种基于价值链错位的互补性,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冲突的隐患。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上移,中德经贸关系出现了互补性下降而竞争性上升的趋势,经贸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在下降。(63)参见寇蔻、史世伟:《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国际论坛》2021年第6期,第49—68页。最近十年,德国对华经济疑虑上升,除了抱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开始担心中国企业在德技术并购,警惕德企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德国对华价值观批评的声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抬高的。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德安全关系出现了竞争性转向的迹象。发生在欧洲的战事,提高了传统安全议题在德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而中俄相互合作的战略关系也让中德关系有了安全议题化的可能。目前,德国对华政策更加强调所谓“去风险”。2023年3月,欧盟提出对华“去风险”的概念后,德国在其发布的《德国对华战略》中直接沿用了“去风险”的表述。未来,如果德国对华的安全顾虑加深,中德出现价值观摩擦的可能性将进一步提高。
五、价值观对外政策案例的简要分析
西方国家是否追求价值观的对外政策选项,主要取决于其对安全目标、经济目标、价值观目标的利益最大化综合考量,而其对战略利益的追求是凌驾于对价值观目标追求之上的。通过对2012年前美国对华政策、2015年前后德国对埃政策、2013年后美国对华政策、2021年后德国对华政策四个案例的分析,均对上文的模型推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简化分析,上文对以上案例的分析只聚焦于安全目标、经济目标、价值观目标,而现实世界远比高度抽象的模型复杂得多,学界对以上案例也存在其他不同解释。本文的贡献在于,为解释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决策行为“黑箱”提供了新的学理层面的推断,因此本文对于以上案例的分析也可视为对现有其他解释的一种补充。
首先,在1972—2012年美国对华政策中,中美安全关系的合作性转向为经济关系的发展打开了空间,也压制了价值偏好的影响力,而后合作性经济关系的建立进一步降低了价值观议题的影响力,加之价值偏好趋于温和,最终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去价值观”。
其次,在2015年前后德国对埃政策中,尽管德国对埃及军人政府抱有强烈的价值观敌意,但恐袭威胁和难民压力使得德国和欧洲对埃及有迫切的安全合作需要,而价值观上的沉默是欧洲安全和稳定的必要代价。此外,经济关系的合作性发展更强化了“去价值观”的趋势。
再次,在2013年至今美国对华政策中,以奥巴马第二任期为过渡、特朗普和拜登时期为标志,中美安全关系向竞争性转向,为价值观偏好的表达打开了空间,而前期经济关系的合作性未能阻止这一趋势。随后,经济关系的竞争性转向进一步减少了价值观对外政策的阻力。最终,随着更加激进的价值观偏好形成,美国对华政策急剧“价值观化”。
最后,在2021年以来德国对华政策中,尽管中德价值观差异始终存在,但在安全关系中性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对德国对华政策起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德经济关系的竞争性发展,德国对华政策的价值观色彩正在加深。乌克兰危机让中德安全关系有了竞争性转向的可能,未来德国对华政策的价值观化有进一步加强的可能。
由以上案例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并不是其极力宣扬的“普遍价值”,也并非真心追求民主与和平,而是为了服务本国利益、维护国家霸权的工具。西方国家常常以所谓“价值观”为名,对他国内政横加干涉。但在实际行动上,又一贯“双标”,当符合本国利益时则用,不合则弃,违背其所谓“价值观”理念的案例比比皆是。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和科技霸权,滥用“价值观”的名义打压外国企业,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畅通造成损害。
六、结 语
本文构建了解释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价值观化”和“去价值观”的理论框架,指出影响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价值观化”或“去价值观”的主要变量,一是战略利益(主要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二是价值偏好。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基于“字典序偏好”的价值观对外政策决策模型,指出战略利益终究是凌驾于价值偏好之上的考量,决定西方国家价值观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因此,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绝非其所宣扬的“中性理念”,而是一种精心伪装过的、不断寻求扩张的意识形态。
本文基于广义的价值观理解指出,价值观应有“普遍”与“狭隘”之分:“普遍价值观”通常抽象、简洁、宽广,受众广泛;“狭隘价值观”通常具象、复杂、特殊,受众有限。西方的价值观对外政策无非是将“狭隘价值观”伪装为“普遍价值观”的一种欺骗操作。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普遍价值”的定义不应由某个国家主导,而应尊重各国的多样性,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中国倡导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切实回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期待和共同诉求,为国际社会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可信的价值纽带。
历史上,因价值观的隔阂与误解,曾经引发过很多战争与流血,唯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人类才能找到一条化解冲突与斗争的国家间相处之道,才能确保世界持久和平、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