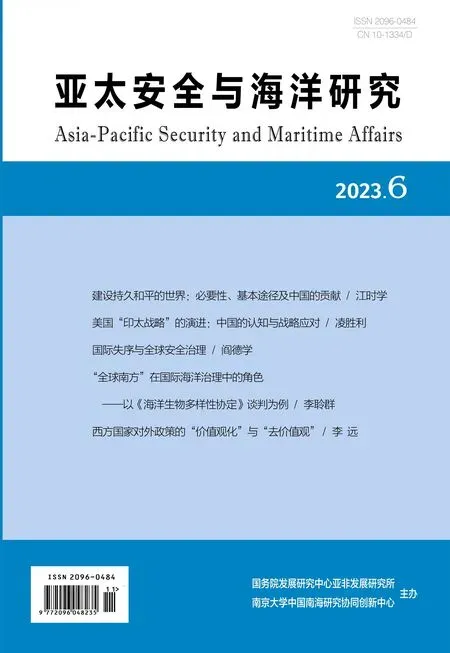“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角色
——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为例
2023-02-18李聆群
李聆群
内容提要:“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根源于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提升。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一直较为活跃。在近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全球南方”团结协作、贡献巨大,并将继续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发挥作用。这是“全球南方”成为世界政治一股重要力量的力证。为继续在未来海洋治理以及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全球南方”要消弭因内部差异和外部势力干扰而产生的离心力,加强区域和国际组织机制的建设和利用,大国也要付诸行动形成合力。作为“全球南方”当然和重要一员的中国,要继续支持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并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的一个前沿热点领域。2023 年 6 月 19 日,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政府间会议再续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2)The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或《协定》。,并决定于2023年9月20日开放签署。在联合国的主导下,从2004年设立针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议题的特设工作组开始,至2023年6月达成最终文本,历时近20年。此期间,会议磋商历经九次特设工作组会议、四次筹备委员会会议、五次政府间谈判会议,受新冠疫情影响,有三年时间转为线上会商。可以说,几经波折,《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才最终得以问世。
在《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来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力量不容忽视。联合国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米格尔·塞尔帕·苏亚雷斯(Miguel de Serpa Suarez)指出:“全球南方为了集体利益努力推动了海洋法的进一步发展。”(3)引自联合国法律事务副秘书长米格尔·塞尔帕·苏亚雷斯于2023年 6 月 28 日在中国青岛举办的“BBNJ 协定成就和展望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讲话。这是对“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有独特影响力的政治共同体的肯定与支持。
近年来,“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世界事务讨论的热词。从海洋治理、气候变化到贸易谈判,媒体和政治家对于“全球南方”一词都青睐有加,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对“全球南方”的使用也呈指数级增长。“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体现了“全球南方”作为当今世界政治的重要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在增强、能力在提升。然而,正如下文对该概念的梳理所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较为新近的事物,现有研究虽然对其概念的缘起和演进已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在以下三个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1)学界对“全球南方”的概念内涵及实体构成存在一定争议;(2)现有研究对“全球南方”和其他相近概念之间的异同尚未厘清,无法凸显“全球南方”概念的学理性和分析力;(3)对“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机制和效果的认识较为笼统,有待开展更加精细化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系统梳理“全球南方”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和出台过程中的表现,结合相关国家在前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的实践,分析“全球南方”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角色、诉求、实践机制和效果,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加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并充分发挥作用的可能方向。
一、“全球南方”的兴起
“全球南方”概念兴起于冷战结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南方”越来越受到的学界和政策界的关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全球南方”的表现引起了美西方战略界的重视和热炒。然而,对于“全球南方”作为世界政治进程中的参与者的角色和作用,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全球南方”概念的缘起
1969年,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在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上撰文称,越南战争是北方“统治全球南方”历史的顶峰,这也许是“全球南方”第一次被使用,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单独讨论。(4)Mukhopadhyay,C.,C. Belingardi,G. Papparaldo,and M. Hendawy eds.,Special issue:Planning Practices and Theori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Dortmund,Germany: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hool of Planning-Young Academic Network,2021,p. 9.彼时的发展中国家更多被称作“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这一词语最初由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于1952年创造,即作为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西方和苏联两大势力集团之外的国家,索维将其与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letiers état)进行了类比。(5)参见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82页。20世纪80年代,“南方”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词汇中,联邦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题为《北方与南方:一项求生存计划》(North-South:A Program for Survival)的报告中提出,如果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世界一分为二,那么这条分界线将沿北纬约30°穿过美国和墨西哥、北非和中东,向北爬升越过中国和蒙古,然后向南倾斜,将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圈进来,线的两边分别是富裕的北方国家和贫穷的南方国家,这就是著名的“勃兰特线”(Brandt Line)。(6)后续不乏关于“勃兰特线”的研究,如尼古拉斯·李斯(Nicholas Lees,2021)借鉴权力转移理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平等、经济实力和政治满意度等方面对南北差距进行了系统评估,认为“勃兰特线”基本上完好无损,世界政治因经济多样性被重塑,但并未削弱“勃兰特线”所描绘的南北鸿沟。参见:Nicholas Lees,“The Brandt Line after forty years:The more North-South relations change,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 47,No. 1,2021,pp. 85-106;Willy Brandt and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North-South:A Program for Survival,Cambridge,MA:MIT Press,1980。该线显示出南方和北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差异。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进展,受“全球化”话语泛滥的影响,“南方”逐渐与“全球”一词结合形成“全球南方”。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打造全球南方”(Forging a Global South)倡议的发布,在引起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关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第三世界”这个词由于通常与贫困、肮脏和动荡的形象相联系,受到非西方国家的排斥,“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边缘地区”等术语也因将非西方国家描绘为落后国家而被诟病,而听起来更中性的、带有较少等级或进化隐喻的“全球南方”取代了它们。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极限制裁,并频繁向各国施压,要求与其一道支持乌克兰,然而有80多个国家没有选边站队参与对俄制裁。2023年2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对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进行的投票中,共有7个国家反对,32个国家弃权。虽然决议得到通过,但包括印度、哈萨克斯坦、南非在内的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公开投票时不同意西方的立场,而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一半。面对西方对部分国家与俄罗斯继续保持贸易关系的指责,印度外长苏杰生公开表示,欧洲总认为“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这让许多西方领导人和评论家感到惊讶。(7)Francis Gilès,“Global South does not buy western stance on Ukraine,” May 1,2023,https://www.cidob.org/publicaciones/serie_de_publicacion/opinion_cidob/2023/global_south_does_not_buy_western_stance_on_ukraine [2023-09-10].
当前,围绕“全球南方”的博弈,已成为美西方战略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显示出“全球南方”在面对西方国家施压时逐渐有了勇敢说“不”的政治底气,体现了“全球南方”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提升和“依附性”下降。(8)参见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80页。2023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了“南北合作”专场讨论,强调西方要争取“全球南方”。同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日本作为轮值主席国提出加强与“全球南方”合作的主张,并邀请了多个南方国家与会。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争取和拉拢,强化了“全球南方”的集体认同。“全球南方”通过南南合作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变得更加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中也越来越注重团结协作。在外力和内力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南方”已成为其涵盖的许多国家所认同的统一身份,亦使得“全球南方”成为学界重视的研究主题。
(二)“全球南方”研究的争议
虽然“全球南方”已引起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但作为一个较为新近的事物和概念,“全球南方”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学界对“全球南方”的认识存在三个方面的争议。
1.关于“全球南方”的概念内涵
“全球南方”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概念,其内涵在世界政治的动态演进中不断生成,无论是政策实践者还是研究者,都会基于自身视角和经验对其进行审视和界定。因此,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南方”的概念范围和内涵迄今未有统一的认识,但大致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从地理层面界定,“全球南方”泛指位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二是从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界定,“全球南方”指称位于勃兰特线以南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经济上欠发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处于中间偏后部位。三是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角度界定,“全球南方”具有反殖民主义、反霸权的意识形态特征和价值诉求,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方向上具有一致性,认为现有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能很好地解决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也没有为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9)Kevin Gray and Barry K. Gills,“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ThirdWorldQuarterly,Vol. 37,No. 4,2016,pp. 557-574.四是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全球化将世界所有地区深刻融入全球性的资本市场和经济分工体系,“全球南方”国家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边缘”或“外围”地区,对北方国家和资本有很强的依附性。亦有学者将视角从国家单元层面转移到国家内部和跨国层面,关注受到现代资本主义扩张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地区与人群,重视国家内部的贫富和权力差距以及跨国政治主体性和底层反抗,将“全球南方”定义为可以在全球任意地区发生的反霸权反剥削现象。(10)更多对“全球南方”内涵的讨论,参见:Anne Garland Mahler,“Global South.”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Literary and Critical Theory,Eugene O’Brien,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Anne Garland Mahler,From the Tricontinental to the Global South:Race,Radicalism,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
2.关于“全球南方”概念的分析视角
“全球南方”是否具有作为分析视角的独特价值?抑或新瓶装旧酒,只是原有概念的一个新说法?这个问题的产生部分源于对“全球南方”与其他相似概念之间的异同尚未厘清。在现有研究中,“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常常混同使用,也与“不结盟运动国家”“欠发达地区”“中间地带”“77国集团”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这些概念有必要进行相应区分和廓清。“全球南方”概念缘起于“第三世界”,在实体构成上涵盖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77国集团”等。同时,在当前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政治目标亦与曾经的 “不结盟运动”和“中间地带”有相似的基础。
然而,这些共性不能否定“全球南方”作为当今世界政治演进的一个重要分析视角的独特价值。一方面,“全球南方”概念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特征”,它见证着国际社会变革的历史事实,承载着“全球南方”国家新的共同体身份意识,也孕育着越来越明确的集体行动纲领和目标,不能简单地视其为替代“第三世界”的地理隐喻;(11)Arif Dirlik,“Global South: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GlobalSouth,Vol. 1,No. 1,2007,pp. 12-23.其特征也无法由“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表达,其具有主动性的行动纲领和目标亦远超“不结盟运动”和“中间地带”所指向的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政治诉求。(12)参见:Sinah Theres Kloß,“The Global South as Subversive Practice: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 of a Heuristic Concept,” TheGlobalSouth,Vol. 11,No. 2,2017,pp. 1-17;Siba Grovogu,“A Revolution Nonetheless:The Global Sou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GlobalSouth,Vol. 5,No. 1,2011,pp. 175-190;Nour Dados and Raewyn Connell,“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Vol. 11,No. 1,2012,pp. 12-13;Hollington Andrea and Salverda,Tijo eds.,Concepts of the Global South,Köln: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Cologne,2015;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79—90页。另一方面,“全球南方”代表着非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展示出“第三世界”时期从未拥有过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国家”等词描绘了经济低迷和能力孱弱的形象,但“全球南方”并非如此。正如近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腾飞和近期巴西等国试图推动和平计划以结束乌克兰危机以及为解决巴以冲突中的人道主义危机所做的努力,“全球南方”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经济增长与政治主导齐头并进,促使“全球国际关系学”“亚洲世纪”和“后西方世界”等讨论的出现。(13)参见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Jorge Heine,“The Global South is on the rise-but what exactly is the Global South?” July 3,2023,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global-south-is-on-the-rise-but-what-exactly-is-the-global-south-207959 [2023-07-31]。因此,以“全球南方”为分析视角,将有助于准确把握世界政治的动态演进。
3. 关于“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作用机制和实践效果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力量新格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知识失灵”的危机。以超级大国的实力指标为准的、基于美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全球南方”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所产生的新问题时,面临理论失焦、方法论不适配等问题,中层理论的兴起正是对此问题的纠偏。(14)参见漆海霞:《国关中层理论创新需受到我国学界重视》,《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3期,第Ⅲ—Ⅵ页。“全球南方”从二战后的反殖反帝反霸的历史实践中走来,向着前所未有的后西方多极化世界动态演进,不断涌现的新现象和新经验需要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并需根据实践的丰富发展不断做出相应调整。因此,“全球南方”的研究虽然致力于确立一个系统的研究范式,但这是个长期目标。在现阶段,更加缺乏的是对“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各领域中所承担的角色、作用机制和实践效果的精细化研究,这是未来构建系统的研究范式所必须依赖的知识生产基础。例如,“全球南方”存在显著的内部多样性,这对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南方”的南南合作是否析出了实质性机制,利益冲突如何协调?面对南北竞争,“全球南方”对新秩序的诉求产生了哪些独特的规范和原则?针对这些涉及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的研究,将有益于推动摆脱“大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窠臼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动态实践。
有鉴于此,下文将聚焦海洋治理领域,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谈判和出台为案例,结合相关国家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的前期实践,分析“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角色、诉求、机制和效果,以此对以上三方面的争议做出更深入的探讨。
二、国际海洋治理中的“全球南方”
20世纪国际海洋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是广大中小国家团结协作、反对发达国家海洋霸权、积极创造维护自身权益的海洋治理体系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发展历程。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新独立国家和许多中小国家就开始对传统海洋强国的海洋自由霸权提出抗议,呼吁扩大领海范围。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于1930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法编纂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讨论领海宽度。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小国家开始积极参与海洋秩序的塑造,努力打破西方海洋强国对海洋规则制定权的垄断。
二战后,海洋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人类使用海洋的密度、深度和频度不断上升,国际社会产生了对海洋使用进行系统建章立制的广泛需求,国际海洋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一波去殖民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大量新独立国家涌现,参与到战后海洋治理新秩序的建设进程中。联合国分别在1958年、1960年和1973年组织召开了三次海洋法会议,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许多国际组织参与讨论,最终形成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对海洋空间规范和规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也因此被称为“海洋宪章”。(15)Tommy koh,“Commemoration of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Opening for Signature of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December 10,2010,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0/11/TommyKoh-Speech-to-UNGA-10Dec12.pdf [2023-09-10].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反对海洋霸权,取得了扩大海洋管辖权、将海洋治理纳入全球治理议程等重大成果,贡献出了“承袭海”“专属经济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等多个创新性理念和原则。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取得的最重要的立法成就,是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两个补充协定(《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议》和《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之后海洋法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协定》覆盖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尚未详细规定的水域范围,加强了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所承载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将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近2/3的海洋提供保护,并解决这些地区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协定》主要包含四个方面议题的规定,即:包括公正和公平分享惠益在内的海洋遗传资源问题、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等措施、环境影响评价,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协定》的出台,弥补了《公约》遗留的空白水域缺陷,在“《公约》+《协定》”的基础上,国际海洋治理体系建立起覆盖全球海域的法治框架。
《协定》通过后,各方对其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指出,该《协定》“给了海洋一个新的生命和希望”,“对于应对全球性威胁和确保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16)António Guterres,“Statement at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June 15,2023,https://www.un.org/bbnj/sites/www.un.org.bbnj/files/06-15-2023-final_bbnj_statement.pdf [2023-09-10].
目前,针对《协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所涉的各项议题安排的问题上,对“全球南方”在其中的参与情况探讨较少。事实上,“全球南方”对《协定》的顺利出台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与此同时,《协定》的谈判进一步塑造了“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新兴政治共同体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中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发挥。
(一)形成身份认同
在《协定》之前的历次海洋法会议当中,中小国家已有团结协作的实践,但彼时并未浮现“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而到了《协定》谈判时期,发展中国家展现出了较为明确的“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前文提及,在不同议题领域“全球南方”的内涵和实体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全球南方”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包括坚持多边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殊地理位置国家以及它们根据不同利益诉求组成的多个国家集团。
1930年召开的国际法编纂会议有42个国家参加,其中有不少中小国家代表的身影。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领海宽度,中小国家纷纷要求扩大领海宽度,而西方海洋强国坚持窄领海制度,双方立场针锋相对,中小国家由于实力弱小,未能实现领海范围的扩大。(17)Jesse S. Reeves,“The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territorial waters,” 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 24,No. 3,1930,pp. 486-499.二战后,联合国牵头组织召开了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会议磋商过程中,众多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传统海洋强国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任意侵犯发展中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及凭借技术优势肆意开采海洋资源、破坏海洋环境等海洋霸权行为。但在这些实践中,中小国家的身份认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等。例如,在1974年7月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25次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柴树藩大使发表演讲称:“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第三世界国家关于200海里管辖权的主张为改变过时的海洋旧秩序、创造公平合理的海洋治理新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洪都拉斯代表卡瑞艾斯·查帕塔(Carias Zapata)紧接着发言称:“近期国际层面的发展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一种新的觉醒和强烈的行动,此次海洋法会议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8)Document:A/CONF.62/SR.25,“UNCLOS III Summary Records of Plenary Meetings 25th plenary meeting,” United Nations,https://legal.un.org/diplomaticconferences/1973_los/docs/english/vol_1/a_conf62_sr25.pdf [2023-10-14].
到了《协定》磋商期间,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全球南方”,这种身份认同体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发言、会议声明和工作文件中。这一方面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在表达诉求时,援引“全球南方”作为其立场的合理性来源。例如,“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适用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海洋国家之间分歧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作为“全球南方”的成员,支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纳入《协定》是“全球南方”的共同立场,是保障“全球南方”塑造一个公平公正海洋秩序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各国有意识地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进行划分,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例如,在《协定》第五次政府间会议的再续会上,磋商各方对《协定》文本的出台程序和实施细则展开深入讨论,很多国家呼吁,“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要在《协定》实施问题上加强合作,提供支持。会议纪要中特别强调,多个来自“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代表在此事上表达了南北合作、共同为《协定》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的积极态度。(19)“Summary of the Further Resumed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to Adopt an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EarthNegotiationsBulletin,20 June,2023,https://enb.iisd.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6/enb25252e.pdf [2023-10-14].《协定》磋商的顺利完成也被视为是“全球南方”通力合作的成果。巴基斯坦国际法研究协会助理研究员拉斯·纳比尔(Lars Nabeel)称:“这也许是全球南方第一次建立了统一战线,让我们对全球多边主义的未来充满希望。”(20)引自巴基斯坦国际法研究协会助理研究员拉斯·纳比尔于2023年6 月 29 日在中国青岛举办的“BBNJ 协定成就和展望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对全球南方的重要性》。
(二)发挥协作机制
相比历次海洋法会议,在《协定》谈判中,“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事务,更加主动地运用协作机制来协调立场,凝聚共识。
在1930年的国际编纂法会议以及分别于1958年和1960年召开的前两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中小国家主要是以单独发声和地区组织的形式提出各自立场和观点,在反对发达国家的海洋霸权规则方面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再加上整体实力较弱,因此在这几次磋商中未能取得预期目标。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更加注重团结协作,有意识地运用77国集团平台来协调立场,增大音量。例如,在会议中期,各方讨论成立专业委员会针对几个核心的议题分别磋商,齐头并进,推进会议效率。为此,发展中国家利用77国集团平台集思广益,形成联合提案,对专业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主席人选、磋商程序提出动议,力图确保专业委员会程序公正,防止议题磋商进程被海洋霸权国把持。77国集团的努力使得专业委员会的组织架构最终与其提案相符合。(21)Document:A/CONF.62/C.1/SR.26,“26th meeting of the First Committee,” United Nations,https://legal.un.org/diplomaticconferences/1973_los/docs/english/vol_6/a_conf62_c1_sr26.pdf [2023-10-14].然而,在这一时期,77国集团平台的协调作用并不突出,更多的政策协调工作是由以地理位置划分的区域集团来承担的,比如拉丁美洲集团、西欧集团、陆锁国和地理不利国集团等。
在《协定》磋商期间,“全球南方”更加注重有效运用协作机制来协调各方立场。“全球南方”主要借助“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一方面在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创造数量上的优势,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另一方面也起到协调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平衡,增进发展中国家的互信。“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有力地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特别是在谈判困难时期发挥协调作用,使得会议在面临各方分歧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突破。谈判后期,各国代表团围绕《协定》第二部分议题出现严重分歧,分歧的焦点是针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数字序列信息方面的活动而产生的惠益,是否需要并应如何进行分享,在协议中又应如何体现。以古巴和萨尔瓦多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谈判早期就提出并支持纳入关于惠益分享的案文,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也认为要进行惠益分享并以公正公平的方式分享货币和非货币惠益,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利益。(22)“Summary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IGC)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19-30 August 2019,” EarthNegotiationsBulletin,September 2,2019,http://enb.iisd.org/oceans/bbnj/igc3[2023-10-14].然而,部分发达国家的提议是不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或者只认同非货币的惠益分享。在这一问题上,会议各方相持不下。为打破僵局,“77国集团和中国”发挥了主动性和建设性,配合会议主席开展闭门磋商,以务实态度协调各方立场,连续花费了近 40 个小时不停歇地讨论此部分内容,确保最终在公正和公平分享海洋遗传资源和数字序列信息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取得了创新的平衡。
在2023 年 6 月第五次会议再续会时,“77 国集团和中国”代表 134 个国家提交了一个正式文本,阐明了发展中国家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和具体诉求,其中很多都得以呈现在《协定》当中,特别是第十一条、十二条和十四条,分别对惠益分享的原则、制度和实践做了详细规范。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数字序列信息和惠益分享是实现公平公正的关键所在”(23)引自77 国集团主席代表理查德·图尔·德拉康塞普西翁于2023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青岛举办的“BBNJ 协定成就和展望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77 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对 BBNJ 进程中海洋遗传资源及公平公正地分享惠益谈判的影响》。。对于“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的领导力和协调力,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代表团都表达了认可和支持。(24)“Compilation of statements made by delegations under item 5 ‘General exchange of views,’at the further resumed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as submitted on 30 June 2023,”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3/232/21/PDF/N2323221.pdf?OpenElement [2023-10-13].
(三)引领规范原则
“全球南方”在《协定》磋商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原则,起到了规范引领的作用。
1.多边主义原则
这是“全球南方”在参与各类国际事务中普遍坚持的一个主要原则。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全球南方”除了面临南北竞争,也面临南南差异的现实。“全球南方”涵盖广大亚非拉地区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差异性极大。这其中,既包括人均收入仅有300美元的中非共和国,也包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既包括平均海拔达3000多米的南美洲内陆国家玻利维亚,也包括平均海拔仅有1.2米、被预计将在50年后因海平面上升而消失的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内部显著的差异性会体现为利益诉求的多样化,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维护和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有效原则。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提升谈判的代表性,77国集团和中国多次在会上呼吁对更多发展中国家代表给予资助。(25)“Summary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7-18 March 2022,” EarthNegotiationsBulletin,March 21,2022,http://enb.iisd.org/marine-biodiversity-beyond-national-jurisdiction-bbnj-igc4 [2023-10-14].在《协定》得以通过的政府间会议第五次会议再续会上,联合国秘书长、会议主席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都表达了对于多边主义的称赞,“代表们庆祝这一历史性成就,认为这是多边主义的胜利”(26)“Summary of the Further Resumed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to Adopt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19-20 June 2023,” EarthNegotiationsBulletin,Friday,June 23,2023,https://bit.ly/BBNJ_IGC_5-3 [2023-10-13].。
2.坚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项重要原则,到了《协定》谈判时期,海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是否要采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或公海自由是否应适用于全球海洋资源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那些支持公海自由的国家强调自由获取海洋遗传资源(MGRs),而那些主张“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国家则呼吁某种国际监督和公平的利益分享。(27)“Summary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4-17 September 2018,” EarthNegotiationsBulletin,September 20,2018,http://enb.iisd.org/oceans/bbnj/igc1[2023-10-13].《协定》磋商从始至终,“全球南方”一直致力于引入这一原则并最终取得成功,《协定》第七条一般原则和方法中明确规定缔约方应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这将确保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都能受到监管,加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各项法规和机制的效力,真正使得全人类后代受益。
3. “海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海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也是“全球南方”贡献的创新性原则。2022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首次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纳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推进进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是指以数字方式存储和转移的遗传资源的基因序列信息。掌握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就可以在无须遗传资源实物的条件下通过所获遗传序列信息实现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使得其在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海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是海洋生物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此背景下,在第五次政府间会议续会上,“77国集团和中国”牵头提出讨论“海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问题,提议将“海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以与“海洋遗传资源”并列的方式纳入《协定》的第二部分,并达成了目标。最终,《协定》中对于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等规定,都加入了“海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作为补充。
在此之前,“海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甚至没有出现在第五次政府间会议期间提交审议的草案中,正是在“77国集团和中国”要求下才得以纳入。正如古巴代表在第五次政府间会议续会上所提到的:“‘77国集团和中国’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条约与2022年8月几乎达成的版本完全不同的原因。正是这一群体的力量,使得有可能达成一个真正平衡的模式,分享利用海洋遗传资源和数字序列信息的惠益。”(28)“Compilation of statements made by delegations under item 5,‘General exchange of views,’ at the further resumed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as submitted on 30 June 2023,”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3/232/21/PDF/N2323221.pdf?OpenElement [2023-10-13].
(四)平衡各方利益
“全球南方”巨大的内部差异性,决定了各国在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一定的立场和利益诉求的分歧。(29)参见施余兵:《一步之遥: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分歧与前景展望》,《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1期,第36—50页。在实践中,“全球南方”通过三方面的途径来协调内部的分歧。
首先,为“全球南方”内部实力较弱的部分国家提供机制和智力支持。有学者指出,并非所有“全球南方”国家都全程参与到谈判当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围绕该问题召开的相关区域和国际会议中,参会程度与连续性较低、智力和技术支撑较少、参与意愿也有限,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30)Robert Blasiak and Jeremy Pittman,“Negotiating the Use of Biodiversity in Marin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FrontiersinMarineScience,Vol. 3,2016,pp. 1-10.为弥补它们的参与度不足,“全球南方”通过“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为其发声。
其次,“全球南方”内部也存在多个区域组织和基于特定利益关切形成的国家集团,比如非盟、加勒比共同体、小岛屿国家联盟等。这些组织和集团也十分活跃,积极参与《协定》进程,塑造磋商的方向,甚至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诉求流派。例如,在《协定》磋商进程中有几个特定的诉求流派——海洋利用派、海洋环保派、公平公正派、特殊需求派、多元关切派等。其中,特殊需求派就是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加勒比共同体为代表,重点关注诸如传统知识、气候变化等个性议题。在这几个议题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加勒比共同体提出了符合其利益关切的原则和细则,其中部分得以在《协定》中体现。(31)参见蒋小翼、卢萃文:《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的主要争议点及各方立场评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3期,第32页。正视这些特殊利益关切,通过广泛磋商来协调分歧,而不是强求步调一致,是“全球南方”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的体现。
最后,“全球南方”国家在立场协调上注重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平衡,这体现在坚持自身核心关切的同时,尽力为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做出让步。例如,在供 2022 年 8 月第五次政府间会议审议的、也是最后一次统计的案文提案汇编中,多数国家已经没有或很少提案,巴西、印度、古巴等都没有提案,中国、美国和欧盟分别只有2条、7条和7条。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和委内瑞拉提案有 17 条和19 条,加勒比共同体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也有 15 条,其中主要关切是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增强和规范缔约方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有助于这些国家从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资源中获得更多货币和非货币的惠益分享。然而,为了保障磋商的整体进度不受影响,这些国家最终做出妥协,并在《协定》文本正式达成后表示支持《协定》的尽快落地和执行。(32)Rahmad Nasution,“Indonesia supports adoption of BBNJ agreement,” June 21,2023,https://en.antaranews.com/news/285813/indonesia-supports-adoption-of-bbnj-agreement [2023-09-10];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Through BBNJ Agreement,Indonesia Pushes to Accelerate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and Utilisation,” June 22,2023,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4872/berita/through-bbnj-agreement-indonesia-pushes-to-accelerate-global-ocean-protection-and-utilisation [2023-09-10].
(五)推动《协定》落地
《协定》通过之后,其生效需要获得60个国家的批准,并在第60个国家批准后的120天生效。对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海洋主任明娜·艾普斯(Minna Epps)表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使《协定》在2025年6月法国尼斯举办的联合国海洋大会上生效。(33)Minna Epps,“A legally binding agreement - but what next?” July 21,2023,https://www.iucn.org/our-union/members/welcome-unite-nature/legally-binding-agreement-what-next [2023-09-10].要达成这一目标,仍然离不开“全球南方”的支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南方”的整体团结不仅贯穿于谈判始终,还将继续体现在《协定》生效和落实上。
早在2023年3月第五次政府间会议续会结束后,智利代表就正式提议,将《协定》秘书处设在智利。时任智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娅·乌雷霍拉(Antonia Urrejola)指出,智利带着责任和信念提出这一建议,将《协定》秘书处带到智利就是将全球治理带入“全球南方”国家,《协定》旨在解决国际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白,智利希望成为其实施的核心参与者。(3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le,“Chile formalizes its proposal to host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BBNJ treaty,” March 9,2023,https://www.minrel.gob.cl/news/chile-formalizes-its-proposal-to-host-the-secretariat-of-the-united [2023-09-10].《协定》由60个国家批准生效后,预计将在第一届缔约方大会上决定秘书处所在地,智利对此信心满满。《协定》在6月获得通过后,智利重申了其立场,建议将秘书处设立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市,作为促进其快速实施《协定》并保证以“全球南方”为基础的管理结构。这体现了智利作为“全球南方”的成员,为全球海洋治理做出积极贡献的强烈意愿。
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也对《协定》的通过表达了欢迎和支持,一些国家已开始付诸实践。古巴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指出,《协定》的通过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进步性协议方面的胜利,要肯定“全球南方”为确保其包容性惠益分享模式、数字序列信息共享以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纳入所做的努力。《协定》“开启了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新时代”。(35)“Summary of the Further Resumed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to Adopt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19-20 June 2023,” IISDEarthNegotiationsBulletin,Vol. 25,No. 252,June 23,2023,https://enb.iisd.org/marine-biodiversity-beyond-national-jurisdiction-bbnj-igc5-further-resumed-summary [2023-9-10].
帕劳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感谢所有参与方对这一进程的支持和对子孙后代的承诺,强调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以及承认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的强有力的规定将加强海洋治理,认为落实和执行《协定》离不开资金和技术资源的支持,也欢迎私营部门和行为主体参与到执行工作当中,为此帕劳呼吁安排缔约方会议继续开展,讨论包括资金以及技术合作等问题。(36)Ibid.墨西哥外交部指出,墨西哥积极参与了谈判的所有阶段,展示了其在拉丁美洲核心集团中的领导力和对条约目标的承诺,呼吁各国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尽快签署和批准《协定》,以确保其早日生效。(37)“Foreign Ministry welcomes adoption of the High Seas Treaty,” June 22,2023,https://www.gob.mx/sre/prensa/foreign-ministry-welcomes-adoption-of-the-high-seas-treaty?idiom=en [2023-09-10].巴西代表在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第 64 次会议上,推动理事会成员就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达成共识,扩大全球环境基金的职权范围,使其成为《协定》财务机制的一部分,全球环境基金还将支持各国批准《协定》并尽早采取行动。(38)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 Council approves plans for ‘game-changing’ global biodiversity fund,” June 29,2023,https://www.thegef.org/newsroom/press-releases/gef-council-approves-plans-game-changing-global-biodiversity-fund [2023-09-10].巴基斯坦国际法研究协会助理研究员拉斯·纳比尔表示,《协定》能否与现有海洋治理机制和谐共生还有待观察,对此“全球南方”国家不能坐视不管,要及时评估自身需求并实现承诺,同时“全球南方”也必须要相互帮助,继续取得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减小对“全球北方”发展援助的依赖性,这将成为《协定》中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部分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39)引自巴基斯坦国际法研究协会助理研究员拉斯·纳比尔于 2023年6 月 29 日在中国青岛举办的“BBNJ 协定成就和展望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对全球南方的重要性》。
可以预见,未来“全球南方”将继续在包括《协定》在内的全球海洋治理事务上发挥越来越具有引领性的作用。
(六)中国立场和担当
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和重要成员,中国在《协定》所涉的各项议题上的立场与“全球南方”的整体立场保持高度一致,积极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注重特殊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平衡。中国认为,应坚持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处理《协定》谈判中的各项议题;《协定》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补充和完善,应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目标和宗旨,遵循“不损害”原则,即不违背现行国际法和现有全球、区域和部门机制,不损害各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享有的各项权利;在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方面,中国主张遵循平等自愿、合作共赢的原则,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关于《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也持有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相似的谨慎立场,即主张争端当事国应首先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若谈判无效,可考虑在双方明确同意的基础上将案件提交给第三方程序,避免司法滥权。(40)参见郑苗壮等编:《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国代表团发言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施余兵:《BBNJ国际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探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6期,第12—26页。
中国在《协定》谈判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 “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是“全球南方”在《协定》磋商中进行协作的主要机制。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时期的77国集团机制变成《协定》磋商期间的“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是中国认同和支持“全球南方”并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的有力体现。在《协定》谈判中,中方同样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多次派出代表团参与各轮磋商,积极表达观点意见,不断增进共识,并且举办一系列相关国际研讨会,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为《协定》通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了各方的肯定。
在《协定》达成一致的第五次政府间会议续会上,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咨询管辖权问题上的立场虽未能获得完全采纳,但中国代表团仍然建设性地参与折中方案的讨论和制定,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各国的利益平衡,使得《协定》如期达成。2023年9月20日,在《协定》规定的开放签署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协定》,再次体现了中国对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真正多边主义的践行和维护。(41)参见《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代表中国签署〈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9月2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tyfls_674667/xwlb_674669/202309/t20230921_11146367.shtml [2023-09-21]。在2022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上,中国作为主席国与各方共同确定《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意在与《协定》齐头并进,共同完善全球海洋生态治理。中国始终从人类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积极推进海洋治理体系和海洋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这体现了中国主动作为、发挥“全球南方”引领性作用的大国担当。
总之,中国参与《协定》磋商的具体实践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呈现,在相当程度上兼顾“全球南方”国家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获得了其他南方国家的广泛认同。这再次印证了中国是“全球南方”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中国的支持是“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必要支撑。
综上所述,“全球南方”在《协定》谈判过程中展现了与历次海洋法会议不同的特点:一是“全球南方”展现出了很强的身份认同和集体凝聚力;二是“全球南方”有意识地运用“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统一共识,协调立场,提高集体谈判策略的有效性;三是“全球南方”更加具有主导权意识,积极参与议程设置,提出一系列具有引领性的原则和规范;四是“全球南方”更加坚守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注重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平衡,并致力于推动《协定》尽快落实生效,展现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担当。
三、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全球南方”:探索参与路径
“全球南方”为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和最终达成一致发挥重要作用并非孤例,在其他全球治理的事务领域,“全球南方”也展现出了越发主动的姿态,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可以预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崛起将有力地推进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
“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体现在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增强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升。“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增强,主要是由于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不能满足快速崛起的“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公平公正参与其中的需要,具体体现便是对国际新秩序和全球治理新安排的畅想和呼吁。早在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就聚焦于“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重塑全球治理体制的需要。报告认为,许多全球性机制不能匹配南方国家崛起带来的世界格局剧变,呼吁建立一个在国家层面上由“负责任主权国家”推动的更加“一致的多元化”的全球治理体系。(42)参见杨川梅:《南方国家群体崛起全球治理跟不上变化》,《中国经济导报》2013年3月19日。此外,“全球南方”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共同利益的要求也有延续性,是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
伴随参与意愿增长的还有“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按购买力平价估值计算,155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2022年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已达58.3%。(43)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 2023:A Rocky Recovery,” April 11,2023,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4/11/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3 [2023-09-10].据欧洲专利局发布的《2022专利指数》,中国是2022年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第四位,也是申请数量前20位的国家中增幅最高的国家,共申请19041项专利,同比增长15.1%,占申请总量9.8%。(44)“Patent Index 2022,” March 28,2023,https://www.epo.org/about-us/annual-reports-statistics/statistics/2022/statistics/patent-applications.html#tab2 [2023-09-10].可以说,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快速追赶是“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前提,现在的“全球南方”国家不但有能力拒绝北方国家的要求,而且有能力就国际秩序的未来提出自己的愿景并为之奋斗。(45)参见黄忠:《全球南方国家的“新不结盟”运动》,《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5期,第111—130页。
身份认同的加强结合国家实力的综合增强,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在近年来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不断突破传统议题领域的限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南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低位政治领域,比如海洋治理、环境治理等领域。在传统安全、金融等美西方主导的议题领域,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这一现象在近年来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
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正在扩大。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全球南方”国家虽然面临美欧的施压,但并未跟随美欧的脚步,而是展现出独立自主的姿态。“全球南方”国家没有一边倒地对俄进行谴责,也反对实施极限制裁。同时,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土耳其、沙特等国,还主动斡旋创造新的政治空间来帮助解决乌克兰危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例如,沙特于2023年8月5日在吉达市召开了首个由非西方国家主办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邀请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南非等42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参会,这体现出以沙特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传统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的提升和战略自主性的增强。(46)参见《吉达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强调通过国际协商实现和平》,新华网,2023年8月7日,https://www.xinhuanet.com/2023-08/07/c_1129789843.htm [2023-10-14]。
在经贸金融领域,“全球南方”越来越能发挥引领性作用,在创制金融规则和改革治理机制方面不断突破。中国政府提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响应。以金砖国家为首的金砖机制也成为“全球南方”推动久受诟病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抓手,2023年3月,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任命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为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金砖银行)行长,并在4月访华时出席其宣誓就职仪式。8月,南非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南非邀请了67位非洲国家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出席“金砖—非洲”会议和“金砖+”对话会。峰会期间,南非亚洲及金砖事务特使苏克拉尔表示,已有十多个国家正式致函申请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金砖+”机制扩容浪潮展现了“全球南方”共同推动金融经贸领域的全球治理改革的能力和决心。(47)参见黄仁伟、朱杰进:《全球治理视域下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当代世界》2022年第7期,第29页。在2023年9月举行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上,134个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布《哈瓦那宣言》,倡议改革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轮值主席国古巴的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更是明确指出:“此前北方国家一直按照其自身利益来组织世界,现在应该由南方国家来改变游戏规则。”(48)转引自《“77国集团和中国”发出全球南方强音》,参考消息网,2023年9月18日,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a3905d8bd98a41999629b2ccbfc25340/1/2023-09-18%2010:20?childrenAlias=undefined [2023-09-19]。
此外,越来越多的地区大国有了“全球南方”的担当意识,这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更具建设性和引领性的作用。例如,印度和巴西等国积极投身于“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形象塑造,试图引领“全球南方”合作的新浪潮。2023年1月,印度邀请了125个国家在线上召开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埃及在气候治理领域,也展现出领导“全球南方”的潜力。2022年11月,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巴巴多斯领导人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牵头发起“布里奇顿倡议”,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需求提供资金,倡议推动发达国家在会议上承认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历史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甚微的非洲和亚洲国家,“这一承认就可能改变随后所有全球谈判的基调和性质”。(49)Ravi Agrawal,“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Policy,January 12,2023,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2/global-south-geopolitics-economics-climate[2023-09-10].会议最终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即为遭受气候灾害严重打击的国家建立并实施“损失和损害”基金,专门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破坏,这是“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又一力证。
(二)探索“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
虽然“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地缘政治回归、阵营化趋势加剧、国际格局动荡的现实,对“全球南方”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产生了一定的挑战。面对内部需求的差异性、美西方的拉拢和分化以及机制供给不足等问题,“全球南方”应坚持多边主义,求同存异,防范外部势力的干扰,并加强现有区域和国际组织机制的建设和利用,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平公正和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1.消弭内部的离心力
“全球南方”涵盖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这一事实,既意味着团结一致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能量,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地理资源禀赋和国情体制等带来的巨大差异,如何找到平衡点、扩大共识面,考验着“全球南方”的集体智慧。总的来说,“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同存异,并防范西方国家从内部分裂和扰乱“全球南方”的企图。
从长远来看,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并不一定与追求本国自身利益相矛盾,前者甚至是后者赖以实现的条件,因为即使部分“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很难突破当前西方国家在很多领域仍占据主导的现实,在诸多全球事务中只能靠单打独斗式地实现目标。
就外部势力干预而言,“全球南方”也要防范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分化为不同的小群体,避免沦为美西方维持霸权的工具。2023年5月,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广岛召开,作为轮值主席国和东道主的日本,邀请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全球南方”国家参与。这是发达国家重视“全球南方”的表现,但也透露出遏制中国和拉拢分化“全球南方”的浓厚意味。从5月20日发布的峰会公报来看,表面上肯定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承认有必要在全球挑战和共同利益领域与中国合作,但文中充斥着与中国“脱钩”和“去中国化”的暗示,并在南海局势和人权问题上“污名化”中国,其对中国的敌视可以说仅次于被持续强硬针对的俄罗斯。(50)“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May 20,2023,https://www.g7hiroshima.go.jp/documents/pdf/Leaders_Communique_01_en.pdf [2023-09-10].“全球南方”国家要对此保持敏感和警惕,看清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本质,避免“全球南方”的凝聚力因外部势力的干扰而受到削弱。
2.加强组织和机制建设
加强由“全球南方”国家组成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强化机制建设,充分利用相关组织和机制参与全球治理。这有利于多边主义的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平公正和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方面,“全球南方”可以加强“77国集团+”机制的建设和利用,进而提高对全球治理事务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机制,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具有重大共同关切的议题中联合发声并取得理想的成果,这一措施的有效性已经在包括《协定》谈判在内的历次国际海洋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全球南方”在谈判中取得的成功,离不开对77国集团、区域国家集团等组织的灵活利用,“77国集团+”等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安全方面,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由南方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在塑造地区安全秩序层面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此次乌克兰危机中,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蒙古、巴基斯坦、中亚五国和伊朗等,秉持更加客观中立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的对俄政策。近年来,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开始对上合组织表示兴趣。2023年7月4日,伊朗成为新成员,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增至九个。上合的持续扩容,表明该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塑造地区安全秩序方面扮演越来越有分量的角色。在中东地区,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之下,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中东的安全秩序也随之发生转变。包括阿联酋在内的中东国家开始退出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沙特、伊朗、阿联酋和阿曼宣布组建海上联合巡航舰队。未来,中东地区将加快建设完全由区域国家组成、排除西方大国干扰的区域安全机制。
在经济方面,“全球南方”可以利用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等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倡议。例如,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 42%,经济总量占全球 24%,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国际力量格局变迁的重要变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因。(51)参见陈凤英:《全球治理视角下的金砖合作机制化趋势》,《当代世界》2021年第10期,第11页。“全球南方”国家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有着共同需求,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有利于增进南南合作,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推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改革。总而言之,“全球南方”要继续加大力度建设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组织和机制,提升其国际地位、代表性和话语权,抱团取暖,结伴而行,为全球治理的变革和完善创造更多契机和空间。
3.大国的尊重和协作
整体来看,当前全球治理主要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滞后于不断涌现的治理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对于世界认知的进步,在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网络安全威胁、难民危机、粮食与能源危机等全球治理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时,以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风险和新挑战令全球治理体系应接不暇。二是部分国家的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导致全球治理效能受到严重削弱。比如,美国近年来不仅实行单边贸易制裁和投资保护,建立“小院高墙”,严重阻碍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还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借口实行歧视性、排他性的小集团治理,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排除在圈子之外,分化原本捉襟见肘的全球治理力量,干扰多边主义合作,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治理效能受到严重削弱。
“全球南方”在《协定》谈判和其他全球治理事务中的实践证明,凝聚起来的“全球南方”可以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效能提升做出积极贡献,但大国的协调与合作是充分发挥“全球南方”作用的必要条件。传统上主导着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的西方主要国家要认识到,边缘化、阵营化“全球南方”,不利于发现全球性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妨碍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应尊重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重视“全球南方”的需求,将“全球南方”视为国际舞台上成熟的参与者,与“全球南方”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原则,用言行一致的方式赢得“全球南方”的信任与合作。
美欧等西方大国需要摒弃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和家长主义,重塑自身国际形象与信誉。美国长期轻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将“全球南方”当作大国竞争及对抗的工具。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优先”的外交方针,严重打击了“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政策稳定性和坚持多边主义的信心,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更是明确将“全球南方”国家当作遏制中国的棋子。欧盟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认为欧盟是“虚伪、自私、新殖民主义”的。近年来,欧洲的对外援助政策的政治性动机和实际成效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52)参见:Maurizio Carbone,“The European Union,Good Governance and Aid Coordination,” ThirdWorldQuarterly,Vol.31,No.1,2010,pp. 13-29;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135—155页。新冠疫情期间,欧洲没有帮助“全球南方”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而是采取更加孤立的战略,囤积疫苗并反对疫苗豁免,也引起“全球南方”国家的不满。(53)Rosa Balfour,Lizza Bomassi and Marta Martinelli,“Coronavirus and the Widening Global North-South Gap,” April 25,2022,https://carnegieeurope.eu/2022/04/25/coronavirus-and-widening-global-north-south-gap-pub-86891 [2023-09-10].国际格局正在进入新的调整期,如何充分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合作,共同增进人类社会福祉,是西方国家面临的新课题。如果不尊重“全球南方”的利益和诉求,继续将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全球南方”,它们会成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障碍因素。
对中国而言,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和当然成员。中国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及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具体实践为抓手,切实推动国际海洋治理的发展完善,并支持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海洋治理、气候变化、经贸合作等诸多领域的参与,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指出,为了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各国需要坚持公平合理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这体现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上坚持多边主义和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参与。习近平主席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态度: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54)参见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团结协作 实现更大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7月5日,第2版。为此,中国要基于自身经济崛起和综合国力上升的经验,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全球治理参与能力提升的“中国方案”,强化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挑战的韧性。中国也要担当起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变革提供“中国智慧”,推动形成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国际秩序。
四、结 语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全球南方”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都在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实践和成果也愈发丰富。《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继承和发展,是近年来国际海洋治理领域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展现了国际社会在日趋严峻的海洋治理挑战面前,对于多边主义和全人类利益的坚守,也为其他治理议题的磋商做出了良好示范。“全球南方”作为一个较为团结的整体,在《协定》谈判过程中积极参与、贡献巨大,并将继续成为《协定》批准、生效和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南方”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实践显示,“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已是既成事实。同时,“全球南方”正在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多边磋商和协作的平台和机制,贡献出更多有益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规范和原则。
在当下国际格局动荡、阵营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全球南方”对于多边主义的坚持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认同,消弭“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因自身差异和外部势力干扰而产生的离心力,加强现有区域和国际组织机制的建设和利用,进而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平公正和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将继续考验“全球南方”的集体智慧,也是未来学界需要重点关注和探讨的议题。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和重要一员的中国,要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力量,积极探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南方”实践充分结合的具体路径,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起为全球治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