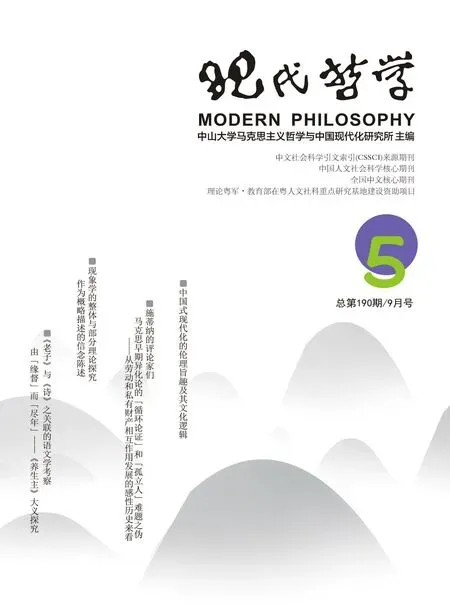从纯粹快乐到最好生活
--柏拉图《菲丽布》中的幸福观探究
2023-12-21张波波
张波波
引 言

如果跳出这两篇就会发现,柏拉图在别的对话录中极端仇视快乐。譬如,在《斐多》中,他似乎旗帜鲜明地反对与身体相关的快乐,说它们是对纯粹哲学追求的干扰(Phaedo64e-69d)。读者甚至可发现,他在这里似乎切断了快乐与幸福之间的任何关联,但同时又颂扬哲学家的生活是满足而快乐的。这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柏拉图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有人则称他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也有学者如拉塞尔(D. Russell)(6)D. Russell,Plato on Pleasure and the Good Life,p. 11,p. 11,p. 12,p. 12.选择一条折中路线,认为柏拉图在《斐多》中认为快乐既不是好也不是恶,而是一种条件性的好,即快乐是好还是恶取决于它在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撇开这种争论不谈,如果把关注点转向中期作品《理想国》就会发现,柏拉图强调“好”不可能等同于快乐(RepublicVI 505b-c),但又指出哲学生活最令人愉快,而追求美德既应是为了美德本身(作为灵魂健康),也应是为了它令人愉快的结果(IV,IX)。如果说幸福是整体性的,其包括人之为人(充满激情、情感、欲望、快乐和痛苦)这一复杂物种所有层面的繁荣(茂盛),那么根据《理想国》(尤其是第4、9卷)中柏拉图的看法,快乐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即它不是作为智力的补充,而是作为智力所要改造并使之繁荣的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柏拉图在证明德性生活幸福时,赋予快乐以重要意义;有美德者幸福,因为他们过着完整而繁荣的人类生活,而人类是情感性的存在(7)D. Russell,Plato on Pleasure and the Good Life,p. 11,p. 11,p. 12,p. 12.。美德是一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灵魂健康,所以从《理想国》看,柏拉图并不希望将快乐从好生活中剔除出去,而是希望将快乐整合为健康、繁荣的人类灵魂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利用“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对快乐进行“理性整合”(rational incorporation)(8)D. Russell,Plato on Pleasure and the Good Life,p. 11,p. 11,p. 12,p. 12.。
根据理性整合的阐释思路,柏拉图自然认为快乐是幸福所必需的。快乐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问题不在于好的生活是否令人愉快,而在于快乐的本性是什么,以及它在好生活中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作为柏拉图晚年快乐观研究的重要文本,《菲丽布》与同一时期完成的对话录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理想国》中的快乐观,即同样反对快乐至上,却又都固守着一种强烈的真快乐情怀。《菲丽布》通过对快乐的细致而深入的讨论而得出:好生活或幸福生活,既不等于纯粹智思(phronesis)的生活,也不等于纯粹快乐的生活,而是由前两者的混合构成。这再次说明,柏拉图在此阶段进一步认识到快乐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不是因为他否认美德足以使人幸福,而是因为在他看来美德是对于“自我”所有方面的理性整合。换言之,快乐之所以是幸福所必需的,正是因为美德是一种合适的整体,足以使人获得幸福(9)D. Russell,Plato on Pleasure and the Good Life,p. 11,p. 11,p. 12,p. 12.。
如果撇去柏拉图早、中期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式快乐观的因素,就柏拉图晚年对幸福的思考而言,依凭《菲丽布》的快乐新论而得出的混合型幸福观,似乎可以认定柏拉图晚年对快乐的态度总体上趋于友好,至少《菲丽布》显示了柏拉图对快乐的友好一面。然而,在古典哲学领域,近年来很多极具代表性的学者就《菲丽布》对快乐主义的让步力度提出各种质疑(10)G. R. Carone,“Hedonism and the Pleasureless Life in Plato’s Philebus”,Phronesis,Vol. 45,No. 4,2000,pp. 258-259;E. Fletcher,“Plato on Pure Pleasure and the Best Life”,Phronesis,Vol. 59,No. 2,2014,p. 113.。例如,弗雷德(D. Frede)认为,《菲丽布》虽允许快乐进入幸福生活,但这种包含了快乐元素的幸福生活只是第二好(次好)的生活;第一好的生活是一种中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会经历快乐或痛苦(11)D. Fred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Pleasure and Pain in Plato’s Philebu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ed. by R. Krau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 440;Plato:Philebus,trans. by D. Frede,Indianapolis:Hackett,1993,p. xliii.。这种解释试图将快乐从好生活中剔除出去,很容易和《泰阿泰德》的“与神相似”(likeness to God)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果好生活等于与神相似,而神的幸福与苦乐无关,那么人的幸福的上限便是超越苦乐,进入一种无乐无苦的状态。这意味着,我们要做的不是通过理性整合将情感本性纳入到理性本性之中,而是拒绝我们的情感本性,因为后者不是我们真正本性的一部分或我们应当珍视的部分。
《菲丽布》真的像这些学者所言,仍对一切快乐都不看好吗?它仍十分仇视快乐主义并淡化快乐在幸福生活中的作用吗?我们对此深表怀疑。本文将提出一种关于《菲丽布》的新理解:这篇对话自始至终都认真致力于将快乐和智慧的混合生活推举为人类第一好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第二好的生活。相应的,它对快乐的态度与其说是拒绝,不如说是希望将某些快乐整合、融入到幸福生活的大拼图中,就此而言,幸福生活将包括真正的快乐,而后者本身是好的,将作为好生活中有内在价值的构成要素之一区别于混合快乐。为支持这一论点,本文将论证,柏拉图认为某些纯粹快乐是“内在好”(12)R. Kraut,“What Is Intrinsic Goodness?”,Classical Philology,Vol. 105,No. 4,2010,pp. 450-462.,与幸福生活并不冲突,因而无乐无苦的中性状态并不是柏拉图心目中最值得拥有的生活。
下面将以《菲丽布》为中心,旁涉其它对话,讨论神性生活(中性状态)、幸福、纯粹快乐、最好生活以及快乐是否为“生成”等一系列主题,以期对柏拉图晚年的幸福观获得深细的认识。
一、中性状态、混合生活与最好生活
何为最好的生活?《菲丽布》给出的答案是混合生活。为何混合生活最佳?这个问题的解答与柏拉图的“1加1优于1”思维模式有关。《菲丽布》一开始就交代,无论是理智主义的代言人苏格拉底,还是快乐主义的同盟军普罗塔库斯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证明“能够为全人类带来幸福生活的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和性情”(Philebus11d4-7)。普罗塔库斯起初争辩说它是快乐状态,苏格拉底则主张是智思状态。尽管有如此争执,为了让对话得以有效展开,他们最终相互让步并一致同意:如发现有一种生活状态比这两种状态都优越,那这个候选者将赢得最接近冠军席位的排位(11d-12a)。为了事先确定“好”是什么,他们还达成另一共识:“好”有三个属性,分别是完美的、充足的、令人向往的,即它作为人类选择和追求的目标,是让那值得选择的生活有价值的东西(20c-d)。然而,在确定这个前提之后,他们发现,无论是智思生活还是享乐生活独自似乎都不满足“好”自身具备的这三个标准。因为人若无记忆、知识、真实意见或计算,就不会感知到快乐,所以无人愿意过无思而纯乐的牡蛎般的生活(21a-d);与此同时,完全祛除快乐的生活似乎是乏味无魅力的,所以无人愿意过一种拥有完整知识和其他智识能力,但却没有快乐或痛苦的生活(21d3-e5)。
正如不少学者(13)G. R. Carone,“Hedonism and the Pleasureless Life in Plato’s Philebus”,Phronesis, Vol. 45,No. 4,2000,p. 259.注意到的,《菲丽布》提出的人生理想,远非后来斯多亚学派的“不动心”的贤哲理想(D. L. 7.117)(14)M. R. Graver,Stoicism and Emotion,Chicago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p. 35-39.,而是一种满足了人类意义上的完美性、充分性和可取性标准的人生理想。既然快乐和智思在对话一开始都被视为人类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话接下来就着手对快乐和知识进行分类,以便弄清其中的哪种应在人类幸福的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若无进一步的严密论证,我们就不能轻易接受上文提出的这种解释。如前所述,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解释路线并不同意这种解释思路,而是主张柏拉图说话很绕,他实际的想法比上文所阐述的更为隐晦曲折(15)J. McCoy,“The Argument of the Philebus”,Epoché,Vol. 12,No. 1,2007,p. 1.。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应该把该篇对话的其余内容视为对苏格拉底在文本(X)21d-e处最初提出的主张的修正,而非详述。这种观点还明确指出,读者可以在(Y)32d-33c处明显看到对这一主张的修改甚至背离的迹象。在(Y)32d-33a之前,苏格拉底一直在论证,我们可以将痛苦理解为生命体之和谐的消解,将快乐理解为这方面的恢复。然而在此之后,他话锋一转,考虑了除感到快乐或痛苦之外的第三种状态,即生命体不受破坏或恢复影响的中性状态。苏格拉底还补充说:对于选择了智思生活的人来说,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以这种方式生活,因为对于选择了智思和理智生活的人来说,没必要感受到大大小小的快乐(33a3-b2)。有趣的是,对话并没有就此结束:
苏:这对祂来说很可能是可行的,如果这是所有生命中最神圣的,也许也没什么奇怪的。
普:无论如何,神明是不太可能体会到快乐或其对立面的。
苏:没错,极有可能。因这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与祂们而言都是颇不适宜的。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论点有关,我们将在以后研究这个问题。即便我们无法将理智推举为冠军,那我们也仍将相信,它会在争取亚军的战斗中取胜。
普:你说得对极了。(33b-c)
这段文字对我们理解《菲丽布》中的快乐观至为重要。弗雷德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柏拉图在此暗示,某些快乐是作为补救性的好而被包括在最好的人类生活中的--这是必要的,因为与神的完美本性相比,人的本性并不完美。如果人类有可能过这样的生活,那么没有快乐的智思生活会比混合生活更好。这种无乐的理想生活即为神的生活,人类可以希望达到这种理想,但永远无法完全实现。总之,弗雷德的核心看法是,快乐充其量是一种补救性的好,而无乐的、不受搅扰的平静状态实际上更可取、更令人想望(16)D. Frede,“The Tragedy and Comedy of Life:Plato’s Philebus” (review),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 33,No. 2,1995,pp. 331-333.。弗雷德的这种看法并不新颖,一些学者(17)Plato:Philebus,trans. by J. C. B. Gosling,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 103;C. Hampton,Pleasure,Knowledge,and Being,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p. 65.早在她之前就提出了类似论断。为支持这一论断,弗雷德补充了两点看法:第一,苏格拉底虽在21e处同意,无乐的生活对人来说不可取,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讨论继续进行下去。该同意只是权宜之计,是对普罗塔库斯作出的初步让步,不能算是《菲丽布》的最终定论。对话的关键部分则要推翻这一共识。第二,苏格拉底之所以认为,神过着一种没有快乐的生活(22c,33a-b),而且快乐次于中性状态,是因为该篇对话后来从本体论上对快乐进行降格,即把快乐当作一种生成过程,而非具有稳定性的“存在”(53c1-e7)。
下面将证明,这些说法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18)G. R. Carone,“Hedonism and the Pleasureless Life in Plato’s Philebus”,Phronesis, Vol. 45,No. 4,2000,p. 261.。通过对《菲丽布》的仔细研读可发现两点:第一,弗雷德得出的“快乐在《菲丽布》中充其量只是一种补救性的好”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弗雷德关于快乐本性上在形而上学层面地位低下的主张不符合《菲丽布》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我们的论证将分为两部分展开说明:其一,如果将柏拉图专门论述快乐的那些段落置于其上下文语境中,就会发现,柏拉图确实认为最理想、最令人想望、最令人满意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第二好的生活)至少包括一些快乐,而且他准备赋予这些快乐以某种神圣地位,让它们在像神一样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二,我们将讨论弗雷德的第二种主张所依据的一些形而上学假设,并证明它们的不合理性。我们不能忽视不同类型的快乐(如纯粹的快乐和不纯粹的快乐)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不能像弗雷德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的快乐都当作补充匮乏的过程(19)G. Santas,“Plato on Pleasure as the Human Good”,A Companion to Plato,ed. by H. H. Benson,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 319.,并一口咬定快乐充其量只是一种补救性的好。
二、纯粹快乐和最好生活
最好生活是否包含快乐?《菲丽布》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摇摆不定。有人通过区分人与神各自的“好”,证明人的最好生活包含快乐,但神的生活则不包含(20)R. C. Bartlett,“Plato’s Critique of Hedonism in the Philebu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102,No. 1,2008,p.143.;有人则通过区分纯粹快乐与混合快乐,认为无论是人的最好生活还是神的生活都包含某些快乐,如纯粹快乐(21)J. V. Garner,The Emerging Good in Plato’s Philebus,Evanston &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7,p. 69.。本文采取后一立场。
为何《菲丽布》如此偏爱纯粹快乐?这要从《菲丽布》中苏格拉底关于快乐与好生活之关系所持有的两个观点说起。对话没进行多久,苏格拉底就首先提出,(A)快乐和智思的混合生活最好,要比纯粹的智思生活更好(20c-21e)。这说明快乐是最好生活的重要(必不可少)组成部分。然而,他没过多久又主张,(B)纯智思的生活,即无快乐的生活最神圣(32d-33c)。如果柏拉图认为,最神圣的生活等于最好生活,那(A)和(B)这两个说法就自相矛盾(22)G. R. Carone,“Hedonism and the Pleasureless Life in Plato’s Philebus”,Phronesis, Vol. 45,No. 4,2000,p. 261.。如果柏拉图认为,最好的生活是对人而言的,它优于最神圣的生活,那(A)和(B)就共同推导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最好的人类生活(思乐混合生活)比神的生活(纯智思生活)更好(23)E. Fletcher,“Plato on Pure Pleasure and the Best Life”,Phronesis, Vol. 59,No. 2,2014,p. 113.。
要查明哪个说法最能代表柏拉图的心声,即他所言的混合生活、最好生活与最神圣生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当前似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主张《菲丽布》本身充满矛盾言论,而且这些言论之间的张力又是难以消除的;二是说明尽管其中含有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只是文字表面上的而非思想上的,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可以消解的(24)E. Fletcher,“The Divine Method and the Disunity of Pleasure in the Philebu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 55,No. 2,2017,pp. 179-180.。选择哪条路径最佳,这是个长久争讼未决的问题。本文采取的是后一条路线。要消除(A)和(B)之间的表面矛盾,一种办法就是像弗雷德那样,按照出场先后顺序把(B)当作是对(A)的修正。言下之意,随着对话逐步展开,柏拉图慢慢意识到(A)的不妥,故用(B)取而代之。假若柏拉图的确是这么想的,那为了保持对话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他在对话结尾肯定会指使传声筒苏格拉底再次确认:不是混合生活,而是无乐生活,才是最理想、最令人想望的生活。
然而,我们在《菲丽布》结尾处看到的结论并非如此,而是与之相反(60c)。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在对快乐进行细致分类,并对其中的某些种类给出严厉批判之后,又回到前面21e-22b处讨论最佳生活时得出的那一结论:无论是纯快乐的生活,还是纯智思的生活都不是最充足、完善的(60c)。不仅如此,他还提醒读者,(Y)32d-33c处的说法会引人误入歧途,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Z)60d3-4。这再次证实,柏拉图认为,对所有有生命的存在来说,完美的、值得选择的、完全好的东西,不会是纯快乐的生活或纯智思的生活。无人会选择只有快乐而无智思的生活,同样也没人会选择无任何快乐(哪怕最轻微的快乐)而唯有智思的生活(60e-61a)。那么,在谈到最好的生活时,柏拉图是不是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不完美状态,故作出了必要的妥协?换言之,这里的最好生活是不是打了折扣的第二好生活?显然不是。注意,柏拉图在提到“最可爱的生活”时使用的是最高级,这标出了它是指第一好生活,他还说这种生活至少包括一些快乐,即纯粹快乐(61e6-9)。
什么叫纯粹快乐?其本质在于摆脱痛苦,未混杂他物(66c5)。具体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它们明确区别于必要的快乐(62e4-9),是内在固有量度或限度的东西(52c-d)。第二,它们在本体论上是真实的(aletheis)。第三,它们在数量上比任何混合的快乐都要大、更令人愉快(53c)。这一切证据都表明,当弗雷德说所有的快乐充其量是一种补救性的好时(25)D. Frede,“The Tragedy and Comedy of Life:Plato’s Philebus” (review),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33,No. 2,1995,p. 333.,她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柏拉图承认,至少某些快乐本身可以是好的或有内在价值,只要追求这些快乐的理由并非仅仅是获得其他东西的工具性手段。因此,柏拉图并不认为,鉴于人的本性与有着完美本性的诸神相比有很多局限性,如不能自制,因此人会情不自禁地去体验快乐。相反,在柏拉图看来,对某些快乐的追求将使我们的本性臻于完善,趋于充足。
即便如此解释,有人可能仍对苏格拉底在(Y)32d-33c处表达的意思表示不解。他不可能平白无故插入这段话。他似乎通过这段话有意暗示,无乐无苦的生活将是最神圣的,众神将不会感到任何快乐或其反面。可是,这里的快乐究竟是指什么样的快乐?如果是指一切快乐,那最神圣的生活本身将与快乐绝缘。如果是指混合快乐而非纯粹快乐,那就意味着最神圣的生活本身并非是无乐的。回到这段话出现的具体位置就会发现,柏拉图的意思显然是后者。柏拉图是在讨论混合快乐时插入这段话的。具言之,在插入这段话时,苏格拉底刚刚分析了一些诸如干渴时喝饮料的案例--这些案例表明,快乐来自于对生命体和谐的恢复,而痛苦来自于对这种和谐的破坏(31e-32a)--并正准备要分析预期的快乐和痛苦(33d-e)。他在对真正快乐的本性(51b-e)进行分析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苏格拉底在引入(Y)32d-33c这段话之前,柏拉图已经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前提,即如果痛苦在于消解,快乐则在于恢复,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第三种更为神圣的生活(32d-e)。如此理解,我们便可明白,柏拉图为何暗示(26)G. R. Carone,“Hedonism and the Pleasureless Life in Plato’s Philebus”,Phronesis, Vol. 45,No. 4,2000,p. 262,n. 11.诸神不会体验到某种快乐或痛苦,即祂们不会体验到混合的快乐或痛苦,就后者而言,其中的每种状态都是由前一种所引起的。而且,从内容结构安排角度看,《菲丽布》中否认神感到快乐和痛苦的说法恰好出现在涉及宇宙论的段落之后,并暗示宙斯有一个王者般的灵魂(30d)(27)A. J. Mason,“On the Status of Nous in the Philebus”,Phronesis,Vol. 59,No. 2,2014,p. 159.。因此,《菲丽布》就像其他对话录所做的那样,试图重新定义奥林匹斯诸神或一般意义上的神的本性(Philebus48b-c;cf.Timaeus34b,92c)(28)T. K. Johansen,“The Timaeus on the Principles of Cosmology”,The Oxford Handbook of Plato,ed. by G. F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 477-478.。柏拉图的主要观点是,与荷马诗歌传统相反,诸神的特权与其说是随心所欲地体验混合的快乐(甚至倾向于纵欲过度和到处撒谎),不如说是享受纯粹的、不受阻碍的快乐(29)G. R. Carone,Plato’s Cosmology and Its Ethical Dimensions,pp. 114-115.。
可是,快乐真的与“神性”(神圣)沾边吗?从《菲丽布》看,柏拉图至少将某些快乐与神性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论真快乐时,苏格拉底首先将嗅觉快乐(30)E. Fletcher,“Plato on Pure Pleasure and the Best Life”,Phronesis, Vol. 59,No. 2,2014,p. 127,n. 29.视为不那么神圣的一类快乐,以表明存在一种神圣类型的快乐(51e)(31)D. Wolfsdorf,Pleasure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 97.;其次他把一种知识,即以神圣球体本身为关注对象的知识,视为本身是神圣的东西(62a8,b4);最后在指出这类知识通常伴随着纯粹快乐之后(52a-b),他又重申把纯粹快乐归于知识的产物是非常合适的(63e2-5)。
那么,最神圣生活如何与混合生活关联在一起的?柏拉图在《菲丽布》中把神想象成一个宇宙神,本质上是智慧的,并且与“相”有接触,神的理智可以最大程度地分有伴随知识而来的快乐。最纯粹思考(55a6-8)的生活属于最神圣的生活(33b6-8),这不仅表明诸神会思考,而且表明诸神有生命(cf. 33a-b)。如果像《菲丽布》和其他对话录所表明的,神是有生命的存在(cf.Phaedrus245c-e;246b-c;Sophist249a;LawsX 899b;Timaeus30d,32d,40a-d,92c)(32)G. R. Carone,“Hedonism and the Pleasureless Life in Plato’s Philebus”,Phronesis, Vol. 45,No. 4,2000,p. 263.,那么当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两次断言无论是徒有智思的生活,还是徒有快乐的生活都没有资格成为一切有生命的存在所选择的“好”时(一次是22b;另外一次是60c-d),柏拉图肯定不能随便说“这个限定只针对除神之外的所有生物”。与《菲丽布》同一时期写成的《蒂迈欧》也暗示,诸神体验到了快乐(Timaeus37c6-d1)。如果诸神确实体验到快乐,那么祂们将是人类的典范,因为神的构成元素比我们的精微美好,祂们的体验质量比我们的好。但不能说神的体验质量与我们的体验质量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这在于“宇宙”包含所有与我们人类相同的元素(Philebus30a)。因此,人神之间没有互不通气的隔阂。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在其伦理讨论中会把人神放在一起来谈论或对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苏格拉底在《菲丽布》快要接近尾声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人神之中,究竟是快乐还是智思更接近“最高好”、更有价值(65b)?可见,包括诸神在内的一切生命存在都在享受着一种快乐与知识相结合的幸福。这再次强调了神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是他们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离,因为这种亲密,神可以作为人类的近似模型(33)E. Fletcher,“Plato on Pure Pleasure and the Best Life”,Phronesis, Vol. 59,No. 2,2014,pp.141-142.。由此应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生活(无论是被称为最神圣生活还是混合生活)包含快乐。
三、混合快乐与生成
上述分析至少表明两点:其一,柏拉图的第一好的幸福生活是那种至少包含某些快乐的生活,而不是像弗雷德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无乐生活(中性状态);其二,至少纯粹快乐可以是好的或具有内在价值。然而,弗雷德从形而上学角度入手指出,如能证明柏拉图在《菲丽布》中认为快乐一律是一种生成(genesis),那么快乐本身因其形而上学地位低下就不可能是好的。为支持这一论点,弗雷德引用了生成与存在(ousia)这对范畴(54c-d)。按照弗雷德的解释,柏拉图一方面否认生成本身可以是好的或具有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又把所有快乐都当作生成(53c-55c),所以柏拉图肯定不会自相矛盾地认为快乐本身可以是好的。本文不同意弗雷德的这种解读,主张快乐在《菲丽布》中并没有被仅仅视作生成,即快乐并非不可能是好的。为支持这一论断,本文采取的策略将是集中考察这些段落出现的上下文语境和意图,以及柏拉图在分析快乐时利用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苏格拉底把快乐当作一种生成(53c-55c),但我们应该对此将信将疑。有些阐释者把苏格拉底的这种描述解读为快乐的一个本体论定义,如弗雷德认为《菲丽布》中的所有快乐都可以被不加区别地描述为补充损耗的过程。但我们应当注意53c-55c这个文段所采用的假设模式以及如下这一基本事实,即苏格拉底在整篇对话录中并未对“快乐即生成”这一论点做出任何严肃的承诺。相反,他说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快乐总是在生成,快乐根本就没有‘存在’吗?有一些聪明的人试图向我们宣布这个论点,我们应感谢他们。”(53c3-7)苏格拉底虽觉得这个理论对理解快乐的本性大有裨益,但还是刻意与之保持距离,极力撇清自己与它的关系,说它是别人的,即那些聪明人的发明(34)Plato:Philebus,trans. by J. C. B. Gosling,pp. 220-221.。
根据《菲丽布》的看法,存在属于一种本性上最高贵的东西,它自足充盈,无所欲求;相形之下,生成则属于一种次于存在的东西,欲求他物。进言之,后者总是为了某种东西而生成,前者则是后者得以生成所为着的那个目的(53a-e)。在此意义上,生成是为了存在,而不是相反,这就像造船是为了船一样,而不是相反(54a-b)。正因为生成是为了存在,所以所有在生成中起作用的事物也都是为了存在而生成的。目的属于“好”的范畴,而为了某物而得以产生的东西则应被放置在另一范畴之中(54c8-11)(35)C. C. Meinwald,“The Philebu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lato,ed. by G. F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 499.。苏格拉底由此得出,如果快乐真的是生成,那它必然是为了某种存在而得以产生的,因此它应被放置在一个有别于“好”范畴的范畴之中(54c5-7,d1-2)。
可是,快乐真的是生成吗?西尔弗曼(A. Silverman)(36)A. Silverman,The Dialectic of Ess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 241.支持弗雷德的看法,强调根据柏拉图,即使纯粹快乐是有尺度的、非混杂的,它们仍属于“生成”的范畴,总是有所欲求。在柏拉图看来,快乐不管是纯粹的还是混合的,都不可能是一种“好”(37)D. Wolfsdorf, Pleasure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p. 27.。笔者不认可这种解释,理由有两个方面:
第一,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看,必须承认苏格拉底并没有将所有快乐都视为生成。他也从未明确声称“快乐即生成”,只是把一些快乐定性为生成。他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利用这种定性来嘲笑那些声称“快乐即好或是好的”的人,以及在“生成”(如干渴、饥饿和其他情感)中寻求满足并乐此不疲,甚至扬言若没有伴随这些情感而来的东西就不愿活的人(54e)。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些人的可笑之处在于,既然生成的对立面是毁灭,那么他们到头来所选择的则是毁灭和生成,而不是跳出“生灭”死循环,追求那种无一般快乐或痛苦的第三种生活,即最纯粹思考的生活(55a4-8)。
第二,从写作意图角度看,柏拉图插入53c-55c整段文字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所有快乐都可以构成“好”(13b,60a,66d)。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快乐若属于生成领域,而非存在领域,就不是“好”;其二,快乐若是唯一的好,那么一个人是好是坏,将不取决于其是否有美德,而是取决于他在经历着快乐还是痛苦。这必然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最好之人在经历着痛苦时也会变坏,沦为坏人(55b;cf.Gorgias498a - 499b)。因此,从柏拉图的角度看,探索快乐是不是一种生成的理论,将是一个有用的反快乐主义工具,它可以戳穿任何快乐主义的伪装,以打消它们把快乐标榜为“好”或“唯一的好”的念头。
然而,柏拉图是否想要将这个理论,即他在《菲丽布》中提出的来自聪明人的论证,应用于他对快乐的整个说明呢?显然不是。我们应注意到柏拉图引入生成和存在这一对范畴,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快乐的批判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发生在他引入纯粹的快乐(Philebus50e)之后。在对这些纯粹的快乐加以详述,并将其与混杂(不纯的)快乐区分开来之后(50e5- 5lb7),他接着补充道:
强烈的快乐是无度(不均衡)的,与之相反的那一类(即纯粹的快乐)则是有度(均衡)的。允许数量大和强烈介入的快乐,不管它是经常表现得这样,还是偶尔如此,都应归到“无限”那一类,即存在于身体和灵魂中的“较少较多”那类。其他种类的快乐则应归入具有尺度的“那一类”事物当中去。(52c-d)
这段话将当前对快乐的讨论插入先前讨论快乐(23c)时所立足的本体论框架内。根据这种框架,无限(apeiron)这一类东西因其缺乏限度或完善而区别于限度(24b8),它们总是“变得或多或少”(24e6-8),流动不息(38)G. R. Carone,Plato’s Cosmology and Its Ethical Dimensions,p. 86.。这与限度这一类东西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通过引入比例或量度(25a5-b2)处于不动、安息之状(24d5)(39)J. M. Cooper,Reason and Emo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 151-152.。但这对我们理解53c-55c提出的聪明人的论证有何帮助?
其作用在于让我们认识到,聪明人把快乐当作生成的论点与苏格拉底把快乐说成是属于无限这一类事物,是非常契合的。快乐如同无限这一类事物一样,因其波动性质往往显得或多或少(24e6-8;cf. 24b)。如果对照《高尔吉亚》来看,柏拉图在此抨击的是卡里克利斯式的那种快乐主义,后者将快乐视作对身体欲望的满足,不仅主张欲望本身是痛苦的,而且认为快乐的强度与其满足的欲望的强度成正比(40)G. Santas,“Plato on Pleasure as the Human Good”,ed. by H. H. Benson,A Companion to Plato, 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 318.。根据柏拉图,所有卡里克利斯式的快乐都是混杂的或不纯洁的。这类快乐的贪得无厌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它们伴随着痛苦的缺乏而来时,它们就获得强度(Gorgias493d-e)。因此,选择这些作为生成的快乐的人,就是在选择它们的对立面,即痛苦和毁灭(Philebus55a5-7)。作为自身没有确定的量度或程度的东西,无限缺乏限度,缺乏规定性,所以若有人试图以生成的形式来寻求“完善”(完美)无疑是荒谬之举(26a4-6)。达到完善或完美的是限度,而非无限(41)R. M. Dancy,“The Limits of Being in the Philebus”,Apeiron,Vol. 40,No.1,2007,pp. 40-56.。柏拉图在《菲丽布》中引入纯粹快乐,标志着他对于快乐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他开始认识到,不同的快乐具有根本不同的本性,进而由衷地接纳纯粹快乐,并感到不加区分地将所有快乐一个棍子打死是不妥的。纯粹的快乐即是不掺杂痛苦的快乐。只要纯粹快乐拥有比例或量度,它们就有了限度,因而就有了稳定性(cf. 24d,25a-b,26b,26d)。量度和比例在任何地方都是“美”和“好”(64e;cf. 65a)。强烈的混合快乐仅仅是生成,因而不具有稳定性。相形之下,纯粹快乐内部隐藏着一种完善状态,因而时刻保持着其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并享有其对象的稳定性,所以有资格成为某种“存在”的候选者(27b)(42)R. Fahrnkopf,“Forms in the Philebu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 15,No. 2,1977,pp. 202-207.。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一些快乐将能够成为本身就是好的东西,即具有内在价值,其原因如《菲丽布》所表明的,存在作为生成的目标,属于“好”的范畴(54c)(43)J. Wood,“The Unorthodox Theory of Forms in Plato’s Philebus”,Journal of Ancient Philosophy,Vol. 11,No. 2,2017,pp. 45-81.。柏拉图最后的“诸好”(44)E. Fletcher,“Plato on Pure Pleasure and the Best Life”,Phronesis, Vol. 59,No. 2,2014,p. 142.排名表也给纯粹快乐留有一席之地(66c)。如果纯粹快乐被视为生成,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出现在对话末尾的那份“诸好”的清单中。正如《菲丽布》所示,如果快乐真的是生成,那么它应被置于“好”的范畴以外的范畴中(54d)。柏拉图把纯粹快乐作为一种“好”来对待,表明他并不是说所有的快乐都是生成,所以他的快乐理论不能简单等同于聪明人的理论。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柏拉图在《菲丽布》中认为,某些纯粹的快乐本身是好的或有内在价值,因而人类的最佳生活不是无乐的纯思生活,而是快乐和智思的混合生活。如此观之,与《高尔吉亚》和《斐多》等许多早、中期对话中对快乐的负面评价不同,《菲丽布》不仅将某些快乐融入人类最好的生活中,甚至把快乐与智思的混合生活视为比单纯的智思生活更好的生活。因之,我们不同意某些学者的观点,即主张《菲丽布》仍旧认为对人类来说,无快乐的智思生活要比混合生活更好,无乐的神性生活优于有乐的人类最好生活。这些学者之所以倾向于低估快乐对最好人类生活的重要贡献,主要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菲丽布》中提及的所有快乐都具有相同本性,在本体论上都是次于“存在”的“生成”,因而与作为目的的“好”不沾边。本文的分析表明,柏拉图其实并没有对快乐给出一个通用的描述。相反,不同类型的快乐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属于不同的“存在”类别。这种本质区别奠定了对其评价的基础。在该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也确证某些快乐如纯粹快乐是真正的“好”,是最好生活的必要成分。诸多快乐确有某种近似的普遍共性在,但不能以某种通用公式刻板以求,因为并不是任何快乐都一定能纳入某一类之中:有的可以是“存在”,有的是“生成”,或与“存在”的综合或恰好介乎二类之间。快乐的本性是复杂的,《菲丽布》中做出的理论上的种种区划分析,是为了帮助而不是去束缚对幸福生活的构成要素的认识。这种对快乐的本性与价值做出的新评估,乃是《菲丽布》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其最终揭示了贯穿于对话始终的一个评价原则:不同种类的快乐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