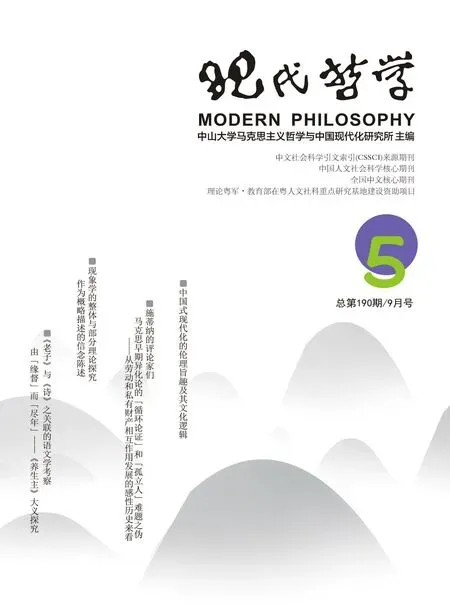先秦“乐”之五种审美形态的嬗变
2023-03-31王顺然
王顺然
一、绪论:作为背景的文化多元性
在近30多年的研究中,先秦时期“乐”常被划分到“雅乐”与“新声”(或“俗乐”“淫乐”)两种类型中(1)简摘数例,作为参考。比如,李方元在1991年和2018年的《音乐研究》中以“雅郑”二元区分到:“在周代,宫廷雅乐是当时重要的音乐现象之一,与雅乐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音乐现象,是春秋初逐渐活跃起来的郑声……由此开始,历史上雅、郑观念就形成了长期的对立。”“‘雅郑’一语,初出春秋末孔子之口,‘雅郑’对立之学术范畴亦由此而生。”又如,钱志熙以“雅俗”二元说,“所谓侈乐、郑声、淫声,都是与雅乐相对的俗乐的代名词,是春秋战国音乐变革中的现象。”再如,有学者直说:“作为一种音乐学的术语,雅乐与俗乐相对……濮上之音与宋音、郑音一样都是俗乐。”(参见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与郑声》,《音乐研究》1991年第1期,第15页;李方元:《“乐”“音”二分观念与周代“雅郑”问题》,《音乐研究》2018年第1期,第43页;钱志熙:《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24页;邹京航、曹建国:《试论周代雅乐制度》,《渤海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15页。),导致学界常以“雅”“淫”对立来解释先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的“乐”审美(2)将多种审美追求统归在“雅乐”一类之中,一方面使“雅乐”概念泛化,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一种“雅”“淫”对立的印象。例如,修海林讲:“从历史文化的延承讲,周代的礼乐活动只是原始祭典活动的延续、总结以及制度化。”“对立”的印象不断固化,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如“先秦俗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感观审美欲望的需要,因而其音声中便包含‘淫’‘过’‘凶’‘慢’四种特征;先秦雅乐,主要适用于宗庙、朝堂等仪式需要,因而表现为缓慢、平稳,肃穆、庄严,广大且曲直得当等音声特征”。(参见修海林:《周代雅乐审美观》,《音乐研究》1991年第1期,第74页;何涛:《论先秦俗乐、雅乐的音声特征》,《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第185页。)。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乐”审美形态的发展是在多元文化相融互摄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新的形态往往根据旧有的文化元素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新的形态需要参与到多元文化的激荡与选择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3)孔子对“三代损益”的讨论就体现出这种文化、制度的动态发展。(参见陈来:《三代礼制之损益》,《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16-219页。)这样,“乐”之审美形态应呈现出多样性与过渡性,以《礼记·明堂位》的记录为例:
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鼓。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
面对殊异的文化传统,周公以“兼容并蓄”之策,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使虞、夏、商、周四代,华夏、夷蛮的不同文化有机共存。(4)“兼容并蓄”是小邦周的传统,“周人在灭殷之后,最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如何以自己微弱的主观力量来有效地统治广大的异族。当其封诸侯、建同姓的时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这些有血缘关系的诸侯来‘藩屏’周室”。(参见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页。)这开启了中华文明从“祭祀时代”走向“礼乐时代”的进程,也塑造了周初文化的多元性。(5)“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夏以前是巫觋时代,商殷已是典型的祭祀时代,周代是礼乐时代。”(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10-11页。)同样是对这一理念的贯彻,周公“作乐”,既有对不同制式乐器、乐律的融合,又有对不同风格乐曲、乐舞的兼采。由此,文化的多元性投射为审美形态的多元性。我们探讨先秦时期“乐”之审美形态发展与变革,也要在这种文化多元性的大背景下展开。(6)文化的渐变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对颜色的偏好与崇拜,也是其中的一个小中见大的角度。(参见郭静云:《从上下到五方:礼仪的色谱与“无色”概念之形成》,《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99-773页。)
二、欲:从“靡靡之乐”到“亡国之音”
可以说,商纣王帝辛对传统的叛离,拉开了“乐”之审美形态变革的序幕,我们也就不妨先从帝辛的“新声”改革谈起。帝辛对传统的叛离,从《尚书·泰誓》记录周武王姬发对他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出,其言:“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考虑到后世对商纣王罪状的累加(7)顾颉刚曾综合考证,发现纣的70多条罪状都是周朝以后逐渐增加,剧情也逐渐强烈,战国时期增加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对“德行”的崇尚,尤其是以“德行”衡量商纣王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周文化倾向。又以“酒”为例,《酒诰》借对“酒德”的确立展开对纣王的批判,但对“饮酒”本身而言,“酒德”是一种限制。(参见余治平:《周公酒诰训--酒与周初政法德教祭祀的经学诠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58、171、236页。),《史记·殷本纪》评价帝辛时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里,帝辛对传统的反叛主要是以高扬个性、突出个人价值,来对抗祭祀传统中对神祇的歌颂和对祖宗的宣扬。
“新声”的创制也体现这一点,《殷本纪》说:“(帝辛)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慢于鬼神。”帝辛以“新声”废弃“(殷)先祖之乐”,形成以“欲”为中心、“高扬个性、轻慢鬼神”之新审美形态。新的审美形态既表现为顺从欲望的猎奇心理,如对“狗马奇物”的追求,也表现在对新奇乐器、乐舞的创制。比如《释名·释乐器》说:“箜篌,师延所作靡靡之乐也,后出于桑间濮上之地,盖空国之侯所存也。”(8)[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31页。按照刘熙的讲法,“箜篌”是纣王乐师师延专门为配合“靡靡之乐”而创造的、复杂的丝线类乐器。丝线类乐器多是小型乐器,本来有“更为灵活轻便,声音也更为婉转清脆、细腻柔美,表现力更强”的特点(9)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而“箜篌”作为一种大型的丝线类乐器有着更广的音域和更丰富的表现力,足见帝辛之“新声”对“婉转清脆、细腻柔美”的追求。
同样出于“桑间濮上”的“亡国之音”,代表了帝辛以“欲”为纲的审美在后世的传承与发展。《礼记正义》记郑玄注说:“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巳而自沈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1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8页。按照郑玄的说法,“桑间濮上”的“亡国之音”与帝辛“新声”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韩非子·十过》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灵公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师涓鼓究之……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11)[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全6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7-70页。
据文所见,卫国旧地“桑间濮上”保留了帝辛遗留的“新声”。至春秋中期,卫灵公偶然得之,可知此“新声”并不在常规演奏的周乐中。其中,师旷的表现也值得注意,他是在“(乐)未终”时制止了演奏,并非“乐”一开始便制止演奏。可见他虽未曾听闻,却应在乐师的传承学习中了解“亡国之音”的特征。同时,重出江湖的“新声”表现出强大的感染力,就通过卫灵公这次采风的契机很快在中原诸侯国流行起来。(12)照季札对《卫》的评价看,“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可以说,作为周姬姓子孙,早期卫国很好地传承了周公礼乐的审美传统,以“周德”所谓审美追求,所以季札在鲁观之《卫》并非“新声”“淫声”。卫灵公之于南子与帝辛之于妲己成呼应之势,卫灵公“闻鼓新声者而说之”可以算作帝辛审美的“知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淫声”的迅速“崛起”扰乱了“正乐”的合理秩序,成为春秋礼乐崩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左传》的编年,卫灵公见晋平公约在公元前533年左右,而子夏为魏文侯师约在公元前424年左右。
“新声”的“复兴”影响巨大,加速了先秦时期“乐”之审美形态的变革。《礼记·乐记》记子夏与魏文侯论乐一段,就讲到“新声”的审美发展出“郑”“宋”“卫”“齐”四种风格:“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若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论乐”为参照,我们能看到百年间“郑”“宋”“卫”“齐”四地之乐的变化趋势:其一,季札评“郑”是“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而子夏说郑音“好滥”,以“滥”取“滥窃”“过度”之意,显然郑音“细”而繁琐的特点在“新声”审美的刺激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3)郑玄依照《诗经·郑风》中男女寄情的篇目较多而注“滥”为“滥窃”,可备一说。([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311页。);其二,季札的品评虽不包含“宋”,但子夏口中宋音之“燕女”是讲乐舞中女子妖娆的表现,体现了以“欲”为纲的审美特点;其三,季札评“卫”是“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这里的“卫”是周天子乐,是正面地表彰“卫康叔、武公之德”,而子夏评卫音是“趋数”,郑玄注“促速”有追求表演技艺之意(14)表演技巧分很多类,其中就包括对乐器、乐律的追求,《汉书》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类似“箜篌”一样,丝弦乐器如果弦音过密,旋律的情绪表现力就会加强。“破其瑟”的说法,即将相邻弦音变大。,或可说卫灵公以降,卫国受“新声”的影响而改弦易辙;其四,季札说“齐”是“泱泱乎,大风也哉”,这种“昂扬”的风格经“新声”宣扬个性的鼓动,转为“敖辟”之音。
总之,帝辛创“新声”在叛离传统的同时,拉开了“乐”审美形态嬗变的序幕。在“高扬个性、顺从欲望、轻慢鬼神”的审美追求指引下,“新声”至战国初期已经发展出“郑”“宋”“卫”“齐”等多种风格。风格的多样性出于“欲”的追求,如《韩非子·十过》中平公所讲:“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15)“在一片批评声中,战国俗乐仍不可阻挡地发展,不仅吸引了一般的人,就连魏文侯这样的好古者,也不得不承认新乐对于他的吸引力远远胜于古乐。”(钱志熙:《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25页。)为顺遂各国国君不同的“所好”,以“欲”为中心的“新声”得到从乐器到乐曲、再到乐舞等层面的多重发展。值得补充的是,除了器物、乐理的层面外,到汉武帝时期,乐师李延年追求以天性之欲直击人心,是以“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汉书·外戚传》),由“欲”进“道”,代表着形上层面对“新声”的辩护。
三、语:从“接引神祗”到“圣王德行”
帝辛创“新声”背弃“先祖之乐”,这里的“先祖之乐”指的是殷商祭祀传统的“古乐”。周公“制礼作乐”效法“四代乐”“六代乐”,这里的“四代乐”“六代乐”指上古传承的“古乐”。总体上,无论是“先祖之乐”,还是“四代乐”“六代乐”,基于其形式的一致性和传承(说)的连贯性,可以统称为“古乐”。这里“形式的一致性”是指,这类“古乐”通过“在舞台上构建起一个脱胎于历史情景的意义世界”来“展现圣王德性生命的历程”。(16)王顺然:《从“曲”到“戏”--先秦“乐教”考察路径的转换》,《哲学动态》2017年第5期,第47页。而“传承(说)的连贯性”是指,传世或传说的“古乐”比较固定(17)从指称内容上看,对帝辛而言的“先祖之乐”相对确定,是指以汤乐《大濩》为代表的殷商祭祀之“乐”,而周公假托的“四代乐”或“六代乐”却存在争议。但无论是数目问题差异还是篇目差异,基本不影响本文的讨论,故不赘述。。质言之,“古乐”审美的核心是“语”,是带有政治功能的言说。我们可以借用以下文段来简要概括:
(上)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祗可得而礼。(《史记·孝武本纪》)
(中)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礼记·乐记》)
(下)夔!命汝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舜典》)
由引文(上)可以看出,“古乐”在祭祀中发挥重要作用,用以接引神灵、祖先。《尚书·益稷》记录帝舜时期创制《韶》的过程也有类似描述:“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闲。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这里的“夔”是帝尧、舜时期的乐官,他是以“咏”的形式让乐来“语说”祖宗的光辉事迹,而特定乐器、乐曲的运用是为了让这些赞扬传递给祖宗神灵。“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闲”,就是以特定的声音、节奏来引导神灵的降临。可见,整个乐舞的文辞、配乐、配舞都是为了方便接引祖宗神灵。反之,只有祖宗神灵降临的乐舞具有了“神迹”,才能保证神圣意志、保证祭祀传统中乐舞的正统性。
这种对“古乐”神秘性与神圣性的强调,似乎更符合殷商以前的祭祀传统,从文献看也是这样。李方元就认为,“西周后的雅乐作为直接体现宗教精神的意义开始有所减弱,而作为社会政治工具以维护等级制的功能在加强”(18)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与郑声》,《音乐研究》1991年第1期,第21页。。而周以降,“古乐”的祭祀价值发生两大变化。
其一,强调祭祀用乐的规范化。如《周礼·大司乐》讲:“舞《云门》,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祭祀的神圣性显然受“神迹”的影响:既然只有“夔”能够以乐引“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那么“夔”就有担当“大司乐”的神圣身份;既然“《箫韶》九成”能使“鸟兽跄跄、凤皇来仪”,那“乐”就有与天地、鬼神、鸟兽的神秘关系。《周礼·大司乐》对“六代乐”演奏的规范,削弱了其中的神秘性:一方面,“六代乐”的演奏分别对应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这种关系清晰明确;另一方面,对演奏的次数及效果,从“一变(遍)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到“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讲明了准确的对应关系。
其二,对“古乐”解释的德行化。《白虎通·礼乐》就讲:
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颛顼曰《六茎》者,言和律历以调阴阳,茎者着万物也;帝喾曰《五英》者,言能调和五声以养万物,调其英华也;尧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箫韶》者,舜能继尧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顺二圣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汤曰《大护》者,言汤承衰,能护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像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故诗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此之时,天下乐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
引文的这种解释显然是在《大武》定型之后才得以系统建立,它将“古乐”在祭祀中的神秘作用,转化为人人可理解的德行表现。以《韶》乐为例,前引《尚书·益稷》文本重点讲《韶》的演奏如何产生神秘现象,却并没有说以《韶》是“舜继尧道”;到《春秋繁露》,是说“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这种讲法依然保留了一些神秘的意味;到了《白虎通·礼乐》,就只剩下“舜继尧道”的说法。
综上,“古乐”在祭祀中的神秘作用,逐步转化为对祖先、神灵之德行的宣扬,“语(说)”的对象也从“祖先、神灵”转向“人”。可以说,以“语”为核心的“古乐”审美形态发生了从崇拜“神秘”向效法“德行”的转化。《周礼·春官宗伯》对“大司乐”职责的解释证明了这一转折:“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语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这里体现了周代学校对“乐”的使用,主要是以其中德行的体现来教化学子。
除在祭祀的作用外,(中)(下)两条引文则体现着古乐“封赏诸侯”和“教化冑子”两种作用。这两种作用也是相辅相成,代表着古乐以“语”为核心的审美宗旨。
从封邦建国的角度看,以“乐”封赏诸侯表达了天子对诸侯政治身份的认同,也代表着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对“制乐以赏诸侯”有这样的疏解:“礼乐既备,后乃施布天下也……明圣人制乐以赏诸侯,其功大者其乐备。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教天下之孝也。‘夔始制乐以赏诸侯’者……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风》以赏诸侯,使海内同孝也。”宣扬《南风》之教化,是诸侯对其政治身份的认同。这里的“孝”重在德行与政治规范,是“欲天下同行舜道”的一环,与后来儒家所重之“德性”有所不同。当孝行成为自上而下的风尚,也代表着天下对帝舜的拥戴。
王道施之于诸侯与王道传承于“冑子”是同样的道理:前者是将“孝”等德行与政治规范,依靠乐之“语(说)”封赏诸侯、宣告天下;后者则如《舜典》所说,是将“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等为政者的政治德行通过乐之“语(说)”教化“冑子”。随着“古乐”宣扬之德行价值不断凸显,它们便化身为“语说”圣王“德行”的载体,“古乐”的神秘性弱化的同时,其用以“封赏诸侯”和“教冑子”的两种作用也变得更为重要。
可见,以“语”为审美宗旨的“古乐”和以“欲”为审美宗旨的“新声”有很大不同,前者注重效法前贤的政治德行,后者追求个性的极致表现。这种差异经商周两代的文化互动而愈发显明,催动着“乐”审美的发展与变化。
四、美:多元价值的混合
“古乐”“新声”之争为先秦时期“乐”审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而周公的“制礼作乐”则将多族群不同审美传统融合到周乐的体系中。如前引《礼记·明堂位》所见,周公制作之“乐”是融不同乐器、乐律于一体,在同一场景中按照特定次序进行演奏,如文见:“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按《礼记正义》孔颖达疏曰,“升乐工于庙堂而歌《清庙》诗”,“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诗”(1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094页。,这是讲堂上、堂下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表演。又曰“非唯用四代之乐,亦为蛮夷所归,故赐奏蛮夷之乐于庭”,这是讲“乐”之制作既容许《大夏》《清庙》等六代乐共存,又容许“奏蛮夷之乐于庭”,根据《白虎通》的解释,庭中所奏的蛮夷之乐“《朝离》《南》《昧》《禁》”分别表达“生、养、杀、藏”四种不同价值。综合来看,周公的“兼容并蓄”稍显杂乱,这种复杂的、排列式的融合降低了“乐”审美形态的内在一致性。
上述《明堂位》的引文代表了相当一段时间内周乐的演奏形态,使得这一时期的审美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换言之,在整个“乐”在演奏过程中,每一部分的“美”都可以进行独立的判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一段对此有充分的展示,文见: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
(一)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a)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
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
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
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b)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也。”
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枫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c)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为之歌《陈》,曰:“(d)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为之歌《大雅》,曰:“(e)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f)至矣哉……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二)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
见舞《大(20)“大”字的出现代表着季札所欣赏的“周乐”已经是几经更迭的周乐,较之周公制作之乐已经有所丰富。(参见王顺然:《从〈大武〉“乐”看戏剧教化人心之能效》,《戏曲研究》第104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147页。)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见舞《韶濩》者,曰:“(g)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
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
季札继承周乐传统(21)吴公子对周公传统的继承,代表着周天子文化的熏陶。(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24页。):其一,“吴公子请观周乐”与《明堂位》所说“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契合,鲁用周公之礼乐、传承有序,季札来鲁国赏乐、评乐是再现周公审美之意趣;其二,季札所赏之周乐确有“兼容并蓄”之气象,八方诸侯之歌诵、“濩”“夏”“韶”“武”四代圣王之乐舞尽在其中。同时,季札赏评“周乐”是对乐曲所反应之诸国风俗、政治进行判定与预言,这一方式也是以乐封赏诸侯的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点评确是对每一部分的“美”进行相对独立的判定:其一,将堂上之歌诵(一)与堂下之乐舞(二)分而论述;其二,诸侯之“风”与周之“雅”“颂”各按标准;其三,“自《郐》以下无讥”一句表现出除风俗政治的审美旨趣外还有其他的审美判断。根据季札的评价可知,这一时期周乐的审美形态以“美”这一概念为核心,将多重含义、多重标准收摄其中:“美”既可以从政治规范的角度来讲,是表现于《周南》《召南》的“勤而不怨”,表现于圣王之乐的“周之盛”“圣人之难”“勤而不德”“天之无不帱、地之无不载”,等等;又可以从感官感受的角度来讲,是表现于《郑》的“其细也甚”;同时,季札评价时使用的“(a)美哉”“(b)大之至也”“(c)思深哉”“(d)国无主”“(e)广哉”“(f)至矣哉”“(g)圣人之弘也”等概念,都统摄在“美”的范畴之中。(22)为了表明《韶》乐“美”到极致,季札将“德至矣哉”“大矣”“观止矣”等说法连起来,强调《韶》各方面的“美”。
当然,“各美其美”的审美形态也与政治、文化政策的“兼容并蓄”相互参照。周乐对不同传统的容纳,是在尊重不同传统中“美”之多元性的同时,将多元文化传统中的“乐”向着“四代乐”引导,突出对圣王德行的歌颂,这一点也印证了前文对“古乐”的讨论。从政治、文化层面讲,“兼容并蓄”有着实践中的过渡性和局限性。同样,“各美其美”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互动的审美形态,创造了一个审美形态相互借鉴的氛围。但这种审美形态并不稳定,不同传统间的张力需要在变革与发展中获得释放。
五、人/仁:从“习乐见人”到“依仁游艺”
根据《左传》《国语》等文献的记录,至春秋中晚期,多元文化传统进一步碰撞,“乐”不仅在祭祀中的神秘作用不断弱化,其政治功能和现实价值也逐渐消解。在此背景下,孔子提出“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说法,以“仁”之超拔,为“乐”开出“见其人”的审美形态。“见其人”一词出于“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在《史记》《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均有记录。《史记·孔子世家》曰: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引文将孔子学琴分为“曲”“数”“志”“人”等四个阶段:一者,每一个阶段都对应一种独立的审美标准;再者,不同审美标准依次排列、不断超拔,形成一统摄的审美形态。
将四个层次分而论之,依次来看:
“习其曲”,代表孔子从“欣赏者”转以“演奏者”的身份来面对《文王操》,这种转变能使孔子对乐曲的领会更为细致。一段时间后,师襄子第一次对孔子说“可以益”,鼓励孔子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旋律)来学习。不断寻求新的内容,对应着“好新声”的审美追求。
孔子并未采纳师襄子劝其求“新”的建议,而是进一步在“曲”中见“数”。前文见季札说《郑》是“其细(数)已甚”、子夏评《卫》是“趋数烦志”,“数”“细”都是对应乐律来说的。“习其数”,一方面代表着孔子能够像乐工一样从乐律层面来处理乐曲,另一方面代表在跟随感官感受而“求新”之外,知觉理性也可以介入对乐曲的理解。因此,“数”本身成为一个有别于“曲”的独立审美标准。
顺着“数”向前,“志”“意”就在理解中逼显出来。“志”“意”与“古乐”的审美形态相关,重在乐的“语(说)”教化能力。师襄子传承乐教,对“志”“意”之境很熟悉,也就能看出孔子“得(曲之)志”的不凡之处。真正令师襄子“辟席再拜”的,是孔子达致“见其人”之境界。
这里需要对照《韩诗外传》的相关引文来看。(23)《史记·孔子世家》引文与《韩诗外传》相关文本的差异需要注意。前者将孔子学琴分为“曲”“数”“志”“人”等四个阶段,《韩诗外传》则增至“曲”“数”“意”“人”“类”等五个阶段。对照《论语》的语词习惯来看,《韩诗外传》所用的“伟”“粉”“弹”“丽”等不符合孔子的言说习惯,而且“类”更接近一种对“见人”的补充性解释,由此推知《韩诗外传》“孔子学琴”之成文当在《史记》之后。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孔子是以“伟”“粉”“弹”“丽”等乐曲表达的“志”“意”,归纳出作曲者有“仁”“和”“智”“殷懃”的德行,再根据这种德行之“类”倒推出作曲者是周文王。这一说法将“见其人”“得其类”“习其志”等都落在外在德行来讲,反而丢失了“见其人”的境界意义。只有将“见其人”和“人而不仁如乐何”连看,才能在“人/仁”的这个最终境界中看到从外在“德行”向内在“德性”的审美转向。
“德行”向“德性”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五行篇》记曰:“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仁德根植于内心的行为叫“德之行”,可以是尚未表现出来的“品性”,这和表现为事功之“(德)行”有差别。孔子透过乐曲看到的是文王的“仁”,这是“品性”而不仅仅是“德行”。所以说,《韩诗外传》在文本上的补充虽然让孔子之“见人”更符合逻辑,但在境界上反而落了下乘。当孔子起身“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史记》)时,是乐曲演奏过程中,心灵产生的共振与感通。《礼记·乐记》说“(乐)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文王操》作为共振的中介,让孔子对文王产生一种“同声相应”的感通。
将四个层次统合来看:孔子所言之“见其人”是发前人之未发,在境界上是对“语”之审美形态的超越。这种审美标准的建立有两层意义:一是将多种独立的审美形态融合成系统,二是为“乐”建立起内在德性的价值。正面讲,确立内在德性的审美价值,是将圣王之“圣”落在德性上讲,不同的审美标准在这一体系中得以融摄;反面讲,要提升审美境界,首先要确立对内在德性的追求。
与此相应,《乐记》记子夏论乐充分反应出子夏对孔子“见其人”之审美形态的继承。对于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的“病症”,子夏开出的对治之方是“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这也是对“见其人”三字的解释。以“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为例,君子借乐器(如“丝”)所发声音对情感(如“哀”)的引动,唤起与情感对应的德性心理(如“廉”),再将此内在德性投射为外在德行(如“志义之臣”)。(24)《礼记正义》记孔颖达疏曰:“哀,谓哀怨也,谓声音之体婉妙,故哀怨矣。廉,谓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314页。)由此,“琴瑟之声”与“志义之臣”的共振,便是君子辨识“古乐”的进路,也是“见其人”的进路。
总之,孔子提出“见其人”,恰将“乐”看作体贴圣人内在德性的依凭。其云“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就是强调在“见其人”境界中,“乐”成为启发内在德性的钥匙。
六、和:先秦“乐”审美的定型
“见其人”的审美形态已将传统中多元的审美形态加以融摄,形成一个“曲”“数”“志”“人”层层递进的体系。针对这一审美形态,先秦诸子还有进一步的争论。
墨子的“非乐”虽然闻名,但其言“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这对“乐”之审美形态而言并无损益。然墨子倡导以“利”为标准,判定当时之乐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可以看做是注重“乐”的现实功能性、政治性,也是对“语”之审美形态的复兴。事实上,真正对以“仁/人”为核心的审美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是老庄对“自然”的高扬,二是孔门后学对先秦人性论讨论的深入。
具体而言,于前者,不同于孔子以“乐”启发人内在德性,老庄将“自然”作为“乐”审美的终极追求。无论是“大音希声”(《道德经》41章),还是“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庄子·齐物论》),老庄欲在逐步消解有声之乐的过程中,进入无声之“自然”。这就在“仁/人”之外又增加了“自然”的最高价值。于后者,人情、人欲是否应该放在审美形态的最底层,得到重新审视。《荀子·荣辱》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在对“乐”之美感的探求中,人情、人欲本来就是乐官从事专业工作的重要基础。当瞽叟成为上古乐官的代表时,感官欲求也已成为神秘且私密的认知方式。可见,人情人欲在“乐”的审美追求中有特殊价值,不能简单地放在最低一层看。
同时,基于感官欲求而进行的乐器翻新、乐律更制与乐舞设计等,要分情况看待。拿乐器创制来说,有被称为圣王德行的,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有被看作放纵欲望的,如“(周景)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既然帝舜造五弦琴、周景王造无射大钟都离不开感官的指引,那么人情、人欲的“节制”与“放纵”就需要寻求新的标准来判定,“和”概念的价值也被重视起来。
按照《国语·周语下》的说法,“和”本来就是“乐”之审美形态的重要标准:“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然而,这里“和”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伶人口中制成“大钟”的“和”,与“王崩,钟不和”形成了判断的对立结果。依赖于外在后果或者事后反思,都代表着此时“和”的审美理论还有模糊性。到《庄子·天地》说“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时,“和”才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形态。“闻和”代表着“和”成为一种追求、一种从“有声”到“无声”最终指向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同于“见其人”之处,就在于它不再以向内之“仁”为追求,而走向与天地自然为一体的新路向。“和”的上升并未就此止步,“仁”与“自然”也有相通之处。到《礼记·乐记》,“和”有了系统性的解释,以“和”为核心的审美形态才得以完型。《乐记》论“和”有两段重要的文字是:
(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二)《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引文一是从宇宙气化的角度讲“和”,“乐”的审美要符合自然的规律,乐律的意义和感官欲求的价值由此建立。在这一点,“和”的理论具备了客观性与普遍性。引文二则是从人伦道德的角度讲“和”,这里包括君臣之敬、长幼之顺、父子之亲,还包括祖宗神灵的神秘关照(25)所谓“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肃肃敬也、雍雍和也。《礼记·少仪》也说“鸾和之美,肃肃雍雍”。可见,“和”在祖宗神灵的层面接续了“乐”在祭祀传统中的审美旨趣。,安顿人情的尺度由此证成。“和”在宇宙气化和人伦道德两方面的意义是并行的:一部分感官之“欲”归摄在对自然的认知和对自然美的追求之中,一部分性情之“欲”归摄在对人伦的直观和对伦常和谐的维护中。
以此再看“舜作五弦琴”和“景王作大钟”两例,不难发现:从自然的角度比较,帝舜之“五弦琴”和于音律、《南风》悦耳动听,景王大钟的巨大声响反而直接伤害了景王的生命;从伦常的角度比较,《南风》宣扬孝悌、注重人伦,景王为造大钟以君压臣、耗费民财,违背君臣之敬、父子之亲。这种审美标准不再向外寻求神秘后果,而是将判断内化于“乐”本身之中。
可以说,《乐记》用“和”融摄了多元的审美形态,成为先秦时期“乐”之审美形态的一个综合。“和”的审美,摆脱了“古乐”审美的外在性与神秘性,修正了“曲”“数”“志”“人”层层递进的线性结构,吸收“欲”作为审美形态的一个支点,并开出通向“自然”“人伦”的两层价值。
综上,站在多元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看,先秦时期“乐”之审美形态是在相互批判与吸纳之中逐次展开的。在经历“对立”“兼容”“归摄”等阶段后,“乐”之审美先后表现出以“语”“欲”“美”“人(仁)”“和”等观念为核心的五种形态。加之每一种审美形态又发生着内在的转化与革新,这使先秦时期“乐”的审美形态更加丰富,补充了以往学界“雅”“淫”二分的“乐”审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