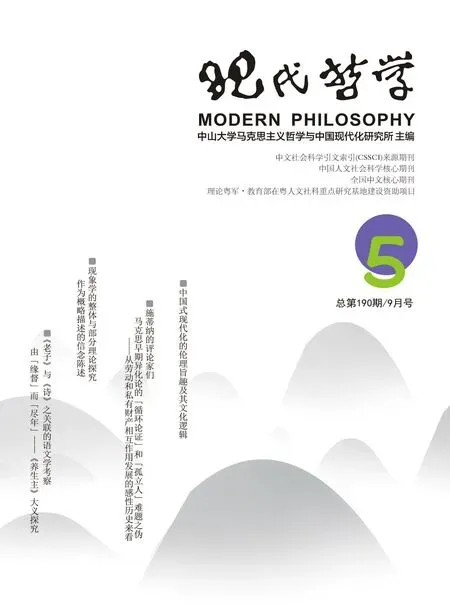圣凡之间的教化
--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孔子
2023-03-31邝其立
邝其立
皇侃学识斐然,曾疏释《论语》《孝经》与《礼记》。可惜的是,皇氏仅剩《论语义疏》得以完整传世。宋《国史志》云:“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1)[宋]王应麟:《玉海》第2册,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771页。可见,该书曾盛行一时。但至于北宋咸平年间(999年),朝廷便命邢昺删削皇《疏》,改作新疏。自此,皇《疏》渐微,终至佚失。幸而唐初传入日本的《论语义疏》,在该国广为流传,于是幸得保存并在乾隆年间回传。学界主流认为,《论语义疏》多涉清玄,是以玄解经的代表作。皮锡瑞云:“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2)[清]皮锡瑞撰、周子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3页。刘恭冕云:“梁皇侃依《集解》为疏,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3)[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7页。诸家皆以《义疏》为不守故常、虚玄说经的典型。此论亦为吴承仕、戴君仁、董季堂、牟钟鉴等学者所接受。但此说未免失之笼统。首先,《义疏》所收录的众多六朝经注,虽能一定程度反映皇侃的思想取向,但不能径直将之等同于皇侃的思想。辨析其间的差异以把握皇疏之特色,是解读《义疏》的要务。其次,在强调皇疏涉玄之余,应重视皇侃思想与传统经学的联系,这仍是有待澄清的问题。
为回应上述问题,需寻得一个探究的着力点。谷继明认为:“相对于汉朝的《论语》学,‘圣人’之形象的讨论乃是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一大特色。”(4)谷继明:《“同物示衰”--南朝〈论语注〉中的圣人形象》,《人文杂志》2018年第1期,第9页。诚然,圣人观是六朝的理论焦点,也是注解《论语》的首要问题--对孔子的不同定位,将从根本上影响了对经文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圣人观是了解皇侃《论语》学的绝佳切入点。
一、体无、同物与教化
王弼与郭象都曾注解《论语》,惜已亡佚。幸得皇《疏》存有王、郭注之吉光片羽,留下了可资对比的宝贵线索。作为魏晋玄学的两面旗帜,王弼与郭象分别展现出与皇侃迥异且颇具玄风的圣人观。兹先通过与王、郭注对照,将皇侃圣人观的核心呈现出来。
王弼注以“贵无论”为基点阐释经文。这导致经文时常成为贵无论的注脚。(5)王弼注“志于道”云:“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魏]王弼撰、楼宇烈校点:《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4页。)对王弼而言,注经终归是阐发的手段。或许是耽于本体论建构的缘故,王弼的圣人观沾染了浓重的形上学色彩。所以他更着眼于圣人与道的关系,强调圣人体无的面向。譬如,其释“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句:
温者不厉,厉者不温;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则不安,安者不恭,此对反之常名也。若夫温而能厉,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调,五味不形;大成之乐,五声不分;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6)同上,第625页。
孔子体无,故能不限于一隅,兼备温与厉、威与不猛、恭与安等特质。皇侃颇受王弼影响,对王注多所称引,亦诩孔子为体无者。皇疏云:“圣人体道为度,无有用意之知”,“圣人忘知,故无知知意也。”(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4页。可见,皇侃与王弼所见略同,皆以孔子为体无之圣。不过,在圣人有情与否的问题上,二者产生歧见。皇侃在《论语义疏》的自序中写道:“但圣人虽异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则朽没之期亦等。故叹发吾衰,悲因逝水,讬梦两楹,寄歌颓坏。”(8)同上,第1页。皇侃虽然引述辅嗣之言,但未真的承认圣人有情。他随后拈出两个例子,一是夫子观水叹“逝者如斯夫”,二是《檀弓》所载的故事:孔子晨起悲歌,子贡近前请益;夫子自述畴昔夜梦,预感命不久矣。值得注意的是,皇侃将后者解读为孔子“讬梦两楹,寄歌颓坏”,即通过“讬”“寄”的方式启发弟子。换言之,孔子并非直抒心迹,而是有为而发,有迂曲行教的意味。“讬”“寄”二字彰显出王、皇的根本差别:若如皇侃所言,孔子托以哀歌,旨在引发弟子的追问,则其情感或话语不必是真实的,毋宁说是为了便于行教的有意为之;王弼则认为圣人所流露的莫不是真情实感。
将圣人之情或行解读为方便教授的例子,在《义疏》中并不罕见。最典型者莫过于皇侃对“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句的释义:“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9)同上,第25页。孔子的圣性完满无缺、圆融自足,本身并不需要学习,此即“圣人异于人者神明”的一面。但为了勉人向学,才有意藏匿圣性,委身同凡,此即“同人者五情”之“同”意。在皇氏看来,孔子本身未必怀有如此世俗的感受或需要。又释“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句云:“然圣人悬照本无俟梦想,而云梦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圣人无想,何梦之有?盖伤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于不梦,发叹于凤鸟也。’”(10)同上,第156页。皇侃认为,孔子如悬照之日月,不应有衰,亦无思虑与梦想。尽管如此,与人方便说法时,仍委身而同物,示人以己衰,意在便于受教者感同身受、领会教义。至于是否确有其事、情,则不必较真。可见,皇侃虽化用“同于人者五情”,实则对“同”字作出了新诠,修改了语义。如果说王弼的圣人观是神明知几的体无者,侧重圣人与道的联系;那么皇侃之圣人就是隐圣同凡的教化者,更着眼于与受教者的互动。王弼之“圣人有情”,皇侃则谓之借“情”施教。比于王注,“同物”论为皇疏之特色所在。
不过“同物”论虽屡见于《论语义疏》,却并非皇侃的孤明先发,西晋郭象已有此说。郭释“颜渊死,子哭之恸”句云:“人哭亦哭,人恸亦恸,盖无情者与物化也。”(11)同上,第272页。臻于至境的孔子,澄然如镜,遂能如镜像般映出众人的喜怒哀乐,融入凡俗之中。似若有情,其实无情,所谓与物同化。又释“阳货欲见孔子”章云:“圣人无心,仕与不仕随世耳。阳虎劝仕,理无不诺,不能用我,则我无自用。此直道而应者也,然免逊之理亦在其中也。”(12)同上,第444页。基于圣人无心的前提,郭象认为孔子之所以出仕,并非出于利禄之图或济世宏愿,毋宁是条件反射般的“直道而应”。无心圣人生于凡世之中,依于世俗的规矩与凡人的情态,游刃有余地融入人世间,这便是郭象意义上的“隐圣同凡”。其所谓“同物”,实即“物化”之意。在郭象的笔下,圣人是同物应世、乘物游心的逍遥者。
无独有偶,郭象之同物论亦见于他注。例如,江熙即云:“圣人体是极于冲虚,是以忘其神武,遗其灵智,遂与众人齐其能否,故曰‘我无能焉’。子贡识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之’也。”(13)[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375页。圣人以冲虚为体,遗其灵智而与凡俗齐同,故自谓“无能”。又如,孙绰注云:“圣人德合于天地,用契于四时,不自昏于盛明,不独曜于幽夜。颜齐其度,故动止无违。”(14)同上,第159页。德合天地之圣人,韬光晦迹,大隐于市,所谓“不独曜于幽夜”是也。是说亦与郭象深契。可知,同物论流行一时,已然成为六朝《论语》学的独特思路。
不过,皇侃的同物论自有其殊别之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则故事:“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皇侃解“畏”为“心服”,认为孔子隐圣同凡,自述己德,希望籍此感发匡人,使其心服。皇侃同物论中的教诲意味,尤其值得注意。与之相对,孙绰亦援引“同物”论,却作出迥异的解读:“畏匡之说,皆众家之言,而不释‘畏’名,解书之理为漫。夫体神知几、玄定安危者,虽兵围百重,安若泰山,岂有畏哉?虽然,兵事阻险,常情所畏,圣人无心,故即以物畏为畏也。”(15)同上,第210页。孙绰认为,圣人稳如泰山,纵使兵围百重,也丝毫不为所动。但圣人之所以展露畏惧之情,是因为夫子无心,故能如镜像反射一般“以物畏而畏”。可见,“游心物化”与“同物示衰”两种同物论之间截然不同。区别在于,究竟是将“同物”视为教化的手段,还是圣人无心的表现。皇侃意在揭示孔子应机行教的一面,郭象等注家则试图展现夫子与的体无境界。
体无论与同物论,属于皇侃浸染玄风的思想痕迹,而非其圣人观之特色所在。以孔为师的教化论,才是让皇侃殊别于王、郭等玄士的关键,体现出皇侃对汉代《论语》学的传承。不过,皇侃并非绕开玄学而重回经学,而是取径于六朝玄思而复归传统。同物行教之圣人形象,实最能体现其《论语》学儒玄兼综之特色。那么,皇侃究竟如何糅合经学与玄理,从而建构起教化之圣人观?
二、教化形象的树立
欲树立教化为核心的圣人观,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教化何以可能?教化之可能,以人性论为前提。譬如,因秉持“性各有分”的静态人性论,郭象一并否定变化的可能与教化的必要,遂有“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的惊人之语。(16)[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9页。与之相对,皇侃从乃师贺玚处继承了一套动态的九品人性论:
此谓为教化法也。师说云:就人之品识大判有三,谓上中下也。细而分之则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则是圣人,圣人不须教也。下下则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须教也。而可教者,谓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1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142页。
性,是先天禀受天地之气所得,有厚有薄,所以分为三六九等。第一等是圣人,搅之不浊,无须教化。末等是愚人,澄之不清,亦无教育的必要。至若介于其中者,便是亲贤而迁善、近墨而染黑的待教之人。此纵向分层的人性论,其实就是对董子“性三品论”的细化。由此,教化问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在这套动态人性论中,皇侃将圣人定义为与众人判若云泥的“生而知之者”。那么,等而次之的凡人能否成圣?不妨举重以明轻,将问题明确为:庶几为圣的颜回,能否学以成圣?若颜子尚无可能,则遑论其余。皇侃否定了这一可能:“自形器以上,名之为无,圣人所体也;自形器以还,名之为有,贤人所体也。今孔子终日所言,即入于形器,故颜子闻而即解,无所咨问,故不起发我道,故言‘终日不违’也。”(18)[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31页。孔子至圣,颜子上贤。圣、贤之间,悬隔于有、无之际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见,皇侃仍坚持“圣不可学”的汉儒旧义。孔子独据九品之中的圣人分位,贤如颜子也只能仰之弥高,叹可望而不可即。虽然圣不可学,但颜子仍能在孔子的诱掖下“既竭吾材,如有所立”,日臻进境。动态的人性论,几乎给每个人预留了进步空间,教化因之得以可能。
除了可塑的人性论与圣不可及,皇侃人性论的第三个要点是对董子情恶论的继承。皇疏“性相近,习相远”句时,详述性情论:
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动彰事,故曰成也。然性无善恶,而有浓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恶,亦不可目为善,故性无善恶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恶之名,恒就事而显,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以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此皆据事而谈。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迁,其事则邪,若欲当于理,其事则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19)同上,第445页。
汉儒董子以阴、阳释情、性,又解性为仁、释情为贪,遂发展出性善情恶的说法。皇侃继承之,故释“情”为“有欲之心”。但圣人圆满自足,不应起欲逐物,遂使情感与圣人格格不入。通过援引同物论,皇侃模糊圣人之情的真实性,从而规避这一问题。借助于同物论,皇氏化解了圣性与“有情”之龃龉。
可见,人之可塑、圣不可学、以欲释情,是皇侃人性论的三个要点。正因人性可塑,才有教化之可能。因圣之超绝,故须降同众俗以示教。而且,若以情为恶,则圣人无情,其所示之情,不过隐圣同凡而已。这套传统的人性论,实为同物论与教化论的基础,亦为建构新说的出发点。
基于颇具古典色彩的人性论,皇侃证成教化之可能。因之,孔子顺理成章成为教化者。不过,皇侃亦将孔子定位成体无者。“无”意味着剥除一切既有规定,所以“体无”一语含有很强的否定、消解意蕴。那么,体无与教化两重属性,如何能融通如一?皇侃试图援引玄学的本迹之分,兼包两面。皇疏云:“圣人作教应机,不可一准。今为其迹涉兹地,为物所嫌,恐心实如此,故正明绝此四以见本地也。”(20)同上,第209-210页。夫子应机所予之教,莫不因嵌入具体情境而限缩了意涵。因此,皇侃将夫子之言喻为语境化的陈迹。换言之,学者无法执定孔子的言说来揣摩“本地”,学成圣人。依据本迹之分,皇侃将孔子的本然面貌与教化形象析而为二。并在本体层面安顿体无之本,而视行教救弊为当世行迹。在本迹二分的框架中,孔子之言行,将无碍其本然之完满。这意味着夫子可以在无损其圆满自足的前提下,施行教化,拯溺扶衰。
那么,悬隔世外的体无者,为何要入世行教?检寻疏文,未见皇侃有明确的说明。这或许正说明了孔子教化是其最根本的理论前设。虽然体无论可以通过撤销有限的规定性,成就无限的可能性与绝对的完满性,但教化论是皇侃不能也不愿消解的核心。又问:超凡入圣的体无者,应如何入世行教?皮迷迷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论语义疏》给出的回答是:隐圣同凡。这正是孔子的两重面貌得以合于一身的关键所在”(21)皮迷迷:《“隐圣同凡”:〈论语义疏〉中的孔子形象》,《哲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83页。。凡俗无法达至圣域,只能寄望于圣人同凡的汲引。可见,同物论与本迹论二说虽异,其意欲在圣人体无的前提下树立教化形象的旨归则同。概言之,籍由对古典人性论与玄学思想的吸收,皇侃为教化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刻画”出夫子的两幅面貌,建构起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的圣人观。
三、教化事业的展开
取径儒、玄,皇侃打造出本迹二分的圣人观,并树立起孔子的教化形象。基于此,通过疏解经、注的方式,他描绘了一幅圣人教化的图景。
皇侃《自序》云:“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22)[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2页。这足见夫子的施教对象、行教方式和教化内容并不惟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同为“问孝”的四人,却得到夫子全然不同的答复:对于孟懿子问孝,子对曰“无违”;针对孟武伯之问,答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答子游之问,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子夏之问曰“色难”。问同答异,耐人寻味。皇疏总结道:“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其人有失,故随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明教也。”(23)同上,第31页。他将上述四次问答,归为“随疾与药”与“寄人弘教”两类。所谓“随疾与药”,是指孔子依据请益者的情况,示以相应教诲。这种教法极具针对性,其效力通常仅限于听者。“寄人弘教”则不然,其适用对象或普遍程度要大得多。《先进》篇记述一则故事:门人希望厚葬颜回,但孔子不许,门人却执意为之,于是夫子感慨道“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皇疏引范宁注云:“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门人之意耳。此以抑门人而救世弊也。”(24)同上,第273页。彼时厚葬成风、奢侈过甚,孔子抑止门人厚葬的请愿,旨在针砭过犹不及的时弊。所谓“寄人弘教”,即是孔子通过责斥弟子的方式来弘扬教义。
皇侃为何要将夫子之应答,判分为“与药”与“弘教”两种方式?关键在于请益者身份的不同:孟懿子和武伯皆非孔门弟子,且有“僭滥违礼”之嫌。就“随疾与药”之名而思义,可知二者为“病人”,所以夫子之教犹如治病良方;贵为四科十哲的子夏、子游,自不与其等量齐观,更无亟待医治之疾。因此,夫子只是借着贤人弟子“明知故问”的话头,施予针砭之教。换言之,贤人弟子触发弘教的机缘,助成教化的事业。在“季氏将伐颛臾”章中,面对将伐颛臾的局面,供职于季氏的冉有、季路无动于衷,夫子大动肝火,怒斥弟子的无所作为。皇疏引蔡谟注申之云:
冉有、季路并以王佐之姿,出彼家相之任,岂有不谏季孙以成其恶。所以同其谋者,将有以也。量己拨势,不能制其悖心于外,顺其意以告夫子,实欲致大圣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发明大义,以酬来感,弘举治体,自救时难。引喻虎兕,为以罪相者。虽文讥二子,而旨在季孙。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强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宁社稷。斯乃圣贤同符,相为表里者也。(25)同上,第424页。
冉有、季路皆王佐之才,不可能袖手旁观。只不过自计无由劝阻季氏,于是泄谋于夫子,欲致圣言,拯救时难。因之,冉有与季路的形象被彻底颠覆:从为虎作伥,变为与圣人相表里之贤人。为了行教,孔子与弟子配合演了一出戏。弟子原无疑惑,却有意设问。孔子心领神会,故施予普遍的教诲。问答之间,达成弘教使命。“寄人弘教”之“寄”,是指用假托、寄寓的方式予以方便说法,有“同物”的意味。这是需要孔门师徒勠力“隐圣同凡”与“隐贤同凡”才能完成的一桩事业。
这是否意味着助成教化的贤人弟子无需受教?并非如此。除面向时人的“与药”和“弘教”,孔子尤其寄望于通过劝学先王之道,将弟子培养成一代经师。皇疏“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句云:“古人谓学为治,故书史载人专经学问者,皆云治其书、治其经也。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籍正典,而杂学于书史百家,此则为害之深,故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26)同上,第35、36页。这里旨在强调异端的危害。皇侃却将诠释的焦点转向“六籍正典”,进而断定异端之害不过是分散了学者沉潜经籍的精力,毕竟修习先王之道乃是儒者志业。五经六籍所蕴涵的“为政之道”,俾有益于培养建构秩序的经师。皇侃认为,所谓“三十而立”是指经业成立,继而引述孙绰注“四十而不惑”句云:“四十强而仕,业通十年,经明行修,德茂成于身,训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无疑惑也。”(2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25页。经籍中的先王之道,所教予的是“为师为君之法”,是培养经师的教材而非普罗大众的读物。就此而言,皇侃近于汉人旧义,未曾偏离五经之学的思路。
不过,既然孔子矢志于劝学先王之道,说明其政教之志未泯,为何仍将其定位为教化者?皇侃意识到这一问题,故于“吾与点也”章释云:“孔子闻点之愿,是以喟然而叹也。既叹而云‘吾与点也’,言我志与点同也。所以与同者,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28)同上,第295页。这里,孔子探问诸弟子之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皆答以为政之事。唯独曾皙坦言向往与师友逍遥游咏的时光。孔子许之,遂生喟叹。皇侃通过引入时运的因素,化解了从政与行教之间的张力,或者说为教化者存留了为政的念想。圣贤生不逢时,有德无位。值此衰世,只能“另辟蹊径”,通过言教而非政教的方式济世。至此,可对夫子的教化事业作一番回顾:通过学经,孔子将弟子培养成经师;继而与此贤人君子共行教化,敲响救弊的“警世钟”。因之,皇侃构建的孔子教化形象,逐渐立体而丰满起来。
四、余 论
取径于儒、玄之间,皇侃树立起两面之圣人观,却不免予人割裂之感。因为析离圣人之本与迹会招致两个后果:首先,若学人无法通过经文了解孔子,圣人将在虚玄之境中,逐渐面目模糊,脱离现实;其次,将“现身说法”视为隐圣同凡,意味着夫子之教由言说对象所决定,体无者不会也不应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观点。不可避免地,言教终将堕为陈迹。皇侃对此并不讳言,甚至承认教诲就是“弊之所缘”。(29)同上,第385页。若诚如此,则皇侃之教化圣人观,难免由于教诲意义的阙疑,而一并随其本体陷入虚无之中。此为以玄解经之困难。或因于此,后学摒弃此两面圣人观与《论语》学。武内义雄总结道:“今取皇、邢、朱三家书而读之,邢氏剪皇疏之诡异,稍附以义理,而朱注则变本加厉,义理之辨弥精,而援证之博不及于古。盖邢疏出而皇疏废,朱注行而邢疏又废。”(30)同上,第532-533页,附录武内义雄《〈论语义疏〉校勘纪序》。于是,《论语义疏》逐渐淡出视野,最终销匿声迹。
不过在思想史中,仍依稀可见《义疏》的“踪影”。圣人观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节,对孔子的不同定位,将导致《论语》学乃至经典观的变化。理解的转向甚至导向了后来宋学的形态。具体说来,教化之圣人观,将直接颠覆《论语》与五经的关系。《论语义疏》序云:“故言《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镜。”(31)同上,第3页。若以孔为师,五经便不首先是素王之法或三代史录,而是以“为学”的眼光,视之为承载为政之道的“教材”。(32)参见皇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句。(同上,第192页。)只是,在讲道理的意义上,五经反不如《论语》那般直接明了,虽则在体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道理的完备性、丰富度上皆难与后者媲美,于是有“明珠”和“巨镜”之喻。从教或学的角度看,《论语》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换言之,经典观随圣人形象的转型而变易。后来四书与五经的消长之势,于此已绽露一些苗头。对经典的解读也许会过时,但理解经典的方式却有可能常新。在这个意义上,《论语义疏》从未“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