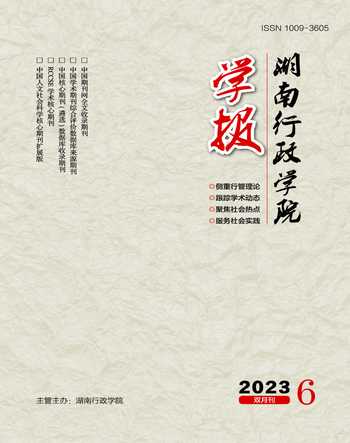生物技术时代人的尊严何以为能
2023-12-21王巍,唐师哲
摘要:生物技术发展的最高伦理公设应是维护人的尊严及其自然地位,但生物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生物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基因编辑技术亦是如此。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人的尊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基因编辑技术涉及对人的基因进行直接改造,触动了人对生命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引发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恐慌,导致了一系列涉及人类尊严的危机,如人的自我认知危机、人的自主权危机、隐私暴露危机、社会歧视危机、人的重塑危机等。我们需要对基因编辑技术展开伦理辨析,并制定相应的伦理原则,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使基因编辑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关键词:基因编辑技术;人的尊严;伦理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6(2023)06-0032-08
如果说20世纪是物理学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的世纪,生物技术的发展将给人类带来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基因编辑技术是生物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指在基因组上对目标DNA序列进行敲除、插入、定点突变等,通过对人体基因的改变从而实现人的某些性状的改变,以达到疾病治疗或者个体增强的目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和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变革。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里夫金所说:“遗传工程既代表着我们最甜蜜的希望,同时也代表着我们最隐秘的恐惧。”[1]135特别是2018年人类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南方科技大学的诞生,再次引发人类社会对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的激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会问:“在基因编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的尊严将何以为能?”为了使基因编辑技术更多更好地促进人类的发展,维护人的尊严,必须对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提出相关伦理对策及原则,以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及机遇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是随着基因工程的进步而进步的,根据技术手段的发展历程,基因编辑在发展上主要经历了ZFN(锌指核酸酶技术)、TALEN(转录激活样效应因子核酸酶技术)以及CRISPR/Cas(常间回文重复序列丛集关联蛋白系统技术)三个主要阶段。
CRISPR/Cas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基因编辑手段,有着“基因剪刀”的外号。利用序列特异性sgRNA的引导,CRISPR/Cas能够精准地在目标DNA的确切位置导入双链切口,从而完成对目标基因片段的编辑。这一技术源于1987年在科学家对大肠杆菌编码的研究实验中被意外发现,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改良发展,2012年CRISPR/Cas正式问世。相较于ZFN和TALEN,CRISPR/Cas有了巨大提高,不仅降低了细胞毒性,同时操作上更为方便、高效,具有巨大的潜力。但目前CRISPR/Cas在技术安全上仍具有较大风险,一是“脱靶”风险,即基因编辑时有概率会切割原定基因片段以外的基因,不仅会使基因编辑失败,同时可能发生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基因突变;二是“镶嵌”风险,即同时编辑多个细胞时,可能只有部分细胞编辑完成,使编辑完成和未完成的细胞“镶嵌”在一起,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
(二)基因编辑技术的现实际遇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在应用和实践领域可分为基因治疗和基因增强。基因治疗是指出于医学目的,通过对人体某些缺陷基因进行改造或者去除等,以达到对部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基因技术开始逐步在临床上应用于对部分基因缺陷而造成的遗传病的诊断和治疗,同时现在也开始用于对某些家族遗传病的预防之上。人类基因编辑技术之所以能在社会上获得一定认同感和正当性,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基因治疗背后所释放出巨大人类健康福祉。目前基因治疗技术已经广泛用于医疗之中,虽然受到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限制,基因治疗技术只能实现对单个基因靶位点的识别、判断和替换,[2]所以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成熟应用的范围仍比较受限,该技术对多基因遗传性疾病的效果并不明显,同时针对后天由于多基因突变引发的疾病如癌症、艾滋病等疾病的治疗效果也不出众,仍需进行进一步研究。
基因增强的目的大多与医疗无关,是指通过对人体基因进行编辑或选择以达到提升或增添人类的某种能力或性状[3]。关于基因增强的讨论已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之一,基因增强给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如人类可以通过基因增强提高自己的体质、改变自己的外貌以及提高自己的智力等等,使人能更好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重塑自己。同时,可以通过对自己后代进行基因增强,以达到对后代进行“特质选择”或“特质增强”的目的,使人的后代也更加趋于“完美”。
但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的道德观、伦理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因编辑技术中,不管是基因治疗还是基因增强,都直接涉及改造人的基因,触动了人对生命的定义以及曾经神圣无比的生命范畴,不可避免损害了人的生命的内在价值,对人的尊严造成了巨大威胁,引发人的尊严危机。
二、基因編辑技术引发人的尊严危机
尊严是对人的认同,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也是构成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和品格的基础。[4]对于人的尊严之特征,作为道义主义伦理立场的创始人,康德曾如此评价道:“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5]尊严,是我们作为人应有的类本质,是每个人身上无法被替换的价值。正如著名的人本哲学家马斯洛在他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强调的那样,“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需要或欲望,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6]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开始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人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它自然的关系。”[7]但当人的生命成为一种人能任意控制其走向的事物,那么,人的生命将被异化。康德始终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他提出的绝对命令的第二个准则是:“要这样行动,以便将人类,包括你自己及其他所有的人,永远只能当作目的而不是单纯的手段。”[8]如果基因编辑技术大范围推广,基因编辑通过对基因的改造使人的基因序列被随意修改,带来人的性状和能力的改变。可能使人在出生之前,其各项特质如外貌、体力、智力等等就因为基因的改造而被人为选择。让社会和他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批量生产”和改造人类,人由此变成了“手段”,从而失去人的“目的”和“尊严”。如果人一旦能被加工改造,这将会使人类的进化方式发生彻底改变,使原本的“自然人”逐渐演化为某种意义上的“人造人”,不仅颠覆了长期以来人类在进化中形成的自然进化规律,而且损害了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尊严。
(一)人的自我认知危机
人的自我认知,即人的“自觉”,是人的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康德所说,“我作为仅仅意识到自己的联结能力的理智而实存。”[9]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直接涉及改造人的基因,而基因关系到人类种群的遗传、进化以及我们每个人个体性状的生成。在我们的认知中,自然的我是不可以被改变、也不应该被改变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也天然地构成了独立的我、自由的我、完善的我,[3]即最自然的“本我”,也正是由于个体之间基因的不同,使我与他人划定了天然的永久界线。但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却使人类可能会在自我认知上出现紊乱。基因编辑技术对人体基因的改变使一个“忒修斯”式的自我认知悖论出现了[10],(即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虽然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的改造较为特殊,它并不是直接更换“人”这艘船上的每一块“木板”,但是它改变了人体最本质的构成材料——基因,从而也使得人体的其它部分随之发生改变。尽管人脑对整个生物体的变化具有统筹协调的作用,但是统筹不同于同一,甚至在进行基因编辑之后,我们的大脑认知都可能会随之改变,导致人类的自我认知危机。对大多数人的伦理观念而言,不管自然的我如何,我始终是自然的我,人的基因被改变后,人的自然属性遭到了改变,人们不禁会问:“这个时候的我还是我吗?”致使人在自我认知上出现怀疑和紊乱。
(二)人的自主权危机
自主权是人的尊严价值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人应该有自主选择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权利。但在基因编辑中,人的自主权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对于基因编辑特别是对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而言,胚胎并没有意识,它不可能自己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基因编辑,但父母可能会“替孩子做决定”,通过基因编辑的手段对孩子的基因进行检测和编辑,对胚胎细胞基因进行“特质选择”来生出自己最想要的孩子而未“询问胚胎是否愿意接受基因编辑”,虽然“询问胚胎是否愿意接受基因编辑”的这种讲法难免可笑,但不可否认的是,胚胎有孕育成人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又应该去保护和尊重他的自主性呢?一旦我们决定在胚胎上实施基因编辑,就相当于人为地改变了胚胎在自然状态下被孕育成人的路径,影响甚至彻底改变由此胚胎孕育出来的人的发展方向[11],使他成为了别人想要的“人”而非自我的“人”,使人对自己的自主权在尚未出生时就完全被剥夺,人的自主性尊严将置于何处?
(三)隐私暴露危机
保护隐私是对人性自由和尊严的尊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基因隐私是每个人最天然的隐私,人的基因中隐藏着每个人最基本的最自然的隐私,隐藏了一个人生命的全部奥秘。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查明,人类的全套基因中,99.9%的基因是相同的,正是剩下的0.1%造成了每个人个体上的差异,也正是这0.1%,我才与他人构成了在自然条件下的天然不同的,独立的自我,构成了独属我自己的基因隐私。但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只需要一点血液甚至几滴唾液就可以得到一个人全部的基因和遗传信息,通过对基因信息的读取不仅可以获得有关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禀赋,甚至可以获取整个家族的遗传信息,如果不对基因隐私进行保护的话,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毫无隐私的社会,彻底变成一个“透明人”,甚至我们的基因信息会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进行资本逐利的工具。同时基因隐私权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社会歧视—基因歧视[1]138,一旦个人的基因信息被公开,那些天生带有某些基因缺陷或者不利基因的人将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遇到难以想象的危难和阻碍,使社会出现新的弱势团体,他们的尊严将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进一步增加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因素。
(四)社会歧视危机
实现社会平等,消除社会歧视,对于维护人的尊严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消除不平等,进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在给人们的健康发展和疾病治疗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歧视风险。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无论出于何种意图,操纵一个人后代DNA的能力,都会对政治秩序造成影响,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等级制度自然化。[12]“社会总被有产者和无产者、当权者和无权者、精英和劳动阶层之间进行划分”[13],特别是在私有制和资本逻辑主导下,精英阶层极有可能会垄断相关技术和产业,他们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自己后代的基因进行调整与增强,使他们的后代在“天生”上就成为与众不同的“超人”或者通過基因编辑对自己的身体等进行改造,达到智力和体力的进一步突破;但平民阶层却可能因费用的缺乏和医疗水平的限制,无力甚至无法利用这一技术对他们的后代的基因进行改进与完善,使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不可能像精英阶层那样有条件有资源去对自己进行相关改造。而这将极大地扩大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以往的贫富差距只是物质上的,现在连人与人的基因之间都存在了“贫富差距”,形成巨大的遗传势差,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和更“严格”的划分方式,即基于基因的方式,这将诱发严重的基因歧视与难以预估的社会鸿沟,形成严重的阶层固化。
(五)人的重塑危机
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生命和基因的奥秘也不断向人们展现,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设计生命的工程师,人再次取得了对自然的巨大“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又如何保持客观理性?如果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控制后代和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当“按神的旨意”出生的“自然人”转变到“我的旨意”改造出来的“人造人”,我们又该如何为生命定义?[1]163此时的我们又将如何对待生命这一范畴?是在生命面前盲目自大、自以为是,还是谦虚谨慎、谨小慎微?正如部分生物保守主义者所言:“基因工程并不认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而是人类能够理解和操纵的一系列物质原因的总和。所有这些都不尊重人的尊严,违背了上帝的意愿。”[14]人类将如何面对人类身份的转变,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自我重塑危机,已成为生物时代人类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
三、基因编辑技术应坚守的伦理原则
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技术的出现给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改变,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部分新技术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又往往可能会损害人的尊严,从而引发人们在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基因编辑技术就是这样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它给人类创造了利益也给人类带来了危机,但科技是善是恶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类如何使用,正如科学家威斯特法尔所说:“科学本身并不值得我们惧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运用科学,科学能产生最好和最坏的结果。”[15]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就停止科学探索的步伐,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16]。对于基因编辑技术亦是如此,不能因为其带来的部分伦理问题就完全否认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而是需要制定明确的伦理原则,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
(一)以人为本原则
任何理论体系都应有某些不证自明的公理,生命伦理学的最高公设就应该是维系人的尊严及其自然地位,人的尊严无论何时都应该受到社会和科技的尊重和认同,科技发展也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原则基础之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变革,也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和强大推力。面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一方面要更新观念,要看到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机遇,加强基因编辑技术在疾病治疗等有利于人类福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监管,制定细致的伦理规范,绝不能放任自流。要明确基因编辑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为人类服务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对生命,对自然保持敬畏,任何时候都不应伤害人的尊严,无论何时都不可将人贬低成“物”,将人视为被利用的“手段”。
(二)责任担当原则
相关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是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排头兵,也是技术规范和治理的第一责任主体。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法律制定和技术监管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仅靠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强化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担当意识。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研人员可能对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16],这个时候,科研机构的责任意识就显得极为重要。相关科研机构必须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设置技术禁区,使相关实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保证。如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尚不成熟,更应加强在实验室内的实验而不应先用于人体之上。同时,为了始终保证基因编辑的相关研究始终处于保证人的尊严和遵循社会伦理的前提之下,对于人类胚胎细胞的相关实验更是要慎之又慎,对于涉及社会伦理禁区的实验要坚决予以禁止。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之所以对社会伦理造成了极大冲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涉及到了社会公认的对胚胎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技术禁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人的尊严造成了巨大威胁。所以对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而言,一定要强化责任担当,划定明确的技术界线。
(三)发展透明原则
社会对技术发展的伦理恐惧和担忧很大一部分源于对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的未知,特别对于基因编辑技术而言,由于其直接影响到人的自然属性以及人类种族的未来繁衍等等,如果其发展和应用不为社会所知,必将极大地引发社会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恐惧。[17]因此,必须确保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公开透明,使基因编辑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同时,保证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公开透明也是确保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应用不偏离正确轨道和正常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可以加强社会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监督,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可以让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在消除社会公众的恐惧、紧张、担忧心理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社会对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偏见和误解,更好地促进基因编辑技术的良性发展。
(四)公平正义原则
公平正义是社会中每个人心中的期盼,是人的尊严的重要价值内涵,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对于基因编辑技术而言,要让社会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基因编辑技术在疾病治疗,遗传病防控等方面的福利,必须防止有人垄断相关医学资源,优先获取治疗机会,包括基因修饰或者延长寿命的机会,或者使基因编辑技术成为少数人牟取暴利的工具。尤其是要杜绝让基因编辑技术成为少数人的“玩具”和“专利”,成为他们为了巩固自己和家族地位的手段。如果人为地造成遗传阶层分化或人生起跑线上的不平等,这将诱发严重的基因歧视与难以预估的社会鸿沟,形成更加严重的阶级固化。要建立健全符合科技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打击行业垄断行为,加大对贫困地区和人群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上的扶持,加大对基因编辑技术在使用上的审查,尤其是要杜绝带有目的性和满足少数人私欲的“基因定制”现象的发生。同时要看到,保障隐私权是人本社会的一个重要要求,也是保障公平正义和维护人的尊严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对于每个人最天然的隐私—“基因”而言,对基因隐私的保护更是要制定严格的法律和伦理规范,由于基因信息存在着天然的内隐性、自在性、排他性等特征,基因的不同构成了人与人天然的不同,其属于人权的典型范畴,特别在基因信息越来越容易泄露的当下,更是要加强对每个人基因隐私的保护,要保证个人对自己基因信息使用的自主权,知情权,同时对有关个人的基因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给本人之外的第三人或作其他用途。尽最大努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稳定。
四、结语
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生物技术时代下,对作为其重要分支的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伦理探讨,进一步维护人的尊严已越来越具必要性。基因编辑技术的發展正在将人类推向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基因编辑技术在基因治疗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其发展必然会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使人在更大程度上成为自己的主宰。但由于基因编辑涉及对人的基因直接进行改造,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也给人的尊严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果不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进行伦理约束,人将失去人的“目的”,而彻底沦为“手段”,人的尊严将荡然无存。因此,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关的伦理原则,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使基因编辑技术在维护人的尊严的基础上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巍.生物技术与人的发展[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2]朱佩琪,蒋伟东,周诺.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的发展及其在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J].中国比较医学杂志,2019(2):116-123.
[3]陈龙.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之维[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8):85-90.
[4]唐凯麟.尊严:以人为本的新诠释[N].光明日报,2011-01-31(11).
[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4.
[6]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3版.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8]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372.
[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1.
[10]易显飞,万礼洋.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融合主体”及其人文透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9):47-54.
[11]孙伟平,戴益斌.关于基因编辑的伦理反思[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9.
[12]Francis Fukuyama.Our Posthuman Future: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M]. New York:Farra,Straus and Giroux,2002:50.
[13]里夫金.生物技術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M].付立杰,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63.
[14]Fukuyama F.Our Posthuman Future [M].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3:89.
[15]李艳鸽.现代反科学的社会认识根源[J].中国科技论坛,2004(3):93-96.
[16]段伟文.技术的价值负载与伦理反思[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8):30-33+54.
[17]王巍,唐师哲,李卓群.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3):97-103.
责任编辑:高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