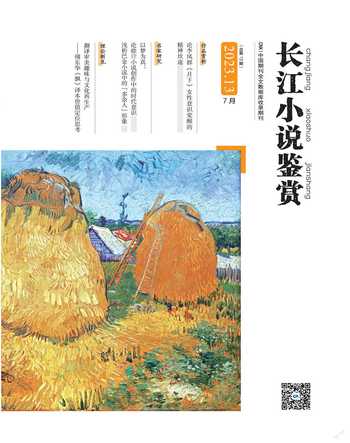论《狂野之夜!》中主人公的身份危机
2023-12-20王沛然
[摘 要] 欧茨的短篇小说集《狂野之夜!》以精妙的构思以及大胆的想象将我们带进大师们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延续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同时亦吸取了诸多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技法,在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中折射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本文旨在从个体身份、家庭身份以及社会身份三个层面分析《狂野之夜!》一书中出现的现代人的身份危机,并从创伤性记忆、伦理的扭曲、族裔与职业等角度阐述书中人物的生存困境,从而揭示高速发展、存在各种痼疾的资本主义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危机和社会问题,并探寻欧茨如何借“身份”之名表达对人类命运的忧虑。
[关键词] 身份认同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狂野之夜!》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3-0028-04
一、引言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oral Oates, 1938—)是20世纪最多产的美国作家之一,迄今已发表《大瀑布》《北门畔》《漂流在时间里的人》等作品70余部,曾獲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当今世界文坛“心理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其小说多以女性视角描绘美国人的生存境况,通过内心独白、意识流、象征主义等手法展现现代人对生活的困惑和现代人所感受到的日趋严重的异化感,呼吁人们对当下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狂野之夜!》以大胆颠覆的笔触描绘了爱伦·坡、艾米莉·狄金森、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最后时光”,作品在延续欧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同时亦融合超现实主义元素,“对美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侧面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精神蜕变的原因”[1]。国内学界对欧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大瀑布》等获奖小说上,并就其性别、族裔等作品内含主题,大屠杀叙事以及非自然叙事等叙事手法,心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等进行分析阐释,对其后期创作的小说关注不足,以《狂野之夜!》为例,目前仅有一篇评介文章发布于国内核心期刊。本文将从个体身份、家庭伦理身份、社会身份三个角度出发,分析《狂野之夜!》一书中折射出的现代人的身份危机。
二、含混不清的个体身份
1.自我意识的分裂
个体身份的迷失首先表现在自我意识的分裂,即表现出来的自我及被压抑的自我。在《爱伦坡遗作,或名灯塔》篇章中,欧茨刻意仿照坡一贯的哥特式写作风格,描摹了坡在两种自我意识的较量中逐渐迷失个人身份的动态进程。
现代人为迎合社会环境而付出了“人格萎缩”的代价,即根据外部环境改变或重塑自我,使得原本的自我因受到压抑或排挤而处于边缘地带。根据克里斯蒂瓦的理论,“卑贱物”是指某种熟悉却受到压抑的东西,人们对其“又禁止又欲求,让它游弋于原始压抑的边界上”[2]。半人半兽、奇形异状的怪物往往作为卑贱的形象出现在现代小说中,以此指涉被压抑的自我。小说中的坡出于对自我隔绝的好奇参与了肖博士的实验,来到一座与世隔绝的灯塔。起初,他很享受这种免于社交的“孤独”,对灯塔的一切充满热情与使命感,在维持一个“社会人”属性的前提下尽情释放在费城被压抑的自我。然而在这种孤独与放纵中,他由“体魄康健、精神十足”变得“饥饿难耐、心神不定”,并在其“本我”的自我意识占据上风的拉扯中逐渐走向极端;由不屑于记录污秽不堪的低等生物到与岛上生物抢夺食物,再到躲避人类、与独眼兽繁衍后代,“社会人”的属性荡然无存。小说中的“卑贱物”独眼兽海拉则折射出坡内心“最强烈也最邪恶的欲望”,生吃活物、四脚行走更反映了其原始兽性的回归,于是他“放下那支烦人的笔” [3],同时也放弃了作为文明人的身份,放任自己迷失在被压抑的自我得到完全释放的人格之中,与“爱人”海拉居于洞穴,真正成为费城上流社会口中的“疯子”。
2.创伤记忆的困扰
《爸爸在凯彻姆,1961》以“他想死”开篇,讲述了海明威饱受躯体疾病、精神抑郁、文思枯竭、童年创伤折磨的最后时日。“由于创伤的经验结构或接受和日常生活经验不同,因而创伤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而保留”[4],故而“三十年来,爸爸的魔咒一直困扰着他”,父亲之死对海明威影响巨大,以至于多年之后他仍清晰记得父亲自杀的全部细节,甚至对这位羸弱的父亲产生钦佩之情:“如果要干掉这颗脑袋,那活儿一定要干得干净彻底。”[3]这种创伤记忆使得海明威游离于两种身份之间,欧茨也通过对风景意向、卧室陈列等的描写及意识流、非自然叙事等创新手法展现“思想的混乱、混沌、解离、冥想”[4],以此呼应其含混的个体身份。与低下的自我价值感相伴的是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水平的低下[5],从“Papa”(指其本人)和“Father”(指其父亲)这两个频繁变化的指代中可以明显看出,海明威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少不更事的他曾对父亲的身体冷嘲热讽,现如今,他却时不时觉得自己从父亲那具衰老的身体中醒了过来”[3]。童年创伤使得他总无意识地模仿父亲的言行举止,却又挣扎着将自我意识推向高地。在这种创伤记忆的折磨下,他总是生活在不同自杀方式的臆想中,无法区分现实与幻想,更无法找寻作为个体的身份。
三、冷漠疏离的家庭身份
1.婚姻关系的异化
欧茨对家庭伦理问题颇为关注,“家庭功能失效和家庭伦理道德失范”贯穿于其创作之中,再现了“紧张、疏离、冷漠的”家庭关系,并指出处于这一环境中的家庭成员“内心是孤独落寞、幽暗封闭的,人格是扭曲的”[6]。婚姻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婚姻关系的异化导致自我孤立、欲望失控,疏于交流的畸形状态削弱了家庭承受外界压力和经受危机考验的能力,充盈的物质生活却无法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进而产生身份危机,家庭一步步走向崩溃。
在《狄金森仿真人》篇章中,克里姆夫妇结婚多年,生活富裕却时常相顾无言,毫无生活情趣,故而他们购入了一台“狄金森”仿真人,以期能为他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趣味,并结束这种不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然而,由于夫妇二人对“狄金森”的态度大相径庭,本已陷入困境的婚姻关系变得更加疏离:克里姆太太对仿真人“既心存恐惧,又被她强烈地吸引”;克里姆先生则坚持认为“她只是‘它,我们是她的主人,不是她的同伴”[3]。随着妻子与仿真人日渐熟络,她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与“狄金森”的相处之中,并试图与其成为无话不说的姐妹,此举俨然激怒了丈夫,而被排斥在姐妹情谊之外的丈夫“怒不可遏,烦躁不安,心生怨恨,全都因为她:‘艾米莉”[3]。故事在一个寒冷的秋夜达到高潮:陷入狂乱的克里姆先生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得不到任何抚慰,故而想要通过强暴仿生人的方式重获“一家之主”的家庭身份,这种心理失衡及出格行为非但没有挽救他的婚姻,反而加速了其身份危机的进程。
2.代际伦理的扭曲
代际关系的扭曲通常表现为伦理混乱,这种畸形的伦理关系“一方面是因为缺少正常的爱,另一方面是因为错乱的情感泛滥”[7]。这种缺位的亲情与畸形的爱恋往往表现为对于亲生子女视而不见甚至抱有敌意,却对家庭伦理关系之外的孩童怀有异乎寻常的爱恋,在家庭中未能承担起作为“家长”的身份与职责,“传统的代际伦理彻底被摧毁”[6],让家庭支离破碎,无法建立认同感。
在《克列门斯爷爷和天使鱼》中,马克·吐温作为父亲,对自己的二女儿克拉拉异常冷漠疏离,并称其为“厉害的老姑娘”“凶悍的克拉拉”“粗暴的女儿”“令人窒息的女性”。对于这个“尖酸刻薄”的女儿,他连基本的信任都做不到,更谈不上父女亲情。尽管克拉拉一直没有放弃修复与克列门斯爷爷之间紧张的父女关系,甚至哭着恳求“爸爸,我是你的女儿:这难道还不够吗?”却只换来他冷冰冰的拒绝:“亲爱的克拉拉,我或许真的是个冷血的畜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马克·吐温对于家庭之外的小女孩怀有异乎寻常的爱恋:他对10至16岁的女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她们“温柔可爱,天真淳朴,善于信赖”,是“宠儿”“宝石”“天使鱼”。他对其中一个叫麦德琳的孩子颇为偏爱,常与她书信来往并渴望与之独处,因为他从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他早逝的女儿苏西的影子,并对其产生了异乎寻常、超越伦理关系的爱。克列门斯爷爷对父亲身份的逃避模糊了家庭的概念,更扭曲了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他醉心于营造幽默风趣的“马克·吐温”,却忘记回归“克列门斯”本人的家庭序列。然而,当麦德琳超过16岁(苏西去世的年纪)时,他像对待克拉拉那样将小女孩无情地抛弃,将不和谐的家庭伦理身份传递到麦德琳身上,从而导致身份危机的连锁反应。
四、交织矛盾的社会身份
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往往需要得到他人或外部世界的肯定或认同,才能获取社会身份,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当职业身份、族裔身份的建构过程交织在一起,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则会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生活中出现伦理秩序的混乱。
1.族裔身份的摇摆
作为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一直困惑于自己的身份问题,而他的国籍及族裔成为其社会身份的关键因素。身份认同“是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8]。亨利·詹姆斯在美国人、英国人这两种族裔身份之间摇摆不定,他热忱地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前往圣巴塞罗缪医院,被安排收拾残羹冷炙、处理污秽狼藉却依旧充满热情、毫无怨言,夙兴夜寐、兢兢业业,甚至自掏腰包帮伤员向家中写信寄信,以抚慰他们战后心灵的伤痛。尽管这些对亨利·詹姆斯这位垂垂老矣的“大师”的身体造成极大负担,常常累得上氣不接下气,他似乎仍未通过护理督导爱德华兹的“考验”:“同事们都跟我说,你没有拒绝任何一项工作,并且大部分工作完成得相当不错……不过,詹姆斯先生,你还是个美国人,是这样吗?还不是我们的人?”[3]这令他感到伤心,因为他从内心深处期望获得英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做一个真正的英国人。然而,詹姆斯的英国化之路并不顺利,从他的外表到言谈举止都显示出想要获得身份认同极其艰难。当医院众人得知詹姆斯仍是“美国人”时,他被惩罚似地“被派去做医院最低贱最肮脏的工作”,备受冷嘲热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始终没有获得英国人的身份认同:他的族裔身份仿佛就是他的原罪,这也成了他的心魔,直到他在72岁那年放弃了美国护照,小心翼翼地在圣巴塞罗缪医院奉献自我以维持这来之不易的认同感。
2.职业身份的冲突
欧茨同样关注“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命运乃至生活状态”[9]。不同职业对身份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冲突,人在无法兼顾多重职业身份之时便会产生自我怀疑,进而引发身份危机。二战期间,世界著名文学大师亨利·詹姆斯成为圣巴塞洛缪医院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照顾战后伤员。作为文学大师,他活跃于国际文坛,勤耕不辍,善于分析人们的心理状况,备受敬佩,而作为一名志愿者,他发现自己在面对战争和伤员时显得苍白无力,无人关心诗歌及小说创作甚至他的作家身份,周遭弥漫着绝望与伤痛;他的作品中从来不会出现污秽血腥的场面,甚至都不会出现“肉体”,但他所在的医院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充满伤残病痛的实实在在的肉体,这使得詹姆斯必须在两种职业身份之间跳转以适应周遭环境——“这将是他人生的关键考验”[3]。起初,亨利并没有放下“大师”的架子,无法适应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的身份,这对他的自尊心来说是一个打击:没有人会在那里欢迎他的到来,没有人会告诉他在哪里可以找到护士长,没有人会称呼他为先生,甚至没有人认出他。当他逐渐适应志愿者的身份后,其文风及精神状态亦发生变化,并开始怀疑其作为作家的意义,这种冲突促使他不断压榨自己的价值,通过献血、做苦工等方式执拗地发挥“余热”。作为文学大家,他肩负以文学揭露社会现实的责任,在文坛叱咤风云;但作为志愿者,他对战士们的创伤有一种无力感,甚至将创伤转移到自己身上,无法消解。两种身份在冲突斗争中推着詹姆斯逐渐走向迷失。
五、结语
“当代美国小说往往通过绘制、窥测与再现等方式与世界对话,切入人物内心世界,大都在后现代语境下表达各自反思人性,希望从失意中获救的愿望。”[10]如何从高度发展、存在各种痼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保持自我身份,这正是欧茨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众多美国人难以回避的现实,欧茨在创作中也更多地通过“身份”问题表达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忧虑。尽管五个篇章的故事皆为欧茨刻意模仿大师笔触的想象之作,却都巧妙地将美国的现实和名人的生活结合起来,展示了个人生存因与家庭、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将人物置于多重图景之下进行综合考量,并从个体身份、家庭伦理身份、社会身份三个层面对《狂野之夜!》中的身份危机进行分析论证,探寻欧茨对现代人生存现状的人文关怀,以期引发人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毛信德.美国小说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2] 胡晓华.“卑贱”的回归——论欧茨小说《圣殿》的自我认同观[J].外国文学,2011(4).
[3] Oates C J.Wild Nights![M].New York:ECCO Press,2015.
[4]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6).
[5] 顾悦.鲍勃·迪伦、离家出走与60年代的“决裂”问题:欧茨《何去何来》中的家庭系统[J].外国文学,2017(5).
[6] 唐丽伟,季水河.消费主义的家庭伦理镜像:欧茨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之内涵呈现[J].当代外国文学,2016,37(2).
[7] 郭晶晶.《海》中的身份认同危机及伦理悲剧[J].当代外国文学,2015,36(4).
[8] 刘兮颖.《赫索格》中的身份危机与伦理选择[J].外国文学研究,2015,37(6).
[9] 朱莉.囚徒·玩偶·自我——评《掘墓人的女儿》中伦理身份的演变[J].当代外国文学,2015,36(2).
[10] 杨金才.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2).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王沛然,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