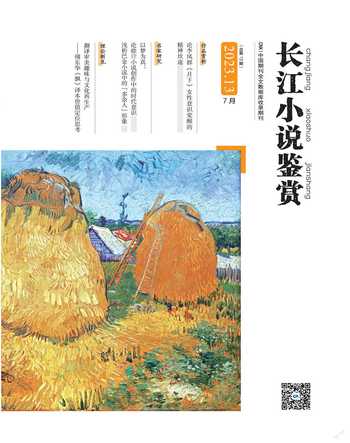以梦为真:论徐訏小说创作中的时代意识
2023-12-20窦承慧
窦承慧
[摘 要] 因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徐訏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作品中多次出现亦幻亦真的“梦”与“鬼”的形象,“话梦”与“话鬼”为文本带来相当丰富的诗性特征,也是作者言说自我的方式。通过“梦”與“现实”的跳跃与转换,徐訏在文本中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现代转型,展现出某种“超越性”的时代特质。而作为抗战时期的作家,徐訏始终秉持着一种时代意识进行写作,他以“流亡人”的身份探索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并以此回应启蒙与救亡的宏大主题,同时也自觉地与主流话语保持一定距离,作为“门边文学”而与之构成了带有距离感的“对话”关系。通过对徐訏小说创作中的时代意识进行探讨,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40年代“文化综合”时期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文学样态。
[关键词] 时代意识 徐訏 新浪漫派 四十年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3-0056-0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展到后期,西方现代主义与连绵的战火共同催生了具有相当哲学深度、旨在探寻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文学潮流,即“新浪漫派”[1]。新文学从“为人生”的浪漫派发展到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从而形成神秘、传奇的文学审美,同时又具有通俗的外部文学表征,徐訏就是典型代表作家之一。以20世纪50年代赴港为界,徐訏前期作品中呈现出幻梦与奇诡的浪漫气息;到了后期,他的作品走向成熟,在浪漫之中蕴含着直面现实的家国情怀,从而具有相当的时代特征。
本文选择20世纪40年代徐訏的小说作品分析、思考作者的时代意识。首先,由于这一时期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徐訏在精神上追求自由与浪漫,因而在创作上带有中国文学传统的传奇色彩与现代感觉,渗透了作者不羁的想象力与浪漫诗性的主张,他是自觉地带着时代意识进行写作的,以此为锚点观照其前后期的文学创作,能够使我们对小说中的时代意识有更加全面的认知;其次,20世纪40年代有着十分特殊的文化背景,作为中国文学发展格局中“承上启下”的存在,这一时期不仅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息息相关,也因与救亡的主题相连而发生了新变。战争促使文学发生空间上的流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的多元并存取代了“北京-上海”的单一文学中心,展示出相当丰富的文学生产格局。
作为既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又深受现代主义与法国浪漫主义影响的学者,徐訏有着相当开阔的文学视野。赴法留学与哲学、心理学的教育背景,大陆和香港的两地漂泊经历铸就了他“梦”的底色,使得他能够自由穿梭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其40年代的小说作品体现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人性的现实关怀,无一不蕴含着他对生命体验的关注和对所处时代的深入思考。
一、言说自我的方式:“话梦”与“话鬼”
鬼神与梦境在徐訏前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据相当重要的篇幅,对梦境的偏爱和对鬼神的描述无一不浸染了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情,这与其赴法留学的经历不无关系:“法国的文学、哲学精神与他个人心灵气质的神秘投合,更使他有一种自由飞升的快感……巴黎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与艺术资源。”[2]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核心主题之一,死亡体验的自由想象与徐訏内心的美学诉求深深契合,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大量有关梦境与神鬼的描写。
以其1938年的成名作《鬼恋》为例,“我”在深夜的上海南京路上遇到的一位自称为“鬼”的问路女子,并在一次次的偶遇中爱上了她,遍寻不得的“我”在白日的偶遇中揭开了她的身份:一个曾经最为入世、满怀激情的革命者。在经历了理想破灭、爱人离世等种种挫折后,她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中,以人鬼之别拒绝了“我”的示爱,也拒绝回到“人间”:“同侪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3]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人物内心独白,情节的展开也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语言进行的,使读者得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产生细腻而丰富的情感共鸣。“我”与女子缠绵悱恻的爱情亦真亦幻又扣人心弦,人内在的情感与外在怪诞的世界互相交织,展现了心灵深处空虚痛苦的内在意蕴。
如果说《鬼恋》中的女子并非真正的“鬼”,那么《阿剌伯海的女神》则直接描写了一段离奇的梦境——海上波涛汹涌,无边的烟雾与迷蒙,“我”在船上遇到了一位女神并和她展开交流,但小说结尾,“我”醒了,恍然大悟原是一场梦。徐訏在创作中大量运用想象、象征等手法,使得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与梦中的世界成为小说的主线,渗透了作者不羁的想象力与浪漫诗性的主张,让思维在文学文本之中自由翱翔,从而带来诗意的审美特质。故事总是发生在坟边、海上、深夜,发生在“我”的梦中。异国女郎、海妖、神仙、灵魂都成了可以对话的对象,人物扑朔迷离,情节飘忽不定。借助梦境与鬼神,徐訏探讨的是生与死的界限,通过虚构和想象创造出生动的情节,营造出梦境与真实交织的世界,从而展现出异质性的、超验性的特征。
类似这样描写幻梦、书写想象的文字在徐訏的作品中十分常见,写“鬼”实则写人,话“梦”实则指代人间,人物的处境与选择是对现实生存境况的折射——《鬼恋》写于抗战初期,但作者并未过多落笔于当时紧张的社会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环境,而将关注重点放在看破红尘的夜行女子身上,以“宁做鬼而不当人”为切入点,侧面展现出理想幻灭的不甘与痛苦。从人与鬼的两重视阈来展开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这与他在《一九四〇级》里所表达的对小说创作的精神向度和艺术手法所持的态度不谋而合:“人生有时很神秘……虽说你的小说采取写实的态度,而实际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故事。这倒是我自己常常说的,伟大的小说一定是具有浪漫主义的气魄与写实主义的手法。”[4]
从这一角度而言,对梦境与鬼神的书写实际指向的是现实人生,而在梦中所建构的精神世界中有着作家本人的思考,也是徐訏所特有的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方式。
二、探寻生命意义:在时空的分野之中游走
因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徐訏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相对朦胧的环境中,通过对梦境的描述和幻想中的世界来展现内在的情感真实。从另一角度而言,这样在梦境与幻想之间、虚实之间的自由穿梭,在时间与空间的分野间游走,也是他试图打破经验世界的僵持而做出的尝试。
与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的浪漫派作家不同,徐訏致力于创造一种与经验世界无关的体验,这与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和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不无关系。《阿剌伯海的女神》便充分利用时间的变形与空间界限的模糊展开故事:“我”与女神的谈话伴随一次次的相遇而展开,不设章节的特点使人难以察觉想象与现实的界限,而只在最后点出,“我一个人在地中海里做梦。是深夜”。这样回环的艺术效果带有浓厚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唐传奇《枕中记》中,青瓷枕作为空间分隔的道具,内部时间与主人公所处的现实社会流速迥异,给人“山中一日,地上千年”之感。区别在于,作为道具的“瓷枕”在徐訏笔下变为主人公的“梦”与想象,借助梦境来实现空间转换,“南柯一梦”的故事原型在这里得到充分应用。因而有学者认为这篇小说“无论在结构的复杂多变、时空变化的娴熟把握和容量的深度方面,都达到中国现代小说前所未有的高度”[5]。“梦”带有更加隐秘的空间转换效果,使读者被代入其中而无所察觉,附着在意识上的时间在梦境中失去了逻辑性,一觉醒来方觉是大梦一场,徒留满心怅惘。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小说重视时间线索,重视故事在时间上的顺序与完整,而在徐訏笔下,时间与空间的位置发生变化,在线性时间内发生的故事可以被重复、颠倒与置换。《阿剌伯海的女神》通过主人公“我”的梦完成了从想象到现实、从古至今的空间与时间场景变换,从而体现出作者对时空关系的重新把握。这样,空间形式的转变带来了“陌生化”的故事效果,时间则成了可以隐匿的文本要素。
发展到后来,深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徐訏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模糊梦境与现实界限来表现二重性的冲突,而更多“着眼于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思考和探索,并以其多重性思考和系列性探索构成了独特的恢宏气派”[6]。即使是在《风萧萧》中,主人公也始终处于香港-大陆、乡村-城市、传统-未来的多维交汇之中,情节中饱含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与具象化的想象,在时空的双重视野之中展现小说主人公的自我探寻。在这里,作者深入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开始探讨人的存在问题。通过对人类困境的深层次思考,徐訏揭示了对彼岸世界的深度怀想,展现浓郁的神秘色彩的同时给人别样的阅读体验。
徐訏的写作风格也与其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自幼父母离异,遭逢国难而四处漂泊,一生颠沛流离,这样矛盾而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呈现出一种“超越性”——40年代的作品中,徐訏努力耕耘的并非宏大叙事的土壤,而是选择在想象与现实的空间中游走,时间与空间都不再成为束缚其思维的枷锁,转而成为作家独特的表现方式。
三、两地三处漂泊:“流亡人”的家国情怀
徐訏在小说中所建构的空间与时间最终形成了一种指向人性与美的精神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同样关注到当下与现实人生,以探索个体精神的姿态回应启蒙与救亡的宏大主题,并由此展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造成了当时中国作家们集体性的苦难经验,也成就了这种人生经验的描述与升华。战争使他们发现了生命的魅力与庄严,探寻具有人类整体价值的精神向度。
抗战爆发时,徐訏在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学习。得知战争的消息,他放弃未完成的学业,于1938年1月义无反顾地回到当时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和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他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救亡情怀,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8年,他写长诗《一页》,以此来歌颂人民自发组织起的队伍:“我们的头发像火山顶口的火焰/像是五千的旌旗在那儿飞扬/每个人的脑子都像火山里荡漾。”实际上,整个40年代,徐訏都辗转于孤岛上海和当时的大后方重庆,这一时期的作品因受到战争影响也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这在他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41年,《风蕭萧》开始在重庆《扫荡报》连载,小说中的人物在战火之中挣扎求生,也寄寓了他对于社会的关注与想象,包含着作家特有的、对于新中国的理解与阐释。
面对当时动荡的局势,徐訏发出“人间多是愤怒忧郁”[7]的感慨,“愤怒”于外来侵略,“忧郁”自然是指徐訏面对时局的态度。也正是比旁人多一分“忧郁”,《风萧萧》的情节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激烈冲突,外来侵略之下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而奋起反抗的故事被转化为各方势力之间的心理博弈,以“风萧萧”作为书名,似乎也预示着故事中人物如同荆轲一样义无反顾的命运。
事实上,去往香港之后,徐訏的作品融入了更为复杂的“本土”与“异乡”的情调。小说《江湖行》以主人公周也壮为线索,展开他从小城镇到大都市、从土匪营到红色根据地、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的辗转人生,呈现出抗战中期社会各方暗流涌动、爱恨交织的“江湖”风云。周也壮的成长历程中贯穿着认识自我、不断前行的主题,“从生存的角度去审视这个时代与社会的悲剧,赋予了作品更深层次的思考与阐释空间”[8],也正是在战争动乱下,家国和个人的命运沉浮才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以“流亡人”的身份站在香港遥望内地,同样是作家“为了人类进步光明与正义的事业而勇于承担漂泊命运的精神体现”[9]。少时父母离异,青年出走留洋,遭逢乱世而多次辗转,晚年客居香港,徐訏将对山河家国的眷恋融入笔下人物的平凡人生,内化为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对个体精神的永恒追求,通过书写人物的自我反思与成长历程展现出对家国意识的深刻认同。他认为,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在于个体觉悟的提升、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特征体现在小说中,就产生了一批内心迷茫、转而坚定自我的“成长型”青年形象。对此,有评论者做出了相对中肯的评价,即徐訏所书写的,“是在战争的特殊挣扎中人们所放射出的‘生的光辉,也在战争的生与死里找寻爱、美、人性与民族的关系”[10]。
这样,由战火中生长的民族认同感与救亡意识在精神上互联互通,转而推动作品产生凝聚人心的意蕴内涵。从《鬼恋》到《风萧萧》再到《江湖行》,从留洋巴黎到返回祖国,从小家小我到民族国家,宏大的家国主题以鲜活的个体生命为依托,徐訏半生漂泊,也在小说中展现出宽广的社会现实。
四、“门边”文学:溢出时代话语的书写
如上文所言,徐訏40年代的小说创作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与主流审美保持一定距离的疏离感,其个人体验也显示出向内开掘的特质。时代风云之中,他认为自己是以一种相对疏离的姿态进行写作的。在谈起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时,徐訏坦言:“我偏是在‘门边……我能谈的恐怕只是门边文学,因为我确实无法看见文学的‘正门‘右道。”[11]如果说当时主流文学话语是讲求文学“为人生”的写作方式,那么徐訏的这种创作风格,无疑超出了时代的主流话语。
与“门边”相对的是“室内”,作为一位曾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作家,徐訏的重新发现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过程。学者吴义勤认为:“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又被湮没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12]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严家炎特别注意到40年代徐訏小说在文坛的一度风行,并首次将其与无名氏等命名为现代小说的“后期浪漫派”[13],也被称为“新浪漫派”。从流派划分而言,与徐訏有着相似文学风格的作家还有无名氏、张爱玲,将徐訏及其所属的“新浪漫派”放置于文学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会发现40年代中国文学中具有一种对于普遍意义的生命哲学的追求,这也是无名氏、张爱玲等人在爱情叙事框架之下所展现出的共性特征。
而当我们再度回看五四时期的文学史时会发现,新文学在独立之初就被赋予了“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因此自然而然地带有改良政治和改善人生的责任。不论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都必须立足社会现实,是“人的文学”之下的启蒙话语。发展到后来,40年代的革命战争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五四时期“浪漫主义”逐渐成为成仿吾在郁达夫小说《沉沦》中未能找到的对于“灵”的追求,成为超越社会世俗层面、转而关注个体归宿问题的“新浪漫派”。
因此,在革命话语逐渐占据主流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徐訏、无名氏为代表的作家,认为自己“必须为人的存在的个体性原则辩护,必须在激进的现实功利性原则压倒一切的时候还能顾及个人的生活情趣、浪漫情调,必须面对时代整体主义的价值吁求而做出符合个人意愿的回应与选择”[14]。在社会革命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流话语之下,徐訏展现出将理想落脚于人性、人格圆满之上的审美倾向。
五、结语
总的来说,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徐訏在小说中呈现出相当丰富的文学色彩,作品里频繁出现的梦境与神鬼是其言说自我、表达情感的方式,通过“梦”与“现实”的跳跃与转换,他试图打破经验世界的僵持,并由此生成某种超越性特质。在创作出具有相当浪漫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的同时,其小说中也蕴含着对于家国情怀的深切追求,宏大的家国主题以鲜活的个体生命为依托,为我们展现了宽广的社会现实场景。
徐訏本人的文学历程十分复杂,曲折迂回的漂泊经历使他跨越了诸多文学版块,从国统区、“孤岛”上海到大后方重庆、再到香港,这样的文学选择之中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的时间和空间信息,因而成为文学长河之中的生动个案。可以说,徐訏见证、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这些蕴含丰富社会历史意义的内容在他笔下化为个体生命的背景、化为对永恒人性的孜孜索求,在自觉书写、反映时代的同时,也与这一时期“多中心”的文学格局遥相呼应。
参考文献
[1] 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2] 吴义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传[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3] 徐訏.鬼恋[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4] 徐訏.徐訏文集(第六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
[5] 王璞.一个孤独的讲故事人——徐訏小说研究[M].香港:里波出版社,2003.
[6] 孔范今,潘學清.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J].文史哲,1990(2).
[7] 饶良伦,段光达,郑率.烽火文心:抗战时期文化人心路历程[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8] 张露.史诗性场面下的悲剧与反思——论徐訏《江湖行》的悲剧意识[C]//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USA,Asia Pacific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Hong Kong.Proceedings of 2017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EERES 2017)V109.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2017.
[9] 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10] 张学昕,鲁斐斐.“抗战小说”的叙事伦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4).
[11] 徐訏.门边文学[M].香港: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2.
[12] 吴义勤.“通俗的现代派”——论徐訏的当代意义[J].当代作家评论,1999(1).
[1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4] 耿传明.大动荡时代的个人性话语与时代话语——20世纪“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责任编辑 夏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