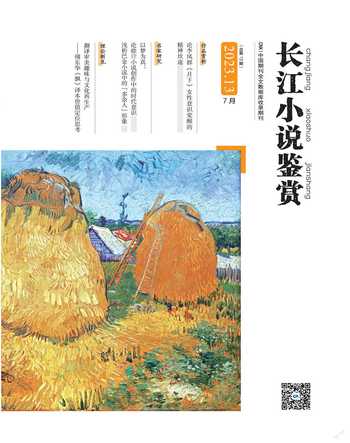论史铁生“残疾”与“命运”主题书写
2023-12-20徐子寒
[摘 要] 史铁生作为十分重要的当代作家,回看他的小说创作历程不难发现相似的人物与情节时常自由地游走于文本,作品之间的隔阂在他笔下的“写作之夜”被彻底打破。本文分别从“残疾”和“宿命”两个方面出发,着重关注《务虚笔记》《午餐半小时》《山顶上的传说》《原罪·宿命》等小说作品,分析这两类议题究竟如何发源并在文本中发生演变:第一部分“残疾的登场与‘角落”,从个体独特的残疾体验入手分析史铁生如何逐渐关涉到广义人类的残疾主题;第二部分“命运的过去与未来”,从史铁生形而上的思考中,分析在被“偶然性”所占据的人生中如何看到过程的意义。以此两点试图为史铁生作品里的融合与断裂的形成寻找不一样的发现和注解。
[关键词] 史铁生 “写作之夜” 残疾 宿命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3-0065-05
回看史铁生的创作历程,学者梁鸿[1]认为其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受时代精神的影响所创作的“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作品,代表作是1983年发表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二个阶段是对残疾、命运和爱情主题的描写,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我与地坛》1991年发表于《上海文学》,一经刊出就引发了广泛的好评与热议,成为史铁生走向“经典”的标志性作品;第三个阶段以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为代表,“作者则把思维视线投向社会生活中人的生存境况,重新阐释‘永恒‘唯一‘爱情的意义,由此而延伸对整个人类生存和社会生存的思考”。然而对比史铁生写作过程后面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顿挫感”更强烈。《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下简称《清平湾》)与《山顶上的传说》创作时间上相差一年,但两部作品表现的风格有较大的差异。《清平湾》中,史铁生根据自己在陕西插队的亲身经历用回忆的视角诗意地展示了清平湾的风土人情。而《山顶上的传说》却是以爱情故事为落脚点,一个残疾的男青年寻找丢失的鸽子,由此展开对于命运的思考。为什么相近的时间创作出的作品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逻辑?张均认为,《清平湾》之后的史铁生的确得到了文学界的褒赞,但这之后文学界对于“现代派”和新潮小说的追捧使得史铁生与“当时语境、文学成规、氛围、批评等制度化环境‘脱轨” [2]。因此后续作品里,史铁生进行了一系列“修补”来缓解被文学界“忽略”的忧虑。这些“修补”表现为文本中添加的“技术元素”,“有意识地构建自我写作与文学新概念之间的共生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史铁生写作的变化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创作转型问题,程光炜在《关于疾病的时代隐喻》提出,史铁生从“牧歌般的《清平湾》”的追忆诗化写作转向具有“沉思病痛之意义的《我与地坛》”,不只是因为创作转型,“地坛”还承担着时代“纪念碑”的意义。他推断,写作《我与地坛》的史铁生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小说家,为何还要一遍遍徘徊于地坛前,写下《野草》式暧昧难解的文字?《我与地坛》的文本中内含史铁生面对时代和历史重大事件的沉痛、质疑和犹豫的心绪,被反复提到的“地坛”或许是史铁生在信仰的废墟上树立起的“纪念碑”[3]。
相比于創作阶段划分中出现的“顿挫感”,史铁生作品中时常出现文本交杂的“既视感”。史铁生写作风格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线性发展,在创作进行中会与自己之前的作品进行对话。轮椅的确限制了他走向外部世界,但这并不是无路可走的绝境,反而促进史铁生向内开掘的深度与广度。史铁生就像他在《原罪·宿命》中所写的全身瘫痪的“十叔”,虽然只能通过镜子的折射来观察外面的世界,但就是这一方镜像让他在头脑里编织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小说《务虚笔记》是史铁生第一部长篇作品,也是一个写作阶段的集大成之作。小说里所有的人物被做了模糊化处理,他们没有具体的名字而是用“身份+字母”作为区分。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勾连交织的故事又有着相同和不同的部分。这些情节不加区分地频频闪现,甚至史铁生之前创作的作品也于“写作之夜”直接登场。比如“我”在“写作之夜”的喃喃自语提到了《奶奶的星星》所描写的情节,“我”无意间知道了奶奶是地主,那个瞬间成为我的“生日”。为什么这些相同的形象可以在文本中毫无遮拦地游走?学者吴俊提出史铁生小说“有一种明显的回忆性”,“所谓回忆实际上便成了史铁生走向宿命——同时也就是获得解脱——的心里途径”[4]。“回忆性”的确是对文本中频频出现的类似情节的精准概括,但这一概念显然被赋予了方向感,“回忆”是一种看向过去的视角,这缩小了史铁生小说视角的范围。“历史”摆脱了单行性,他自己也化身为“写作之夜”里的上帝,击碎了作品之间的壁垒,它们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被一视同仁地在自己编织的“历史之网”中铺展开,进行“印象式”的对话。因此,寻找史铁生小说“印象式”写作形成的踪迹,循着史铁生的目光重新回看那些文本中频频回放和逡巡的人物与时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遁入“写作之夜”后史铁生那些喋喋不休的形而上的玄思。
一、残疾的登场与“角落”
二十二岁的史铁生由于脊椎的病变导致双腿瘫痪,“残疾”成了他余生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也是他创作中难以绕开的话题。一个坐着轮椅的青年人总是在史铁生“写作之夜”的迷雾里缓缓现身,登场返场。然而那些最初的创作里,痛切的人生经历并没有让史铁生急着全盘托出,《爱情的命运》《兄弟》和《法学教授及其夫人》这几部早期作品一定程度上受到“伤痕文学”的影响,尽管比起同时代的作品它们没有沉醉在控诉的氛围里,但也难以从中辨别出“残疾”的影子。直到史铁生创作了《午餐半小时》,一个躲闪的、稍一露头就迅速退场,却又频频出现的“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在文本中登场了。当街道的大爷大妈因为“红旗车”展开联想时,“小伙子”穿梭其中打着算盘清算工资,似乎意味着将沉浸在荒谬想象的人们拉回现实。这是史铁生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残疾人形象,之后的创作中直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才再次看到一个因为腰腿疼最后双腿萎缩的“我”。刘芳坤认为史铁生早期的创作有明显的“角落的印记”[6],与史铁生在街道工厂工作的经历息息相关。街道工厂里的人们多是没有工作的老年人和需要照顾的残疾人,这些人需要街道帮扶和安排才能找到自己的工作和社会位置,处于整个社会运行的“角落”。类比来看,此时在《午餐半小时》出现的“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在史铁生的写作序列中也处于“角落”的位置。到《足球》《山顶上的传说》等作品里,不管是两个坐着手摇轮椅去看球赛的年轻球迷,还是丢失了爱情和鸽子的瘸腿小伙子,他们都比《午餐半小时》里出现的残疾人形象要更加明朗和重要。因此,“角落”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心态,残疾对于此时的史铁生仍是需要回避的。
“角落”的位置意味着忽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呼之欲出、想要登场的欲望。《清平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那个“躲闪的”瘫痪青年又消失了,到了《足球》之后才又重新登场。小说一开始就埋下了两难的情感期待,去看比赛的残疾青年只有一张门票,小刚不能拄拐没办法跨上体育馆的楼梯,山子等着去捡小刚的漏,两个人里注定会有一个人失望而返。这是史铁生身为残疾人必然经历的细节,言语里呼吁对残疾人要做切合实际的关怀。然而,这篇小说想要表达的含义不止如此,小说里盘踞山子脑海中的最强音不是能不能看上球赛,而是他喜欢的女孩晚上要来找他。山子渴望通过他热爱的球赛来冲散现实的烦恼,更希望忘记自己是残疾人,残疾是一切烦恼的源头。尽管不少作品里史铁生都表达了想要“忘记残疾”,但是对于残疾的遗忘已经不再是遮蔽现实以求得心理安慰这么简单。小说《山顶上的传说》对于这一想法表达得更为清晰,恋人一时口误提到了“瘸子”这个词,瘸腿小伙子不為恋人的口误生气反而感到轻松,“他感激地望着她。但愿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忘了。忘了吧,别总记着。只记得有那么个名称倒没关系……”[7]因为“瘸子”不是一个开玩笑的“外号”,“瘸子”是一种对身份的认定,背后牵扯出来的是现实中残忍的事实。忘记具有双重意味,他渴望自己忘记残疾,获得像做梦一样可以休息和喘息的机会,同时他也希望别人忘记残疾,因为残疾必然带来他人异样的眼光与下意识的歧视。瘸腿小伙子想要发表自己的小说,反复修改之后始终不能如意。给他帮助的文学家劝他别太较真,小伙子细想后发现一个恐怖的逻辑,“凭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羞辱”,残疾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在潜意识中将残疾者与正常人区分开,只要打上了“残疾者”的烙印,注定就要低于常人,“理所应当”得到人们的同情与关注,哪怕除了残疾其他方面表现得并不比任何人差。这样的“同情”显然是伪善的,甚至是不人道的。因此,停留于表面的同情远不能概括史铁生对于残疾的表达,他真正想要关注的正是“残疾”所引发的差别处境,为残缺的躯体求得灵魂上的平等与公正。
真正的差别是直击灵魂的。如果只关注对肉体残缺的歧视会造成视角的单一化,生活中更显而易见的事实被残疾身份遮蔽了,即使没有肉体残疾作为条件,社会中依旧处处存在着差别与歧视。因此,史铁生在回复学者吴俊的信里提到了“人的广义残疾”,不再将残疾的主体局限在伤残的个体,而是对全人类的灵魂进行拷问。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里有一个情节,取得过硕士学位的詹牧师频频不得志,他想要向社会奉献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却不被当时的社会接纳。有人想要找詹牧师学外语,詹牧师对此事怀有很高的期待。但那个年轻人仅来过一次之后再也没出现,詹牧师由此大病一场。詹牧师的身上没有任何残疾,可现实中他仍处于一个被差别化的位置,他被闲置了。詹牧师身上的“有用性”被剥夺,如同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失去了双腿,也如同在街道做临时工的身份,处于一个社会的“角落”。小说《别人》里出现了一位失恋者,“失恋”这一遭遇含有强烈的隐喻,不仅灵魂被剜去了爱情的部分,更代表一种孤立隔绝的状态。失恋者总是怀疑自己被人看作“疯子”和“流氓”,这种担惊受怕的状态已经意味着一种精神与灵魂上的残疾。某种意义上,残疾不是降临在某个人身上的灾难,而是全人类都难以幸免的事实。因此读者时常能看到那些残疾的身影在史铁生的小说中徘徊,他们总是寻找着什么来填补灵魂上的残缺。《山顶上的传说》里寻找鸽子的瘸腿小伙子一路找寻到《务虚笔记》,瘸腿小伙子“化身”为“残疾人C”,也变成“写作之夜”中的任何一个灵魂残疾的人,找寻生命中处处隐现的“白色羽毛”。尽管广义上的残疾将平等和差别摆在了同样的位置,但史铁生不是要在创作中将平等和差别简单地二元对立起来,进而抹杀掉差别的意义。《务虚笔记》中展开的“写作之夜”,两个在树下玩耍的孩子代表了人类演化的童年期和雏形,灵魂上的平等使他们“是所有的角色,也是所有的演员”,但按照史铁生的逻辑推演下去,如果人类真的在本质层面毫无差别,那么差别的世界又是何以衍生的?两个孩子又是怎样变成那些小说里登场的“画家F”“残疾人C”?
二、命运的过去与未来
阅读史铁生后期作品很容易陷入他的思维漩涡中,浓郁的形而上氛围弥漫在“写作之夜”里,沉浸其中的史铁生是小说家更是一位哲人。那些缠绕的概念与想法里,占据绝大部分的是史铁生对于命运的思考。尽管就像在第一部分提到的,强调史铁生的残疾身份可能有违本人所愿,但“残疾人”的身份注定会使他获得特殊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生活。除此之外,知青与插队的经历也使得史铁生必然会关注命运。在他1979年发表的小说《爱情的命运》里,彼时还稍显青涩的史铁生讲述了一个爱情的故事。“我”与小秀儿是青梅竹马,可是“文革”彻底颠覆了“我”的家。患难之中“我”跟小秀儿谈起恋爱,然而等到父亲平反,“我”也读了大学后,父母却因为小秀儿的家庭问题不同意“我”与小秀儿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史铁生在这个并不新鲜的故事里提到了“命运”,“……客观世界里总有一些我们尚未认识的矛盾,而它们却又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有时会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这就是被人神话了的命运的本来面目”[8]。关于“主观客观”的形而上思考直到《我之舞》中还在进行着。尽管此时他对命运的思考更像是对爱情的注解,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是对兵团知青所面临的生活现状进行忧伤的拷问,但是他对“造物主”等概念形而上的思考已经可以窥见日后史铁生作品里宿命氛围的端倪。
史铁生命运主题的真正显现开始于他对“偶然性”的追问。他专注于此却不沉醉其中,因为追问的过程里答案已经浮出水面,对于“偶然性”史铁生始终是清醒且抱有怀疑的。早期小说《巷口老树下》描写了一群被“八卦算命法”所吸引的人,关键道具“硬币”是偶然性的具象化,硬币落下后“麦穗”面还是“国徽”面是完全随机的。然而故事的最后算命的人宣布“错了”,硬币上“国徽”与“麦穗”的结果颠倒了过来,原本算“坏命”的人变得欣喜,“好命”的人只能“木然地”承受命运的反转。显然,戏剧化的情节构成了对偶然性的嘲弄。同样的硬币也出现在《山顶上的传说》,瘸腿小伙子想通过硬币来帮助自己做选择,当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时产生了“五局三胜”的想法,故事的最后他在山底下用硬币换了一个烧饼,硬币对于命运的指引就变成了一种讽刺。《原罪·宿命》里出现了史铁生对偶然性最清晰的反讽,“我”原本有大好前程摆在面前,却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双腿瘫痪。小说中的“我”一遍遍地在头脑中做思维演算,试图找到一条可以拯救自己的方法。最后“我”将目光锁定在一个笑个没完的学生身上。当多年后“我”问起学生为什么笑,学生却说因为他看到了一条放屁的狗。追根溯源,这一切的悲剧的起源就像“上帝”的一则玩笑。对于偶然性一边紧咬不放地进行追索,一边又在答案显现之时进行怀疑戏谑地玩弄,这似乎构成了一种思维上的矛盾。毕竟如果将人生的意义全然寄托于偶然上,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帝的嘲弄”,那么史铁生又是依靠怎样的意志能力进行写作的呢?或许对偶然性的追问与怀疑并不是为了得到某个“终极答案”,将偶然性本身的“严肃性”进行消解可以得到一种情感上的慰藉。人生的一切如果都在冥冥之中是“上帝”的精心安排,那么“残疾”一事就成了一件合乎逻辑的事实,也变成了人应当背负的“原罪”。学者吴俊提到,“所谓宿命意识,本质上不是属于理智的,而仅仅只是情感的;它是一种基于苦难经验之上的情感和无可究诘的思索”[4]。
如果继续沿着故事逻辑追问下去,为什么会是一只狗出现在学校?答案必然陷入停顿,因为追问如同圆周率的延展一样无穷无尽。史铁生在文中提出“上帝”来给追问匆匆做结,因此可以看出把宿命归因于偶然在“写作之夜”中不是完美的逻辑,“上帝”的确可以做暂时的精神避难所,但是一旦刨根问底地追问下去,“上帝”也难免变得不再可靠。到这里史铁生没有停下他在“写作之夜”的跋涉步伐,事实上他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既然走向终点去迎接“上帝”并不能得到圓满的答案,那么中途的“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命若琴弦》里的老瞎子知道那“治疗眼睛的秘方”就是一张白纸后还要给小瞎子定下更高的目标,就是因为目标的意义只是虚设,但通往目标的“过程”是真实存在的。小说于结尾处又回到了开始,“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攒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9]文本的循环性宣布小瞎子和老瞎子正在经历命运的轮回。然而对于老瞎子来说“过程”代表着向后看,在所剩无几的余生中回顾他的命途;而小瞎子的“过程”是向前眺望,他的生命将在那张“药方”的指引下缓慢铺开。目的的虚伪性已经预设,但是“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将发出真实悦耳的声音,这不可虚构,也无法欺骗。同时,老瞎子拥有余生,小瞎子拥有未来,这也注定了对于“过程”的理解具有双重的含义。对比同样具有“向后看”含义的偶然性,穷尽追问也只能在已经过去了的既定历史中与自己的回忆论战,审视的目光无疑是绝望的;只有过程才能既向后抚慰灵魂的隐痛,也能向前勾连出可能性对一个人的生命进行有意义的延续。这样史铁生的文字才被真正打开,避免掉入固步自封的逻辑诡辩的圈套。此外,史铁生不厌其烦地在其作品中提到“上帝”“造物主”等具有宗教意味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他本人皈依了某种宗教,“上帝”其词本身被剔除了宗教赋予的历史文化含义,留下的“宗教精神”才是史铁生一直喋喋不休的文学主题。因而,不停地跳回和重复生命的某些时刻,让那些印象式的形象不停地游走穿梭于文本中,不是为了通过肢解事件来挖掘出写作与生命的意义,在漫长的写作之夜跋涉的过程中,他已经踏入他所祈望的神坛。
参考文献
[1] 梁鸿.史铁生:残障生存与个体精神旅程的哲理叙述[J].北京社会科学,2003(2).
[2] 张均.史铁生与当代文学史书写[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1).
[3] 程光炜.关于疾病的时代隐喻:重识史铁生[J].学术月刊,2013,45(7).
[4] 吴俊.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J].文学评论,1989(1).
[5] 史铁生.务虚笔记[M]//史铁生作品全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6] 刘芳坤.诗意乡村的“发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80年代文学批评[J].南方文坛,2011(5).
[7] 史铁生.山顶上的传说[M]//史铁生作品全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8] 史铁生.爱情的命运[M]//史铁生作品全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9] 史铁生.命若琴弦[M]//史铁生作品全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徐子寒,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