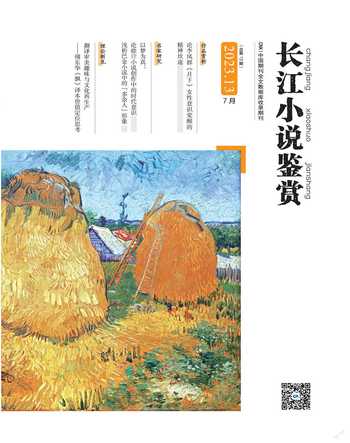论李凤群《月下》女性意识觉醒的精神坎途
2023-12-20刘点
[摘 要] 小说《月下》通过女主人公余文真近十余年的婚恋故事展现出小城女性的心灵成长历程,作者以尖锐犀利的笔触深入当代女性的内心,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精细分析,呼应不断演变的现实。主人公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是她自我审视、寻求自我呈现和价值实现的过程,并深刻触及现代社会中女性意识觉醒的困境。从反抗到疯狂,最后归于沉寂,余文真试图挣脱原生家庭和城市环境的束缚,但最终选择和解与回归,以“选择”消解“命运”,是她用来对抗时代洪潮和实现自我现代化的精神武器。
[关键词] 《月下》 女性意识 心理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3-0003-05
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曾经历过很长一段发展时期,反叛与逃离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其最初阶段主要表现为对男权的反叛,首先是对父权和夫权的反叛。……直到三十年代,情况才有所变化。大都市的发展为逃离家庭的新女性提供了可能。”[1]时代的洪流中,社会的更新迭代使得女性自我的确认不断经受新的考验,在《月下》里,这一考验掩藏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对人的精神产生某种摧毁性的力量,是平静时代中最值得深刻洞察的悲哀。
《月下》以一个虚构的县级市“月城”为背景,书写以余文真为典型代表的小城女性在时代变革中产生的怯懦的欲望、孤独的觉醒与疲惫的抗争,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困境通过心理和精神表征极其细腻复杂地表达出来,大量的心理描写和细节填充在文本之中,令人信服且惊心动魄。余文真的觉醒充斥着痛苦与迷茫,并有迹可循,原生家庭塑造她的人格,成长经历撕裂她的情感,然而等到最终醒悟才发现,她始终身处于“城市的迷宫”之中,社会意识与女性意识的驳杂相交给予余文真巨大的冲击,原本因两性交锋而建立的“受害者”思维生出的嚣张、跋扈、怨尤,最终都变成和解、救赎与巨大的宽宥,给读者生命的蓬勃之感。
一、源起:“看”与“不看”的挣扎
准确地说,被“看见”是余文真整个成长历程中最深切的渴望,文章开篇便忍不住叹息:“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见。”[2]渴望是因为缺失,正是因为她现实中一直“不被看见”,从少年、青年到中年,十余年的生活中与无数人相遇,她都沉湎于对被“看见”的渴望之中,却往往收获失望,由此余文真觉得自己是“巷子里的一把扫帚,搁置在角落里,见风被风刮,见雨被雨淋,实在无关紧要”,“几乎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似有似没有”。作者笔下的余文真存在感近乎为零,让人不禁感到夸张的同时也忍不住唏嘘。初二年级春分时,学校曾组织学生去东郊踏青,她不仅全程没有存在感,更是在回程时被遗忘,只好自己辗转坐公交回程,等到了家却发现一切如常,没有任何人发现自己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存在感稀薄的本质在于不受重视,由此,余文真渴望“看见”的背后,是对日常生活“平庸性”的抵抗,她渴望改头换面,对新生活和新世界充满向往,这是余文真的初心。
平庸和边缘曾是月城的基调,不足百万人口的县级市,交通不便,全市只有唯一一所本科院校,“月城的显要特征就是‘不被看见,这也是余文真的显要特征”,这也奠定了月城原住民的处事作风。因其安然无缺的平凡家庭和甘于平庸平淡的父母,余文真没有生长出复杂的心机和欲望,又因长久被忽略,内心时刻充盈着梦幻和理想。某种意义上说,她将平庸视为原罪,而儒雅绅士章东南的到来让她被他“看见”,乃至“注视”,为她打开通往新世界的窗口,就像地狱里垂下的蛛丝,承载着帮她逃离和解脱的希望。
然而,理想和现实总还有一段距离,在余文真与章东南交往渐深后,被“看见”的同时也让她感到被某种东西束缚,是来自旧世界的拖拽。与男友的谈婚论嫁总是不顺利,她开始消极以待,然而家庭的压力让她难以喘息,“看着妈妈转来转去,一刻不停,余文真突然一阵心慌,爸爸虽然已经加入赚外快行列,但仍有旺盛的精力在饭桌上配合妻子唱双簧,努力想为女儿即将偏离的人生航线做舵手。他倒不指桑骂槐,只是一味慈祥地注视。只要在这个屋子里,他的目光就无处不在”。人格的弱点让余文真面对这种“看见”时忍不住怯懦和退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需求,却又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和勇气,兀自痛苦和压抑,这是她最初的缺陷,或者说,是一种惩罚,是对她试图背离风俗和群体的警告。于是余文真开始试图寻找“不被看见”的避难所——出租屋“小留”和人情冷漠的公司大楼。戏剧性的是,位于福禄寺巷的“小留”曾是她为了更好地被章东南“看见”而寻觅,最终沦为供她舔舐伤口的避难所;而人来人往的公司大楼曾经承载她的努力和光亮,最终却只成了一座让她虚度光阴的建筑。从“多么渴望被看见”到“被人关注自然是好的,被人忽视也坏不到哪里去”的态度转变,余文真一直在被“看见”和“不被看见”的两端挣扎徘徊,反而让她离被“看见”越来越远。
虚荣与浮躁侵蚀了余文真的意志和理想,章东南带来了新世界的风,但也打乱了她的生活,平庸和新調在她静谧的世界里陡然相撞,让她目眩神迷却也无所适从。余文真声称自己渴望被“看见”,但却一再与新世界错过,月城飞速发展,但她却无法跟上时代的洪潮,沉湎于渴望之中,徘徊于犹豫之中,守着最后被拆迁的“小留”和“铁打的余文员”怅然若失。我们能够看到,当“一方面‘个人努力从各种似乎束缚了个人意识发展的‘共同体(集体)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却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个人的主体性被高度地‘零散化”[3],这是现代社会中女性自我想要得到确立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底层和边缘的时空背景下,月城的城市化催生了余文真女性意识的觉醒,老旧的清凉寺巷和繁华的城东商业区分别指向她的过去和未来,因为渴望“看见”而反抗,却又不断徘徊于“逃避”之中,余文真做出了最初的选择,也成为她意识觉醒之路上极不稳定的导火索。
二、动荡:“受害者”到“加害者”的畸变
当余文真意识到自己的需求时,她的反抗和觉醒是由浅到深的,从一开始的试探到逐渐沉浸,直至学会愤怒、尖刻和疯狂,余文真单纯而青涩的精神世界生起巨大的波澜,在这一过程中,两性间的交锋成为动荡的主题。章东南与余文真纠缠了十余年,作家以心理现实主义的冷峻笔法书写余文真从作为被中年男人欺骗的“受害者”到饱含报复心理的“加害者”的心路历程,这种畸形的情感变化令人感到惊心动魄,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似醒非醒的女人,在规训和反抗之中“触底反弹”,理智和崩溃仅一线之隔,沉浸在无限的遐想之中。
最初,余文真的觉醒意识仍围绕着想被“看见”,不拘于是何种形式,因此她曾尝试复刻中学时期的故事,在大学最后一个暑假去浙大参加职前辅导培训时,故意留在服务区,充满快意和叛逆地看着大巴车离她而去,然而因为没有足够的花费,此时又恰好一辆去月城的车停在身旁,最终这“象征命运的选择”还是让她无奈且乖巧地回了家,最后她突然发现“这恶作剧般的一时冲动,除了导致失去一只装满半新不旧衣服的行李箱之外,对其他人,对这个世界,什么影响也没有产生”。直到遇见章东南,这个狡猾的中年男人对她轻易给出了充实而有趣的“看见”,此后十余年,余文真逐渐将自己对“看见”的渴望不断收紧,直至与她对所谓“爱情”的渴望完全重合,爱与自由不分时间、场合、对错地达成一致,是造成余文真“受害者”身份的悲剧原因之一。
过年时与妈妈发生争执,继而在福禄寺巷租下“小留”,她认为是章东南的爱给了自己反抗和拒绝的勇气,“小留”的存在也是期冀他们幽会的地点能够超出酒店的范围;与男友周雷的分手更是出于方方面面的对比,“婚约解除使章东南变得更加重要。相当重要”,即使此时已经有些许意识到章东南对她的敷衍,但也丝毫不愿给自己反悔的空间:“他没有当真。他不会当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不,她不允许自己这样想。这样想了,她就没有勇气解除婚约,这样想了,她必定要做一个撤退计划。”她的渴望和自由完全系于章东南一人之手,于是忍不住要求更多,情感的交锋和对抗自此占据了余文真成长的大半时光,让她消瘦、憔悴,随后透出从灵魂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疲惫与漠然。真正让她意识到自己是彻底的“受害者”,彻底对章东南失望的时机是天涯论坛上那个讨伐“渣男”的帖子,精英中年男人的套路在这个世界的许多角落都一模一样,余文真终于发现自己被彻底地欺骗了,醒悟过来,她对章东南的谎言“之所以能忍受到今天,因为她幻想着章东南会带她脱离她原本孤独和贫瘠的生活,她假装一切都是爱情的必经之路。因为也是他提供了一种机会,一种摆脱这死气沉沉的生活的途径,她认定他有把事情解决的义务。这个虚无缥缈的幻想已经浇灌她好几年了。如今,幻象全破了”。两性的主导性逐渐颠倒,受伤到极致的女性学会了愤怒和“尖叫”,而这种触底反弹式的觉醒某种程度上正契合了“女性主体性”这个价值理念的核心,作家将余文真的精神动荡聚焦于两性交锋之中,正如曾有学者说“性別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离开人类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单纯的生物自然性问题……隐藏着历史的和社会的奥秘,隐藏着人类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求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天然合理的生命诉求”[4],交锋和拉锯之中蕴含余文真女性意识发展的坎坷与波折、理念与诉求。
另一方面,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情感和地位的“畸变”反而进一步佐证了余文真的成长,女性心理意识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一种“恍然大悟”之中,更需要清醒而理智的自省。“某种经年累月形成的自律像被抽走了似的。一种野蛮力量在滋长,她有一种想做点什么任性事的胆识。就像一个贪生怕死的士兵,在大军压阵前豁出去的瞬间。我跟你们拼了。她听到一种浑厚的声音从身体里发出来,对着她耳边说。”余文真学会了报复,报复章东南,报复对她性虐待的新婚丈夫,甚至忍不住对父母亲人都产生怨怼,她疯狂地给章东南打去威胁的电话,说无尽尖酸刻薄的话,不断提出无理的要求,在被男人平和而疲惫地接受之后,她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加害者”的身份,体会到原来报复并不会产生快感,“胜利也包含耻辱的滋味”,作家跳出通常女性文学作品里的感伤和常规的“受害者思维”,冷静克制地写出了一位普通女性心灵世界的自我革新。余文真审视自身“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不自知的虚荣”,并自我惩罚,通过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忏悔,又在经过自我接纳之后,和章东南平和地坐到一起,以期完成最后的告别,也准备迎来自己的新生。
三、沉淀:“传统”与“现代”间的罅隙
作家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余文真与章东南之间的情感纠葛,并用“误解”这个词一以概之,章东南最初的出现,带给余文真情感上的栖息处,加深对自由和新鲜的渴望,让她从死水般的境地苏醒,重新审视生活。这种“误解”在两人波澜壮阔的爱恨情仇沉寂下来之后越发清晰,我们随着余文真一同恍然和叹息,“这迅猛多端的变化,这洪水一样的大潮,……当时以为惊涛骇浪的情绪,在岿然不动的大势之下,不过像蚂蚁眨了一下眼睛。甚至让她领悟到的这个时刻,也必将化作徒劳和一场空,一切都将无声地消散,变成模棱两可的历史和虚无。”他们的情感和渴望变成时代变革中的一滴水,不过是月城城市化进程背后的阴影,她始终将自己困在阴影中,落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罅隙,难以自拔。
清凉寺巷的拆迁、城东商业区的崛起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交替,同时也是她的过去和将来,在这之间是她的当下。清凉寺巷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性等依旧保有农业文明的基因,城东代表了现代大都市的新文明的冉冉升起,“乡土在这个城市化时代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它遭遇的不是战争或者历史运动一类外部添加进来的苦难,而是内部的乡村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粗粝与野蛮,甚至是家庭内部的压抑导致的困难”[5]。余文真见证了城东从月城的“小疙瘩”变为“冲天犄角”,最后成为“圆月”上的“王冠”。她最终看见的,是城市和生活。在不断的自我审视之中,余文真的个体意识得到空前高涨,并不断呼应自己最初的渴望。她曾经对家庭一脉相承的“拷贝”感到坐立不安,对月城不断变动自己却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感到疑思,对城东的飞速发展感到迷惘。余文真最终醒悟:自始至终最重要的不是被他人看见,而是自我的看见。
余文真恍然:“爱很重要,接受没有爱也很重要,比起这两者,没有恨更重要。”对余文真而言,最初的她不是走向一个男人,而是从传统生活走向对现代的欲望追求,最终以悲剧收场。于是在这样的当下她选择与自己和解,与时代和解,在性别意识之外,社会意识的认知让她更为理智与平和。
这样的和解实质上是不完美的,乃至残缺的,是基于“不爱”的和解。余文真生活中最缺的,就是被爱,以及爱的能力,就像她最终也没有选择和妈妈和解,但却与婆婆相处愉快,她认清自己的罪过,“亲人和城市组成了她的栅栏,她的四壁,她的绳索,她的过去和未来”,也看清这些罪过和错误可能会伴随她的一生:“她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孤零零的,走在没有人的街道上;她看到了更远的将来,必定有更多的失望:男人,其他人,自己,这个城市,她不理解的事……”小说结尾“路”的隐喻让余文真得到救赎,她以“选择”取代“命运”,承受痛苦和放弃追求都是她的选择,这些选择“令她变得复杂,增加了她身上的分量,水分也好,痛苦也好,反正把她变得更有重量就是了。同时附着在她身体里的怨气也荡然无存了”。她不再说爱与不爱,而是接受庸常的生活,成为她自己,这是余文真为自己规划的自由,正如作者曾经在采访中说:“我不满意狂风暴雨,我不满意欺骗和恶,我不满意大规模的拆与建,但我满意风暴终得平息后,余文真身上所持有的勇气。不爱自己的生活,仍然有勇气继续。”[6]
四、结语
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在早期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似乎与社会意识互不相干”[7]。而《月下》仿佛是给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翻开了新的篇章,作家善于书写城市中的女性,女性被置于庞大的社会场域之中,且不再是以“逃离乡土、漂泊于城市”的女性视角,而是身处“现场”,以城市边缘女性的经历展现城乡关系的复杂性,“随着城乡关系的复杂,城乡空间的切换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频繁。这种频繁,带来的并不是不断在城乡之间辗转的人对城乡感情认同的融合,反而加剧了无论是对于城,还是对于乡的认同的分裂”[8]。于是,“在这个大变动的过程中,混杂、多样、丰富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9],构成了《月下》的基本格局。
在《月下》的研讨会上,有人认为文章上半部是女性主义的,对男性享乐与不忠的批判,犀利而不留情,但下半部又解开这个死结,慈悲和有情;也有人提出,余文真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认命可能最能接近她的生活本性[10]。但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具备多样性的,人格的不同使得“意识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女性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终极的、固定不变的,……女性意识的演变也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11]。作家对余文真形象的刻画,是对女性生存境遇的现实呈现,深入日常生活和心理幽微,人物悲剧性和觉醒之路是“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描写,表征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消费的价值被凸显出来,个体生命的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运行就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意义”[12]。以女性个体经验的独特来抵抗日常生活的平庸,消解对命运反复无常的怨怼和消极,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
参考文献
[1] 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文学自由谈,1991(3).
[2] 李凤群.月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
[3] 羅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J].文学评论,2008(5).
[4] 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J].南开学报,2005(2).
[5] 唐诗人,李凤群.人性书写与城乡文明互认——李凤群访谈[J].写作,2022,42(3).
[6] 舒晋瑜,李凤群.小说是我对残缺现实的补充和续写[N].中华读书报,2023-01-11(11).
[7] 赵稀方.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J].文艺争鸣,2001(4).
[8] 赵普光.城乡之间的钟摆:新世纪以来青年作家的乡土书写——以李凤群的“江心洲叙事”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8(2).
[9] 吴丽艳,孟繁华.新文明的建构与长篇小说的整体转型——2013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J].小说评论,2014(1).
[10] 李凤群长篇小说《月下》研讨会举行:一个平凡女性与世界的对话[EB/OL].(2022-12-28)[2023-05-28].http://www.cbbr.com.cn/contents/508/82709.html.
[11] 刘钊.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批评[J].妇女研究论丛,2004(6).
[12] 张颐武.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J].河北学刊,2006(4).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刘点,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