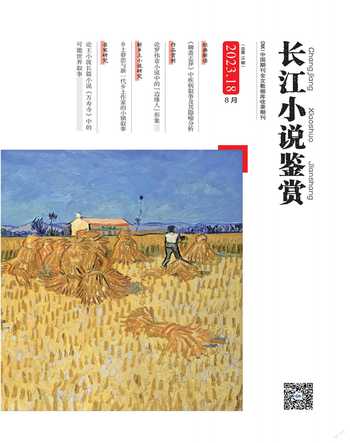乡土眷恋与新一代乡土作家的小镇叙事 □ 宗小琰
2023-12-20
[摘 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新一代乡土作家登上文坛,他们关于小镇文学的创作愈发多元,在丰富小镇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作家表达了对家乡故土的留恋。本文从小镇的二元属性切入,依据丁帆对乡土文学的“三画”理论,从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三个角度分析小镇叙事,通过对新一代作家小镇叙事的解读,深入挖掘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乡土作家对乡土中国的深切眷恋。
[关键词] 小镇叙事 乡土文学 乡土眷恋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8-0083-05
城乡发展一直是作家群体密切关注的问题,从沈从文发出“乡土美,都市恶”的感叹到孙犁对城市“恐惧感、窒息感、无可奈何感”[1]的描述再到路遥与贾平凹对进城后坎坷奔波的农民工形象的塑造,终究都离不开“城乡对立”的主调。改革开放以来,具备城乡双重属性的小镇进入大众视野,面对物质文明发达的城市,小镇叙事呼吁传统和质朴的书写风气,倡导沉稳的笔触和下沉的视角,偏爱“真”“善”“美”的人性呈现,表现了作家群体对乡土文明的深切怀念。
丁帆认为,乡土小说具备三大要义,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这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2],鲁迅和茅盾也用“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来归纳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小镇叙事虽以小城镇为描写对象,传达出现代意识和小镇风情,但每当作者在构建心中的精神家园之时,与之相关联的乡土意识、乡土情感、乡土画面也若隐若现,表现出对家园的“精神眷顾”。
一、风光旖旎的原乡风景
杨袭在《三声蛙鸣》中描绘的那金黄一片的黄河滩、金字塔状的新鲜豆棵和一畦畦规整的稻田,是游子梦回故乡的精神寄托,光滑的石板记录着小城镇逝去的记忆。魏微在《异乡》中所描述的吉安小城是这样的:“青石板小路,蜿蜒的石阶,老房子是青砖灰瓦的样式,尖尖的屋顶,白粉墙。”[3]这些未被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的风景带有作家明显的原乡意识,他们用怀旧的方式,将原乡风景嫁接到熙熙攘攘的小镇之中,消解了城市的后现代传统并表达了对城镇现代化转型的抵抗。
1.白雪皑皑的槐花洲
王秀梅来自有“雪窝”之称的山东烟台,在这片冬天被厚厚白雪覆盖的土地上,作者写下了这部凄凉而唯美的作品——《血红雪白》。两位主人公林雪和杨雪的名字中都带有“雪”字,她们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有雪花的见证,甚至出生时天上都下了大雪,这暗示了雪必将成为她们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情结。
在这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雪”贯穿整部小说,成为一种象征。雪是萧瑟寒冷的代名词,意味着人的压抑与不幸,两位女主人公不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张惠和王小雅在一个雪夜中了两个男人的阴谋,林雪和杨雪又在雪夜呱呱坠地,张惠决绝地将生命结束在冰天雪地中,而林雪一个人孤苦地住在寄宿学校时,外面也时常飘落雪花:“雪花从裂缝里悄悄地落下来,那些雪在摊子上轻声细语,以至于我不敢翻身,生怕惊醒了它们。”[4]这些如雪般美丽的女人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书写着自己凄惨悲凉的命运,也暗示了她们终究会像雪花融化一样悄然逝去的结局。尽管如此,雪也象征了女人们的圣洁、坚忍和纯粹,即便张惠被林宝山以各种形式强迫,但她依旧向往自己的爱情,在无数个雪夜与贾特谈诗弹琴;而看似放荡的王小雅,在自己的理想破灭后对现实采取激烈而勇猛的反抗,最终,光头在雪天骑着摩托车,戏剧性地死去了,皑皑白雪帮助王小雅满足了自己复仇的愿望。作者在《致敬,我的十年》中说道:“槐花洲作为一个意象,不仅仅充当了我写时间流逝和停顿时的道具,同时已经成为故乡的代名词。”[5]槐花洲已成为王秀梅的精神家园,在面对生活本身的疲惫、承受其带来的创伤时,槐花洲不仅是作者一种乌托邦式的主题意象,更是她的灵魂净土。
2.流水淙淙的花街
徐则臣来自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那里降水丰富,河流众多,他说:“童年的成长基本上都是在跟水打交道, 我理解世界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水。”[6]于是徐则臣笔下的“花街系列”以水为枢纽,描绘出一个内敛、湿润、朦胧、轻盈的水乡小镇。发生在花街上的那些儿女情长的往事,那些被爱欲和物欲驱使的灵魂,那些人间烟火气,都与夜晚挂在女人门前的一盏盏红灯笼一起,装饰着水汽氤氲的运河。
花街因水而生、依水而兴、以水为美,徐则臣沐浴着来自花街的雨,将有关童年和青春的细琐回忆嫁接到这座乌托邦式的唯美小镇,并将有关故乡的朦胧记忆用桃花源式的书写表达出来。《石码头》中,年幼的“我”在槐花树上偷窥到叔叔对花椒的侵犯和婶婶与酸六的秘密,这不曾目睹的罪恶给幼小的“我”带来极大震撼,只有潺潺流淌的运河才能安抚“我”。“槐花的香气已经闻不见了,空气中飘荡着清爽的石头和运河的水的味道,有点甜。”[7]运河像母亲一般可以包容所有污秽与丑陋,只将世界的纯洁展示在“我”眼前。《梅雨》中,连绵稠密的梅雨营造出花街独有的暧昧情调,这为正值青春期的“我”遇到清冷神秘的高棉提供了环境衬托,“花街在阴雨天显得更幽深。青石板路面放出闪亮的青光,雨水一处处汪着,雨点击打路面的声音在两边的高墙间回旋。潮湿的青苔爬满半墙”[8]。少年满怀憧憬,在细雨中不断寻觅与徘徊,与高棉生硬晦涩地搭讪,得到的却是一场破碎的梦:“有一天夜里做夢,梦里也下雨。满天地都是雨,好像有人告诉我那就是悲伤欲绝的小雨。”[8]徐则臣用细腻婉转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故事,描写了少年单恋的开始与结束、成长中的希冀与疼痛,并描绘出一幅神秘的故乡图,将故事的真相与不为人知的秘密埋藏在江南梅雨中,这精致古典的写作手法如戴望舒的《雨巷》,朦胧氤氲之美扑面而来。
二、古朴厚重的小镇风俗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优秀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原乡风俗作为多元文化中特定地域的精神结晶,反映了民族历史文化沉淀、彰显了地域人文情怀、展现了小镇风土人情。风俗与人情是和谐一致的,它们是地域人民或淳朴厚重、或热辣奔放的天性的外在写照。
1.平乐镇的川味习俗
巴蜀大地孕育了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被颜歌收进《我们家》的文本构建中。对颜歌而言,写平乐镇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心理抚慰,她曾在采访中说,之所以热衷写小镇是因为“非常怀念过去的日子,懷念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光”。因此,颜歌对平乐镇的叙述是希望以此记录在这个四川小镇度过的岁月。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过:“语言写到生时, 才会有味, 语言要流畅, 但不能‘熟。援笔即来, 就会是‘大陆话。”[9]颜歌用一种“贴近地表”的语言来言说真实,将书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市井化,多用四川话来描写人物内心世界,放弃了虚构故事的野心,彰显了生活本来的面目。她擅长使用“不好看?钟师忠你再给老子说一句!我薛胜强啥时候睡过不好看的女人”[10]此类原汁原味的川味对话,再加上“平头菊花提虚劲,癞子光头最亡命”等一系列四川俗语,她的语言没有扭捏含蓄,没有遮掩羞涩,像四川海椒面、辣火锅一样热辣滚烫,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巴蜀味道。与此同时,食物描写也是彰显地域特色的方式。“他就站起来给他们拌兔丁,空出手来把花生、大头菜、芹菜、芝麻、花椒面、白糖、醋,还有那抓心烧肺的兔丁都丢到那个大铝盆里面去,哐哐哐哐,手起筷子落地拌完了。”[10]一道具有四川特色的麻辣兔丁就呈现在读者面前。她还在小说里提到了邱鸭子、红糖锅盔、七仙桥的肥肠粉等四川小吃,也令读者垂涎欲滴、口齿生津。这些川味符号,再现了作者在四川小镇的成长体验,不仅表现了平乐镇独特的地域文化,更表现出颜歌对巴蜀大地的深切热爱,由此纪念一去不复返的儿时光景和岁月记忆。
2.涔水镇的湘味习俗
在艾玛的情感世界里,不乏对故乡的赞美,她用深情真挚的叙事语言将涔水镇的家长里短、衣食住行、丧葬嫁娶、生老病死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路上的涔水镇》中,作者这样写道:“仿佛涔水镇也像我一样, 长了两条腿, 多年来一直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疾步前行, 动不动就会与我不期而遇。”[11]涔水镇的故事,都源自艾玛内心深处最浓郁的乡愁。
小镇人保留了祭天地、拜神佛的传统。比如《小强的六月天》中,艾玛详细叙述了家乡的祭祀仪式。在别的地方,人们都以只称农历七月十四这天为“鬼节”,而涔水镇的人民则大大方方地将之作为一个节日来过。白天,家家院子里都在逮鸡杀猪,到了晚上镇里变得静悄悄的,祭奠的重要环节便来了:先是“请”,人们在院子里的大树下焚烧香烛纸钱;接着是“叫”,他们嘴里念叨着逝去亲人的名字,以防鬼魂找不到自家的门;最后是念经,“死时见血带着凶的,驱邪镇魔的《金刚经》是一定要念的,这样活着的人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活”[12]。就像沈从文所言:“一切生活都混合迷信与经验,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到的进步,无迷信掺杂,便不容易接受。”[13]小镇东边的山头、西边的墙角、碗筷的摆放、说话的语术都能牵连出一段历史故事,甚至一粥一饭也具有浓郁的文化意味,或许这才是小镇最具魅力的地方。
三、邻里相依的小镇风情
都市里,人与人之间距离感明显,但在小镇上,邻里朋友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处境艰难时共渡难关,偶尔的矛盾摩擦也无法泯灭他们之间情感的自然凝聚,因此,小镇叙事中不乏对纯真自然的人情之美的的描绘。
1.泥河镇的邻里之情
杨袭在泥河镇叙事里常描绘邻里之间相互扶持的小镇风情。《泥河调》中,每当有客人到来时,悦来客栈的老板谷米都会赠予客人一个布鸡,还有一碗冒着热气的米汤和一碟自己腌制的爽口咸菜,美味的食物可以帮助客人除去奔波的疲惫。《风过泥河》中,媳妇小唐与毛三吵架后离家出走,周围邻居们知情后丝毫不敢怠慢,为了找到小唐,他们“沿着出泥河的大道小路,追到周边的所有乡镇,追到县里,追到集市”[14],有人甚至发着高烧追到省里,在汽车站蹲点蹲了两晚,回来时“满脸的燎泡”。《三声蛙鸣》中,年迈的护坝人老邱每年秋天都去河滩里收割蒲草,用镰刀将草叶割下,灵巧地编织成草席,不求回报地送给不常见面的老朋友或常在他屋前落脚的旧相邻,因为在老邱看来,即便是稍稍在他屋前歇息或是搭话问路的陌生人也是“有缘人”,都应热情款待;即便怀有身孕,绣春依旧乐于助人,挺着大肚子并不轻松地穿过大半个小镇,她不顾世俗的目光,每年都准时给老邱缝补棉衣为过冬作准备。“邻里之情固然是乡民们维系亲切质朴又温馨绵长的情感的重要基石,但这种情感在青年乡民之间,也许是需要用更具有时代气息的友情表达更为恰切。”[15]《八三年》中,被青春期的生理问题严重困扰的李广州碰上了张江苏,张江苏是“街面上”的“贵族”,而李广州则是“胡同里”的“土鳖”,张江苏向他解释了“青春期”这一神秘的人生阶段,从来没有交集的两位少年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好友。他们表达友谊的方式就是去南湾浮水,在静谧的南湾里,李广州还得知张江苏的姥爷喜欢喝荷叶茶,这让一向懒惰的李广州勤快起来——他要为张江苏的姥爷晒满好几床荷叶茶。可笑的是,采集了许久的荷叶竟然是没用的花骨朵儿,愤怒的李广州没有勇气面对张江苏,躲了他好些天,而谁曾想同样对友谊无比渴望的张江苏为了将一罐上好的莲花茶赠予李广州,竟也在花丛里躲了两个小时,还被蚊子叮了满身包。在“泥河系列”中,杨袭以厚重的乡土情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幸福安稳的小镇图景,烘托出泥河镇特有的温馨氛围,凸显出小镇人的乐善好施的美好情谊。
2.香树街的邻里之情
在宗利华的短篇小说《放爆仗》中,小鱼儿与胖嫂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行为是对邻里之情的最好诠释。在中国的小镇中,胖嫂的形象并不少见:她话痨、抠门、爱八卦,但也勤快、节约、踏实、体贴。小鱼儿与胖嫂相识是因为胖嫂的丈夫,也就是小鱼儿的远房表哥大胡子,“那不是我哥,是表哥,八竿子才打得着的表哥,在我们那个村,这样的表哥数不胜数”[16]。在家里,上有姐姐们,下有一个宝贝弟弟,爹不疼妈不爱的小鱼儿在表哥家得到了比自己家还充足的爱。她们一起来到香树街,相互扶持相互帮衬,即便没有血缘关系,小鱼儿与胖嫂也胜似亲姐妹。小鱼儿与老公闹离婚,胖嫂安慰她:“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满街跑。”[16]离婚后的小鱼被自己老板骚扰,幸亏胖嫂举着杀鱼刀及时出现,这才避免了一桩惨案。因为得罪了老板,小鱼儿毫不意外地失去了工作,走投无路之时,“她又往前走了几步,才发现,是朝着胖嫂的火锅鱼店的方向去的”“见到胖嫂,心里总算稍稍舒服点”[16]。当然,她们的关系并不是胖嫂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两人互相的扶持。小鱼儿发现自己的表哥与街对面的风尘女子小柔产生了暧昧的苗头,于是暗地里与小柔较量,而小柔又是香树街的混混头子马三儿的追求对象,小鱼儿因此还得罪了马三儿。在香树街,人人都对臭名昭著的马三儿避之不及,而即便是为自己报仇,胖嫂也强烈反对小鱼儿这样做,还像家人般教训她:“小鱼啊小鱼,早晚有你吃亏的那天!”[16]香树街中胖嫂与小鱼儿之间筑起的那座坚实的友谊桥梁,可以看作是作者向淳朴的乡村情感的回望与致敬。
四、结语
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本就具有探求“我之所以成为我”的潜意识。这种意识总是牵动作家最敏感的情思,因此,“故鄉情结”成为当代文坛避不开的主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徐则臣、魏微、艾玛、杨袭等新一代作家,他们在小城镇长大,却居住于城市,远离“灵魂栖息地”的思乡之情使作家们用那些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小镇做基点,用文字构建自己的理想王国,展示了21世纪小镇人民的生活图景和精神面貌的同时,完成了心理上的文化皈依。在当代文坛,不少乡土作家都继承了五四时期“为人生”的写作传统,心中怀天下,笔下有苍生,力图摆脱精神上的漂泊性、虚幻性和紊乱性,用扎实绵密的文字对小镇进行见微知著的描写,以慈悲与温情审视着小镇背后的故乡的影子,从而获得精神归属、灵魂安顿以及文化认同,最终完成心理上血脉的精神回归。
五四时期,鲁迅、彭家煌、王鲁彦等作家树立起乡土文学的旗帜,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叙事模式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结构框架。而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之头,城之尾”的小镇,容纳了大量的人口,受到了文坛的密切关注,成为一方新的文学空间。小镇的风光、风俗与小镇人民的生活景象的交融使得小镇叙事成为极有意义的文学样本,文学原乡逐渐向小镇位移,小说中的小镇图景也成为传统生存样态的最终影像。可以预想,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小镇将为当代文坛提供更丰富的话语资源,小镇叙事也将呈现出更深厚和纯粹的文学质地,承载更多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 孙犁.陋巷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2]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魏微.姐姐和弟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4] 王秀梅.血红雪白[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5] 王秀梅.致敬,我的十年[N].烟台晚报,2011-11-02(A33).
[6] 李徽昭,徐则臣.运河、花街,以及地方文学[J].创作与评论,2015(8).
[7] 李超.临水的花街:徐则臣小说创作的精神“故乡”[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4).
[8] 徐则臣.梅雨[J].西部,2007(8).
[9] 高万云.汪曾祺的文学语言研究[J].焦作大学学报,2006(2).
[10] 颜歌.我们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11] 艾玛.路上的涔水镇[J].黄河文学,2010(1).
[12] 艾玛.浮生记[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13] 刘荣华.重建人心秩序:沈从文的叙事伦理研究[J].学术论坛,2013(4).
[14] 杨袭.风过泥河[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
[15] 王晓梦.论杨袭“泥河系列”小说的人性书写[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16] 宗利华.香树街[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宗小琰,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2021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1CZWJ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