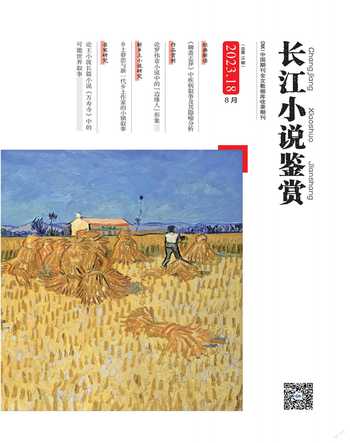镜像与想象
2023-12-20洪雪宜
[摘 要] 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的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以刻画美国边缘族群对主流社会的抗争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而备受关注。小说分别塑造了三个华人形象,生活于美国底层的草根杨先生、与白人争夺孩子的贝比和二代移民美玲。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这三个华人形象,进而分析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产生这类人物形象的政治文化原因。由此可见,这三个华人形象不同于美国白人文学中的华人形象,而是伍绮诗本人的现实投射与其想象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 《小小小小的火》 伍绮诗 形象学 华人形象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8-0047-04
一、引言
伍绮诗(Celeste Ng)是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她曾在报纸和文学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短篇小说,出版了两篇畅销小说《小小小小的火》(Little Fires Everywhere)和《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作为出生于美国的二代移民,伍绮诗从小接受着美国的文化熏陶,虽然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却不能同初代移民那样,坦然接受中国人的身份。她曾在采访中直言自己不会说中文,是亚裔文化的局外人。正是因为她是亚裔文化的边缘式人物,她在刻画美国华裔身份形象时能够采取不同于其他华裔作家的独特视角,更多讨论少数族裔在美国遇到的种族身份和社会融入问题,不再拘泥于华裔群体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华裔群体的问题。
有别于以华裔为主角的传统亚裔文学,《小小小小的火》描写了居住在保守社区西克尔高地的白人理查森一家与大胆无畏的艺术家米娅和她的女儿之间的故事,再现了边缘人物对主流群体的挑战和抗争。《小小小小的火》虽不是以在美华人的故事为主线,但是小说中却多次出现华人的身影,他们穿插起故事情节,呼应关注少数群体的主题。近年来,对华人形象的研究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新内容,孟华教授提出“自塑形象”这个概念,用以代指华裔或华人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塑造出的华人形象。而要成为“自塑形象”,需要满足的条件是:“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华人为描写对象。这些形象具有超越国界、文化的意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异国形象,至少也可被视作是具有某些‘异国因素的形象,理应纳入形象学研究的范畴中来。” [1]因此,分析华裔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对于研究小说内核具有重要价值,而用形象学的方法研究华人用英文创作的作品,有利于对比中西文化的差异,揭示华裔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冲突问题。目前中国学者对《小小小小的火》中的华人形象研究并不多,本文将运用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对作品中所出现的三个华人杨先生、贝比和她的女儿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作者的写作背景,分析冲突背后的政治文化原因。
二、杨先生:异乡的奋斗者
杨先生的初次登场是在理查德森太太的回忆中,他是一个孤身来到美国的异乡人,“英文讲得磕磕巴巴,口音浓重”[2],搬家前因为收入微薄住在房租低廉的旧房中。理查德森太太认为,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杨先生“永远无法住进这样的好社区”[2],只能在“偏远的巴克艾路找一处不起眼的灰色公寓,或者(更有可能)去东克利夫兰的那片绿化不足的三角地碰运气——那里经常被误认为唐人街,房租异常低廉,被遗弃的旧房子随处可见,警笛每晚至少会响一次。”[2]杨先生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米娅母女离开时,他为两位邻居的离开表示伤心,并祝愿他们一路平安。虽然小说中杨先生出现的次数很少,涉及杨先生的字数寥寥,但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华裔草根人物,他品性善良、工作勤奋,其形象更贴近于随着移民潮来到美国工作的一代移民。因为“语言障碍、社会政治原因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他们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地位低下,不被重视,默默无闻,但是生命力顽强。”[3]杨先生虽没住在唐人街,但与第一代移民一样,由于在美国举目无亲,英语说得也不流利,只能在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从事司机和打杂的工作,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民。
伍绮诗的父母都是科学家,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来自香港的移民二代,家境优渥的她自然没有体验过杨先生的生活,所以杨先生这样一个小人物并非伍绮诗本人在书中的映射。作者塑造杨先生这类华人形象,一方面,是受到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初代移民的话语影响,从他们的口中,伍绮诗了解了初代移民在美国的生存困境,“对于老移民的后人而言,‘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空洞的地理名词,是想象的文化符号,但又不是一种向壁虚构。”[3] 伍绮诗通过杨先生这个角色重塑想象中的中国,再现了父辈记忆。华裔作家重塑祖先历史,“一方面在美国历史的空白处寻找被湮没的英雄,另一方面不断建构新的华裔英雄,构筑祖先在美国创业的历史,证明华裔生活在美国的合理性。”[3] 另一方面,杨先生是她在日常生活中以美国人身份审视在美华人生存现状后的投射。伍绮诗并未采用汉语书写文本,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偏向美国化,看待中国的角度受到了居住地对中国的集体想象的影响。美国对在美华人及华人社区,如唐人街,常带着种种偏见和刻板印象,而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学作品对这种刻板印象的加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再现反映,文学表征着空间、生产着空间,文学直接参与了社会性、历史性与人文性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与价值的内涵。”[4]学者萨义德(E. W. Said)提出,“建构他者的策略基本上依靠文本”[5]。美国作家将华裔群體定义为他者,操控文本使华裔与美国人区别开,因而早期美国作家所描述的唐人街多是罪恶和贫穷的收纳所。而“在第二代华裔作家的笔下,唐人街失去了水仙花、林语堂笔下那种和谐愉悦的氛围,而经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社区狭小逼仄,封闭压抑……”[6]在美国集体想象和二代华裔作家的写作惯性的驱使下,伍绮诗创造出杨先生这样一个人物也不足为奇。
对于华裔作家而言,“中国既是形象塑造者的‘故国,同时也是作为塑造对象的‘异国”[7]而与其他的异国形象刻画不同的地方在于,在美的华裔作家们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异国形象,因为它并非来自完全陌生的一方的表述,而是在另一种文化的参照之下对本族文化的回望和审视。”[8]伍绮诗刻画的在美华人,一方面重构其祖先历史,追溯其身份渊源,构建起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她也糅合了他国的文化对中国的想象和建构,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具有“他者”性的华人形象。
三、贝比:沉默无助的母亲
虽然贝比·周与杨先生一样是初代移民,但不同的是,贝比不仅是一个在美的工作者,更是一个母亲,她还要面临孩子的抚养问题,而她与美国白人麦卡洛夫妇对自己孩子美玲的争夺,也成了小说的高潮。贝比在两年前从广州来美国,说着蹩脚的英文,在餐厅干着服务员的工作。她与一个中国男人生下美玲后惨遭抛弃,不得不独自抚养女儿。然而贫穷让她和孩子难以维持生活,在绝望之下,她选择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了消防局的门前,而正是这一行为使她丧失了孩子的抚养权,从而引发后续与麦卡洛一家对女儿美玲的争夺。
“中国早期的移民妇女经常面临着生活的艰苦、当地白人对其的敌意与鄙夷,因而每天都处于惊恐不安之中。”[9]贝比的处境与早期中国移民妇女的遭遇相似,作为一个非法移民,她从事廉价的工作,在白人至上的社会艰难生存。在争夺孩子抚养權的过程中,她孤立无援,而她的对手麦卡洛夫人不仅获取了她的白人朋友理查德森太太的援助,还掌握当地新闻媒体的话语权。她的败诉成为必然,最终只能采取“偷孩子”的下策让孩子重回自己身边。美国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本地人对于来美的有色族裔的歧视根深蒂固,“那些没有携带人文和金融资本的移民族群生存在较低的社会和经济层面中,同时歧视也阻止他们获得资源。”[10]歧视让一些原本就在语言和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少数族裔成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被剥夺话语权的边缘人。当他们与白人争夺资源时,自然是争不过的。
此外,贝比的母亲身份也是值得讨论的地方,“母亲的定义是什么?是血缘关系还是爱决定母亲的身份?”[2]在“在美国华裔女性小说发展历程中,对‘女性关系的关注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传统,并被很好地保留下来。”[11]早期的华裔女作家善于通过描写母女矛盾来再现母亲的故事,以消解母亲在男权社会和华裔男性作家笔下被赋予的“他者”形象。同时,描写华裔母女的矛盾也是华裔女作家借以探讨中西文化冲突的方法,正如华裔文学研究学者蒲若茜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女性而言,其精神传承或冲突的背后实质上是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形象就是华族文化的隐喻,而女儿则是美国文化的缩影”[12]。然而,伍绮诗在传承这种写作传统的同时也深化了这一主题,她不再受限于探讨华裔母女的矛盾关系,她提出了对母亲的选择问题,这个决定了出生于美国的少数族裔后代的归属。选择白人母亲还是黄种人生母,意味着小孩是否会与华裔文化完全脱离。而在小说的结尾,贝比在晚上趁麦卡洛夫妇睡着的时候,偷偷带走孩子并逃回中国,麦卡洛太太认为孩子在被抱走时觉得安全而并未哭闹,这一情节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情感倾向,即母亲并不能与孩子完全割裂,华裔后代始终需要与他的出身文化相连接。
通过刻画华人女性贝比的形象,伍绮诗重现了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即底层女性权利的缺失、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以及对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的排他性。同时,她也传承了历代华裔女性作家对母女关系的写作传统,在作品中进一步细化其文化内涵。
四、美玲:双重身份的背负者
美玲是二代华裔的象征,她由中国人所生,却被美国夫妇所收养,围绕在她身上的文化选择与困境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华裔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被不能生育的白人夫妇收养后,美玲被赋予了英文名字米拉贝尔(Mirabelle),中英文的称呼彰显出她身份的双重性。美玲的归属是文中着重笔墨刻画的部分,在贝比养育权的争夺官司中被提出的种种问题也是探讨中西的冲突与融合问题的关键。
作者研究构成了形象学研究的关键要素之一,这是由于作为文本人物的塑造者,作者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以及他和本国或他国的接触体验与情感倾向,都会直接反映到其作品中。既拥有中国人血脉,又被美国白人麦卡洛夫妇所抚养的美玲与伍绮诗本人有一定的相似性,小说所反映的贝比的身份认同问题正是伍绮诗现实困顿的投射。杨乃桥认为,在海外的华裔作家有两种可能的文化身份,其一是移居国外,其二是从小就在国外生活,他们虽受到了国外的文化影响,但在血液他们仍是中国人[3]。伍绮诗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香港移民家庭,中国对她而言是陌生的。美国华人“在新的环境中能够吸收多少文化,这取决于他们出生和居住的条件,及年龄和个人的经历。”[13]部分出生于美国的二代移民自小受到美国的教育,说的是英语,他们难以在居住的国家里找到中国的真实痕迹,无法把中国与故乡等同起来,自然难以产生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就与美玲抚养权官司上有人所提出的现状一样,美国商场没有售卖黑发黄皮肤的娃娃,多的是金发碧眼的芭比;没有真正刻画中国人的书,书中只有一些“带着苦力的那种帽子”“眼尾向上斜”[2]的中国人形象。这种不经意间的文化灌输让部分二代华裔抗拒中国人的身份,潜移默化中与自己出身的文化逐渐脱离。
在美国教育与社会等因素的作用下,二代移民更容易从心理上认同自己美国人的身份。然而,外貌上的中国特征还是令他们难以真正被美国社会接纳。华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陈素贞(Sucheng Chan)指出,亚裔美国人因其肤色的原因,成为无法被美国社会所接纳的“永远的外国人”[14]。与从中国前往异乡的初代移民不同,他们对于中国没有故乡概念,他们更希望自己能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美国学者马库斯·李·汉森在其文章中就指出,二代移民想要忘掉和故国相关的一切,包括“他讲英语时的外国口音;仍不时让人回忆起童年艰苦的家庭宗教信仰,甚至那本该是最愉快的家庭生活习俗。”[15]
伍绮诗借贝比这个双重身份拥有者的角色,来揭示在美国社会中包括她自己在内的移民后代所面临的文化和身份困境。在美国社会中的华人始终处于两种文化的对抗中,血统赋予他们的外貌特征与美国社会环境带给他们的文化认同,使他们时常陷入对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困惑和迷茫之中,中国血统与美国社会所构成的双重身份迫使他们不得不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面对失衡的危险。
五、结语
作为新生代的华裔女作家,伍绮诗在创作时不再以华裔家庭为主线,关注的也并非使命感强烈的种族、政治等严肃话题。然而,她凭借自我审视和故国想象塑造出的华人形象,却表明她并未与中国文化完全割裂。相反,刻画在美国的华裔小人物形象,揭示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实际也是反映作者本人的现实境况。另一方面,伍绮诗对华裔生活的再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反思。塑造各类美国华裔的形象,也是通过揭露他们遭遇的文化困境来寻求中西文化和解的方法,为构筑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而做出嘗试。分析华裔作家所刻画的华人形象,能够促进美国社会关注和了解少数群体,有利于中西民族间的互相了解与沟通,消除歧视和刻板印象。
通过分析文本所刻画的华人形象,以此来揭示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所隐现的权利关系,也可以借助海外华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美国华人作家凭借语言功底与地理优势,在向国外读者展示中国文化、塑造华人形象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中国已屹立于世界东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华人文学对华人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也反映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构建。我们期待华人作家笔下的中国能够跳出西方的刻板印象,借助文学窗口向西方呈现出中国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新形象。
参考文献
[1]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Ng Celeste.Little Fires Everywhere[M]. New York:Penguin Press, 2017.
[3] 杨华.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济南:山东大学,2012.
[4] 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 D Cavallaro.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hematic Variations[M]. London and New Brunswick,NJ:The Athlone Press,2001.
[6] 蔡晓惠.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D]. 天津:南开大学,2014.
[7] 唐海东,邬晓丽.异域情调·故国想象·原乡记忆——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三种中国形象及其批评[J].中国比较文学,2008(4).
[8] 詹乔.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D]. 广州:暨南大学,2007.
[9] 令狐萍.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11] 董美含.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11.
[12] 蒲若茜,饶芃子.华裔美国女性的母性谱系追寻与身份建构悖论[J].外国文学评论,2006(4).
[13] 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4] Sucheng Chan.Asian American: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M]. Boston:Twayne,1991.
[15] 尹晓煌. 美国华裔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特约编辑 孙丽娜)
作者简介:洪雪宜,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