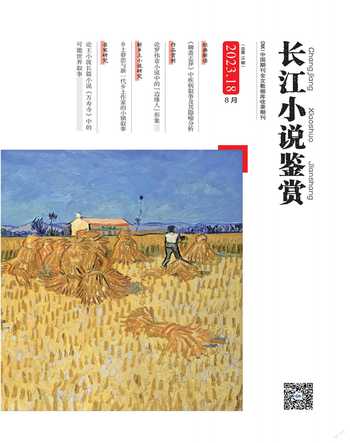人物亚审丑视域下南高小说《志飘》的美学意义
2023-12-20梁珊珊
[摘 要] 《志飘》是越南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南高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农村题材小说,也是越南现当代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志飘》通过刻画武代村既具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的若干人物的丑态以及发生的丑事,揭示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现象,以小见大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黑暗,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本文从人物亚审丑角度出发,分析了“丑”在武代村的几个典型人物身上的张力,并探析南高的创作审丑意识,进一步发掘《志飘》所具有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 《志飘》 南高 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8-0025-08
一、引言
南高是越南现代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2部长篇小说及60余篇中、短篇小说。南高的作品“并未集中笔锋直指封建主、殖民者的压迫,反映物质生活的贫穷苦难,而是瞄准了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忧愁,特别集中笔墨追求美好人性、人品,活着有价值的强烈渴望”[1],这为1930—1945年的越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贡献了独特的视角。因此,他的作品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视作衡量越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尺子。越南学者何文德在研究越南现当代文学时曾认为南高“在1930年至1945年批判现实文学潮流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曾直言:“开发这一现实荒地的人流中,南高像晚开的花朵,可皎洁无瑕、芬芳馥郁。”[2]越南学者风黎在其书《南高文学事业》中也写道:“南高是一个出色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3]。作为越南现实主义文学(1940—1945年)的杰出作家、越南新文学建设的先驱者,南高具有明确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凭借这些成就,南高于1996年被追授越南国家最高奖——胡志明文学艺术奖。
本文选取南高的中篇小说《志飘》为研究对象。付梓于1941年的《志飘》,是南高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农民题材作品,这部小说的发表确立了南高在越南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小说以主人公志飘的视角展开叙述,志飘是个弃婴,辗转于多个家庭,吃着百家饭长大;他20岁的时候在时任里长的百户建家做长工,却惨遭诬陷而含冤入狱,出狱回村后敲诈勒索、欺压乡邻、酗酒滋事、甘心给百户建做走狗,成为一个村民们避之不及的撒泼耍赖的恶霸。直到氏娜的出现,40岁的他被善良的人性和真诚的爱情所打动,内心尘封已久的良知被唤醒,他开始渴望与人为善并憧憬美好未来,但他与氏娜的爱情遭到了氏娜姑妈的反对而被迫结束,绝望的志飘刺杀罪魁祸首百户建,随后自杀以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小说通过刻画典型人物志飘的个人经历,反映了越南广大穷苦农民在旧社会制度中悲惨的遭遇,凸显了南高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与当时反动势力作斗争寻找出路的现代文学中,南高的《志飘》是最突出的、最深刻的”[4]。不论是将南高的《志飘》置于越南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纵坐标,还是将其置于与中国同类题材小说相互平行的横坐标上,《志飘》都不失为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从近年来的学界研究以及评论界的反应来看,国内学者对南高及其小说《志飘》的关注度不够。而在越南,虽然《志飘》极大激发了评论者的阐释冲动,学者、评论者纷纷从叙事艺术、救赎主题、悲剧美学、影视创作等多种研究视角对《志飘》加以充分的关注,这似乎也说明它的审美意义还有许多内容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在已有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被隐藏的论述空间,比如小说中涉及的美学问题及其相应的人物形象内涵,而这些问题又直接关系着小说文本呈现出来的张力,以及小说背后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对于这样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研究者需要以哲理性及美学的眼光去透视小说复杂的内容和藝术形式,挖掘作者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时的深层意图。本文拟从人物亚审丑角度出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探析《志飘》的审美价值,以期指引更多的读者进入新的《志飘》世界。
二、丑学发展历程及亚审丑的界定
何为“丑”?在古希腊美学思想中,一切的“不和谐”都是“丑”;中世纪,在神学的影响下,人们将与神性相悖的观念定义为“丑”;而在早期传统美学家的眼里,“丑”不具有其本体价值,“丑”之所以存在,不过是为了衬托美、完善美、认知美。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以及中世纪封建专制、教会神学的没落,“相对美”逐渐取代“绝对美”的观念,“丑”的存在及其作用才开始慢慢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让哲学家们在美丑问题上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1750年鲍姆嘉滕创立了专门研究人类感性认识的新学科——感性学。鲍姆嘉滕明确提出:“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就是美;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5]。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推波助澜下,“丑”学率先在文学领域盛行,美的垄断地位被歌德和雨果等文学家打破了;在艺术领域,过去流行的夸张美以及理想美也随着现实主义画派的出现而走下神坛,渐渐形成了一种“美丑共赏”格局。可以说,在近代社会以前,对丑的研究都是依附于美学之上的。直到1853年罗森·克兰兹发表《丑的美学》,才使得丑学得以独立并被人们所认知,“丑作为美的否定,必须是崇高的积极的倒错,必须是悦人的积极的倒错,必须是单纯的美的积极的倒错”[6],因此罗森也被认为是现代丑学之父。
对于“审丑”,有人视其为“审美疲劳”的产物,也有人认为“审丑”本身是审美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总而言之,“丑”是相对于“美”而言的。谈及“亚审丑”,借用孙绍振的“亚审丑”概念,即在美学领域,“丑”不“丑”无所谓,只有无情才是“丑”,外物的“丑”所带来的感觉,如果还是强烈的、浪漫的,那还算是审美[7]。审丑和对象的关系并不太大,不管对象是美是丑,只要带来强烈、丰富、独特的感情,这个过程就仍然是审美的,因为英语的aesthetics,即美学,讲的本来就是和理性相对的情感和感觉学。欣赏具有不怕丑的倾向且还包含感情的文学作品,不能一言概之为“审丑”,它只是接近于审丑,应该就叫作“亚审丑”[7]。因此,笔者认为“亚审丑”不完全是审丑,而是处于一种非美非丑、是美又是丑的状态,诚如恩格斯所言:“辩证法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相互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方互为中介。”[8]所以亚审丑是一种“非此即彼”又“亦此亦彼”的复杂审美活动,任何一个事物的实际存在都是十分模糊和不确定的[9]。对于审美主体而言,杂糅的丑有时候比单纯的美更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以及深刻的感悟,其美学意义便由此产生。
三、武代村众生相的亚审丑特征及表现
小说《志飘》以善与恶、美与丑、理智与疯狂,甚至是人性与非人性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起小说风格和叙事空间,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不仅体现在小说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写实主义的美学架构上,还体现在小说故事细节和人物形象设计上。但站在整个亚审丑场域的视角之上,我们会发现小说的核心是“丑”,有物理意义上的“丑”,也有人性的“丑”、社会阴暗面的“丑”,这种“丑”是不同程度的“丑”,是复杂的“丑”。而“丑比美深刻。美直接取悦感官,取得快感与愉悦,美停留在感性,拒绝超越感性,所以,美是肤浅的。丑则刺痛感官,引起思考,在痛苦与厌恶的交织中获得精神的真实”[10]。换言之,武代村这些丑人的丑态丑事包含着一种呈现时代特色的复杂性张力,表现形式为人与人以及人与时代之间的多重矛盾冲突,彼时现实社会的总体诉求、限度、症结及其历史根源也在这些矛盾中得以呈现。因而,一个个美学意义层面的丑人形象在矛盾冲突中逐渐浮现出来并成为典型人物。
1.百建户:悲剧始作俑者
在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肖像描写上,除了百户建,作者对其他人物的描写或多或少地提及他们容貌的美或丑。虽然小说对百户建的面容进行了模糊书写,但随着故事的发展,百户建丑的形迹越发清晰,丑的矛头尖锐地指向了他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武代村,百户建善于勾结各股势力,收编亡命之徒,使唤他们“放火烧屋或者捅几刀子”“扔个酒瓶或者上门寻衅然后撒泼骂街”,去祸害所有不顺从自己的人,因为“无论结果怎样他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11];三姨太明目张胆地勾引年轻力壮的志飘,但百户建也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男人,所以转而去陷害志飘,将其投入大牢以泄私愤。百户建还假公济私,暗中操作把敢跟他叫板的眼中钉年寿投进了大牢;他甚至利用税收之机中饱私囊,残酷镇压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温顺的村民只能咬紧牙关供养以百户建为代表的乡绅土豪。此外,在人的种种欲望中,最强烈的是性欲和食欲[12],值得玩味的是,年老孱弱的百户建在临死前还处在浮想联翩的性幻想中,过激的性欲让他恨不得把那些和四姨太开玩笑逗趣的年轻人投进大牢,“万恶淫为首”的性欲便是隐藏在他内心的一种恶,同时也让他罪上加罪。
贪婪狡诈的品行使得百户建成为作家鞭挞和讽刺的首要对象,而百户建软硬兼施、口蜜腹剑的惯用伎俩则让人们痛恨至极。百户建作为掌管一方的乡长,作威作福,村民无不惧怕他。村民聚众围观志飘上门闹事的时候,他先是板着脸训斥了姨太太:“你们几个回屋去,妇道人家就会胡说八道,懂什么!”[11]转而又以轻柔的语调劝说村民道:“各位父老乡亲,都回了吧!区区小事,没什么好看的!”[11]这种红白脸策略尽显百户建的虚伪,从小说对百户建的语言描写来看,这并非个例。面对志飘酒后闹事,百户建心里自是咬牙切齿的,但念及自己的头衔和名声,他只好一边和颜悦色地拉拢着志飘进屋喝茶,劝其有事好好说,另一边则对儿子阿强使眼色,佯装“斥道:‘阿强呢!看你这该死的家伙干的好事!还不赶紧叫人烧水喝茶!”[11]在面对兵职怒目圆睁地质问他当兵时的汇款去向时,百户建连忙接话道:“您手头紧跟我说一声就是了。既然那笔钱都被你老婆花光了,那就算杀了她也是拿不回来的了,何苦这么折腾自己找罪受呢?”[11]借此掩盖自己私吞兵职钱粮汇款的真相,然后哄骗兵职心甘情愿地当他的爪牙。在志飘上门找百户建讨要说法时,百户建先是掏出钱扔地上让志飘“拿上赶紧滚,让老子清净下,你自己不养活自己,还指望别人一直养活你不成?”[11]看到志飘怒目圆睁似要发作之际,他态度又软下来,而当“志飘掷地有声地说‘老子想做个善良的人”[11]时,百户建又以毫不在乎的大笑回应,讽刺志飘性情大变可谓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11],在他眼里倘若志飘都能与人为善,那天底下就没有坏人了。他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以及他对志飘的蔑视遭到“现世报”,他的丑恶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他的恶剥夺了村民的话语权,他的恶是兵职和志飘异化的催化剂。从亚审丑角度来说,他丑的一面是恶,而这一面可以激起读者丰富情感,所以他的亚审丑意义体现于此。
2.志飘:亦丑亦善亦真
从小说对志飘的人物塑造来看,志飘并非概念化的扁平人物,他的形象鲜活且丰满,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处在动态和矛盾性的张力之中,所以他的丑不是绝对的,他的丑是引人深思的。尽管小说以志飘的“谩骂”和心理活动开头,精心设置了志飘的首次出场方式,对志飘的“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描写,激发读者的特别关注,并顺应读者“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势,给读者勾画志飘的“轮廓”添了几个关键词,即喝酒,骂人,身世成谜。而从视觉上的外貌描写来看,作者也尽量把志飘往牛鬼蛇神般的恶人形象上靠,“脑袋剃得光溜溜,牙齿被刮得白晃晃,黝黑的面庞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双眼目露凶光真是吓人!他穿着黑粗丝布裤,上身披着件土黄西装,装敞着胸膛,满身满手都是龙、凤、手持尖锥的阎罗文身”[11]。平日里的志飘将撒泼无赖进行到底,恐吓酒肆老妇要酒喝,喝完酒便骂人,拿刀威胁百户建把自己送回牢里,但最后却“不慌不忙地削起了格木桌的边”[11],他撞墙、割脸、打打杀杀,以至于“脸上沟壑纵横,交错着数不清到底多少条疤——这些一次又一次寻衅骂街时酒瓶碎片留下的痕迹”[11],而身体的残虐,暴力的宣泄,实则是美学上的反转和逃脱。之后在百户建的诱导下,他一步步沦为百户建的爪牙,做了多少欺凌、打砸、厮杀、迫害村民的事情,身边的人对他避之不及。客观而言,他对氏娜的感情由来也不过是跨过了道德底线的性冲动。由此,志飘是丑且恶的,但这并非他的底色。
人物性格是对立统一的,是矛盾的有机体。人物性格并非凝固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正、反因素可以互相转化[11]。志飘这一角色纠结了复杂的善与恶的内在矛盾,志飘既有无赖撒泼、作恶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被裹藏在恶之下单纯善良、渴望被爱的一面。志飘在二十岁初到百户建家做长工的时候,经常被三姨太以捏腿为由,使唤他做有悖于伦理道德之事,他是“嗤之以鼻的”[11],“他觉得耻辱多过欢喜,何况还惴惴不安”[11];他也曾“憧憬过有个小小的家,丈夫租地耕种,妻子在家织布,两人再买头猪来养作为本钱,过得好还能买个三五分地来耕种”[11],希望过这样简单而美好的男耕女织生活。由此,不难以看出他正直善良且纯情的一面。他酒后跑到百户建家闹事,围观群众散去后,他“内心固有的、来自久远过往的恐惧有所苏醒”“无党无朋、无亲戚无、无兄无弟,甚至无父无母”[11]的他表面上无畏无惧,心里实则是不断自我否定又肯定的波涛汹涌。他开始借酒麻痹自己,“他醉着吃饭,醉着睡觉,又醉着起床,醉着撞墙划脸,骂骂咧咧,威胁恫吓”[11],他不愿醒来,不愿清醒地知道自己已成为村里欺凌众生的恶霸,他的恶行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他只能选择在丑的刺激中短暂地忘却“沉重的肉身”于人世的苦难和蹉跎,他是弱小无助又无奈的。他亦醉也亦醒,在黑夜里,他看着“只围着自己脚底打转”“时而缩短时而又拉长,被分割成好几块”[11]轻飘飘的影子而“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不起腰来”[11],一个平平无奇的影子也能让他如此开心,以至于忘记了报仇。或许对他而言,对他不离不弃的也只有这影子了,而影子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他呢?现实中矛盾而分裂的他和被黑夜分割成好几块的影子冥冥中存在相通之处,所以他的笑是单纯的,也是悲凉的。而氏娜的出现,一碗温热的葱头粥下肚,唤醒了志飘尘封已久的良知,他渴望和氏娜有个小家,渴望与人为善,渴望重新“回到那个岁月静好、祥和安乐的属于善良的人们的世界”[11]。这时志飘的心理活动,几乎让人看到了志飘与自我的和解、与生活的和解,重新以一个善良的人格回到大众视野的可能性。但最后氏娜拒绝了他,这象征着志飘通向善良之路被阻断了,加上氏娜转述其姑妈的嘲讽,让压抑的志飘深感受到奇耻大辱,触发了过激反应机制,他内心深处的怨念和仇视直指百户建,于是他径直冲进百户建家中与其对峙,怒斥其夺走他作为人的良知,求而不得的他只能捅死百户建,最后自我了结。志飘这一角色展现了个体抗争和社会压抑的矛盾,展現了大时代的滚滚车轮如何碾压小人物的命运,同时也在符合逻辑的情况下展现了小人物也有庞大、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从艺术高度来看,杰里·克里弗认为“人的头脑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地方,许多思想斗争就在这里持续不断地上演。人物与自身的斗争可以让我们对于这个人物的性格拥有最深刻的理解”[14],所以研究者对志飘的态度就不应全是厌弃和反感,志飘这一角色“丑”的张力还展现在万般不由己的悲凉上。在异化与救赎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志飘从“人-兽-人”的转变,他亦丑亦善亦真,因而在小说中具有最高的审美价值。
3.武代村女性群像:美丑并存
小说《志飘》不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志飘悲惨的遭遇,还通过氏娜及其姑妈、百户建的三姨太、兵职老婆的女性形象影射了当时现实社会中女性的困境。
氏娜在相貌上一反男权社会中传统女性形象的理想特征,南高以一种戏谑的口吻精细地描摹了氏娜的相貌之丑,“一个如同古书里面描写的愚者般呆傻,还丑得神憎鬼厌的女人。她的脸就是造物者的讽刺:它短得让人觉得似乎脸宽比脸长还要长;糟糕的是两颊还深陷。如果两颊稍微丰润点,那氏娜的脸可能还能称得上酷似猪脸——一张本已很难想象会长在人脖子上的脸了。鼻子又短,又大,又红,还疙疙瘩瘩像厚皮酸橙的表皮,肥大得似乎想要尝试遮住那张也在努力翘起以免被鼻子盖住的厚唇。也许正因为努力过了头,两片唇翘得似乎要胀裂开来。就算是这样了,氏娜还喜欢吃掺烟槟榔,肥厚的双唇又厚了一圈。不过也多亏嚼槟榔染上点红色,遮住了乌黑的唇色。都如此这般了,牙齿还又大又龅,想必它们觉得自己这样可以平衡几分这张脸的丑吧”[11]。这还不够,南高还进一步在她身上加了几个减分项“穷、丑、蠢”“祖上还有麻风病遗传史”,以至于“人们对氏娜犹如恶心之物般避之恐不及”“三十开外了氏娜还未嫁”[11],作家极力把氏娜塑造成一个边缘人物,试图把丑女氏娜和志飘捆绑在一起进而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
另一方面,南高在氏娜身上安插了一个“寓美于丑”的视点,氏娜的丑只是外表上的丑,她的美是情感美。当所有人都对志飘心生惧怕而避之不及时,她并没有囿于世俗的眼光,反而能够和志飘正常且和平相处,相熟起来,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就这么憎恨这个人?”[11]志飘生病时,她因怜悯志飘而在床上辗转反侧,她暗想道“还有什么比生著病也只能孤零零地蜷缩着更可怜的呢?”[11]于是天刚亮她就起床为志飘熬好葱头粥,她为“挽救了一个生命感到骄傲”[11],她甚至觉得自己似乎是爱志飘的,对她而言“这是份施舍者的爱,但同时也是受恩者的爱”[11]。氏娜以其身上的同理心、向善的品质包容接纳了志飘,所以在丑的外形衬托下,其美的灵魂就显得尤为突出。作者通过艺术语言的“抽象”和“变形”,将氏娜形象进行“陌生化”处理,即使日常经验的熟悉对象变得生疏起来,调离经验的自动性,使艺术作品具有新颖别致、出奇翻新的效果[15]。特别是在爱情面前,平日里没心没肺的氏娜竟会扭扭捏捏,“一个奇丑无比的人在恋爱时也会娇嗔”[11],在志飘眼里显得“这么丑还羞羞答答也还是可爱的”[11],这让读者看到了氏娜形象的丰富性,她是有相当的审美价值的,美丑并存使氏娜成为小说中突出的一个文学形象。但奈何氏娜也是深受封建荼毒的普通人,她不得不听从姑妈的意见而与志飘分开,一场在志飘和氏娜之间看似相互救赎的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氏娜这样的底层女性,在那样“吃人”的社会里根本没有权利决定个人幸福。
氏娜姑妈也是一个长期受封建文化毒害的普通农村劳动妇女,当她听到氏娜要和志飘共度余生的时候,出于对封建贞节观念的维护,她像是个疯婆子一样吼叫“天啊,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祖宗啊”[11];氏娜姑妈作为过来人,已经知道独自生活的苦楚,却极力反对氏娜和志飘在一起,她怒骂:“一个品行如此端正的女人看到自己侄女竟如此不守本分!真是丢人现眼!都过了三十了还是处子之身,都过三十……谁还跑去嫁人!谁等到这个时候还嫁人”[11]。她用封建的伦理思想去争做封建专制的奴隶,封建话语对女性的禁锢,让她理所应当地觉得“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那就一辈子忍下去,谁还去嫁志飘这么个家伙!”[11]贞节观念一方面象征了封建礼教,另一方面也成为姑妈内心的自我感知和自我折磨。姑妈或是出于自怜身世,为自己孑然一身的人生经历感到酸楚,心酸化为怨恨,氏娜便成为她情绪的宣泄口。简而言之,她的反对也是出于她的自私,她畸形的心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荒谬且残酷的成见,深刻反映了封建文化毒害了人的思想。
百户建的三姨太年轻貌美,长得珠圆玉润,却经常逼着志飘给她捏脚、捶背、揉肚子,“还嚷嚷着要他不断往上捏”[11],总是一副弱柳扶风样的三姨太却是“虎狼一样的娘们”[11],在志飘眼里“她只是想着给自己找乐子”[11]。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三姨太只顾自我享乐,沦为物欲、情欲的奴仆,丧失了人性中美好的品质,已不具备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思,百户建三姨太的身份的确给了她高于其他女性的地位以及优越的生活质量,但这也恰恰构成了她女性本能的压抑,即压抑了个人的欲望、私密的情感和身体的本能。在长期的秩序化规则下,在“理”和“欲”的矛盾挣扎中,她通过变形的丑,即违背公序良俗来反抗主流的“妇道”话语,以达到抒发内心苦闷的目的,然而究其根源是受到当时专制制度和庸俗环境的戕害。同样,兵职的老婆“秋波似水双颊绯红”[11],但她在家庭结构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处于被支配状态。而在外部关系上,她更没有自身的独立性,在外遭人调戏,懦弱的丈夫不仅不维护自己,反而回家家暴自己;在丈夫一气之下跑去当兵后,她更是沦为“村中那群大大小小的里役轮流使用的免费妓女。就连里长阿建,尽管那时已经有了三房姨太太,也没舍得寸这口天上掉下来的肥肉”[11]。外表的美对她来说无疑是种负担,但她只能默默地忍受。她是封建道德语境下被遗忘、被剥削的女性,毫无话语权,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读者可以通过武代村的女性群像,看到她们通过日常性的压抑来完成美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感知到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逐渐失去了内在的活力。
四、《志飘》亚审丑现象溯源
1.社会异化现象
刘勰有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6]。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自然与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时代作为一个与人的意识紧密联系的客观环境,也受文学能动的影响。所以要想深入地理解文艺作品,必须从时代和历史的角度宏观地把握,必须将作品放到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历史)背景中去,还原到产生它的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气候中去[11]。
自1885年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越南人民同时承受着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与剥削,国家处在封建社会解体、民族危机深重、阶级矛盾和斗争极其尖锐的时代[17]。特别是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波及了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统治,“法国政府为了解决自身的危机,为了巩固其在越南社会中的地位,便开始向越南市场大量倾销其剩余产品,对越南人民强行征收各种名目不一的苛捐杂税。与此同时,印支银行大幅度缩减了纸币的发行,越南的商品、农产品随之变得廉价不堪,众多农民和工商业者纷纷破产,失业人数急剧上升。除此之外,连年的灾荒使得越南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苦不堪言”[18]。《志飘》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小说中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丑态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尽管小说并没有点明具体的时代背景,主人公志飘更是身世成谜,但是作者南高思考的是带有普遍性、超时代的人性问题,所以他通过“丑”这一视角批判了当时病态社会所显露的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等问题。
2.作者对文本的影响
法国作家法朗士曾说:“所有的小说,细想起来都是自传”,表明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作者的影子。在南高的创作生涯中,他曾表明自己的创作思想深受越南古典文学作家阮攸、阮廌的影响,但“他更喜欢俄国的契诃夫”[19]。众所周知,契诃夫的小说题材涉及广泛,揭露专制压迫,鞭笞市侩庸俗,描绘贫困愚昧,对俄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全面、深刻地反映,特别是“乡村”主题在契诃夫的创作艺术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契诃夫“从最开始关注农民外部行为和生活的粗俗与无趣的幽默小品,到中期逐渐深入农民内心世界的抒情描写,再到后期全方位关注乡村未来的现实主义情怀,他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对20世纪乡村书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所以南高的作品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契诃夫的“声音”。南高出生于越南河南省里仁县大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农村是南高文学的故乡。另一方面,南高首先是以“作家”的身份進入人们的视野并被广大读者熟知,但除了作家这一身份,南高还是一名记者,一名越盟运动的战士。记者身份开拓了南高的社会视野,作家兼记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判断以及思考能力。南高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价值取向在其多部作品中都有迹可循。特别是本文所论述的《志飘》,南高通过树立典型形象,承认角色性格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对话语言和独白语言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小说的独特叙述方式。他凭借自己的农村生活经历以及对人性独到的洞察力刻画了武代村的一个个丑角,并突出丑以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揭露现实生活中潜在的阴暗面,反映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现象。
五、结语
“文学即人学”,这已然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性的看法。严格来说,文学是人以感情为核心的包括感觉和智性的动态变幻艺术[11]。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具有以“人”为基点的创作意图,经由作者创作出来的人物并非无意义的出场。小说中典型的形象蕴含深刻的意义,南高将他内在的同情怜悯和理解,不着痕迹地渗透在武代村每一个人物形象中,折射他所希望表达的作品主旨。《志飘》以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巧妙的叙事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其中包括志飘、百户建、阿强、氏娜及其姑妈、年寿、兵职及其老婆、三姨太等,他们或是封建官僚政治代表的剥削者,或是腐化变质的奴性农民,或是封建道德语境下被遗忘、被剥削的女性,每一个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丑”的一面。但丑和美并不是完全割裂开的,美和丑之间是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的,这就需要站在亚审丑的场域上,去正视否定性的美,去正视否定性人物的美,而这也意味着丑是对生命的异化、扭曲、变形等因素的自我否定。文学在正视否定性人物的过程中,对其美学评价自然是否定性的,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恰恰是肯定性的,这就需要研究者全面且客观地解读和阐释作品的价值。所以在亚审丑的视域下,我们可以看到南高抓住“丑”本身所具有的张力,通过间接的方式唤醒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和自身被隐蔽的、被压抑的批判意识,从而捕捉到《志飘》的美学意义。
参考文献
[1] 余富兆,谢群芳.20世纪越南文学发展研究[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
[2] 何明德.南高——伟大现实主义者[M].河内:文学出版社,2001.
[3] 风黎.南高文学事业[M].河内:人文科学出版社,2009.
[4] 阮庭诗.文学的几个问题[M]//武俊英.南高——人和作品.河内:越南作家协会出版社,2000.
[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 鲍桑葵.张今译.美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 孙绍振.散文:从审美、审丑(亚审丑)到审智——兼谈当代散文理论建构中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J].当代作家评论,2008(1).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潘知常.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10] 尼采.悲剧的诞生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 南高.南高小说选[M].巫宇,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
[12] 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3] 陶长坤.论小说结构的深层机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1(5).
[14] 杰里·克里弗.小说写作教程:虚构文学速成全攻略[M].王著定,译.戴凡,校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5] 谭好哲.超越形式禁忌与形式崇拜—马尔库塞“美学形式”论探讨[J].文史哲,1990(3).
[1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 张海云,谢群芳.基于语料库的文学作品检索分析——以越南中篇小说《志飘》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
[18] 胡雯青.越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越南民族性格研究(1930-1945年)[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1.
[19] 余富兆.论越南现代作家南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
[20] 欧萌莲.契诃夫小说中的乡村书写探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9.
(特约编辑 孙丽娜)
作者简介:梁珊珊,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越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