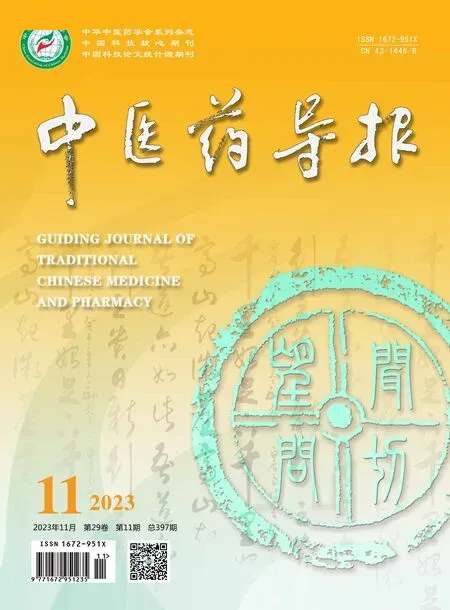徐旭英分期论治坏死性筋膜炎半阴半阳证经验*
2023-12-18刘威池徐旭英吕春燕焦琳茜
刘威池,徐旭英,吕春燕,郭 卉,焦琳茜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100010)
坏死性筋膜炎(necrotizing fasciitis,NF)是一种罕见的潜在威胁生命的进行性感染疾病,是由细菌入侵皮下组织和筋膜引起的急性坏死性软组织感染,可伴毒血症、败血症及多器官衰竭等[1],属于外科危急重症。治疗关键在于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主要治疗原则包括:早期彻底清创引流,使用广谱抗生素,予以营养支持治疗,监测生命体征,反复评估病情[2]。尽管对坏死性筋膜炎的医学认识和治疗手段不断提高,但因其进展快、早期症状不典型等特点,该病死亡率为12%~35%[3]。且坏死性筋膜炎患者的住院周期长、清创次数多,创面较一般外科创面修复难度大,患者生存质量较差[4-5]。中医学对该病目前无确切定义,根据病程的不同症状表现将其归属于“烂疔”“流注”“痈疽内陷”范畴。《诸病源候论·丁疮病诸候》曰:“亦有肉突起,如鱼眼之状,赤黑,惨痛彻骨,久结皆变至烂成疮,疮下深孔,如大针穿之状……一二日疮便变焦黑色,肿大光起,根硬强,全不得近……患此者,二三日便死。”[6]中医药早期介入能够有利于缓解临床症状,改善疾病预后,减轻患者心身负担[7-8]。
徐旭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名中医,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从事中医外科学临床、科研、教学工作二十余年,对于各种外科疾病的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证经验,尤善于使用中医外科“阴阳辨证”分期论治坏死性筋膜炎。笔者有幸跟师学习,受益匪浅,兹叙述经验如下。
1 坏死性筋膜炎半阴半阳证的认识
《疡科纲要·论阴证阳证》曰:“疡科辨证,首重阴阳。”[9]《疡医大全》云:“痈疽之候,纯阳固多,纯阴原少,惟半阴半阳之证最多。”[10]阴阳作为外科辨证总纲,其贯穿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的整体过程。半阴半阳证并非确定节点,可由阴阳两证转化而来,也可由疾病本身表现出阴阳特质,是动态的病理过程。《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对半阴半阳证的描述为“似阳微痛微焮肿,如阴半硬半肿高。”[11]坏死性筋膜炎初起时症状多不典型,与蜂窝组织炎类似[12],皮肤红斑,形态平塌、边界不清、不易溃破。但因其病位较深,感染迅速且循筋膜扩散至肌肉组织层,引起局部炎症反应。患处皮色紫红,皮温升高,肿处高突或发硬,疼痛剧烈而拒按,全身伴恶寒发热,心悸烦躁等。若感染控制不及时,皮损因组织大面积坏死则不易收口,疮面愈合周期较长;若感染泛及全身,患者易出现脓毒血症休克,表现出高热、烦渴、神乱,甚则阴尽阳绝。《外科正宗》中描述半阴半阳证:“五善虽兼有,七恶未全逃”[13]。徐旭英教授认为坏死性筋膜炎局部疮面与全身情况符合半阴半阳证的特色表现,介于“痈”“疽”[14]之间,兼有两者特性,但结合本病初起、进展与预后的阴阳特性,其阴性征象较阳性征象重,故坏死性筋膜炎属于阴重阳轻的半阴半阳证。
2 病因病机
《外科正宗》称半阴半阳证:“肿而不溃因脾弱,溃而不敛为脓饶。”[13]《医门法律》卷二云:“论胃中水谷与精气,与水谷之悍气也,皆正气也。”[15]半阴半阳证发病通常与脾胃相关,为本虚标实之证。坏死性筋膜炎常因火毒之邪引起,患者常伴随免疫受损情况[16]。中医认为诸邪皆可化火,如肝经湿热化火好发于会阴部;也有因外伤后毒邪入侵而发病者,多见于体弱旧病,气血虚损,卫阳不足,极易“内陷”。故患者素体脾胃之气必先受损,正气不足,外伤火毒侵犯机体,气血阻滞于经络筋膜之间郁而化热,热盛肉腐表现于皮肉外。
3 分期论治
坏死性筋膜炎常表现出阴重阳轻的半阴半阳证特性,患者在就诊阶段多为典型皮肤红斑肿胀、水疱及不成比例疼痛等阳性征象,故临证时常将此病程阶段归为早期。清创术及抗感染治疗作为治疗坏死性筋膜炎的必要手段,可以逐渐减轻局部及全身阳性征象,然疮面仍有疼痛,疮周仍有红肿等表现,故为中期。后期则是针对坏死性筋膜炎疮面溃后难敛、迁延反复等阴性征象特点,以及病程的不同阶段,中药内服和局部外用制剂的治法不尽相同。
3.1 早期 坏死性筋膜炎早期呈明显阳性征象,表现为病损处边界不清的红斑或红肿,肿处硬,皮温热,疼痛剧烈而拒按,常伴随明显的全身症状如恶寒发热、心悸烦躁、烦渴引饮等表现。此时应及时“给邪以出路”,剪除全部失活组织及坏死筋膜,充分引流,并沿切口扩创观察感染涉及范围。术后以凡士林纱条填塞,加压包扎患处。《疡科心得集》云:“凡治痈疽、发背、疔疮、乳痈、一切无名肿毒,先须托里,勿使毒入附延骨髓;托里之后,宣热解毒、定痛排脓,是为急切功夫。”[17]故遣方中投白术、黄芪、升麻等以升阳益气,托里扶正;金银花、车前草、苦地丁等以清热解毒;玄参、知母、牡丹皮凉血定痛。金银花和黄芪常以量大效专而作为疡科名药,如《名医别录》中载金银花可治“寒热身肿热毒”[18]。其提取物金银花醇具有抗炎活性[19],可大剂量使用至30~60 g。黄芪味甘,具有补虚、托毒生肌、排脓止痛之功[20],临床可使用至90~120 g。
3.2 中期 《外科正宗》云:“凡疮溃脓之后,五脏亏损,气血大虚,外形虽似有余,而内脏真实不足,法当纯补,乃至多生。”[13]《素问·玉机真藏论篇》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六腑之本也。”[21]患者清创引流术后气血大失,结合本病为本虚标实之证,导致真阳受损,表现为精神萎靡不振,大汗出,四肢逆冷,语声低微,脉数无力等。考虑患者疮周仍存在红肿疼痛、腐肉未尽、脓液积蓄等阳性临床征象,治疗原则上扶正大于祛邪,治法以补托气血为主、清洁余毒为辅。常用黄芪、白术补气养血;当归、鸡血藤兼有活血之功;阴津不足见潮热盗汗,声音嘶哑者,予五味子、麦冬等补气养阴;真阳不足见四肢逆冷、语声低微者,加肉桂、干姜、附子等温阳救逆;另投入金银花、生槐花、土茯苓等解毒清热。针对创面应使用蚕食清创术,从远端组织到近端组织、周边到中间的原则,分次清除失活组织。同时配合朱红膏纱条[22]填塞创面脓腔内以化脓祛腐、煨脓长肉。创周可配合复方化毒膏[23],行箍围解毒法收束创周,保持护场与根脚的稳定。
3.3 后期 经上述治疗,患者正气稍复后疮面疼痛及疮周红肿减轻,疮面肉芽组织可呈淡红色正常生长,但皮瓣潜腔内残存坏死组织易包裹肉芽出现水肿,疮周皮色暗淡伴结痂死皮,疮面难以收口。此时疾病呈现出明显阴证征象,应“透阴转阳”[24],在黄精、黄芪、党参等健脾益气基础上予肉桂、桂枝等温阳通络;疮面疼痛持续,可配伍皂角刺、白芷通络止痛。坏死筋膜炎常见基础疾病为糖尿病[25],后期则可加入墨旱莲、女贞子、乌梅等“滋补肾阴,阴中寓阳”[26-27]。外治清创前提是不损害肉芽组织,使用朱红膏纱条配合蚕食清创术清除剩余坏死组织,疮周皮肤逐渐收束后覆以甘草油纱条[28]解毒生肌,疮周则可使用回阳生肌膏[29]温阳益气。
4 验案举隅
患者,男,59岁,2020年12月16日初诊。主诉:左肩背红肿疼痛破溃1个月,加重3 d。1个月前患者因左肩颈红斑、水疱伴痛痒就诊,诊断为“蛇串疮”后并予相应治疗。10 d后皮损处出现一个鸡蛋大小红肿斑块,中心破溃黄白色脓液,分泌物培养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建议行清创术,患者拒绝并自行挤压疮周排脓。3 d前肿块范围进一步扩大,伴发热寒战,体温最高为38.9 ℃。刻下症见:左肩背红肿破溃,疼痛,伴大量黄色浓稠分泌物,发热,体温38 ℃,精神烦躁,纳差,眠欠安。舌红,苔黄,脉数。既往病史:2型糖尿病30年、1级高血压病30年、高血脂症半年余、左肾癌切除术后10年。专科检查:左肩背部有一块范围约20 cm×20 cm肿物,中央皮肤呈皮革样坏死,色鲜红,边界欠清,张力增高。可见3处约1 cm×1 cm大小破溃,伴大量黄色浓稠分泌物流出(见图1),波动感欠佳,皮温高,压痛阳性。浅表组织B超:肩背部皮下可见不均质回声,范围约15 cm×12 cm×1.7 cm,边界欠清,可见血流信号,部分病变累及皮下,未见明显液化。血常规检查示:WBC 30.25×109/L,Hgb 10.4 g/dL,ALB 28.7 g/L,CRP 187.5 mg/L,PCT 1.14 ng/mL,Cr 116.8μmmol/L,UREA 8.81mmol/L,ALT 68.9U/L,AST 52.9U/L,HbA1C 9.2%,GLU 12.01 mmol/L,Na+125.1 mmol/L,LAC 3.66 mmol/L,LRINEC评分11分。西医诊断:坏死性筋膜炎?低钠血症;肝功能异常;慢性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1级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中医诊断:烂疔(湿热毒聚证)。治法:益气祛邪,清热解毒。方选五神汤加减,处方:金银花45 g,茯苓30 g,车前子30 g,黄芪30 g,升麻30 g,苦地丁6 g,怀牛膝10 g,苍术6 g,牡丹皮10 g,生知母15 g,生地黄20 g,当归20 g,麸炒白术15 g,枳壳10 g,甘草10 g。1剂,1剂/d,水煎服,分早晚温服。并立即行清创引流术治疗。基础治疗方面予抗感染、控制血糖及支持治疗。

图1 局部疮面表现
2诊:2020年12月17日,诉疮面存在坏死组织及脓液,疮周暗红疼痛,体温恢复正常,有大汗出、乏力,精神萎靡等症。舌暗红,苔黄腻,脉数无力。考虑患者气血大失,真阳衰微,暂不予清热解毒之法,投黑顺片、肉桂、姜炭以温阳救逆。方选八珍汤合阳和汤加减,处方:生黄芪90 g,麸炒白术15 g,茯苓30 g,红参片10 g,当归30 g,赤芍12 g,生地黄30 g,肉桂15 g,厚朴6 g,陈皮6 g,五味子10 g,麦冬15 g,白芷15 g,黑顺片6 g,姜炭10 g,炙甘草10 g。1剂,煎服法同前。外治采用蚕食换药法,疮内填塞朱红膏纱条以化脓祛腐、煨脓长肉,疮周外敷复方化毒膏箍聚疮毒,透脓外出。
3诊:2020年12月18日,诉疮面坏死组织较前减少,汗出缓解,仍心悸烦躁。血常规检查示:WBC 29.05×109/L,CRP 90.5 mg/L。予2诊方去黑顺片,肉桂减至12 g,加金银花30 g。3剂,煎服法同前。外治法同前。
4诊:2020年12月21日,诉已无心悸烦躁,汗出,偶有乏力,疮面有新鲜淡红色肉芽组织生长,疮周色暗红,疼痛较前明显缓解。血常规检查示:WBC 13.93×109/L,CRP 63.5 mg/L。考虑患者阳气稍复,可行清解余毒之法。予3诊方去红参片,金银花减至15 g,生黄芪减至60 g,五味子减至6 g,麦冬减至6 g,加玄参15 g,党参30 g,滇鸡血藤30 g以补气养血。3剂,煎服法同前。外治继予朱红膏纱条蚕食换药以化脓祛腐、煨脓长肉。住院9 d后考虑患者全身症状较前好转,疮面控制尚可,予其出院继行中药口服及外治治疗。
5诊:2020年12月31日,诉疮周皮肤较前收束,肉芽组织因少量坏死组织包裹呈现水肿状态,疮周无明显疼痛,舌淡光滑,苔薄黄有裂纹,脉细。治法:益气养阴,温阳通络。方选益气养阴汤加减,处方:当归10 g,黄精10 g,黄芪45 g,党参15 g,女贞子10 g,墨旱莲10 g,青黛3 g,紫草5 g,白芷20 g,皂角刺10 g,金银花30 g,赤芍10 g,乌梅5 g,冬瓜皮30 g,土茯苓10 g,生槐花10 g。10剂,煎服法同前。外治继予朱红膏纱条蚕食换药,外覆以甘草油纱条解毒生肌。
6诊:2021年1月11日,诉右侧疮面出现较多坏死组织,且疮周右侧呈红肿之势,炎症侵润明显,伴发热恶寒,舌淡,苔薄黄有裂纹,脉细数。考虑患者正气尚未完全得复,局部余毒复发,予上方加肉桂10 g温补脾肾,野菊花20 g清解余毒。14剂,煎服法同前。外治法同前。
7诊:2021年2月1日,诉疮面右侧肿势渐消,疮周皮肤较前收束。舌淡红,苔白,脉弦。予上方去野菊花,加泽兰10 g,牡丹皮10 g继以活血消肿。10剂,煎服法同前。外治予疮周外敷回阳生肌膏温阳益气。后随访,患者状况平稳,疮面愈合,未出现复发。
按语:本案患者诊断为坏死性筋膜炎,患者既往有2型糖尿病、左肾癌切除史等,素体正气亏虚日久,外感火毒后气血阻滞筋络发病,中医辨病为烂庁,辨证属湿热毒聚证。早期呈典型阳性征象,故见局部红肿破溃,疼痛,伴大量黄色浓稠分泌物,发热等表现。外治及时予“给邪以出路”同时,内治以清热解毒,凉血定痛,方以五神汤加减投之,君药金银花搭配苦地丁清热解毒,配伍牛膝补中散毒,更添黄芪、麸炒白术、升麻等以升阳益气、托里排脓。2诊、3诊时患者清创术后余毒未尽,但出现气血大失,甚则阳气衰微,表现为全身呈乏力,大汗出,脉数无力,故予八珍汤合阳和汤加减,方以大剂量黄芪配以麸炒白术、茯苓健脾益气;当归、赤芍、生地黄养血活血;红参、黑顺片、肉桂温阳益气;佐以麦冬、五味子敛阴清热。外治予朱红膏纱条填塞疮内祛腐引流,疮周使用复方化毒膏箍聚疮毒,建立护场。4诊时患者阳气稍复,继续秉持扶正祛邪思想,逐渐减量清热解毒之品,加玄参、党参、滇鸡血藤等补托气血,配合朱红膏纱条祛腐生肌。5诊时患者全身条件尚可,疮面见长势良好的水肿肉芽,可行“透阴转阳”原则,方选益气养阴汤加减,方中黄芪、党参温阳通络;黄精、女贞子、墨旱莲益气养阴;针对水肿肉芽,在金银花、青黛、皂角刺清热活血基础上加冬瓜皮、土茯苓、生槐花利湿解毒。外治在朱红膏纱条填塞疮面基础上外覆甘草油纱条解毒生肌。6诊时考虑患者机体气血生发不足,疮面余毒复发,疮周呈红肿之势,表现为恶寒发热状,在益气养阴扶正基础上加以金银花清解余毒,佐以肉桂温阳通络,外治法同前。7诊时患者疮周红肿较前减轻,则佐以泽兰、牡丹皮活血消肿;外治法使用回阳生肌膏温阳通络。后患者疮面愈合,未再复诊。治疗过程中,徐旭英教授根据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治疗,内、外治法相互配合,随证辨治,灵活加减,临床效果显著。
5 结语
坏死性筋膜炎是少见的外科危急重症,临床死亡率较高,且存活患者生存质量不高。徐旭英教授以阴阳辨证为纲,指出坏死性筋膜炎属于阴重阳轻的半阴半阳之证,并根据疾病发展不同阶段分为早、中、后期,分别遵循“给邪以出路”“扶正兼祛邪”“透阴转阳”的治疗原则,采用中医内外治法结合治疗坏死性筋膜炎,临床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