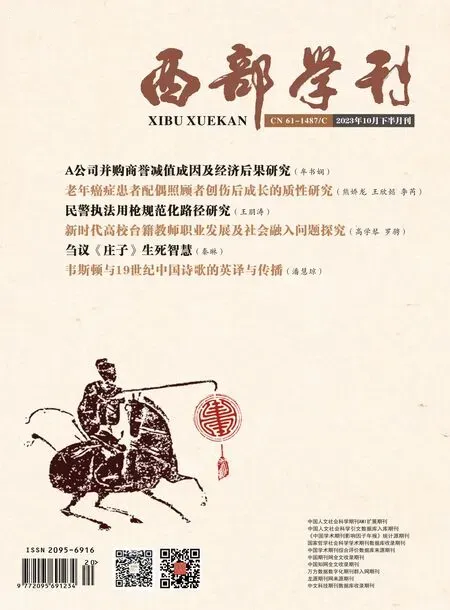刍议《庄子》生死智慧
2023-12-18秦琳
秦 琳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在柏拉图的眼中,“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1]25,哲学家终其一生,实际上是在“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1]17。在兵荒马乱、人命如草芥、生存环境极度困苦的先秦时期,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以“生生”为代表的民族特色,诸子百家极尽所能地在家国碰撞和体认天命中寻求延续生命之道。死亡哲学作为其反面,也成为了各流派必须思考的命题,“死生亦大矣”[2]559。儒家以“死得其命”“慎终追远”“舍生取义”等方式言及死亡,实际是为了以死亡为中介,引导世人更加关注生的现世性,以达到“知生方知死”的目的。而庄子的生死智慧则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微观上尊重、保全个体生命的同时,于宇宙层面也更强调“生死齐一”“薪尽火传”的运行之道,通过跳脱小我的束缚,以达到“安时处顺”的人生境界,对死亡达成独特的认识。
一、贵生之法
(一)形骸之内:保身全生
“喜生恶死”是常人对待生死的基本态度,“喜生”的程度之高可以用“贪生”来诠释。庄子对待世间诸事淡泊无为、随遇而安的态度也常常使人误解为“不重死也不重生”。事实上,“无为”的反面恰恰是“无所不为”,庄子虽不刻意采取手段延长人的自然生命,但其对待生命的观点同样充斥着尊重敬畏。在某种程度上,庄子也是“喜生”的,只是其“喜生”的程度并未极端至“贪生”,而恰当好处地停留在了“贵生”“重生”的层次上。“贵生”“重生”的实际举措就体现在“保身”“全生”之上。如果无法保留形体,一切将成为空谈,如同《达生》中的单豹和张毅一般。单豹好隐,却死于饿虎爪下;张毅好恭,却亡于内热之病。前者从内体认道,后者从外涵养道,但仅仅在精神上对道有无限的向往和追求是有失偏颇的,内在涵养的充实必须建立在保养形体的基础之上,人的生命具有整体性,形神兼备,不可疏漏其一。只有做到“缘督以为经”[2]100,才能够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具体而言,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都不应去追求某种极致,而要秉持内心的中虚之道。中虚之道的原理与庖丁解牛的方法是一致的,解牛需顺筋骨纹理,中虚之道的把握也需在万物自然而然的理路中顺势而为。用心体认、顺应自然形势,实则也是在无为中达成无过无不及之效果,从而尽最大可能在世间留存生命。
(二)形骸之外:成和之修
与贤者圣人逍遥自在、游离于方外相反,世人常被形体束缚,将“养生”局限于将养形骸,以无限的物欲供养肉身。而实际上,对形体的眷恋过深,精神上的负累也就越重。如果想要到达不拘泥于形体的逍遥境界,就必须远离世间烦扰,只有如此才能够心正气平,进而精气不亏、体认大道。如何在形骸之外找到精神和德性的寄托之处?其本质是对人世欲望和杂念的剥离。一方面,可以借助“坐忘”的途径,《大宗师》篇有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2]213在忘却自身形骸之后,还需将一切由外界附加的束缚全部抛空,使精神不被礼乐制度所限制。人对形体的眷恋与物欲息息相关,正因“知识”常常将人的物欲一步步推至顶峰,才需与“离形”一并舍弃掉。“忘我”的境界并非仅仅停留在“坐”的层面,“坐”更多展现的是一种静止无波的状态,实际上要在随时随地都能够达到“忘我”“忘物”的心境。另一方面,“同于大通”的本质、“坐忘”所追求的境界实质上也是“心斋”的奥义,即将心灵之中无限的杂念全部清除干净,使自身不再因感性和理性的侵扰而持有固着的、具像化的关切对象,从而达到如气般中虚平和的阶段:不拘泥于己见,不拘泥于世俗;不执着于生、也不执着于死。当干净澄澈的心感悟到大道,体会大道与己并行、明白大道运行大化的规律时,也就能够于形骸之外享受和谐。
二、安之若命
(一)生死齐一:万物同状
生死齐一,实际揭示了大道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德充符》篇云:“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2]158其本意为个体之间命运有所不同,哪怕是同样的境遇,造化也会天差地别。而从个体自然生死的层面来看,无论后羿的箭矢是否能命中他,最终都无法逃离生死必然的命运。《大宗师》篇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2]185死生如昼夜,昼夜不停,夜以继日,白昼只有通过黑夜才能展现其光芒,黑夜在白昼的反衬下更显静谧,二者只有在互相辅助中才能凸显意义。自然界如此,个体生命亦是如此,生死相依。
儒家常“以生观死”,丧葬礼仪、死亡方式的选择往往是生的注脚,最终目的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无限弘扬仁与义。道家则另辟蹊径,“以死观生”“视死如生”,力图将个体之死亡返璞归真。《田子方》有云:“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2]542庄子生死齐一的智慧建立在其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个体之间虽千差万别,但是,都是“有待”而存在、由道所孕育的。道生育养长万物,万物成熟衰退后复归于无尽大道之中,即完成了生命的循环,由此,大道运行的规律具有无限性和必然性,死既是生的终点、亦是新生的起点。以燃烧着的薪柴为例,薪柴终有烧光的时候,但火种却能得以延绵。个体生命虽然有衰亡的一天,却又能够在衰亡的同时作为大道的分子重新复归于大道、转化为新生命的组成部分。当从个体“小我”的局限眼光扩散至宇宙“大我”的运行演化中,“生”也就从有限转化成了无限。而这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万物一体,生死同状”[2]310的大前提,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78。
人之为人皆因造化使然,无法自由选择生存的形态,相较世间万物而言,有更深层次的理性智慧,但这并不代表世人即是世间主宰。本质上,人与万物都有共同的生命来源,因而人就能够运用自身的共情性、通过“物化”的方式打通物我界限。当万物浑然一体之时,个体之生死、个体与他者之是非之间也不再有绝对的对立性,而是处于无限的转换之中,个体之死也可成就他者之生。庄子将死,要求与天同葬、星月为伴而不被乌鸢食所惧,因其早已领悟到了自我与万物生灭互相交融的道理,死不过只是生存方式的转变,因而无需以厚葬的方式来安慰自己。
(二)安时处顺:哀乐不入
庄子的生死齐一,模糊了我与非我的界限,以豁达乐观的心态直面死亡,也就极易导致“乐死恶生”的理解偏差。对此,郭象做出纠正:“若然,何谓齐乎?所谓齐者,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生死之情既齐,则无为当生而忧死耳。”[3]倘若庄子恶生,也就不会养生、贵生了。实际上,生死一体、生死齐一的视角并非寓意死亡无所轻重,死与生完全一致——死虽能生,却由个体之死转为群体之生,不能轻易等同。生与死的状态虽在大道之内能够互相转换,但仍需要世人以安之若命的态度同等地对待生死,无论人生走在哪个节点,都以乐观心态安然处之。“乐生好死”是庄子生死智慧的前提,是全身心融于大道,感受生死相依的保证。倘若无法意识到这个道理,就会成为束缚自身的“桎梏”“天刑”。如果想要对“乐生好死”有正确认识,就离不开对“乐”和“好”的情感把握。在《德充符》中,惠子和庄子展现了对情感的两种不同认识。
惠子认为,“既谓之人,恶得无情”[2]172,他对情的理解更加偏向于常人,而在现实情境中,这类情感也往往更容易被是非物欲所浸染,情的发出并非出自本意,而是刻意所为;与惠子相反,庄子主张的情以无情作为展现方式,即“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172。与刻意生发的情不同,无情之情更加偏向于一种生于混沌、同于大道的原生态朴素情感,而这种情感所处于的状态可以用“水停之盛”[2]163来表达,即心处于平静如水的状态,情的发出只需顺应自然而为,以和顺的天性来面对自然不可知的变化,淡然接受一切安排,“不知说生,不知恶死”[2]176,不会仅仅拘泥于好恶之情中。这并非是对人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存在状态的否定,而是强调人在顺应自然大化的过程中,无情之情所呈现出的情感反应是自然、适度、有限的,进而带来“哀乐不能入”的效果。子舆重疾,弯腰驼背至匪夷所思的角度,但仍然安时处顺、自得其乐,不似常人一般郁郁寡欢、憎恨时运,甚至还能够欣然接受更加离奇的变化。哪怕将身体的部位变为公鸡、弹丸、车轮,他也能够随遇而安,顺势接受这些新事物,并将其化为己用。
当意识到人不能离于大道而独立存在,其短暂的实存早早被天地之大炉、造化之大治规定时,也就自然通晓了生命是适时而拥有、死亡是顺时而变化的道理。造化之运行“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2]462,无法预判、无法避免。但人至少拥有随心观化的自由。面对造化,倘若“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2]109,实则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2]109,将会永远无法摆脱倒悬之苦。
三、死非无乐
(一)夫俗所乐:此乐非乐
在伊壁鸠鲁的视角中,哲学具有医疗的作用,虽不能平息肉体苦楚,却能够帮助灵魂减轻痛苦。灵魂最大的痛苦恰恰在于人的必死性。无人能够长生不老,这一事实也就提示着享受欢愉的人们,其享有的一切都具有暂时性。因生之短暂,夫俗常常会尽最大的能力扩张其欲望,以求得更多快乐,以对抗死亡丧失一切的恐惧。什么是天下最大的快乐?庄子在《至乐》中得出了“至乐无乐”[2]458的结论。
财富、地位、长寿和荣誉,是夫俗皆趋之若鹜的;与此相对应,贫穷、卑贱、短命和声名狼藉,人人都想避开这些不幸。幸福与不幸总是相伴,恰如“享乐主义的悖论”所言,追求快乐的人,往往不能够得到快乐。这些令人追求的东西并非是绝对值,而是相对的。当一人拥有权势地位时,就会想去奢求更多,同时也会终日忧虑失去的那天。看似享有天下的“至乐”,却反被“至乐”所捆绑,终日与忧愁相伴。如果对生的眷恋更多是对“至乐”的不舍,整日沉迷于抢夺竞争之中,“活着”本身就仿佛成了一种刑罚、一种工具本身。庄子提出“至乐无乐”,实则内蕴物极必反的道理,避开纷争、远离是非,保留一颗恬淡的心,就能与人世间和解。如果生者的眷恋是“至乐”,那么眷恋之物也不如预期中美好;如果生者对死亡的忧虑在于丧失一切“至乐”,死后世界仿佛也没有预期中可怕。
(二)骷髅之乐:南面王乐
对死后世界的探寻也是哲学家意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伊壁鸠鲁认为,死后世界不可感知,生时无法觉察死的状态,至死也就无需恐惧已有的事实;孔子认为,人应活在当下,如果连活都活不明白,更遑论弄清楚死亡……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对死后世界不作过多探及,因为毫无意义。但造成死亡恐惧的最大诱因也在于对未来世界的不可知,世人恐惧的并非死亡事件本身,而是死亡带来的未知性。自古以来,中国本土常常将死后世界称之为“阴曹地府”,佛教也有“十八层地狱”之说,本不可知的死亡就与黑暗的阴影划上了等号。而庄子在《至乐》中,借由与骷髅的谈话,为众人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死后景象。
庄子遇见骷髅的反应是与常人一致的,他问骷髅是死于背信弃义,还是死于兵荒战乱,抑或是其他情形。而在骷髅看来,如何死、怎样死常常是夫俗的烦扰,真正的死后世界并无这些累患。人常将死看作至悲之事,恨不得能够永远长生不老,而当庄子问及骷髅是否想重新拥有生命时,骷髅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2]466死亡虽然意味着个体形骸的消解,却也代表着君臣义务的解绑、四时之事烦扰的消散。倘若终日为全家生计奔波劳碌,万事皆以礼教为先,对内外上下都需行之有度,死反而是一切劳苦的终结,是哪怕南面为王都无法匹敌的乐事。“若果养乎?予果欢乎?”[2]470骷髅真就因死而悲哀吗?夫俗真就因生而惬意吗?如若是方外之人,万事顺应自然,死即是身心无所束缚的逍遥;如若是方内之人,生前汲汲营营,死即是一切责任义务的休止,是生时难以寻觅到的安歇之地。
四、结束语
长久以来,世人皆恐惧死亡,将死亡视为人类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庄子》中蕴含着关于生死的诸多真知灼见,却总被人们以“过于脱离世俗”为由,忽略其潜藏价值。实质上,“超凡脱俗”只是世人对庄子的片面化理解,在庄子的话语体系下,生的状态也是弥足珍贵的,形骸之生与德性之生一样不可或缺,需要每个人都珍重对待、用心涵养。与淡化死亡威胁的生死态度不同,《庄子》生命智慧的独到之处更在于,当个体之生的状态不得不被打破、生命个体不得不面临着死亡挑战时,人们也能用安之若命、安时处顺的平和态度予以应对。一方面,接受原子式的、小我生命的阶段性完结,期盼宏观的、大我生命的无限延续和升华;另一方面,既不高估现世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也不否定和片面低估死亡带来的安逸与舒适。在生命和死亡严重脱节、死亡教育极度缺失的当下,庄子的生死智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现代人的死亡焦虑,助人在珍惜已有生命的同时,也能超然对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