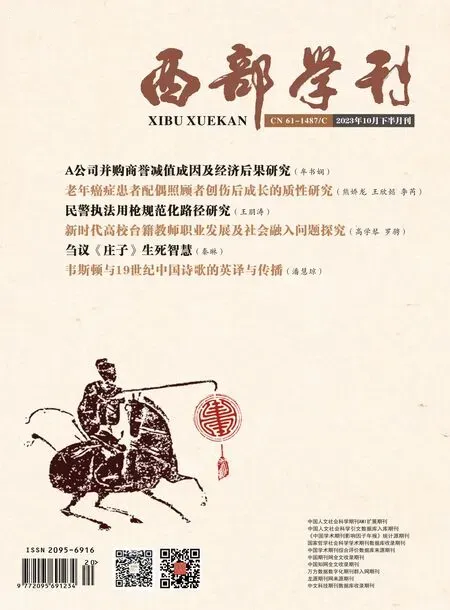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抗战文艺大众化研究
——以《抗战文艺》为例
2023-12-18纪杰
纪 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006)
《抗战文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的会刊,1938年5月4日创刊于武汉。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故抗战文艺编委会和出版部迁往重庆,同年10月15日复刊于重庆,1946年5月4日在渝终刊。《抗战文艺》是贯穿全面抗战始终的中国出版文艺代表刊物,充分反映中国文艺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愈加丰富的抗战文学内涵。同时,《抗战文艺》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主张的基本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为此,笔者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视域下,观照中国抗战文艺大众化与全民族统一抗战总基调下的人民书写。
一、《抗战文艺》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点契合
(一)彰显正确舆论导向与正面宣传相统一
从《抗战文艺》的性质来看,它作为“文协”的机关刊物肩负起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抗战文学的组织与领导的历史使命。因此,《抗战文艺》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要发挥文艺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疆场上的文化引导与民众宣传作用,同时“要把整个的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运动,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1]由此可知,通过借助文艺的正确舆论导向与新闻的正面宣传,文艺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调动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力量。例如,穆木夫在第一卷第六期的《抗战文艺的据点》中所说,抗战文艺工作者应当是抗战大众的心灵导师,担负起用文艺武装抗战大众的心灵,在抗日的战斗中所得到的经验认识去教育大众,会聚大众抗战的磅礴力量。
《抗战文艺》在舆论引导上能够正确把握和引导舆论形成后的流动方向,对于敌人在文艺界开展的侵略行径和国内文艺界所产生的错误思想进行强烈批判与诚心指正。姚篷子在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敌人屠刀下的思想与学术》中曾谈及某博士以“安心研究学问和生活条件优渥”为幌子,劝谏中国文艺界知识分子留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北平。对此,姚篷子先生强烈批驳这种在敌人血腥屠刀下研究学问和为日本军阀文化侵略服务的错误思潮与举措,主张文艺工作者应当联合起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沉痛灾难和文化麻醉政策的险恶用心。《抗战文艺》在正面宣传上始终坚持弘扬抗战救亡的民族主旋律。笔者以1941年“珍珠港事件”为分界线划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两个历史时期。在全面抗战前期,《抗战文艺》正面宣传了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生存与独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后期则突出宣传中国人民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发挥的关键作用。
(二)突显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相统一
《抗战文艺》作为贯穿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始终的典型刊物,在宏观与微观上如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蹂躏与迫害,同时也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底层民众生活进行真实而细腻的刻画。马克思在关于“报刊有机运动”的论述中深刻说明:“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2]所以,《抗战文艺》在突显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相统一的基础上,反映出抗战时期民族矛盾的社会本质和整体面貌。
在宏观真实上,《抗战文艺》始终围绕抗战救亡主题,通过每一期的微观真实,共同串联起表现中国人民抗战之艰难与必胜之决心的丰富内容。通过深入研读文本和纵向整体考察可知,《抗战文艺》经过了主题单一化的“战争书写”到主题不断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化的“人民书写”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明线上既客观反映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所表现的宏观真实性,在暗线上也从民众生活的角度展开观照,真实揭示由抗战初期的戮力同心到后期民族劣根性和社会黑暗腐败现象滋长的宏观变化过程。
在微观真实上,《抗战文艺》通过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的方式如实展现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和中国人民誓死抗战的决心。杨维铨在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中发表的《二月四日》真实记录了日军在1939年2月4日对贵阳城区进行血腥轰炸的惨景。作者在文章前面以诗铭志:
“二月四日,不要忘记!日帝国主义,敌机,丢下炸弹,烧夷,把三山路的小巴黎,把我放在里面的行李,新买的皮鞋,棉被,和年来的草稿,笔记,把来不及逃出的老人,小孩,全部,全部烧死,毁灭!”“把我们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财富,和几千和平居住的老幼男女,在顷刻间夺了去”。“碎的肉,紫的血,万丈的浓烟,火柱,烧成一副恐怖的画图”。[3]
作者真实记录了日军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并在诗的结尾处用愤激的情感向民众发出敌人“只烧毁了我们孱弱的外衣,可烧不毁我们顽强的意志”的反抗号召。
(三)呈现人民性与社会责任相统一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曾使用过“人民性”的概念,并在《第六届莱茵省会议的辩论》等相关文章中系统阐明人民性的特征。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来看,新闻媒体所拥有的传播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在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之下承担社会责任。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
《抗战文艺》呈现出抗战救亡总基调下大众化主题与人民书写的重要表征。适夷刊载于第一卷第一期《纪念“五四”——为大众的文化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需要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利用文艺力量唤醒人民群众的斗争意识,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同时,文艺传播不能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内,而应该走进人民,走进现实,以普罗大众为基础,才能铸就出宝贵崇高的文化。同样,在抗战后期的小说主题中,着重突出刻画底层人民大众的生活,如周而复的《春荒》,巴金的《猪与鸡》,列躬射的《吃一顿白米饭》和路翎的《卸煤台下》等,都真实描绘人民群众战时的贫困生活,表达对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怜悯,也充分彰显《抗战文艺》在大众化的格调下书写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抗战文艺》呈现出呼吁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众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以群在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扩大文艺的影响》中认为,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战斗武器,负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推进社会现实进展的任务。因此,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文艺应该发挥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不断丰富和激发人民群众在抗战期间面临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和高压下的心灵世界和激情斗志,在利用旧形式的过程中,将新内容传播给大众,使大众逐渐从落后的旧文艺毒素中抽离出来。此外,《抗战文艺》积极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构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化阵地。例如,1938年5月4日对外国文艺者在武汉的报道,希望外国文艺者在实地考察中把中国抗战的事迹通过诗歌、文章、小说、电影等文艺形式向世界传播,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
二、《抗战文艺》大众化的“三重”呈现
(一)人民语言:抗战文艺大众化的传播载体
语言是文艺传播的基本载体,也是文艺表达的主要形式。《抗战文艺》通过对文艺大众化的大量探讨,最基本的一点还是基于对于表达方式的讨论。民间艺术是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文艺形式,作品的文艺价值在于新内容的表达上,不在于旧形式的利用上。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宣传需要,新文艺需要通过表达方式的改造而形成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形式的首要条件则是老百姓所最容易接受的。倘若抗战文艺过分执着于文艺专业性探讨,则无法深入民众现实生活,亦不能达到调动人民群众共同抗战的效果。为此,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中认为,我们不能将“艺术性”与“宣传性”分离对立,我们也不能凭空构建出“活的语言艺术”。“五四”以来,中国文艺先驱从“死语言”中解放文学,以活的民族的“语言艺术”代替了旧式文人和官吏书生私有玩弄物的旧文学。此外,发表在第三卷第三期的《我们对于抗战诗歌的意见》中,李华飞认为,“应该把地方语言充分表现在诗中,同时尽量利用旧的语言”。长虹在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中发表《如何用方言写诗》中也鼓励民众采取方言和大众语入诗,使文化语和大众语在实践的融合中产生新的语言。因此,在抗战文艺大众大的传播过程中需扩大民间语言的采用,创造出民众容易接纳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形式。
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语言和文字的分离是亟须克服的问题。罗荪发表在第三卷第七号《创造语言》一文中写道:“必须开扩语彙,从人民大众的日常语言中汲取活的言辞,变革那些附庸在文字词藻之间的陈腐滥调,创造中国大众自己底语言文学。”[5]因此,在广泛宣传抗战的情势下,创造新的语言艺术,不仅是让语言和文字统一起来,更需要创造出表现活的大众化的口头语言文字。罗荪同时举例说明,普希金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是因为他创造了俄罗斯自己的语言,沟通了俄罗斯的民间文艺,用了“自己的”活语言,表现了“自己的”生活。最后,罗荪号召每一个文学工作者,深入民间生活,向广大民众学习语言,汲取鲜活的语言表达方式,才能使语言和文字相互融合,更好地将抗战文艺向人民大众中传播。
(二)小说主题:抗战总基调下的“人民书写”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中日战争格局也迎来重大转变,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曙光逐步显现。在《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的“约稿八章”中明确指出:“本刊欢迎来稿,但必须与抗建有关。”同时在编后记中表示:“因为浮躁与狂热的时代早已过去,热情逐渐内潜于清醒的理性之光里,整个抗战的作风如此,一个文艺刊物的作风亦应如此。”由此可见,《抗战文艺》由初期的文艺服务于抗战主张转变为文艺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格调。
在抗战后期,虽然围绕战争的书写还在继续,但是抗战文学的中心主题已转变为抗战总基调下的“人民书写”,描绘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表现人民群众在长期战争生活压抑之下的所思所想,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表现底层民众经过战争洗礼后的艰难困苦生活和疲惫不堪的心态。例如,巴金在第八卷第三期中发表的《猪与鸡》一文就描写到严老太“两个多月连猪油气也没有沾到”。第八卷第四期躬列射发表的《吃了一顿白米饭》描写林雨生夫妇与黄夫妇的交谈中,折射出不同阶层的孩子在饮食方面的巨大差异:处于生活底层民众的孩子“很少有油在肚子”,而富裕阶层的孩子则“不只白肉不吃,就是瘦的不也高兴吃,要吃头肉”。并且通过小孩子春明编唱的歌谣:“天老爷,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不下雨,吃泥巴!”警醒人们在抗战后期不得不面临阶层鸿沟所产生的社会民生问题。又如,第八期第一、二期合刊中,梅林发表的《疯狂——献给在“大时代”重力下呼吸的女性群》一文中,着重表达女性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生存的艰辛,在生活压力的作用下使个人的精神状态逐渐烦躁不安而近乎疯狂,更有甚者自暴自弃,就此沉沦。同样,贾植芳在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中发表的《人生赋》中展现人们在抗战后期压抑的生活现状,充斥着迷茫而不知所措的生活态度。
抗战后期《抗战文艺》站在“人民书写”的立场剖析抗战后方的群体矛盾和文化冲突。在残酷压抑的战争环境里,有烦躁不安、疲惫迷茫的人,也有大发国难财、醉生梦死之徒。例如,第八卷第三期发表程远的《蚜虫》深刻揭露了后方权贵与商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罔顾民族大义,大肆发国难财以满足个人纸醉金迷、贪图享乐的卑劣行径。从而也揭示出由于抗战“蚜虫”的存在,人民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同时,还要经受官员权贵的巧取豪夺和商人在经济生活上的压榨,尖锐地揭露当时社会阴暗面下的群体矛盾。第九期第三、四期合刊中刊载葛琴的《一堵板壁》,通过描写作者与家人到江边避暑,由于居住空间较为狭窄,负责接待的军官建议拆除板壁拓宽空间,由此围绕一堵板壁“拆”与“不拆”的问题而陷入纠纷。作者借助这一件小事的缩影映射出当时社会本地人与“下江人”、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文化冲突。
(三)抗战诗歌:反映民众现实生活与真实情感
诗歌作为民间文艺最为活泼和最具有强大原始生命力的文学通俗读物,与散文结合可成为散文诗,和戏剧结合可成为歌剧,语言高度凝练富有韵律美,能够集中反映战时社会生活,抒发民众真情实感。为此,全国文协诗歌座谈会在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中登载紧要启事,决定创办抗战诗刊,定名为《抗战诗歌》,内容包括诗歌理论与创作(散文诗在内),民谣小调鼓词诗评以及国内外诗坛消息等。顾颉刚在第二卷第八期上发表的《我们怎样写作通俗读物》中认为,通俗读物的任务是要适应抗战的需要与民众的要求。由于日本军阀是我们“全民族”的敌人,我们须以“全民族”的力量对付它,因此抗战与民众是不能分离的。同样,第三卷第三期整理刊发诗歌座谈会上的讨论中,长虹认为民众是民族抗战的基本动力,诗歌的创作需要准确把握中心事实具体描写,让大多数民众看得懂,进而产生情感共鸣,鼓舞人心,共同抗战。
抗战诗歌是对战时民众现实生活的真实观照。首先,抗战诗歌集中反映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无尽痛苦。例如,平林在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仿小白菜调子的《难童谣》,以朴实直白的口吻写道:“飞机炸呀,大炮轰哟,中国百姓,遭大殃啊”;“鬼子来了,都烧光啊。家乡烧了,没处藏哟,剩下一个,来逃荒啊”;“东洋鬼子,心肠毒哟,杀人放火,真可恶啊”[6]。又如,何容在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战壕小调》中写道:“你小子要是还有脊梁骨,早该跟军阀把脸翻,受了压迫你不敢反抗,来到我国犯野蛮,烧杀奸淫你无所不干,你比野兽还要凶残”,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大众化民间语言和平铺直叙的写作手法,将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民众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一笔一画诉诸纸上。
抗战诗歌以强烈的感情色彩鼓舞中国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第一卷第八期刊载的《抗战歌曲:河边草》,以放牛娃“从早放牛直到晚,无衣无食到处受饥寒,何时何日回家乡”的现实遭遇为背景,用“恨不得,牛群为战马,长鞭变刀枪,号角吹起,进行哟,驱逐敌人,收回故乡,牧童永不流落在它方”的真挚情感表达了中国民众自发奋起驱逐日寇,共建美好家园的迫切愿望。又比如,任钧在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中发表的《战时杂咏——警报声中》流露出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我们诅咒日军敌机的残暴,因为它们蹂躏了我们的国土和虐杀了无辜的同胞。然而我们也感谢战争,正是因为战争将中国人民怀着同样悲愤的心情以前所未有的团结站在一起,同时感到共通的命运。无独有偶,雷石愉在《人生难得这一回》中也认为,日本法西斯的残暴侵略“正好使全民族觉醒”,并且以慷慨激昂和富有斗志的情感号召中国人民积极主动参加到争取民族解放与全人类和平自由的伟大战争中来。
三、结束语
关于如何利用“旧形式”的民间文艺推动抗战文艺向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传播,《抗战文艺》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其中所体现出的人民观对我国在新时代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7]。这充分表明,在新时代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新闻宣传中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推动新闻工作与文艺作品向大众化进程迈进,传播人民正能量,倾听人民心声,凝聚人民伟力,唱响人民主旋律,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扬帆远航。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推动当前文艺工作向大众化方向发展。首先,要让人民群众成为文艺宣传工作的真正主角,在国内新闻报道上深入群众生活,用饱蘸人民情感的笔墨去书写富有大众真实情感温度的作品;在国际上要以人民为出发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新闻传播的国际影响力。其次,要贴近人民大众,积极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使人民群众能够从文艺作品当中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最后,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加深同群众的情感联系,优秀的文艺作品必定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文艺作品从本质上脱离人民大众,那必然不能完整地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同样也不能经过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淘洗而成为时代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