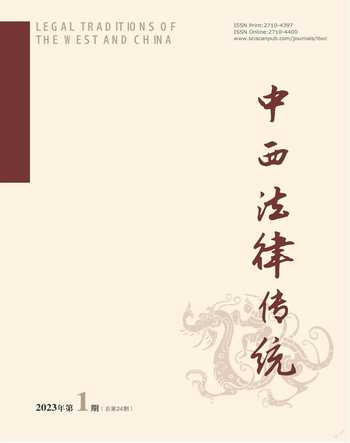先秦时期“乐”文化与儒家政治哲学
2023-12-06范依畴郝辛汇
范依畴 郝辛汇
摘 要|“礼乐文明”是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更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在古代政治思想与实践中,礼乐因素有着崇高的地位与影响力,“礼”与“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礼乐政治”的政治模式。其中,在多数情况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乐”与“礼”相融,作为儒家社会制度与教化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展示了其在政治哲学上的独特作用与影响。先秦时期是“乐”文化的初发时期,这一阶段“乐”文化的演变与政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新生时期的儒家思想,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乐”文化进行继承、诠释与改造,这些活动奠定了日后儒家思想的根本精神与发展基调,塑造了儒家的独特政治哲学。
关键词|礼乐思想;儒家文化;礼乐政治
作者简介|范依畴,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郝辛汇,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禮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记·乐记》)。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礼治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范式,政治上则为“礼乐型”的政治模式[1]。古人将“礼”与“乐”并称,两者都是政治教化的具体内容,共同构成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品格。“乐之道通于天人之际,与礼平行以治世”[2],它们一同作为儒家治平的工具对古代中国社会的运行赋予深刻的影响。徐复观先生将“礼乐之治”定义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3],是历代儒家追求的理想之境;
“礼”与“乐”之间的差异也显示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记·乐记》),与彰显社会差异的“礼”相比,“乐”更具哲学思辨性,是儒家学者追求和谐大同的体现。即使在“礼崩乐坏”后,“乐”也能内化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文明中,“乐”是包含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而不仅仅局限于后世“音乐”这一语词的意涵[1]。在艺术视域之外,音乐与政治相互融合且彼此影响,“乐”对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乃至社会理想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乐”这一视角分析其对儒家的政治思想与治国模式的独特影响,展现出“乐”在儒家政治哲学生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乐”文化的演变与内涵
(一)“乐”文化的地位与历史发展
作为单纯艺术形式存在的“乐”在上古时期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在国家成立之前,人以部落或者聚落为组织单位生存时,“乐”是某单位进行农事、宗教、战争的辅助工具[2]。夏商时期,统治者对音乐加以利用,除自我享乐之外,更多的是利用音乐加强自己的神权统治,取悦神灵、歌颂先王,进而达到威慑人民的目的[3]。这一时期音乐通常使用于大型的祭祀活动中,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宗教政治意识有关[4]。原始社会时期,“乐”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与巫术、礼仪活动相关,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后世,“礼”与“乐”始终作为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共同发展。
西周时期,“乐”在先周乐舞的基础上发展成型,融入了更多的政治元素,“礼”与“乐”的功能从朝拜神鬼走向服务人伦,礼乐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组成部分之一。《礼记·乐记》中记载:“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周公制礼作乐,建立起官方的礼乐仪式;“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和“分封制”相配合,成为维系周王朝政治社会秩序的三大支柱,实现了礼乐社会的建立。但此时的“乐”处于一种侧重实用性价值的工具定位,尚无后世儒家学说所阐述的丰富内涵。周公在对“礼”加以制度化的过程中,“乐”实际上与车服、鼎、爵、尊等一样,只是“礼器”其中一种,用来维护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5]。
西周的礼乐制度从时间上来看仅仅持续三百余年,在王朝晚期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礼乐制度随着王权的衰落而失效。但衰落之后,“礼”与“乐”于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各家学派展开了对礼乐制度的观点讨论,“乐”呈现出制度化、理论化的发展趋势。儒家学派致力于恢复周礼,重建礼乐制度。“礼”与“乐”经过儒家学者的阐释,形成了系统化的思想理论。汉武帝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显学,“礼”与“乐”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广泛、持久、且深刻地影响着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乐”文化的功能定位
先秦时期,音乐最重要的功能是强化统治阶级的统治。周是礼乐制度的成型时期,“乐”文化中蕴含着周统治的基本精神,即“礼治”,这一时期的音乐已经具有了鲜明的阶级化与等级化的特点。音乐被广泛应用在婚娶、丧葬、祭祀等场合,根据所用场景的不同,统治者对乐曲与乐舞的要求也不同。如《周礼》中有关于乐队排列与所用乐器数量的记载,王、诸侯、卿大夫各有规定。对于民间音乐,统治阶级在使用时同样经过了筛选与分类。《仪礼》中描述燕礼的音乐节目有由专业乐工演奏的,这些歌曲的内容为描绘赞美贵族生活;也有由群众合唱的,内容是现实的爱情、劳动生活等[6]。统治者以不同仪式使用音乐的差别来表征等级制度的合法性,他们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的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这些措施亲和并控制宗周与诸侯之间以及宗法等级社会中的政治关系[7],加强了礼乐制度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周王朝的宗法等级秩序。
“礼乐崩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基本继承并发展了周代的礼乐制度。“乐”文化的政治属性得到增强,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尤其被关注。孔子坚持礼乐的等级划分,十分重视礼乐制度以及制度背后所维护的社会秩序,当看到鲁国大夫季氏僭越采用天子所用的乐舞时,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侑》)。“礼”与“乐”作为道德伦理的作用也被孔子推崇,礼乐制度不再只是增强统治的工具,还具有更内化的价值。儒家对礼乐本质进行理性思考,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对礼乐作出了思辨性解释[1],“礼”与“乐”从制度升华为系统性的伦理思想。在“礼”与“乐”之上,孔子探讨了“仁”的精神,“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侑》)。以“仁”为核心的礼乐精神能够引向人的内心世界,用它来实现“内以建立个人的崇高的人格,外以图谋社会的普及的幸福”的目标[2]。
(三)“礼”与“乐”的相通与分异
礼乐制度包括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的等级秩序,以及以“乐”来和同共融“礼”带来的社会差异,是“乐”从属“礼”的制度。“礼”与“乐”一般同时出现,两者作为儒家的伦理符号相辅相成。但与此同时,礼乐之间存在价值取向上的显著差异,正是这些不同能够让两者功能上互补,精神上相通。
“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3]“礼”与“乐”虽然隶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但作为儒家社会制度和教化体系的两端,它们之间存在难以分离的关系。在实际应用上,“礼”与“乐”相伴而生。周时期的礼仪活动需要音乐配合进行,礼乐相合,“乐”遵从于“礼”,并为其服务。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乐”在实践上社会政治性功能衰弱,孔子对“乐”的重新构建让“礼”与“乐”有了共同的精神追求——“仁”;“仁”指的是由个人培育起来的道德意识和情感,被视作“礼”的精神基础[4]。经过孔子阐释后的“乐”从仪式价值转向内向的伦理价值,“乐”与“礼”不仅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成为人格教化的主要内容,能够落实于个人的修养、品质的培养中。
“礼”与“乐”的分异在于其价值取向上。《礼记》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礼记·乐记》),“礼”分别贵贱、长幼、亲疏以维持社会分化,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性;“乐”则通过声音与旋律让人们触发情绪上的波动,萌发出相似的情感,最终追求的是万物和谐的状态。音乐作为艺术形式能够广泛地引起人们的内心共鸣,“礼”与“乐”的对人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礼”从外部规范人的行为,以典章制度的形式来使社会按照秩序运行,并且“礼”与刑罚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礼”带有一定的社会强制力。但“乐”的作用与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内心产生的情感不会受到外界的逼迫,是一种自为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记·乐记》)。
二、先秦时期“乐”文化的政治实践
“乐”的影响力能够折射到不同领域,对人的道德修养、文化教育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培养等都产生显著的影响。先秦時期音乐已经在政治活动中被广泛应用,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在辅助礼仪作为仪式用乐之外,国家行政系统内设置了正式的音乐机构,乐官承担着管理、授学、表演等多项职能,这是音乐与政治教化相结合的结果。
(一)仪式中对音乐的使用
把音乐作为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加以使用的行为,在西周已经具备雏形。西周的祭祀活动属于五礼中的“吉礼”,宗法制、等级制的日益发展使得祭祀与君臣父子的伦理结合更加紧密。相较于前代,祭祀活动的宗教意义减少而现实意义增加。在表达图腾祟拜之外,更多地用于赞美生产劳动。西周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也蕴含在祭祀之中,是其政治纲领的反映。雅乐的使用在周代政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祭祀仪式音乐得到发展,礼乐政治逐渐成型。
西周祭祀的对象种类繁多,范围涵盖了天地鬼神到先王旧臣,这些不同种类的祭祀时间、地点以及程序不尽相同,音乐都需要参与其中。周代礼制涵盖政治、生活的各方面,“乐”除了在政治礼仪场所使用,亦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场所。不同的乐种,所奏之场所亦不同,不能混乱。《周礼》中详细记载了祭祀用乐的具体规范,仪式所用的乐器、歌曲、乐舞都有标准,乐律也有相应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嘉乐不野合”(《左传·定公十年》)。如“郊天”祭祀,是仅能由天子举行的最重要的祭祀,按照《周礼》的规定,“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周礼·春官·大宗伯》)所以祭祀天的仪式需要“乐六遍”才能感召神明,达到礼神的效果。祭祀地示的“方丘”,则“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周礼·春官·大宗伯》),但在仪式的末尾没有“郊天”中天子亲自率人舞蹈的步骤。西周时期宗族观念发达,宗庙祭祀是西周社会影响最大的祭祀活动,需要进行“九献”,也即九次献酒作乐才能进入到乐舞的程序。规范化不同类型祭祀程序之间的仪式差异性,能够区分贵贱、维护礼制,彰显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这一时期,音乐主要是在祭祀中发挥作用,负责请神、降神,安慰取悦鬼神以及烘托心情和气氛,以达到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目的。周代礼乐制度在实践中走向规范。“乐”在仪式中发挥着加强伦常与等级观念的效用,引导人遵守规范秩序,人们的情感诉求通过仪式中的音乐获得抒发。政治制度、礼仪、音乐三者形成了全面的体系,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增强周统治者的政治力量。
(二)治理学政的乐官
《周礼》中记载了西周的官员设置,在春官宗伯下设有大司乐、乐师等负责乐歌舞诗的职务,建立了完整的乐官系统,是西周行政制度的一部分,归属于王朝官制之中。这些乐官除了参与祭祀典礼,也进行政教活动,体现了周王朝政治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乐”是古代最早的教育内容之一,地位最为崇高,是教民之本。乐官负责主持乐教,贵族子弟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作为乐官之长的“大司乐”就是通掌学政的总执事,掌管所有的王宫乐事与乐教。《周礼》中记载“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周礼·春官·大司乐》),乐官承担培养国子道德品质的职能。国子教育是以培养行政人才为目的,行政与学政合一,教育为礼仪服务,对所教对象的品德要求较高,教学内容以礼乐为重。乐师协助大司乐,“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春官·乐师》),乐师培养出的学士成为王朝官员,形成了周时期“贤人政治”的政治传统。
在教育功能之外,乐人也对传承历史作出了贡献,乐官体系中有“瞽蒙”一职,在音乐演奏职能之外,还担任着“讽诵诗,奠世系”(《周礼·春官·瞽矇》)的责任。瞽蒙是盲人乐官,虽然目不能视,但这种生理上的缺陷让他们能够免受外界干扰,对声音保持敏感,因此格外擅长音乐和记诵。吕思勉曾说:“窃疑《大戴记》之《帝系姓》乃古《系》《世》之遗,《五帝德》则瞥暖所讽诵者也。”瞽蒙因其身份得以参与大多数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承着往古的世系及相应的史迹,使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保存下来。从范围上看,瞽蒙赋诵的内容覆盖面极广,但主要是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在没有文字可供记录历史的漫长时期,瞽蒙负担着重要的历史重任。
乐师的另一重要的政治职能是对君主进行劝谏。古代虽然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是通过音乐的讽喻作用,统治者能够进行反省与改进政治实践。西周时期,乐官用音乐议政对君主箴导规谏、发出警示。《左传》《国语》之中,记录了多件乐师讨论政治的事件。前述的“瞽蒙”在传颂历史时会对史事表达评价与见解,达到规劝君主的目的。采诗与献诗制度也能达到讽谏王政的目的,行人所采之诗与公卿大夫所献之诗,最后都汇集到王室乐官之手,由他们来汰选、加工和编辑,然后由瞽史讽诵,用以讽谏天子。
(三)作为政治的反映与评价标准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太平盛世的音乐是安详欢乐的,象征着政治的和谐;乱世的音乐是带有怨恨和愤怒的,政治上混乱无常;亡国之时,音乐哀伤,能够感受到民众的困苦,这就是“音乐通乎政”。
古人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政治状况运行如何能够映现在音乐中,君主与百姓之间通过音乐获得联结,因此音乐也成为朝野间评判政治得失的一项标准。《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天子通过音乐判定民生,了解百姓生活,以民歌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期有名的贤人季札对各国乐舞的评价,将各代兴亡治乱与音乐风格进行联系,以本国音乐预测国运。如“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他认为郑国的音乐过于细弱,百姓无法忍受,所以郑国将来亡国,要比别的国家都早。后郑国果真在较早的时间灭于韩。
三、“乐”文化对于儒家的特殊性
(一)儒家与其他学派对“乐”文化的观点对比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乐”的作用与影响加以讨论分析,其中唯有儒家给了“乐”极高的地位与推崇。其他学派多对礼乐持否定的态度。所持音乐思想的不同反映出儒家学派具有的独特思想内核。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勒令》中,把儒家所提倡的诗书礼乐定义为“六虱”,认为这些学问都是破坏农战、阻碍国家富强、扰乱上下秩序、蚀毁社会治安的害虫,反对“以六虱授官予爵”,否则会导致国家的衰弱。墨家呼吁的“非乐”思想也异于儒家的“倡乐”。墨家的思想中充满实用主义的色彩,生活于社会动荡时期的墨子能够切身感受到民众的贫困潦倒和统治阶层荒淫无度之间的强烈对比。墨子反对声势浩大、劳民伤财的音乐艺术活动,认为音乐会让人沉迷而不顾自己的事业,对天下无益。“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墨子·非乐》),最终得出了“乐,非所以治天下也”(《墨子·三辩》)的结论。墨家所排斥的是王公贵族的音乐仪式,体现出底层百姓的立场,这种对于礼乐秩序的批驳也是墨家学派“背周道而用夏政”的表现。《墨子·非乐》中也有对音乐作用的记载,并不否认音乐给人带来的美感与快乐,但墨子并不从此入手而论乐,而是从音乐在社会中的负面作用入手,这是与儒家的根本不同之处。
道家对于音乐的态度与法家和墨家偏于负面的观点不同,道家同儒家一样追求音乐之美,以“和”为目标。儒道两家的分歧在于道家推崇的是音乐自身的天然规律,批评儒家的“仁义”和“礼乐”,认为“五音令人耳聋”,主张“攘弃仁义”,颂扬“天乐”。“大音希声”,道家中音乐的情感表达是本真无为的,道家眼中儒家的礼乐学说则是丧失自然本性的世俗之乐,与“天乐”存在根本的不同。道家尤为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的思想,对于奉行“无为”之道的道家来说,以外界的教化来学习音乐是违背自然的行为。儒家看重“乐”的工具性价值,道家则推崇“乐”的纯粹艺术性。
(二)儒家学派对“乐”重视的原因
从前述可以看出,儒家与其他学派相比格外重视“乐”的价值,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1.文化渊源
关于儒家的起源,学界说法各异。阎步克教授在《乐师与史官》一书中分析了“儒生与文吏之分立和融合”,指出周代官僚体系中的乐师与儒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出儒“最初当指受教于乐师、并参与以舞祈雨等事的青少年舞人”。将“儒”的源起推于乐师。虽然这种观点存在以偏概全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起源发展中文教系统起到的重要影响,以六艺教人是儒家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而“乐”是六艺中关键项目,极大地作用于儒家的发展过程中。最早的儒者起源可以追溯为殷商时期具备巫祝能力的王室贵族,他们需要熟知的典礼仪式,需要使用音乐,祭祀活动的丰富与频繁促使礼乐文化的发展与成熟。西周时期乐官系统正式形成,大司乐、乐师等是“以诗书礼乐教”功能的承担者,而接受、传承这些教育的学士具备了礼乐修养,被名之为“儒”。对礼乐的尊崇是儒家与诸子百家的显著区别,带有礼乐色彩的文化传统是儒家得以成长发展的土壤。“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使得孔子拥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契机,为儒家学派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
2.实践诉求
“乐”有“合爱”的功能。儒家能够通过具象的“礼乐”这一载体,把浸淫盈融于其间的“仁爱”传承下来。在实践效果上,“乐”通过柔和的方式去影响感染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与道德教化作用,能够缓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对立和社会矛盾,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们接受儒家所提倡的“仁”的精神。从实践范围来看,通用于各类仪礼中的音乐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可以影响到包括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在内的全部社会层级。荀子在《乐论》中详细表述了音乐的教化作用,他认为“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仅凭借“礼”的外部作用难以达到规范人心的教育作用,“乐”的教化效果是体现于无形之中的,积于中的和顺,发于外的英华,具有强烈的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樂”的移风易俗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其他教育科目无法比拟的。
3.价值理念
“和”是古代重要的哲学范畴,早在先秦诸子之前,就发展出了其哲学与美学内涵。古代美学以“和”为美,表现出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的朴素认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是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根本出发点。儒家思想体系中“和”是被追求的崇高价值理想,“礼”调节社会的目的为最终的“和”,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乐”的本质也“可以用一个“和”字作概括。“雅乐”本身代表着理想社会的规范,从外在表现来看,“乐”的器具、音声、调位的潜恰能达到平和协调的效果。“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礼记·乐记》),各类乐器的配合演奏又从内在以义心来纠正人之过失,以感化教人改过。形式背后是礼乐所承载的世界观、伦理观;“乐”秉承天道,与天地自然规律相吻合。“乐”代表着和谐统一的状态,儒家的和谐思想在“乐”文化中孕育形成,同“中庸”的思想一脉相承,彰显天地万物之情理。
四、儒家对“乐”文化的发展改造
通过上文的叙述可知,对于周王朝的“乐”文化各家学派均有自己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之时,也是礼乐文明秩序的重建之际,儒家作为最重视礼乐秩序的学派,对“乐”进行了创造性地诠释与升华,使“乐”从礼乐仪式的规范活动升级为富有哲理性的系统理论,赋予了其精神意义。其中以孔子与荀子对“乐”的讨论最为关键。
(一)“美”“善”“仁”——孔子的音乐观
孔子对于音乐的讨论多见于《论语》《礼记》以及《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内容包括对琴、瑟等乐器的言论、音乐活动以及对礼乐的认识等,主要以“礼乐”为基点进行展开,对“礼乐活动”的评述是体现孔子对“乐”思考的重要维度。于个人而言,孔子自身即为一名音乐爱好者,通晓各类乐器的演奏与音乐的研究,具有极高的音乐修养。他生活于音乐之中,即便于临终之前仍倚门而歌[1]。《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并最后凭借出色的天赋技艺胜过师襄子的经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表明了孔子对于歌唱活动同样热衷;对于音乐的热爱与学习使孔子意识到音乐教化人的内心以及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乐”能够推行“礼”的价值。
孔子尊崇周公,是礼乐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认为“乐”要通过各种礼仪活动实现“合于礼”[2]。孔子的礼乐观是对周礼基本精神的延续,他对于“乐”的改造也是在复古周礼的基础上进行的。先秦时期,诗乐一体,孔子对“乐”文化的继承通过编订《诗经》来进行。在周游列国仍无法实现其政治抱负后,孔子将其事业的重心转为教育弟子与整理文献。孔子不满礼乐的混乱状态,在对《诗经》梳理时,将不符合礼义的部分删减,即《孔子家语》中所说“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
《春秋》”[3]。《史记》与《汉书》都对孔子删诗的做法进行了记载。《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4],《汉书·艺文志》也记载了“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5]。通过删诗,孔子将非礼之乐除去,对礼乐秩序进行修整,孔子将他的行为定义为“正乐”,认为“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在对宗周的礼乐传承与修正时,孔子对“乐”的价值进行了升华。孔子在欣赏《韶》乐后,作出了“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侑》)的感想评价,“美”是艺术层面的追求,“善”则为道德层面的目标,这是他对音乐的两个评价标准。与《韶》乐做对比,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矣。”(《论语·八侑》)孔子的音乐观强调音乐的道德价值必不可少,否则就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标准。在“美”之上,孔子将“乐”的意义扩展到崇高品德的表征,音乐不仅为形式上简单的钟鼓之乐,精神内在上具有“善”的境界。“善”的价值又直接指向于儒家思想核心——“仁”,孔子的所谓“尽善”,就是指“仁”的精神而言[6]。所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最后追求“仁”与“乐”的统一,艺术与道德的融合。这种对“乐”文化的重新解读让起源于宗教活动的礼乐弱化神学元素,梁漱溟先生对周孔之后的礼乐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孔子)把别的宗教之拜神变成祭祖,这样郑重的去做,使轻浮虚飘的人生,凭空添了千钧的重量,意味绵绵,维系得十分牢韧”[7]。孔子将“乐”的深层价值与“仁”进行融会贯通,使得“樂”文化更富有人文色彩,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势。
(二)“礼乐政治”——荀子的“乐治”模式
孔子以复兴周礼为目标对“乐”文化进行了重构,设想出其向往的“礼乐社会”,荀子通常被视为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诠释“乐”文化的内涵,构建出了“礼乐政治”的理想秩序。
荀子“乐”的理论见《荀子》一书,书中专辟《乐论》一章,集中阐释了荀子的“乐论”美学思想,除此之外,三十二篇中其他各篇也不同程度地涉及,荀子“乐论”的具体实践也体现在其中[8]。荀子论“乐”以性恶论为基础,他认为“乐”的本质在于人内在本性的自然发生,情感是“乐”产生的根源。音乐影响人的情感,“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荀子·乐论》),荀子严于“乐”之雅邪之分,有“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乐论》)之说[1],人性本恶,“邪乐”会让人心更加混乱。因此音乐需要符合礼的要求,乐事皆须合礼,才不会流于俗欲。礼乐的教化作用能够让人们过一种合于“道”的生活,这是乐对于人格修养层面的特别意义。
荀子对于音乐的思考不止在个体道德修养上,还与政治进行结合。乐教延伸到政治领域,是荀子“乐论”的一个重要维度[2]。审乐知政,“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莫善于乐”(《荀子·乐论》)。“乐”关乎国家治理,雅乐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如果出现“礼乐废而邪音起者”的情况,则“危削侮辱之本也”,“邪乐”的出现直接威胁了国家的生存。其次,荀子作为先秦各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创造了“礼法”的概念,这样的“礼”更注重规范性与强制性,“礼”用来区分贵贱长幼,通过礼的“区隔”作用,社会成为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的统一体[3]。但是如果仅依靠“礼”的作用,就会导致社会等级关系的僵硬,无法达到和谐的政治目标。“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荀子·臣道》),“乐”能够把被“礼”所分开的各个阶层能动地调和起来,礼乐结合方能使社会和谐。荀子对“乐”作用的重视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理论的威权色彩。“乐”是儒家“道德的政治”体系中关键的一环。儒家的价值观是一种德性本位的整体性价值观,在政治层面追求“道德的政治”[4]。“雅乐”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平和有序、端庄肃穆的音乐是道德的升华,因此荀子提倡人民欣赏“雅乐”,修养高尚的性情。对于统治者而言,通过“雅乐”才能真正领略先王的道德政治理想,贵族子弟需要学习礼乐来明白政治道理,维持政治统治[5]。荀子理论中的“乐”有雅邪之分,“雅乐”能够提高个人修养,在国家层面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乐”与“礼”共同构建了“礼乐政治”的模型。
五、儒家“乐”文化的政治美学
儒家在各个领域都推崇教化的作用,“礼乐”是教化的具体内容,在政治上儒家以达到政通人和的理想境界为目标。“乐”文化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具有独具一格的贡献,造就了儒家的政治传统,并以其艺术特性为儒家政治观赋予了美学价值。
(一)影响了儒家“言谏”传统的形成
中国“言谏”思想萌发已久,西周时期的采诗和献诗制度中所获得的诗,汇集到王室乐官之手,整理后讽诵用以讽谏天子[6]。儒家思想对规谏的作用尤为重视,也是儒家政治理论中极具特色的方面。儒家认为言谏制度是君主专制下王权的内在调节与制约机制。乐人讽谏是礼乐传统中重要的一环,《毛诗》中“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7]。记录了和乐而歌进行言谏的形式以及进谏对于王政的重要性。孔子强调诗歌的规谏作用,后世的儒生更多以规谏为己任,以迂回温和的方式对君主进行劝谏,承担政治责任。
(二)塑造了儒家“道德政治”的价值倾向
“乐”文化影响并塑造了儒家独特的政治性格。礼乐教化的目标就是培育仁德,“乐”与“礼”使儒家政治呈现出重视伦理道义、主张德治的特点。儒家的政治哲学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哲学,推崇人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主的道德水平在政治运行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需要进行教化加以培养。自西周以来形成的乐教传统经儒家继承后获得了长久的发展,并赋予了更多的美德意义。“乐”文化又因为其与“礼”不同的价值指向对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观”有更明显的作用力,倡导道德自律,维护社会秩序的统一。梁漱溟先生认为孔子所期许的道德理想,必须依靠礼乐才能真正启发[1]。
儒家采用宣扬抽象的道德原则这一形式来参与政治,表达对政治理想的诉求。乐官司礼教但不涉身兵刑钱谷之政务,对待现实政治也多采取通过知识分子申说道义的批评立场;但法家的理论则对专制官僚政治实行具体的规划[2]。可以看出与法家相比,儒家因其人治思想,而较少关注具体制度的建立与改革,更多的是注重道德品性等抽象的、主观的方面。
(三)构建了儒家“美政”的政治理想
儒家对于“美政”的追求也是礼乐价值渗透的结果,最早将“美政”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的是荀子。“乐”本身就具有审美属性,是和谐而优美的。“乐”应用于政治之中,带来了“美”的政治寓意。
儒家的政治哲学富有伦理色彩,呈现出温和的特点。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思想的政治架构下,渗入礼乐文化的政治运作,这种伦理建构实际上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表达,最终展现出来的是超伦理而入审美的天地境界[3]。“乐”以其特性在儒家政治制度与秩序的构建之中提供了“美”的情感与力量。
六、结语
“乐”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乐”功能与目的的发展变化能够反映出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变;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乐”参与到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乐”的教化作用。西周时期,“乐”与“礼”共同组成了礼乐制度,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先河。“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礼乐制度受到现实冲击时,儒家在周代礼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继承演化,形成独具特色的乐论,最终成为传统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乐”文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生民之道,乐为大焉”(《礼记·乐记》),儒家理论中的“乐”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还能够承担道德教化的作用,更是治国理政的必要手段。“乐”的政教功能使儒家政治哲学延伸出“美”的向度,刻画出富有审美价值“美政”。“乐”文化以其内化的作用形式,和谐大同的价值追求和广泛深入的影响力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至善至美的“乐”所代表的人文关怀和追求的大同理想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