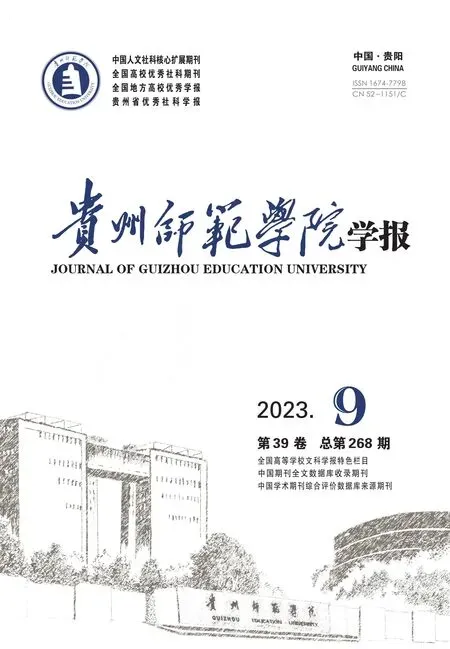南宋世变背景下“词史”作品的形成与特点
2023-11-29邓婷允
邓婷允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引言
“词史”常见的含义有二个,一是对词这一文体整个发展演变历史过程进行梳理的简称,二是对具有历史性特质词作的指称。前者是指词的发展史,即“词”的史;而后者是指词作者有意识地将历史事件如实记录在词作中,反映出词作与历史的密切联系,从词作中可以读出历史的意蕴,从而使人逐渐产生“词史”的观念。“词史”一词最早见于清代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曰:“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渖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1]4这反映了周济对当时“词史”概念的理解。“词史”这一概念虽最早出于周济,但词与史的密切联系早已存在。
“词史”概念的理解具有开放性。本文所论的“词史”主要是词人用词来记录当下的社会事件,以词来书写史实,从这些词中甚至可以触及社会历史的兴衰规律,从而具有“史”的某些意味。与前代词坛相比,南宋词坛呈现出独特的新风貌。在南宋动荡的大背景下,尽管词体创作大多仍集中于抒情感伤之类,但在内容和风格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许多词人用词来记载史实,初步构建起“词史”的大厦,成为南宋词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词史”作品的形成过程
“词史”的本质属性偏向于“词”,词要承担起抒情的基本功能。而“史”的基本要求是真实的记录历史事实,其显著属性是叙事性。从词的发展历程可见,词逐渐从单纯的抒情性向与叙事性相融合的方向转变。词原本是和乐之作,产生于胡夷里巷之中,故地位较为低下。后来经过苏轼“以诗为词”的作法,在无形之中提升了词的地位,使其慢慢向“诗”靠拢。南宋时期,由于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社会时事成为词人书写的重要内容。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词体的内容和境界发生显著变化,“词史”意识开始萌芽。直至清代,词的地位才有了质的提升,学者们将其抬高到与“史”相媲美的地位。
词诞生于燕乐的土壤之中,是在杂糅了胡夷里巷之曲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文学样式,也叫“曲子词”。词在诞生之初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吴熊和先生言:“词本是一种音乐文艺,唐时称为曲子、曲子词、歌词或小词,与燕乐乐曲有着某种亲缘关系。”[2]330词在兴起之初多传唱于勾栏瓦舍之间,之后慢慢进入到文人聚会的酒席筵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3]1。词作为宴会上的一种消遣文体,文人倚声填词,歌姬当场进行演唱助兴,其一开始便形成了柔美婉约的抒情风格。因此,倚声填词与现场演唱一起构成了词的原生状态,奠定了其婉约的基调。在有宋一代,词成为当时的主要文体,文人填词愈加普遍,但词却不受当时文人的重视。“在宋初文人的眼目中,词的作用和地位,‘方之曲艺,犹不逮也’(胡寅《酒边词序》),与‘明道’、‘载道’之文,‘言志’、‘致用’之诗,更不可同日而语。钱惟演自称‘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词’(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等而下之,至于其极。”[4]39-40扎根于俗文化的土壤,使得词亦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以至于出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5]49的盛况。
作为抒写人们性情的抒情性文学而言,词在更深的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幽深的精神世界。但是,由于各种纷繁复杂的原因,词被当成“小技”,仅仅作为侑觞佐欢、应歌应社的工具,无法充分展示出它承载历史重量的重担。但苏轼的词作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比较充分地完成了词的“士大夫化”,形成了一种“以诗为词”的新型创作观念。闻一多先生曾指出,“歌”的本质是抒情的,“诗”的本质是记事的,“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6]153。在苏轼“以诗为词”的观念下,词逐渐从具有抒情性的“曲子词”发展为具备记事性的“诗性”文人词,“词所经历的这种由‘歌’向‘诗’的升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轼创造性地以用典的方式将词引入了文人交际的领域。苏轼充分利用了典故能以精简的核心词汇替代叙述完整故事的强大叙事性功能,将词发展成为北宋文人交际的重要载体”[7]。苏轼在“以诗为词”的言语中透露出当时的文坛已开始正视词体亦能继承诗歌的优良传统,词与诗乃一脉相承,也具有叙事的功能。苏轼在词体的开拓方面具有突出贡献,龙榆生先生赞叹苏轼言:“于词体拓展至极端博大时,进而为内容上之革新与充实;至不惜牺牲曲律,恣其心意之所欲言;词体至此益尊,而距民间歌曲日远。”[8]词在内容上和词风上获得了新的活力,虽离民间歌曲渐行渐远,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从抒情性迈向叙事性的步伐。
南宋以来,直至宋元之际,词体随社会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朱彝尊在《词综》中说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9]8这不仅指出了南宋词在创作技巧上的极尽工巧之能事,也反映了在南宋至宋元易代之际词人将家国之感寄寓于词中。时代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文学的发展。朝代变迁在中国历史上虽非罕见,但南宋世变的社会历史状况是比较复杂而且微妙的。当时的词人面对外族入侵、社稷倾覆之际,大多数词人亲身经历或目睹南宋的沧桑巨变,他们对“词史”的书写自然有着切肤之痛。南宋世变加诸于词人的复杂经历和微妙心态对“词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实际上,在词的发展历程中,词体的内蕴与时代世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叶嘉莹先生曾说过:“中国词的拓展,与世变,与时代的演进,与朝代的盛衰兴亡,结合了密切的关系。”[10]100-101时代的动荡常常是痛苦与机遇并存,词人饱受战乱离别的巨痛,可这也促进词体的发展演变,词人往往将国家动乱的历史记入词中,进而促成了词史创作的萌芽。“词史”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愈为动荡不安,词人可抒发的情感愈深,其承担的思想重量愈为深厚。“词史”中“史”的概念往往是词作内容中反映当下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内容,且试图从南宋词人的词作中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虽然无法明确得出南宋时期的词人已经有了清晰的“词史”意识,但是在“词史”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南宋时期可以看作是一个关键的重要环节,词体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词体的地位在清代达到高峰,清代的文人学者正式将词确立为赵宋的代表文学,将宋词置于无比崇高的地位。至此,宋词正式与唐诗、元曲并为“一代之文学”,这一提法也是到清代才成定论的。[11]在这一过程中,词逐步获得文学话语权地位。词在清代的复苏,是有其特定原因的,谢桃坊先生曾言:“在其深层意义上是反映了当时汉族士人隐密而特殊的政治意图。他们试图以词这种含蕴的文学样式来曲折而巧妙地表达清朝统治下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发现唯有词体是最理想的形式,于是在新的文化条件下改造并利用了它。”[12]209其言下之意是将个人不能言明的情感融入词中,借词意寄托曲径幽深的心境,词中蕴含的政治意图更是加深了词的深度,进一步提升了词的地位。而阳羡词派陈维崧更是将词提升至与经、史同等的地位,“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13]61。此种说法,将诗、词这类文学作品直接比附于经、史这类正统之学,从根本上否决了词为小道的说辞,将诗词的地位抬高到顶峰,可谓是惊人之语。继陈维崧之后,周济更是提出了著名的“词史”一说,词所承载的社会现状和历史重担进一步加重。至此,词已具备一定的“史性”,通过词可以印证历史记载的事实,甚至触及历史发展的脉搏,从而使这些词具有“史性”的意味。
二、南宋世变背景下“词史”书写的思想内涵
宋元易代之际,刘辰翁、张元干、文天祥、张孝祥、刘将孙、朱敦儒、汪元量等著名词人面对社会变局,深受时事刺激,自觉将史实入词,用词来记录当时的历史。此时虽未明确提出“词史”理论,但已表现出“词史”的意蕴。“词史”是词和史相互交融渗透所形成的兼具诗意性和史学性的文学作品,此类作品所叙述的历史多与国家民族相联系,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巨大变革的缩影,而作者将自身感情寓于历史叙事之中,故能产生真诚感人的力量。如刘辰翁《六州歌头·乙亥二月》《金缕曲·壬午五日》《兰陵王·丁丑感怀和彭明叔韵》《兰陵王·丙子送春》《柳梢青·春感》《永遇乐·余方痛海上元夕之习,邓中甫适和易安词至,遂以其事吊之》,张孝祥《水调歌头·和庞佑父》《水调歌头·凯歌上刘恭父》,汪元量《洞仙歌·毘陵赵府兵后僧多占作佛屋》《莺啼序·重过金陵》《六州歌头·江都》《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等“词史”作品。在此基础上,我们试着从词史作品所体现的国家民族灾难、家国情怀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褒奖与讽刺三个方面来探讨词史作品的内涵。
其一,用词来抒写动荡不安的时局,展现国家民族灾难,表现出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国家易代之际,国家民族陷入动荡不安之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达到巅峰,此时的词人不再沉溺于软香细腻的温柔乡中,而是将视线和笔触投向复杂的政局时事之中。动荡的社会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词人的创作,用浸泡着血泪的心去感悟这乱世,用词来记录这罹难的黑暗人间,以词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奏出了时代最激昂的声响。汪元量生逢历史变局,被迫随行北上赴燕。途中,看到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情景,写下了《洞仙歌》《莺啼序·重过金陵》《六州歌头·江都》等词,反映了民族的大灾大难,抒发了亡国的悲痛之情。同样处于宋元易代之际的刘辰翁,经历过元朝灭南宋的时代巨变,作词的手法开始更多地偏向于书写苦难的社会现实。如《六州歌头》序:“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此。”[14]3229该词便是直接记录1275年贾似道在太平州鲁港兵败事件,词人痛心疾首地用词记下这段屈辱的历史,写下了自己的痛心与悲愤。在刘辰翁其他词中,极少像《六州歌头》词那样直白批判历史事实,更多的是以历史事件作为词的背景,但依然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词中沉痛的历史事迹。如其所作的压卷之作《兰陵王·丙子送春》[14]3213: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沈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
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该词作于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时当宋恭帝德祐二年,本词作于虎溪。……本词实是悲叹临安沦陷,恭帝及太后随元兵北行”。[15]231春日时节,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后俘虏宋恭宗和太后北上,宋朝发生重大变故。该词的题意是送春,实则是把“春”比喻成“宋王朝”,从中蕴含着亡国的意味。“海门”暗指文天祥等爱国人士为保家卫国而奋勇抵御外族入侵的英雄之举,但依然挽救不了这颓唐之势。“箭雁沉边”比喻被元军掳去北边的君臣,“梁燕无主”比喻失去皇帝的无辜百姓,“风沙”和“乱鸦”比喻元军。此词开篇先写临安被攻陷之后破败不堪的景象,接着通过暗喻的手法展现出南宋被攻破、君臣被俘虏北上、老百姓无依无靠的凄苦景象,最后表达亡国之痛和飘零之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此词云:“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16]220本词实是悲叹临安沦陷,恭帝及太后随元兵北行。词人在词作中融入当时的历史事实,通过春日的意象,暗喻君臣被掳、南宋灭亡的历史,抒发出对南宋王朝灭亡的痛心。
其二,“词史”作品往往将个人的喜怒哀乐融汇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中,从而形成崇高而伟大的家国情怀。从强调自身情感上升到家国情怀,除了作者本人生命力的催动,更受其所生活时代的时事与政局因素影响。张元干是南渡时期的爱国词人,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其词作不仅仅是表达个人的离愁别绪,更是把自身的悲欢离合放置于国家危难的背景之下,如《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14]1073: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免。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该词是张元干在险恶的形势之下毅然决然送别好友胡铨所作的送别词。词中记录了国家当时的离乱情形,百姓饱受战争之苦。可造成这生灵涂炭后果的统治者却逆来顺受,一句“天意从来高难问”表达了词人对最高统治者采纳不抵抗政策的愤怒。接着写送别友人的情景,在秋天悲凉的气氛中送别友人,道出了离别的痛苦。末尾词人将送别之情进行升华,自身纵有万般无奈,可与国家濒临外敌的丧乱与百姓流离失所的悲痛相比,自身的儿女情长又算得上什么呢?这首词呈现出了那时的士人胸怀天下,以国事为重的情怀。将社会的苦难代替个人的忧愁,展示了那一时代士大夫的风范。宋元之际,刘将孙《沁园春》一词将个体流离之悲凉融入到对国破家亡的悲恸和无辜妇女的同情之中。“记宰相开元,弄权疮痏,全家骆谷,追骑仓皇”[14]3529写宰相贾似道把权朝政,元军入侵江南时无力抵抗,全家仓皇逃命,国破家亡。在此之际,词人并不是只顾自身安危,而是悲痛战乱中女子“二十载,竟何时委玉,何地埋香”[14]3529的悲惨遭遇。此词记录了亲眼目睹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作者对国土沦陷产生深深的苦楚,对战乱中处于弱势的女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具有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感人的爱国人士,他们将国家人民的安危放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形成了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
其三,词史作品强调忠恶观念,爱憎分明,对英雄人物极尽赞美,对宵小之流极力嘲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史”的影响,把褒贬之意蕴含在字里行间。在贯彻了词史意识的词作中,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作者精心挑选的,这对培育民族气节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绍兴三十一年(1161),虞允文于采石大败完颜亮,张孝祥听闻此捷,写下《水调歌头·和庞佑父》一词。词中“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14]1688等句对虞允文的功绩进行称颂。南宋末年,风云动荡,国事飘摇。文天祥在看到国破家亡的惨象时已是痛苦至极,他在《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一词中通过赞赏历史英雄人物表明自己坚贞不屈的决心。《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14]3306一词: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沈,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在元军大举进攻,国家陷入危急情形之际,文天祥赴潮阳抗击元军。在潮阳时,文天祥拜谒了张许庙,并且写下传唱千古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一词。词中爱憎分明,对张巡和许远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推崇备至,将之奉为后世楷模。而对当今“卖国”“降虏”的“奸雄”之人鄙夷唾骂、恨之入骨。这首词借古讽今,古有英雄人物为抵抗侵略英勇抗争,誓死不投降,而今却有奸险之人卖国求荣,屈辱投降之举。词中映射了当时面对外部侵略的形势,朝堂之中的投降派希冀通过割地赔款来获得暂时的缓和,而文天祥等爱国人士追慕前贤的英勇之举,舍生救国。此词通过赞赏英雄人物,痛骂卖国奸雄来表达自己忠贞的爱国之情。特别是“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一句,时刻警醒世人要注重保持自身的贞洁,不要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词中褒善贬恶之义对世人产生极大的影响,更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气节。
三、“词史”书写的艺术特色
词是一种抒情文体,其抒情程度比起诗来,更纯粹,也更细腻。词本身便带有悲剧性的忧患意识和伤感色彩,这可以反映出词在表达情感方面的“真”和“深”。与诗相比,词确实更擅长于抒写那类深微细腻的感情。词在抒情方面是极为细腻的,它擅长描写人类感情中最为深挚的一部分情感,敢于描摹自己的心态,承担起了更多言情的功能,而词中所表现的情感大部分偏向于儿女私情。到了南宋时期,面对历史巨变,民族危机,词人不再沉溺于温香软玉的温柔乡中,受时事刺激,词人开始有以史实入词、以词纪事的倾向,用词抒写沉重的国仇家恨,此时的词坛交织着愤怒的亡国之音和哀伤的忧国之音。在南宋社会历史环境的助长之下,出现一种不同风格的词作——“词史”。“词史”是以历史的叙事性与文学的抒情性相互交融为主要特征,成为词的一个新品种。
大部分“词史”作品具有精炼简洁,含蓄蕴藉的艺术特色,这正是深加锻炼,藏情于内的结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词史作品形成了叙事与抒情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特色,词史作品不仅具有艺术审美价值,更具有以词证史的价值。
词史作品的文字表述简洁,对历史事件的概括性强。这一方面是受到史学家的影响,历史论述的文字要简洁有力。孔子整理修订的《春秋》一书使用的文字可谓精辟简洁,全书记录了242年的历史事迹,总字数16000字左右,每年平均才用六十多个字。简洁的文字背后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事件与评价,后人将这部书的写作手法称为“春秋笔法”。书中不仅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要展现出“一字寓褒贬”的评价。这种简洁精辟的历史论述方法被后来的史传文学继承并发扬光大,刘知幾的《史通》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明确提出了历史叙事要简要精炼,“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17]168。历史叙事的语言贵在简洁,终达到“文约而事丰”的目的。另一方面是词这一文体自身的要求,诗词的语言,追求文字凝练精简。诗词的篇幅使得它无法像长篇大论的文章那般对历史事件进行大刀阔斧地描述,而必须用有限的文字来记录历史事件,而且在简略的叙述之中还要包含作者的思想深度。作者谋篇布局的水平,所用语言的表现力,思想的深意,皆展现在精炼简洁的文字叙述之中。
词史作品追求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道。诗词作品之所以引人深思、余韵悠长,自有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效果。刘知幾在《史通·叙事》指出用晦之道:“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组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17]173晦,即含蓄蕴藉,作者想要表达的深意隐含在文字的背后,这也造就了词史作品内涵的深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词作的传唱。尽管其与词作浅显易懂、广泛流传的特点相悖,但是含蓄仍被视为古代诗词的美学风格。词史作品追求词作韵味的含蓄性,这类作品极少直接表露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批评与讽刺,而往往是通过诗意的语言含而不露地进行批判。从含蓄的语言中渗透出中国人温柔敦厚的理念和品格,“言造物之功,发泄不尽,正以其有含蓄也。若浮躁浅露,竭尽无余,岂复有宏深境界,故写难状之景,仍含不尽之情,宛转悠扬,方得温柔敦厚之遗旨”。[18]21温柔敦厚的风格可以让作者把握好尺度,在褒贬之时可以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这也符合儒家“中庸”的审美理想。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词史之作一般都会比较委婉含蓄,语言耐人寻味。因此,温柔敦厚和含蓄蕴藉成为词史之作的艺术特点。
四、结语
战乱与词史的书写往往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在北宋南渡、宋元之际等历史大变革时期得到了证明。词与历史事件相互融合,既是词本身的选择,也是时代的推动。词从抒情性发展到兼具叙事性,在词的性质上实现了突破,而处于动乱背景之下,词作中融入了当时的历史事迹,使词的内容发生了转变。这在题材内容上确实可以写出意义深远的大词作,但在艺术上却很难达到柳永、苏轼、李清照等大家的水平。“词史”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其优秀卓越的一面,但也存在艺术上普通平庸的一面。本来,战乱的年代正是诞生伟大作品的时机,可是,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词作在整个词的发展历程中显得仍然不够突出,除了受词偏向于柔弱婉约的本性影响外,也与“词史”作品在艺术水平的欠缺有一定关系。但“词史”作品确实给整个词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拓展了词的深度和广度,词的繁荣发展与词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