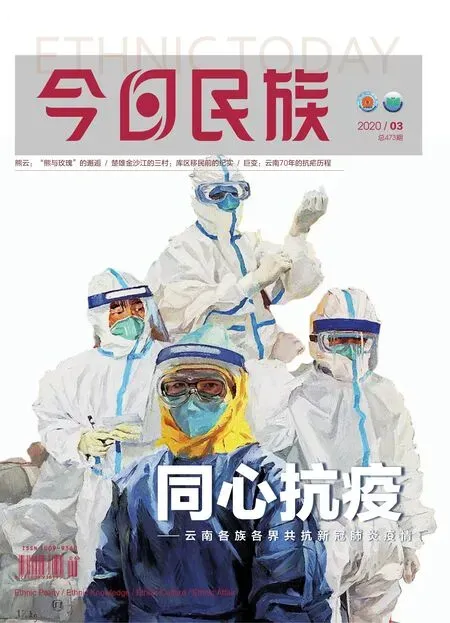瘴气与环境:从云南看当代世界
2020-10-21龙成鹏
□ 文/ 龙成鹏

人类要给自然留出生存、发展空间维持两者的平等和动态的平衡
周琼,云南姚安人。云南省云岭学者,云南大学首批东陆学者、历史与档案学院二级教授(特聘),中国史环境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第12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环境史、灾荒史、生态文明、灾害文化、西南地方民族史、地方文献整理及研究。
瘴气,云南的过去一面

探访陇川户撒的阿昌族家庭
今日民族:周老师,先请教一下,在历史上云南有哪些危害比较大的传染病?
周琼:首先一类是疟疾,第二类是血吸虫病,第三类是鼠疫。鼠疫近现代以来(1896年、民国年间),有几次大的暴发,对云南影响比较大;1896年鼠疫对外传播,从腾冲传到了香港(这点还有争议)。第四类疾病就是麻风病,在云南很多地区流行过,尤其是在滇南、滇东南等地区流行时间比较长,导致很多人伤残甚至是死亡,也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癞病”恐慌心理,是社会影响较大的疾病。
除了这些疾病外,还有伤寒、痢疾、登革热等,以及一些地方性的小型疾病,很多疾病跟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紧密相关。比如大理等地有钩虫病、绦虫病,西双版纳等地方的猩红热等。
今日民族:现代医学进入云南之前,人们谈论较多的瘴气,怎么理解?
周琼:瘴气在云南历史存在时间比较长,对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文化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瘴气是理解云南疾病史和环境变迁的关键点,是一个融合了医疗疾病史、环境史、民族史、人口史、经济史等多个领域的复杂课题。
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如姚永政等人用现代医学研究瘴气,对云南、贵州等地的瘴气区进行了调查、取样、研究后认为,瘴气就是疟疾。我个人认为,瘴气和疟疾不能完全画等号。瘴气是一种由很多种疾病混合在一起的综合的疾病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疟疾,但还包括其他一些疾病,比如伤寒、麻风病。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地,当地人会把麻风算到“瘴气病”里面。做瘴气调研的时候,有些地方把血吸虫病也归入瘴气病。归类的认知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人进入瘴气区吸入那里的空气,喝了含有瘴毒的水,就会得“瘴疠”病,然后肚子就变大了,得“大肚子病”,事实上是血吸虫病等疾病的表现。这也是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的记载来源,即南方很多民族把不能解释和不认识的疾病,都称之为“瘴”。
今日民族:瘴气或瘴气病这个概念,虽然都在用,但意思不一样。您这个观点,我觉得特别重要。那么,从空间、时间(历史)等不同维度看,云南瘴气的多义性有哪些具体的内涵呢?
周琼:云南的瘴气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认知和理解是不一样的。这点我再补充几个例子。比如说,西双版纳橄榄坝、德宏遮放坝、临沧的孟定坝子,以及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比较湿热的地区,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和传播疟疾的按蚊比较多,大家就觉得,得了瘴气病就会“发摆子”(疟疾症状)。但是到了丽江或楚雄,人们说的瘴气病,得的就是“大肚子病”。到了临沧、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人们说的瘴气病就是“癞子病”。都是瘴气病,为什么不同?
现代医学表明,人肉眼看不见的细菌、病毒导致了绝大多数疾病,其中当然包括瘴气病中的各项疾病。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细菌、病毒并不是无所不在,而是聚集在对它们生长有利的环境里。瘴气区实质上就是各种病菌、毒素聚集的地方。所以,表面上看是各地的瘴气病不同,实则是各地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中适宜生长繁殖的细菌病毒不同。造成疟疾的疟原虫及不同种类的按蚊,喜欢湿热的环境,所以气候炎热、水草植被丰茂的地方,就容易滋生各类致病的病毒和微生物、昆虫。一些瘴气区生存有大量传播疟原虫的按蚊,在春夏秋三季所得的瘴气病也多是疟疾。事实上,即使是疟疾,在不同地区及不同类型的按蚊传播的疟原虫也有不同种类,恶性疟疾很容易致死,其他疟疾如间日疟、三日疟等的发病症状各不相同。至于血吸虫病,过去在丽江、楚雄、大理等地发病率高,是因为这些地区当时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适合钉螺的繁殖及生长,少数民族近水的生产、生活方式,钉螺及尾蚴容易通过皮肤、粘膜与疫水接触受染。当时的人将这种无法解释的“大肚子病”称为瘴气,但导致这种疾病的是“瘴水”。
把瘴气区视为不同细菌、病毒聚集的生物多样性较为突出的原始生态环境,并把瘴气放在特定的气候、地理地貌、生态背景下看待,许多跟瘴气有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西双版纳的生态与丽江气候生态不同,其间繁殖的生物、微生物种类各不相同,被当地人都称之为瘴气的东西自然就不同,所谓的瘴气病,当然也就不同。
瘴气不仅从空间看各地不同,从时间看其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云南的瘴气,明代跟清代就可能不一样,因为生态在变化,生物非生物种类在变化,瘴气所含的有毒素生物及微生物也在变化及重组。
所以,我们在用瘴气这个静止的概念讲述不断变化的环境,笼统的描述生态复杂多样的云南时,需要做很多界定,需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考察。
瘴气与地方性知识
今日民族: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瘴气究竟看得见,还是看不见?
周琼:很多经历者记载、宣称瘴气是看得见的,但各自所看到的似乎区别很大。有的说,它是灰色的一股,有的则说是花花绿绿的一片,有的还说,风吹的话,它会动。瘴气是存在的,但它们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肉眼看到,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也已经是不可能证实的问题。不过,当地人凭借生活经验,的确能够感知到瘴气的存在并在现代医学知识传入之前,根据瘴气的颜色形状及其出现、存在的时间及地点,有意识地回避,对当地的瘴气病做一定程度的防治。
今日民族:面对瘴气造成的疾病,或者其他传染病,有哪些防治经验今天特别值得总结?
周琼: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首先是医疗方面,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上已形成了较有体系的民族医药。比如傣族的傣医,彝族的彝医,藏族的藏医,苗族的苗医等等。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即使没有形成较系统的医药体系,但各自都有一定的医疗尤其是用药经验,对当地流行的疾病,有一定程度的医疗应对。
第二个层面,是认知层面。当地人根据生活经验,能够知道什么坝子、什么水(潭、塘、河、井)、什么山(箐)、什么林里有危险,什么季节、什么时候去危险,进而避开危险。这个知识体系比较复杂,不仅涉及对自然、地理的知识,还涉及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

调查西双版纳傣族村子
有的地方认为当地的瘴气,是蟒蛇吐出的,或者是一些像车轮那样大的蛤蟆哈出的毒气,或者是毒蛇、盘结巨大如足球场的螃蟹吐出毒液等。这种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未必经得起现代生物学或学术研究的审视。但其中一些诸如尊重生物生存领地和空间不去破坏、容纳有毒或对人不利的生物非生物存在的观念,值得重视。比如,尽管人们认为瘴气的源头是生活在洞里的大蛤蟆、毒蛇等,但人们并不去把洞堵住,而让这些动物生存在那里;人们认为某个动物跟瘴气有关,但却不把这一类动物杀掉。人们的办法,只是避免接触和侵犯动物的领地,给自然万物留出生存空间。人们在行动上体现了尊重自然的本真理念,对自然界的不同生态现象及生物非生物也保持敬重和宽容。这个认知观念和传统行为,在国家提倡生态文明的今天,我认为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第三种应对,涉及到思想、文化象征层面。包括宗教、民间信仰、禁忌、习俗、法律系统等。一些少数民族认为,人之所以得瘴气病,是村寨里的鬼神作祟,是人们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得罪了神灵,侵犯了圣物,于是要“送”鬼怪、祭祀神灵,这也可以看成是当地人对瘴气病的一种应对方式。人们在鬼神那里,在思想上找到了病因,并由此诞生形形色色的“医治”“应对”“尊崇”的方式。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它对持有这种信仰的人群,产生了一定的心理抚慰作用——在瘴气或者重大的传染性疾病暴发时,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心理的健康。
不同民族的禁忌、习俗,以及当地关于动植物神异性能的认知传统及原始分类等等,同样包含很多应对疫病及客观上保护生物的传统知识。比如,在德宏采访,当地人就跟我说,大蟒蛇有灵性,不能打。他们的解释是,某某人家因为捕杀了大蟒蛇,吃了蛇肉,全家莫名其妙相继病死。很多时候,身边的例子经常与某种传说、传统禁忌互相印证,互相激发,以致禁忌、习俗一代代维持。
整体看,我们今天经常讨论的民族文化,其中一部分直接或间接跟疾病的防治有关。其中,医药知识是这类文化中比较直接、有效的方法,而信仰、禁忌、原始分类等方面则不那么直接,反而很抽象、模糊。但其间包含了各民族对生态环境、对生物、对疾病应对的丰富的传统知识,尽管看似不合理、不理性,甚至是有蒙昧的色彩在内;我们要深入理解民族文化,不可不注意它们与疾病、生态等方面的关联。
瘴气与生物多样性的世界
今日民族:云南的瘴气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周琼:瘴气是特定生态环境的产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历史上并非静止不变。我们的研究发现,瘴气是不断衰减、不断退却的。清末民初,云南境内的瘴气衰减明显,瘴气区域不断缩小,而瘴气在云南最后的消失,则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关于瘴气最后消失的这个时间节点,是我2005-2006年前后集中做的一些口述田野调查中得出来的。比如,访谈当时的初中、高中学生,每当问他们有没有见过瘴气,他们很肯定地说没有,甚至有的都没听说过。三四十岁这个年龄层的,他们说听过,但没经历过。到五六十岁这一年龄层,就更熟悉一些,有的说自己的亲朋邻居见过、得过病。至于七八十岁一辈,则可以很生动地讲瘴气,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他们自己或者亲戚朋友遇到瘴气,有的还因为瘴气病而死亡的。这些例子,在我的《寻找瘴气之路》(刊《中国人文田野》第1-2辑)的调研报告里有详细的描述。
今日民族:瘴气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周琼:瘴气的消失,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及产生瘴气的多样性生物的减少及灭绝。瘴气的产生及存在,一般都具备下面这些条件:生态环境比较原始,生物多样性特点比较显著;气候炎热、湿润,如河谷地区;地理空间上相对封闭,空气流通性差。随着气候和生态的变迁,这些条件正在消失。气候的干热化是全球趋势。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趋势也很明显。在云南,随着工业开发、森林面积的缩减,生态环境及其景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云南的元谋为例,明清时期瘴气还很严重,明代杨慎的《元谋县歌》如此写道:“遥望元谋县,冢墓何累累。借问何人墓,官尸与吏骸。山川多瘴疠,仕宦少生回。”但是森林植被的破坏,致使元谋气候及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干热化让这里瘴气自清代中后期之后逐步消失。
另一个原因,当然离不开近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前面提到的几种典型的、危害比较大的疾病的消失,都与此有关。如疟疾及麻风病、血吸虫病、鼠疫、伤寒、痢疾等以前无法防治的疾病,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作为重点疾病进行防治,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及医疗人员,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及成效,各民族对这些疾病从陌生到熟悉,从束手无策到可防可控。各民族地区没有了这些疾病,作为无法解释而统称的瘴气,在人们的意识及思想里的存在感,也就慢慢减弱,无论在事实层面,还是认知层面,都逐步退出云南人的视野。
今日民族:对人类有害的瘴气的消失,与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有关。但从环保或者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持又是积极鼓励的价值观。那么,生物多样性要多到什么程度?我们要建立怎样的价值观?
周琼:我们应该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其生存和发展,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一方面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人类为中心和以生态为中心,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我认为,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不可取。
强调人类的利益,为此不惜牺牲环境,那人类最终也难逃自然生态的惩罚。因为大自然中的确藏着很多危险,微生物及病毒的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危险的要素,是有独特的生存及活动区域的,不去打破、不去触碰,它们相对是比较平静守法的,一般不会胡乱越界活动。但如若其生存空间被打破、其生态系统被破坏,一旦被释放出来,人类即使暂时抵挡住,攻克了治疗难关,代价也会很惨痛,并且未来依旧会存在各种潜在的、未知的危险,防不胜防。相反,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强调环保主义,忘记了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则人类生存和发展,该如何安放?因此,人在自然界中该处于什么位置,该如何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相处,该具有什么理念及制度,该怎么确定我们的行为准则和习惯,是人类应该思考的。目前,生态文明建设提倡的“人与自然共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与自然朝向文明共处方向发展的愿景。而且一个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应该比一个粗放发展的社会更有能力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就目前而言,我们应该慎重地思考、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在自我发展的时候,要给自然留出生存、发展空间,维持两者的平等和动态的平衡。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全世界主流声音,都支持这样的主张,只是在具体的实践上,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