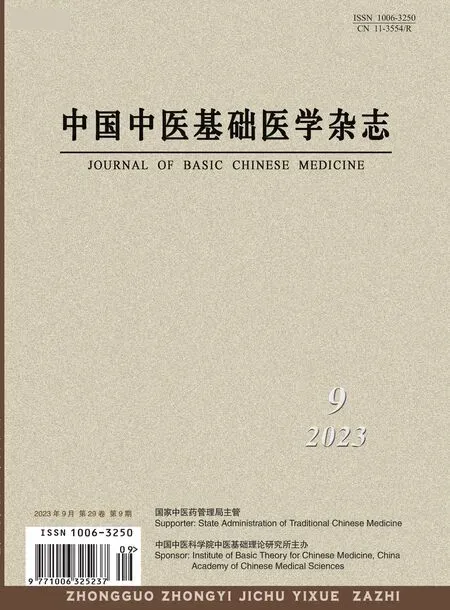从“肝藏魂”论治儿童NREM觉醒障碍❋
2023-11-19马金叶姜永红刘旭华樊秋月
马金叶,姜永红,刘旭华,李 赛,樊秋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发生在非快速眼动(non-rapid eye movement,NREM)睡眠期的觉醒障碍,是由深睡眠中的不完全觉醒所致,包括意识模糊性觉醒(confusional arousals)、睡行症(sleep walking)和睡惊(sleep rerrors)。觉醒障碍时感觉传入受阻,其对外界感知功能降低,认知反应下降。他们很难被唤醒,或被唤醒后的意识也易呈现混乱状态,并对前次发作部分或完全遗忘[1]157。有研究表明,3~13岁儿童中意识模糊性觉醒的患病率为17.3%[1]159。上海地区学龄期儿童睡行症发病率可达1.93%[2]。有报道认为整个儿童期睡惊症的总体患病率可达56.2%[3]。通常西医治疗包括基本的睡眠卫生建议、深度放松以及认知疗法等,儿童很少应用精神类药品进行治疗。若发作频繁且严重,受伤风险较高,则可使用药物治疗,通常是慢波睡眠抑制剂或是抗抑郁药物等,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中医药对小儿觉醒障碍的机制及治疗有着独特的认识。中药整体辨证,用药灵活,对于该病的治疗有着独特的优势。我们通过大量临床观察发现,存在NREM睡眠期的觉醒障碍的患儿大部分可从“痰火内扰,肝不敛魂”论治,并且采用清肝调神的治疗方法,常可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
1 古代医家对于该病的认识
古代医家对于梦飞、夜魇、梦魇等讨论较多,对于睡行的阐述较少。《救生集·急救门》中“中恶鬼气”症,描述了一种夜间到处行走的病证,“其症暮夜或登厕,或出郊野,或游冷室,或行人所不至之地”,此处所述似与睡行类似。明代李梴《医学入门·论伤寒杂证》中有“但睡中或欲起行,错言妄语”[4]的描述。古书中对儿童睡惊的叙述较为丰富。曾世荣《活幼心书·夜啼四》有云“时时若有恐惧……两手抱母,大哭不休”[5]。其描述了小儿夜惊的表现,并将其归因为“误触神”。《幼幼新书·中客忤第二》不但详细描写了睡惊发作时的临床症状并认为客忤就是睡惊症发病的原因,同时区别了客忤与痫证、痉证[6]。可能由于意识模糊性觉醒通常和其他睡眠问题同时出现,常被古人忽略,并未见古籍中有相关描述。“中恶鬼气”与“客忤”同义,均是指人体感受秽毒或冒犯非常之物。说明古代对于睡行、睡惊这种觉醒障碍,多认为是感受不正之气所致。
2 “肝藏魂”与NREM觉醒障碍
2.1 “肝藏魂”的理论依据
魂是阳气充盛到一定程度所生,主动主升。“魂者阳之精,气之灵也”[7]。《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云“心神总统魂魄,并赅意志”。魂随神往来,受心神统摄。魂决定人向外表现的性格、气质等特质的,同时也是人感受外界信息并进行处理、反应、学习的物质基础。有学者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探讨中医“五神脏”,认为魂与认知心理模型中提取和输出认知信息的功能类似,因此肝魂具有提取和输出认知信息的生理特性[8]。《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有云“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肝为魂之寄篱,肝脏功能会影响魂的活动,肝之疏泄功能正常是魂往来运动的条件。《灵枢·本神》曰“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悲哀太甚伤肝,肝伤则魂伤,魂伤则致精神狂妄而不能精明,言谈举动失常。肝血充盛则是魂舍于肝的物质基础。《灵枢·本神》有云“肝藏血,血舍魂”。又有“魂,肝之清阳,赖血以养”[9]之论(《血证论》)。阳魂依靠精气血滋养,当精血充盛,肝有所养,魂得所充,夜卧时血归于肝,则魂亦归肝。
2.2 肝魂与睡眠的关系
《血证论·卧寐》“人寤则魂游于目,寐则魂返于肝”[9]。当白天时或人体清醒时,魂在脏腑之外,机体的知觉、思维活动相对活跃,表现为觉醒行为,使人能够发挥正常的认知和反应功能。而当夜间来临或人体入睡时,魂在神的引导下归于肝脏,机体的知觉、思维活动显得相对静止,表现为睡眠状态。《太乙金华宗旨·元神识神》亦有云“魂昼寓于目,夜舍于肝,寓目而视,舍肝而梦”[10]。贾竑晓教授认为肝魂能够连续地提取和输出多角度的认知信息,为思维的进程提供了导向,而肾志主藏,古有“肾藏志,专意而不移”之说,能聚焦信息于某一点或某一类型。故而从认知心理模型来理解睡眠与觉醒的机制,肝魂从肾志中提取“睡眠”或“觉醒”信息,为这一机制的重要因素[11]。
2.3 肝魂与觉醒障碍
现代医学认为患者觉醒障碍时高级认知功能缺失,意识不清,表现为无目的性的自主行为。实质上是觉醒障碍时不同大脑区域功能的交错,并伴睡眠惯性和睡眠状态不稳定。有研究提示,意识模糊觉醒发生时,海马和相关额叶皮层已进入睡眠状态,而运动皮层等仍活跃或清醒[1]161。中医则认为肝魂具有负责认知信息提取和向外输出的认知心理特点。当肝魂不能正常归舍于肝,魂游于脏外,发挥部分认知功能,则会表现为“睡眠-觉醒”状态的混乱,出现觉醒障碍。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觉醒障碍的启动因素有许多,睡眠剥夺与情景压力是最强的启动因素,另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环境因素等也会诱发觉醒障碍[1]160。而从中医理论来讲,肝受邪气侵扰,魂不归于肝,则易发生“睡眠-觉醒”问题。《赤水玄珠·怔忡惊悸门》言“卧而惊者属肝,卧则血归于肝,今血不静,血不归于肝,故惊悸于卧也”[12]。邪扰肝脏,致使肝藏血功能失常,则易发生睡中惊悸。《柳宝诒医案》云“人身魂藏于肝,肝有伏热,则魂气不得安其舍,而浮越于上”[13]。六淫邪气或机体内在病理产物如风、痰、热、瘀、湿等影响肝脏疏泄、藏血功能,魂无所归,游于脏外而致诸多病变,以致夜惊、梦游等症。
气血不足而发生“睡眠-觉醒”问题。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虚劳喜梦候》云“夫虚劳之人,血气衰损,脏腑虚弱……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14]。若血不养魂,则魂不内收则卧寐不安。亦有《景岳全书·卷之三道集》指出“肝气虚则魂怯而不宁”[15]35。《血证论·卷二》有云“肝经气虚,脏寒魂怯”[9]。肝虚则魂怯,精神耗散,梦寐不安,易醒易惊。清代张璐亦认为是“肝经本虚,虚风内袭,所以魂游不定”[16]。何梦瑶《医碥·杂症》有云“血虚则心之神无所依,肝之魂亦不藏。五脏之热,皆得乘心而致惊”[17]。由于肝血虚,血不养魂,魂失血之所舍,或加之邪气侵扰,则发生睡惊之症。
3 小儿觉醒障碍之病机
3.1 小儿禀质——阳气稚嫩,神魂易扰
《育婴秘诀·五脏证治总论》云“小儿初生曰芽儿者,谓如草木之芽,受气初生,其气方盛,亦少阳之气方长未已”[18],小儿体禀少阳,生机勃发,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医学衷中参西录·治小儿风证方》提出“盖小儿虽为少阳之体,而少阳实为稚阳也”[19],更是强调了小儿少阳阳气稚嫩的特点。宋代钱乙于《小儿药证直诀》提出“小儿本怯”,意指小儿先天怯弱,禀质不足,易惊多恐。而觉醒障碍最常于童年起病,青年后发作减少。小儿稚阳之体,神气软弱未定,阳魂易扰,感受不正之气或接触陌生人,神气受扰,精神不定,而致睡中惊跳,惊啼不止,睡中游行等症。
3.2 本病病机——痰火内扰,肝不藏魂
儿童觉醒障碍病位在肝,痰火内扰,肝不藏魂是其主要病机。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脏腑娇嫩,神机清灵,魂魄质弱,易受饮食、节气、物候、起居影响。如小儿因外邪、惊吓、情志不舒等致气机不畅,津液停聚而内生痰浊,气郁不解,郁久而化火,则生痰火,郁火不散,扰动肝魂,加之小儿后天失养,精血不足,血不藏魂,最终使魂不能归于肝,眠时肝魂游于脏外。肝魂从肾志中提取“睡眠”或“觉醒”信息功能异常,有时亦会伴有入睡困难,甚至表现为“睡眠-觉醒”状态的混乱,出现觉醒障碍。
《素问·痿论篇》云“肝主身之筋膜”,而四肢运动,又赖筋力所为,故肝的功能又会影响身体运动。当小儿突受惊吓,或客忤,痰火内扰,肝魂不安,动扰心神,睡中觉醒不全,虽卧眠于床榻,或出现坐起,离枕环视,发为意识模糊觉醒;或下床行走,发为梦游之症。深睡中突然惊恐,尖叫,运动、言语错乱,发为睡惊。
3.3 相关脏腑——心神与胆决
《类经·情志九气》云“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该志意”[20]。《四圣心源·天人解》曾有“神发于心,方其在肝,神未旺也,而已现其阳魂”之论[21],说明小儿神机未全之时,魂最先随神而生,二者关系密切。《素问·举痛论篇》中有云“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故如小儿为外物所惊,则心神最先受扰。心神掌控最高级精神活动,魂是在其支配下活动。如心神受外物惊扰,则肝魂亦不能免其扰。当惊吓伤神,或心血不足以荣养心神,或心经热盛,心神受扰,亦会影响肝魂。
肝与胆相表里,共主枢机,且胆主决断,定“五志”,胆虚神怯则易恐易惊,如《景岳全书·卷之四十谟集》认为小儿惊啼多因“小儿肝气未充,胆气最怯”[15]485。而胆气不宁,痰气烦扰,则症状多变。正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惊悸证治》所载“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心虚烦闷,坐卧不安”[22]。
4 清肝调神以治觉醒障碍
《素问·病能论篇》有云“帝曰:善。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脏气耗伤则睡卧不安。中医治疗儿童觉醒障碍应积极祛除影响肝藏魂的痰火,调补肝之阴血,使魂有所归,魂有所依,养心调神以定其魂。
小儿觉醒障碍应治以清肝化痰,敛魂调神,临床可选用胆南星、竹茹、姜半夏、茯神、菖蒲、远志、钩藤、白芍、百合、灯心草等。
4.1 胆南星、半夏——清热化痰,力专祛邪
胆南星为天南星与动物胆汁共制而成的炮制加工而成,其味苦、微辛,清肝化痰息风,因天南星善降气化痰,但辛而不守,故胆汁制其性燥急,兼清相火;姜半夏善治各种皮里膜外之痰湿、气滞,气行痰化则邪除寐安,正如《本草害利》言其能“宣通阴阳,和胃安卧”,以助胆南星清热化痰。二药力专祛邪烦扰,使热清、痰化、气行,以使肝不受邪,血静魂安。
4.2 竹茹、茯神、菖蒲、远志——祛痰利气,魂归神安
竹茹善痰火内扰之证;茯神健脾益气,更能宁心安神,叶天士《本草经解》谓“开心益智,安魂魄,养精神”[23],为治疗睡眠问题的要药,茯神又可健脾祛湿,助半夏祛痰。菖蒲、远志二者性用相似,祛痰开窍,宁心安神。《备急千金要方》中治疗安神定志诸方即常用菖蒲、远志药对。黄元御《玉楸药解》中云菖蒲“开心益智,下气行郁……除神志迷塞,消心下伏梁”[24],力善行气祛痰而醒神,远志则“开心利窍,益智安神……辛散开通,治心窍昏塞”。上诸药配伍,利窍安神,能使痰邪得除,气机得利,肝魂得藏、神得安,夜卧以宁。
4.3 钩藤、白芍、百合、灯心——柔肝敛阴,清心除热
钩藤清热平肝,息风定惊;白芍柔肝敛阴,兼以养血;百合养心安神,《本草述》中言“百合之功,在益气而兼之利气,在养正而更能去邪”[25]。钩藤、白芍、百合三药配伍柔肝养血,使魂有所藏,神得以安。灯心草除心经烦热安神兼利小便,使邪热有出路。诸药配伍使痰热得清,魂有所舍,神得以宁,睡眠得安。
4.4 详参机变,临证加减
小儿证候多变,临证时需沉心思辨,灵活加减药物,才能效如桴鼓。如夜醒频繁,惊悸恐惧甚者,可加龙齿、珍珠母、磁石重镇收涩之品,以镇惊安神,以助肝敛魂;烦躁易怒、痰火较旺者,可加郁金、天竺黄清肝化痰,以除痰热之邪,使魂安神静;神怯胆小者可加当归、熟地黄、小麦以补气养血,血足魂藏;如体禀不足,难以入睡者可加熟地、柏子仁、酸枣仁,以调补肝肾,安神强志。
5 验案举隅
患儿,男,7 岁,2020年9月18日初诊,主诉:夜间惊醒2月。患儿2月前晚上在户外玩闹时受到惊吓后出现夜间惊叫,哭闹,有时大喊“不要”,有时喃喃呓语,睡中睁眼、坐起,每周3~4次。多在睡后1小时内发生,一般持续3~4分钟,醒后不自知。曾于外院就诊,脑电图检查未见异常。患儿服用“维生素B12、葡萄糖酸锌”2周后病情未见好转。2020年9月以来患儿发作频繁,近一周来每晚发作1次。日间时有易怒,情绪烦躁,神疲乏力,易受惊吓,面色欠华,胃纳可,大便质干,小便黄,舌边尖红,苔薄白腻,脉数。父母无梦游症史。中医诊断:夜惊症(痰热内扰,心神不安)。西医诊断:睡惊症。治则:清肝化痰,潜阳安神。处方:胆南星4 g、姜半夏5 g、竹茹6 g、菖蒲6 g、制远志4 g、郁金6 g、天竺黄6 g、钩藤5 g、百合9 g、生白芍9 g、灯心草3 g、琥珀2 g、龙齿15 g、珍珠母15 g。中药免煎颗粒,予7剂,每日1剂,晚七时温水冲服。2020年9月25日二诊:家长诉患儿服药后病情好转,服药后1周发作2次,且发作时间缩短,但仍有神疲乏力,易受惊吓,胃纳欠佳,小便调,解便顺畅,舌红,苔薄白,脉细数。处方:上方加大枣9 g、酸枣仁5 g。予14剂,用法同上。2020年10月10日三诊:家长诉患儿近日稍有入睡困难,胃纳一般,二便调,舌红,苔薄白,脉细数。处方:上方加首乌藤9 g。予14剂,用法同上。随诊2月家长诉患儿未再发生睡惊,入睡正常。
按:本病患儿症状较重,睡惊伴有意识模糊觉醒。发病前收到惊吓,患儿睡中惊叫哭闹,且平素时有烦躁易怒,便干溲黄,舌红苔黄腻,当为肝火较旺,痰热内扰魂神,故治当清肝化痰与安魂定惊合用,敛魂调神。郁金行气解郁,《本草备要·草部》谓“凉心热,散肝郁”[26]。天竺黄清热豁痰,宁心定惊。二者配伍,气行痰消,共助胆南星及姜半夏清热化痰,清泻肝火。琥珀入心、肝、小肠经,可定惊安神,《本草经集注·草木上》谓“主安五脏,定魂魄,杀精魅邪鬼”[27]。珍珠母质重,善平肝潜阳,安神魂。龙齿主入心经,长于重镇安神,清热除烦。龙齿、珍珠母配合琥珀镇潜浮越之火,定惊安魂,正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上》所论“重:怯则气浮,欲其镇也,如丧神守而惊悸,气上厥以颠疾,必重剂以镇之”[28]。因小儿体禀少阳,以阳气引导“生发”为主,阴相较于阳而不足。病程日久,阳邪同样也会耗伤阴精,初诊时,邪气较旺,使阴血不足不显。二诊时,患儿肝火痰热较前稍清,阴血不足之象才现,故予大枣、酸枣仁补养肝血,宁心安神。三诊时,患儿出现睡眠困难,此为痰火烦扰心肝日久,肝魂游于脏外,以致阳不入阴而不寐。故以首乌藤养血滋阴,安神定魂,引阳入阴。诸药合用,使肝火得清,痰热得除,邪已尽除,阴阳自和,故肝魂得有所归,心神得安,患儿得以睡眠如常。
6 结语
儿童觉醒障碍是儿童睡眠过程中常见事件,属于非器质性的睡眠障碍,一般不发生严重的问题,但通常会影响孩子甚至是其他家庭成员的睡眠质量,并引起家长的焦虑。中医对睡眠障碍治疗经验丰富,除了可以选择内服汤剂,还可选用推拿、穴位敷贴、灸法、捏脊等外治疗法。“痰火内扰,肝不藏魂”与小儿觉醒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从肝魂论治儿童觉醒障碍,并不只强调清肝安魂,更有调肝、养肝以敛魂,重视肝魂与心、胆的关系,配合安神、养神,清胆、化痰,使脏腑和谐,五神各司其职。此外,对患儿进行及时安慰,疏导不良情绪,避免刺激不良心理诱因,促使患儿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对于该病亦有较好的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