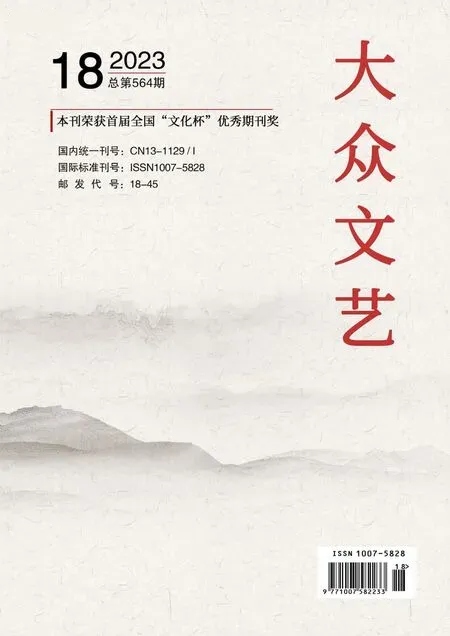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真实呈现与艺术表达
2023-11-15张嘉慧
张嘉慧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000)
一、当代历史题材纪录片发展现状
历史题材纪录片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人物或物件进行表述。用影像的方式通过视听语言对历史和文化进行折射,使当代人对其认知和反思,其纪实性、客观的特点,在中国文化大力发展的语境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11年,我们国家拥有了第一个纪录片频道,让纪录片成了传播形象、发展文化、承载历史的重要渠道。在央视纪录片频道中,历史纪录片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播出量和收视率都稳居高位。随着播出量增大、种类增多,拍摄手法叙事手法更加多样,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不再是唯一的目标。
市场需求的刺激以及广电总局的政策驱动,历史题材纪录片发生了很大转变。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为纪录片专门设置了“纪录单元”,由此为纪录片创作者以及整个纪录片市场注入了对外创新输出的动力和对内学习输入的活力。《二十二》院线上映,虽然票房不如同年上映的《战狼2》《羞羞的铁拳》等商业片,但历史题材纪录片从此进入的观众视线,对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呼声和期待也是越来越高。
除了传统院线和电视媒介外,互联网平台突破了传统媒体资源有限、受众较窄、创新困难等瓶颈,储存量大、互动性强、受众年轻化、制作步骤简单等互联网平台特有优势更加有利于优质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一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央视播出时并未引起很大热度,而在B站上的播出才让其迅速走红,国产历史题材纪录片也是从那时开始成为“网红”。
二、新纪录电影与历史题材纪录片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纪录电影开始重新思考与使用“虚构”这一表现手法,称为西方新纪录电影。21世纪初,中国纪录电影学者开始了对西方新纪录电影的关注,[1]“虚构”手法的使用让中国浩瀚漫长的历史可以展现的时空得到了扩展。新纪录电影激发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表达欲望,对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新纪录电影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西方纪录电影出现了一个新词——“新纪录电影”。美国电影理论家林达·威廉姆斯以“新纪录电影”一词概括创作界的新倾向[2]。当时出现的一系列影片都不避讳使用“操纵性手段”,由于技术的更新迭代让镜头下的事物越发真假难辨,因此纪录电影创作者们会刻意创作出满足观众期待中的真实的镜头,例如《证词》《细细的篮线》《罗杰和我》等影片。
《证词》的导演莱兹曼把自己拍摄电影时运用的方法称为“对现实的虚构”,这种“虚构”是不同于故事片的,纪录片的虚构在于过去事件已经无法自动浮现时,为了讲述已经发生的事件而通过各种手法将已经不存在的事物搬上荧幕。单万里在《纪录电影文献》中认为“新纪录电影”的“新”,在于不再赞同真实电影以及其他纪录电影流派对于“虚构”的否定,“新纪录电影”是同意且乐于采取各种手法来达到认清过去事件的意义。
(二)新纪录电影对历史题材纪录片影响
历史题材纪录片在新纪录电影思维的影响下,在20世纪末成为西方纪录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新纪录电影对“虚构”手法的使用让纪录电影可以展现的时空得到了扩展,激发了人们对于探索过去的好奇心。新纪录电影对人类认知丰富和探索意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影响下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这一类型增进了人们今夕认知、了解社会、发掘自身价值的兴趣。
威廉姆斯在《没有记忆的镜子》中就如何表现难以表现的历史进行过细致的分析,《蓝色警戒线》用表现主义的风格进行场面的搬演,坦白的谈话让真实从谎言的拆穿中显露,而《证词》是通过采访将记忆重新刻画,用曾经发生事件的场景体现出屠杀是如何让他们的生活成为今天的样子。斯通的《刺杀肯尼迪》模糊了故事片与纪录片的界限,这种界限的模糊对历史题材纪录片影响至今。
历史题材纪录片虽兴起于西方,但在中国的纪录片中也占领半壁江山,不仅在央视频道中占比高,在互联网语境下也并不逊色于更加新颖的视听形式。如历史题材纪录片《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从特定的历史时代、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中出发,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其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加以判断和认识,纪实影像成为传承这份记忆的最直观的介质,然而特殊时空使过去注定难以复现。林达·威廉姆斯曾表示“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虚构的手段以达到真实”。因此影片运用了可以体现真实又能加深人们理解的方式,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逻辑与史实相统一的方法进行创作。
追求真实是纪录片诞生的意义,有限的历史资料来还原真实使成为信息量巨大的视听作品,是历史题材纪录片最大的难题。在新纪录电影的影响下,并伴随着社会语境改变、社会矛盾改变以及大众审美需求的改变,当今为呈现真实而运用的手法愈加多样。
三、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真实呈现
历史题材纪录片是依据历史资料,严谨地对历史事实进行挖掘,因而历史题材纪录片的首要条件是历史真实。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还原和呈现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主流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方有人物访谈、文献资料、旁白解说、情景再现、虚拟技术重现等,其手法下创作出的真实感赋予了历史题材固有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使命。
(一)人物访谈
运用采访方式还原历史真实的代表作《证词》讲述了犹太人被屠杀的战争灾难,不同于对同类题材期待的搬演手法,该影片并没有进行场面的重现来达到产生视觉冲击的目的,而是只通过采访,在采访中叙述、回忆悲惨的屠杀历史,伴随着对讲述地点场景当下的情况进行记录。
采访对象是历史的亲历者,这是比文字图像更加生动和更加信息丰富的,除了语言外采访可以记录人物在叙述时的表情与动作,不同采访的场景氛围也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比如幸存者得知当时被带到毒气室即将被毒杀时,因回忆产生的痛苦情绪为采访语言增加了真实感受。观众出于亲历者信任的心理让人物访谈这种复原历史的手法以真实为基础,产生了心灵的震撼。
(二)情景再现
纪录片在创作中会由于受到建筑遗迹,历史资料完整度等因素的影响,使纪录片的真实感无法被广大受众认可,因此需要进行场景还原、情景再现的手法丰富信息量,还原逻辑性,为相关历史事件有更全面的呈现。在20世纪末,艾罗尔莫里斯就采用过情景再现的手法,创作了《细细的蓝线》这部影片。打破了剧情片与纪录片无法融合的固有观念。将每一个人的证词都进行再现拍摄。罗生门式的结构和情景再现的手法使纪录片丰富了真相的层次,从而使人们感受到更加接近真实。
纪录片《故宫》也是一个情景再现的典型案例。故宫作为精神文化艺术的符号集中体,承载的历史时空无法重现,因而其中的工艺、人力、结构、皇家故事、艺术等等,需要通过情景再现的手法得以呈现。除了展现真实的历史情况外,还考虑到建筑本身的氛围,承载的历史厚重感,因此用情景再现的手法能够打造在故宫背景下所产生的特殊气氛,能让受众对古代建筑工艺和历史脉络有更加全面的观察,从而被带入历史时空,用情景再现的手法打造出时空真实感。《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中演员表演尽也可能真实地还原了人物的表情、动作和语言,使观众了解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的产生与发展。如淳于髡在齐王沉迷声色时,眉头紧蹙、欲言又止,特写镜头使人物面部微表情尽显;李斯与韩非初次见面因身份的巨大差别令二人表情尴尬、行为局促,演员表演惟妙惟肖。角色扮演不仅复原了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物形象,还还原了人物当时的心境。以此给予观众沉浸历史的移情感受,将观众的情感从当下世界召唤进历史故事之中。
(三)虚拟技术重现
《无声的功勋》运用解说词、历史资料、情景再现、数字技术以及微缩景观和沙画等创新的技术展现了隐蔽战场的斗争,这部纪录片除了传统地运用史料和情景再现以外还注重表达的多样性。创新运用微缩场景、沙画、手绘动画还原历史场景,利用探针镜头在微缩场景中穿梭,将只留存于史料图片中的真实故事,运用虚拟技术得以重现。《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中在临淄当下现实的土地上运用3D技术复原了稷下学宫,通过动画详细且快速地呈现了搭建过程,使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那段辉煌的历史。纪实影像借助数字技术为观众再现历史时空,最大程度弥补了史料欠缺的直观感受,还原历史建筑与历史场景,方便观众进行联想,置身其中。
但此处的虚拟与真实并不是冲突的。布莱希特曾在《布莱希特戏剧论》中提及:“将事件或人物的某些不言自明、一目了然的因素进行剥离,使人对之产生好奇心。”[3]我国学者也对其进行解释,认为用某些手段规避观众过于入戏产生的间离感是有助于观众思考的。虚拟技术一目了然的虚拟性对再现行为的不隐瞒,能够让观众意识到过去的种种无法复制还原,这种不隐瞒的“诚实感”可以增强观众对影片真实性的信任。
四、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艺术表达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风格往往是严谨的、有权威性的,因此会常常给观众严肃刻板的印象。但随着在2014年左右纪录片播放平台的转变,由传统电视向网络平台的转移,纪录片也需要转型来对抗这种固有风格带来的审美疲劳感。不仅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其他纪录片的娱乐性也明显的增强,这更能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适应在当下社会发展情况下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运用弹幕、戏化历史、增强视觉美感、形式创新、充分运用技术等创作手法吸引了更多的目光,把握了知识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平衡,让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收视率和好评率一路飙升。
(一)创新手法与美学元素增强视觉美感
《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章节性字幕的设计也是一大亮点:采用汪洋恣肆的毛笔艺术字体,通过书法艺术展现符合时代的洒脱与自由,增强了文化精神的代入感。而极具文学性的解说和台词则填补了信息空白,黏合了画面内容,美感的画面与诗意色彩的解说词流畅衔接,确保了情绪的流畅,增强了情感的深入。如此多种历史塑造的路径有助于产生心理认同和情感召唤,身临其境与多维感知对纪录片的加持更加符合当下精品化的审美需求,为国际化传播夯实了基础。
电影视听语言经历百年发展逐步完善,敦煌题材纪录片《敦煌 生而传奇》这部影片由专业电影调色团队进行调色。随着电影艺术多元化发展,音乐在影视作品中烘托氛围、表现人物、交代背景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片音乐制作堪比大片,由爱尔兰作曲家进行主题曲的创作、爱乐乐团演奏,视听效果宏大壮丽,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视听审美需求。而另外一部纪录片反其道而行之,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使用台词,动画,音乐等方法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性。解说者最大限度地表达出符合有趣的画面,俏皮可爱的声音状态,拉近了观众与国宝的心理距离,消除了文物作为严肃历史载体所带来的疏离感。此外,这部纪录片的时长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对于历史宏大严肃的消解,碎片化从形式上让知识易于接受。
由于腐蚀磨损,历经岁月的文物会存在残缺破损、难以辨认、有碍观赏,影响观众的视觉体验和影片理解,因此《如果国宝会说话》这部纪录片还运用大量数字动画技术,多光谱的采集技术才恢复文物的原貌呈现完整形态。技术的运用对无法完整展现的文物进行还原和修复,审美的精致追求能够触发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艺术手法在影片制作中被烘托,能够在获取史实外触发历史的感怀,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
(二)叙事手法多元增加可看性
纪录片叙事手法不断多样化,告别了单线的顺序,叙事开始自由灵活地进行排列组合,通过不同的组合表达出不同的内涵。
纪录片《敦煌》采用了双时空叙事手法,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交错讲述,实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自由穿梭。这样的方法拉近了人们与民族文化的距离,产生古今连结的效果,便于观众理解历史,身临其境具有可看性。《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这部纪录片运用首尾呼应的方式站在世界视域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表现。影片在开篇中提到:伟大的精神觉醒同时在中国、印度、希腊三个地区发生,历史学家将三个文化发源地命名为“精神原点”。将稷下学宫开启的东方教育制度体系架构至世界文明的高度,体现古老的东方智慧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符合文化交融视域下人们对于文化多元与文化自信的认知倾向。
影片《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中采用了很多影视资料来强化着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影片采用了《彭德怀元帅》《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经典电视剧和电影,不仅将历史事件更好地融入进当代社会,还将战争的历史记忆与电视剧放映的年代记忆相结合,使久远的历史与人们的生活进行更紧密的相连。影片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在镜头的时空场域切换中表述出国家历经的风霜,民族的成长与历史长河中精神内涵的锤炼与传承。
结语
当今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将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潮碰撞融合,对人们产生积极的影响。相比于传统的文献图片展览等媒介,纪录片视听方式更易被大众认知,门槛更低,壁垒更小,更易被接受,从而广泛传播。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产生出的传统文化蕴藏在一个个的历史物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之中,影响着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现存的国家,这一定论让中国本应拥有历史文化强国地位。国家文化形象就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文化作品、历史事实向国内外人们传递的一种文化精神和文化形象,它是国家形象的核心部分。[4]因而更需要运用与时俱进的手法与时代接轨,打破文化壁垒,更好地向下向外传输。
在社会进步,消费文化以及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之中,人们的审美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可接受的事物更加多样,对于传统文化与创新的需求越来越高。历史题材纪录片,在保证真实呈现的情况下注重艺术表达是文化与思潮融合,引导了审美,为大众提供知识,提升文化自信,能够在思想上得到进步,在艺术上体现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