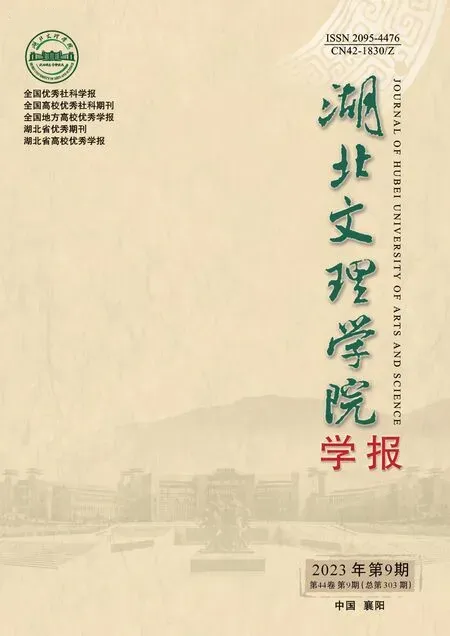杜威美学对传统艺术观念的颠覆
——基于《艺术即经验》的解读
2023-11-14李晓婷
李晓婷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20世纪的西方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和分析美学看似分庭抗礼,实则分析美学更占据主流。实用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杜威,其美学代表著作是出版于1934年的《艺术即经验》。佩伯高度肯定《艺术即经验》,称其为美学中仅有的四五本伟大著作。[1]然而,《艺术即经验》出版后并未在西方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引下,才广受关注。比尔兹利甚至盛赞《艺术即经验》为该世纪用英语写成的最有价值的美学著作。[2]20世纪末,长期占据主导的分析美学悄然退却,杜威美学却备受瞩目。
如果将《经验与自然》看作传统哲学对经验概念理解的纠偏的话,那么可以将《艺术即经验》看作艺术哲学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纠偏,《艺术即经验》有力地冲击了把艺术看作固定且神圣不可侵犯之对象的传统美学观。[3]传统美学大都以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切入,与康德、黑格尔及其继承者们的艺术观不同,杜威认为艺术的范围远远大于当下所理解的艺术,艺术是完满的经验。在《艺术即经验》中,杜威从活的生物(live creature)出发,反对那种断裂的审美经验理论。[4]当然,杜威对艺术的讨论也散见于《经验与自然》《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书中。总体而言,杜威美学对传统艺术观念的颠覆在三方面最为突出:重新界定艺术、恢复艺术的连续性以及强调艺术的工具价值。用舒斯特曼的话说,杜威美学在西方美学史上的地位处于分析与解构之间。[5]59审美和艺术实践中的现实变化,相应地要求美学和艺术研究作出新的回答,毋庸置疑,杜威的美学思想为构建新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这也是杜威美学在当下不断被重新发掘的原因所在。
一、重新界定艺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
自柏拉图时期伊始,“艺术是什么”就成为西方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最早使用“aesthetica”一词来命名其著作(常译作“美学”,也有译作“审美”),鲍姆加登将“美学”看作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认为“美学”即“感性学”。[6]虽然人们普遍认同艺术与感性密切关联,但直到20世纪后半叶之前,人们往往忽视艺术与感性、与人们的体验之间的关系。美学史上的诸多理论如游戏理论、符号理论、艺术界理论等也曾回应过“艺术是什么”的问题,然而,这些理论大都聚焦于艺术的显著特征或个别属性,有的过于宽泛,有的过于狭隘。[5]59杜威认为艺术是具体的、经验性的,本身不可被定义、难以被分类,更不可能仅凭借抽象的语词就能概括其本质。进而言之,仅仅使用一成不变的定义来界定艺术,只会使得艺术沦为一个僵化的物质实体。实际上,在生动活泼的具体经验面前,任何界定艺术的“本质”都是虚幻的,都是人为的强制,既然这一界定并非艺术自身的性质,因而不具有永恒的意义。这种人为地将美学限定于狭隘、孤立范围的做法无视了理智在审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并非生产者的立场,而只是消费者的立场,因此最后只能画地为牢[7]。由此,人们难以理解:我们与艺术家同样面对相似的生活,艺术家为何能从生活的原始材料中创造出具有表现意义的对象,而这种成功又是如何迁移到人类整个经验领域的?为此,杜威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立场,指出艺术活动创造的过程也是审美的过程。这一立场大大改变了传统的艺术批评习惯,突出了审美经验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啻为接受美学诞生前的先声。
为了融通传统美学在理智与感性之间形成的对立,杜威以经验自然主义作为美学的基础,以此探寻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重新界定了艺术。[8]在《艺术即经验》中,他用一整本书回答了什么是艺术——艺术即审美经验,或“一个经验”。不同于柏拉图、康德等人通过寻找美的先验原则来为艺术下定义,杜威用“一个经验”帮助我们理解审美经验,在他看来,只有完满、连贯的经验才能称为“一个经验”,但“一个经验”又与审美经验不同,审美经验集中体现了“一个经验”[9]。受工业革命的影响,艺术逐渐脱离人们的日常经验而呈现商品化趋势,从而沦为“艺术产品”[10]。为了改造传统的艺术观念,杜威进一步将艺术产品(product of art)与艺术作品(work of art)作出区分。与传统美学把艺术看作超越经验之上的抽象的艺术品不同,基于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艺术的异化,杜威指出艺术作品与经验紧密相连,是“产品所做和所起的作用”[11]179。他认为艺术产品是物质的、潜在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时代机械复制的产物;而艺术作品则是能动的、完满的、和谐的、令人愉悦的、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中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艺术产品要想成为艺术作品,需要被人知觉且融入到人的经验中,否则只能被看作是潜在的艺术作品。例如,被陈列在博物馆和美术馆中的艺术品仅仅被视为“艺术产品”,而艺术作品存在于某个独特的经验中。因此,艺术作品贯通了创造者和欣赏者,更强调经验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发挥美的因素对经验的改造作用,也要努力尝试将那些被博物馆化、被隔离的“艺术产品”转化成“艺术作品”。[12]
综上,传统的艺术观念将艺术界定为有边界的凝固存在物,如绘画要以画布为媒介,当我们欣赏一幅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也被限定在边框之中。但是,当杜威明确区分了艺术产品和艺术作品后,人们就会发现,艺术作品与艺术产品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艺术作品增加了人们新的审美经验,而且在于艺术作品的张力使得艺术作品与整个宇宙存在关联,使人们在自身之外去认识自身,在自然之外去认识大千世界。可见,杜威重新界定了艺术——有价值的美学并不是给出确切的艺术定义,而是引导人们如何才能形成丰富、完满的审美经验,以此丰富人的生命活动乃至提升人的生存质量。
杜威用审美经验来界定艺术有什么优势呢?新实用主义美学代表人物舒斯特曼指出其中的两重意义:一是表明经验在艺术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让人们意识到艺术是审美经验的有目的的生产。[5]99换言之,“艺术即经验”不仅凝练地总结了过去的艺术现象,而且进一步点明了艺术具有丰富人们的审美经验的作用。与美学史、哲学史上的传统研究路径大相径庭的是,杜威将美学焦点从作为客观对象的艺术品转移到人的经验中。在实用主义美学之后的分析美学虽然也承认审美经验的重要性,但总体上仍将其排除在美学研究的范畴外。实际上,当人们欣赏那些或举世闻名或寂寂无闻的艺术品时,大多数人并不是像分析美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从艺术品、艺术史的研究中获得科学知识,而是为了获得或令人愉悦、或发人深省的体验。传统美学乃至分析美学之所以没有充分理解审美经验,也许还因为审美经验是感性的,无法用理性主义的逻辑去把握。
此外,在对待审美的态度上,传统美学以及分析美学都把艺术当作模仿、表现、审美或娱乐等看待,新实用主义美学代表人物舒斯特曼就批评分析美学家丹托以语义学的、狭隘的、描述定义的审美经验去取代了杜威源于生活的审美经验概念,由此导致艺术定义没有生命力而走向终结。[5]21杜威虽然并没有为艺术是什么作出明晰的定义,但他以描述为方法,用众多事例和反复论证对艺术性质进行描述性界定[13]。也许这种缺乏严谨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受到美学界的诟病,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将艺术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将美学等同于对美的艺术自给自足的接受,那将使美学陷于狭隘的困境[14]。从杜威对艺术的界定也可以看出,其艺术观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正是这种艺术研究路径使得杜威美学在当下仍具有特殊意义。
杜威重新界定了艺术,打破了审美活动与哲学、伦理、逻辑、功利、实用之间的人为区隔,“审美经验”的内涵也由狭义的、纯粹的、非功利的转向宽泛的、模糊的、实用的。可见,杜威对审美经验的系统阐述突出了活生生的审美经验,激发出美学的无限活力。
二、恢复艺术的连续性
西方哲学主客两分的矛盾从柏拉图开始,到康德愈演愈烈,尽管黑格尔用理性化解了主客二分的矛盾,但是理性的绝对化使得哲学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面对这一问题,杜威试图构建一元论哲学来彻底改造传统的西方哲学,凭借的正是美学思想。在杜威看来,传统二元论哲学在美学领域的表现在于,传统美学造成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心灵与肉体等的二元对立。[15]为此,杜威主张恢复艺术的连续性。
首先是恢复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连续性。杜威批判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纯粹的“静观”的做法,认为审美经验不过是日常经验的完满化和清晰化,将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区隔,人为地拉大了审美与人们的距离,贬损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杜威指出艺术的任务是“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5]3。
因此,杜威认为审美经验应该从日常经验出发,从普通经验中发掘其中的审美性质。日常经验与审美经验并非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一个粗俗的经验,如果它真的是经验的话,也比一个已经从其他方式的经验分离开来的物体更加适合于提示审美经验的内在性质。”[11]10人类的所有经验没有质的分别,只有量的分别,日常经验虽然经常是不完满的、碎片化的,但也存在着完满的经验,即“一个经验”。“任何实际的活动,假如它们是完整的,并且是在自身冲动的驱动下得到实现的话,都将具有审美性质。”[11]42日常生活中的春花秋月,鸟语蝉鸣,都能成为审美经验。这种重视日常经验的做法可看作后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萌芽。需要指出的是,杜威并非粗暴地把艺术等同于任何普通经验,他认为艺术品“来自于日常经验得到完全表现之时,就像煤焦油经过特别处理就变成了染料一样。”[11]10
其次,杜威还试图恢复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连续性。杜卡斯由此认为杜威贬低了高雅艺术,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杜威只是不满意掩盖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之间的连续性的做法。传统美学认为高雅艺术具有“灵韵”(aura)的精神性,20世纪的大众艺术如电影、爵士乐、连环漫画等就不被传统美学认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逐渐分离,使得高雅艺术远离了大众,当高雅艺术被高高在上地供奉在庙堂之上,就会由于难以亲近而使人民大众望而却步,“他们出于审美饥渴就会去寻找廉价而粗俗的东西”,长此以往,通俗艺术也逐渐降低了品味。[11]6
前面提到杜威注重的“日常生活”,其中也包含了日常娱乐的内容。杜威开风气之先,提倡回到日常娱乐中去寻找艺术内在的审美价值。他对先锋派艺术持批评看法,却对原始艺术青睐有加,认为原始艺术具有让现代艺术相形见绌的能量:“文身、飘动的羽毛、华丽的长袍、闪光的金银玉石的装饰,构成了审美的艺术的内涵,并且,没有今天类似的集体裸露表演那样的粗俗性。”[11]6究其原因,原始艺术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无法回到原始时代,而开始“原初的”审美经验却是能够达到的。“原初的”审美经验指那些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支配我们的“栩栩如生”的经验,例如火车的开动、从传送带上抓住发烫螺栓的钢铁工人。[11]11也涉及一些更加安静的活动:一个劳作的妇女、观看篝火闪烁火焰和破碎灰烬的人。[11]268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场景。舒斯特曼也追随杜威的脚步,努力为大众文化的艺术合法性进行辩护,由此,艺术不再由过去历史实践那样,仅局限于某种在传统上有特权的形式和媒介。[5]86
此外,杜威还试图恢复美的艺术(Fine arts)与实用的艺术之间的连续性。传统美学认为艺术品是美的艺术,以实用为目的制造出来的物品不能称作艺术品。美的艺术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音乐家、画家、雕刻家与木匠、铁匠、石匠所从事的内容只是随着人们划分知识门类以及掌握一些抽象的艺术规则后才逐渐与实用的艺术分离。
杜威的深刻之处在于看到了传统艺术观念将艺术局限于观赏性的艺术的问题,杜威指出,实用的艺术也能体现审美价值,例如,对于非洲的族群部落而言,雕塑家所塑造的当地雕像就比衣服、长矛这些或用以御寒或用以求生的工具更为实用,然而,过去这些被认为更具使用价值的雕像,如今却被看作美的艺术。[11]26可见,实用与不实用并不是杜威判定艺术品与否的标准,杜威根据创作与欣赏经验的完整程度,把一切丰富了生活感受的对象都看作艺术,美的艺术让艺术家“通过欣赏而拥有他们的生活”,从而“使整个生命体具有活力”。[11]27其实,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与经验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艺术的范围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经验,当人们带着审美的态度看待它时,艺术就诞生了。人们建造帕特农神庙之初正是始于自身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出于创造美的艺术本身而去建造的。[11]4-5
正如舒斯特曼指出,杜威的连续性美学揭示了艺术与生活、美的艺术与实用艺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等传统二分观念在根本上的连续性,为当代审美和艺术实践作出有力辩护。[5]86总体而言,杜威将艺术恢复到前现代的情境中,这种做法超越了现代的语境,拓宽了审美经验的范围,也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范围。
三、强调艺术的工具价值
传统美学固守审美活动无功利、无目的、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的性质,保持精英化、贵族化的立场,认为美自身就具有价值,不在于能否产生其他价值。[6]受此影响,美学界普遍认同艺术具有纯粹的内在价值,是非工具性的,不能直接带来利益。虽然现代社会已将艺术的范围大大拓宽,例如,男用小便池这种大俗之物也被艺术家杜尚命名为《泉》,并作为艺术品当众展出,但是,鲜有美学家赞同艺术具有工具价值。虽然批评审美无功利态度的呼声不绝于耳,如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强调艺术要反映社会现实,但最彻底推动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化的还是杜威[16]。杜威反对传统二元论哲学造成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对立。
前面提到,杜威所认为的艺术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而是原始艺术,艺术最初也不是为了激发美感而制作的,而是作为实用的目的,是生活实践的产物。如今在博物馆展览的艺术品,如制作精巧的坛、罐、锅、碗等,最初不过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实践的需要而制作的。概而言之,艺术是自然界完善发展的最高峰结果。传统美学将艺术与自然对立,即艺术由天才的心灵创造,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而自然是天然的、自在的,这种观点招致杜威的批评,他认为艺术的起源与自然界的运行和发展紧密相连,“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是所有经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源泉,从环境中形成阻碍、抵抗、促进、均衡,当这些以合适的方式与有机体的能量相遇时,就形成了形式。我们周围世界使艺术形式的存在成为可能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节奏。在诗歌、绘画、建筑和音乐存在之前,在自然中就有节奏存在。”[11]4也就是说,从起源上看,艺术就包含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之中,艺术充分体现了人类谋求生存的求索过程。在杜威看来,艺术起源于人类利用工具获得生存、获取经验的过程,“由于经验是有机体在一个物的世界中斗争与成就的实现,它是艺术的萌芽”[17]。这里的“经验”是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的生活经验,人们经由它探索自然,揭示自然。传统哲学认为理智是认识活动的终点,人类的实践活动需要依靠理智转化为知识,不同的是,杜威认为知识和理智都是指导人们生活的工具。艺术作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理智的支持,例如画家若在下笔作画之时没有用心来“经验”其所画的每一笔,就难以清晰地知道其画作将走向何种效果。除此,画家还需要根据其想要产生的总体效果来严格思考目前每一笔“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联系”。[11]1当艺术作为具体的、完满的经验时,艺术就与自然、与美感、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了。
由此,杜威将艺术与人类的生存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艺术的发展是自然界和经验双重推进的结果,艺术是人类改造环境的有力工具,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人类运用工具的进步密切相连。杜威重视人类能够制造工具的行为,认为人们通过工具砍树、打猎提高了生存能力,丰富了人类的经验。艺术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表明,使用工具是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不同之处,艺术是人类战胜动物的标志,只有人类能够制造工具,从而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尽管人们可以在任何生命体的活动中寻找到经验,例如,人们可以从处于人类水平之下的动物诸如狐狸、画眉等中寻找审美经验的源泉,窥见审美经验的部分特征,但是艺术却只是人类的活动。因此,艺术作为工具“服务于具有完整而充满活力的整个生命体”[11]136,生动地体现了生命体面对自然时的经验性力量,意味着艺术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可以被人类把握、驾驭,进而享受、利用。
近代美学认为艺术在自身之内就具有内在价值的看法,最终导致了艺术终结论的产生。杜威主张艺术具有超越个人特殊目的的工具价值,这一独特的艺术研究路径表明需将艺术品融入经验中,使其能够真正发挥艺术的价值。这种强调艺术的工具价值的艺术观念打破了艺术领域的二元论、打破了艺术的“博物馆态度”,欣赏艺术的目的也由认知转为增进经验。总之,艺术作为工具使生命体内在的冲动得到了实现,使自然的材料在人的生存实践过程中转化为令人愉悦的经验,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感觉活动,而且拓宽了生命活动的领域,人类社会、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不断拓展的生命活动中延续、发展。
尽管由于分析美学风头盛行,杜威美学一度受到冷落,但自20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当代艺术和审美实践发生了巨大转向之时,西方美学家又纷纷将目光投向杜威美学,希望从中汲取理论资源,寻求理论依据。特别是美国美学家,更是把杜威美学当作挥向分析美学的利剑。传统和流行的美学和艺术理论都是从艺术本身和抽象的艺术概念出发,杜威美学“绕道而行”,从“活的生物”出发来寻求艺术问题的解决,这种打破传统美学建立在传统理论哲学的本质论和二元论基础上的艺术观,正是杜威美学的现实意义所在。
杜威创造性地提出以审美经验为核心重新界定艺术,恢复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美的艺术和实用的艺术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艺术是人类改造环境的有力工具,这种颠覆传统艺术观念的做法扩大了人们对艺术和审美认识的视野,体现出杜威美学思想的创造性,对美学和艺术理论建设、对艺术实践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为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