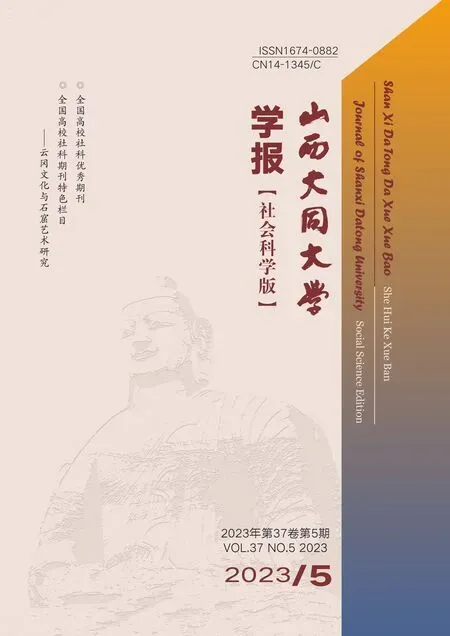汉代识字课本浅论
——以出土简牍为中心
2023-11-07王丹
王丹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汉时,随着文书行政机制的形成与固定,能否“史书”成了评判吏员能力的重要标准,“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又促进了吏员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汉代吏员在提升自身水平的过程中,字书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本文的字书是指用于识字或练习书写的教材。
一、汉代识字课本的载体
《史籀篇》被认为是最早的字书,该书也成为了之后字书的范本,秦时李斯作的《苍颉篇》,赵高作的《爰历篇》,胡毋敬作的《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1](P1721)汉初,这三篇合并成《苍颉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吸收和改造了《苍颉篇》的内容,作《急就篇》,这样《苍颉篇》与《急就篇》成为汉时主要的字书,在全国统一颁布推行,各地出土的写有《苍颉篇》《急就篇》相关内容的简牍可以证实这一点。出土简牍中存在大量写有字书内容的简牍,作为识字课本,笔者认为编连成册的字书册书为普通识字课本的载体,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有87 枚竹简书写有《苍颉篇》的内容,这些简牍中的文字书写工整,格式统一,字间距相同,每支简上的字数相同,可以编连。同样的,在甲渠候官遗址(A8)中也出土了类似的简牍,甲渠候官遗址F22 是当时的文书保存室,存放有大量的文书档案,这个房间中出土的字书简牍,字迹工整,字间距较大,但是多为断简,不得窥其全貌。这种格式的简牍可能是作为普通的字书册书存放在文书保存室中供边塞吏员学习使用。编连成册是简牍文书或简牍典籍的常见形式,不具备代表性,但对于识字课本的学习则存在特殊的载体。
(一)书写范本载体 简牍是当时的主要书写材料,汉代虽然已经出现了纸,但纸并不作为书写材料,而多用于包装,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纸才逐渐代替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简牍的形制多样,觚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呈现出多面立体书写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觚成为练习字书的主要载体。《急就篇》在篇章的开头便有“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属也。”[2](P15)根据颜师古的注释,觚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书写练习。邢义田先生则将关注点放在“奇”上,认为“‘急就奇觚’之‘奇’应指奇偶之奇,也就是三面或者奇数面之觚。”[3](P617)西北汉简中有几枚写有字书内容的三棱觚,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字书范本。
第一枚为居延汉简9.1(图1)的木觚,此觚为《苍颉篇》第五章内容。这枚三棱觚的字迹清晰方正,间距较大。《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3](P1721)习惯上《苍颉篇》以四字成句,此觚除去“第五”篇名,正合每面二十字,三面共六十,每面断五句。居延汉简中的9.2 和307.3与此觚类似,但是没有篇名,或为《苍颉篇》等字书的某部分内容。

图1 居延汉简9.1采自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
《急就篇》由西汉史游所做,以63字为一章,第一部分为姓氏,三言成句;第二部分言物,七言成句;第三部分只有一章,四言成句,三棱觚可以保证其每面21 字,三言成句断为七句,七言成句段为三句,最后一章63字主要为歌颂汉代功德,四言成句,这一章常识性识字性作用较小,四言成句,三棱觚不能保证其每面都有完整的句子,但63 字亦可保证每面字数相同。同样在出土的简牍中亦存在《急就篇》的范本,《敦煌汉简》收录了两枚三棱觚,编号为1972(图2)、2356。这两枚三棱觚每面21字,断为七句,三面共63字。但形制上有明显的差别,敦·1972 截面呈等腰三角形,正面中间有一棱,上端骑棱削一个倒三角,书写篇章名,字书内容书写在棱的两侧,背面平整,觚上端有孔,可能是便于悬挂观看,亦或是作为标准字书展示。敦·2356 与居延汉简9.1 相似,三面等宽,顶端写篇名“第十”,应为《急就篇》第十章的内容。

图2 敦煌汉简1972采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
以上这几枚字书范本,整体书写规范,字间距相同,字体成熟,形制均为三棱觚。这种形制的字书简牍在数以万计的出土简牍中仅仅可找出以上几枚,所以应不是普通字书的载体,而是在识字练习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示范意义的成果。牍(以下称“英藏”)中存在大量的削衣,削衣也是简牍形制的一种,是从简牍上削离下来的薄木片。这些削衣中存在大量与《苍颉篇》相关的内容,胡平生先生认为这些削衣是从练习《苍颉篇》的木觚上削离下来的。[4](P62-75)作为练习字书的载体,觚上的文字并不像字书册书或范本上那样统一,马圈湾遗址出土了一枚四棱觚,编号为639。学界将其内容认定为《苍颉篇》中的姓名篇,白军鹏先生从与《苍颉篇》《急就篇》范本的比较;四棱觚上的字体、字间距;四棱觚的形制与残缺程度几个方面对此觚的性质进行了界定,认为“再将其作为书写范本来看就显得极为勉强,而以两端残破的木觚作为习字之用便容易理解了。”[5](P126)与此相似的练习觚在“英藏”中仍然存在相当的比例,这些内容都属于《苍颉篇》《急就篇》中的某些篇章,但大多残断。与字书范本不同,其载体并不是三棱觚,棱数不一,字体并不似字书范本那样规范,应该是较为成熟的书手练习字书时所写,但依然属于练习简范畴。
字书的其他练习载体亦不像字书范本那样统一,觚只能作为字书练习载体的一种,同样是关于《苍颉篇》的内容,马圈湾出土了一枚完整简,编号844,内容为《苍颉篇》的开篇部分,顶格书写,字迹较为工整,字间距较大,但是此简只有14 字,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的《苍颉篇》册书简一面20字并不相符,应该亦是出自于比较成熟的书手所写。但是需要说明的,书手并不单一练习字书,因为汉代对于吏员“史书”能力有考核要求,以及文书行政的逐渐规范,书手在练习全国统一识字课本的同时,也会练习一些实务用字,这在习字简牍中是十分常见的,习字简牍的形制也不止简、觚,牍、签牌、封检等废弃简都可能被用来削刮习字。所以“英藏”中大量的削衣不止是从觚中削里而来,从其他的简牍中剥离下来也是有可能的。
二、汉代识字课本的主要使用群体
(二)练习载体 三棱觚作为字书范本的载体是觚形简牍较为特殊的情况,除此之外觚也是练习字书的载体,颜师古对《急就篇》开篇的注便是针对觚这一作用的解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简
《汉书·艺文志》中列出了关于“小学”相关的书籍,共45篇。这些“小学”书籍的关系,班固在《汉书》中也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1](P1721)
由此可知,《史籀篇》为周时史官教学童的识字课本,秦汉时期的《苍颉篇》由《史籀篇》发展而来,汉代的字书围绕着《苍颉篇》保留和发展了适用于学童和政务需要的识字课本,这些“小学”书籍中包括《苍颉篇》一篇和后人依据《苍颉篇》所作训的其他字书以及《急就篇》,可见《苍颉篇》和《急就篇》是“小学”学习的重要内容。成书于东汉后期的《四民月令》,其中有:“研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6](P9)《四民月令校注》中对“篇章”进行了说明“依‘本注’的说明,篇章是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其中急就、三仓等字书,应当学会书写。”[6](P10)由此可见,《苍颉篇》《急就篇》在汉代作为学童教科书是比较固定的。
汉代字书另外的一个使用群体是基层吏员。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汉简,除了几枚字书范本外,还有许多字书的残存,上文中已经提及,这里不做赘述,这些带有字书字迹的简牍和削衣证明了基层吏员练习字书的事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基层吏员除了练习字书达到能写会认的水平之外,还需要练习公文书用字、九九表等。练习公文书用字一是因为汉代的公文书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系统,公文书是行政的必要环节。二是国家对于吏民的上书有一定的要求,“字或不正,辄举劾。”[1](P1721)三是汉代边塞在考核吏员的时候“能书”是重要的一条标准,“所谓能书,是指能否以公文长用的书体——史书,也就是隶书写公文。”[7](P568)综合以上三个原因,基层吏员练习公文书是十分必要的,在西北汉简中有大量的习字简,而公文书的练习占有很大的比例。除了字书和公文书,习字简中还存在一部分的九九表,九九表主要练习的是边塞官吏计算能力。“会计”也是汉代对于边塞吏员的基础要求。
综上所述,汉代字书的使用人群主要是学童和基层吏员。诚然,字书作为全国统一发行的识字课本,其使用范围可能更广泛,但根据传世材料和出土文献可以发现,学童和基层吏员是使用字书最为主要和普遍的两个群体,这对于提高国家的基础教育和扫盲有一定的作用。
三、汉代识字课本的意义
作为全国统一发行的识字课本,《苍颉篇》《急就篇》对汉代文化的统一有特殊的意义。首先从基础文化传播的角度讲,《急就篇》是对《苍颉篇》的继承与发展,这有利于基础文化的延续。《急就篇》中分章叙述各种名物,按照相近字体进行排列,内容涵盖了姓名、物品,地理、官职等各方面,不仅为识字而设,还可传布知识。因“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急就篇》中还包含大量的儒家经典,这对国策的巩固和儒家经典的传播是有推动作用的。
其次,字书中的部分内容对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巩固有积极作用。居延汉简9.1 是《苍颉篇》第五章的内容,其中有:“汉兼天下,海内并廁”的描述,这是国家意识在基础教育中的反映,作为全国通行的识字课本,国家意识在社会各个层面得到了认同,从而加强了民族的凝集力。也是在这时,中国传统的“汉”意识逐渐的形成,当然这和当时汉朝综合实力的强大也是分不开的。
最后,字书的普及也影响了汉时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在当时人的姓名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一些学者针对《苍颉篇》《急就篇》中的人名,与传世典籍、出土印章中的人名进行了互证,白军鹏先生在《马圈湾汉简“焦党陶圣”章释文、性质及人名互证研究》中将马·639 简中的姓名与《苍颉篇》进行了互证研究,并将姓名分为:常用、不常用、稀有、其他能四种。邢义田先生在《汉简、汉印与〈急就〉人名互证》中就汉简、汉印中的人名与《急就章》进行了互证。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大多属于公文书,汉简中出现的名字多是官府吏员。汉印无所争议的是汉朝的官员,汉代官员在执行公务发布公文时有用印的固定制度,一是为了体现公文的真实性,二是体现公文的权威性。汉简、汉印中存在大量可以和《苍颉篇》《急就篇》互证的名字。[8](P84-101)但这两篇文章并没有体现出字书对于姓名的作用,这里就会出现两方面的疑问,是官员的姓名影响了字书还是字书影响了姓名,笔者认为是字书影响了姓名,《苍颉篇》《急就篇》中都有姓名篇的存在,《急就篇》更是在开篇便有“罗列诸物名姓字”的特征概括。一方面字书作为全国统一的识字课本加以推行就使得相同姓名的普遍存在成为了可能。一方面字书也使百姓和官员的基本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西北等边塞地区,这些地区的吏员文化素质较低,大量习字简牍的存在以及公文简中稚嫩的字体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字书是这些人们增长知识的主要来源,根据字书起名也是文化增长方面的体现。另外,作为吏员练习的内容之一,字书不仅促使其达到考核的标准,也增加了见识,提升了整体吏员的水平,使得政府工作可以更加有效的运转。
结语
汉代的识字课本主要以字书《苍颉篇》《急就篇》为代表。从出土的写有字书内容的简牍可以看出普通的字书是编连成册的,而字书范本的载体主要是三棱觚,觚中每面书写的文字字数相同,字间距较大,字迹规范,出土简牍中也存在其他形制的写有字书内容的简牍,这些简牍多是练习字书的载体,为简牍材料的再利用。作为基础教育教材,学童和基层官吏是汉代使用字书的主要两大群体,儿童学习字书是汉代童蒙教育的体现,而基层官吏学习字书一方面反映了汉代对文吏的培养要求,一方面反映了基层官吏为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所做的努力。字书除了扫盲作用,在对于汉朝提高吏员素质,增加民族意识,巩固儒家思想,影响百姓日常生活等方面亦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