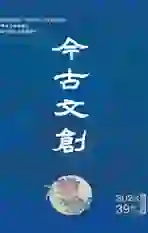“ 吃与被吃 ” 视域下 《素食者》中的女性困境书写
2023-10-30侯家琦
【摘要】“看与被看”模式是鲁迅小说作品情节、结构的重要模式,笔者认为韩国作家韩江的小说《素食者》中也存在类似模式,即“吃与被吃”模式。本文将简述《素食者》的内容并引入“吃与被吃”模式,进而通过“肉”这一意象的分析、小说中三对“吃与被吃”关系和英惠姐姐形象的解读展现《素食者》中的女性困境,最后加以总结。
【关键词】“吃与被吃”;《素食者》;韩国;女性困境
【中图分类号】I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39-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9.004
一、《素食者》内容梗概及“吃与被吃”模式
在韩国作家韩江的小说《素食者》《胎记》和《树火》三个环环相扣的篇章中,韩江通过叙述声音的转换全景式地展现了家庭主妇英惠从素食主义者到向往成为植物的心灵异化过程。暴力与唯美在小说中实现了吊诡的统一,隽永却充满挣扎与不安的文本暴露了来自核心家庭、家族和社会的结构性暴力对英惠的摧残。小说中“女性是否只能通过自己的身体进行反抗”的隐含命题揭示了女性困境作为现代文明症候对女性身心的禁锢与摧残。
鲁迅对“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痛苦的关注在文学领域的投射即是“看与被看”二元模式的形成。[1]37这种对立发生在社会地位低下的“苦人”与权势者、看客之间(如《祝福》和《孔乙己》),也发生在先驱和大众之间(如《药》)。
“看与被看”模式中包含了强者对弱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凝视”。这与《素食者》中男性权力对女性个体尊严的消弭有相似之处。但是鲁迅小说中的“看与被看”模式集中表现的是被“凝視”者话语权被剥夺的困境,如鲁镇的看客通过消费祥林嫂失去阿毛的痛苦实现心灵满足和酒馆中的顾客质疑孔乙己的文化水平、嘲笑其偷窃行为以获得“快活的空气”。
而韩江长于通过文本揭示暴力对个体的伤害,譬如在以韩国光州民主化运动为历史背景的小说《少年来了》中,作家大胆罗列了尸体等与死亡相关联的意象,展现出作为暴力施加者的权力对个体生命的无情践踏。再如《素食者》中,家族成员或“呵斥”,或“大发雷霆”以胁迫英惠吃肉,全然不顾其感受。这场闹剧以父亲掌掴英惠,英惠试图割腕自尽而收场。“暴力”是贯穿这一情节的核心意象。
正如英惠自尽未果后住进医院,母亲对她的指责:“你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2]48在《素食者》中存在的情节、结构模式相较于“看与被看”模式,更注重冲突的刻画,情感烈度更大。这一模式可抽象、概括为“吃与被吃”模式。
二、对“肉”这一意象的分析
(一)“肉”是英惠命运的隐喻
在家人逼迫英惠食肉的情节中,韩江不吝笔墨,“炒牛肉、糖醋肉、炖鸡和章鱼面”等意象铺陈列锦,[2]35美味的肉食与剑拔弩张的气氛反差鲜明。在英惠姐姐的新居这一空间内,实际上存在着两对“吃与被吃”的关系,即食物与人、家族成员与英惠。正如英惠拒绝食肉后小舅子与岳父的“怒吼”与母亲的“绝望”,英惠是否食肉反映了英惠对家长的服从度,也说明了她对男性权力的接受度。“食肉”在情节中事实上与家长意志和父权话语深度绑定。人与肉食之间的消费与被消费关系因而指向了家族成员的命令与英惠个人意愿的收编与抵抗的矛盾。家人强迫英惠食肉的尝试最终宣告失败,但是英惠生命垂危,在出院后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福柯认为:“处于西方文化的各种极端体验中心的,无疑是悲剧体验。”[3]272不论是雕塑《拉奥孔》中拉奥孔面对死亡的苍白无力,抑或是李煜诗词对人类普遍苦痛的承载,悲剧往往给予人极致的审美体验。为拒绝对肉食的消费和来自家庭的暴力,英惠不惜采取伤害自己肉身的自我牺牲式的行动,这种悲剧美极富艺术张力,扣人心弦。
正如肉食的最终归宿是被人类消费,英惠的叛逆最终被来自家庭与社会的暴力碾碎。“肉”这一意象是英惠命运的能指,在“吃与被吃”的宿命闭环中,英惠如他人的盘中餐一般,无法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二)“肉”象征着男性权力对女性的规训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饮食“在出生前就由母亲开启,生出来了后继续由母亲供给”[4]52。男权话语将准备饮食规定为女性的义务,而忽视了女性在单独从事繁重家务劳动时的被剥夺感。《素食者》的文本中存在大量描写女性加工肉食的内容。譬如在英惠拒绝食肉前,“她一手拿着钳子,一手拿着大剪子,剪排骨肉的架势相当稳重”[2]13。再如英惠的丈夫回忆家族聚会的情景:“岳母还会切生鱼片,妻子和大姨子都能娴熟地挥舞四方形的专业切刀把生鸡大卸八块”[2]16。在体力上更占优势的男性在准备食物这一过程中却存在缺位的现象,“贤妻良母”的神话抹杀了女性从事此类劳动时的辛劳。“男人们围坐在客厅喝酒、烤肉的时候,女人们则聚在厨房里热热闹闹地聊天。”[2]16男权话语试图回避参与家务劳动的义务,而将女性限定于厨房这一空间中。韩江作家通过“客厅”与“厨房”两个空间的对比展现了有余与不足的对立。
在小说中,“肉”这一意象是连结女性的劳累与男性的享受的媒介,指涉了在家庭生活中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付出与所获不对等的结构性矛盾。作家对切块、腌制等肉食的处理方式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或隐喻了女性在象征着传统、权威和理性的家庭场域中,在家庭中的定位、作用由男权话语支配的困境。
(三)“肉”折射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
笔者认为,建构于民主政治、现代工业、现代科学三大支柱之上的现代社会,以标准化为重要特征。他人对英惠拒绝食肉感到不解和反对,根本原因不是对其身体健康感到忧虑,而是这一行为在现代社会是越轨的、有悖于“常理”的。例如在英惠丈夫所在公司的宴会上,人们对素食主义的饮食习惯议论纷纷:“……这就证明了吃肉是人类的本能,吃素等于是违背本能”[2]21“……最后觉得还是均衡饮食最合理”“什么都吃才能证明身心健康呀”[2]22。
高档饭店这一特定的空间和公司的科层制组织方式都是现代社会的派生物,英惠与在场的其他人在饮食习惯上的不同取向即素食和肉食的对立,实际上是规范人类生活的现代性因素与个体话语的碰撞与冲突。“食肉者是正常人”的观念是在场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式,群体话语借助“膳食平衡”“身体健康”等现代理念对英惠坚持素食的立场加以“规劝”和收编,可见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普通个体往往陷入失语困境,原子化的个人也会遭遇异化的危机。
三、对小说中三组“吃与被吃”关系的解读
(一)丈夫与英惠之间的“吃与被吃”
第一组“吃与被吃”关系存在于二人组成的核心家庭中。福斯特认为:“爱在小说中的描写是何等举足轻重。”[4]57但是,韩江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二人的家庭生活的情节中却刻意抽离了爱情这一要素。英惠的丈夫对自身的外貌、经济状况等条件缺乏信心,选择与英惠结合的理由也是由于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同时也找不出什么缺点。”[2]1英惠丈夫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焦虑往往转化为愤怒与焦躁的情绪,施加于英惠。譬如由于丈夫急于出门办事,不断催促英惠,使其在慌乱地准备烤肉时不慎割伤手指,刀具因此出现了缺损,他在发现肉中的刀齿时暴跳如雷。这一事件正是英惠放弃肉食,选择素食主义的导火索。韩江在文本中往往使用表较强烈语气的疑问句与感叹句组织丈夫的语言,如“我要是吞下去了怎么办?你差点害死我!”[2]17再如“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扔掉?”[2]8可见丈夫的言语暴力和繁重的家务劳动造成的精神创伤郁结或是促使英惠拒绝食肉的重要因素,核心家庭内部的暴力是英惠悲剧的滥觞。
面对家族成员对英惠的责难和公司同事对英惠的不解,丈夫也没有给予英惠充分的理解与保护。可见,英惠的丈夫既在夫妻二人之间形成的“吃与被吃”关系中处于压迫者的位置,也在英惠与其他人之间的“吃与被吃”关系中扮演了看客的角色。
(二)父亲与英惠之间的“吃与被吃”
据小说文本可知,父亲是越战老兵,固执己见、脾气暴躁,英惠“被这样的父亲打小腿肚一直到十八岁”[2]28。英惠童年时期还目睹了父亲杀狗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梦可以包括追溯到童年早期的那些印象。”[5]184在英惠放弃食肉前的梦中,充斥着肉块、鲜血等阴郁恐怖的意象。笔者认为,这一噩梦是英惠在童年时期遭遇或目睹各种形式的暴力,个性受到家长压制而形成的潜意识的映射。同时英惠出身于小城镇,父母开办了木材厂,梦中阴暗的森林和仓库似的建筑物一类的场所或与英惠童年生活的环境有所关联。
荣格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又有所突破。他提出了“集体潜意识”理论,认为个人潜意识中包括祖先经验的沉淀和浓缩。[6]英惠的父亲作为一位传统的家长,存在性格缺陷,其强调体罚作用的教育理念也是存在一定错误的。他的潜意识中或积淀了先祖固有的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权思想,这也是他对英惠施加暴力的重要驱动力。但是,英惠的父亲一定程度上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人生里最大的骄傲就是参加过越战,并且获得过荣誉勋章。”[2]28他高声讲话的习惯可能也是军旅生活的烙印。残酷的战争或造成了英惠父亲的精神异化,使其难以完全实现从战争前线到和平生活的环境适应和从兵士到丈夫、父亲的角色转变。笔者认为,军队中“命令——服从”二元逻辑的桎梏是他独断专横,在家庭中往往通过暴力而不是平等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原因之一。
作为群体记忆的战争创伤,通过暴力的途径从英惠的父辈传导至英惠。在父亲与英惠的“吃与被吃”关系中,父亲向英惠输送了具有负面色彩的群体意识,这事实上导致了英惠潜意识的主基调是忧郁的、痛苦的,为英惠的心理健康埋下了隐患。
(三)姐夫与英惠之间的“吃与被吃”
精神分析学派强调性本能对人行为的驱动作用。英惠臀部的胎记点燃了英惠姐夫的创作灵感,也将他对英惠的同情、怜惜的朴素情感扭曲为情欲。在二人的身体上画满花朵的那个夜晚,英惠姐夫性本能击溃了理智。为了拍摄二人交合的画面,他不惜以自己家庭的破裂为代价。在英惠之家这一理性的场域中迸发出姐夫内心的非理性激情,人性与兽性、艺术才华的挥洒与伦理秩序的混乱被吊诡地融合于一体。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3]199英惠姐夫知名艺术家的身份、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和伦理红线这三条防线在他的性本能面前不堪一击。由此可见现代文明赋予人的道德观念、社会关系等无法完全禁锢人的欲望,非理性因素仍然可以驱使人突破理性的框架从而进入疯狂状态,疯癫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
笔者认为,英惠姐夫施加于英惠的暴力使得英惠进一步丧失了对人类群体的信任,是促使她彻底放弃人类身份,选择变为植物,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直接原因。其破坏力大于丈夫和父亲的暴力。在这组“吃与被吃”的关系之中,英惠的精神失常没有成为保护其免遭姐夫侵害的屏障,她的性自由被姐夫剥夺也映射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普遍困境。
四、对英惠姐姐形象的理解
英惠姐姐在小说的每一章节均有出现,形象较为丰满,应是圆形人物。首先,从“吃与被吃”的结构来看,笔者认为,在他人与英惠形成的“吃与被吃”关系中,英惠姐姐充当了看客的角色,见证了父亲与丈夫对英惠施加的暴力。
其次,从叙述视角来看,小说第三章《树火》完全以英惠姐姐的叙事视角展开,英惠姐姐也是小说除英惠本人以外的唯一女性叙述者。她遭受了来自父亲的暴力和来自丈夫的背叛,其遭遇一定程度上可与妹妹英惠的处境形成“互见”,启示读者英惠的不幸不是个例,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再次,从英惠形象的塑造来看,姐姐的存在凸显了英惠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作为英惠的女性直系亲属,她虽然关心英惠的健康状况,但是始终无法理解英惠极力希望成为植物的价值追求,也没有领悟到英惠蜕变的根本原因。她与英惠之间虽有姐妹关系的情感纽带,但始终不能形成与英惠的真正共情。二人之间的隔膜恶化了英惠的精神状态。在小说的尾声,英惠最终拒绝了食物的输送,生命垂危。在成为植物的最后挣扎中,作为破坏性本能的死本能彻底释放,英惠在意识模糊中达臻了“超我”的境界,以生命为代价的激越反叛升华了她的人格。送医途中,英惠姐姐试图安慰英惠:“……说不定是一场梦。”[2]187可见姐姐最终仍然没有与英惠感同身受。
最后,从作家价值取向的体现来看,英惠姐姐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她关爱妹妹,珍视与儿子共同度过的时光。韩江作家关怀弱者、关注普通个体生存状态的形而下的立场与尼采“‘幸福者’:群氓理想”的激进精英主义的形而上立场尖锐对立。[7]189笔者认为,个体中心主义的文学理念一方面彰显了韩江的人本主义情怀,提升了小说的叙事温度。另一方面,平凡的小说人物作为“时代棱镜”,折射了潜藏在现代性神话之下普通个体的迷惘与苦痛,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深度。
五、总结
《素食者》通过“肉”这一重要意象、三组“吃与被吃”的关系和英惠姐姐这一人物的设置立体地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等领域遭遇的多重困境。正如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引用的狄德罗的观点:“束缚人类的锁链是由两根绳索做成的,假使另一根不断,这一根是不会松掉的。”[8]135如果不能更新旧有社会观念,实施有为的女性支援政策,女性困境这一现代文明的症候或难以消解。
笔者相信,随着立法保障的强化、社会治理的优化和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韩国将实现从“厌女社会”到“女性友好社会”的转型,《素食者》所展现的女性困境的“围城”也终将得到化解。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韩江.素食者[M].胡椒筒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
[3]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
[4]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5]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6]刘宏宇.弗洛伊德与荣格精神分析文学批评观比较[J].湖北社会科学,2014,(08):144-147.
[7]尼采.權力意志[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8]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
侯家琦,男,汉族,天津人,本科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现当代韩国文化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