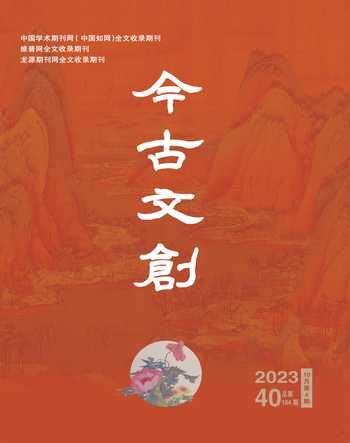论网络流行语“六(6)”的语言变异
2023-10-30熊美林
熊美林
【摘要】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人们的语言使用产生了影响,网络语言不断被人们使用,人们往往追求幽默、简洁的表达方式。语言使用者常常故意偏离语言常规,创造性地使用一些语言,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词发生了语言变异,以此来满足人们的表达需求。近年来以“六”构成的网络流行语在网民的交流中盛行,为满足人们的交际需要。以“六”构成的网络流行语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发生了语言变异现象。本文将从语言变异的角度来探寻“六”在网络语境中获得的新词义,以及语言变异的类型。
【关键词】语言变异;网络流行语;“六”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0-011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0.037
一、引言
近年来,短视频和互联网行业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方便快捷,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语言表达,尤其在年轻群体中,人们更愿意接受和使用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大多是指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现实社会发生的新闻事件出现在网络上,引起网民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的热门词语,也被叫做网络热词语。网络流行语最能代表语言的变异性,同时具有幽默、时尚、简单的特性(刘文良,2021)。维索尔伦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人们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做出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顺应性、以及协商性。语言的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束定芳,2014)。“变异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网络语言的变异性最能体现语言的这一属性,网络语言也常常被人们看作是网络时代的语言变异。(唐蕴,2016)。与语言的变异性不同,语言变异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目的,故意偏离常规,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本文将从语言变异的角度来分析以“六”构成的网络流行语的语言变异形式,以及在网络语境下“六”获得的新词义。
二、语言变异
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沟通时往往会遵守一些规则或者语言“常规”(norm),即语言社团所周知的,约定俗成的语言交际标准,然而,当在某些特定的交际语境下,语言使用者往往会刻意地偏离某些语言交际标准,能动性地使用语言,这就造成了语言的变化及其表达方式的突兀感,通过这种方式语言使用者实现了最精粹的语义表达。这种偏离语言常规的形式被称为语言变异(Languagedeviation)(柴磊,2005)。也就是说,人们在某种语境下为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打破了原本语言社团所公认的语言交际标准。但是这种违背语言交际标准的言语行为并未导致交际失败,反而更好地实现了交际双方的交际目的。语言变异与原型范畴有一些不同,语言变异是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下,打破语言常规,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语言变异强调的是对语言常规的偏离。而原型范畴理论是对“家族相似性”原理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原型范畴”主要是指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范畴,在原型范畴内包括原型和非原型的范畴。(黄钰涵、岳好平,2019)。原型是典型成员,它是范畴中的核心成员,与其它范畴成员相比,原型具有更多的属性,其他的范畴成员处于范畴的不同位置,其位置排序是以该范畴成员与原型成员的相似程度决定的,与原型成员相似性较低的范畴成员就构成了范畴的边缘成员,原型(prototype)在范畴的形成和理解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郑银芳,2007)。语言变异与原型范畴的侧重点不同。但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从认识语言学的视角下分析网络语言的语言变异现象,会发现语言变异利用了词义的相似性进行变异,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葛双林,2022)。也就是说语言变异和原型理论都是基于相似性的。两者即相区别,又有相同之处。语言变异并不是一种无序的、任意的变异,而是基于词语意义相似的方面进行变异的。
网络语言的变异是指语言在网络传播以及使用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變化偏离了某些现代汉语语言系统规则和标准(张婷,2014)。语言变异包括语音变异、语法变异、以及语义变异。通过分析发现网络流行语“六”发生了语言变异现象,主要涉及语音变异和语义变异。
语音变异是在语音层面上的变异,谐音变异是语音变异中最常见的一种。谐音变异又称语音造词,是指常规语言中所隐含的具体意义被用语音形式相同或相近的语言符号所指代。这里所提到的发音相近或相同的语音形式就是语音变异的具体形式(徐先梅、马冬,2015)。语义变异是指语义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形成了陌生化的效果。进行了语义变异的网络语言是一种与其常规语义不同的语言变体,这种网络语言的语义变异现象打破了其常规的语言形式,当然,这种语义变异并未完全脱离其原本的语义。其语义含有愈来愈少的原有语义特征,语义变异形成了新的语义和使用方式(李邦静,2016)。
三、“六”的常规语义概述
(一)五加一的和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的解释是:六是五加一后所得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六”是一个数词,是五加一的和。
(二)《易》卦之阴爻称为六
在《周易》中阴爻“--”用六来表示,坤卦用数字来表示就成了“六六六”。《周易》坤卦卦辞为:“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顺”就是这段卦辞的主要含义,即要守持正固安顺。因为“---”用数字表示即为“六六六”,于是“六”就成了“顺”的象征(黎治娥,2003)。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六”代表着吉祥,顺利。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互发红包常常发带有数字六的红包,来表达美好的期望。
(三)“六”还具有“满、全”的含义
佛教语言中也有不少与“六”相关的词汇,例如“六大”指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识大,亦称“六界”,此六者是构成众生世界的六种要素。“六根清净”指修行之人六根不染六尘。“六根”泛指人的各种感官。“六欲”指人的六种欲望,泛指一切阻碍修行的感情愿望。因此,“六”隐含的“满、全”之义更加凸显(王丽会,2017)。例如:成语“五脏六腑”意思是人体内脏器官的所有总称,“五亲六眷”是指各种关系的亲眷。其中“六”都隐含了“满、全”的意义。
四、“六”在网络语境中的新词义
在分析网络流行语“六”时,语境对于词的使用、以及其语义的识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境即言语环境,语境既包括语言内部因素和语言外部因素,语言内部因素是指句法或者语篇的上下文,语言外部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参与者和方式等(魏在江,2016)。因此,在理解和使用网络流行语“六”时,要充分考虑语境因素避免产生歧义,注重语境的影响以此来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或交际效果。以“六”构成的网络流行语在网络语境中获得了新词义。通过分析发现,以“六”构成的网络流行语发生了语言变异现象,其语言变异主要涉及语音变异和语义变异两种类型。
(一)通过语音变异的方式构建新词义
谐音变异是语音变异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网络流行语“666”是口头语“溜”的谐音数字。在口头表达中“溜”常常有熟练、很厉害、很牛的意思。例如:当你和朋友在一起组队玩游戏时,你的队友对你说“666”。意思是夸赞你玩游戏玩得很溜很厉害。在这种语境下“666”常常用来形容某人或某事很厉害,是一种夸赞。网络流行语“666”就体现了谐音变异,当人们单独看“666”和“溜溜溜”时,可能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然而,在网络语境下人们使用“666”,正是利用了“666”与“溜溜溜”之间相同的语音形式用来指代“溜溜溜”的常规语义。
(二)通过语义变异的方式构建新词义
1.“666”
网络流行语“666”通过网络在各大平台不断传播,其意义迅速被人们接受。在人们不断的使用中,网络流行语“666”发生了语义变异,在某些语境下“666”代表一种反讽、调侃。有人会把“666”当作一种反语来使用。例如:当你玩游戏和队友配合不好,让你的对手胜利时,你的队友对你说“666”。在这种情况下,“666”是一种反语,用来调侃你。
2.“6”
“6”在现代网民的认知里,单独使用网络流行语“6”不是一个简单的数词,在网络语境下,“6”常常单独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它隐含了不屑、敷衍、嘲讽的意义。例如:别人给你分享了很多对方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你就只回复了“6”。在这种语境下,“6”就有了敷衍的意味,也代表着你不愿再和他深入聊天。在过去“6”常常作为数词使用,常用来表示数目或次序。在网络语境下“6”获得了新的词义,常常被人们单独使用。人们在使用该词时打破了过去语言社团公认的语言常规。
3.双击“666”
双击“666”通常广泛应用于抖音或快手短视频中。例如:
新进直播间的老铁们,双击“666”。(快手)
直播间的家人们,如果喜欢我的舞蹈,请双击“666”。(抖音)
双击“666”原本是一种快手文化,后来被各个主播广泛使用。双击“666”代表着喜欢这个视频或者直播间,点赞的意思。现在,网络流行语双击“666”成了主播与网友们互动的一种方式。主播常常通过这种方式与直播间的网友们建立联系,拉近主播与网友之间的心理距离,活跃直播间的气氛。
4.老六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老”的第十六个释义为:前缀,用于称人、排行次序、某些动物名。“老六”,顾名思义,是排行第六的意思。例如:
她原本是山西祁县人,家有8个兄妹,她排行老六。(《作家文摘》1996)
老六的本义是排行第六的意思(杨洁琼,2022)。但在现在的网络语境中,“老六”这个词发生了语义变异获得了新词义。“老六”最早被人们在游戏CSGO的竞技模式中使用,每队都有5名成员,人们常常用来代指那些玩游戏玩得不好或者脱离团队四处游荡的成员。随着网络流行语“老六”在网络中不断盛行,使用该词的人愈来愈多,这一词不仅仅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使用,还可以表示某人做事的方法,思维模式与常人不同,在网络语境下“老六”这一词并不含贬义,常常用来调侃某人,并没有敌意(杨洁琼,2022)。例如:当你的朋友想去找喜欢的女生却又不敢时,你可以说:“你这个老六什么时候才能勇敢点呢。”“老六”在网络语境中并不含有贬义,常常用于朋友之间。
5.六公主
“六公主”在网络语境下并不是指某个国家的第六位公主,而是指中国的中央六台CCTV6(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公主”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君主的女儿。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公主具有傲娇、任性、与众不同的特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中央六台CCTV6因其对待新闻事件,热点事件持有独特的观点,以及它无所畏惧,敢说敢言的特点,被人们称为“六公主”。“六公主”在网络语境下发生了语义变异。“六公主”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语的一大原因是,它暗含了隐喻机制。“六公主”一词隐喻了中央六台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与众不同,对于事物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个隐喻机制是基于中央六台与公主形象之间的相似性。当然,语境对于隐喻的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们想要理解隐喻时必须充分考虑语境因素,正确地理解语境(魏在江,2018)。
五、结语
汉语词“六”在中国人的认知里代表着顺利,吉祥。人们常用它來表示美好的祝愿和期许。随着互联网和短视频的不断发展,“六”在网络语境下发生了语言变异。通过分析发现“六”的语义建构模式主要涉及两个类型。一是语音变异,主要涉及的是谐音变异。二是语义变异。在网络语境下以“六”构成的网络流行语共获得六个新的词义。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流行语“666”在网络语境下进一步发生了语言变异,获得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语义。一个语义形容某人或某物很厉害,很溜,是一种褒义。另一个语义表达了不满,调侃,反讽。在使用这一网络流行语是人们应该注重对语境的把握,避免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造成交际失败。网络流行语“666”的两个语义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表达夸赞的语义最先被人们使用,表达反讽的语义后来才进入人们的视野。由此可见语言变异并不是一种无序的、任意的变异。
丁崇明教授认为语言变异可分为5个阶段,即个人语言变异、部分人模仿变异、部分群体模仿变异、泛群体变异和言语社团变异等阶段。个人语言变异是指某个个体的语言产生了新的语言形式。部分人模仿变异是个人的语言变异得到了其他人的效仿。与部分人模仿变异相比群体变异要更加深入,模仿的人数增加,就形成了一定的模仿群体,这种变异阶段更加稳定,具有有序性,该变异与社会要素形成了其变的联系。泛群体自然变异更加深入,再继续发展就成为了言语社团变异,此时言语社团普遍地接受这一语言变异形式,该语言变异形式具有完全规范性,至此语言变异过程也就结束了(丁崇明,2002)。例如:双击“666”最初是一位东北的快手短视频博主在直播时使用,该词发生了个人语言变异,后来通过该直播间的网友不断模仿就发生了部分群体变异。随着双击“666”一词在网友间不断的传播和应用发生了群体变异。群体变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变异成分与社会因素建立了共变的联系。我们发现双击“666”不仅限于在直播间使用,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应用。最终,双击“666”这一变异形式得到了言语社团的普遍接受,至此这一变异过程就结束了。以“六”构成的网络流行语遵循了语言变异的五个阶段。这些网络用语被人们创造性地使用,获得了新的词义,同时这类词也丰富了人们的语言表达。
参考文献:
[1]陈红波.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的网络新词语语义构建研究[J].科技视界,2021,(14):58-59.
[2]柴磊.网络交际中的语言变异及其理据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05,(02):43-46.
[3]丁崇明.语言变异与规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6):78-82.
[4]葛双林.探析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网络语言变异[J].作家天地,2022,633(36):97-99.
[5]黄钰涵.岳好平.原型范畴理论下网络流行语的语义分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5(08):70-72.
[6]黎治娥.數字“六”小议[J].汉字文化,2003,(01):9-11.
[7]李邦静.网络语言的语义变异现象[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3(08):131-132.
[8]刘文良.网络流行语语言变异现象的社会语言学解析[J].汉字文化,2021,(16):16-17.
[9]束定芳.什么是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10]唐蕴.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网络语言[J].科技视界,2015,(13):180.
[11]王丽会.汉语词“六”略论[J].青年文学家,2017,618(18):164-165
[12]魏在江.语境与隐喻的产生与理解——认知语言学中的语境研究之三[J].中国外语,2018,15(06):33-38+47.
[13]魏在江.认知语言学中的语境:定义与功能[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39(04):39-46.
[14]徐雪琳.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网络语言变异[J].黑龙江科学,2020,11(03):54-55.
[15]徐先梅,马冬.网络流行语语音变异形式及御用效果分析[J].理论观察,2015,107(05):127-128.
[16]杨洁琼.网络流行语“老六”初探[J].汉字文化,2022,323(S1):233-235.
[17]张婷.汉语网络流行语词汇变异现象的社会语用分析[J].民俗研究,2014,(05):116-121.
[18]郑银芳.谈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J].中国成人教育,2007,(20):124-125.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