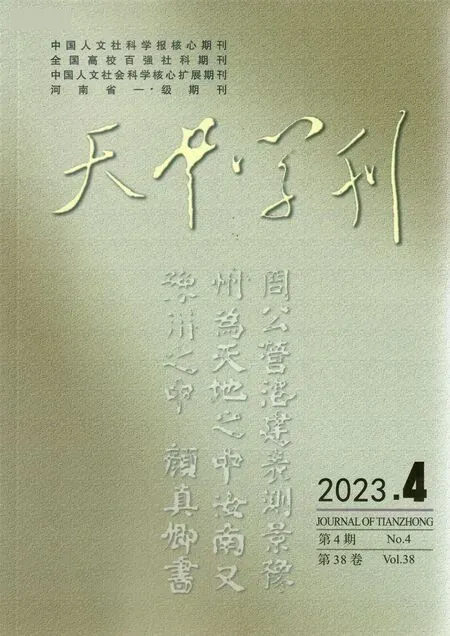六朝美学与文论“心”范畴发微
2023-10-28程景牧
程景牧
六朝美学与文论“心”范畴发微
程景牧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心”是六朝美学与文论中的一维极其重要的元范畴,其衍生出“用心”“会心”“师心”“游心”“动心”等多种美学范畴,不仅仅渊源于玄学与佛学的理论概念,更得益于六朝“心丧礼”的催生。“心”范畴广泛运用于六朝书画、音乐等艺术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等众多美学领域,美学蕴涵不断丰富,学理价值持续增益,尤其在文学批评领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呈现出理论的系统化与多元化统一的发展态势,获得了永恒的美学意义和文艺价值。
六朝美学;文学理论;心范畴;学理蕴涵
“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古典美学与文论的重要范畴,自先秦以来即是一维重要的概念术语。六朝时期,“心”的内在蕴涵与艺术价值在美学领域得到了充分呈现和极大拓展,不仅衍生出“用心”“会心”“师心”“入心”“游心”“动心”等次范畴,而且在书画、音乐、文论等领域发挥着持久恒定的作用。“心”作为元范畴在六朝美学与文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至今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当下关于六朝美学与文论中的“心”及其衍生的诸多范畴的研究成果均较为零碎、不成系统,笔者有鉴于此,尝试对六朝美学“心”范畴做一番系统梳理与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心”范畴的学理蕴涵
“心”范畴在先秦时期的诸子典籍中即得到广泛运用,而正式进入美学领域,成为美学范畴,则是在六朝时期。六朝时期是我国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期、大转折期与自觉自立期,儒释道三家思潮开始交融,玄学与儒学分庭抗礼。儒学、玄学与佛学是六朝时期的三大学术思潮,六朝美学的发展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三大思潮交融与博弈的结果。作为六朝美学的一个元范畴,“心”概念的产生和衍化既得益于玄学与佛学的义理,又脱胎于礼学中的“心丧礼”。
如果说汉代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是由外及内的,那么六朝玄学的内在理路则是由内及外的。换句话说,汉代经学着眼于外在的社会政治,六朝玄学着眼于内在心性。正始玄学的代表者何晏、王弼建构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即“贵无论”,提倡名教本于自然,为了更好地诠释“以无为本”,王弼对《周易》复卦进行了阐释,将无与本、天地之心紧密地联结了起来。他在《周易注·复》中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1]王弼指出“复”的运动为天地之心的表现,而天地以至静为本,本即为至静或无,复则是复归其本,这个本即是心、即是无、即是自然,以无为心、为本、为自然即是王弼贵无论的落脚点。基于此,王弼进而揭示出天地之心即为宇宙的本体。因此他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三十八章中指出:“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2]天地之心即是以无为本的具体彰显。在以心为无、为本的贵无论的基础上,王弼又进一步提出崇本举末的理论主张,而要实现崇本举末,就离不开强调言象意的一致性,所以得意忘象忘言、言不尽意的思想理论即成为玄学的重要命题,而这其中的“意”,即是与心联系在一起的“心意”,是心的一种外在呈现。可见王弼易学对心范畴是极为重视的,所以刘宋时期颜延之在《清者人之正路》中讲到易学时说:“荀王得之于心,马陆取之于物,其无恶迄可知矣。夫象数穷则太极著,人心极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3]358颜延之对荀爽与王弼的易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得之于心”,而“人心极而神功彰”,他们的易学“极人心之数”,即达到了最高的学理境界。竹林玄学的代表嵇康、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与“心”密切关联的。嵇康《释私论》云:“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4]368可见,越名教任自然即是越名任心,任心才能越名教,自然即心,心即自然。西晋玄学的代表郭象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主张名教即自然,当然也离不开“心”这个概念,如其在《庄子·逍遥游注》中主张要像圣人一样“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5]28、“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5]268。可见,魏晋玄学三个阶段的理论主张,无论是名教本于自然,还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抑或是名教即自然,均与“心”这个概念范畴具有密切的关联,“心”在玄学义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心”成为六朝美学的重要范畴与佛学也有关联。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著及佛学论著大量涌现。佛学教义本身即着眼于心性理论,所以关于性空、实相、心无等理论的探讨成果极为可观,如道安撰有《性空论》,《心经》在三国时期由支谦译出,嗣后又有鸠摩罗什的译本。晋代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中即有以温法师与支愍度为代表的“心无家(宗)”:温法师主张空心,无心于万物,不滞于心外物;支愍度则创立了心无义,主张从绝对虚无又顺应内心出发来观照万物,而不关注对象世界的有无问题。“心无家(宗)”影响极大,僧肇在《不真空论》中指出心无家(宗)的理论成果之得失在于神静与物虚之间,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梁代僧祐所编的《弘明集》涉及中古时期佛教的诸多基本教义,而关于“心”教义的讨论文章数量也极为可观。可见,对“心”的探究是六朝佛学的重要论题。
如果说玄学与佛学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来讨论“心”之概念,儒家礼学则更多地从形而下的层面进行“心”的理念之实践。六朝时期是士族社会,士族需要借助礼学来维系门第、区分等级,是以礼学得到复兴,三礼之学突飞猛进,五礼制度不断完善,清人沈尧落在《与张渊甫书》中指出六朝人最精于礼学。由于丧服礼最能集中彰显出亲疏等差、门第高低,所以在六朝时期,尤其是西晋以后丧服学愈发兴盛起来,涌现出大量丧服学著作。曹魏政权取消了三年之丧的制度,西晋建国后,晋武帝恢复了三年之丧,并提倡与践行心丧制度。晋武帝提倡以孝治天下,其为父亲司马昭服心丧三年。武帝在诏书中解释自己的服丧之举云: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绖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食稻衣锦,诚诡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剥,奈何!奈何![6]614
武帝指出自己出生于世代传礼的儒学世家,当然要按照儒家礼制服丧,而且这是孔子所倡导的,也是人之常情的自然彰显。所以,武帝在全国推行三年心丧之制,得到了大臣们的赞同,如司马孚上疏云:“陛下随时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权制,既除衰麻,而行心丧之礼,今复制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参议宜如前奏。”[6]615在晋武帝君臣的倡导和影响下,心丧礼也越来越正规起来,成为王朝的正式礼制。东晋琅琊王属官丁潭上疏请为琅琊王司马裒服丧三年,元帝“于是诏使除服,心丧三年”[6]2064。南朝刘宋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丧三年”[7]395。心丧礼不但成为定制,而且心丧礼之期限、服装与仪式也得到了礼学家的重视与探讨,不但《晋书》《宋书》《南齐书》《陈书》《隋书》等史书记载了诸多讨论心丧礼的事典,而且贺循《丧服要记》、王俭《丧服古今集记》、何佟之《仪注》也对心丧礼进行了详尽的诠释。可见,作为凶礼的一种,心丧礼是六朝时期五礼制度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六朝缘情制礼思想的一种具体实践,表现出情与礼的融合。礼学与礼制建设对于人的情感的重视,即是对人们内在心灵的空间重视与感知。六朝时期的礼学影响极大,对“心”的体认与感知,促使人们在礼制建设中自然而然地推行心丧制度。
总的来说,“心”范畴在六朝时期的发展与衍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学理思想蕴涵。对心的空前重视与认知是时代发展的逻辑必然,长此以往即形成了一种对“心”进行探究、考察与运用的集体无意识。《世说新语》记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8]107–108很显然,简文帝提出“会心”这个概念是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又如“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8]110桓温在此提出“入心”这个概念,与当时的儒学尤其是礼学对心的重视是有关联的。再如“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8]730王坦之在文中提出“纵心”的概念,深得佛理之妙。无论是玄学、佛学、儒学,抑或是政治制度皆对“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皆倾向于在“心”的概念与范畴上做文章。而在六朝,玄学、佛学、儒学三大学术文化思潮又是在冲突对立之中不断交融汇合从而发展演化的。对“心”的共同重视与阐发,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六朝学术的多元性与整合性。可以说六朝美学的“心范畴”具有儒、玄学、佛学共同的学术思潮背景与文化基因,同时亦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因素,因此“心范畴”的学理蕴涵较为复杂但又是可以理解的。
二、“心”范畴在六朝书画音乐理论中的拓展
就六朝美学的整体性而言,“心”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在书画理论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书画作品属于视觉艺术,具有强烈的直观性,其艺术境界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学养与技法,在具体创作层面,则主要是心与手的高度合作与协调。六朝书画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远逾前代,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书画理论极为成熟,彰显出对创作根本的体认,即对“心”的重视与探讨,这自然是六朝学术文化对“心”的重视所致。
在书法理论方面,东晋女书法家卫烁论述执笔云:“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又有六种用笔,结构圆备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超妙矣。书道毕矣。”[9]1563卫烁将执笔问题归结为心手问题,主张心手缓急要协调好,强调“意在笔先”,而这个“意”即是“心”,所以她在后面强调用笔前要“心存委曲”,用心揣摩,如此方能使书法创作臻于妙境,书道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书圣王羲之曾随卫烁研习书法,其书法理论表现出对“心”强烈的重视。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9]260他将书法创作比喻成打仗,将心意比喻成将军,认为先要用心构思,然后方能写字,王羲之在这里提出的“意在笔先”,即是“心在笔先”,强调的是心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书论》中又有不同的比喻:“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仍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心欲急不宜迟,何也?心是箭锋,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10]29同样是强调意在笔先,字居心后,此文将笔比喻为将军,将心比喻为箭锋,强调的是“心”的重要性,即要求“心欲急不宜迟”,主张在书法创作过程中达到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之境界。此外在《笔势论十二章》的《启心》一章中,王羲之也集中探讨了“心”在书法创作中的功用。学界一般过于强调王羲之“尚意”的书法理论思想,而忽略了他“重心”的思维理路,其实“尚意”即是“重心”,心与意比起来更具有决定性、枢纽性与本元性。
萧齐书法家王僧虔也极为重视心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其《笔意赞》云:“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10]62他强调书法家要心、手、笔相忘,达到主客合一的精神状态,才能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仪平策指出王僧虔的意思是:“即在以心为本、以意为主的基础上,达到心手两忘、笔意相契的创造境界,实际上也就是讲究写意与象形、表情与用笔、必然与自由的中和兼备,均衡统一。”[11]王僧虔《书赋》云:“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风摇挺气,妍孊深功。”[12]76强调心在书法创作中的中枢地位,建构了“心—手—毫”互动的书法创作结构模式。梁武帝萧衍酷爱书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卫烁、王僧虔等人的书法思想,他在《论萧子云书》中说“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13]68,在《答陶弘景书》中指出书法作品“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13]58,提出了“适眼合心”的书法美学观点,认为书法作品的好坏关键在于是否“合心”。
六朝书法理论彰显出明显的重“心”美学倾向,以心为本、以意为主,心与意为“心”的一体两面,所以与其说六朝书法理论尚意,毋宁说“尚心”。与书法理论相呼应的是,六朝画论也彰显出强烈的重“心”精神。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论画》中评价卫协画作《北风诗》云:“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14]33顾氏指出画作的神气主要取决于画家内在的心灵,画作之神仪乃人心之达,所以他提出了“迁想妙得”的美学思想,强调画为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晋宋之际的书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3]192十分重视心在绘画中的重要性,所以强调作画应达到“应目会心”“目亦同应,心亦俱会”的状态与境界。宗炳提出了“应目会心”的画论美学主张,重视内在心灵对自然万物的体察记忆,主张绘心写意,追求一种心灵超越外在事物、具有神味意趣的理想创作境界,“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即是对心的自由境界的追求。刘宋时期另一位书画家王微在《叙画》中指出:“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亡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固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14]48与宗炳一样,王微也认为作画是画家内在心灵的彰显与外化,只有将外在的物体形状与内在灵动的心融汇起来,山水之形与人之心灵熔铸弥合,心物相应,交感变化,才能最终达到“拟太虚之体”“画寸眸之明”的境界,才能在笔墨间彰显出灵动的神采气韵,世俗之心也随之升华为美学之心。宗炳与王微运用“心”这个范畴将绘画从以往的合政教之用转化为内在心灵的抒写,其画论彰显出重“心”的美学取向。宗炳与王微二人重“心”的画论美学思想是与当时的学术文化思潮相对应的。宗炳作为一个佛教徒、居士,曾参加慧远主持的“白莲社”,其《明佛论》等著作收入《弘明集》中,《画山水序》即彰显出浓郁的佛学思想。南朝陈代姚最在《续画品》中评价梁元帝的画作云:“右天挺命世,幼禀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非复景行所能希涉。画有六法,真仙为难,王于像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12]400姚最用“心师造化”“心敏手运”描述梁元帝的绘画造诣,点明其画作“特尽神妙”之缘由,由此可以看出“心”在绘画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音乐虽不同于书画,但音乐美学理论在六朝时期也同样彰显出对“心”的重视。六朝以前,学界普遍认为音乐从根本上说即是心之声,所以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之说。但嵇康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琴赋》中说遁世之士“羡斯岳之弘敞,心慷慨以忘归。情舒放而远览,接轩辕之遗音,慕老童于𱅡隅,钦泰容之高吟,顾兹梧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乃斫孙枝,准量所任,至人摅思,制为雅琴”[4]127。在嵇康看来,遁世之士为了借助外物抒发内心的情思,所以制作雅琴,“于是器冷弦调,心闲手敏,触如志,唯意所拟”[4]128,“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憯懔惨凄,愀怆伤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4]130。可见弹奏乐曲既可以抒发弹奏者内在的心意情感,又能感染听众,使内心幽怨的听者情不自禁地“愀怆伤心,含哀懊咿”,这样便使得主客体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情感共鸣。在赋的结尾,嵇康说道:“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嵇康将琴德与内心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均是变幻莫测、幽邈难觅的事物,琴音是隐士心声的代言者,而隐士心声即自己的心声,所以琴音本身并无哀乐之情感,而是士人内心的彰显。他在《声无哀乐论》中探讨了音乐与人心的关系,提出了“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的音乐美学思想:
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4]316
夫声之于心,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4]323
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4]325
嵇康指出音乐与人的情感毫无关系,情感的哀乐是先于音乐而存在的,音乐仅仅是一个促使心曲得以宣泄的媒介,所以他说“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摆脱了两汉政教理念的束缚,彰显出玄学思想的特质,对揭示音乐的美学本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嵇康对音乐本质美的探索,还是基于心物关系的探讨,进一步说即是探究心与声的关系,可见心范畴在音乐美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书法史上,有晋人尚韵的说法,所谓“尚韵”,即是指书法作品具有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潇洒飘逸、放浪形骸的丰神情韵,彰显出魏晋风度。但如果寻绎晋人自己的书法理论,与其说是“尚韵”,不如说是“尚意”,或者进一步说“尚心”更好。六朝的书画美学集中体现了“尚心”的特点,彰显出对心灵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六朝的音乐美学思想则不但表现出对心灵的重视,同时更体现出对心灵的再认识。总之,六朝书画音乐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不断地发展完善,开拓了六朝美学思想,而“心”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与概念,在书画音乐理论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心”范畴在六朝文论领域中的发展向度
“心”范畴的美学蕴涵在六朝书画音乐理论中得到了发展,构成了六朝美学的重要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心”范畴不仅在上述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文学领域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论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进一步完善了六朝美学的蕴涵。“心”范畴在六朝文论中的发展呈现出多维向度的发展趋势。
魏晋之际的学者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追溯辞赋的发展史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9]756–757他赞扬荀卿、屈原的辞赋有“古诗之义”,即风雅之韵,因文寄心、托理全制,故能成为辞赋中的上乘之作。因文寄心即借助文章寄寓心志,皇甫谧提出寄心这个概念,彰显出其对辞赋本质的看法及其衡赋标准。
西晋陆机《文赋》主要讲文学创作的构思问题,文中多次用“心”进行立论阐释,如《文赋》序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9]1024所谓“用心”,即创作时的心思构想。陆机十分关心才士创作时的“用心”,其撰写《文赋》的动机即是担心文士在创作时“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里的“意”,即心、心思之谓,可见《文赋》的写作缘起即与“心”有密切关系。陆机在《文赋》中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艺美学命题——“诗缘情而绮靡”。缘情即心有所感,情之所系则源于外物的触发,所以他在阐述创作的冲动时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9]1024陆机强调诗人因为对外物的变化极为敏感,以致“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敏感的内心催促着文士进行文学创作。在讲到艺术创作的第一个环节——构思时,他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9]1024“心游万仞”指的是心灵的任意驰骋,也即构思的浮想联翩。心在创作构思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与司马相如“赋家之心”说、刘勰“神思”说的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他说:“吐滂沛乎寸心”“惬心者贵当”[9]1025,认为文章的宏大思想皆出于小小寸心,文章写作要合情合理,使心灵快意才是得当之作,“惬心”既是写作动机也是写作目的。在具体谋篇布局、按部就班地进行创作时,就要“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9]1025,即要排除杂念、澄净内心、专心思考,将内心的话语整合为语言文字。陆机在此又提出了澄心的概念,澄心即静心,这与道家虚静,“涤除玄鉴”的美学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在论及具体创作问题时,陆机还说“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虽浚发于巧心,或受㰞于拙目”[9]1026,无论是以牢落说心,还是以巧说心,均离不开对心的重视与体察。可以看出,“心”在《文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章的立意、阐述均离不开对“心”的演绎与拓展,遂产生出“用心”“澄心”“寸心”“惬心”“巧心”等文艺美学范畴,对后世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臧荣绪《晋书》云:“(陆)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作《文赋》。”[15]239即看到陆机对“心”的重视。
晋宋之际,山水文学兴起,诗赋作品以自然山水为题材演绎出一片新的文艺天地,究其本质还是在玄学思想的感染下对内在心灵的体察与观照。元嘉诗坛三大家之一的谢灵运在《山居赋序》中说:“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7]1754谢灵运认为就内在心灵来说“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彰显出他随遇而安的心态,而作赋的动机是“顺从性情,敢率所乐”,即点明心灵为辞赋创作之本源。谢灵运还指出自己摒弃汉代以“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为题材的创作思路而代之以“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的格局,主要原因还在于“心放俗外”,因此赋作要“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即以自然清丽为本,不屑于雕琢修饰,彰显出老庄自然之旨趣。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赋是与心范畴密切相连的。
在南朝儒、释、玄、道多元学术文化思潮交融的背景下,文人继承了魏晋以来重心的文艺思潮,在文论领域对心的内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开掘。萧齐张融《门律自序》云:“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16]729南朝文风以“新变”为尚,张融也主张新变。他认为文章不应拘于常体,更不能因循守旧,所以他开篇即提出“师心”的文章创作主张与美学概念,可见新变与师心是相辅相成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艺理论对心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其《文选序》云:“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13]222萧统说自己阅读文学作品时“心游目想”,即强调“心”在阅读思考中的重要地位,而他选录文章的标准“事出于沉思”,也是对心游目想的另一种表述。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密亲离则手为心使,昆弟晏则墨以亲露。”[13]216萧统点明自然万物变化引起心灵的感悟与变化,从而施墨于笔端,进行文学创作。萧统提出了“心游”“心使”的美学概念,是对心的进一步开拓。萧子显与萧统一样,也对心的范畴进行了开掘,他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16]907萧子显首先提出性情为文章之风标,接下来又指出文章的“气韵天成”是由内心的游运促成的,他的“游心内运”与萧统的“心游目想”内蕴是一致的。作为萧统的弟弟与继任者,简文帝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说:“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13]114萧纲提出了“写心”的文学创作观念,这也是当时文人的共识。在《与湘东王书》中,萧纲写道:“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17]690此处之“用心”与陆机《文赋》之“用心”内涵一致,均指作家的构思想象。作为萧统与萧纲的弟弟,梁元帝萧绎在文论著作中也表达了与乃兄一致的文学观念,他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说:“子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顷常搜聚,有怀著述。”[13]195与萧子显一样,萧绎提出了“游心”的文艺创作观点,这与萧统“心游”、萧纲“写心”“用心”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诗歌的“三义”说,三义即兴、比、赋三义,并进一步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8]19他认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应当将此三义结合起来,方能使“闻之者动心”,以此达到诗歌的极致境界,“动心”即诗之至的标志。钟嵘在感物说中列举了大量例子,用以阐述诗人感物而作诗的创作过程,他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者,莫尚于诗矣。”[18]20–21他指出外界自然景物和人文事典均能“感荡心灵”,是故陈诗骋情、兴观群怨、慰藉心灵皆自然而然之事了。在具体品诗中,钟嵘称赞《古诗十九首》云:“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8]32“惊心动魄”四字形象生动地昭示出读者在诵读古诗时的心理反应,其力度比动心、感荡心灵来得大且深。可见钟嵘的感物说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感心说,探讨的其实是心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上文论作品虽然重视对心的演绎与阐发,但较为零碎,不成系统。《文心雕龙》从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几个角度,多层面地探讨了心的美学蕴涵与艺术价值,对心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建构。在本体论中,《原道》篇指出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9]1。在这里,刘勰将心灵看做文章之本源,并在文章最后的赞语中说“道心惟微,神理设教”,“道心”指的是道之精意,也是人之心的另一种表现。在文体论中,刘勰对心的阐述主要集中在《乐府》《哀吊》《书记》三篇之中。《乐府》篇云:“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19]102点明诗歌为音乐之心灵,强调的是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哀吊》篇云:“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19]240刘勰指出因痛心而作文便情辞切当,而为了文辞而抒发痛心则显得浮夸造作,主张为心而造文,反对为文而言心。《书记》篇指出“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19]456、“述理于心,著言于翰”[19]457,即是认为心为文章之本源,强调心之作用。在创作论中,刘勰更是对心做了集中而深刻的论述。《神思》篇云:“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19]493《神思》篇是创作总论,主讲构思问题,具有浓重的玄学色彩,刘勰在这里主要论述了形体与心灵的辩证关系,指出神思是以心为本的,可见心在创作构思中的重要性。在赞语中,他说:“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19]495这里涉及了心物关系:心物交感互动,所以文章的声律与比兴手法自然就萌生出来了。《情采》篇赞语云“心术既形,英华乃赡”[19]539,即是说内心的情思通过文辞彰显出来,文采方显得丰富。可见,刘勰将心放于首位,将辞采置于其后,以心统文。刘勰在此处提出了心理、置心、心定、心术等范畴与概念,对心的范畴做了较为全面的拓展。《隐秀》篇云:“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19]632这与《情采》篇一样,同样提出了“心术”的概念,强调心术在文章情感抒发中的重要作用。在批评论中,刘勰对心也进行了相关阐释。如《才略》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19]700这里也提及了“师心”的概念。在最后的《序志》篇中,刘勰阐释了文心的含义:“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19]725在赞语中又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这里使用“用心”以诠释文心之心,用陆机之说,进一步强调了心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在六朝文论中,心的美学内涵得到了多向度的开拓,从创作论、本体论到文体论再到批评论,心范畴的蕴涵显得越发深邃,越发具有深刻意义,这是书画及音乐理论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说能够真正体现六朝心范畴学理蕴涵的,非文论莫属。
心范畴在六朝儒、玄、佛等多元学术文化背景中得到不断演绎与推阐,因而具有了深刻的、区别于以往的美学蕴涵与学理价值,从书画、音乐等视听艺术理论到文学批评理论,心范畴的美学蕴涵不断得到转移、拓展与阐发,相应的美学价值也不断地得到深化。学界以往论及六朝美学与文论,大抵好以尚韵、尚意来概括其特质,但尚韵、尚意的背后其实是尚心在起根本作用,心才是六朝美学与文论尚韵、尚意的原动力,是以心这个元范畴以及用心、会心、师心、游心、动心、隐心、心术等次范畴共同建构了六朝美学与文论心范畴的思想体系与理论系统,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1]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336–337.
[2]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93.
[3] 严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刘孝标,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 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11] 仪平策.中古审美文化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16.
[12] 严可均.全齐文全陈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3] 严可均.全梁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 俞剑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一编:先秦至五代画论[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15] 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239.
[16]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7]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90.
[18] 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9]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I209
A
1006–5261(2023)04–0084–09
2023-03-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2YJC751009)
程景牧(1985― ),男,安徽凤阳人,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