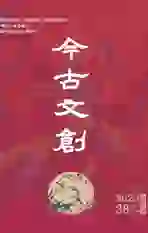生存的焦虑与位置的缺失
2023-10-27吴丽婷
【摘要】作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黄春明的小说创作格外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在其短篇小说《两个油漆匠》中,黄春明将笔触深入到离开家乡而游走在城市边缘的两位青年身上,透过他们的生存境遇表达出对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注与思索。本文便通过身份的缺失与边缘、生存基础的摧毁以及沟通的断裂与失效这三个方面内容,对现代都市发展如何抹杀小人物的尊严与价值进行了探寻。
【关键词】黄春明;小人物;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8-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8.005
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黄春明以自己的笔触描绘出了台湾乡土的风貌,以及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乡土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危机。曾建民曾指出:“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关怀社会、关怀乡土以及关怀底层民众的文学精神,在文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年代中,起了开创性和启蒙性的作用,成立‘乡土文学’的范本之一。”[1]纵观黄春明的小说创作,底层小人物的故事占据了黄春明绝大多数小说的主题,他也因此被台湾文坛称作小人物的代言人。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处境的特殊,传统的乡土文明被都市的物质消费文明无情倾轧,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愈发艰难,他们面临的不只是家园的失去,同样还要面对着谋生的艰难、尊严与地位的丧失以及沟通的断裂。黄春明为底层人民发出了声音,对他们的人生与内心进行了深刻理解,并对他们充满悲剧性的命运给予了无限的温情。
《两个油漆匠》是黄春明1971年发表的作品,此时,依靠外来势力发家的中产阶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的下层民众却深受剥削与压迫,“他们的人格和民族尊严又备受拜金主义风气的腐蚀和洋商买办的凌辱”[2],与此同时,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农村劳动力向都市的流入、城市中的自杀率不断上升、环境污染问题等等。黄春明这一阶段的乡土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巨变而造成的后果进行反思,《两个油漆匠》讲述了两个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谋生的青年在工作结束后爬到高空倾诉苦闷,却被误以为是要自杀寻死而引来了警察记者的关注,一场闹剧过后猴子却真的一跃而下,以真正的悲剧而收场。黄春明在小说中对来自异乡的边缘小人物的悲惨而压抑的生活给予了关注,通过这两个具有典型性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可以探析出当时台湾的台湾人民如何在内外的夹击中艰难生活。本文旨在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两个油漆匠》中导致小人物生活困境的原因,即身份缺失与边缘、生存基础的毁灭以及沟通的失效,从而探究出台湾复杂背景下现代化的发展为底层人民和传统乡土带来的影响。
一、身份的缺失与边缘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为身份一词下了一个定义,即“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3]。作为社群中的个人,只有取得了一个合理的身份,即在他人的眼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和重要性,才能取得存在的合法性。這种身份的意识促使每个个体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定位,以此获得社会上的认同。而身份的缺失则意味着社会对于个体存在的背弃,失去身份的人在社会中只能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卑微地生存,这种对于身份的重视自古以来便成为社会的共识,而其程度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变得愈发加深。《两个油漆匠》中的猴子和阿力是两个远离家乡在都市里谋生的油漆工,来到城市之后,他们面临的状况是原有的家庭身份和都市中的社会身份的双重缺失,这种身份上的缺失带给他们的是生存地位的边缘化和自尊的丧失,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之下,他们无所适从,只能被迫背负起社会中牺牲者的命运。
阿力和猴子是同乡,来自东部山间的金家厝,乡村生活的凋敝使得他们十分渴望走出家乡。城市对他们而言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他们不顾一切地抛下了原本的乡土生活,毅然踏上了外出谋生之路。出走之后的他们失去了原本的家庭身份,即便后来都市生活带给他们的只有无助和痛苦,他们还是坚定地选择不再回乡。阿力和家里的唯一联系,便是每月向家中汇款,一想到母亲,阿力脑海中浮现的便是母亲向他哭诉生活的不易。母亲的来信催促着他快些寄钱回家,言语间并没有关心阿力在异乡是如何的艰苦和无助。阿力每个月需要借钱来补足为家里汇款的数额,经济压力使他无法安心地离开城市重返家乡,而在他无法及时向家里汇钱时,他内心的罪恶感也油然而生,经济关系成为维系家庭关系的唯一重要纽带。而猴子则是主动地放弃了家庭中的身份,小说中并没有提到猴子的父母,他与大伯和伯母一起生活,他的大伯经常赌钱且输个精光,他渴望着掌控自己的生活,他对家庭充满了厌恶,甚至不愿再踏上有伯父生存痕迹的土地。猴子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家庭身份,带着一种青年人的异想天开彻底挣脱了家庭身份的束缚。在从乡村向城市蜕变的发展过程中,青年人在经济与社会的裹挟下与故土决裂、与亲人分离,成为了失去身份的出走异乡的流放者。
家庭身份的失去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获得了向外的自由,但也使他们失去了内心之根。他们来到城市却没有在社会中找到相应的身份与地位,茫然无措地在城市中做着无聊的工作,他们被遗忘在城市的角落。猴子形容他们从家乡来到城市是“下火车搭贼船”“只能上,不能下啊!随便它开到哪里”[4]。阿力和猴子两个人原以为来到城市便能够靠着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但殊不知现代化的社会并没有赋予他们生存的合理性,他们做着连自己也不理解的工作,但为了谋生也只能继续不停地工作下去。他们悬在半空中规律地在墙上刷着油漆,下面的人并不会对他们多加注意,也正隐喻了他们受到忽视的生存地位。“无论是选择固守在乡村还是选择走向城市,高速发展现代化的城镇难以融入,而曾经封闭的乡村已经回不去。这些小人物不可避免地沦为双重边缘人。”[5]猴子和阿力是台湾在现代化进程中困窘的进城务工人员的缩影,他们的境遇正体现了漂泊无依、在社会中受到排挤的底层边缘人的艰难境遇,故乡固然已经回不去了,而城市空间也并未真正接纳他们的存在。“边缘的性质,从政治上看,就是弱势的,无权势的;从经济上看,就是落后的,不发达的;从文化上看,就是少数的,可以忽略的。”[6]黄春明注意到了在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后,涌入城镇寻找生活出路的小人物的生存焦虑,他们处在被挤压的地位中,在乡村与城市的边缘地带苦苦挣扎,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归途与出路,只有异乡边缘人专属的生存困境。
二、物质文明对生存基础的摧毁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工业物质文明也逐渐侵入了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拜金主义风气盛行,人们心中固守的本土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西方价值观念冲击之下逐渐被消解,人在这种物质文明的侵袭下也逐渐异化为了资本的工具,个体价值被扭曲,个体尊严被践踏,畸形的城市文明摧毁了作为人的内在生存基础的主体性。阿力和猴子在城市里做着油漆匠,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公司画宣传海报。他们在一面巨大的墙上每天不停地涂抹着,画报女郎“一对乳房有好几层楼高大”,到后来“连自己都怀疑到底是在干什么”[7]。他们原本抱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而来到城市,却不曾想到两年多来他们只能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猴子和阿力在工作中逐渐丧失了真实的自我,工作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反倒使他们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被监督和控制的对象。他们时常在工作中觉得受到了欺骗,却又为了生存而无法脱离这一生存模式。当猴子和阿力努力爬到高处向下望时,却发现整座城市就像手表里面的机器一样沿着一定的线路来来往往。黄春明敏锐地发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现象,人在这种经济关系中逐渐变得丧失尊严,失去了内心的生存基础。
马克思曾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8]猴子和阿力在工作中缺失了自我,在机械化的物质文明中被异化为了实现资本价值的工具,猴子意识到了这种状态对自我价值的摧毁,于是产生了想要逃离的想法,可最终却从高处的铁篮子中跌落而亡。猴子并没有选择被城市文明拯救,他的坠亡恰恰使他保全了最后一丝作为个体的尊严,通过书中杜组长与记者的对话可知,自从大厦建立之后,每年跳楼自杀的人數也逐渐增多,人们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处可逃,猴子的死亡也反映出了作者对现代物质文明摧毁人类生存基础的控诉和批判。
资本主义的涌入造成了社会分配的极度不公,底层人物在被剥削中生活得愈发艰辛,同时农村经济在城市经济的冲击之下也受到了相应的破坏。黄春明以底层人的视角看到了社会变革带给人们的冲击,看到了城市劳工生存的艰难和无所适从的苦楚,也看到了城市经济发展对传统乡土经济作为生存基础的摧毁。阿力出走之后的第一次回乡,村里人像面对外星人一样围住他向他询问着有关城市的一切情况,连村长也拜托他在城市里为家里的阿木介绍一份工作。城市经济的发展引诱着村庄里的青年人不断从乡村世界中脱离,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劳动力的流失,传统的农村经济已经无法支撑起人们的生存,“回家也没有钱”,于是只能在异乡苦苦挣扎。为了缓解内心的煎熬感,猴子在涂油漆时上瘾式地哼出家乡民谣,体现出了身处都市艰难求生的农村青年无意识的怀乡。[9]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与繁荣中包含了无数小人物的眼泪与无奈,他们只能割断身上与生俱来的乡土之根,成为城市中的浮萍。
三、沟通的断裂与失效
黄春明是一位与时代保持着同频的作家,他的作品关注到了台湾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种种困顿局面,传达出了一种对于传统乡土人情的怀恋以及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隐忧。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血肉相连的伦理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经由辛苦的开拓和长期的互相依赖所建立起来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土地上的事事物物之间的伦理关系”[10]成为束缚整个乡土社会的牢固纽带,所有人都在这个纽带之中互相扶持、互相关联。长期的交互关系为乡土社会提供了和谐与平衡,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充满温情的依赖与关怀,人的尊严也因此受到了保护。乡土的存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也为人们的沟通与交流留下了天然的空间。然而都市文明的发展却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切断了人与土地的联系,同时也切断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与沟通的渠道。人们忙着在商品经济泛滥的时代中嗅闻着利益的所在,忙着捕捉一切信息与热点,而逐渐遗忘了对于尊严与理解的坚守。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经济浪潮的追逐中愈发加深,相互理解已变得不可能,人与人之间沟通在现代社会已然断裂与失效。
猴子与阿力在高台上原本是为了互诉衷肠、倾吐苦闷,然而当他们被人发现时却被误解为是要自杀,无论他们如何解释自己并无寻死的想法,组织营救的工作人员依旧对他们的言语保持着怀疑,坚信着“他们一定是要自杀”的判断。在与工作人员一遍一遍地重复解释之后,猴子和阿力发现了沟通的无效,他们的内心逐渐走向崩溃,别人对他们行为的错误理解以及重复的无能为力的解释使他们深感无奈和烦躁,沟通在此处发生了断裂与错位。在工作人员的眼中,事实就是“他们”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而猴子和阿力的解释仅仅是在掩盖这一事实。于是“他们”失去了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权,仅仅成为了合乎想象的被固有观念所塑造出来的人物,甚至和墙上的油漆画没有什么区别。沟通在本质上是为了加深彼此的了解,使得双方的思想观念得以有效的交流,而沟通的断裂则意味着对话的双方均无法深入对方的内心而互相理解。猴子与阿力在高空中铁篮子里,在物理意义上与他人保持了隔绝,同时在沟通的过程中内心也逐渐被隔绝。
除此之外,猴子和阿力与记者的沟通也是失效的,作为记者本应具有深入把握对方言语与心理的能力,但他们的问话却只是让猴子和阿力感到不耐烦,双方的交谈并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在最后记者反而成了被采访的对象。潘记者面对猴子的提问感到不知所措,他的支支吾吾其实也隐喻了他与猴子和阿力其实同处于在城市中苦苦挣扎的境遇。在与记者进行交流的同时,阿力和猴子的注意力一直被杜组长与其他记者的对话所吸引,他们偷听着这些来自城市的人将要如何拯救他们,可恰恰是那些拯救方案使他们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当中。“警察很尽职地保卫着他们,记者也很关心社会人生,其实却构成一种迫害性的力量。”[11]在进城之后,城市文明第一次对这两位小人物展现出了全部的关心,但这种关心依旧是以物质为核心的,采访、拍照、录音、照明,机械式的关心一应俱全,可这两位小人物的内心却并没有被这座城市真正了解过,一场关于自杀的闹剧最终演变为了真正的死亡悲剧,沟通在城市中的失效使得猴子最终成为了一位被城市话语完全挤压的受害者。
四、结语
台湾的农村经济被破坏之后,小人物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城市的发展挤占了乡土的空间,同时也侵占了人的生存场地。人的尊严在城市空间的挤压之下被践踏,人的自我受经济关系的制约被抹杀。擅长刻画小人物的黄春明对底层市民的掙扎进行了格外的关注,他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对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表达了充分的同情,也对现代物质消费主义社会进行了严肃地批判。小人物在城市中顽强地挣扎,却又不可避免地步入一种悲剧的结局,巨大的城市如机器一般吞噬了温情,使人走上了一条隔断根基的被异化之路。现代化社会的运行规则使生存在其中的人们无处遁形,身份的缺失、生存基础的毁灭以及沟通的断裂与无效是导致猴子死亡的原因,同样也是构成更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的原因。他们在丢掉了乡土生活又在城市之中缺乏身份,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大机器中丧失了主体性的生存基础,他们无法与外界进行真正的沟通以唤起他人对内心的理解,他们的尊严在枯燥无情且充满重压的城市生活中被无情掠夺。通过书写底层人物生活的重重困境,作家表明了他对于资本主义抹杀人的个性、挤压底层人物生存空间的深切批判与控诉,也有助于读者对台湾底层人民在发展过程中的生存困境有所了解。
参考文献:
[1]曾建民.从台湾社会的现实中一路走来——论黄春明小说的时代开创性、启蒙性和艺术性[J].海峡论坛,1999,(16).
[2]陆卓宁.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01.
[3](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
[4]黄春明.看海的日子[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124.
[5]宋媛媛.浅析黄春明台湾转型期小说中的悲剧[J].文学教育,2014,(03).
[6]张书群.价值的缺失和追问——黄春明小说中的边缘人物论[J].语文学刊,2006,(17).
[7]黄春明.看海的日子[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115.
[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53.
[9]林丽锜.“保有本土的精神,拥有现代的面貌”——论黄春明小说的美好传统倾向[J].华文文学评论,2017,(00).
[10]尉天骢.读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乡土小说的随想——代序,看海的日子[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4.
[11]尉天骄.黄春明笔下乡土小人物生与死的意义[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1).
作者简介:
吴丽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