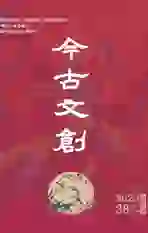《约翰·伍尔曼日记》中的记忆与双重叙事
2023-10-27杨俊建
【摘要】《约翰·伍尔曼日记》历来被认为是清教徒自传的典范,本文从世俗与神圣双重叙事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从中挖掘伍尔曼在两者之间的含混态度。在世俗生活层面,伍尔曼终生经营生意,偶尔流露出对妻女的眷恋,会受友情的影响而改变其布道策略,从中能看出他对世俗生活的眷恋。在神圣生活层面,他很难摆脱世俗经验的羁绊,他的神圣图景和道德规约,最终是伴随着旅行的空间拓展而展开的,其中对风景及风俗的叙述简约精到,它们最终摆脱了神圣图景的约束,具有了独立的可能性。伍尔曼的日记,实际上是双重叙事的相互纠葛,它们彼此难以分离,却又互为对方的价值落脚点。
【关键词】《约翰·伍尔曼日记》;记忆;双重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標号】2096-8264(2023)38-002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8.007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校级课题“记忆书写与形构:美国开国时期三大自传研究”(项目编号:2019B004)。
约翰·伍尔曼(John Woolman,1720-1772)是北美殖民地时期的一位贵格派教徒,并不以文学为业,但他在作为信徒与牧师宣讲的一生中,有记录自己生活和沉思的习惯。在他去世的两年后,一本名为《约翰·伍尔曼日记》的小册子便问世了,这本书在当时及后来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国内学界鲜少关注这位“作家”,西方学界则习惯于将伍尔曼看作是一名“未被册封的圣徒”(查尔斯·艾洛特语),或者“与种族、贫穷和战争主题”最相关的殖民地作家,认为他在日记中使用的文学技巧既少又简单,甚至还带有自我否定的特性[1]。
这种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如果我们撕掉这些贴在伍尔曼身上的大标签,去挖掘日记中所呈现出来的伍尔曼的记忆与生活本身,就会发现伍尔曼本人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综合体。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犹疑在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两重维度之间:既渴望世俗生活,但又觉得不该全身心投入;渴望靠近上帝,却又对现实生活充满依恋。这种生存的困境,自然而然会反映在他的日记中,由此便形成了双重叙事。
所有自传都是记忆的天然载体[2]9,伍尔曼日记也不例外,伍尔曼在日记中对于记忆事件和记忆形象的使用,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佐证其观点,支持其逻辑言说的意图,对于这些地方需要更细致地处理,而除此以外,有些记忆事件出现在其日记中,则是本着真实讲述其生活经历的目的。
一、日记中的世俗生活叙事
伍尔曼在日记的开端,就对自己生平做了一个异常简短的介绍,“我于1720年出生于新泽西博林顿郡的北安普顿。”[3]146之后就谈到他本人从7岁起就对上帝产生了仰慕之心,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信徒讲述其自我生平的基调。
在日记的最初部分,他的确努力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的意义都与上帝挂钩,俗世似乎只是被他看作是彼岸世界的幻影,并无意义,如果从他最初的持论来看,他似乎缺乏马克思·韦伯所提及的“天职”观念,也并不认同教徒在此世的成功是对上帝的荣耀的观念。但从他日记的记载来看,在他的一生中,他并没有严格按着这种方式去生活,他同样会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自身生存的意义,无论在他个人、家庭还是他的社会交际生活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
约翰·伍尔曼这位信徒,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经历。在营生与生活享乐方面,从日记中可知,从少年时期开始他便从事农场种植。在21岁的时候他跟着一位店主看店记账,为他工作了好几年,之后又动了学习裁缝的念头,“若能从事裁缝业,兼营一些其他生意,也尽可以维持一种平淡的生活了,无需干大买卖。”[3]155
学会裁缝之后,伍尔曼便经营起了裁缝店,不仅如此,在1756年之前,伍尔曼还兼做零售生意,这一零售生意包括售卖衣服的花边,以及售卖衣服衣料,伍尔曼以一种世俗精神坦诚:“我想经商。”也因此,我们发现他会“售卖酒类、糖和蜜糖这些奴隶劳动的产物,那时对这些买卖心中并不会觉得不安,只希望对酒类的应用稍加限制,但也并不十分积极地提倡”[3]234。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伍尔曼并没有不安,酒似乎也不是那么坏,“我有时候亦在骄阳下劳作,并欲借酒解除疲乏,但从经验中我知道喝了酒后是无法平静的……”[3]167
当然,这种生活方式是否是符合神圣原则的?以及是否是不那么“虔诚”的?伍尔曼有自知之明,“……有一种愁闷之感涌上心头,因为在生活上我习惯应用的一些东西,是超出神所希望我们应用的。”[3]209这种不安的根源还是在于世俗生活与享受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伍尔曼想戒绝这一点,但效果就未必那么好了。
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在1761年,伍尔曼想找一块天然色的皮料来制作一顶(白色的)帽子,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必将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白色帽子是那些讲究时装服饰的人所喜欢戴的”[3]211,这种新奇的白色帽子,并不是传统的贵格派教徒会佩戴的,属于标新立异的穿着,在那个时期难免会引起教友们的反感。不过他还是这么做了,理由是他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因为它是上帝所吩咐的。这种说法,我们倾向于认为是以援引宗教记忆来为自己的兴趣做辩护,要知道,在贵格会的教理中,认为人是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在上帝那里接收信息并按其意愿行事,而这往往是比较出格的。有学者指出,17世纪有位叫福克斯的贵格教徒不穿鞋只穿袜子,步行穿过了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县,类似于一种使徒行纪;而另一位贵格教徒约瑟夫·鲁勒,则穿着白色袍子进入白金汉宫[4]。这些之前的奇装异服的记忆形象,具有“转变为道理、概念和象征”[5]30的作用,能够证明某一行为本身的合理性。这些记忆形象客观上充当了约翰·伍尔曼的前驱,使他最终以这一理由来为自己的爱好辩护。
相比于严苛自持的修士生活,伍尔曼更倾向于健康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自己应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只买卖一些有益的货品,而且规劝穷人在购物时只捡最实用且廉价的货品来买。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自主劳动也是有必要的,“我有一片苹果园,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园中除草、移植、修整和接枝。”[3]167
通过以上勾勒,我们能够形成了一个伍尔曼的画像:节制、简朴、勤劳,与此同时喜欢做生意,一生钱财无缺,但他又压制这种欲望。
在家庭生活方面,伍尔曼着墨较少,关于他的父母,只有寥寥几句话语—— “当我开始启蒙时,父母就开始教我读书”,“1750年秋天我的父亲塞缪尔·伍尔曼因发烧而去世,享年60岁,他一生十分关爱他的孩子……”[3]160伍尔曼兄弟姐妹较多,但日记中几乎未曾谈及他们,唯一出场的是他的一位姐姐,还是她染天花去世的消息,也只有一句话。
他不仅对家人着墨少,对自己的婚姻大事的叙述也非常简洁:“主果然乐意赐给我一位好女子,她叫莎拉·埃利斯,我们于1749年8月18日结婚。”[3]160这种平淡、简洁的文风,导致我们很难从其日记中勾勒出其父母、妻女的形象,出现了所谓记忆形象缺失的现象。这种现象要么关联于遗忘,要么相关于叙事风格的形构。在这里,伍尔曼的刻意“遗忘”也是具有意义的:“遗忘比记住更有助于创造性地表达。”[6]48这一创造性体现在伍尔曼要营造一个整体性故事,它相关于神圣,在这一故事版本中,亲情没有多少立足之地,它只能是随手插入的无足轻重的记忆事件。
这一神圣的宏大叙事,压制了伍尔曼在日记中对亲人的依恋与追忆,但它并不总是一直有效的,在有些地方,依然能看到伍尔曼对家人的依恋与温情:“……自从和你(指妻子)分别以来,我常常会想念你和我们的女儿以及朋友。在外面的这些日子,当你们生病的时候,我不能照顾你们,这让我十分揪心。”[3]200在日记中记下的这封写给妻子的信中,伍尔曼摆脱了神圣秩序的钳制,露出了人性的温暖,也显示出实际上他难以割舍亲情。
在社会生活方面,相比于家庭生活而言,他更多体现出依靠常识和世俗精神去看待友情与公共事务的特点。
作为一名贵格教徒,伍尔曼喜欢到不同的教区做交流,他游历四方,交友广泛。这过程中自然难免受到其他人的招待,提供住宿、饮食等给他,从而建立起一种朋友间的友谊。同样也难免的,他会受到友谊的牵绊,而无法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尤其是在他认为招待他的人偏离了上帝的指引时,“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种和谐顺畅的氛围中,想要和那些款待我们的人亲切地谈论一些物质利益问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时候,当我觉得真理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因为肤浅的友谊而无力胜任。”[3]204他为此而反省,觉得应该避免陷入这种友谊的圈套中,说明他本人在相当多的境况下,是依靠世俗精神与其他人相处的。
在对待公共事务上,伍尔曼同样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策略。
比如对待战争税这件事上,伍尔曼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与神圣职责并不协调。当一位军官要求他为士兵提供食宿,有相应的报酬,伍尔曼认为战争之事与宗教不符,但他又认为军官的做法有法律依据。显然这里出现了神圣法与世俗精神相冲突的情况,伍尔曼采取了折中而实用的策略,即“当局指定我招待士兵,我是不会拒绝的,只是此事与战争有关,我不愿接受报酬。”[3]186-187为了替自己的这一折中做法做辩护,他随后举出了一位名叫托马斯·厄·肯培的人,他面对神圣条例时同样采取了灵活的策略,这一记忆形象可以为他提供合法性支撑。
西方学者多倾向于将伍尔曼看作是一名圣徒,或许如此,但他在面临世俗生活时实际上采取了务实的、实用的态度,从而我们得以在他身上看到鲜活的、世俗的一面。
二、日记中的神圣生活叙事
不可否认的是,日记中呈现出的伍尔曼形象,更多是靠近神圣这一維的,他以上帝的言行来处处要求自己,规范自己,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称得上是一名圣徒。在对世俗生活的讲述中,伍尔曼总是会以神圣精神作为阐释依据,以至于两者往往是密切纠缠在一起的。不过,当伍尔曼要言说神圣时,他发现直接言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借助于现实或者世俗生活本身才能开口言说,这就导致他的神圣生活叙述,也并非那样纯粹。
伍尔曼日记中记载了超过30次的布道之旅,作品中有70%的内容都与他的旅程相关,平均每年都有一个月在旅程行,他的足迹所至,最远甚至到了英国本土,并最终在那里去世。所以,旅行是他的神圣叙事中无法忽视的环节。
有学者指出,伍尔曼的布道之旅对于他的精神与伦理构成很重要,他对于神圣启示和道德的洞察力,是随着旅程展开及所见风景提供的空间而发展起来的[7]。举例来说,1763年6月,伍尔曼前往殖民地边境去游历,在一个叫拉哈瓦哈妙克的河湾遇到了暴雨,“我们的独木舟在指定地点等着我们,我们就留此过夜。大雨连续不停地下,水冲过帐幕,人和行李都湿透了。第二天我们再路上发现前夜的风雨吹倒了许多树木,这叫我们想起了主的恩眷,他在暴风雨袭击下位我们在山谷中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方。”[3]218我们注意到,这段朴素的文字,实际上是把旅程中经历的现实与神迹的阐释结合到一起了。这只是伍尔曼进行旅行叙事的一种方式。
另外,他还会引用宗教记忆来表明自己的关切,在1767年的一次旅行中,因为对旅行所到地方的信仰状况不满,伍尔曼引用了先知的一句话“我因听见而疼痛,因看见而惊慌”[3]230,而且还提及了基督的受难场景来说明在这里布道的艰辛,对这一宗教记忆的使用,“……明确表达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作为一个永恒秩序和一致性缩影的宇宙”[8]16。显然,伍尔曼的旅游见闻叙事,最终是为他的永恒秩序建构服务的。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神圣叙述无法抛开具体世俗生活而独立,而这部分叙事中最鲜活的恰好正是他对旅行中所见风景的描写。
比如,“在移民区与维哈鲁森之间只有一条羊肠小径可通过,而路上杂草丛生,树木横躺其间,阻挡住去路,加以山峦、池沼、怪石等各种障碍,旅途艰难,此外又有响尾蛇为害,我们曾击毙了四条。”[3]222或者“野草甚多,我们用刀割下一些,准备当作晚饲料。然后我们把马拴好,又找来一些灌木放在橡树下,躺上去。”[3]181这些质朴的文字,反而才是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伍尔曼希望读者从道德的、神圣的角度去看风景,它们从属于神圣秩序本身,但野外风景的美学观感和体验,显然超出了他所设定的这种预期。
不仅如此,伍尔曼对所到地方的风俗的呈现同样生动,比如他对伦敦物价的描述就充满生活气息。“我发现黑麦的价格约五先令,每蒲式耳小麦八先令,一百二十磅燕麦粉十二先令,每磅羊肉三便士到五便士不等;黄油八便士到十便士,一个贫苦人家一年要支付的房租为二十五先令到四十先令,每周支付;烧火用的木材极其匮乏,因而昂贵不堪;一些地方每英担煤两先令六便士,但是,靠近煤矿的就要便宜四分之一。哦,希望富人能关照一下穷人。”[3]250以上这些依附于神圣秩序的风景和社会风俗描写,之前往往被视为无用的边角料而为人所忽略,现在看来,它们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景致与人情之美,同时又兼具了写实的功效,已经游离于伍尔曼所构想的神圣图景了。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引文最后,伍尔曼希望富人关照穷人的表述,更显现出了人性之美,它不再诉诸神圣本身,而是转为向鲜活的人发出呼吁。
在这里,伍尔曼所倡导的神圣秩序,至少是被局部性地打碎了,它变得有些黯然失色,而在背景板上的风景、风俗反而变得更鲜活、更重要,它们独立出来,以世俗的美否弃了高高在上的神圣美。
伍尔曼做的工作与但丁相似,奥尔巴赫指出,在《神曲》中,“但丁将尘世的历史性搬入了他的彼岸世界”[9]226,伍尔曼也做了一样的工作,但尘世生活的复杂性和生动性,总是难以被完全包容于神的永恒秩序中,甚至可以说,他这种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世俗形象总是比神的形象更为鲜活,更为重要。
三、结语
传统上,伍尔曼一直被认为以虔诚和种族问题先驱而出名,学界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但对他日记的细读后可知,他的叙事可以分为世俗叙事与神圣叙事两维。
在世俗生活领域,伍尔曼在当时以生意人的身份更为人所熟知,他有经商的热情和头脑,并且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乐于出售奢侈品,他的私人生活中是有享乐成分的,这也是他后来对此觉得忧心忡忡的原因。在家庭生活中,伍尔曼很少提及家人,因为他要营造一个有关神圣的整体性故事,在其中,家人并没有立足之地。不过从他流露出对妻女的眷恋来看,这种亲情感只是被他有意识压抑了。
在社会生活方面,伍尔曼同样难以摆脱来自友情的牵绊,以至于他有不少时候无法对朋友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对待公共事务上,他也表现出了务实的精神。
在神圣生活层面,伍尔曼同样也难以摆脱世俗生活的羁绊,他的精神生活始终伴随着旅行,他对于神圣生活的拓进,是因旅程的展开和空间的拓展而逐步形成的。这过程中,对风景与风俗的描写,最终造成了它们比神圣本身更形象,更有力。
伍尔曼的日记,实际上是双重叙事的相互纠葛,它们难以彼此分离,却又互为对方的价值落脚点,实际上,他对世俗生活的呈现才更有价值。
参考文献:
[1]Daniel B.Shea.Book Review:The Journal and Major Essays of John Woolman[J].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1973,(2):204-205.
[2]Suzanne Nalbantian.Memory in Literature: From Rousseau to Neuroscience[M].Palgrave Macmillan,2003.
[3](美)约翰·伍尔曼.哈佛百年经典:约翰·伍尔曼日记[M].翟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4]Geoffrey Plank.The First Person in Antislavery Literature:John Woolman,his Clothes and his Journal[J].Slavery and Abolition,2009,(1):67-91.
[5](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美)大卫·格罗斯.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A]//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11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Jon R.Kershner.’A More Lively Feeling’, The Correspondence and Integration of Mystical and spatial Dynamics in John Woolman’s Travels[J]. Quaker Studies,2015,(1):103-116.
[8](德)揚·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M].黄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9](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作者简介:
杨俊建,男,汉族,山东临沂人,河北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记忆理论,自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