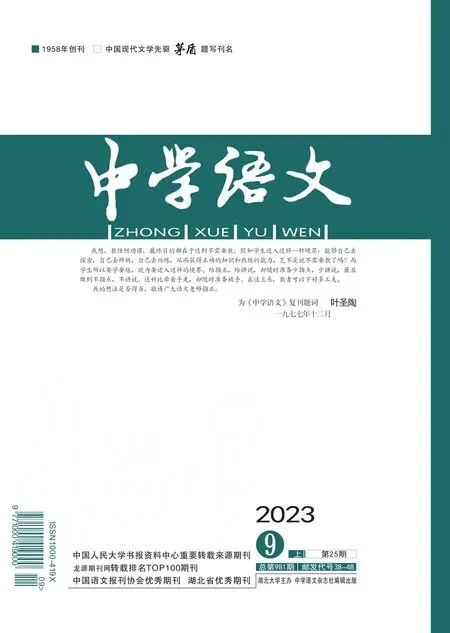情起意象生 情转意脉动
——浅析《声声慢》中的“愁”
2023-10-20刘捷莉
刘捷莉
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早期词往往以“艳歌小词”的形式出现,风花雪月与闺阁怨事构成了早期词作的基本主题,抒情言志的词作只星罗棋布地散见于苏轼、贺铸等词人笔下。宋室南渡之后的破碎山河引发了一场由“留连光景惜朱颜”向“欲将血泪寄山河”的情感转变,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南渡词人往往以愁为歌,“离人心上秋”成为他们真实的精神写照。作为南渡词人中的典型一员,李清照也由早期轻盈妙丽的望夫词转向沉重哀伤的生死恋歌,“薄雾浓云愁永昼”的人生际遇使得李清照发出了“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悲戚之鸣。《声声慢》中的“愁”流露出落落寡合、失落惆怅的迷茫情绪,将此愁引渡至李清照背后的家国身世显然更具备解释效力。显然,只有将“愁”及背后的历史原因与李清照的创作相联系,《声声慢》才可能赢得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与美学意义。
一、知人论世识才女,血泪之词感愁悲
事实上,词本有“男子而作闺音”的传统。当李清照以一介女流的身份闯入文学这座以男性为主的殿堂时,她既以一位才女的形象受人瞩望,又在举手投足之间显露出文士的面孔。李清照不仅收获了“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的至高赞美,更是以一种云中鸟瞰式的视角评价诸多前辈的文学造诣,评柳永虽“变旧声作新声”,但“词语尘下”;评张先等人虽“时有妙语”但“破碎何足成家”。这样看来李清照的成功似乎不足为奇,女性的身份使她处理词体时更加得心应手,不同于男性词人代拟闺情词的矫揉造作,李清照能够将女性的真实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无疑使诸多男性词人相形见绌。
同时,山河破碎所引发的心理阵痛并非男性作家特有,女性词人的家国情怀亦在此刻浮出历史地表。南宋徐君宝妻作《满庭芳》词后投水而死:“从今后,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刘氏则题《沁园春》于长兴酒库:“我生不辰,逢此百罹,况乎乱离。”“君知否,我生于何处,死亦魂归。”当女性触碰到历史脉搏的真实脉络,闺房内外的冷热殊遇使她们跳出了闺情词的传统范畴,李清照也不例外。少女时期的李清照可以用“一枝春欲放”来形容,《点绛唇》中“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通过见客羞走、倚门回首、细嗅青梅等一系列动作,使怀春少女的俏皮羞涩跃然纸上。嫁作人妇后,李清照与赵明诚聚少离多,词作间也多夹杂苦涩滋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当宋室南渡,与赵明诚阴阳相隔时,李清照便以“憔悴损”的面目示人。在《永遇乐》中,李清照自言“如今憔悴,风鬟霜鬓”,在追忆“中州盛日”时也不由得感叹如今“人在何处”,心中愁肠百结却无人陪伴,唯有“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以作慰藉。
由早期《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等恋情词向后期《武陵春》《声声慢》《永遇乐》等伤乱词的转向,预示着词人心境的巨大转折。曾经满怀至情,连篇痴语都化作字字血泪,声声呜咽。这“载不动”的“许多愁”,止不住的“千行泪”,“凄凄惨惨”的哀语,无人诉说的“万千心事”,皆非虚构拟造的白日梦呓,全是发自肺腑的血泪之词。“愁”作为李清照后期创作不变的主题,其中的酸楚需要读者细细品味。这些融汇家国感伤、世态炎凉的悲凉之词,皆源自词人泪向九泉的真实境遇,是李清照坎坷人生、南渡词人落魄境遇、两宋之际悲剧时代的集中映射。
二、刻画悲秋意象群落,渲染悲凉凄清氛围
陈玉兰在《论李清照南渡词核心意象之转换及其象征意义》中提出将李清照词的核心意象归为南渡前后两类。南渡前以“楼”“月”“琴”“花”为主,而“江”“雁”“雨”“梦”等意象则多见于南渡之后的作品。其中前者“融汇成一脉作为怀春心理表征的闲愁——美丽的忧伤情愫”,而后者则派生出“江湖倦客离乱愁”,这与“南渡前词中那一片深闺少妇的儿女闲愁是大相异趣的”。[1]诗词作品中核心意象的选择亦是作家立于现实之镜前的倒影,其与作家特定时期的审美趣味、心境遭遇等诸多现实要素有着必然的联系。
《声声慢》全词共有五个经典意象,分别为“酒”“雁”“黄花”“梧桐”“细雨”。在南渡前便是核心意象的花,在南渡后的作品中也能觅其踪影。在如此剧烈的现实转折之后,花的意象又是否发生了迁移呢?答案是肯定的。李清照词作中的花意象寄寓着词人的个人形象,不论是“香脸半开娇旖旎”或是“人比黄花瘦”,李清照或欲凸显自身形态品格,或抒发愁思,感叹容颜易逝。而《声声慢》中的“满地黄花堆积”便显得尤为凄厉。即使在《醉花阴》中的卷帘西风下,菊花的形象也不过是雨打风吹后的瘦枝黄花,依旧可以“暗香盈袖”。而“满地黄花堆积”暗示黄花早已落下枝头,凋残殆尽,往日的瘦花在此时一朵难觅。正在“寻寻觅觅”无果之际,李清照又问“如今有谁堪摘”,年华易逝同爱人离去的悲情从中满溢而出,这种人生谢落的凋零体验也被词人嫁接至零落尘埃的枯花意象之中。
其次是酒。李清照的词作里“酒”和“愁”有如一对密不可分的孪生姐妹,“李清照词45 首(从王延梯《漱玉集注》,附词未计)虽无一题‘咏酒’之类,但是竟有23 首涉及饮酒,居一半还多”。[2]乍一看似乎有些矛盾,李清照素以婉约之词著称,为何却像李白、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文人一样嗜酒呢?这又要回到“愁”字上面。李清照饮酒颇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架势,《念奴娇》中李清照“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而《声声慢》中“愁”味更甚,“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中三杯两盏尚且难敌晚来风急,那“怎一个愁字了得”的人生滋味又该如何面对?词人以酒的淡映衬愁的浓,由泪水酿成的苦酒泛起苦涩的涟漪,词人心中的压抑忧郁又是否能够被这三杯两盏化解?
三两杯淡酒落肚,却见雁回旧相识。李清照说:“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旧时相识何来?这或许可以追溯到《一剪梅》与《蝶恋花》。由《一剪梅》中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可知,鸿雁成为李清照与赵明诚分离异地的传话信使,“云中锦书”承载的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闲愁。而在《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中李清照直言“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词人坚信姐妹们会将音信寄予自己,因为东莱不像蓬莱仙洲一般遥不可及。雁作为飞渡两地的信使,它的到来意味着远方友人的挂念即将落地,但《声声慢》中的雁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是鼓翼远去,只留下满地黄花、梧桐细雨还有独守空窗的秋愁。雁作为全文的核心意象不仅上承寻觅无果之惑,下启孤守秋愁之苦,更引出后文的“梧桐细雨”意象。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爱情做了生动注脚,但李清照对“梧桐细雨”的理解却更为生动。前文方才“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后文便“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此时已家破夫亡,纵使鸿雁飞往,也无信可传,只能凭栏倚窗,苦等天黑,千般愁苦只化作一句:“怎一个愁字了得!”
此五个经典愁苦类意象所形成的意象群落,看似跳跃,实则在感官、空间的变化联系中有机组合,形成一幅丰富生动的悲秋图景。在感官上,对大雁、黄花一类视觉意象的书写随着愁的推进而转向对梧桐细雨这类听觉意象的描绘,进而使画面更加立体可感。从空间上,有远近、有天地,视觉的层次感使人有如身临其境。词人运用多种感官来感知身边的事物,所见、所感、所听都是自然的、流畅的、和谐的,一切皆因情而起、因愁而发。
三、“滚雪球”式递进意脉,塑造饱满极致愁情
在触碰词作内在肌理的过程中,我们力图将《声声慢》中“愁”的多重要素整理出一套可供理解的秩序,一种走向清晰的轮廓。在把意象结合的来龙去脉确定之后,这种“滚雪球”般步步积累、层层递进的文章意脉便成为我们破译《声声慢》的重要参照。简而言之,《声声慢》情感之厚重已无法用单一的语言文字概括,因此,走通意象、意脉、形式的三级台阶就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寻觅无果引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口气叠十四个字,历史上李清照为第一人,且这七个叠词并非随意堆砌,而是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叠词与情感达到了高度的和谐[3]。词作以“寻寻觅觅”为开头,但李清照想要寻觅什么?我们却不得而知,只知道她由“寻寻”这样粗略的翻找递进为“觅觅”这样细致的搜寻。那她又寻找到了什么?偌大的庭院中只有“冷冷清清”默默地注视、陪伴着词人。词人迫切地想要从中突围——她需要寻觅到某件事物来摆脱冷冷清清的状态。但苦寻无果的她只能任由这份失落惆怅长驱直入、横闯内心腹地,“凄凄惨惨戚戚”的出场也就显得合情合理。我们注意到,《声声慢》中叠词的运用强化了李清照内心的情感,叠词数量的叠加推动词作情感的递进,词人内心深处的悲愁被逐步调动引出。
其次,淡酒秋风添愁。该词作于初秋时分,天气忽冷忽热,“乍暖还寒”之时。“将息”释为养息、休息,但心中尚有记挂之事又岂能高枕无忧?词人欲“借酒消愁”,可“怎敌他,晚来风急”。敌谁?敌不过傍晚急急而来的秋风吗?这看似说的是抵不住入秋的寒凉之气,实则是词人压不住内心的绵绵愁丝。李清照的词作中曾多次出现酒,但唯独《声声慢》中强调是“淡酒”,可见其欲言之意不在“酒”而在“淡”字。词人满怀郁积、愁肠百结,以至于入喉苦酒也变得味道寡淡。此为真情虚感,悲情满溢,外物皆着我之色彩,愁浓而酒淡。
再次,雁过回忆增愁。“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如果说上文中我们尚且不知李清照为何而愁,那么此刻答案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雁过伤心,愁便愁在一个“旧时相识”。曾经与丈夫举案齐眉的日子充满欢声笑语,而现在却是“冷冷清清”地独守空房,其中滋味可想而知。曾经寄载着云中锦书的爱情信使无法再唤起“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了,纵然此情依旧“无计可消除”,但对家破夫亡的李清照来说,无信可传不只叫人徒增烦恼吗?
接着,满地黄花堆愁。愁本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情绪,但词人用“满地”“堆积”两个词,将愁的数量和厚度体现出来。愁似黄花铺满庭院般填满内心,悲伤似乎有了可供衡量的尺度。但具体表现如何呢?李清照以“憔悴损”作出了回应。在《醉花阴》中,词人自比黄花,虽然“人比黄花瘦”,但依旧在“薄雾浓云”“帘卷西风”中独自盛开。到了《声声慢》,女词人早已在风吹雨打中落得个“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的凄惨境遇。她无法再像从前那般躲在深闺怨阁中独自咀嚼思念爱人的苦果,或是享受与爱人重逢的喜悦,而是以弱柳之姿来独自承受本不应该让她承受的孤苦悲凉的人生。因此在《声声慢》中,词人并没有对黄花本身的形、味作描写,而只看到其“堆积”的状态。此时人与花在空间上拉开了距离,词人不在花间驻足流连,而是在屋里默默观望,对花的亲近不似从前。
最后,黑夜将至溢愁。如果人的内心似容器一般,对于情绪情感的承受有容纳限度,那么在最后一层,词人便是要打破这容纳愁情的限度,将愁情在天时、地利、人和的铺垫下推向极致。“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为何要守在窗边?视觉上,在梧桐细雨之前,仍能看见窗外的大雁、黄花,词人本将情感寄托于窗外景物,而绵密雨水的介入却阻隔了词人与景物的视觉联系。听觉上,细雨有柔和的特点,是高雅的、温和的。雨是细密的、轻的,按理听到的应是连绵的雨声,而词人却能听到“点点滴滴”,声音不是连续的,而是间断的。世界一片阴暗,愁情没了去处,便直达内心。“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细雨拍打梧桐,点在叶上,滴在心里,词人直面更加深刻的孤独,愁外愁,愁上愁。
通过对五个意脉层次环环相扣的描写,情感的累积达到高潮,悲凉情绪愈发饱满,以致词人最后一句直接抒情,使愁之深重走向极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并没有在《声声慢》中对自身的愁情做一次惟妙惟肖的肖像速写,反而将“愁几何”的问题交由读者自行体会。难怪《金粟词话》评《声声慢》为“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
综观整篇词作,虽“愁”字于末句才出现,但愁绪在意象群落和意脉中贯穿始终,将词人孤单凄凉的处境、悲凉空虚的心境剖于字里行间,使该词成为传世佳作,令人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