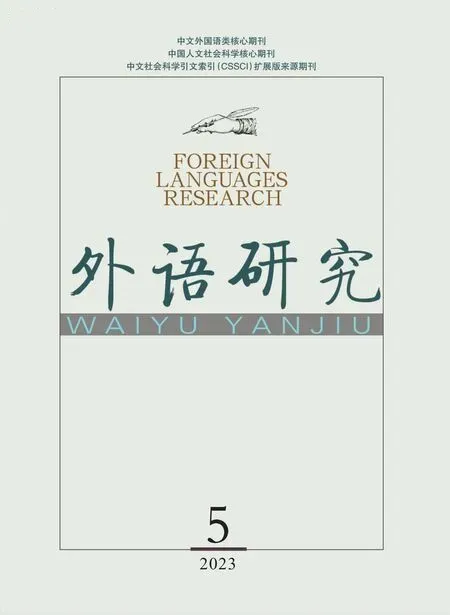中国非遗术语外译的译者规范化实践模式构建*
2023-10-10冯雪红魏向清刘润泽
冯雪红 魏向清 刘润泽
(1.南京大学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基地,江苏 南京 210023;2.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3.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0.引言
非遗的译介与传播是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促进世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内容。非遗“既是地方性知识,也是共享性资源”(李牧2019:66)。中国非遗资源极为丰富,迄今为止,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3 项之多,位居世界第一。中国非遗的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是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世界共享,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非遗是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代表,蕴含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而“‘地方性知识’的深描离不开术语这一话语工具的应用与传播”(魏向清,杨平2019:94)。非遗术语表征非遗文化实践的核心概念,是非遗知识的语言结晶,更是非遗知识体系及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的核心介质和重要基础。作为传统文化术语,中国非遗术语“既是当代国人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也是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理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钥匙”(姜海龙2016:103)。现阶段,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力实施,本土术语外译输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术语输出是术语本土化的逆过程,是国家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表现之一”(李宇明2003:8)。非遗术语的有效输出关系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译介的整体效果。
近年来,我国自主的非遗对外译介实践日趋活跃,促进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增强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非遗对外译介活动面广量大,加之非遗译者群体庞杂且素养参差,非遗术语翻译的规范化问题也日益突显。“由于术语的翻译可以被视为知识转移到另一个语言社区过程中的第二个术语形成过程,术语的标准化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Li &Hope 2021:61)。非遗术语外译规范化问题已经成为非遗术语输出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其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其规范化实践是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的重中之重。“非遗”保护是一场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事件(李向振2021),非遗术语翻译具有特殊复杂性,要提升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的总体水平,不仅要有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非遗译名审定与管理,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对译者群体的翻译实践进行规范化引导。鉴于此,非遗术语翻译的译者规范化实践模式有待构建与推广。
1.中国非遗术语翻译实践规范化问题管窥
据相关数据统计,除43 项世界级非遗项目外,我国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约1,575 项,如再加上省市县各层级的非遗项目,非遗项目数量可谓众多,非遗术语的数量更是惊人。为说明我国非遗对外译介中术语翻译实践的规范化现状,本文以世界级非遗“南京云锦织造技艺”英译实践为例进行考察,以见微知著。经数据分析发现,非遗术语翻译的主要问题如下:
首先,非遗术语英译中存在一名多译问题。以“南京云锦”这一术语为例,现有英译名多达五大类十几种之多,详见表1。

表1:“南京云锦”英译名
造成这种一名多译现象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术语英译实践中目前仍缺乏相关规范化翻译资源可供译者参照,如由专业机构审定和推荐的规范化译名或相关双语/多语术语库等。相比之下,更值得反思的是,现实中不少译者缺乏规范化意识,对译名的选择和翻译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如,2019 年,有译者将“南京云锦”译为Nanjing Brocade。这一英译名在《南京云锦》(黄能馥2003)一书中初次使用,原译者李长生对该译名做出了后续调整,相继改译为“Nanjing Brocade(Yunjin)(徐宁2012)/ Nanjing Brocade(Cloud Brocade)”(钱小萍2019)。除此之外,2019 年之前其实还存在其他由权威媒体或机构使用的译名变体,均可供参考,如Yun brocade(新华社),Nanjing Yunjin brocade 以及Cloudpattern brocade(《中国日报》英文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Nanjing Brocade 这一译法显然已被放弃,该译者显然对已有译名缺少了解。这个例子说明术语翻译的规范化意识在译者群体中仍然欠缺。
其次,非遗术语英译中存在知识性误译问题。如,有译者将“吉服”译为“lucky robe”,将中国传统色“绛红”译为“magenta”等。这里的“吉服”译为“lucky robe”,显然是囿于字面义而未能表达出源术语概念所包含的地方性知识,即“吉服”是指古代祭祀时穿的礼服。“绛红”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色,指大红色。红色是正色,以此为主色调衍生出中国红系列如榴红、枣红、胭脂红、绯红、橘红等,而“magenta”在潘通色卡上对应的颜色是紫红色(purplish-red),两种颜色并不相同,且文化意蕴相异。从这两个例子来看,译者忽视了术语翻译的知识理据,导致知识性误译,其结果无疑会影响到中国非遗文化知识对外传播的准确性。
再次,非遗术语英译中存在传播有效性问题。众所周知,在文化特色词汇或表达的翻译过程中,音译往往是译者所采取的权宜变通方法。然而,在术语翻译实践中,如果一味采取音译处理,则很容易因译名形式异化造成语义不透明,势必影响非遗知识的有效传播。如,现有非遗术语翻译中,有译者将“斗牛”音译为“Douniu”以及将“妆花”译为“Zhuanghua”等,一味使用这些音译方法,往往无法有效传输非遗术语所蕴含的知识内涵,起不到应有的译介作用,导致跨语知识的无效传播。
2.非遗术语翻译的本质及其规范化实践的知识理据
术语翻译的本质是“对原语术语相关知识的一次再度阐释,可以使原语知识系统中的概念在译语接受语境下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延伸。这也是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和知识体系互动的表现”(魏向清2014:25)。非遗术语翻译作为实现本土传统知识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样具有这样的知识实践本质特征。相应地,非遗术语知识的本体内涵也就成为非遗术语翻译实践中不可不察的根本理据。以上非遗术语英译实践中出现的规范化问题实则反映出译者对于术语翻译的本质以及非遗术语的特殊性认知不足,对其所需的知识理据重视不够。由于非遗知识体系的民族性与历史性,相关术语及术语系统在概念类型、语符形式以及交际特征方面存在多维度的特殊性。这就需要非遗术语译者高度重视翻译过程中相关的知识理据,以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最终译介诉求。因此,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除了一般意义上词汇翻译的基本形式理据外,更需要深层的知识理据。这也是术语翻译规范化实践的难点与重点所在。
以“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术语英译为例,译者要充分了解该项非遗的内在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掌握翻译规范化实践的知识理据。译者译前需要了解清楚“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知识系统主要是由六大部分构成:起源、品种、织造工艺、织机、原材料、图案纹样、配色等,每一部分的术语均有其类型特点。“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术语从表征的知识类型可分为表征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和活性知识的术语。表征不同知识类型的术语又有其各自的独特性,这也增加了术语翻译的复杂程度。例如,表征隐性知识的术语主要包括传统技艺类术语,如“挑花”“结本”“挖花盘织”等。“对于作为‘隐性知识’的手工技艺而言,所有的知识与要领都藏于脑、隐于手、感于心、存于器,并内嵌于地方的自然环境、文化风俗与社会结构之中”(张君2020:72),此类术语也主要用于专业人员的现场学习和交流场景中,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则需要必要的解说,这就意味着,在翻译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与受众选择相应的译法。再如,表征活性知识的术语一般与民族的信仰和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如“神帛”“织女”“权纹”“龙袍”“斗牛”等。“活性知识是表达价值观、理想、追求、动机、信任、满意度等的知识内容,是对价值观和兴趣的表征”(屠兴勇2012:23)。此类术语往往具有鲜明的文化异质性,因此在跨文化传播时需要注意文化差异性所带来的理解问题,需要考虑目的语受众的文化认知语境,必要时需作一定的解释和说明。
“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术语知识系统构成的多样性和所表征知识类型的复杂性要求译者在术语翻译规范化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形式规范化的语言学理据,还应注重内容规范化的知识理据。以往的术语翻译规范化重点关注语言学理据,如语符的构成原则、音译的读音、词性规范、指称与意义的一致等,忽视了术语翻译规范化的知识理据。如上文中列举的将“吉服”译为“lucky robe”从语言符号和意义的对应关系来看是合理的,“吉”有“吉祥”之义,因此可以译为“lucky”,“吉服”译为“lucky robe”具有一定的语言学理据。从语符构成的形式上来看,两者都是二字词组。但从术语知识传播的理据来分析,“lucky robe”恰恰是一种误译,重译为“ceremonial robe”方能准确译介出该术语概念的地方性知识内涵。再如,“妆花”音译为“Zhuanghua”,从读音和拼写的角度来看,都是准确的,但同时会带来目标语受众的知识理解与接受障碍,不利于实现非遗术语翻译的知识传播目标。考虑到该术语翻译的知识理据,将其重译为“hollow-out technique”则更为合理,符合非遗知识译介的总体目标。由此可见,术语译名要力求做到内外协调一致,要将内在的知识作为规范化的重要理据。
“术语常被称为知识的结晶、知识元”(龚益2009:442)。正因如此,术语规范化工作往往也是以相关领域或主题的知识体系为基础才得以开展的。术语翻译作为属于规范化工作中的重要对象,也理应如此。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的基础应该是基于非遗知识体系的知识理据,这是非遗术语译者应有的基本认知。
3.非遗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规范化实践解析
下文将结合“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术语英译实例,解析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译前、译中和译后实践规范,为构建非遗术语译者实践规范化模式提供依据。
3.1 译前选择规范
译前阶段,译者一般需要学习相关非遗领域的知识体系,梳理术语系统,确定源术语的主要概念特征和知识内容,为能够准确地译出术语做好知识准备。此后,译者还会选择出能体现知识传播者所代表的利益的术语核心知识要素在翻译中进行突显。
译者还需要辨析表征同一概念的多个同义术语,从中优选出规范的源术语。在源术语选择方面,为更好地进行非遗知识对外译介和国际传播,译者应选择名实相符的源术语。所谓名实相符,一方面是指“‘知识’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的一致性”(李瑞林2022:55-56)。具体来说,术语的知识表征即话语事实应符合非遗的知识本体事实。比如,“通经断纬”这一术语虽在南京云锦相关文本中经常出现,但非遗传承人①指出云锦织造中并不“断纬”,因此这个术语不准确,名实不符,但在缂丝技艺中使用则是恰当的。因此,在选择南京云锦源术语时,译者最终排除“通经断纬”这一源术语,从而在译前就规避了可能的知识误传。名实相符的另一含义是指,术语语符的知识表征较透明,通过语符语义即可初步判定术语概念内涵。例如,相比于“八答晕”,“八达晕”是更优选择。除此之外,选择源术语时,还要考虑表征同一知识类型的术语集在形式构成上的一致性,比如,选择“八达晕”作为规范源术语的一个重要理据,还在于云锦中常见的基础纹路还有“四达晕”,再如,面对“库金”与“织金”这一对同义术语,考虑到表征云锦主要类型的术语还有“库缎”“库锦”,为形式上的一致,应选择“库金”作为源术语。
综上讨论,非遗术语译前具体规范化操作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厘清源术语概念(同步搭建源术语知识体系、聚焦目标知识单元)——知识传播内容选择——源术语规范化,详见图1。

图1:非遗术语译前规范化操作流程图
3.2 译中操作规范
在译前规范化实践基础上,译中的操作环节,译者以知识跨语传播为目标,遵循与源术语知识内容对等的关系规范,并在这一关系规范的制约下,选择有利于知识跨文化传播的术语翻译策略系统。
译者选择的相应翻译策略系统是:一级策略——跨语知识传播;二级策略——找译(寻找目标语中的对等术语)等。在二级策略“找译”的实施过程中,译者需查询各类前期相关术语翻译资料,必要时,还需咨询权威专家和译者。二级策略的实施通常会出现以下三种结果:(1)找到已有的规范译名;(2)找到未规范化的多个译名;(3)未找到译名。面对第一种结果,译者通常会直接选择使用规范译名;面对后两种结果,在后续翻译操作中译者一般会对术语译名进行选择、初译或重译。详见图2。

图2:二级策略“找译”的实施结果及后续翻译操作图

图3:译后评价规范图
具体而言,译者主要依据术语所表征的知识类型,在知识对等关系规范的制约下,进行译名选择或翻译。以“南京云锦制造技艺”术语英译实践为例,对包含显性知识内容的术语如表类别的术语以及表原材料的术语如库锦(palace brocade)、团花(rounded figure)、缠枝(coiled branch)、孔雀羽线(peacock feather threads)等,译者多采用对译的翻译方法;对包含隐性知识内容的术语使用的具体翻译方法有转译法,增译法,如挖花盘织(figure hollow-out coiled weaving)、纹刀引纬(weft leading with the pattern knife)、“锦上添花”(adding flowers to the brocade)等。关于配色中的中国传统色名等活性术语的英译,译者多采用了对译、换译等方法,如明黄(light yellow/bright yellow)、石青(azurite blue/azurite)、绛红(crimson)、神帛(sacred silk)、官诰(edict)、官补(insignia)等。
3.3 译后评价规范
非遗术语译者的职责是通过翻译活动实现非遗知识的跨文化传播目标,而译后评价的主要诉求是评价术语译名是否利于实现这一翻译目标,这其实也是对译者行为合目的性的评价。具体而言,译后评价需要从术语译名知识内容的准确性和易传播性、译名的精确性和简洁性以及交际有效性等方面予以展开。
译名知识内容准确性评价关注译名表征的知识域、知识类型和知识内涵是否与源术语的一致,这其实是对译名知识表征的名实相符度进行评价。对单个术语译名的知识内容准确性进行评价时,需要将译名与源术语所表征的知识内容进行对比,以确定是否符合知识对等的关系规范。此外,译名知识系统性特征也是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表示花纹类的“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术语集“团花”“散花”“满花”为例,其对应的规范英译名“rounded figure”“scattered figure”“full figure”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和参照,具有系统性特征,且能表达出相应的知识类型。
非遗术语翻译的交际有效性实则强调的是非遗知识传播有效性,即源术语的知识信息能够通过译名被受众接受,这是非遗术语翻译活动评价的最主要规范。“为了交际的有效性,信息应该尽量简洁,且不影响意向和知识内容的传输”(Sager 1990:105)。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交际效果,术语译名的语符形式要具备“明确的知识领域的关联”(ibid.),同时还需具备简洁性特征。简洁性在知识信息传输过程中可以减少传播者和接收者的交际努力程度。实际上,在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过程中,译者常会通过缩短词长、名词化和使用非语言代码等方法优化术语译名的表达形式,以达到易于识读、记忆、理解和使用的效果,如将“卍字纹”译为“卍design”,将“palace satin brocade”(库缎)重译为“palace satin”,将“palace gold thread brocade”(库金)重译为“palace gold(gold woven)”以及将“gold/silverwoven brocade”(库锦)重译为“palace brocade”等,这样一来,译名语言形态更简洁,形式构成的知识系统性也更强,从而达到更好的跨文化知识传播效果。
译后评价规范对译者行为有修正作用。一般情况下,若译者发现译名不能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知识传播目标时,会返回到第一步对术语进行重译。例如,李长生将“zhuanghua brocade”和“lucky robe”重译为“hollow-out techniques/hollow-out brocade”和“ceremonial robe”,以突出译名的知识内涵。再如,他将“palace satin brocade”(库缎)重译为“palace satin”等,以提升译名形式的简洁性和交际有效性等。
4.非遗术语译者的规范化实践模式构建
“翻译规范是内化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体现出了某个群体共享的价值观”(谢芙娜2018:7)。翻译规范都是基于译者的翻译行为规律提出的。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12)在图里(Toury)提出的前期规范、初始规范、操作规范、文本规范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期待规范和职业规范。这些翻译规范研究的前期成果对于非遗文化术语译者规范化实践模式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研究从上述非遗术语翻译实践规范的理论探讨出发,基于作者参与“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术语英译实践过程的自省式回顾研究,结合对该非遗项目术语翻译权威译者②访谈、非遗译文审读专家反馈以及译名文本分析结果,将描写与规定性研究相结合,尝试构建一种中国非遗对外译介的术语译者规范化实践模式,详见图4。

图4:非遗术语译者规范化实践模式图
译者是翻译实践的核心要素。由于“当前从事翻译实践的主体发生很大变化,开始进入‘大众’翻译时代,译者队伍的规模空前庞杂”(魏向清2016:152),因此,要想取得理想的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效果,必须提升作为规范化实践主体的译者的规范化意识和规范化实践水平。术语译者的规范化实践对于术语翻译规范化总体水平的提升无疑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上图所示,该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实践模式以译者为中心,强调译者在术语翻译规范化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期术语规范化研究偏重术语本体研究,而忽视术语产生过程和术语使用规范的不足。与此同时,这种基于特定翻译实践类型围绕译者展开的自下而上的规范化研究,更加契合大众翻译时代非遗对外译介实践的需求,有助于发现具体翻译实践的规律,为非遗术语译者提供可遵循、学习和仿效的一个模式范本。正如黄鑫宇和董晓娜(2019:99)指出,“译者常难以在现有中国特色术语译名中选择合适的译名,或判断译名正确与否,这一‘选择性’难题揭示了中国特色术语翻译的过程性机制。”本研究探索的这一规范化模式体现出术语翻译规范化过程的动态性,如在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若发现翻译策略、方法或是结果并不能达到知识传播目标时,常常会返回上一阶段重新开始选择或是进行翻译操作,而不是直接进入确立、推荐和推广该译名的环节。这一规范化实践模式可与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译名审定规范化实践模式形成互补,从而更好地指导非遗术语翻译实践。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提出的术语翻译译者规范化实践模式是基于织锦类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实践经验的描写性研究和理论总结,实施流程与方法比较具体,可直接用于指导其他非遗类别的术语翻译规范化操作实践。非遗术语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可以按照不同阶段的规范化流程和方法进行操作。具体而言,在译前阶段,译者可根据非遗知识体系选择规范的源术语,同时对源术语进行知识解读,明确知识的使用域,了解术语的知识框架(术语集),分析源术语表征的知识类型,并根据翻译目的选择核心知识理据等;译中阶段,译者遵循知识对等的关系规范,并在翻译策略系统指引下根据术语所表征的不同知识类型选择适用的术语翻译方法。译后阶段,译者还需对译名与源术语知识内容的契合度、译名的语符形式以及译名的交际效应进行评价。
5.结语
本文以“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术语英译实践为基础,探讨了非遗术语翻译的特殊性与跨文化知识传播本质,提出了以跨语知识传播为目标、译者为中心、知识为内在规范化理据、过程与结果并重的非遗术语译者规范化实践模式。这一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实践模式能够显著提升译者主体的规范化意识,进一步促进术语翻译实践全过程的规范化,有助于减少规范化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译名选择随意性和知识性误译等问题。这一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模式是对“自上而下”的术语翻译规范化工作的有益补充,能够为术语译名审定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有助于提升名词审定的效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作为两种不同的非遗术语翻译规范化工作范式可谓殊途同归,相得益彰。二者相结合,共同作用,可以更好地提升中国非遗术语外译规范化水平,促进我国非遗知识的有效对外传播。
注释:
①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金文老师于2021 年接受笔者访谈时发表了以上观点。
②笔者访谈的主要对象李长生老师系织锦类非遗相关编著的权威译者,译作包括《中国南京云锦》(2003)、《南京云锦织造技艺》(2012)、《中国织锦大全》(201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