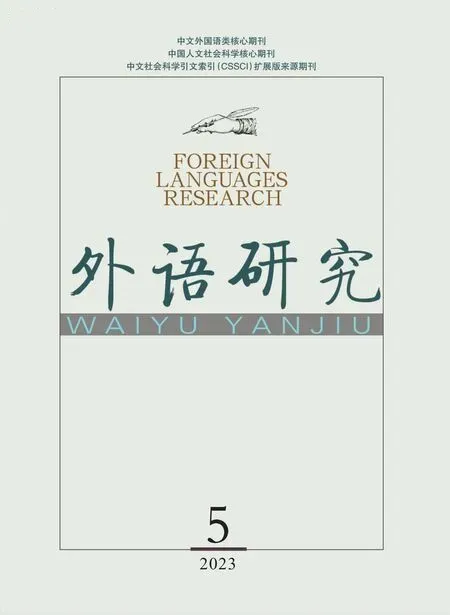中央文献翻译中的隐转喻互动研究*
2023-10-10宫宇航
宫宇航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天津 300204;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外语教研室,天津 300350)
0.引言
隐喻和转喻在国内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术研究体系,二者之间模糊的边界以及密切的关系(Dirven 2003:17)使得关于隐转喻的综合研究呈上升趋势,如Goossens(1990),Taylor(1995),Radden(2003),Ruiz de Mendoza &Díez(2003),刘正光(2002),李孝英(2022),项成东(2009),还有学者如王寅(2019),金胜昔(2021),潘震(2013)等,将其运用于翻译研究领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央文献的翻译研究中,虽然不乏以隐喻为视角的研究成果,但有关转喻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而隐转喻这一术语则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此外,以往对于中央文献翻译中的隐喻研究通常也只是局限于隐喻表达的分类、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以及翻译方法的总结,即便有些研究以认知隐喻为切入点,但并未很好地解释隐喻的认知内涵,“有盲目挂靠‘认知’之嫌”(谭业升2012:18)。虽然隐喻和转喻都会违反真值条件且普遍涉及语义变化,也都能达到真实的语言修辞格状态(Warren 2003:127),但认知语言学认为,二者都是心理认知机制,不应与它们的语言表达或其他方面相混淆(Barcelona 2003:216),所以有必要从隐转喻的认知视角出发,对中央文献翻译展开研究。
1.隐喻和转喻的关系:连续统
关于隐喻和转喻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Jakobson(1971)的论文“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他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体现于人类行为和语言的两种基本极点或表现形式,通过对两种失语症案例的分析,他验证了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和基于邻接性的转喻的存在,并以此暗示二者之间的连续统关系(continuum)。
除了域间映射和域内映射的区别之外,隐喻与转喻通常被视作同处于一个连续统中,“典型的隐喻和典型的转喻分处连续统的两端,而在这一连续统的中间,是一个隐转喻的模糊地带”(王军2019:1)。Radden(2003:408-413)曾以微观视角对high 一词的“字面意义—转喻—隐喻”连续统现象进行分析,表1展示了该词由字面意义到转喻再到隐喻的过渡:

表1:high 的“字面意义—转喻—隐喻”连续统
Radden 指出,(a)中的high 仅凸显出字面意义“高的”,而(b)中的high 却存在较弱的转喻性,既可表示海水高度,又可间接体现海水的总量,转喻邻接关系为UP FOR UP AND MORE,相比之下,(c)中的high 则具有较强的转喻性,通过“高”来指称温度的增加,凸显了UP FOR MORE 的邻接关系,(d)中的high price 介于转喻和隐喻之间,其中所涉及的两个概念“高度”和“数量”既可被视为同一认知域内的两个子域,形成UP FOR MORE 的转喻,也可被理解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认知域,形成MORE IS UP 的隐喻,而(e)中的high 由于指的是评价的维度,很难被认为与“高度”处在同一个域内,因此便构成了GOOD IS UP 的隐喻。简言之,(a)中表示纵向维度的high 是基本概念,通过转喻可激活出纵横维度(b),再激活出数量维度(c)(温度)、(d)(价格)以及评价维度(e)(质量),其中,(c)、(d)、(e)涉及从空间维度向数量维度和评价维度的映射,故三者之间存在隐喻关系,“字面意义—转喻—隐喻”也因此而构成了一个连续统。
以上分析是通过拉近(zoom-in)隐转喻连续统的观察视角所得出的。然而认知与思维通常是无意识的,人们自然不会经常下意识地去思考连续统内的中间链接,“而且也无法说清这种链接的数量”(范祥涛2017:85)。例如:
[1] These changes will be applauded.(Goossens 1990:329)
[2] I should/could bite my tongue off.(ibid.: 333)
例[1]中的applaud 原意为鼓掌。当人们在“鼓掌”认知域中进行互动体验时可了解到,该词通常代表着欢迎或赞许。这是一个以“身体动作指称动作意图”的转喻,然而人们在使用该词时也可能直接采用隐喻思维“鼓掌是赞许”,因为二者并不会在认知经济性层面产生太大差别。例[2]的隐喻性要强于例[1]。鼓掌和赞许可以存在于一个认知域内,但“咬掉舌头”却不一定会直接形成“保持缄默”的概念认知,这两个概念所处的认知域的距离相对较远,需要通过“咬掉舌头→不能说话→保持缄默”的隐转喻连续统才可使“保持缄默”的意义具有心理可及性。然而bite my tongue off仍可表示从身体行为到言语行为之间的隐喻映射,这主要是由于当观察视角被缩小或拉远(zoom-out)之后,人们往往会在隐喻或转喻思维过程中忽略那些不具有凸显性的邻接关系,进而选择相关且具有认知经济性的概念来组成隐喻。毕竟,人们的认知思维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便对于同一个文本来说,也可能会激活人们不同的认知推理或加工方式,隐喻和转喻也将因此而存在多种共存的形式。
2.隐转喻互动与中央文献翻译
以上分析对于中央文献翻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时我们说某个句子难翻译,究其根源实际是隐喻在‘作怪’”(叶子南2013:16)。然而,由于隐喻和转喻都是人们普遍且基本的认知机制与思维方式,且往往构成共存的连续统关系,那么二者的结合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翻译策略去帮助解决文本中看似棘手的隐喻现象。
例如“以权压法”的翻译:place their own power above the law(Xi Jinping 2017:139),原文体现了一种普遍、隐性的意象图式类隐喻(详见叶子南2013:34-36),该隐喻包含了两个事物之间的上下图式、力量图式,以及“权、法是实体”的概念隐喻。译文通过above一词传达了上下图式的含义,但力量图式却是通过转喻加工与上下图式的共同作用才得以体现于译文之中。
凭借对外界进行感知互动所获得的身体经验,我们对事物A 和事物B 之间的力量图式通常会有这样的认识:将A 放置于B 上(条件),意味着A 对B可产生施加压力的潜势(结果),所以这个图式中存在“条件指称结果”的邻接关系。再结合上下图式所生成的两个概念隐喻“UP IS CONTROLLER”/“DOWN IS THE ONE BEING CONTROLLED”可知place A above B 能同时体现两个意象图式所承载的概念信息,具体流程见下列表达式:
(条件→结果)∈力量图式∩概念隐喻1⇨以权压法
条件→力量图式∩概念隐喻2/3⇨place A above B
“条件→结果”的邻接关系属于(∈)力量图式,故而可用条件指称该图式。当力量图式与概念隐喻1(权、法是实体)相交(∩)时便可产生“以权压法”的表达;当指称力量图式的条件与另外两个概念隐喻相交时即可加工出place A above B 的译文表达。这种分析表明,隐喻和转喻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
2.1 隐转喻的互动模式
Goossens(1990)曾提出四种隐喻和转喻的互动模式:隐喻源于转喻、转喻寓于隐喻、隐喻寓于转喻、隐喻语境中的去转喻化,但目前学界公认的有效模式通常只有前两种(Evans 2007:141),而后两种互动模式在语料数据中却是极为罕见的(Goossens 1990:336)。项成东(2009:18)认为,“前两种互动其实是运用同样的概念运作手段,因为两者都是对隐喻的源域中未能明说的(underspecified)信息加以转喻扩充。”此外,二者在本质上都体现了一种“隐喻套转喻”(唐承贤2018:37)的模式,区别也只不过是认知视角的差别而已。相比之下,Ruiz de Mendoza &Díez(2003:518-527)所提出的互动模式则较为全面。两位学者基于Ruiz de Mendoza(2000)的研究,结合域缩减和域扩展的转喻发展形式,以及转喻映射所发生的场所(隐喻的始源域或目标域),提出了5 种互动模式:(a)隐喻始源域的转喻扩展;(b)隐喻目标域的转喻扩展;(c)隐喻目标域内对应概念之一的转喻缩减;(d)隐喻目标域内对应概念之一的转喻扩展;(e)隐喻始源域内对应概念之一的转喻扩展。
这5 种模式在国内外隐转喻互动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相当重要的意义,很多相关研究也都源自于此,如Ruiz de Mendoza &Peña(2005),杨波和张辉(2008),张辉和卢卫中(2010)等。然而这些模式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模式的分类并不完整且存在重复或衍生关系。一方面,(c)、(d)、(e)可被认为是基于(a)、(b)模式的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按照上述逻辑,至少还应该包含“隐喻始源域的转喻缩减”“隐喻目标域的转喻缩减”“隐喻始源域内对应概念之一的转喻缩减”的互动模式。此外,由于人们认知视角的不同,扩展和缩减之间的界限或区别可能不是那么清晰,例如:
[3] 就是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守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强战斗堡垒……(习近平2020:94)
该句中的“战斗堡垒”通过隐喻和转喻的互动来指称“各级党组织”,以凸显党组织的重要特征,具体分析见图1:

图1:“战斗堡垒”的隐转喻互动
例[3]中的“战斗堡垒”可被理解为“至关重要的建筑”范畴内的典型成员,而“至关重要的建筑”也可被看成是“战斗堡垒”的特征之一,前者是域的扩展,而后者则是域的缩减。视角的变换将导致“扩展”和“缩减”的表达方式在面对某些概念时多少有些“无能为力”。虽然扩展、缩减的说法对于转喻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来说确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为了使后续研究不至于复杂化,我们将使用“延伸”一词来进行替代。此外,由于转喻和隐喻经常处于一个连续统之内,且首尾概念之间的隐喻关系往往是通过中间概念而生成,因此,可重新得出如下三种基本的隐转喻互动模式:
(1)隐喻始源域的转喻延伸
(2)隐喻目标域的转喻延伸
(3)隐转喻连续统内的转喻延伸
无论是域的扩展还是缩减,隐转喻互动的基础几乎都离不开概念的转喻性延伸,这样的分类既有利于对隐转喻互动模式作出进一步精简,又可在应用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境进行多样化的搭配或组合。
2.2 隐转喻互动的翻译策略
对于中央文献翻译来说,基础的分类模式可衍生出多样化的隐转喻加工方式,译者应做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非在头脑中对先前复杂的互动模式进行逐一验证。下文将通过相关译例来分析中央文献翻译中的隐转喻互动情况,进而验证其作为翻译策略的可行性。
[4] 原文: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的挡箭牌。(习近平2017:128)
译文:No one may use the Party’s leadership as a pretext to override the law with their own arbitrary fiats...(Xi Jinping 2017:138-139)
[5] 原文:把症结分析透,把对策想明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习近平2017:224)
译文:We need to find out the root cause and come up with targeted solutions.(Xi Jinping 2017:246)
[6] 原文: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习近平2017:538)
译文:Cold War mentality and power politics still exist.(Xi Jinping 2017:589)
以上句中的划线部分都涉及了具体域和抽象域之间的映射,故而通常会被认为是隐喻现象。通过译文与原文的对比可发现,译文中的相应喻体基本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不会将其简单地归纳为“译为不同的隐喻、取消隐喻或增加隐喻”等译法,仅把研究结论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表象对于翻译策略的构建来说并无太大意义。毕竟,“翻译不能硬套规律,译者还得见机行事。”(叶子南2013:133)而透过翻译现象去深究其本质也绝不意味着远离文本以及翻译本身,基于隐/转喻思维的显性或隐性的语言现象终归还是会落实在具体的文字之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很有可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研究与实践打开新的局面。
全球陆地不同物理类型降雨空间分异及其变化趋势和波动特征研究(1979—2016年) 孔 锋 孙 劭 王 品 等 (6) (76)
从整体来看,例[4]体现了“领导是挡箭牌”的概念隐喻。“领导”一词具有权力属性,权力又可成为一些行为的借口,所以领导和借口之间构成了隐转喻关系,而“挡箭牌”也可通过一系列的链式转喻来指称借口,并形成“借口是挡箭牌”的概念隐喻,二者结合便可产生“领导是挡箭牌”的概念隐喻。因此例[4]的隐转喻互动可被表述如下:
通过对图2 的分析可发现,例[4]的原文涉及了本文所提出的三种隐转喻互动模式,隐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分别通过链式转喻而得以将域内概念进行延伸。其中,挡箭牌和借口、领导和权力之间的概念距离较远,所以通常又会被认为是处于不同域内的概念,故而可构成概念隐喻。这种隐转喻的互动模式可使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深入解读,选择互动过程中适切的语义节点来加工译文。由于挡箭牌具有一定的文化和认知差异性,所以译者可以LEADERSHIP IS PRETEXT(领导是借口)的概念隐喻为主体语义结构来加工译文。例[5]、例[6]的翻译同样是以隐转喻互动的形式对概念作出语际间的延伸,具体分析见图3、图4。

图2:“挡箭牌”译文构建的隐转喻互动

图3:“症结”译文构建的隐转喻互动

图4:“阴魂不散”译文构建的隐转喻互动
例[5]的原文体现了“问题是疾病”的概念隐喻,而译文的加工则是在此基础上对隐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进行转喻延伸,从而发展出“问题的根源是病根”的概念隐喻,并将其用于译文表达之中。例[6]的隐喻产生于连续统内部的转喻延伸。虽然原文存在“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是鬼魂”的概念隐喻,但考虑到始源域概念所承载的民俗和宗教文化内涵可能会给译文带来负面影响,所以鬼魂/阴魂的概念表达通常不会出现在译文中。从整体语义结构来看,不同的语言社团在表达同一个意向性指称对象时所采用的语义节点通常是不同的,例[6]中的译文由于文化原因使得被选取的语义节点要少于原文语义节点,故而译文与原文之间仍存在“部分—整体”的转喻关系。以上分析也间接证明,无论是在原文的解读还是译文的加工过程中,又或是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转喻都是无处不在的,它不仅是隐喻得以被构建的基础,也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认知机制。
隐转喻互动的认知翻译策略有助于译者摆脱对于概念或隐喻意象的增、删、改的方法层面的束缚,还可使其不再局限于隐喻对等或认知对等的理论窠臼。一方面,不是每个概念隐喻都可以在跨文化交际中被他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任何一个认为客户的要求至高无上的理论,都不会强调原文隐喻,不会瞄准隐喻对等这个目标,除非客户要求将隐喻作为关注的目标,但后者仅有理论上的可能,实际提出这样目标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叶子南2013:65)。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转喻、隐喻和隐转喻视为翻译中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机制,却不仅仅是文字层面上的“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而追求翻译中的认知对等同样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甚至可以说,语际间的认知对等其实是一个悖论,原因在于:认知基于体验,认知对等则意味着体验对等,然而,体验以及体验的主体、方式、时空环境等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对等的。所以即便是对忠实性有着较高要求的中央文献翻译来说,也绝非是通过认知对等的方式来实现译文的政治忠实,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从事实际翻译的人会从这个角度看翻译。”(同上:86)
3.隐喻始源域和目标域的再现
上述的隐转喻互动情况体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当原文存在较为明显的隐喻始源域或文化负载性较强的概念时,译者对目标域概念进行语言例示的可能性通常要大于始源域概念。这是一种相对“保守”且更为普遍接受的译法,但绝非是译者唯一的选择。本研究将在本节拉远(zoom-out)研究视角,以隐喻为主要切入点,详细分析始源域和目标域在译文中的再现情况。
3.1 始源域的直接再现
对于那些在文化和认知上完全不相容,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概念或意象来说,直译通常不会是最佳选择,但这并不会否定把原文始源域概念直接传递于译文之中的可行性。实际上,这样的翻译方式也不占少数,例如“照镜子、正衣冠”“打虎”“拍蝇”的翻译基本就是对原文始源域概念或意象的直接移植。但这样的文本概念与笔者之前分析过的文本概念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首先,这类概念对译文语境的依赖性更高。Bartsch(2003:55)认为,理解一个概念(包括情境、意象)需要将其嵌入到相似或邻接数据集的序列之中,并继续保持该序列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如此一来,若要在译文中嵌入这类“略显突兀”的概念或意象,并使其被理解和接受,则需要其与译文之间存在相似或邻接关系,也就是隐喻或转喻关系,但这样的概念或意象在译语中往往又很难会产生和原文相同的隐喻或转喻认知。若要使这种有意为之的动机性凸显(motivated prominence)与译文的“数据集”之间保持稳定和连贯,则通常需要译者对译文语境信息进行调整,毕竟,概念意义只有在相关的语境之下才可被探求。
其次,“照镜子、正衣冠”这样的概念给读者带来的感官和心理刺激往往要比“阴魂不散”之类的概念弱很多,这意味着即便是采用直译的方式,前者也未必会产生具有负面影响的译文。也就是说,当译者认定某个始源域概念或意象在译语文化和认知层面既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违背外交原则时,在译语中对其直接再现也未尝不可,这样翻译甚至还可能会增加译文的“新鲜感”。只是译者仍需尽力保持文化之间的平衡,毕竟,新鲜并不意味着可以被接受。一般来说,新的概念、意象或话语在其他文化中的流通与接受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与他族语言系统兼容;(2)为特定人群或学术共同体认可;(3)成为一定群体的公共文化资源或知识基础(廖七一2020:89)。其中,条件(1)与上述Bartsch 的观点存在相似之处,一个概念被他族语言系统所兼容也可被理解为在他族语言数据集内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条件(2)则需要通过语际、文化间共享的体验认知(宫宇航,项成东2022)来得以满足,但条件(3)却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通过时间和一些外界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可实现。
“问题是怎样才能追捕大贪污犯呢?要打大‘老虎’,首先要把中小‘老虎’搞清楚,这样大‘老虎’的尾巴就露出来了。”
对此,Barnes 给出的译文是: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we going to set about catching the big bribe-takers? If we’re going to get the big tigers we must first know all about the medium and small tigers,for once we know that the big tigers’tail will be revealed.”(Zhou Erfu 1981: 584)
由此可见,tigers 在英语中表示“贪污犯”的用法至少在20 世纪80 年代就已出现,当然,这个意义的产生自然也离不开语境的作用,如catching the big bribe-takers。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宣翻译的不断增加,“打虎”“拍蝇”之类的概念、意象就开始走入英语读者的知识范围,并逐渐被其接受。余小梅和汪少华(2015)曾在国内外主流英文媒体中搜集了2013 年2月至2014 年10 月期间有关“打虎”“拍蝇”的报道共88 篇,其中的85 篇直接使用了tigers 和flies 的表达。因此,这种已经融通中外的表达方式或相关的隐喻始源域完全可以直接出现在译文之中,当然,这需要译者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增加百科知识储备,并合理利用相关语料库或数据库进行检索和考证。
3.2 基于隐转喻互动的目标域再现
虽然译者可能出于对忠实性的考量而选择在译语中直接再现始源域,但这种动机性凸显却通常要以文本概念的适切性为前提。然而由于认知的差异性,语言文化之间大量存在的概念缺位现象往往会使很多概念、意象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前提。这意味着始源域的直接再现或移植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可取的。如此一来,通过隐转喻思维在译语中对目标域进行再现,就会成为另一种可行的翻译方式。下文以文化负载性较强的概念或意象为研究语料,进一步探究隐转喻互动对于这类翻译的指导意义。
[7] 原文: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习近平2020:201)
译文:Efforts to reduce tariff barriers and open wider will lead to interconnectivity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global trade,while engaging in beggar-thy-neighbor practices,isolation and seclusion will only result in trade stagnation...(Xi Jinping 2020:237)
例[7]的原文体现了“国家是身体”的概念隐喻和“国际经贸是身体器官”的子隐喻。隐喻始源域和目标域内的一些概念之间存在着转喻邻接关系。首先,目标域内的“削减壁垒”“以邻为壑”分别通过转喻的概念延伸,得出了“减少障碍”“损人利己”的意义,在结合“扩大开放”“孤立封闭”的文本概念之后可分别激活“连通/通畅”和“堵塞/停滞”的意义,而始源域中的“打通血脉”“气滞血瘀”同样也可激活这两个意义。由于原文的中医文化对英语读者来说过于陌生且难以理解,所以这种隐转喻互动的方式可将原文中的语义逻辑关系“削减壁垒和扩大开放可使国际经贸打通血脉”加工为“减少障碍和扩大开放可使国际经贸连通/通畅”。与之同理,“以邻为壑和孤立封闭会导致气滞血瘀”就可被转换为“损人利己和孤立封闭会导致堵塞/停滞”,这样一来,译者就可将目标域内的概念体现于译文之中。具体分析见图5。

图5:句[7]目标域再现的隐转喻互动
[8] 原文: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习近平2020:542)
译文:At present,among our Party members and officials,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will,courage or ability to take on responsibility....They panic whenever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arise.(Xi Jinping 2020:628-629)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例[8]的原文中有两个概念隐喻:“一些党员干部是泥菩萨”“问题/困难是风雨”。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于“泥菩萨”的理解与认知基本都来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俗语,“自身难保”的意义在原文中处于背景化状态,但导致“自身难保”的主要原因“过河、河水”却被凸显出来。因此,始源域中与水有关的“风雨”和“经不起”结合之后便可激活目标域内的“害怕/惊恐”,二者构成了“原因指称结果”的邻接关系。目标域内的转喻机制则更为复杂。“矛盾和斗争”经过转喻延伸可发展至“问题/困难”;“打摆子”可激活“因生病而发抖”的意义,而“发抖”又可与“惊慌失措”共同激活出“害怕/惊恐”的意义。这样一来,“遇到矛盾、斗争会惊慌失措、打摆子”就可被加工为“遇到问题/困难会害怕/惊恐”,这也是“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通过隐转喻综合处理之后所产生的意义,所以译文只需体现目标域内的概念即可。具体如图6 所示:

图6:句[8]目标域再现的隐转喻互动
在译文中对目标域进行再现并不等同于对始源域进行简单的释义或解释性翻译,在文字层面看似具有差异性或创造性的译文也并非是对原文的“叛逆”,而是以隐转喻互动为认知基础所作出的一种“妥协”。毕竟,“翻译是一种相遇、相知与共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为相知,必尊重对方;为共存,必求‘两全之计’”(许钧2020:113)。不经变通的“拿来主义”往往会引起译文的语义不通以及读者的排斥。译者追求原文的忠实或精确,其目的是为了使译文无限接近原文,“可是不‘通顺’的译文令人根本读不下去,怎能接近原文呢?不‘通顺’的‘精确’,在文法和修辞上已经是一种病态。要用病态的译文来表达常态的原文,是不可能的”(余光中2000:56)。换言之,“如果原文是清畅的,则不够清畅的译文,无论译得多么‘精确’,对原文来说仍是‘不忠’”(同上:57)。因此,基于隐转喻互动的目标域再现就可成为实现译文忠实性的另一种可行途径。
4.结语
中央文献翻译中的语言文字、概念和意象转换的背后往往离不开转喻和隐喻的共同作用,作为普遍且基本的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二者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从隐转喻的认知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中央文献翻译过程中的隐转喻现象,验证了隐转喻互动作为认知翻译策略的可行性。翻译总体的策略“不应该鼓励细节的对应”(叶子南2013:123),而隐转喻互动的翻译策略则可使译者脱离细节对应的束缚,使翻译不再囿于隐喻对等或认知对等的窠臼。本文并没有在翻译策略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翻译方法或技巧,是因为“我们无法像一个‘执法者’那样,去规范译者的每一个翻译决策”(同上:78),而真正从事翻译实践的译者通常也不会把思维局限于此。正如钱钟书(2011:154)所说,“盖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虽然中央文献翻译的译者不可能完全地“从心所欲”,但多样化的隐转喻互动模式却可使其在“不逾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甚至还可能根据具体的文本内容创造出更为有效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