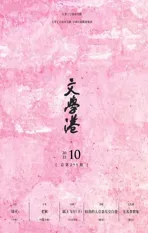柿林村
2023-10-07剑云
剑 云
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看到“第九洞天”几个字,喷绘的。青山映衬着的喷绘广告,总是鲜艳的。既然别有洞天嘛,我先是以为这山下面有一个深长的仙人洞,结果沿着新修的亭子下的木栈道,往下走,没有看到。从山上远远望过对面山上,有悬崖峭壁,青灰色石崖透露出一点紫红,但也不是红得鲜艳。道家说天下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山为“第九洞天”,叫 “丹山赤水洞天”,我找到了——宁波余姚大岚镇的柿林村。
我想是不是因为对面那些石崖有些褐红,所以称呼这里为丹山呢? 或者这里也住过炼丹的道人? 将那丹霞朱砂变幻为柿林村高树悬坠的红柿子了?
一道宽阔而古老的石台阶出现在层峦叠嶂的山坳里。我脚跟没站稳,书法家陈先生就招呼到山拗里他家所在的村子里喝茶去,他小时候在这村子长大,村子里有他本家的人住。走过那种常见的售票处,往山下去,右侧的山坡,绿色掩映着一片灰蓝色的青瓦房顶,天气燠热啊,让人想赶快走下去在哪户人家喝茶纳凉。石阶旁一棵盘龙遒劲的大柿子树,被修竹簇拥。
我正想随着大家一起走下石阶,却被路边的碑子吸引。“大清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三月立”,是钦命浙江巡抚提督刘彬给儒士沈明忠妻子立的 “贞节碑”。女子名叫吴一心,也确是 “一心”!原来这柿林村里,有一个小伙沈明忠,在和吴一心结婚那天,到山上给爷爷造墓,被老虎咬死了,吴一心就无儿无女地一直守寡到92 岁仙逝。这事迹——如果可以叫事迹的话——叫暗访来此的巡抚了解到了,上报给了道光皇帝,皇帝也感动了,就下诏建立贞节碑。结婚这天,大喜的日子,却去造什么墓呢? 我想。那时候山里的老虎多啊,现在怕是连狼都没有了吧!我想。

石台阶上,是新修的公路,公路旁小坡上的石坎内是“清国学生沈公载某”“仝配宋氏孺人之墓”,这位沈公的名字看不清啦。石坎前拴着一头吃草的白羊,目光冷静地抬头看我,让我给它摄影。
石台阶宽有两米多,可以并行四五人,脚板在石条的边沿磨出岁月柔和的痕迹,从道路的气魄可以感到这个柿子树村曾经的兴旺。
四明山被郁郁葱葱的竹子覆盖,柿林村也是一样,夏天的烈日照射在竹林里,竹林又把阳光的集束斜射在石板上,反射出迷离的光雾。我把照相机贴近石板地面向上照去,照出的道路上,恍惚着岁月的寂静恍然。
喝茶的同伴很快就不见了人影,我也不急着追随。听着念诵佛经的声音从那古老的青瓦蓝砖里传出,那是许多个老母亲声音的汇合,落在树叶和道路,落在空气里的旋流;那是山谷里和竹林飒飒的声音一起聚合的言语,我只知道那是虔诚的祈祷。而那渔鼓的节奏,似乎和山谷里的溪流声融合,渗透出空灵的气息,让人有了一点凉快。
我注意到有一户人家的铁门上用铆钉铆出“出入平安,吉祥之地”的字样,注明是“2001 年10 月”;许多人家敲打在铁皮上的,倒过来的 “福”字,昭示着,这里是一块福地。
我在石板路上坐着听了一会儿,慢慢走下去,走过村门口两侧的两个石质的柱顶石,有一个石鼓样的柱顶石搁在一扇小石磨上。我走进右侧靠山的屋子里,那十多位老母亲的宗教里,打扰了她们,装作没有理解她们不要打扰的眼神,拍了她们传着经盘的场面。
经盘里放着木刻印制的黄裱纸,黄裱纸上中间的天官,手执扫除凡尘的马鬃掸子。天官两边的对联曰:“四季平安,大吉大利;子孙满堂,荣华富贵。”上面横额是 “百万家财”。左边印着招财进宝的金钱树、聚宝盆,上面盖着佛寺印章。
还有一种纸马,中间有俩女宾举着仪仗,护卫的人物是天宫的 “娘娘”。“娘娘”莲花发髻,胸前衣服上双凤和鸣。“娘娘”坐在祥云之上,俯瞰下界。
老人们一遍又一遍念着经文,在这张纸马上要用蘸着红印泥的签子戳下多少三角形的红印点。好比这红点就是她们写给天官的天书,诵念结束后,就要送到寺庙里,邮寄给天官。那寺庙好比就是人间和天堂之间的邮局? 我仔细看,两边的红印点是菱形,由九个点组成,顶上的金字塔一样的图案由十个点组成,三个点的在横额和最上面间隔点缀;也有六个点组成的金字塔,形成的文字点阵,有一股神秘的意味。
在我搜集到的浙东纸马上,龙身上要点红点,二龙戏珠的珠子上要点,太阳里是七个红点,每个火焰三个尖,点三个;聚宝盆上的铜钱点四个。我感到这些点的组合似乎是一种符咒,老母亲们边念诵边点红点,深深地传达着人生的祷告、祈愿。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天书”吧? 就是说这纸马其实就是一封人间的信徒写给天宫娘娘的信,信封上写明了邮寄人的地址。这信要装在印有 “预修植福信牒”信封里,送到佛寺里。既然是预修,那就是说来世的福分是今世修下的,今世修下的福分要通过这信牒让上天知道。至于这上天是儒释道里的哪位神明,那是要到附近的庙宇里去考察的,一般而言,是上呈佛祖的。
祷告的老人里,有一位老婆婆灰白色的辫子又粗又长,缀在背后,觉得她们从少女时代到今天,在岁月的长河里,在这山中,孕育儿女,祈福祷告,生活在人世和神灵之间,而我这缺乏宗教信仰的人,其实只是生活在人间罢了。
伴随着诵经的歌声,林海竹光下,长辫子一样潺湲轻歌的溪流,摆动远行,流出山壑,形成瀑布,汇入余姚梁弄镇的四明湖里,与红杉林知会。
站在石板路上看参差接连的青瓦房舍,错落有致,方明白 “鳞次栉比”这个词儿。就像一张大大的蓝印花布,被远风吹来,挂在柿子树稍,落在了山坳里;又像一只银灰色的鸽子,卧在丹霞与绿海之间。进了村子呢,曲折的回廊巷道把家家连接了起来,形成一个8 字形的道路。人在房中,路多在檐下,就没有炎热的感觉了,一车人簇拥而来,忽然就看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行走在两三条小狗的追随中,忽然感觉空落。还有一所屋子里,有一位老奶奶独自在念佛;还有一位肤色黝黑、皮肤皱绌的老爷爷,躺在竹椅子上,摇动着芭蕉扇,望着树梢的鸟儿。
有一些人家的男人穿着短裤,端起一碗凉开水喝下去,端起凉水浇下身去;有一家孩子光着屁股爬在檐下凉席玩着,想从奶奶家爬回到妈妈家去。有一家老老的屋门半开着,门边挂着干枯了的端午节的菖蒲和艾草,清瘦的老人躺在竹板床上看着电视,见我拍照,摇摇手叫不要拍。
风景多在墙头,一盆蒜苗、一盆洋葱苗、一盆小葱苗,也有韭菜;一盆红花、一盆绿树,也有石榴树、指甲花。墙头多在屋后,出了自家屋子后门,站在后院里就可以伸手浇水。你感到你是客人,客人还没有到门口,就有红花绿叶笑脸迎迓了;你感到你是主人,住下就不想走了。
情趣在院子里晾晒的竹竿上:一片片小孩的尿布,好似美好岁月的小旗帜;几件熊猫形象的绒布玩具,挂在竹竿,不见有小孩在村里玩,好似奶奶思念长大了,到城里上学去了,只留下了一些乡土的玩偶;偶尔有架起的竹竿上,晾晒着红色的乳罩、紧身的短裤、雪白的袜子,让人感到青春的气息,意识到这村子里还有年轻人生活。
我这个正午时分寻寻觅觅的人,遇到最多的不是人。人大多在自家的凉席上午睡,小狗闻到了陌生人的气息,汪汪冲我叫,我挥挥手就跑走了。小狗大多是给人止心慌的玩伴,看家的大狗在柿林村也是很少的了。
村子里的墙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锉成方块的石头,颜色紫红,或者做基石,或者做照壁,和青砖的房子的墙面,构成一个一个的巷道,两边的房檐伸出来一点,交头接耳,可以避一点雨。
村子由这些巷道构成一个八卦阵,参差错落。最感动的是遇到一株红指甲花,长在房基上的石缝里,已经有我的小腿那么高,绽放着指甲盖大小的粉红色的花儿;石缝里的指甲花叶儿嫩嫩的,枝干亮盈盈的,花儿依然像童年的粉红,有点羞答答的样子。奇怪指甲花举着繁盛的花冠,在石缝里斜倚着,没有倒下去,走近了看,有一根细线挽在她的腰里,另一头锥在墙上面的院子里,拉着她。
在这株指甲花下站了许久,想起我的老姑姑,去世已经很多年的我的老姑姑,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我家的菜地里给我和妹妹们种下指甲花,等长得饱满了,榨汁,积着一点明矾,敷在指甲盖上,用核桃树叶子包上,等到第二天起来指甲就红了。这家人也有一个老姑姑吧? 或者一个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小姑娘?
柿林村有好多雕刻的艺术呢,最好的在檐头下的木雕上。村口电线杆上挂着阿土饭店幌子,入院,房檐下木雕的小狮子憨顽调皮,眼睛好奇地望着大门里出出进进的人儿;孔雀衔着牡丹花枝,飞临寻常人家,她的羽毛柔婉舒展;斗拱上的小象的鼻翼向嘴巴收拢,动势向下,显得富贵而有威慑的力量。这些深木雕,浑厚,淳朴,亲和,有一股和人的精神融为一体的祥和感。
窗棂上是福到眼前,一只纹路细密的蝙蝠,翅膀舒展,触角和尾翼被雕刻成如意纹样,只是一边的蝙蝠只剩一个平面,宽阔的翅膀已经被岁月的风霜侵蚀了;窗棂下的兰草梅花还依然新颖,清奇。这不是清代的建筑就是明代的吧? 只是门户紧闭着,只有很小的鸟儿在檐头下出入。
转到村尾,看到一棵老柿子树——如果说这村子像一头卧在山里的狮子,这棵柿子树就如一只狮子的大尾巴。古老的柿子树已经有120 多年的历史了,树身上钉着一块白底蓝字的荣誉牌 “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牌”。树身两人才可抱住吧? 没有人和我拉手拥抱这一棵柿子树。柿子树身上疙里疙瘩的凸起岁月,就像攥起而凝固,一直没有舒展开来的拳头。枝干的断茬,就像一孔黑色的喉咙,哽咽着许多历史的感慨。这是我见到的最老的两棵柿子树中的一棵,具有北方柿子树的风格——另一棵在我家乡甘肃泾河原上任家坪的大场里,据说有三百年的树龄。
只是这棵四明山里柿林村的柿子树的树冠依然葱绿,油油的、厚厚的、墨绿色的柿子树叶,反射着蓝天晴光。柿子树的叶子里蕴藏着漫长的岁月里,一个古村落殷红的浪漫。而秋天的时候,这满山的柿子都红了的时候,山坳里就丹红一片了,不,是这柿子树上红色的小灯笼点亮了天堂,然后柿子树的叶子都写成了一封封寄给冬天的红签——被鸟儿与风月带往四明山周边湖泊,携往象山、舟山的大海,甚至落于西子湖上吧……
记得童年的时候,到一位远方的姨奶奶家里去,十来岁吧,站在黑河山边异乡的山头上,看满山的柿子树,叶子都红枫一样落了,飞走了,满山只有褐色的柿子树上的柿子是红的,我孤独得大哭,后来一直从那孤独里走不出去。这次离开柿林村,却一直想再去坐在山道上,等风尘仆仆的贺知章或黄宗羲们走过,唠叨几句话,当然这是我读多了浙东唐诗之路的诗歌,一种顽固的幻觉罢了。我更多的是贪念那一篮篮红柿子,一口可以吞下的软柿子,被游客带出山去,都送给了红颜知己吧?
不不不,该这样认为,柿林村的红柿子,就是四明山的“红颜知己”——天地之间,太阳也就是一颗硕大的红柿子——乃世界人间的“红颜知己”。“红瓶瓶,绿盖盖,千人走过万人爱。”即使在柿子最红的时候,还有绿色竹林的映衬,松树、樟树的欣赏。柿林村的老奶奶,坐在月光下,要过路的货郎猜这古老的谜语:“红瓶瓶,绿盖盖……”
柿子树村的柿子,状若椭圆形的灯笼,叫“丹山吊红”,这名字真美。我觉得柿子本就是我老家陕甘一带的特产,却在这南方的腹地遇到,殊为惊异。说是村里种植柿子已经有四百来年的历史了,说不定它就是从北方移植来的呢!柿子喜温、喜湿、喜阴,这真是找对自己“隐居”的地方了,隐居不是为了埋没自己,柿子色泽鲜艳,肉质甜美,先苦涩而后蜜甜,想来早先村民们担子担到余姚城里去卖,要走那羊肠古道,多不容易啊。何况一定会走到甬城宁波月湖边,鼓楼沿……
现在公路盘山而上,进山是容易的。就到村口,就有村官迎接。秋天住下来,铺个凉席,等那柿子在风里摇软了,会落在你舌尖上的,你怕打疼嘴巴,就用手掬着吧。这美好不比春天带着恋人来摘樱桃差的!
和那举起孩子,让孩子直接尝那树枝上的杨梅儿比,到柿林村 “研学”多了一些醇厚的况味,又似乎是拜谒撰写 《梦溪笔谈》的沈括老先生来了。
老柿子树见证过那位贞节老人全部的人生心酸吧? 老柿子树旁,是一个茶叶加工厂,工厂里沿着墙边是一圈灶台,灶台里的铁锅被茶叶磨得光光的。一条黑狗独霸着,在放置家什的房间里,吼出一些寂寞的回声。这些大锅,等待着来年的春天,再炒出清香的 “四明仙茗”来。
我惊异这石头村里第一个来到的沈家的开村先生,他与北方的关系原来这么明确!也惊异他的家族与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的关系。祠堂里有记载:宋代沈括是柿林村沈家的第二十四世祖。这位村子的创始人姓沈字太隆,叫林十五,是第四十五世祖。《沈氏家谱》有文曰:
公行林十五,字太隆,隐居高逸事也,仙游自适,不喜繁华,有避尘绝俗之致焉,自亨一,太祖迁于本邑江口之下坝,一十有九,世族大事,繁不胜扰,攘无以稍安。闻四明山青水秀,有洞天福地之称,因而游览胜迹,寻访名区,观白水,登石窗。沿路而行,无有倦息。至如邻邑限制雪窦,仗锡,罔不到焉。总之,情之所钟,不辞足力,山回路转,忘其远近,踪迹至此,即所谓峙岭也。旁有撤药岩,上有神仙石,山号龙,溪名双鹿,若将军,若爵禄,若三台,若玉屏等,种种名胜不一而足也。岂非天造地设? 而人成事居于此者,为子孙长计忽? 遂口占一绝曰:“洞天福地甚奇哉,不染人间半点埃。相士择宜居此乐,岭头惟有白云来。”即同祖妣龚氏,子学成公筑室于兹而居焉,其所从来所由是矣。迄今十四世,为子孙者不敢忽其所自述,其巅末由载于谱首以志,不忘云尔。
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腊月上浣之吉
后裔立 通志 同熏沐谨识
四明山的文化有深深的隐士文化传承,那些文人墨士之隐居,却往往是隐而不居,或居而不隐,而沈先生确是真隐居者也。慢慢算来,他是元朝末年来到这里的,距今有650 多年了。
柿林村东北角的沈氏家祠叫 “忠清堂”,集聚全族之力,从道光四年 (1824)开始筹建,历经艰难,险些未建成而颓败,直到道光十五年 (1835)才最后建成。背依身后松柏苍翠竹林修然的 “官山”,前有一湾清莹泉水,睡莲绽放,红鱼游曳。确如林十五公沈太隆所愿,有 “不喜繁华,有避尘绝世之致”。
迎门照壁是雕刻在木板上的 “家训”,家训虽然也是古诗,却语言通俗,妇孺能懂,细细读来,觉得有温馨教诲里含着严肃要求。我匆忙间抄下一段来:
义训
凡属一本亲,皆有关怀意。
钱物相往来,见利勿忘义。
疾病需扶持,老幼须携提。
最怜四无告,尤宜善调剂。
莫说功德小,竹桥也渡蚁。
祠堂里悬挂着一些牌匾,有 “簪缨世家”,有 “玉洁冰清”,有 “科第传家”“文肃世家”,我还是独爱这 “玉洁冰清”的横额,配有两副楹联:
丹山存胜迹八百里四明风姿独秀,
赤水溯梦溪千余年风雨德泽流长。
历姬周嬴秦刘汉李唐赵宋诸朝授武职谥文肃屡建安邦千秋业,
经西岐汴梁钱塘会稽余姚各地觅佳境择仁里终居丹山万世传。
这千秋业、万世传的楹联乃一九九四年镌刻撰写,我感慨地想,文化就是一代又一代,这一年增加一点,再一年,再增加一点,文明就厚重了,文化就有活力了。我自己家居黄帝的故乡,依傍着黄帝陵所在的子午岭,以秦陇子民为荣,而这大岚沈家也是黄帝后裔姬姓后裔;其先祖就是 《梦溪笔谈》的作者、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这让我再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 “源远流长”,祖国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于斯可见。而那旁边刻勒的捐款资助维修者名单,一行行,又一行行,就是祠堂前站立祭拜的沈家后裔,就是这些叫做 “老百姓”的民众,就是这民众养育的艺人建造了这藏之名山的艺术祠堂。
沈家祠堂梁头柱上斗拱处有木雕牡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牡丹,古劲沧桑,尽情怒放,我不知道怎么描写,才能表现出那牡丹的 “国色天香”? 匠人采用的木料很厚,没有量,目力看,足有一尺五左右吧,牡丹不是在侧面平刻,是从正面直接镂空挡头,深雕进去。
从下往上有四朵花,第一朵含苞待放,第二朵蓓蕾初绽,第三朵灿烂怒放,第四朵俯视空域,敞开全部的胸怀。从新生到繁盛,你能在这样的木雕里听出屈原吟唱楚辞的灵魂决绝,艾青抒写长诗 《光的赞歌》的荡气回肠!我站在那雕花下直想,这就是中国民间无名大师的命运交响曲!
那雕刻的刀子从木头的表层开始镂刻,留下的花瓣的线条龙蛇般虬曲苍劲,柔肠百结,是无所畏惧的浪漫的展示,是不屈服于命运的心灵的呐喊? 那木雕的花瓣就犹如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大卫头上蜷曲的青春的卷发,只是我们的木雕艺人的刀子犹如一位伟大作家的笔,探入一个民族灵魂里最美的疆域一样,我在这一刹那,感到他的刀子引领着他的膂力做到了。
在那七八个花瓣中心的花蕊,你能感受到一棵大原木,作为曾经的一棵大树,它最后一次的绽放多么辉煌!对,就是辉煌,就是壮丽这样的词,才能道出木头和木匠之间的壮烈激情。那大木头一生总是举着枝叶春花秋实,而自己的年轮本身的开花绽放却是在木匠的刀子的歌唱里。
这就是从大树和木匠的心底里开出的艺术,可是那木雕两面上立体的战将马上的决斗形象却被另外一种刀子撬走了,都撬走了,好像独留下花朵的愤怒,牡丹的死不瞑目,在一个遗落的古村里美丽着、美好着!
是不是二百七十峰的四明山像这样传统建筑保存完整的村落只独留这一处了? 看来,民宿之幡旗招摇、逐渐热闹的柿林村,它该不会再遭遇什么劫难了吧?
看忽然觉得异常空落,在那村边的小平地上,那些挂在屋檐下的很不协调的红灯笼,召唤着城里人,可城里人中该不会有瞄上了那房头上的绝美木雕的人吧? 城里人钱多,钱多的城里人,总有识货的,想用钱币买走这个世界上的美好,将艺术据为己有。
越是不懂得创造的人群越是贪婪。看资料说,第九洞天的牌坊原来立于梁弄西侧狮子山下,建于南宋理宗时期,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站立坊下,梁弄美景尽收眼下。惜1958 年被毁。与此同时建成的洞门1987 年被拆除。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就是牌坊的原在地,面向柿林村口上面向对面的 “丹山”所建的亭台廊梯是不是要复原那古人的艺术,只是惊悚1958和1987 这两个拆除的时间。每次浩劫结束之后,中国人的文化觉醒,并不是完全、真正恢复!
我们今天,对文化的保护可能还没有真正落实,我们新的创造可能并没有真心开始的时候,文化依然岌岌可危。在某一个伟大的时间点上,柿林村的生活,似乎戛然停止,每一个家庭都将财富换算成了城市的一套楼房——这种某个时代的生活的突然转变,导致一种文化遗忘,于是,那么,这藏在山里的柿林村,就是非常幸运的国之遗珍了。
我有些惆怅,村里的年轻人很少很少的,村子的入口已经被旅游局的售票站把守了,这是守护。可是我到的那天,来观光的客人颇少,听着老人们祈祷的木鱼在空落的山壑里空悠悠的回音,我不知道为啥就有些苦涩失落了,我使你感到那个沈家祠堂里太寥落了吧?
我转出村口的时候才看见一口浅浅的井。柿子树是柿林村的迎客树;山井映月,是松鼠和玉兔的啜饮池,柿林村的迎客井边,石头光滑,脚窝若勺。浅井照树,高树映泉,这井是村落的命门,是一个人,千里万里跋涉,行走到这里,终于落脚的首要之因。也许,一定就是,在这半山腰上的一片洼地上,他发现了这汪泉水,才歇息下来,搭起了茅棚,住下来的吧?
我站在井边,井水照着我。我在文化里这么多年盲目的乱跑,显得苍老,忽然有点顾影自怜,就连下去拾一枚井里的小石子做个纪念的动作也没有。伫立着,伫立着,那指甲花染得殷红的岩石,也许就是柿子般的血——柿林村的先人垒石造田,千顷万亩,纤夫般劳累渗透到土地上的血痕? 我的沉思有点沉重了。
关于那丹山何以丹? 是这里的古人记载在书册上的传说? 是羊血流淌岩石,沁染而成?是山中的枫树、樟树秋天叶子变红了,映照得石头都脸色红润? 抑或是这柿林村的柿子照得天地敞亮? 或者是那山里人种植了几千年的小小红樱桃? 或者是哪个村里都会有的杨梅? 丰收的硕果,红火的生活,总比道家的想象附会要来得快乐些的。
我想在这村子里住下来,住几天、住几月、住几年,才能领略更多的美好吧? 前贤黄宗羲就是余姚本地人,他于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 年,踏勘四明山,六十七天,返家后编撰 《四明山志》,历三十余年,志中称山中有岩称杀羊岩,赤壁数里,与山下溪水相映,传说那是仙人刲羊血渍染的结果。
转完了四明山的房前屋后,还没有遇到那些去喝茶的朋友,我就自己先返回石板古道。道旁的竹篱笆上绵绵瓜瓞,黄花午眠,叶子也是收敛水分的样子,可稍子上的几朵嫩叶和新花,怡然舒展,婴儿般微笑着,向着高大的银杏树跟前长着。下去的时候疏忽了这些,和银杏树爷爷没有打个招呼,他老人家站在这里多少年了?
忽然悟到,村前的银杏树就是老爷爷,村后的柿子树就是老奶奶,村里清盈盈的泉水井,就是美丽的孙女呀。遗憾没有掬起一捧井水喝,洗洗脸庞和眼睛。觉得那穿着青衣褂子的娘,睁着泉水的眼睛,手抚着银杏树,在等亲人回来,也嘱咐我再来。
李白四到浙江,四入四明,他的印象里黎明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在李太白的怀念里,傍晚 “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照谁家”,霞光里的女儿,月光里的娘啊,丹山下赤水上的柿林村,总有一颗柿子一样红的太阳,荔枝一样白的月亮在等我们回去。
我们离开的时候,山边的那只白山羊不见了,被仙人丹丘子领走了吧? 我忘了告诉你,在一家的房门上,我看见钉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画着虎头八卦,这是镇宅守村的 “守护牌”,愿这虎王永远护佑着柿林村的山水生灵。